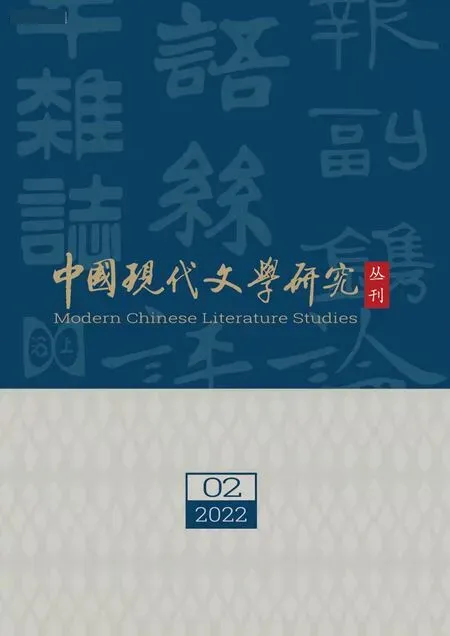用史实还原一个真实的郭沫若
——评李斌《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
商金林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同时也是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一生雄姿豪放,业绩辉煌。周恩来将他誉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①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茅盾将他1920至1940年代的奋进历程称作“中国前进的知识分子所度过的‘向真理’的‘天路历程’”。②茅盾:《为祖国珍重!——祝郭若沫先生五十生辰》,(香港)《华商报》1941年11月18日。王若飞称赞他是“国家的至宝”。③王若飞:《中国人民需要郭先生——在重庆各党派领袖和文化界人士欢宴文化战士郭沫若的盛会上的发言》,《新华日报》1945年4月9日。郭沫若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怀着要把全部的力量、精神和生命“无条件地拿出来”,为完成革命事业、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热忱,肩负起重大的使命。像郭沫若这样一位伟大诗人、史家权威、革命前驱,我们应该加以爱戴,对他的评价应该实事求是。只是1980年代以来,有人为了颠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重构一个经典谱系,对郭沫若本人及其作品进行严厉的批判。学术研究应该与时俱进,原有的“排序”也不是“铁律”,但“重构”不是“主观构建”,郭沫若在某个特定时期的缺点和作品的某些缺失也不能一律视为本性缺陷予以放大,结论不能依从一家之言任性推演。正是这样的“放大”和“推演”,把郭沫若脸谱化和漫画化了,“红的发烫”“要作时代的留声机”“献媚”“风派人物”“摧眉折腰”“人性‘堕入暗夜’”之类的酷评连篇累牍,曾经被誉为“一座高峰”“万仞风光”①田间:《高峰——悼念伟大的劳动者诗人郭老不幸与世长辞》,《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94页。的郭沫若,成了被有些人任意拿捏的“丑角”。
可喜的是青年学者李斌的新著《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为我们认识郭沫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郭沫若开拓了视野,让我们看到郭沫若研究还有很多新的领域、新的天地。是书2021年5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采用了郭沫若1949年以后大量未曾公布的书信、手稿和档案等文献史料,结合时代背景和郭沫若特定的身份,从郭沫若对“《历史人物》《地下的笑声》《洪波曲》以及古文字类著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蔡文姬》的创作以及学术著作《管子集校》的编撰过程;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所投入的精力和取得的业绩;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如何在文坛发言;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享誉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郭沫若如何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和知识分子交往等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和解读,让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郭沫若鲜为人知的心灵独白和特有的精神魅力,读来津津有味。
一 “书生意气”
《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第一章《旧著再版费思量》第二节“张治中与《洪波曲》的修改”,从郭沫若纪念馆馆藏的郭沫若致张治中的两封信札说起,谈起郭沫若在《抗战回忆录》中写到的发生在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抗战回忆录》1948年8月25日至12月4日在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连载。后经修改以《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为题连载于《人民文学》1958年7月至12月号,1959年收入《沫若文集》第9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38年10月,按照周恩来的部署,郭沫若带领第三厅从武汉撤退途中经过长沙。长沙当时在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管辖之下,张答应给第三厅六辆卡车,但未能兑现。突然遭遇“长沙大火”,郭沫若只好带人狼狈出逃。出城时遇上周恩来和叶剑英,大家对“放火”都十分愤慨。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提出“焦土抗战”政策,即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指望以空间换时间。在日军占领岳阳后,1938年11月12日蒋介石密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命令将长沙全城焚毁。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派出士兵,在全城各处点火,长沙全城烧毁三分之二,100余万户民舍被焚毁,数以万计的无辜民众葬身火海。而大火之后,日军并未立即进攻长沙,舆论哗然。国民党政府无端烧毁长沙城的行为,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怒。郭沫若在《抗战回忆录》第十五章《长沙善后》第六节中对张治中进行了严厉谴责,称“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张治中,在《人民文学》看到《抗战回忆录》后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申辩,说当时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恳请郭沫若“高抬贵手、笔下留情”。他在信中写道:
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同事十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一九四八年,而在一九五八年五月您“把旧稿整理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十年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进而援引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国民党性质和成分的分析,说自己是个“进步的民主分子”,可在郭沫若的笔下,却成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贪图功名’的‘党老爷’‘官老爷’了,这怎能叫我不喊冤叫屈呢?”作为“亲历者”的郭沫若当然不会冤枉“进步的民主人士”张治中,但也不愿意违背史实,随意删改,只是表示《洪波曲》出单行本时也把张治中的长信“作为附录”。张治中表示同意,并对郭沫若的“雅量”致以“崇高的敬意”。岂料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郭沫若修改,致使《洪波曲》单行本中非但没有把张治中的长信“作为附录”,原文也改为“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把张治中从“长沙大火”中解脱出来。周恩来也是“长沙大火”的“亲历者”,虽说当年也十分愤慨,而今作为共和国的总理,站到团结“进步的民主人士”的高度处理历史问题,用心良苦。周恩来是郭沫若的直接领导,郭沫若在周恩来面前始终是“协力”“同心”,这次当然也不能违拗。
周恩来和张治中相识于黄埔军校,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教育长。解放前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一个是共产党的中坚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为了各自政党的利益也时有争执,但也在长期的交往中却结下了真诚而深厚的友谊。解放战争后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进行和谈,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谈判破裂,国民党的代表们面临着去与留的选择,是周恩来的劝导和关爱,使张治中一家决定留在北平,因而被誉为“和平将军”。据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最恨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的马歇尔,一个便是张治中。张治中改弦更张,成为中共的追随者,让蒋介石恨之入骨。出自对张治中的关心和保护,周恩来要求郭沫若修改《洪波曲》是很自然的事;而郭沫若与张治中“同事十年之久了”,还在揭露“长沙大火”的“真相”,对“长沙大火”这样极为敏感问题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年前,真可谓“书生意气”。
修改《洪波曲》是“遵命”,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有时也是“奉命”而为。《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第二章第二部分“《蔡文姬》应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从郭沫若留存下来的书信及相关史料中说明历史剧《蔡文姬》的创作是遵从“指示”。郭沫若1959年2月16日夜给周恩来的信中说:
一月廿六日陪墨西哥客人到广州后,因孩子们在春假中到了广州,我便留下把剧本《蔡文姬》写出了。二月三日动笔,九日晚脱稿。兹寄上清样本五册,请饬交陈总和周扬同志各一册。如请暇审阅,请提示意见,不日回京后再修改。这个剧本是通过蔡文姬替曹操翻案。这个主题是根据主席和您的提示。去年十一月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鸿宾楼吃晚饭,陈总亦在座。我坐在您的旁边,您曾向我说,不妨写一个剧本替曹操翻案。案是翻了,但翻得怎样,有待审定。
郭沫若提到的“主席”的提示,指的应该是在1957年11月,毛泽东与郭沫若、胡乔木等人共进晚餐时的谈话。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毛泽东的“提示”比较委婉,周恩来的“提示”可就极为明确了。1958年11月,周恩来当着陈毅的面希望郭沫若“写一个剧本替曹操翻案”,郭沫若就不得不高度重视了。剧本《蔡文姬》写出后,经反复修改,演出效果相当好。1959年6月2日《文汇报》发表的一篇剧评中写道:
首先从剧本分析,作者发挥了高度的想象力,信手拈来,指挥如意,使用历史资料,随心所欲,左右源源,但却如“杜少陵诗,无一字无来历”。同时,作者一面坚定了为曹操翻案的历史观点,一面又深切切合当前民族政策,予人以一定政治感染。在这些方面,也完全体现了厚古薄今的时代精神。总观全剧,就是一首感情非常充沛,用意温柔敦厚,风格却又瑰丽美婉,体裁则是洋洋洒洒的长诗。至于舞台画面色调的和谐古艳,那又是一幅唐、宋名家画的著色《文姬归汉图》。它凌驾了过去的《虎符》,向前跃进不止一大步。而好处更在从神韵上从形象上无论巨细都在继承着古典戏曲的民族传统。并有所发扬。(景孤血:《写在看话剧〈蔡文姬〉后》)
紧接着,郭沫若开始酝酿历史剧《武则天》。与《蔡文姬》的“遵命”不同,而《武则天》的创作则来自考察奉先寺石窟时触发的灵感。1959年7月1日,郭沫若到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考察,他在《访奉先寺石窟》中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并加注云:“奉先寺木建部分已毁,唯雕像尚完整。岩上刻有《大卢舍那象龛记》,乃开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所刻。其文有云‘以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至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案咸亨三年,武后年四十九岁,助脂粉钱建雕像,较之清慈禧太后以海军费建颐和园者,有上下床之别。”这之后,郭沫若与吴晗、尚钺、翦伯赞、吕振羽、田汉、李伯钊、周扬、胡乔木等知名历史学家和戏剧家、理论家反复探讨,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力求写出一部“好戏”来。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同年5月《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就《蔡文姬》和《武则天》相比较而言,郭沫若更看重《武则天》。《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第三章《文联主席如何在文坛发言》第二节“筹备第三次文代会”,写到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周扬所作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中称赞《蔡文姬》,而郭沫若则希望周扬能更换为《武则天》。周扬之所以否定郭沫若的提议,大概是出自他的政治敏感。《蔡文姬》是毛主席授意的,要给曹操翻案的还有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呢;而创作《武则天》只是郭沫若一时的灵感,是“我要写”,孰重孰轻,周扬自然掂量得出来。相比较而言,郭沫若还是“书生气”。
二 真诚而炽热的情怀
巴金在《永远向他学习——悼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说:在郭沫若身上“人们看到了战士、诗人和雄辩家、智慧、才能、气魄、热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同郭沫若接触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①新华月报资料室编:《悼念郭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页。通览《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我们更能感悟到巴金所说的“印象”,是知人之论。
《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第二章《新著撰写密相商》第一节,写郭沫若“校补”许维遹与闻一多合著的《管子校释》,寻找“参考之书籍”的经过和“校补”的过程,着实令人感动。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50年许维遹在北京病逝,由许维遹纂集,闻一多校阅的《管子》中途辍止。1953年秋月,闻一多夫人将《管子》书稿交给中国科学院,希望能够组织专人整理出版。郭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接受了这个嘱托,亲自动手“校补”。郭沫若这样做,一是出自对战友闻一多敬仰和怀念之情,要完成战友未竟的事业;二是出自对祖国文化瑰宝的热爱。《管子》一书汇集秦汉之际诸子百家学说,是战国秦汉学术的宝藏。虽说整理工作很艰巨,但意义重大。郭沫若在《管子集校·叙录》中写道:
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及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宂赘之举。①《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第69、79页。
这项“校补”原定为“集体项目”,郭沫若召集冯友兰、余冠英等学者商议,大家答应分头去做的。可到截稿时间,有些人还没有动笔,交来的稿件质量也参差不齐,郭沫若这才决定单独完成。他从寻找资料入手,花了近二年的时间,“收集到17种宋明版的《管子》”,“搜集到自朱熹以来有关《管子》校注、研究著作近50种”②《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第69、79页。,从郭沫若的相关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寻找资料”真的是不知疲倦,竭泽而渔。一些珍稀版本,如陈奂校《管子》抄本、丁士涵《管子案》残稿、安正书堂《管子》等,郭沫若看后还都写了“题跋”或“题记”,说明此书的学术价值,并对收藏家表示感谢。1955年8月4日,杨树达将他从王先谦后人手上购得的《管子集校》稿本寄给郭沫若,并打听大著“何时可令快读”。郭沫若在9月6日的回信中写道:
遇夫先生:
八月三日赴北戴河,昨日始返京,得读八月四日手札,并得王葵园《管子集解》,甚为快幸。《管子集校》一书系许维遹、闻一多遗业,余为之校补,较原稿可增多一倍,现正校对中,今年或可望出版。王书来,恐又将有所增益矣。
敬礼!
郭沫若
《管子集校》原来计划于1955年出版,后来延后至1956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延后的原因无非是又“有所增益”。“较原稿可增多一倍”,这个“一倍”大多是很难寻觅的珍稀版本。别人都不愿意做的“冗赘之举”,郭沫若却乐此不疲,气魄之宏大、学识之精湛固然可敬,而更可敬的恐怕还是他为人和治学的精神。
郭沫若这种真诚而炽热的情怀在国际交往中表现得也很充分。在国际交往中,郭沫若一方面严格遵守组织原则,另一方面热情待客,不厌其烦,尽可能做到有求必应,皆大欢喜,这在《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第五章《有朋自远方
来》中有一系列很感人的事迹。如1956年邀请居里夫妇的外孙女、约里奥-居里的女儿、法国核物理学家海伦娜·郎之万和她的丈夫米歇尔·郎之万来北京,参加“世界文化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皮埃尔·居里、玛丽·居里纪念会”;1968年为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教授寻找治疗代谢性骨病的中药;1972年邀请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访华等,这一系列重要的外事工作都做得尽善尽美。1964年8月下旬,坂田昌一教授带领由61名日本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日本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由我国承办的国际科学讨论会。8月27日晚,郭沫若在四川饭店宴请坂田一行,用餐后郭沫若为61名成员每人写了一幅字,日本客人喜不自禁。1970年10月16日,坂田昌一教授谢世。1973年4月上旬,坂田昌一的夫人坂田信子和有山兼孝夫妇来我国访问,了解我国的幼儿教育情况,受到郭沫若的盛情接待和宴请。坂田信子请求郭沫若为她写一幅李贺的《莫种树》:“园中莫种树,种树四时愁。独睡南床月,今秋似去秋。”坂田信子说她常常吟诵这首诗表达对丈夫坂田昌一的哀思。郭沫若没有写《莫种树》,而是作了一首《宜种树》:“园中宜种树,最好是梧桐。叶落日常在,冬来不觉冬。”并写了一个小跋:“坂田信子夫人嘱书李贺《莫种树》,今反其意成《宜种树》一首以应。”过了两天,郭沫若又以墨宝相赠,这回写的是“一生充实有光辉,满门桃李正繁枝。孟光不愧梁鸿志,天下英才教育之。”附跋云“坂田信子女史乃故友坂田昌一教授之夫人,决献身于幼儿教育事业,嘱题,赋赠。”并为“孟光不愧梁鸿志”一句加注:“梁鸿,纪元一世纪时隐士。所作《五噫歌》,富有阶级意识。东汉章帝想逮捕他,他隐藏起来了。其妻孟光,与鸿志同道合,以耕织为业。”并录《五噫歌》:“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人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郭沬若还特地写了一首诗送给有山兼孝:“樱花时节海棠开,好友随春一道来。园内牡丹犹有待,含情留客无忙回。”有跋云:“有山兼孝先生下访即事,题求哂正,并以为纪念,惜笔墨劣耳。”李斌在书中没有对郭沫若的接待和题赠作过多的阐释,只是援引了坂田信子的一席话。坂田信子说她离开北京去南京时,“于立群在北京机场又安慰我,又说给我郭沫若先生对诗的解释,我激动的到南京下飞机时还未哭完。”离开深圳去香港,坂田信子夫人在深圳桥头依依不舍,“又一次激动的流了泪”(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编:《接待日本坂田信子和有山兼孝夫妇简报》第9期,1973年5月7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以真心换真心”,读来令人感动。
三 求贤如渴 唯才是举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他对于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象甲骨、金文、石刻、文书以及戏剧、诗词,书法等,几乎无不精通,在各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社会科学大师。
诚可谓“大海不弃涓流才见壮阔”。生活中的郭沫若谦卑好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第二章第三节“《武则天》的创作与修改过程”写到,“酝酿期间”,郭沫若曾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进而关注文艺界有关越剧《则天皇帝》的讨论、广泛查阅有关武则天的材料,初稿写出后送请田汉、陈白尘等同好指教,并由周恩来组织了以周扬为首的五人小组修改。与此同时,郭沫若又派专人到四川广元考察武则天庙,调查武则天的相关资料,力求对武则天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武则天》五幕历史剧定稿后,文艺界于1960年10月召开《武则天》座谈会,郭沫若根据座谈会意见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修改。1961年5月14日,《光明日报·史学》发表陈振的《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与郭沫若剧本中有关武则天出生的相关观点展开讨论。1962年2月,郭沫若将再次修改后的剧本稿送请邵荃麟、田汉、光未然、吴晗、严文井、翦伯赞、陈白尘、王戎笙、曹禺、李伯钊、焦菊隐、阳翰笙、阿英、夏衍等名家审阅,并再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1962年6月,郭沫若对剧本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由五幕改为了四幕。同年7月7日,郭沫若观看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后,决定再作修改。7月13日,郭沫若因听觉不好,拜托王戎笙代替他参加座谈会,听取文艺界同人对《武则天》的意见。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曹禺、田汉、焦菊隐、景孤血、高文澜、张艾丁、李超、王子野、张季纯、戴不凡、朱琳、曲素英、赵韫如等数十人。1962年9月,《武则天》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据我自己的经验,文章的多改、多琢磨,恐怕还是最好的办法。”“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文章的多改、多琢磨”的前提,恐怕得要像郭沫若那样的谦卑好学,求贤如渴,心胸开阔,气象宏大。
《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第四章《延揽古代史研究人才》第四节“筹备中国科学院学部”,这一节写到1954年9月上旬,经过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历史学家杜国庠的联系,陈寅恪同意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党组成员、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代郭沫若拟了一封感谢信,信是这样写的:
寅恪先生大鉴:
学友杜守素先生来京,得悉身体健康,并已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
学部是科学院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的机构,事务不多,先生仍可全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中有何困难,科学院定当设法予以解决。目前正在积极进行,详情将请守素兄返粤时面达。
尊著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见到。对《历史研究》的编辑工作如有指导意见,望便中示知。即颂。
著祺!
郭
郭沫若看后作了修改,现抄录于下:
寅恪先生大鉴:
学友杜守素先生来京,获悉先生尊体健康,并已蒙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
学部乃科学院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之机构,事务不多,不致影响工作。目前正在积极筹备,详情将由守素兄返粤时面达。
尊著二稿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达览。《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尊处于学术研究工作中,有何需要,亦望随时赐示,本院定当设法置备。专此,即颂。
著祺!
郭
郭沫若修改之后,于9月30日返还刘大年,并附便笺说:“文稿略有润色,已书就,望交杜守素同志转。”对陈寅恪,郭沫若可说是十分崇敬,因为他爱重人才。郭沫若认为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应该尽其所能,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因而对于有才能的人,他总是尽自己之所能,奔走呼吁。山西大学有位教师名叫宋谋玚,在1957年和“文革”初期前后二次戴上右派帽子,被开除公职,1971年在湖南老家接受改造时给郭沫若写信,说他在研究《资治通鉴》,也研究《红楼梦》和鲁迅旧体诗。郭沫若觉得他校点《资鉴校补》颇认真,解释鲁迅的旧体诗也有独到之处,居然在1971年夏天致信吴德和吴庆彤,郑重推荐,“希望能够调用宋谋玚从事研究工作”。吴德当时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庆彤担任国务院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协助总理、副总理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郭沫若如此重才,可见他有很单纯的一面,说是“真正的学人”也不过分。1949年3月27日郭沫若率领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代表团团员丁玲4月13日在给陈明的信中写道:“沿途民主人士轶闻亦不缺乏,但都不如文艺组之调皮,田(汉)洪(深)两兄表现都不甚好,尤其是洪,郭老常常生气、着急。郭的确是一可爱之人!”①王增如:《丁玲赞美郭沬若是可爱之人》,《世纪》2021年第3期。研读汇集在《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的大量信札,我们确实看到了郭沫若那些鲜为人知的“可爱”的一面。
以上是我在阅读《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时的一些感想和体会。李斌的这本新作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出发,客观翔实,在材料的组织和分析评价上恰到好处,且富有创见,真正将晚年郭沫若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作为年轻学者,这种勤奋和扎扎实实的治学态度值得称颂。郭沫若研究近年来有所起色,郭沫若在学界的形象有所改观,这和以李斌为代表的年轻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期待李斌继续奋进,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