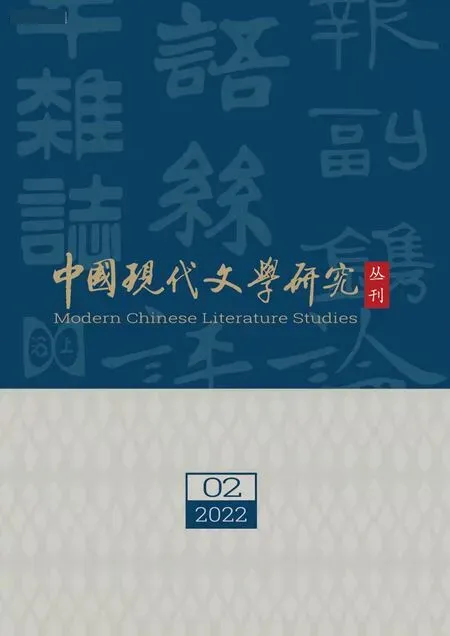诗人之死:朱湘自沉的舆论背后※
邱雪松
内容提要:1933年,诗人朱湘自沉引发热议。上海知识分子以《申报·自由谈》为平台,责问事件背后隐伏的社会病灶。与之不同,在天津《益世报》集结的作家认定自杀是性格使然。北平的文艺人士则以同人刊物进行文学的闭环讨论。1934年,赵景深在其主编的《青年界》组织纪念号,通过怀人文字塑造诗人形象。因刊物的性质,“诗人之死”演变为“青年之死”,全国各地学生自办刊物中随之出现大量共情习作。同时,官方的《中央日报》《人民周报》等参与其中,讨论更趋分裂。朱湘自杀事件的舆论风潮及其后续,寓意着后五四时期出版市场重心的转移,表征了左翼力量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预示着代际更替的发端,社会剧变即将到来。
1933年12月5日,诗人朱湘投江自尽,结束了29岁的生命。作为突发性事件,它迅速发酵了社会舆论,各种力量参与其中,一直持续到1937年才逐渐消歇。本文举其要者予以细致解读,阐释报刊文字的“实”与“虚”,情景化讨论不同媒体对诗人之死的建构,追踪事件背后寓意的出版市场重心偏移、文化领导权争夺、青年代际更替等诸多社会结构的变动症候,以提供观察1930年代缠绕繁复历史的窗口。
一
1933年12月4日,朱湘自上海赴南京谋事,6日,朱湘妻子刘霓君收到其所乘“吉和轮”账房来信,她第一时间联系了北新书局编辑赵景深。赵景深与朱湘相识于1927年,他以开明书店编辑部主任的身份接洽出版后者的诗集《草莽集》。文学趣味的相契使两人成为知交。据后者所叙信函内容:
本月四日有一客,买三等船票,从上海到南京。讵于次日(五日)晨六时投江。急放救生船捞救,已无踪影。遗有皮箱一,夹袍一件。夹袍内藏有一信,方知死者名朱子沅,内有贵处地名,故持函来报。希于十三日持信往敝轮可也。①赵景深:《朱湘》,《现代》第4卷第3期,1934年1月1日。
朱湘离职安徽大学时,赵景深曾代为处理欠薪问题,不久他将朱湘自沉事告知安大学生,消息随即在校园传布。15日,《安徽大学周刊》刊载了一则题为《前外语系主任朱湘先生之死谜亟待事实反证》的报道,质疑朱湘自杀系谣言,“事既发生旬余,而京沪各报亦未见只字登载,是此项消息,殊不令人无疑……姑志之,以待事实之反证。”②《前外语系主任朱湘先生之死谜亟待事实反证》,《安徽大学周刊》第139期,1933年12月15日。朱湘执教期间曾就课程设置、教师聘用等与安大校方屡生龃龉,乃至最终因所授课程“英文文学史”被改名“英文学史”愤而辞职③赵景深《朱湘》叙及诗人离职原因“校方任意替他改了一个字。大约是‘英文文学系’替他改了‘英文学系’吧?因此他就怫然而去。”此说法被研究界采信为朱湘离开安徽大学的原因。但《前外语系主任朱湘先生之死谜亟待事实反证》中仍称“外国语文学系”,系名并未变动。又据向锦江《我的意见》(《中央日报》1934年1月12日)中有“他可以因安大教务处将他所讲授的‘英文文学史’简称为‘英文学史’而非常动怒”语,可证赵景深记忆有误,朱湘离职原因实为所授课程被改动之故。,校方此举颇有摆脱舆论被动的用意。不过正如《安徽大学周刊》所言,的确没有“新闻”报道朱湘自沉,诗人之死是通过“杂文”这一文体获得确证的。
17日,何家槐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朱湘之死》是第一篇见诸全国性报刊的文章,它奠定了上海报纸解读此事的政治化基调。何家槐认为朱湘作为“在社会上总算是有相当地位的”留学生、教授、诗人,选择自杀,“生活穷困实在是这惨剧的最大原因”。他强调诗人自杀“这件事报纸上面好像没有什么记载,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的意义并不限于朱湘一个人”,他相信问题出在社会,“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不但不给他舒服的生活,而且简直不给他生活”。同时,诗人没有认清问题本质,“他不能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既不承认能够优容他,把他像花草一样培养起来的某种环境已经崩溃,更不相信那个光明灿烂的时期真会实现,所以他只看到一片深沉的黑暗”。文章最后感叹“朱湘已死了,跟他选上这条死路的,恐怕在这大批彷徨歧路的智识群中,还有不少的候补者罢。”①何家槐:《朱湘之死》,《申报·自由谈》1933年12月17日。何家槐作为进步文艺青年,1932年加入左联,在左联下属创作批评委员会、小说研究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三个组织工作,并一度担任大众文艺委员会主任②姚辛编著:《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具备阶级视野的他未将朱湘之死视作孤立个案,而是由个人穷困溯源到社会结构不公,并暗示读者就此展开反思,显示出对非常文学事件思考的理论自觉度。
两日后,《自由谈》又刊登了余文伟的《悼朱湘先生》。作为昔日中学同事及引荐朱湘到安徽大学就职之人,他与朱湘关系匪浅,虽然他承认“他的性情,不免孤僻,这是他的一般朋友所共知”,但余文伟与何家槐论点完全一致,“他的死,可说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并进一步解释“生活的不安,社会对他的漠视,都是他自杀的近因”。③余文伟:《悼朱湘先生》,《申报·自由谈》1933年12月19日。值得一提的是,两日后有读者致信《自由谈》,表示余文已在他报发表,黎烈文为此特意在“编辑室”回复:“以后自当注意不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同时盼惠稿诸君切勿一稿两投,读者幸甚!编者幸甚!”④黎烈文:《编辑室》,《申报·自由谈》1933年12月21日。由此侧证朱湘自杀事件已是沪报一时话题。
曹聚仁于25日在《自由谈》发表《我们的遭遇》,重申何家槐残酷社会逼得知识分子生存难以为继的观点,并认为“朱湘先生的遭遇,便是我们的遭遇”。⑤曹聚仁:《我们的遭遇》,《申报·自由谈》1933年12月25日。四日后《申报·本埠增刊》发表笔名“立斋”的《现代的文人》,不仅延续何家槐、余文伟、曹聚仁的观点,更因发表于地域增刊的缘故,激进地呼吁与旧社会“对敌”的反抗之路:
处在这样一个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年头和国度,文人的出路原来就有类于“老鼠挖牛角,越挖越紧”。瞻前顾后,认清现实,只有三条出路:其一,是站在旧社会势力的对敌方面,绞自己的脑汁去为被压迫者,挣扎反抗的遭际呼号,其二,贴在旧社会势力的尾巴上硬爬,……其三,认清自己的潦倒不过为“理之当然”,既不标榜“安贫”也□认真“憎命”暂时浑浑僵僵的过日子。
不幸诗人朱湘,竟走了第三条路而又不能泯灭自己的智慧,结果就成为“无路”,他终于战胜不过现实,竟至自杀了。
致无限的悼意于朱湘先生,同时希望潦倒作家之群若竟读吾文者,亦将有所感于中而检查一番自己所走的路!①立斋:《现代的文人》,《申报·本埠增刊》1933年12月29日。
对于黎烈文主编《自由谈》时的特征,有论者总结为“左翼主题、编者主导”②参见甄皓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申报·自由谈〉(1933—1935)》,《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朱湘自沉后,沪上知识分子以《自由谈》为平台,不仅率先播布,还充分利用“杂文”的文体特质,将诗人之死与社会结构做了关联讨论,引导读者以相对简明的方式去把握自沉事件背后的社会动因,其中左翼人士发表的文章,更提供了隐含反抗压迫的阶级论的具有强大解释力的话语,上海知识分子及媒体的共识可见一斑。然而,平津两地从文体到取意与之均有不同。
12月29日,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登载了《悼朱湘》诗一首,作者“老马”自陈“近读《申报·自由谈》何家槐《朱湘之死》一文,不禁有感,因作诗以悼之”。此诗共8节,每节4行。首节“朱湘是大教授又兼诗人,/何家槐是赵老爷的徒弟,/赵老爷生平最佩服朱湘,/他一死,大家都叹口气!”诗中的赵老爷指赵景深,何家槐是他在中国公学任教时的学生,诗句首节皮里阳秋之意已尽显。第二节以朱湘诗行工整,揶揄其为“香干诗”,“一家人哭哭啼啼,都说:/他这一死真是死得冤枉!/他的地位已经不算很低,/香干诗要卖四块钱一行。”第四节再以“香干店”比喻朱湘诗歌创作:“世界虽是这样的不景气,/他却已积下了许多诗,/简直可以开一家香干店,/如果不死,那就还不止。”结尾“我们虽然不曾会过面,/但是算起来总是同胞,/我今朝有机会来追悼你,/啊!我多么荣耀,荣耀!”③老马:《悼朱湘》,《益世报·语林》1933年12月29日。则是对《自由谈》系列文章悲痛语调的反讽。《悼朱湘》戏仿朱湘的新格律体,用语尚属暗讽,而梁实秋次日发表的文章是对《自由谈》一系列文章的彻底否定。
30日,梁实秋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悼朱湘先生》。梁实秋谈及自己和朱湘的交谊:“我和朱湘幼年同学,近年来虽无交往,然于友辈处亦尝得知其消息,故于朱先生平素为人及其造诣,亦可说略知一二。”他据此提出个人看法:“他的神经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很重的变态的现象,这由于早年家庭环境不良,抑是由于遗传,我可不甚知道。他的精神变态,愈演愈烈,以至于投江自杀。”梁实秋在详引何家槐和余文伟文章后,认为他们误导读者,强调朱湘之死是性格使然:
余何两位的文章,似乎太动了情感,一般不识朱先生的人,读了将起一种不十分正确的印象,就以为朱先生之死,一古脑儿的由“社会”负责。……我觉得他的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我想凡认识朱先生的将同意于我这判断。
因此,与何、余二人的观点相左,他呼吁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神经并未错乱的文人们,应该知道自处,应该有较强的意志,理性,和毅力,来面对这混乱的社会罢?”文章更以“不过生活着的文人们若是借着朱先生之死而发牢骚,那是不值得同情的”①梁实秋:《悼朱湘先生》,《益世报·文学周刊》1933年12月30日。一句作结,表明对将自杀问题社会化的反感。
1934年1月6日,《天津商报画刊》以《诗人朱湘投江之传说》报道了朱湘死讯,却质疑此事的真实性,“朱君投江以后,尸体至今未获,或者竟尚生存,文学家好为此种惊人之举,以示游戏人间之意趣,亦未可知”。②耳:《诗人朱湘投江之传说》,《天津商报画刊》第10卷第15期,1934年1月6日。市民小报的介入,是一时热点的跟风,目的自然不是为了追问事件来由,故才有了娱乐消费性质的朱湘未死之推测。22日,《益世报·语林》再次就此问题刊登文章《朱湘何独不幸》,此文将原因归罪于家庭。作者评点先后逝世的徐志摩、彭家煌、朱湘三人悲剧俱缘于家庭,此文诛心之处在于叙及徐志摩、彭家煌逝世后遗孀均撰文哀悼,訾议刘霓君未有文字表示,不明就里地散布刘氏送朱湘孩子进孤儿院,文末以“朱湘有灵,能不痛哭!呜呼,朱湘何独不幸”③李痊:《朱湘何独不幸》,《益世报·语林》1934年1月22日。把问题完全归责于夫妻矛盾,封闭了自杀事件社会面相讨论的空间。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认为:“舆论的栖居地以自己的方式构建着舆论,为了不同的目的占有舆论。”①阿莱特·法尔热:《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陈旻乐译,文汇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针对此事上海与天津培育出了不同的解读风向,前者取更有批判性的“诗人”自杀,后者趋向保守性地解读为诗人“自杀”。此外,作者政治光谱有别,南北报纸迥异立场,以彰显各自风格,获取读者关注,亦是个中不可忽视的原因。
与上海、天津两地的论者不同,北平的陈翔鹤将问题聚焦在文学层面。他曾与朱湘在东老胡同为邻,并对“朱湘君同我们发生一种文艺上的同声相求之感者”记忆犹新。他认为自杀是诗歌边缘化而诗人难以接受所致:
由于中国自从新文艺运动发生以后,历年来诗的收获,都是那般的贫瘠,而且有许多从前的作者,此刻或者早已绝笔,或者早已改作散文,即可作为一种证明,……或许痛恨着诗格和诗质的低落,以及深感到中国此时诗人生活的无路可走,这种激愤之情,早已在已献身于诗作的朱湘君的胸怀中动荡着,也是说不一定的罢?
陈翔鹤据此申告“我们的同时代者,或后来的行将将生命献给艺术的后起者们,再重新的述说一遍罢:我们得活着,得活着,得活了下去。”②陈翔鹤:《悼朱湘君》,《沉钟》第30期,1933年12月30日。他的思考是文学论证的闭环,即诗歌因为时代遭际衰落,诗人生活日渐艰辛,但诗人必须更加坚韧地生活,才能在艺术上实现突破。相较于新闻业更发达,更市民化的上海、天津两座租界城市,北平作为彼时文化之都所特有的雍容、稳定以及深厚的传统,是陈翔鹤做出如是思考的土壤。但曾经共同的公寓体验,乃至由此孕育的文艺青年身份意识,更是他做出如上判断的根本所在,文章所刊载的杂志《沉钟》,作为他与杨晦、陈炜谟、冯至等编辑的纯文学类同人刊物,亦保证了文艺维度思考的可能性。
上海《时事新报》由贺玉波在1934年1月14日的副刊《星期学灯》组织了“朱湘纪念专号”。此专号稿源复杂,既有赵景深所写交代诗人死后诸事安排的《朱湘死后》,亦有自陈“我不认识朱湘”的周楞伽所撰《吊朱湘》,还有因发表《鲁迅的狂吠》,与鲁迅论战的民族主义文学追随者邵冠华的悼亡诗《哀师友朱湘》,以及葛贤宁《悼朱湘》诗两首等。此专号应视为作家之间因朱湘自沉,物伤其类的文字集合,并无特别深意①参见1934年1月 14日《时事新报·星期学灯》“朱湘纪念专号”。。不过,其后专号形式被与朱湘有着更为紧密纽带的友朋沿袭采用。
二
1934年以“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②编者:《〈华年〉解》,《华年》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16日。为宗旨,面向青年读者的《华年》周刊刊登了朱湘在安徽大学昔日同事刘大杰的《朱湘的死》。文章认为朱湘之死有终极意义,“因为诗人是不平凡的,所以诗人的死也应该不平凡”。③刘大杰:《朱湘的死》,《华年》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27日。
刘大杰向青年读者传达了朱湘自杀的文学崇高性,赵景深则更进一步,在《青年界》策划纪念专号,通过刊载朱湘照片与友朋文章,全力塑造了一位迥异于报纸社评文字的高洁诗人形象。
《青年界》作为北新书局的招牌,创刊于1931年。1920年代中后期起,“文学”日渐成长为自有目的独立运作的“场域”。作为一种职业可能的“文学”,既需要回应已有文学青年的各种发表诉求,同时亦要源源不断召唤新的文学青年,所以上海出版界应时所需创办了大量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纯文艺刊物,《青年界》即诞生于如上行业背景。《青年界》创刊时销量仅八千份,1934年订户已达两万八千户,1935年更突破五万户,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可谓深巨④《〈青年界〉优待定阅者 突破五万户大运动》,《青年界》第8卷第5号,1935年12月。。因赵景深兼任《青年界》主编的关系,朱湘发表甚多,去世前的1932—1933年两年间就发表包括诗歌、文论、散文、书评在内各式文章27篇,对该刊读者而言,“朱湘”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青年界》第5卷第2期的“朱湘纪念号”于1934年2月1日出版,内收苏雪林的《论朱湘的诗》、柳无忌的《我所认识的子沅》、顾凤城的《忆朱湘》、练白的《悼朱湘》四篇文章,何德明与吕绍光所作两首同题悼亡诗《悼朱湘》,赵景深编辑的《朱湘著译编目》,朱湘遗著数篇,此外还在卷首以照片制版排印出郑振铎、闻一多、饶孟侃、柳无忌、黄翼、苏雪林的哀悼信,以及朱湘与其夫人合影、朱湘子女合影、朱湘诗稿真迹、朱湘信札真迹若干。
纪念号中的影像与诗文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两帧合影传递了朱湘全家和睦的信号,哀悼信影印件则一一标注写信人任职高校,种种举措隐然是对《益世报》论调的反驳,而诗文则集体营构出朱湘怀才不遇的诗人形象。苏雪林认为文坛风气的转变导致朱湘未获足够注意,“五四运动后我们对新诗抱着异常的好奇心与期待的愿望,所以有许多草率的作品,竟获得读者热烈的欢迎,而《草莽集》则在读者对新诗冷落的时期出版的”①苏雪林:《论朱湘的诗》,《青年界》第5卷第2期,1934年2月1日。,柳无忌相信生活的失败是由于诗人全情贯注于创作所致,“他没有去理会到生活里的各种复杂的变化,他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都在想着作诗……他的一生全是为生活挣扎着,他的一生是个失败,因为在他的字汇中没有‘敷衍’两字”。同期杂志还刊登了洪为法的《李贺之死》,这显然是编辑赵景深有意为之,以古今相通来强化此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杂志读者群,上述作者撰写的怀旧文所传递的文学之路愈益艰难的额外信息。柳无忌决绝断言“现今的时代不需要诗人。诗人在世,惟有受讥讽与唾骂,冷淡与压迫。子沅的命运,也是诗人的命运”。②柳无忌:《我所认识的子沅》,《青年界》第5卷第2期,1934年2月1日。
署名“练白”的《悼朱湘》中更直接从诗人之死过渡到了青年文学梦的破灭:
朱湘的死,给了想进身文艺的人,(尤其是诗)一个打击,留学生、诗人、教授的朱湘,尚且为了生活而不免于死,在做着桃色的“诗人之梦”的青年,怎能不被扬子江上的怒涛,澎湃得粉碎么?③练白:《悼朱湘》,《青年界》第5卷第2期,1934年2月1日。
通过《华年》《青年界》等杂志,责问社会病灶的讨论在青年一代中广为传播。但国民政府党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的介入,则让解读更趋对立。
《中央公园》创刊于1932年5月21日,停刊于1937年12月13日,是《中央日报》存续时间最长的副刊之一。在创刊号中,署名“子元”的编辑在《开场白》提出“过去本报的副刊,似乎是纯文艺的,大概是文艺得太过分了吧!好像不大得到群众的彩声,现在想把它纠正过来,要向——副刊文艺趣味化——这一条途径努力,以期得到普遍的欣赏。……使这一个小小的副刊,无论碰到那[哪]一种阶级的人,都感到相当的兴趣。”①子元:《开场白》,《中央日报·中央公园》1932年5月21日。可见其针对与提倡文艺大众化的左翼,目的是争夺文艺话语权。但是由于所用非人,作者队伍参差不齐,文章水平低下,一直毫无生气,以致屡次停刊。1933年7月1日,储安平接手《中央公园》,一改前几届主编新旧杂糅及偏重南京文坛的敷衍做法,大力革新,力求在新文学特别是全国性的议题中有所发声。
1934年12月28日,何家槐致信储安平,提出“他(按指朱湘)的死究竟应归罪于社会,还是应该归罪于他自己或者他的夫人?我想一定有人对这发表意见。所以特别写这封信给你,希望你舆上[论]公开。”②何家槐:《元旦征答》,《中央日报·中央公园》1934年1月1日。储安平在翌年1月1日全文刊出来信,并配以“元旦征文”字样,希望读者就此发表不超过六百字的意见。储安平听取何家槐的建议,其中却又有他个人的考量。对于南北报纸之差异,储安平早有认知。他在1931年就曾认为“北方的新闻事业,要比南方的有生气些,其最大原因,南方的报纸,只是一种Building Affair,至北方则多少有一些Literary的意味”。③储安平:《北行散记》,《申报·本埠增刊》1931年5月8日。可见储安平对以上海为代表的报纸向有不满,认为其有制造事端的作风。此外,储安平主持《中央日报》期间对左翼文学的态度,有一个参照物王平陵,他虽没有完全地去附和后者,但仍是在王平陵的声音下开展自己的工作④张慧:《〈中央日报〉副刊与储安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因此,作为文坛大事件的诗人之死,又遇左翼将其政治化之际,储安平应何家槐之请在《中央公园》讨论此事,于公于私均有充足理由。
虽然是征文,但储安平充分使用了自己的权力。栏目共收到20篇来稿,他刊发了10篇,其中6篇持鲜明的社会无关论。张鸣春《朱湘之死怪谁!?》:“朱湘与社会何涉,与大众何涉?朱湘的死应当与平常人的平常之死一样的不应该惊奇悲叹。我们决不要因他的诗曾要卖一行四元而觉得损失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章伯雨《朱湘的死是自己疼爱自己》:“只要以‘他在安徽大学有三百多元的月薪’这事实就可证明社会对他的死是不能过份[分]负担责任的”,白鸿的《关于朱湘》:“‘生活和文人的剧烈的歇司底里狂’将他逼死的”,苓薯《朱湘之死》:“诗人朱湘的死,是原于他的傲性,不合于现存社会”,沈谔《诗人朱湘的自杀》:“他的死,并不是社会不容他,实他死在怪僻和孤傲的性情里面的”,余之伴《论朱湘之死》:“朱湘的自杀,正合张耀翔先生说的‘中国名人的变态行为’。”①参见《中央日报·中央公园》1934年1月8日,1月9日,1月11日,1月13日。同时,有据可考的,至少张鸣春、章伯雨、白鸿就时有文章见刊于《中央公园》。可见,虽然对外宣称欢迎发表各种意见,但储安平通过数量安排、作者筛选等编辑手段把控了《中央日报》讨论的整体语境。
储安平表示“对此问题,一无意见,故亦无文章可做”②《编者按》,《中央日报·中央公园》1934年1月15日。,但征文结束后的1月15日,《中央公园》刊载了《“朱湘自杀的责任问题”的题外文章:什么诗人文人!》,虽然未署名,但有研究者从口吻、用词和思想判定此文出自储安平之手③韩戍:《储安平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因此它反映了储安平的真实态度。文章起首一再重申“我是因朱湘自杀这件事而谈及其他的感想的”“我自问对于他的自杀问题,没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我下面的感想,都是平时积起来的,与朱湘先生本人无关”,其后切入正题:
我以为“文人”也是“人”,文人也应该注意“为人之道”,假如自己不能好好为人,作有打算的生活,作有经纬的事情,办事不负责,说话不负责,则一旦感受社会的冷酷而自杀,社会实在不能负责任。要知诗人文人的所谓社会冷酷,不一定是真真的“社会冷酷”。也[以]至于某一个人自杀了,不了解那个人一切的人们来讨论他,更是不必!④《“朱湘自杀的责任问题”的题外文章:什么诗人文人!》,《中央日报·中央公园》1934年1月15日。
由上引可见,储安平不仅否认了朱湘自杀社会需要承担责任,还借批评文人的散漫做派,暗中严厉地否定了左翼作家的社会批判态度。
《中央公园》毕竟是有文学取向的报纸副刊,刊发的文章尚属论辩性质,国民党内部政治团体复兴社创办的《人民周报》所刊文章语气则极为专横。3月28日,该刊登载了《从诗人朱湘自杀说到目前的新生活运动》,文章一方面认定朱湘之死是个人所致,另一方面非常牵强地将其与政府此际提倡的改造国民日常生活、提升国民素质为目的新生活运动相嫁接,借以论证后者的合法性。文章挞伐文人习气:“形成朱湘生活之困难是由于他本身的浪漫颓废之故”,因此,“朱诗人的自杀,至多也只能表现他是一个不适于现代生存的弱者”,文章就此引申:“从朱湘之死,使我们感觉到新生活运动在今日,已无可迟缓。”其后文章定义“新生活,从原则上说就是礼义廉耻的生活”,详细阐述其所包含的“道德生活”“智识生活”“健康生活”“集团生活”四个方面的内容,文章最后再次勾连诗人之死与新生活运动以作总结: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全无意义地用眼泪鼻涕来哀悼朱诗人,来为朱诗人开专号,写祭文,我们应该从“朱诗人之死”的教训中,深切体会到新生活运动的严重性呵!①之一:《从诗人朱湘自杀说到目前的新生活运动》,《人民周报》第114、115合期,1934年3月28日。
国民党政府的文化部门显然注意到了朱湘之死所引发的舆论风潮,因此不仅杜绝对诗人之死的社会追问,更连纪念专号形式也予以排斥,希图转移读者注意力,将讨论引流至正在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对此做法,左翼文坛并没有与之纠缠,反而是朱湘的挚友通过出版诗人著作、抚恤遗孤等予以了间接回应。
1934年1月14日,赵景深在《时事新报》发表《朱湘死后》时,率先讲到:“最重要的朱湘身后之事。我想是一替他出遗著,二聚集教育遗孤的基金。这两点现在也没有很好的成绩,否则,我想朱湘至少有一部分不必死的原因了。”②赵景深:《朱湘死后》,《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4年1月14日。23日,时在希腊雅典的罗念生获悉朱湘自沉后,致信友人曹葆华亦提及:“努力收集子沅的遗稿和书信,整理的责任全交与我。问霓君,子沅身后的儿女有没有力量教养?”③罗念生:《致曹葆华》,《罗念生全集》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28日,身在美国纽约的罗皑岚也在《朱湘》文末发出呼吁,“把他身边遗下的诗文,马上收集起来,免得日久散失”“朱湘身后萧条,是谁都知道的。希望大家替他的遗孤筹一笔教育基金”。④罗皑岚:《朱湘》,《益世报·文学周刊》1934年3月14日。
1934年7月,罗皑岚回国,应柳无忌之邀于9月入职南开大学外语系,⑤叶雪芬:《罗皑岚年表》,《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同年秋,罗念生回国,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翻译希腊悲剧①罗念生:《自撰档案摘录》,《罗念生全集》第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加上早前已回国的柳无忌,“二罗一柳”与赵景深一道将诗人之死的后续事宜向实务转化。
柳无忌于1934年应邀兼任《益世报·文学周刊》的主编②叶雪芬:《柳无忌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他们扭转了该报此前在朱湘事件中的立场,朱湘诗作及一些朋友的纪念文章在该副刊陆续登载。1934年12月5日朱湘逝世一周年,他们在《文学周刊》第40期推出了“朱湘纪念专号”,内中有罗念生的《朱湘身世》、柳无忌的《朱湘的十四行诗》、孙大雨的《海葬》、吴奔星的《吊诗人》、李芾棠的《悼朱湘先生》,朱湘遗札以及《朱湘著译编目》。在编后记中,他们向读者说明了抚恤遗孤情况:
诗人朱湘死后,身世很萧条,留下一子一女,因家里没有钱教育他们,尚在南京的孤儿院内住着。现朱湘的友人们,不忍见他的遗孤失学,特发起“筹募诗人朱湘遗孤教育基金委员会”,在京、沪、平、津等地,捐募基金。委员共十五人,有郑振铎、杜衡、闻一多、苏雪林、施蛰存、黄翼、徐霞村、饶孟侃、傅东华、黄自、余文伟、赵景深、罗念生、罗皑岚、柳无忌。本刊承景深先生寄下捐簿一册,托代筹募,读者诸君,如有同情此举,愿为臂助者,请直接赐寄本市南开大学罗皑岚先生或柳无忌先生收均可。③《编后记》,《益世报·文学周刊》1934年12月5日。
除了设法抚恤遗孤,在一干朋友的协力下,1934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石门集》(1935年2月再版),8月北新书局出版《文学闲谈》,10月生活书店出版《中书集》(1937年5月再版),12月北新书局出版《海外寄霓君》;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番石榴集》,人生与文学社出版《朱湘书信集》,4月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永言集》,身前仅出版过两部诗集与一部译作集的朱湘,其诗文译著得以迅速大量出版。
除了作家圈、出版界,此事更在青年学生中激发共情。他们的文字多发表在自办刊物,地域分布相当广泛,既有上海的《大夏期刊》《光华附中半月刊》,也有《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校刊》,福建厦门大学附中校刊《囊萤》,甚至远在河北的《保定新青年》等。学生所选用的体裁,多为散文或诗歌。他们之所以关注此话题,除报纸的信息传递外,更多是《华年》《青年界》由“诗人之死”过渡到“青年之死”的讨论所引发。如在1934年3月《光华附中半月刊》刊载的《朱湘之死》,该文提到了朱湘遗著《我的新文学生活》、闻一多与柳无忌关于朱湘的评价与回忆,并对比了李贺与朱湘,如上内容俱出自1934年的《青年界》“朱湘纪念专号”,可见作者是阅读后的有感而发。
整体而言,青年学生接受了朱湘之死系社会逼迫的观点。如何晴波在《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校刊》的随笔中写道“他的死,虽然是一时意识的朦胧,意识的冲动,无情的社会,总要负责任的吧!”①何晴波:《悼朱湘》,《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校刊》1934年3月10日。陈子棠在《光华附中半月刊》中发文认为“朱湘是给现实吞灭了”。②陈子棠:《朱湘之死》,《光华附中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4年3月25日。从身份认同到政治认同往往是一步之遥,在《大夏期刊》中署名“孟宗”的《祭诗人朱湘文》结尾,可以明显感受到青年对发端于左翼的由朱湘之死吁求知识分子觉醒思路的应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他们今后对于生命所取的途径已不同了,不再像你那样蒙着耳目投进了缥缈的长江。”③孟宗:《祭诗人朱湘文》,《大夏期刊》第4期,1934年6月。青年的习作,幼稚气息不可避免,但其关键在于不同地域的学子传递并分享了上海报纸杂志的观点,可以看出左翼思想已为彼时青年学生所信服。
三
1934年,鲁迅著文感叹“(朱湘的死)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④鲁迅:《趋时和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4页。不过“热闹”并未延续太久,出版市场有着最为直观的表现。正如上文所述,各大小出版社在朱湘自沉后曾集中出版了一批他的诗作,但这些出版物并没有真正兑现为经济赢利。柳无忌就回忆过,他们是用罗皑岚畅销小说《苦果》“赚来的钱津贴《朱湘书信集》的出版”,而“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时,在我的门房间内,还堆积着许多本没有卖出的”。⑤柳无忌:《朱湘:诗人的诗人》,《二罗一柳忆朱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3页。朱湘遗著的滞销,固然有诗歌受众狭小的原因,但更应放置在出版变迁的行业格局中考察。1930年以后,五四运动后崛起的以出版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为业务的新书业进入萧条期,正如书业中人徐调孚所言“近年来出版界受了不景气的影响,新书业觉得出版‘新书’,大有‘此路不通’之感,于是也跟着出版中小学教科书。”①徐调孚:《中国出版界之现势一瞥》,《中学生》第41期,1934年1月1日。简言之,五四新文学在1930年代后逐渐失去了市场的青睐与读者的追捧,其势能已明显衰减,无复1920年代的风光。因此,即便诗人之死成为一时话题,但诗作出版遇冷也是自然结果,它是新书业惨淡境况的缩影。
1930年代峻急的国内外局势,使得朱湘自杀的讨论不可能进入形而上的纯思辨空间,而是在文化、社会、政治、地理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集中地呈现为“个人”与“社会”的两极化理解。认定“个人”原因说,诗人之死就仅仅是孤案,不具有深入反思余地,而持“社会”论者的阶级理论视野,引申出对社会体制的批判,客观上会促使阅读者重新看待身处其中的世界。从上述差异可透视国共两党文艺政策的效用及走向。南京政府没有整合与其相近的以梁实秋、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论述,使他们各自为政,因而在诗人之死的舆论思想市场中竞逐失败。国民党文艺治理缺少有效方法甚至成为体制惯性,它在1934年成立特别针对文艺和社会科学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作补救,此种粗暴手段直接决定了其在文艺领域的彻底失语。与之不同,左翼知识分子在朱湘自杀事件中明晰地注入社会分析话语,同朱湘友人的怀人文字,二者之间彼此渗透、转化和影响,产生更强的感召力,成为了主流观点。行之有效的论述,配合对中间力量的团结,此方式在随后的鲁迅逝世纪念、郭沫若祝寿、《闻一多全集》出版等诸多文坛事件中得到了更为娴熟的运用,而正是文化领导权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获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著名命题,强调媒介形式本身对信息传播与接受的影响②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50页。。关于朱湘自沉事件,不同类型的报刊及其附属的文体、叙事策略承担了区隔性角色,各种观点因刊物的性质发生膨胀收缩,报刊分割了读者,反之读者亦会选择、接受乃至传播其所认同的讯息。诗人之死最终演化为传播甚广且被普遍接受的青年之死,关键就在于《青年界》《华年》等青年刊物的中介,随之才有全国各地学生自办刊物的下渗普及。更长远地看,学生群体将文学事件循左翼脉络衍生性地政治化讨论,昭示了青年的思想动向。
如果说后五四初期存在过由中小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学青年”,他们可以借由文学实现阶层跨越①姜涛:《公寓里的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朱湘之死对更青年一代而言则象征着“文学梦已死”,社会已不复存在个人奋斗的土壤,社会病因说才得以鼓荡,“文学青年”与“革命救亡青年”之间的代际更替才会在其后的历史中呈现。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难以纳入救亡主题的诗人之死失去了继续讨论的价值,甚至朱湘诗歌也成为要被时代扬弃的对象。1936年,期刊《小学生》登载赏析文《朱湘底两首小诗》,系为小学生群体细致鉴析朱湘的《夏院》与《夏夜》两诗,尤需注意的是,介绍诗人时虽延续“因为经济压迫,而投江自杀了”的观点,但文章结尾已转为“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民族的生命已很危险,人民的生活很不安定;所以,以后的诗歌,将要是战斗的怒吼,而不是闲适的低吟了。”②寿清:《朱湘底两首小诗》,《小学生》第6卷第11期,1936年8月1日。《小学生》由北新书局出版,赵景深是编辑之一,文章的发表及结论本身说明了彼时的形势变化。嗣后,朱湘及其诗歌成为文学史的点缀,一直到1980年代才重回文学青年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