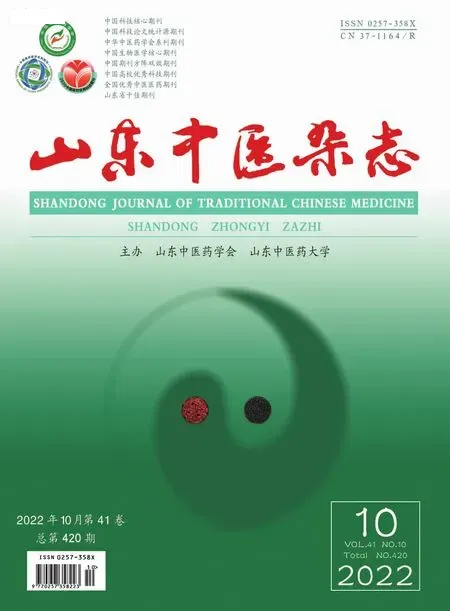中医“通和”思想源流及其意义
刘昭纯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 济南 250355)
“通和”的概念最早见于南朝,可追溯于《庄子》。它融合“通”与“和”的思想内涵于一体,用来阐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规律,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认识事物及相互联系的一种思维方式,又是处理和协调各种复杂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同时还是一种“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的理想状态。由于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通和”思想必然会深深地根植于中医学术之中,构成中医理论的重要部分,并直接影响着中医理法方药立论与临床实践。
1 “通”与“和”的基本概念
1.1 释“通”
“通”,形声字。从辵(chuò),甬(yǒng)声。《说文解字》:“通,达也。”本义为通达、通畅,即通行无障碍、没有阻塞、可以穿过。如《周易·系辞传》:“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吕氏春秋·达郁》:“血脉欲其通也”。日常所说的“通衢大道”(四通八达的道路)、“通邑”(四通八达的城市)等,均为此意。“通”,又引申为疏通,即使之通畅、使之通达、使之不阻塞之意。如《吕氏春秋·慎行论》“以通八风”,唐代柳宗元《柳河东集》“疏之欲其通”。平素大家耳熟能详的“通风”“通气”“通便”“通下水道”等均取此意。概言之,“通”具有“通达”与“疏通”双层含义。其中“通达”是一种目标与状态,而“疏通”则是一种方法与手段。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通”,认为自然界天地万物之间要“通”,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之间也要“通”。“通”是自然界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前提,是人类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根本保证。如《周易·泰·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就是说,在自然界层面,只有天和地之间的阴阳交感通达,才有万物的生生不息,畅通和谐,各遂其生;在人类社会层面,只有君与臣、上与下、人与人的交流沟通,才能志同道合,事业通泰,国家昌隆。再如《易经·系辞下》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言流通、畅通是自然界的常态,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长久发展的前提。《易·说卦》还有“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感而遂通”等,都是在强调“通”的重要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观念的核心思想,它肇端于远古时代的“神人交通”“绝地通天”(《尚书·周书·吕刑》),发展于春秋战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生气通天”(《黄帝内经》),“通天下一气儿”(《庄子·知北游》),而最终于北宋时期形成“天人合一”的概念。所以,“天人合一”的核心在于“通”,即天道与人道相通,自然与人体相通。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人生不断追求的理想境界。
1.2 释“和”
“和”,形声字。从口,禾声。《说文解字》:“和,相应也”。其本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地跟着唱或伴奏。如《周易·中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即鹤在树荫处鸣叫,幼鹤跟着应和。“和”,又有和谐、和顺、适中、恰到好处之意。如《广雅·释诂三》:“和,谐也。”《广韵·戈韵》:“和,不坚不柔也。”《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和”,又引申为调和、和解、调治,即使之和谐、使之适中、使之恰到好处之意。如《尚书·周官》:“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周礼·天官·食医》:“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集韵·过韵》:“和,调也。”张载《正蒙》:“仇必和而解”。平素我们常常提到的“和胃”“和难”“和神”“和天下”等均取此意。概言之,“和”有“和谐”与“调和”双层含义。其中“和谐”是一种目标与状态,而“调和”则是一种方法与手段。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多见于《易经》以及儒家、道家的经典著作。如《易传·乾卦·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大和”就是“太和”,意思是说天道与人道的变化,各有自己的规律,只有保持各自的平衡和谐,才能普利万物,生生不息。再如《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万物各得其和以生”;《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都是在强调“和”的重要意义。
更重要的是,“和”文化早已深深扎根于华夏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民众重要的信仰和思想观念。它既是调节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基本法则,又是协调人际关系、适应社会群体发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性规范,诸如“和能生财”“和能睦邻”“家和万事兴”“和能兴国”“政通人和”等等。
1.3 释“通和”
“通和”一词,是融合了“通”与“和”的涵义而构成的复合词汇,包含着通畅与和谐、疏通与调和等多层含义,具有较好的通用性。它最早见于南朝《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可追溯于《庄子·田子方》。该篇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意思是说地之阴气上升,天之阳气下降,两者相互交通合和而生成万物。可以认为,这里所说的“交通成和”即为“通和”一词之雏形。
“通”与“和”具有不同的内涵。但由于两者关联密切,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又常常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故后世才有可能将“通”与“和”的涵义融合,合并构成“通和”这一新的概念,并用以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凡天人合和、和谐社会、和好的人际关系等,一刻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交流与沟通又常常以“和”为基础条件。不“通”无以为“和”,不“和”亦无所谓“通”。因此“通和”既是一种集“通”与“和”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又是处理和协调各种复杂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同时还是一种“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的理想状态。在现代汉语中将“通和”解释为“互通往来和好”“通畅缓和”“通达平和”等,就是这种既“通”又“和”的理想状态。
2 中医“通和”思想源流
起源于先秦时期的中医“通和”思想,涵盖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人文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其奠基形成、传承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又杂糅儒释道多种文化于一体,深深根植于中医学术之中,构成了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部分,并直接影响着中医理法方药立论与临床实践。
2.1 先秦时期
有了人类,便会有病痛,于是也就有了医疗活动。最初的医疗行为往往是本能的、自发的,比如运动以祛寒、按摩以镇痛等。因此,在春秋以前,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基本停留在本能的、感性的认识阶段。此后,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积累,加之精气神学说、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等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人们开始探索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养生等问题,并逐渐形成中医学的系统理论。因此,与中医学相关的“通和”说大量散见于先秦诸子的文献中,及至《黄帝内经》成书,“通和”已成为中医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帝内经》认为,“通”“和”是人体生命运动的一种常态,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体自身阴阳和平、内在脏腑经络与外在五体九窍关系协调的最佳状态,贯穿于整个生命过程中。而“郁”“滞”“结”“壅”“瘀”“积”“聚”“癥瘕”“痞”等“不通”与“不和”,则是人体生命运动过程中的一种变态,所反映的是一种病理。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因此在治疗上要用“通法”“和法”,以“求通”与“求和”。
先说生理。《黄帝内经》认为,人的生成离不开脏腑气血的“通”与“和”。如《灵枢·天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说明只有血气营卫的“通”与“和”,人体生命运动才能顺利进行。一旦出现“血气虚,脉不通”,则“中寿而尽也”。《管子》也曾说:“气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离不开脏腑气血的“通”与“和”。《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只有五脏阴阳之气调和,五脏与各脏腑组织器官相互联络的通路畅通,人体才能安和健康。如《灵枢·脉度》说:“五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这里重点强调的就是“通”与“和”以及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生理上,内在的五脏是与外在的七窍息息相通的,七窍之所以能“通”,之所以能发挥“知香臭”“知五味”“知五谷”“辨五色”“闻五音”的功能,关键在于内在五脏的“和”,即五脏的功能正常。反之,若“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说明“通”与“和”是常态,是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不通”与“不和”则是变态,是人体的病理状态。而且“通”与“和”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得益彰,互为前提,互为因果。
“六腑传化物而不藏”(《素问·五脏别论》),以降为顺,以通为和,是说六腑之间是互通的,而且只有保持通畅和相互关系的调和,才能发挥正常“传化物”的功能。五脏之间亦必须交通合和。例如,心主神明,为“君主之官”,有“使道”与其他脏腑器官相通,若“君主”明彰,“使道”通畅,则十二脏腑功能安和,身心康健;若心神不明,则“使道闭塞而不通”,疾病丛生,“形乃大伤”(《素问·灵兰秘典论》)。再如,“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明肾与五脏六腑皆通,并为之贮藏精气。唯有此,肾才能通泄精气,以完成人类生殖繁衍之功能。又如《素问·玉机真脏论》说:“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四傍,即肝心肺肾四脏,说明脾脏与其他四脏相通相和。其他如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肝能疏通全身气机、疏通畅达脾土,“土疏泄,苍气达”(《素问·五常政大论》),“土得木而达”(《素问·宝命全形论》),均是在说明五脏之间只有相通相和,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
联络沟通必须要有通路。《黄帝内经》认为人体内存在着多种联络通路,诸如“经络”“经脉”“血脉”“气化”“使道”等。这些通路必须是通畅的,而且通路的各个环节又必须是和谐的。不然,无以为用,无以为和。正如《素问·调经论》所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灵枢·海论》说:“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灵枢·经脉》说:“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难经》是以问答释难的形式编撰而成,为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该书共讨论了八十一难,其中很多内容都涉及到体内各组织器官互通互用以及联络沟通的通路问题。如《难经·二十七难》曰:“圣人图设沟渠,通利水道以备不然”;《难经·二十八难》曰:“沟渠满溢,流于深湖”。就是将十二正经比作“沟渠”,将奇经八脉比作“深湖”。当十二正经气血满溢时,就会流入奇经八脉,蓄以备用;当十二经脉气血不足时,奇经八脉所储存的气血则可溢出给以补充。两者交通成和,互通互用,共同维持着人体阴阳气血的协调平衡。“七冲门”理论为《难经》所独创,涉及到饮食物从摄入、消化、吸收到糟粕排泄的整个通路。其中“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难经·四十四难》)。冲,要也;门,关卡。七冲门即消化通道上的七个重要关卡,其作用在于既要保持消化道的通畅,又不能通之太过。其中任何一个“冲门”发生病变,都会影响整个消化道的通畅,导致在饮食物的摄入、腐熟、运化、输布和排泄上出现异常,甚至危及生命。事实上,七冲门也是整个消化道最容易发病的部位,诸如贲门癌、贲门狭窄、阑尾炎、痔疮等。还有,《难经》认为三焦也是人体内的重要通道,可通行、输布原气于全身,主管诸气的气机与气化。凡肾中之元气自下而上行至心肺,输布于全身;胸中大气自上而下行至肝肾,以资元阴元阳,均以三焦为通路。正如《难经·六十六难》说:“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难经·三十八难》也说:三焦“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
再说病机与治疗。《黄帝内经》认为,很多疾病都是因为“郁”“滞”“结”“塞”“壅”“瘀”“积”“聚”“痞”等“不通”或“通之不畅”所致。因此,“不通”是人体疾病的根本病机,无论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抑或饮食劳逸致病,大抵都是如此。因此需以“通法”治疗“不通”。又因“通”与“和”常常互为因果,所以“不通”又常常同时伴有“不和”。因此在治疗上既要求通、求和,还要注意通中求和,或和中求通。
《素问·热论》在论述热病的成因、传变和症状时说:“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即说明“不行”“不通”不仅是一种病理状态,而且可以危及生命。因此,在治疗上要“各通其脏脉”。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在详述了病机十九条之后特别强调,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疏”,通也。就是说无论病机“皆属于心”“皆属于肺”,还是“皆属于风”“皆属于热”,也无论是“盛”还是“虚”,都必须在弄清病机的基础上,以疏通之法祛除血气中的瘀滞,才能使脏腑机能调达,经络通畅,身心和平。这既说明通法在治疗上的重要性,又同时说明“通”与“和”的密切相关性。重在“通”,以通求和,通中寓和。
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里的“气郁”“阏”“滞”,都是“不通”,是“筋骨瑟缩不达”的根本病机,在治疗上“为舞以宣导之”,就是通过舞蹈这种运动方式进行“宣导”,以使之“通”,最终达到阴阳和平之目的,亦是通中求和。
再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为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可见,体内阴阳和则健康无病,“不和”则为疾病状态,而“和之”是治疗疾病的最好法度。也就是说,“和之”可以使阴阳双方恢复“阴平阳秘”的平衡协调状态。反之,如果不及时采取“和之”这种方法调治,阴阳双方将不再相互维系,“交通成和”的关系将会破裂,以致阴阳不通,相互格拒,或“阴盛格阳”,或“阳盛格阴”,最终导致“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生命运动终止。因此,这里的“和之”既包含着“求衡”,又蕴含着“求通”。
2.2 汉唐时期
汉唐时期,是中医基本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加以验证、充实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主要成就表现在“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药物方剂学方面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黄帝内经》的“通和”思想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使其更具有临床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张仲景非常重视“通”与“和”,他在构建“辨证论治”体系过程中大量援引了这一理念。例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说:“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即是说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五脏元真之气通畅,内养脏腑经络,外濡四肢百骸,内外协调,身心安和。就像“风气能生万物”“水能浮舟”一样;反之,若五脏元真之气“壅塞不通”,则可产生津液停聚,气机郁闭,血液瘀滞,百病丛生。就像风“能害万物”、水“亦能覆舟”一样。总之,五脏元真是否通畅与人体身心安和息息相关,通畅即可安和,安和则可通畅。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这是一个不断良性循环的过程。在病理过程中,则相互影响,相互损害。
在阐述病理和治疗问题上,张仲景认为,很多疾病都是因为“通”与“和”的失常所致,当通不通、当和不和,或通之太过与不及都是疾病。因此,他把“通”与“和”作为重要的治疗手段,同时又将“通”与“和”作为最终的治疗目标。
例如《伤寒论》第387条:“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中医学历来认为“不通则痛”“不荣则痛”。本证“身痛不休”,显然是“不通”所致。正如黄元御所说:“吐利既去而痛不休,以表寒未解,经气壅滞之故”。而张仲景用桂枝汤“和解其外”令“小和之”,显然是在用和法治疗“壅滞”“不通”之证。这是和中求通。不仅如此,张仲景还用和法治疗“通之太过”之证,他认为“病常自汗出者”,是“卫气不共营气谐和故尔”,应“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伤寒论》第53条)。汗孔又称“玄府”,掌控着汗液的排泄。在正常情况下,汗孔是通畅的,且随着体内生理情况和外界气候变化而有相应的调节,可排泄多余的水分,带出热量和代谢废物。若当汗出而无汗,为“玄府”闭塞不通,通之不及;不当汗出而有汗,则为通之太过。本条“自汗”属通之太过,基本病机为营卫不和,因此在治疗上用桂枝汤调和营卫,使“营卫和”则自汗痊愈。这是以和法治疗“通之太过”的异常病变。
再如《伤寒论》第229条曰:“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其中“胁下硬满”是少阳气郁不通,“不大便”是阳明病肠道不通,“呕”是胃气上逆,病在上焦。张仲景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便可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大便自然也就通畅了。众所周知,小柴胡汤为和解之剂,也是和法之代表方剂,而今用以治疗“不通”之证,可见二者可互通互用,相得益彰。和中求通,和中寓通,和则通。
还有《伤寒论》第208条:“阳明病……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至大泄下”;第209条:“阳明病……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第250条:“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小承气汤为《伤寒论》三承气汤之一,由大黄、枳实、厚朴组成。承气者,承顺胃气之下行,可使塞者通、闭者畅,是典型的通里攻下之剂。因此,用于治疗“腹大满不通”“大便复硬而少”等,药证相符,无可非议。然而张仲景不言“泻之”“下之”“通之”,而言“微和”“和之”,除了因为小承气汤泻下作用较为缓和之外,大概还是在提示我们“通”与“和”密切相关。通中求和,通中寓和,通则和。
药物方剂学方面的进步是汉唐时期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期间提出的许多药物配伍原则以及所记载的方药,大都体现了中医学的“通和”思想,为后世中医治则治法的发展以及方剂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著作,对于药物学的运用,提出了“凡此七情,和合视之”的配伍原则,为临床药剂配伍提供了规范。后世徐子才、陈藏器等根据中医病机学说,把药物的作用分为十类,就是历来所说的“十剂”。其中特别提出“通”剂,认为“通可以去滞,即通草、防己之属是也”。
还有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记载了51首方剂,其中有“救卒死中恶方五首”。他认为:“中恶卒死者,皆脏气被壅,致令内外隔绝所致也”,故应“开五窍以救卒死中恶”。五首方均为外用方,每方用药一二味。其作用分别为:点眼以通肝气,吹鼻以通肺气,著舌可通心气,启喉以通脾气,熨耳以通肾气[1]。
事实上,《伤寒论》中就记载了许多“通”与“和”的方剂,专门用于治疗这类“通和”失常的病证。如设桂枝汤调和营卫以止自汗出;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以通肠胃;半夏泻心汤和胃降逆以开结除痞;小承气汤通里攻下以理气和胃;四逆散调和肝脾,通阳气以达四肢;白通汤通阳破阴以合和阴阳;通脉四逆汤回阳通脉以使阴阳通和顺接。凡此,或通中求和、通中寓和,或和中求通、和中寓通,或通和并举。
2.3 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医临床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在理论层面的探索也愈加深入,中医学的“通和”思想也日趋成熟,越来越显示出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
宋金时期,成无己开注解《伤寒论》之先河,首次提出小柴胡汤为和解半表半里之剂。他在《伤寒明理论》中说:“伤寒邪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之可矣。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此后医家均从其说,遂以和解少阳半表半里为和法第一要法,小柴胡汤也就成为和法之代表方剂。然细究之就会发现,小柴胡汤证的基本病机在于表里不和,而表里不和的根本原因在于邪郁少阳,以致少阳经气郁而不得疏泄,“表里相拒”而内外不通,枢机不转则气行不畅。因此,在治疗上应祛除半表半里之邪气,使少阳经气通达、表里互通、气机畅通。故方中用柴胡轻清升散,疏邪透表,“使半表之邪得从外宣”;用黄芩清泄少阳郁火,“使半里之邪得从内彻”(《名医方论》);用半夏散结消痞,和胃降逆;再用人参、大枣、生姜、甘草扶正以助祛邪。最终可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所以,小柴胡汤证的“和解”没有离开“通”。“不通”无以为“和”,“不通”也不可能“和”。
金元四大家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且流派纷争。但无论是寒凉派、攻邪派,还是补土派、滋阴派,都从不同侧面论证了中医“通和”思想,且各有建树。如刘完素提出“留而不行为滞,必通剂而行之”,并创防风通圣散,以散风壅,开结滞,宣通气血,祛除在表之郁热;创三一承气汤通下泻热,以治热邪郁结在里。张从正主张攻邪,认为人体气血宜通不宜滞,“惟以血气流通为贵”,其著名的汗、吐、下三法之主旨即在于“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补土派”以李杲为代表,善用温补脾胃之法,提出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清气不升,九窍为之不利”“脾胃虚则九窍不通”。同时认为疼痛是体内某一环节不通的表现,凡风寒暑湿燥火诸邪侵袭,或瘀血、痰饮、水湿、食积等有形之邪留滞体内,造成气血运行滞涩、经络壅塞,便会产生疼痛,即所谓“不通则痛”。故在治疗上,主张“诸痛为实,痛随利减。汗而通导之,利也;下而通导之,亦利也;散气行血者,皆通导而利之也”(《此事难知·随痛利减》)。即是说“通导”可以畅通气机,调和血脉,治疗疼痛诸症。所谓“通则不痛”是也。朱丹溪是滋阴派的代表,在治疗上虽强调“滋阴降火”,但同样重视“通中求和”。他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悱郁,诸病生焉。故一身诸病,多生于郁”。“郁”者,阻滞、不通之意。郁病,泛指由气机郁滞不畅而导致的多种病证,朱丹溪将此分为“六郁”,即气郁、湿郁、痰郁、热郁、血郁、食郁,并创越鞠丸行气通滞,疏肝解郁。一旦郁滞得解,气机畅通,则气血冲和,万病皆愈。
明清时期,医家们结合临床对金元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加以综合折衷、融会贯通,使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更加趋于完善。在这一阶段,医家们似乎更加重视“通”“和”的治法,并结合自己的临证心得作了较多的发挥,大大拓展了以通和思想论治疾病的范畴。
张景岳对“和”及“和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认为和法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而是涵盖或兼容多种治法。他在《景岳全书·古方八阵》中说:“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之意广矣。”
高士宗认为,调气、调血、开结、升提、补虚、温阳散寒等,同样具有“通”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不通之证,亦应归属“通法”范畴,并特别强调不能单以泻下为通。他在《医学真传》中说:“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下逆者使之上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高士宗大大拓展了通法的适用范畴。
周学海认为“不通”与“不和”具有不解之缘,两者常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因此,“和解”之法可以用来治疗“不通”之证。他在《读医随笔》中说:“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气之杂极者也。寒者、热者、燥者、湿者,结于一处而不得通,则宜开其结而解之;升者、降者、敛者、散者,积于一偏而不相冾,则宜平其积而和之……故开郁降逆,即是和解”。
2.4 近代与现代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出现了大碰撞,中医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迫使中医学(特别在思想理论层面)寻找自我振兴和发展的突破口。在这一过程中,学者围绕中医“通”与“和”的思想以及在临床上的指导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发表了许多较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如王小平[2]“中医学合和思想的研究”、张珍玉[3]“通法俚言”、何天有[4]《中医通法与临证》、曹洪欣“中医理论体系建 构 中 的 和 合 文 化”[5]、姚 魁 武 等[6]“中 医学和合思想渊源探析”等。所有这些,虽然没有将“通”与“和”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但对确立中医“通和”思想的概念,探索其在临床上的指导意义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 构建中医“通和”思想的意义
“通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入中医学之后,就成为中医的一种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医学生理病理之中,并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
3.1 充实中医生理病理学理论
系统整理和运用中医通和思维,可以更好地阐释中医学的某些生理和病理现象,充实和完善中医生理病理学的理论体系。
首先说体内阴阳二气的“通和”。
阴阳双方只有相互交通成和,升降出入有序,才能推动和维持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若两者交通不畅,或不相交通,则会出现多种病理改变,乃至生命运动停止。然而,在迄今对中医阴阳学说研究中,关注点大多集中在阴阳二气的互根互用和消长平衡上,特别是在用阴阳学说讨论人体的生理病理时,很少提及阴阳二气的“通”。这就导致在解释某些病机时显得繁琐牵强,说服力不足。例如,“阴阳格拒”是中医病理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主要表现为内寒外热,或内热外寒。为了解释这一病理现象,常常需要借用“阴阳的对立斗争”“阴阳的消长盛衰”“阴阳的相互转化”“寒热真假”等一系列复杂的原理加以解释,有时还不得不引经据典加以说明。晦涩艰深,难懂难读。反之,如果引入阴阳二气的通和思维,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明了,一通百通。事实上,“格拒”就是阻碍、隔阂、拒绝之意。简单地说就是“不通”。阴阳格拒,就是阴阳不通。比如“阴盛格阳”就是阴气偏盛至极,壅闭于里,格阳于外,阴阳之气不相交通。所以,张仲景设通脉四逆汤以破阴回阳,通达内外。阴阳之气“交通成和”了,不再“格拒”了,诸症自消。还有“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也是在说人体阴阳二气不再“交通成和”,相互维系的关系彻底丧失,人体的生命运动即会终止。
再说脏腑之间的“通和”。
关于脏腑之通,目前关注最多的是六腑“以通为用”“以降为和”“传化物而不藏”,而对五脏自身的“通”,以及五脏相互之间的“通”论述较少。偶有及者,除了经络学说之外,大多依赖于五行学说的生克乘侮,诸如水火既济、肝木乘脾、母病及子等。这是很不够的,也很难较好地解释临床常见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诸如“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五脏盛,乃能泻”“魄门亦为五脏使”等。这些脏腑之间在生理病理上的复杂联系,仅仅依靠经络和五行的生克乘侮是难以阐释的,因此必须有、也必然会有其他联络通路。实际上,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描述了除经络、阴阳五行之外的很多联络通道,用以说明五脏自身的“通”以及脏腑之间的“通”,诸如“使道”“气机”“气化”“以膜相连”“三焦”“虚里”等。只是由于这些内容大多散见于《黄帝内经》不同篇章之中,没能引起后世学者的足够关注,以致至今都没有得到系统地整理、完善和提高。
事实上,“通和”几乎涉及到中医生理病理的所有层面,除了前述的阴阳之气和脏腑之外,经络、气血、表里、营卫、五官九窍、水液代谢通道、玄府、筋膜、腠理、乳脉、脑窍、精窍、经水通道等,都是人体生命运动过程中的重要通道。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通道必须保持通畅,与通道相关的各组织器官必须和谐。只有这样,整个人体才能安和,生命运动才能正常进行。否则,一旦出现郁、滞、结、壅、瘀、积、聚、痞等“通之不畅”或“不通”之改变,即为疾病。
先师张珍玉教授曾结合临床对中医之“通”做过精辟的论述[7],他认为,“通”在中医学中有“生理之通”“病证之通”和“治法之通”,其中“生理之通系指人体气血津液畅通无阻”,五脏“所藏之精气津液亦贵流通”“六腑以通为顺”。“病证之通”是指“异常之通”,是病变。然细究之,病理状态下的“通”又有“通之太过和通之不及之分”,两者尽管病因不同、病位各异,涉及到的脏腑也各有所别,但均属“通”的异常所导致的病变。其中“通之太过者,如泻利、多尿”或“自汗、盗汗、遗精、崩漏、带下”等,“通之不及者,如便结、癃闭等”。其他还有郁、滞、结、壅、瘀、积、聚、痞等,亦属“通之不及”或“不通”之范畴。另外,还有在病理上属于积滞不通,而在症状上则表现为通之太过者,如“痢疾初起、热结旁流、瘀血崩漏等,当通因通用”。所有这些,都大大充实和完善了以“通”为核心的中医生理病理学理论。
3.2 完善中医论治思想与治法
中医论治思想是对疾病治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维方式,它贯穿于疾病治疗的全过程。近年来,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此进行了探索,提出许多具有卓识的学术见解。其中包括整体论治思想、辨证论治思想、求衡论治思想、恒动论治思想、杂合以治思想等[8]。但没有提及“通和”论治思想。
如前所述,“通和”是集“通”与“和”于一体的思维方式,且早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医学术之中。因此,它必然会在疾病治疗上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并贯穿于疾病治疗的整个过程。鉴于此,应尽快挖掘和整理通和思维在中医治疗学上的指导作用,建立通和论治思想的概念,充实和完善中医论治思想体系。
“通和”论治思想在用于指导疾病的治疗上,特别强调的是“求通”“求和”。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各脏腑组织器官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络通路都应该是通畅的,关系是和谐的,这是生命过程中的“常态”或“平和之态”。反之,一旦出现通和失常,无论是“通之不及”,还是“通之太过”,抑或是“不通”“不和”,都会发生疾病。因此,所谓治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用“通法”以“求通”,用“和法”以“求和”。又因“通”与“和”关联密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益彰,又常常互为前提,互为因果,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又常常会“通中求和”“和中求通”,或“通和并用”,最终恢复通畅和谐的生命过程之“常态”。可见,“通和”不仅是指导临床防治疾病的一种论治思想,而且还是防治疾病的大法和治疗手段,同时又是治疗康复的终极目标。
治法,主要指治疗疾病的法则,也是对一类相同病机或病性的病证确立的治疗大法。自清代程国彭提出“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尽之”以来,迄今中医学界多宗其说。因此,在中医目前经常引用的论治八法中没有通法。
然而,自《黄帝内经》以降,历代很多医家都曾论述过通法。如《素问·热论》提出治疗热病要“各通其脏脉”,《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通因通用”;《药对》据性能将药物分为十类,“通”为其中一类,并提出“通可去滞”;《伤寒明理论》认为方有十剂,“通剂”为其中之一;刘完素提出:“留而不行为滞,必通剂而行之。”至清代,高士宗认为调气、调血、升提、开结、补虚、散寒等,均为“通之之法”,并特别强调“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近年来,有人提出“通法是中医数十种治疗法则中的根本大法”,并认为“通法可包括八法”,其中“汗法通肌表,吐法通壅滞,下法通内里,和法通半表半里,温法通凝滞,清法通热邪,消法通积滞,补法以正祛邪”[9]。尽管难免有牵强偏颇之嫌,但确为完善通法的概念提供了思路。
更为重要的是通法在临床应用甚广,特别是随着对活血化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查阅近年来临床常用的中成药,仅以“通”为关键字命名的中成药就达近百种之多。诸如,通心络胶囊、通脑宁心片、通痹片、通便灵胶囊、通窍耳聋丸、通宣理肺丸、通经甘露丸、通络生乳糖浆等等,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常见疾病。“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方即是法”。就是说方与法有密切的关系,治法是组方的依据,方剂是治法的体现,方是从属于法的。既然有这么多以“通”为主的方剂,且能经得起长期临床疗效的检验而成为广泛应用的“中成药”,那就理应尽快建立和完善“通法”的概念,为临床辨证用药提供理论根据。既不能有法无方,更不能有方无法。
通法的确立,是对中医固有治法的补充和完善,丝毫不影响其他“八法”等治法的立论和应用。通法是针对郁滞、壅塞而设,可单独应用,亦可与其他八法同时应用,形成以“通”为导向的汗通法、吐通法、下通法、和通法、温通法、清通法、消通法、补通法等。其中通法与和法相辅相成,通中寓和,和中寓通,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汗、吐、下、温、清、消法等六法大多属于祛邪范畴,主要用于各种实证。而祛邪之目的,又大多在于“通”。这是因为,邪气(六淫、痰饮、瘀血、食积等)郁滞体内,就会导致多种多样的不通。如气血津液运行不畅、经络不通、腑气不通、五官七窍不通、二便不通、玄府不通、经水不通、脏腑阴阳壅塞不通等,故当祛邪以使之通。“补通”则不然,主要用于虚证。由于脏腑功能减退,或元气虚损,动力不足,引起气血运行不畅,或痰湿内停、瘀血阻络、食滞胃肠,故当补虚以使之通。张珍玉教授认为:“通法似有泻通和补通两大类。前者指方药具有通滞功效而言,后者则为扶正作用而论,两者殊途同归。故药物之升降浮沉、寒热温凉在通法中具可用之”[2]。
3.3 指导临床对多种病症的防治与康复
第一,用通和思想指导治疗多种痛症。
“不通则痛、通则不痛”,是中医最常用的术语之一,可溯源于《素问·举痛论》。最初只是针对寒邪稽留经脉,导致气血运行凝涩不通,卒发疼痛而言。后世医家结合临床进一步发挥,认为任何原因导致的任何部位的“不通”,均可引发疼痛。至明代,李中梓著《证治要诀》,明确提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概念,沿用至今,并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对多种痛症的诊断和治疗。
例如,现代中医诊断学根据疼痛的性质将疼痛分为七类[10],其病机几乎均与“不通”有关。其中“胀痛”因于气机阻滞,“重痛”因于湿邪阻滞,“刺痛”因于瘀血阻滞,“绞痛”因于实邪阻滞,“灼痛”因于热结阻滞,“冷痛”因于寒凝阻滞。此六者,均为实邪瘀阻经脉,影响到气血运行的通畅,故出现疼痛。“隐痛”则属于虚证,大多因于气血不足所致。诚然,脏腑组织器官失于气血的濡养亦可引发疼痛,即所谓“不荣则痛”。然而,气血虚则动力不足,必然会伴随着运行不畅。也就是说,在气血不足导致的疼痛中,亦存在着“不通”之因素。故补气多兼行气,补血必兼活血。
再如,颈肩腰腿痛是目前临床最常见的痛症,中医学称之为“痹病”。痹者,闭也,不通之意。因此,治疗这类疾病的关键在于“通”。就目前临床来看,中医治疗这类疾病除了用中药“通络”“通痹”外,最常用的方法是针刺、艾灸、推拿、刮痧、拔罐、热敷等这类“中医适宜技术”。其中大多疗效确切,止痛效果常常立竿见影。而这些疗法之所以对于这类疾病均有较好的疗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疗法具有一个共同特点——“疏通”。疏通气血、疏通营卫、疏通经络、疏通血脉、疏通筋脉、疏通筋膜,虽治疗手段不同,然殊途同归。将不通变得通畅了,疼痛自然消失,“通则不痛”是也。
现代西医学认为,很多疼痛都是血液循环出现障碍,局部组织缺血、缺氧所致。因此改善血液循环,恢复局部血流和供氧,疼痛症状即可得到缓解。美国纽约大学医学教授约翰·萨诺著《别了,背痛》一书,明确指出背痛的主要原因在于因焦虑引起的背部肌肉紧张。肌肉紧张则挤压血管,以致血流不畅,局部的肌肉缺血、缺氧,故出现疼痛[11]。与中医“不通则痛”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要说明,“不通则痛”之“痛”不应仅仅局限在疼痛之痛,而应涵盖病痛之痛,包括各种难受、不适的感觉。也就是说,凡酸、麻、木、胀、痒等不适感觉均应属于“痛”的范畴。因此,亦可在通和思想指导下加以调治。
第二,用通和思想指导慢病康复。
慢病是指一类病程较长,不容易治愈的疾病。包括脑中风、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多种常见疾病。中医学认为,“久病入络”“久病多瘀”“百病多由痰作祟”,因此治疗这类慢病大多需要以通为主,兼以活血化瘀、化痰祛湿、理气导滞等。
例如,脑中风是以卒然昏仆、不省人事、伴有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为主证的一种疾病,临床以脑梗死最为常见。对此,历代医家均有较为详实的论述,其中大多认为该病的根本病机在于气血运行不畅,瘀血阻络。如刘河间提出:“人肥则腠理致密而多郁滞,气血难以通利,故多卒中也”;明代楼英认为:“中风皆因脉道不利,气血闭塞也”;方贤提出“气塞不通,血塞不流”是中风病发生的重要因素;王清任则更明确地指出:“中风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是由气虚血瘀而成”。近年来,许多学者基于大量的临床实践,提出“瘀血证候始终贯穿于整个中风病变过程”,认为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是治疗中风病的基本法则[12]。十多年前,笔者曾提出“瘀血生风”病机假说[13],并通过古代文献、现代临床、药物学分类以及现代实验研究加以论证。认为“凡气虚、气滞、阴虚、血寒、血热、出血、七情过激、跌打损伤等所导致的瘀血,在加重到阻塞经络、上累清空之窍,或影响筋脉功能时,均可产生内风”,“瘀血生风的根本病机在于瘀血阻塞经络,髓海失养,筋脉失润”。既充实和完善了肝风内动的理论体系,又为创建“活血息风”法提供了立论基础,为临床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内风病证提供了理论根据。总之,内风病机在于瘀阻不通,息风的关键在于活血通络。不仅如此,即便是现代医学对于该病的治疗和康复,其关注点亦始终在于“通”。如急性期要取栓、溶栓,促使脑部血管的再通;恢复期的核心康复治疗技术则是“促通技术”,即利用各种方式刺激运动通路上的各个神经元,调节其兴奋性,以获得正确的运动输出。
再如心脏病。心脏病是一个大概念,包括心肌病变、心内膜病变、心包病变、冠状动脉病变,以及各种心律失常等多种心脏病变。在中医学中,大多属于心悸、怔忡、胸痹、心痛的范畴。虽然临床表现各有不同,但“心血瘀阻”“瘀阻心络”往往为其共同的病机。或兼气滞、气郁,或兼气虚、血虚、阴阳两虚,但终不离壅滞不通。因此,在治疗上应以“活血通络”为主,兼以行气、通滞、补气、养血、滋阴、温阳等。正因为如此,临床常用的通心络胶囊、通脉养心丸、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等,尽管配方各有特点,但其共同点亦在于“活血通络”。事实上,现代医学对此有着同样的认识,而且在表述上亦大致相同。诸如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狭窄、心脏传导阻滞等。
还要说明,部分心脏病患者常常表现为肝气郁滞。这类患者除了具有心慌心悸、胸闷憋气外,常伴有睡眠欠佳,易急躁,焦虑,且每因情志不畅或劳累而发作。中医学认为,肝主疏泄,心藏神,共同调节人的精神意识和情志活动。故肝气郁结时,常常会导致心脏病的发生。因此,在治疗上既要通肝气,还要通心络。即以疏肝解郁、理气通滞为主,佐以活血通络。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曾创办“双心门诊”,即从“心脏”和“心理”两个方面开展心脏病的康复治疗工作,可谓殊途同归。
恶性肿瘤大多属于中医学癥瘕、积聚的范畴,其病机在于痰瘀互结,滞留不化,阻遏气机,导致体内的各种通道瘀阻不通,诸如血脉、经络、五官七窍、食管、气道、肠道、尿道等。因此,治疗恶性肿瘤同样需要在“通和”思想指导下辨证用药。或活血通脉、或化痰通滞、或疏肝行气、清热通淋、养阴通便、通阳化湿。我国著名的肿瘤防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剑猷在《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一书中就反复强调用“疏通”“疏导”法治疗肿瘤的重要性。他以四川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为例,援引“岷江分水的鱼嘴”“分洪排沙的飞沙堰”“引水工程的宝瓶口”,来说明用疏通的思路治疗癌症更顺应自然规律,其作用也“更能持久”。他研制的中药小复方“松友饮”,就以具有活血通络作用的丹参为主要药物,并研究证明丹参控癌的机制在于“促进血管内皮正常化,改善供氧,起到抗缺氧作用(缺氧是促进残癌转移的重要因素)”[14]。
其他如高脂血症对人体最大的破坏性是给血管“添堵”,导致血行不畅或堵塞;高血压、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几乎都与血管狭窄、血流不通畅有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组疾病,包括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等,但其共同特点是呼吸道阻塞,通气障碍。因此在治疗上都离不开“通”。
第三,用“通和”思想指导养生防病。
“通和”既是人体生命过程中的常态,又是疾病治疗的“圣度”,还是康复疗养的终极目标。因此,养生防病不能脱离“通和”思想的指导。民间常说“不通生百病,一通病不生”,不无道理。
首先,“通和”思想提示,养生要注意人与自然环境的通达与和谐。即根据四季变迁以及其他自然环境的改变,能动地采取一些养生措施以适应其变化,包括衣着、饮食、起居、劳逸的调节等。《黄帝内经》所谓“生气通天”“人与天地相应”,“顺四时而适寒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等,均是指此而言。否则,若不注意顺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养生,特别是季节交替之时,乍寒又暖,就很容易罹患或诱发多种疾病。此外,昼夜晨昏的变化、地域环境的变化亦对人体生命活动产生较大影响,亦需进行适应性调节。
其次,“通和”思想提示,养生要注意人与社会环境的通达与和谐。人生活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人文思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经济模式等千差万别,人的生命活动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喜怒忧思悲恐惊在所难免。若不注意适时情志调养,很容易罹患“情志病”,又叫“心病”。所以《黄帝内经》要求人们“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要“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都是在强调养生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与他人及社会的交流过程中,适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生活方式,以维持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这对于自身生命活动的稳定、平衡和协调至关重要。
再次,“通和”思想提示,养生要注意人体自身的通达与和谐。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身体各部的通达与和谐是“常态”,即生理状态。然而,由于遗传因素、生活习惯因素(包括饮食、睡眠、运动等)、自然或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常常会导致人自身的通达与和谐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最初可表现为自我感觉身体不舒服、难受,有症状、体征,但还不能确诊为疾病,即亚健康状态或称作“亚疾病状态”,如非明确疾病引起的周身酸痛、疲劳乏力、睡眠障碍、烦闷焦虑、食欲不振、胃肠功能紊乱等均是。中医治疗大多采取疏通气机,调和肝脾。
还有,“带病养生”也要注意人体自身的通达与和谐。虽然医学科技快速发展,特别在现代科技层面上的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刷新,但仍然有很多疾病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如各种癌症、心脏病、脑卒中、糖尿病、高血压等,还有一些因高龄带来的脏器衰老和退行性病变。所以“带病养生”更为重要。近年来我们常常提出肿瘤患者要“带瘤生存”,慢病患者要“带病生存”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养生学意义。事实上,社会人群中目前已经有很多人正是以这种“带瘤”或“带病”的方式生存着。而这类人群要想生存得更好、更长,活得更有质量、更有意义,就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通达与和谐,包括精神情志、五官七窍、二便、玄府、气血、经络、五脏六腑等。
“通和”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深深地扎根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具有极强的通用性和亲民性,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观;中医通和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养生、遣方用药、针灸推拿等层面,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成为“医者日用而不觉”的医学观。鉴于此,通过系统文献梳理,溯本探源,守正求真,提出构建中医通和思想,以期对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与指导临床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