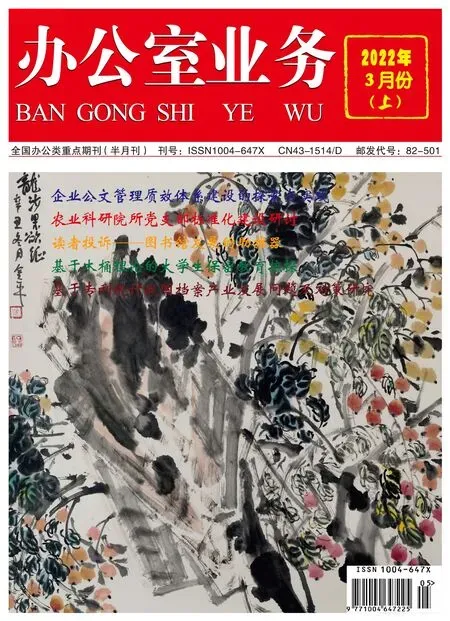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现状与整理保护对策研究
——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为例
文/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陈昌琳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具有丰富而独特的古籍文献资源。本文主要针对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开展普查,摸清古籍的种类、数量等,编制古籍目录,较为全面地掌握古籍的现状;同时结合古籍整理保护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为新时代背景下地方高校馆藏古籍发挥好应用价值提供借鉴或参考。
一、古籍的定义和判别
古籍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记载,是历史的产物,是文明的历史标记。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有着特定的含义。从内容来说,古籍指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书籍;从载体形式来说,主要指以古典装帧形式出现的写本和印本图书;从时间来说,其成书应在与现代对应的古代,当然,这里的古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分期,历史是延续不断的,不能简单地割离开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以上3点是明确古籍概念和判别的重要依据。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将古籍范围确定为:周秦时代到1911年期间成书的图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图书馆古籍编目》(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指出,古籍主要指1911年以前历朝各代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但之后影印、排印的线装古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章氏丛书》《王国维遗书》《过云楼藏明人小札》等也属古籍。其实,古籍不仅包括古书,还包含古书以外其他古代文献,如甲骨刻辞、金石刻辞、简牍帛书、敦煌卷子等。2006年8月文化部发布《古籍定级标准》,关于“古籍”的定义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从上述定义可知,目前对古籍内涵的认识虽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可以从3个维度和层次指导我们加深对学院图书馆现存古籍的认识,对下一步做好相关古籍的保护、整理、初步应用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出版或印刷时间是判定古籍的首要标准。古籍是先代典籍的统称,是古代文化的历史记载和原始遗存,具有唯一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是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兴起和现代存贮技术的飞速进步而渐次隐退的历史概念。换言之,古籍成了一个静止的、定格于某个历史空间的文化存在,它属于过去的时代。对于今天的后学来说,古籍只可以被瞻仰、被学习、被整理、被研究、被应用,却不能被复制。目前大家公认的1911年辛亥革命是古籍的时间下限,但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民国时期影印、排印的部分线装图书因其具有内容形式的古典性和重大学术影响,基本也可划入古籍范畴,适当从宽有助于普通地方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对现有典藏文献的保护和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代再版、影印、整理校订、注释乃至研究的古典文献,无论多么深厚、复古、精美,均不能称之为古籍。
古籍的载体是判定古籍的另一个重要标准。载体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形式载体,如前所说,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说明无论何种材质,古籍一定要体现书的特征,上古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简木简、绢帛,两汉后造纸渐行,线装书成为古籍的主要载体;二是符号载体,严格意义上的古籍离不开书写或印刷的文字符号,这个符号主要是汉字,当然也包括其他民族的文字,就汉语古籍来说,其记录的必须是古代汉语(文言、古白话)。对照形式载体,一般的摩崖石刻就很难说是古籍(东汉熹平石经或可视为石版古籍);对照符号载体,五四运动后兴起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及其实践著作如鲁迅《狂人日记》、胡适《尝试集》等也很难称之为古籍。
二、学院图书馆古籍的基本情况
经过图书馆相关部门的前期普查和本研究团队的调查、复查,目前已基本掌握了学院图书馆现存古籍的总体情况。
2009年以前,学院图书馆采编部曾组织专人对馆藏古籍做过第一次普查,采取手工登记方式编制了古籍目录两本,粗略统计现存古籍在5000余册;2016年、2017年由学院图书馆古籍部和资源建设部牵头对馆藏古籍进行了第二次普查,使用计算机录入书名、作者、卷别、册数等基本信息,并按照《四库全书》经史子集进行分类,相关数据显示,馆藏古籍8237册,其中经部1919册、史部2125册、子部2409册、集部1784册,但因未做校对、勘误,该书目错漏较多,仅为参考;2018年、2019年,随着新图书馆落成并顺利搬迁入住,所有馆藏图书均完成整理上架,本研究团队与学院图书馆古籍部、资源建设部合作开展第三次古籍普查,形成了较为准确、完整的古籍书目。
初步普查显示,学院图书馆现存馆藏古籍1906种、8433册。按照收藏时间、馆藏来源等,现存馆藏古籍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原黔南师专、黔南教育学院、都匀民族师范学校图书馆旧藏的少量古籍;二是2000年三校合并前各校图书馆通过新华书店渠道购买的线装图书,这部分图书占了馆藏古籍的绝大部分,印刷时间大多在1949年至1990年,部分影印图书采用版本为古籍版,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三是黔南民间藏书家潘髯收藏后捐赠给学院图书馆的私人藏书,共计457种、1550册,均为旧版线装古籍,并附带有古香古色传统书柜、书匣,书柜上有“淑珍嫁奁”字样,其价值尤高,不少古籍版本最早可上溯清中晚期,下迄近代、民国,在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中具有重要地位。
从2018年5月古籍文献的建设规划开始,学院图书馆就明确把潘髯私人藏书作为古籍开发利用的重点。目前,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林柏珊老师带领的研究团队,围绕三个方面正在开展相关工作:一是抢救修复破损古籍;二是探索自建具有地域特色的特藏文献数据库;三是通过特色资源库平台为广大师生提供线上线下特色文献查阅服务。该工作团队现已完成潘髯私人藏书古籍的整理及网上比对工作,完成了114种近700册图书的扫描、上传等工作,预计2023年底黔南师院特色数据库潘髯藏书可提供线上阅览。
根据初步研究,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内容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经传类,包括传统经书及其文字、训诂、音韵等“小学”文献,约占馆藏古籍总量的40%。例如清·王鸿绪《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清·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清·焦循《周易补疏》《孟子正义》、清·任大椿《小学钩沉》、清·孔广森《经学卮言》《广雅疏证》、宋·郭忠恕《汉简》、明·陈第《屈宋古音义》、旧题西汉伏生撰《尚书大传》、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唐·颜元孙《干禄字书》、章太炎《章氏丛书》等等皆是;二是古典诗文集或文论类,约占馆藏古籍总量的40%。例如清·张问陶《船山诗草》、明·杨慎《杨升庵词品》、明·杨继盛《杨忠愍公集》、清·宦懋庸《莘斋文钞》、明·袁中道《南游稿》、清·莫友芝《郘亭诗钞》、唐·李商隐《樊南文集》、清·段玉裁《经韵楼集》、金·元好问《元遗山先生全集》、唐·皎然《皎然集》等等皆是;三是史学或笔记杂谈类,约占馆藏文献总量的20%。例如清·尼玛查《西域见闻录》、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南宋·朱熹和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佚名《越史略》、明·陈霆《雨山墨谈》等等皆是。其中《雨山墨谈》为1936年6月商务印书馆平装本;《越史略》比较特殊,为越南古代历史文献,作者不详,约撰于越南陈朝(1225—1400)年间,该书共三卷,采用编年体,以汉语文言写成,记述李朝史迹较详,后附陈朝纪年,乃越南最古史书之一,是记载越南上古时代至李朝事迹的重要典籍。
馆藏古籍中有少量古籍版本弥足珍贵,如《北宋钞毛诗郑笺残卷本三卷》。该古籍为四川成都存古书局民国二年影印,其版本系陈矩随遵义黎庶昌出使日本于古寺中获得,存《王风》第四至第六,长五寸七分,幅四寸二分,每半叶八行,行十八九字,细注双行亦十八九字。陈矩(1851—1939),字衡山,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诗人,在日本寻得各种遗书百余卷,宋元椠本二百余卷,名人著述未刊行五百余卷,带回国内,影印为《灵峰草堂丛书》百卷和《中国逸书百种志》《北宋钞毛诗郑笺残卷本三卷》即收入《灵峰草堂丛书》。
值得注意的是,馆藏古籍中有少量贵州古籍及黔籍或旅黔撰者文献,其中不乏被称为“西南巨儒”的贵州“影山文化”代表独山莫友芝、遵义“沙滩文化”代表郑珍和黎庶昌、“心学”创始人王守仁、出生于贵州兴义的晚清名臣张之洞、清初著名学者诗人贵阳周渔璜等人的古籍文献。特别是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郘亭诗钞》《韵学源流》《莫友芝辑贞定先生遗集》及万大章编《莫贞定先生年谱》(民国二十八年独山莫氏铅印本)、郑珍《巢经巢诗集》《巢经巢诗后集》《郑子尹仪礼私笺》《巢经巢遗诗》《巢经巢文集》《说文新附考》《说文逸字》《汉简笺正》、黎庶昌《拙尊园丛稿》、清张锳《兴义府志》、傅玉书《桑梓述闻》、《贵州通志》《瓮安县志》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版本收藏价值。加强对上述贵州地方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整理、传承和弘扬,对于推进新时代贵州文化振兴、凝聚精神力量,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古籍整理保护的对策建议
高校图书馆是古籍收藏、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机构,但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地方高校古籍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古籍保护管理不善、技术落后、人才匮乏和资金短缺等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各高校图书馆也加大了古籍的整理保护开发力度,在大量研究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古籍数据库建设、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措施。
针对学院图书馆古籍现状,结合图书馆整体建设及功能服务规划拓展要求,为进一步做好现存馆藏古籍的整理保护和综合利用工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供参考:
(一)精准普查,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古籍整理是古籍保护的前提,不摸清家底和实情,就谈不上对古籍的保护。虽然经过三次古籍普查,我们对学院图书馆的现存古籍情况一次比一次清楚,但实事求是地说,每一次普查其实都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学院图书馆的“古籍”(普查认定前姑且称之)数量在省内高校图书馆中还是比较多的,限于时间、人力、技术等因素影响,每一次普查都不尽彻底而且连续性也不够,再加上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古籍书目编录并不规范,准确性和完整性较差,错漏、遗漏、重复录入在所难免,至于版本甄别、典藏查考等更加专业性的工作非一般工作人员所能完成。因此,建议学院图书馆组织有一定古典文献学、版本目录学等专业背景的相关技术人员对照普通书籍的管理方法,对所有古籍文献的名称、作者、内容、数量、版别及馆藏状态等进行认真细致的盘点、清查、比对,落实分级保护管理。对于那些版本较早、价值高、残损程度大的古本要优先妥善保存和修复,特别是馆藏善本、孤本古籍应重点保护,对列入重点保护的古籍应该建立古籍文献资料登录和编目特藏库,将古籍文献资料的数量、来源方式、入藏时间、年代、质地、外形尺寸、质量、完残程度、保存状态、包含数量等基本指标项进行收录,尽早固定留存其照片影像资料,保质保量完成古籍普查梳理工作,为下一步做好保存、整理、加工、研究、利用等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管保结合,完善馆藏条件。传统纸本古籍是图书馆古籍工作的物质基础。古籍历经久远,在流传过程中如果保存不当,就会形成破损,严重的会出现粘连、脆化、絮化等问题,加快损毁速度。在自然条件下,环境的温度、湿度,甚至空气洁净度及大气中紫外线的含量等因素都会影响古籍的保存寿命。根据文化部提出的《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古籍特藏书库环境温湿度应控制在温度为16℃~22℃,相对湿度为45℃~60%,并且温度日较差不大于2℃,相对湿度日较差不应大于5%。这就要求古籍书库配备高性能的恒温恒湿空调系统,配备足量的空气净化装置。然而高昂的设备价格令很多图书馆望而却步,国内仅有少数大型图书馆能满足条件,达到标准水平。
原生性保护指修复原本,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原本古籍,这是还原残损古籍“本来面目”的重要手段,有的技艺高超的工匠修复完的古籍甚至用肉眼都很难辨识出修复痕迹。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真正能落实到各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项资金少之又少。不管是密闭精良、恒温恒湿的古籍储存空间,还是各种先进的现代仪器,甚至单纯的古籍修复工艺,都需要大量、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目前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8000余册,按残损率30%计算,要修复所有的残损书籍需要数十万元甚至更多的资金,如此大额的单项经费投入恐怕很难实现。
前期普查显示,学院图书馆绝大部分“古籍”购于20世纪后期国营新华书店,载体形式虽均为影印线装书,但其印刷出版时间多在新中国成立后,印刷数量应该不少,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献意义上,其版本价值并不是很高。因此,建议学院图书馆在现有古籍书库设施设备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先进的保护性装置,对甄选出的馆藏珍贵善本、孤本重点加以保存保护;同时建立健全有效的古籍管理与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特藏相关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专人专管,加强日常监管巡查,在有效利用与适度控制上找到一个平衡点,避免走向束之高阁或加速湮灭两个极端。
(三)整合资源,构建特藏数据平台。从保护类型上看,古籍保护一般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两类。其中,原生性保护强调对于古籍本身进行全方位保护,从可能对古籍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材料造成印象的外部干扰因素(诸如环境温度、环境湿度、光照、虫害等)入手,通过避免这些外部干扰因素对古籍产生破坏作用,来有效实现对古籍的保护。但现实情况下,即使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介入,仍然无法完全避免纸本古籍作为一种历史遗存在自然规则中渐行渐远甚至最终湮灭的命运。因此,再生性保护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再生性保护是指借助信息技术与数字化技术,将古籍中所包含的文字与图像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做好相应数字备份,以此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便利,同时减少古籍原件的流通,从而有效避免古籍原件这一具备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重要文献资料因流通过程中的各方面外部因素而出现损毁甚至丢失的情况。
新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必须将古籍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改善古籍保护管理环境、提高防火防盗能力、加强灭火系统建设、经验交流等措施来提高古籍原生性保护能力,有效避免外部因素对古籍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图书馆应重视引入信息技术,加快古籍数字化、信息化进程,以此实现对于古籍的全方位保护,既保护古籍原件,又重视充分实现古籍的内在价值,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如前所述,目前学院图书馆相关研究团队已经在着手开展此项工作,但由于缺乏整体战略规划、投入资金和人力物力少、技术难度较大等原因,进展还是比较缓慢。建议学院图书馆高度重视古籍特藏数据库的建设,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联合馆内外、校内外相关领域力量,列入重点专项工作开展攻关,注意数据库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必要时,可与校外有关机构合作,走共建共享的道路,减少重复建设、避免盲目建设,不断提高数字化古籍的质量水平。本研究团队重要成员张霁博士曾将学院图书馆的少量古籍通过拍照方式发给上海相关领域专家、机构开展联合甄别和鉴赏,收到热烈反馈,多个机构表达出希望与学院图书馆合作共建特色数据库的强烈意愿。这一方面证明了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确实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合作共建是可行、可操作的。
(四)拓展功能,提升学科服务能力。图书馆是高校的文化中心,是重要的学术基地,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宝贵资料。古籍的生命力在于应用,高校图书馆应该明确纸质古籍文献的重要性,转变“重藏轻用”的观念,保护传承古籍文化,高效利用纸质古籍文献。纸质古籍文献应该作为图书馆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高其利用效率。但纸质古籍文献整理难度较大,相关工作者应该具备相当的文学素养、史学素养,学习版本学知识、文献学知识、校勘学知识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纸质古籍整理工作落到实处。从古籍保护的角度来说,古籍整理工作要不断优化和升级,做好保护的同时,还要提高对古籍资料的利用率,发挥古籍资料的价值。
但学院图书馆现实情况是古籍文献整理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匮乏,而文学与传媒学院正好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具有一支较为雄厚的研究队伍。学院图书馆若能在落实前3个对策的基础上继续延展功能触角,主动服务学科建设,逐步推进贵州地方古籍文献或馆藏珍贵善本孤本整理、校订、注释等研究,必然大有可为、大有作为。黔南师院原党委书记梁光华教授曾多次到学院图书馆查阅古籍,利用馆藏古籍开展贵州、黔南地方文化研究,在莫友芝研究、沙滩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文传学院李朝阳教授专注于莫友芝研究,著有《影山词注评》(巴蜀书社2015年版)、《莫友芝诗歌创作四期论》(《文艺评论》2015年第10期)等研究著作或文章。上海大学杨逢彬教授曾说:“古籍整理与研究是当代的朝阳产业,很容易出成果,若能对馆藏古籍进行持之以恒的重点整理和研究,可以出很多专家、教授。”斯言不虚也。
四、结语
通过本项目的调查和研究,初步掌握了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的概貌。若以版本论,潘髯私人藏书乃馆藏古籍的珍品,其余古籍虽印刷较晚,但其影印的版本多为民国、近代以前的古刻本,不少可上溯宋元、明清,仍有一定的文献收藏价值。较为惋惜的是部分古籍、特别是潘髯私人藏书损坏较为严重,大部分古籍为残本或多卷残缺本,完全成套的较少。但瑕不掩瑜,我们认为,学院图书馆现存古籍是不可多得的特藏文献资源,堪称“镇馆之宝”,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有关机构或团队应继续推进相关古籍的清理、对比、甄别、修复、整理、加工、应用研究等工作,力争取得更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