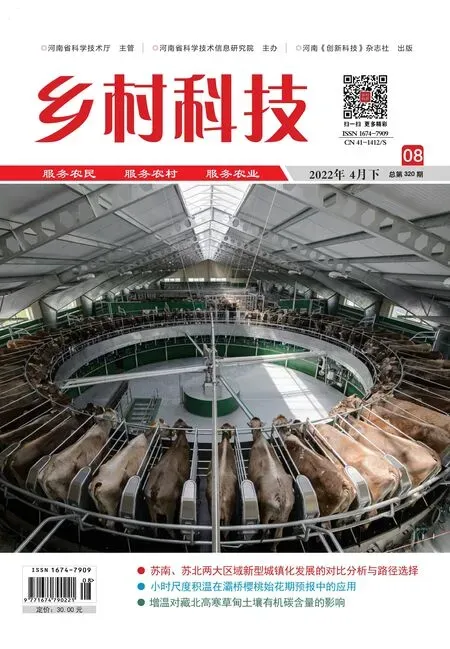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张翠霞
(武川县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内蒙古 武川 011700)
0 引言
过去,我国过分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与治理,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加之部分人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盗挖野生植物,使野生动植物生存遭到严重威胁,已有诸多野生动植物灭绝或濒临灭绝。有关数据显示,在我国3 万种高等植物中,有3 000 多种处于受威胁且濒临灭绝的境地。此外,高鼻羚羊、镰翅鸡、长江白鲟等珍稀野生动物在我国彻底宣告灭绝。野生动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就是维持物种多样性,也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一旦野生动植物资源完全灭绝,整个生态系统平衡就会被打破,人类生存与发展便会受到影响。
为促进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落实到位,我国相继出台多项法律法规。1988 年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2018 年对其进行多次修订。1996 年,国务院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并在2017 年对其进行再次修订。除上述文件外,国务院、国家相关部委还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状况的野生动植物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条例及管理办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林木种质资源管理办法》《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地方各相关机构应深入贯彻执行此类政策及法规条例,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加强保护。
随着我国不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积极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及栖息地修复工作,截至2021 年5 月,已有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国土陆地面积的18%,99%的植被类型与陆地生态系统类型、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85%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得到了有效保护。例如,朱鹮从刚被发现时的7 只恢复至5 000 余只,大熊猫濒危程度降级,206 种濒危植物回归野外。由此可见,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我国非法捕捉捕杀野生动物、盗挖野生植物等案件仍然频发。对于地方基层组织机构而言,有必要严格贯彻国家相关法律条例,加强自身管理制度建设,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贡献应有的力量。
1 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
1.1 保护意识较为落后
目前,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群体加入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行列。然而,目前人们的保护意识较为落后,保护对象更加倾向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对普通野生动植物不够重视,对放生也缺乏科学的认知。例如,为满足市场的鱼翅需求,不法分子大量捕杀鲨鱼,而且部分群众对于鲨鱼存在恐惧的心理,进而纵容捕鲨行为的发生,从而导致鲨鱼群体数量急剧减少。又如2018 年,云南省某湖区群众在海里投放各种鱼类,导致该地方海洋区域承载量严重超标,大量鱼类死亡,不仅没有达到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目的,反而减少了海洋鱼群数量。另外,受法律意识淡薄的影响,部分偏远地区居民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认识不足,经常捕食野生动物或随意挖掘野生植物,不仅威胁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而且给相关保护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严重阻碍。例如,2021 年黄某某得知浙江省淳安县境内的野生杜鹃花价值不菲后,先后组织多人擅自挖掘野生杜鹃花430 余株,严重威胁了地方野生杜鹃花的生存。
1.2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具有犯罪动力强、犯罪对象特殊且隐蔽、范围危害严重等特点。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对该类犯罪的打击力度,表现出了严厉打击的决心。在此情况下,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诸多关于野生动植物资源争议性案件的出现,反映出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具体表现在以下3 个方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内容不完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给出的保护范围狭窄,第340 条、第341 条只是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条例,而与野生植物保护相关的只有6个罪名,保护对象大多是珍稀、濒危动植物,虽然表现出了保护的紧迫性,但是并未涉及普通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二是司法困境明显,难以对行为人进行主观认定,或者存在“法、理、情”间的冲突问题。例如,某大学生先后于河南省某村掏了2 窝小鸟,将其卖出后获利1 000 余元,经有关方面认定该鸟类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该大学生由此获刑10 年6 个月。对此,大多数群众表示无法接受。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条例中给出的处罚条款不具有全面性,也缺少客观的价值评估标准。例如,对于污染野生动植物生长环境、非法加工经营野生动植物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条例中并未给出明确的处罚措施。
1.3 信息化程度较低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动态发展的,采用常规的管理手段,无法做到对现有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全面保护。在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背景下,多种信息技术被应用于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提升了管理保护的全面性。然而,当前地方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具体表现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一些自然保护区并未将全球定位系统及其他动态监测技术与传统管理保护措施进行有机结合,导致区域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不足、保护工作的全面性缺失,一旦出现野生动物需要救治或不法分子偷猎、偷挖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情况,难以对其进行及时处理。另外,保护区普遍缺乏专业的数字化技术人员承担信息化系统平台的运行与维护工作。现有人员尽管具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管理经验,但是不具备较强的信息化操作能力,导致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程度不高。
1.4 保护能力不足
基层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能力关系到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对其资源保护效果的提升也有极大的影响。但是,目前许多地方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4 个方面。①尽管划定了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区域,制定了相关保护名录,但食用野生动物、盗挖野生植物现象依然严重。如2017—2018 年黄某在湖北省黄石市非法狩猎野兔、猪獾、斑鸠、麂子和刺猬等野生动物,经地方有关部门确认,黄某所狩猎的野生动物分别为省级保护动物华南兔、猪獾、珠颈斑鸠、小麂及国家三级保护动物刺猬。②滥用森林资源,随意砍伐树木,导致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不断退化、缩减,种群交流严重受阻。③地方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部分人在旅游途中不注重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环境,乱扔垃圾,导致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严重污染。④受专业型人才匮乏、经费投入不足的影响,动植物检疫工作开展缓慢,存在监测盲区,从而加大了重大动植物疫病传播风险。
1.5 保护监督体系缺乏
监督管理体系的建设有利于遏制涉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提升管理与保护水平。现阶段,很多地方缺乏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监督管理体系。这从频繁发生的非法捕捉、捕猎野生动物及随意采挖野生植物的案件中就可以看出。例如,有群众举报浙江省淳安县某男子非法采挖并贩卖自家附近山林的野生兰花,该男子因此被刑事拘留。在此事件调查过程中,地方保护站负责人表示,该县山林面积较大,兰花品种多样,盗挖现象时有发生。这从侧面反映出该县并未针对野生兰花保护采取相应的监督管理措施。倘若该县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工作落实到位,就能及时发现并遏制盗挖现象,而不是被动接受群众举报。
2 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策略
2.1 强化群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意识
地方政府应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宣传组织,面向群众普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让群众认识到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盗挖野生植物是违法的,使其认识到该类资源的重要性。为保证宣传效果,地方基层组织机构可将线上宣传与线下活动进行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发布文章、拍摄视频、直播等当代人能快速接受的方法扩大宣传范围,利用新媒体工具的信息传递优势来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根据地方野生动植物资源特色开展多元化的线下宣传活动。例如,某地鸟类较多,即使是当地人也不能准确识别其种类,那么基层组织可以组织开展“爱鸟周”主题活动,或者与地方图书馆合作举办鸟类知识科普讲座、知识竞赛,并向群众发放宣传册,宣传保护鸟类的知识。再如,某地群众对野生动物疫病防控没有明确认知,基层组织机构可以借助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的直播功能宣传野生动物疫病相关知识,线下组织开展“野生动物疫病防控宣传月”活动,深化群众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认知。
2.2 健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维持物种多样性,让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有法可依,应从立法层面入手,如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野生动植物保护范围。在此过程中,对现有野生动植物资源种类进行梳理,不只是关注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也要将更多珍稀、濒危范围之外的野生动植物纳入保护行列。同时,要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行为界定,充分考虑非法捕猎、运输、出售及购买、食用等多个犯罪环节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威胁,除了遏制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分子行为外,也要增加对野生动植物食客、野生动植物制品持有者的惩罚手段。因为食客的食用需求及野生动植物制品持有者的收藏需求是不法分子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最大动机之一。
为了减少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的认定困境,同样需要在法律中对野生动植物食客、野生动植物制品持有者的破坏行为及处罚情况予以明确界定。从生物入侵的角度看,无序放生行为可能会造成物种入侵,难以判断相关行为人是否犯罪。国家立法部门应当与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海洋保护等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入侵物种名录,明确指出不允许放生的物种,并警示大家不可随意放生。
牟取高额利益是绝大多数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最终目的,对此类犯罪行为处罚不足是我国实施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对此,我国有必要以犯罪对象为标准,针对不同犯罪情节严重程度,配置罚金刑、资格刑等处罚手段,并提高相关惩戒标准。一方面,对不法分子进行经济制裁,拉紧犯罪红线;另一方面,剥夺不法分子的部分公民权利,从源头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
2.3 推进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信息化
信息化是当前野生动植物管理保护的主流趋势。地方政府有必要将无人机技术、大数据技术、3S 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管理保护措施进行有机结合,推进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信息化,为实现全面的管理与保护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以野生动物普查为例,普查是管理保护工作开展的基础,通过调查、了解野生动物生存情况变化,实施针对性管理保护措施。以往,在野生动物资源管理与保护过程中主要采用人工普查方法。人工普查虽然能准确获得某个或某类动物的生存信息,但耗时长、成本高,难以覆盖大面积广阔区域,也易惊扰野生动物。利用无人机技术则恰好弥补了人工普查的缺点。因此,可采用无人机普查与人工普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野生动物普查工作。对于群体生活的野生动物,应用无人机监控其族群活动,实时监控是否有盗猎者非法捕捉、捕杀野生动物;对于通常独立行动的野生动物,以人工手段进行普查,以获得准确的信息。或者运用3S 技术了解相关资源的分布情况,以及不同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栖息地状况,据此合理划分管理保护区域。
另外,自然保护区应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加强信息化管理相关制度建设,包括信息化基础设施管理制度、信息系统平台运作制度、信息安全保障制度、信息风险预警与防控制度等,为管理保护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根据当前信息化建设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引入、培养技术人才,以满足信息化建设的人才需求。
2.4 全面提升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能力
地方政府应从区域规划、森林资源保护、环境治理及动植物疫病检疫4 个方面入手,全面提升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能力。区域规划方面,对于野生动物活动频繁、野生珍稀及濒危植物生长茂盛的核心区域,严格禁止人类活动,防止人为造成的栖息地环境污染,避免人类活动干扰野生动植物生存;对于恢复生态环境的缓冲区域,应加强中、幼林抚育管理,丰富物种多种性,为野生动植物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森林资源保护方面,可加强对森林资源保护的监督,通过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砍伐森林树木的行为。例如,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深入开展“ 2022 清风行动”,专门设置野生植物违法举报电话,发挥群众力量对违法违规砍伐林木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环境治理方面,依托生态旅游、休闲旅游的发展模式,渗透绿色发展理念,将靠近野生动植物生存区域的附近区域环境治理纳入旅游业发展规划。动植物疫病检疫方面,地方管理机构可外聘研究院、高等院校、疫病检疫部门专家面向检疫人员进行重大动植物疫病监测技术培训,更新检疫人员的疫病监测、防控知识,加强专业人才培训,同时加大相关经费投入,优化疫病监测与检疫手段,为疫病监测与检疫工作的落实创造良好的条件。
2.5 构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监督体系
为有效遏制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提升保护能力,地方政府有必要构建完善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监督管理体系。首先,加快相关配套制度的制定进程,针对采挖、狩猎、繁育野生动植物等制定专门的管理制度,并出台致害补偿办法,以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其次,开展专项非法猎杀、非法经营打击行动,积极落实监督管理工作;最后,加强执法建设,厘清各方权责,构建多方参与的执法机制。就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而言,可参照湖南省监督体系建设经验。2018 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通告》中指出,要在5 a 期限内实现全省全面禁止猎捕野生动物。此外,湖南省开展了野生动物保护监督管理系列行动,具体有“百日”“猎狐”“利剑”等专项打击非法猎杀、非法经营行动,并在2017 年末至2019 年末查处相关违法案件740 起,处罚违法分子764 人,共缴获31.14 万件野生动物资源。现阶段,湖南省野生动物保护监督管理体系已经相对完备,并取得了有效的保护成果。
3 结语
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既对维持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平衡有积极作用,而且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我国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涉及保护意识建立、法律法规建设、信息化发展、保护能力提升及保护行为监督5个方面。作为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重要力量,地方基层组织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加强宣传,提升人们的认识,积极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条例,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信息化建设,并提升自身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能力,同时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等,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扼杀在摇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