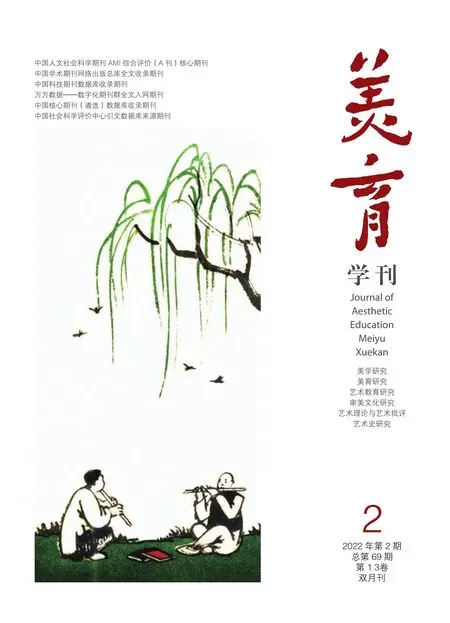温克尔曼论感觉能力:“石膏浆液”“热”及具身性
高砚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1762年,身在罗马的温克尔曼,结识前来“壮游”(grand tour)的里加贵族美少年伯格(Friedrich Reinhold von Berg),在伯格回里加后,温克尔曼撰书信,原题为《献给伯格的意大利之旅》,后改为《论感觉艺术之美的能力及其养成》(äö)。在书信文化颇为显著的18世纪德国,《论感觉艺术之美的能力及其养成》即是献给这位伯格的鸿雁之书,也是一篇严肃谈论如何通过艺术养成美感的理论宏文。它在1763年由德累斯顿Walter出版社印行,于1786年译成法文在欧洲文化界广为流传,赫尔德、歌德、康德等皆对之耳熟能详。赫尔德在《文学批评之林:第四丛》中称此篇实为“滋养一切美学的金矿”。在此文中,温克尔曼提出关于感觉能力的主要理论,其核心观点也正与其艺术批评实践和艺术史学相映照。
一、理想的感觉能力:“石膏浆液”
如果说感觉主义的知觉理论以蜡块比作记忆的印迹,那么温克尔曼则以“石膏浆液”喻指艺术接受中观看者接近艺术作品理想的感觉状态,喻示理想的感觉能力。《论感觉艺术之美的能力及其养成》写道:
对于美的真正感受就像是浇铸阿波罗头部的石膏浆液(flueßige[r]Gips),触摸与包围每一部分。这种感觉的对象,并非冲动、友谊和悦目所称赞的,而是那精细的内感觉所感受的对象。为了美本身,内感官应该摆脱任何意图。
按照Max Kunze的说法,石膏浆液的说法源自普林尼《自然史》第35卷153节关于雕刻家利西波斯的兄弟利西斯特拉图斯首次用石膏模具制作头像的故事。普林尼写道:“西锡安的利西斯特拉图斯,这位利西波斯的兄弟,是率先依着人的面部来制作石膏模具,再用融化的蜡浇铸这个石膏模具来表现人的形象的。”温克尔曼1755年的《希腊美术模仿论》提及通过石膏制作黏土模型:“以石膏来塑形,随后以蜡来铸造。”类似的意象也出现在《希腊美术模仿论》讨论米开朗基罗制作雕塑的段落,米开朗基罗总是用水来确定需要浇铸的雕像,“水几乎能进入眼睛所看不到的部分。它能够敏锐地刻画出细部的抑扬顿挫,并以准确无比的线条刻画出细部的轮廓”。“水”之刻画细部和轮廓的情状,与石膏浆液之浇铸阿波罗头部,如出一辙。
温克尔曼认为,这种“石膏浆液”般的感受力其实是一种“内感觉”。内感觉或内感官的说法,实际上始于英国经验主义的美感理论。英国经验主义提出兼具美学与道德内涵的“内感官”原则及相应的“外感官”概念,柏拉图主义者夏夫兹博里将“内感官”(internal sense)视作反思感官,即我们在精神上赞赏比例、和谐等“神圣”存在的官能,比外感官更为要紧;哈奇生则从知觉和情感(而不是理性)层面对此概念作出了具体规定,他在1728年《论激情和感受的性质和行为,以及有关道德感官的解释》(,)一文中指出外感官和内感官同样重要,内感官是对美与和谐的知觉,尤其涉及内在或精神性的因素。大约受哈奇生影响,鲍姆嘉通在1739年《形而上学》()的“心理学”部分专辟“感官”一节,赋予感觉联系自我与世界的含义。“对我当下状态的表象或感觉(现象)就是对当下世界状态的表象。所以,我的感觉是依据我身体的位置而通过心灵的表象力来实现的。”(§513)鲍姆嘉通认为感觉能力包括内感官和外感官,前者表象心灵状态,后者表象身体状态,两者都是通过表象力来实现的。“我具有感觉能力,即感官。感官表象的要么是我的心灵状态,也就是内感官,要么是我的身体状态,也就是外感官。因此,感觉要么是通过内感官实现(严格地说,是意识)的内感觉,要么是通过外感官实现的外感觉。”(§535)外感官包括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外感官有清晰晦暗之分,有机敏愚钝之分,这取决于器官、知觉对象的状态、相伴随的知觉状态、注意力等因素。跟哈奇生一样,鲍姆嘉通同样重视外感官的能力,因为倘若外感官晦暗,则精神限入昏沉、无能,外感官缺席而仅有内感官的活跃,则会让精神易陷入迷狂,等等。
《形而上学》出版的1739年,温克尔曼正是鲍姆嘉通课堂上的学生。温克尔曼于1738年入哈雷大学,当时鲍姆嘉通已任教。鲍姆嘉通早在173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关于诗的沉思录》中提出美学即“感性认识的完满”之命题,又于1739年的《形而上学》()专辟一章讨论“感觉”。拜厄泽(Frederick C.Beiser)认为,作为一名鲍姆嘉通课堂上忠实的学生,温克尔曼日后著述中的某些议题其实可以追溯到鲍姆嘉通的教导。
与哈奇生和鲍姆嘉通一样,温克尔曼也将外感官规定为身体性,内感官为精神性。但温克尔曼几乎离弃了哈奇生与鲍氏将内外感官相提并论的做法,仅对内感官倾注了较大的理论热情。《论感觉艺术之美的能力及其养成》描写外感官只寥寥几笔,对内感官的颂扬及阐发则不惜浓墨华章。温克尔曼承认美的感觉能力由外感觉(äußeren Sinn)和内感官(innere Sinn)组成,但“外感觉是工具,感觉能力本身其实是坐落于内感官”。“前者务必精确,后者务必敏感而精微。”他写道:
如果说外感官是精确的,那么,我们期望内感官则是相应地完满(vollkommen)的,因为后者是第二面镜子,这就像我们可以从侧面感知外表中最本质的东西。内感官是对外感官印象的表象(Vorstellung)和形象化(Bildung),用一个词概括,即感觉(Empfindung)。然而,内感官并不总是与外感官相应。这就是说,内感官的敏感性达不到外感官的精确程度,外在感官是机械地工作的,而内感官却是精神过程。
外感官通过身体器官摄取信息而形成印象,但不具有表象能力;内感官则是对外感官印象的加工,包括表象和成形。外感官的运作是机械的,内感官则是精神活动。外感官和内感官是一种镜像关系,内感觉是对外感官印象的反思。Ingrid Kreuzer解释说,外感官的知觉促进了内感官的知觉,表现为精神形象的有机诞生,观众由此重复了艺术行为的过程。在这个通过内感官向内触及的过程中,Kreuzer认为观看者意识到他自身的实存,因此返回到自身的精神中去。在这个意义上,反思是双重的,既是对感官印象的反思,也是对自身精神的反思性回忆。作为一种反思的、精神性的感官,内感官同时通达世界的和精神的精微之处。
温克尔曼提出,为了“完满”地感觉,内感官“须是迅捷的(fertig)、精微的(zart)、形象的(bildich)”。这种感觉能力是对外在感官摄取的整全印象进行把握的一种能力,它应是迅捷的、快速的(schnell)。原因在于,第一印象是先于反思的、模糊不定的团块,一俟这印象团块出现,就将它纳入心灵;第一印象是转瞬即逝的,仿佛兔起鹘落之间,内感觉若不疾速反应便无以捕捉。温克尔曼认定,“整体”是先于部分而浮现的,而不是由“部分”逐渐综合而成。在一瞬之间胸纳整体印象是标志性的感觉能力。“任何企图从部分走向整体的人,就会暴露自己无非是一个语法化的头脑,他的内心很难唤起一种对整体的感觉和欣悦神迷。”
这种感觉能力也是柔和的、精微的。温克尔曼接受那种美在诸部分之和谐的观念,并进而界定“和谐”的形态:“和谐的完满形态是柔和的起伏,由此均匀地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并以一种柔和的方式引领我们。”感觉唯其柔和才可接纳和谐之美的微妙运动,唯其精微才可把握细微之处,就像是贴紧对象物而悉知对象物的轮廓、肌理、褶皱和全部微妙差异。理想的内感官不应是激烈的,“激烈的感觉越过中间的过渡部分,而径直走向结果;……激烈的感受也损害观照和对美的享受,因为它过于短促:一下子就将我们引向我们本应逐步体验的地方”。如此,温克尔曼赞赏平静的心智,因为“过于热情的、肤浅的心灵难于发现美”。
内感觉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对所观照之美的生动的形象化(Bildung)能力。这是基于内感觉因其“迅疾”而获取整体印象,因其“柔和”精细而储存细节性质,由此,从外感官得到的第一印象获得呈现,又栩栩然、生动有力地成形,即在感觉中呈现生动而清晰的图像。可以说,内感官是对于总体印象的充满热情的把握,是观看对象时的一种亲密、柔和的移情知觉,是一种将印象呈现为生动图像的能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石膏浆液”比喻。Dimitri Liebsch恰切地指出,它其实道出了温克尔曼论感觉能力的核心理论。Liebsch写道:“围绕石膏浇铸件的液体,仿佛对应于拥抱事物的‘精微’(zart)感觉。灌注和被灌注,是‘疾速’(schnell)的对应物,感觉迅疾括住了作为整体的物体,而不是基于各具体部分的理性分析。温克尔曼认为,在此基础上,接受者获得了某种具体的呈现,即‘被观照之美的生动成形’。”
至此,笔者尝试将温克尔曼的“石膏浆液”之喻转写成审美经验的现象学式描述:
理想观者在接近艺术作品之际,是漫无目的,别无他图,也不受欲望、道德、愉悦的左右的,此刻,惟有体内的精微的知觉、一种幽暗的精神在静悄悄地运作。这知觉,是精确的,仿佛目光完整地触摸作品中所现之物的轮廓,这知觉又是细微的,仿佛爬进对象全部肌理,如同水无知无觉地渗入物体的空隙、褶皱、一切的细节,其所及之处又远非目光所能至——这暗示着对象物并非仅仅只是轮廓表象,或是说允诺了不可戳破的内部。于是,这观者仿佛在心理上全方位地、立体地“重造”了艺术家创造的作品,又在无限接近密闭的轮廓之际遭遣返,返至自身,而产生自身的精神图像。
二、对象物之“热”
石膏浆液之“包裹”“触摸”的想象性动作暗示审美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知觉主体对于对象之实存(阿波罗头像)并非“漠不关心”。Charlotte Kurbjuh认为,它是表示出一种顺从于物的感受力,一种突显移情的感受力,是对移情概念的合法化。Gert Ueding则认为,“这一比喻强调了一种对美的全方位的塑造力,后者是通过移情性的触摸、通过同化而被唤醒的”。
审美活动中的这种移情现象及其包含的主客体关系,实际上可见于《论感觉艺术之美的能力及其养成》开篇的隐晦定义:“感受艺术美的能力,是一个同时包容人和物、包含者和被包含者的概念,而我视这两者为同一。”Michael Baur就此解释道:“温克尔曼似乎指出了一种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全面包容的、非对象化的杂多的统一。”对于主体而言,对象不再只是对象化的存在,而恰恰与主体具有某种切近关系,比如移情。
“包裹”“触摸”也显示出一种超越于眼睛的、形式的感受力(就像石膏浆液的流动所至实则超越了眼睛所见)。温克尔曼并不是在审美形式主义上谈论艺术接受。在他看来,那些可以用目光“包裹”眼前对象的善感之士,甚至可以感知到其“热量”的散发。他毫不顾忌地嘲笑感受迟钝者,对于他们,“艺术美犹如北方的日光,发光却不发热(leuchtet und nicht erhitzt)”。冬季北方日光的热力如何惨淡而不具有涉身能量,是从小生长在欧陆北纬50度以北萨克森地区的温克尔曼深有体会的。在他看来,善感之士不仅感受视觉对象物的“光”,也能感知那些与自身形成涉身性关系的“热量”,即超越眼睛的感觉。在“包裹”对象物的同时,也被它的能量所裹挟——在此情形下,身体是被搅动的、被影响的、被刺激的,是与对象物交互的。如此,“热量”说直指艺术接受的具身性。
温克尔曼之超越形式主义立场也可见于他对原作与复制品的细微辨析之中。他在《论感觉艺术之美的能力及其养成》中写道:“复制品总是以缩减的形式被复制,它只是影子,而不是真实本身。荷马和他的最好翻译之间的区别,也及古代艺术品、拉斐尔作品与其复制品之间的区别。后者是死的形象,而前者向我们说话。如此,艺术中的真实而完整的知识只能通过对原形象自身的静观而获得。”原作之于复制,正如真实之于影子。原作是有生命的,是与观众产生交互的,可传递气氛的,或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是有光晕的。而复制品,哪怕是在形式复制较为完全的情况下,也会由于肌理、材料、尺寸等的改变,致使“热量”削弱,故是“死”的形象。从审美接受上看,唯有“活的”原作,较为可能使观赏者产生交互感和具身化的“热量”体验。
鲜有学者提及温克尔曼与18世纪法国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关系,其本人也极少言及法国唯物论。其实,温克尔曼关于审美效果的说法,与布封、霍尔巴赫等唯物论者以身体变化界定感觉的学说颇有相通之处。18世纪的法国机械唯物论探求精神的身体基础,以霍尔巴赫为例,他在1770年的《自然的体系,或论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法则》中认为,感觉活动也是一种身体内部的运动,感觉“就是被触动,并且意识到在我们身上正在进行的一些变化”。霍尔巴赫一方面承认人的机体组织的能动性,在无外力触动下也可以有感觉活动,另一方面外在事物(包括艺术)在人的有机体上产生了某种刺激和效果,包括感动、泪目。按此逻辑,温克尔曼所说的“热”也正是身体受到艺术作品之影响而“被触动”的结果(类似于斯宾诺莎所说的“情动”)。霍尔巴赫还写道:“一个人,如果雄辩、艺术的美、一切使他感到新奇的事物,都能在他身上引起很强烈的运动,我们就说他有敏感的灵魂。”温克尔曼同样认为,艺术作品能否引发身体性的反应和运动(“热”是一种身体内部细微运动的结果),也是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敏感性的标准。
温克尔曼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在理论上申明,身体的外感官不过是在机械地摄取外在信息罢了,另一方面他的内感觉经验描述分明显示,身体实际上参与着审美判断并被动地接受对象的微妙影响。他接受了鲍姆嘉通理性主义传统之下的身心对立、内外感官有别的论说,但他描述的内感觉经验却显然渗入了身体性反应(即使这种身体反应不是经由明确的外感官通道,而是一种整体的身体效果)。后者与法国唯物论同气相求。
三、身体与具身性感知
艺术感知的具身性,屡现于温克尔曼本人的艺术评论中,比如触觉因素在视觉经验中的在场。温克尔曼承认触觉在审美品评中的有效性。他注意到,古物收藏家阿尔巴尼主教(他在罗马的保护人)是天生的弱视者,但他“可以通过抚摸与触觉,分辨钱币上刻制的是哪位帝王”。温克尔曼本人也拥有一双“触摸之眼”,并潜在地以可触性为标志谈论作品之高下。比如,最好的希腊雕塑往往具有可触性的表象,眺望楼的赫拉克勒斯雕像,“就像这些愉快的峰顶由柔和的坡陀消失到沉沉的山谷里去,——与其说它们是对我们的视觉显示着,不如说是对我们的触觉展示着”。又如阿波罗雕像,“肌肉是如此光滑,如同融化的玻璃吹成了几乎不可见的波纹,它与其说向视觉显现,不如说向触觉显现”。面对此番艺格敷辞,赫尔德言道,温克尔曼的视觉是触觉的还原与代替,他的视觉是被触觉介入的视觉,“那将开始收集的眼睛已不再是眼睛,而是手。知觉转变为此刻的触觉”。在赫尔德看来,温克尔曼是将雕塑立为触觉艺术的理论先驱,也是感觉之具身性的理论典范。
舒斯特曼在一篇近文中写道,“在温克尔曼这里,身体并非笛卡尔式的机器或有待独立的心灵来推动的无精神的物理有机体,而是一具有感觉的、有意图的、活的、交互的、文化的、思想的身体:一个交互的身心实体,本质上既被其周围的物理环境(包括气候)塑造——从中吸收能量和生命气息——也进一步被社会—文化环境所塑造”。身体既是与环境交互的结果,具身性的感知也同样具有其风土性。在1764年出版的《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借取18世纪盛行的以孟德斯鸠和杜博斯为代表的气候论,探讨自然地理对精神方式的影响,特别是气候如何影响人的感觉状态。
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1748)中借鉴了同期神经学的说法,认为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精神特点和内心情感迥然有异。由于神经反应的作用,生活在寒冷气候的人对愉悦和痛苦的感觉,其灵敏度不及生活在温暖和炎热地区的人们。孟德斯鸠写道:“在炎热地区,皮肤组织松弛,神经末梢都呈打开状态,极小物体的极小动作也能感受得到。在寒冷地区,皮肤组织呈收缩状态,乳头状物质受到压缩,神经的小乳凸稍许有些麻痹,只有最强烈和由全部神经传递的感觉才能到达脑子。但是,想象、味觉、感受以及勃勃生气,都依赖这些不计其数的微小感觉。”杜博斯在《关于诗和绘画的批评性反思》(éé,1719)中提及,过度的寒冷使大多数人的想象力冻结,炎热气候的温度激发精神以及身体,寒、热和温三种气候中,以温带对精神发展最有利。
跟孟德斯鸠和杜博斯一样,温克尔曼同样认为气候影响人的体形,认为“空气对体形的影响是可感的、可理解的”,气候在影响人的身体神经的同时也塑造了人的感知力。《古代艺术史》言及,希腊四季的温和气候塑造了轻快、敏感的神经,当这气候作用于精细编织的大脑,便瞬即发现对象的性质,尤其专注于去沉思对象的美。希腊(以及意大利)的大自然在最充分地培育出美的人体的同时,也给予他们最完善的感受力,而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比如德国民族,则人体形态与感知力正好相反。《关于〈希腊美术模仿论〉的解释》同样赞道:“希腊人仿佛是由一种精细的材料制作。神经和肌肉富有弹性、敏感,促发身体最灵敏的运动,一种敏捷、灵活的愉悦自行显现,快乐与友好的本质伴随而来。”在温克尔曼看来,气候影响感知力还在于,气候通过塑造语言发声器官进一步影响感知力。特殊的气候塑造特殊的语言发声器官,寒冷地区的人的舌尖僵硬而慢滞,语言多单音节和辅音,而处于温暖地带的希腊人的语言则元音、辅音相交替,且元音甚为丰富,从而造成了一种柔和、微妙的机制,希腊语还善于通过声音和语言的序列来表达事物的形式与本质,故此,这种语言思维使得希腊人先天拥有了把握概念和形象的感受力。
卢梭在《爱弥尔》(1762)中呼吁,为了思考,我们有必要锻炼四肢、感觉、感官,这是智力的工具;温克尔曼同样意识到身体训练绝非精神发展的障碍。在他看来,希腊社会提供了理想的身心和谐图景:重视身体教育的希腊人,在身体最具活力的青春期便充分吸收外界印象并沉思默想。“希腊人在其青春期就已是沉思者,这比我们通常开始思考起码要早二十年。他们在被身体活力点燃时便运用心智。……少年的思想像是温柔的树皮,保存、扩大着上面的切口。”希腊人在身体灵敏之时即培育并发展出思想与感受交融的精神能力。柏拉图的对话常常始于体育场,为培育高贵的完整的人,身体训练乃是哲学练习的一个环节。Liebsch指出,“对于温克尔曼而言,形体与思想方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循环因果关系或控制论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关系”。
四、结论
18世纪中期,在启蒙经验主义的影响下,欧洲知识界开始寻找认知和精神的心理基础和生理基础,也因此被称作是“人类学”世纪。此时,受莱布尼次的“连续性”概念启发而试图在身体与精神之间建立平滑过渡的计划并不少见。如,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汲汲于寻找某个连接身体与精神的官能(布封在《自然史》中建议以脊椎代替大脑),瑞士医生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的活力论生理学以神经现象为切入点来证明身心连续性。在此意义上,温克尔曼的感觉能力风土论算得上是18世纪人类学计划的一部分。此外,他的内感觉理论兼有18世纪理性主义和唯物论感觉主义的双重性。他的艺术经验表述中展示的具身化感知和触感知议题,虽然在其同时代中并不醒目,却成为后世的一些艺术史家(如伯纳德·贝伦森)和神经美学的探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