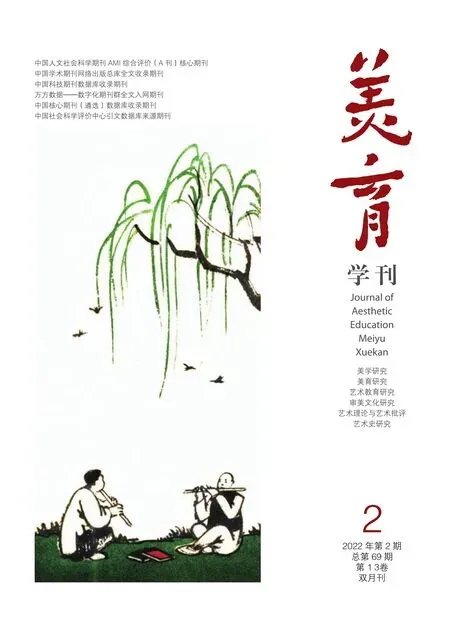“艺术是生命的表现”
——论刘海粟的艺术形上学思想
冯学勤
(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从尼采所高扬的现代艺术形上学思想看,艺术与生命是一起被放置在最高价值的王座之上的,因此现代艺术形上学实际上就是生命形上学,二者的一体性源自创造活动,生命的一切创造均为泛化了的艺术,而艺术的一切创造更为生命的直接显现。当然,现代艺术形上学的这一内核实际上在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这一代学人处并未充分展开,尽管他们奠定了现代艺术形上学思想的本土基础,然而在比他们晚一辈的学人处却屡屡见到,如朱光潜、宗白华、李石岑和刘海粟等人。刘海粟既深受蔡元培影响,同时与宗白华和朱光潜也多有交往,其艺术形上学思想形成的外部原因,与这些交往所产生的相互激发、相互砥砺存在关联。如刘海粟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艺术及美术的文章多发于《学灯》,而宗白华其时正是该杂志的编辑;20年代末刘赴欧洲游艺,与朱光潜亦曾同学;蔡元培则不仅仅是刘海粟美术教育事业的直接支持者,其“以美育代宗教”思想更是对刘海粟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毕生都成为这一思想的拥趸。
刘海粟的艺术形上学思想,可以其“艺术是生命的表现”一语概括。这一思想本身,是艺术作为启蒙、救亡的工具与现代个体信仰所结合的产物,其形成的过程及内在思想因素因而是多方面的:既来自一个民族危亡、社会黑暗的年代之中对本国艺术和文化传统的沉痛反思和深切批判,因而产生叛离传统、推陈出新之启蒙使命,也在这种过程中深入触及到了丧失传统文化之荫庇的现代个体的价值空洞,更何况传统之本土性和西方之现代性的张力及裂痕始终存在。因此,“艺术是生命的表现”一语,实在是刘海粟本人传统—现代张力之化解、中—西裂痕之弥合、个体意义之寻获和社会价值之锚定的最终结论,也是其思想之路与艺术之路相融合的最终结果。与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这些人所不同的是,刘海粟并无学者身份,也没有在学术上直接取经于西方理论的经历,而主要是一位将哲思与创造一体融合、观念与经验相互激发的艺术家,因此这种思想的产生虽然具有一些外部因缘,但是自身的寻求和探索显得更宝贵。
一、“传统的叛徒”与“世俗的罪人”
1930年,刘海粟在欧游途中称:“我们本来就是传统的叛徒,世俗的罪人;我既不能敷衍苟安,尤不能妥协因循。很愿意跟着我内部生命的力去做一我是一个为人讥笑惯的呆子,但是我很愿意跟着我生命内部的力去做一生的呆子,现在的中国就是因为有小手段、小能干的人太多了,所以社会弄到那样轻浮、浅薄。”此处,刘海粟以“传统的叛徒”和“世俗的罪人”自况,显示了一个文化革新的战士的姿态;同时,他又两次提到“内部生命的力”,显然这点构成其勇做“叛徒”和“罪人”的内部信念支撑。而这种只遵循生命之力的“呆子”,却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那些汲汲于私利的世俗之人,这些人在他看来显然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刘海粟的自况,所指是他在上海美专采用人体模特之时所引起的争论及对他的诟病。在《人体模特儿》中他称:“今日之社会,愈是奸淫邪慝,愈是高唱敦风化俗,愈是大憝巨恶,愈是满口仁义道德。荟蔚朝脐,人心混乱,已臻于不可思议之境域矣。试一着眼,环绕于吾人之空气,浊而浓郁;虚伪而冥顽之习惯,阻碍一切新思想;无谓之传统主义,汨没真理,而束缚吾人高尚之活动。……数年来之刘海粟,虽众人之诟詈备至,而一身之利害罔觉,为提倡艺学上人体模特儿也。模特儿乃艺术之灵魂,尊艺学则当倡模特儿。愚既身许艺苑,殉艺亦所弗辞,迕时滋诟,于愚何惧?”此篇表现出刘海粟为弘扬美之艺术而不畏流言、不顾利害之勇气——他甚至愿意“以身殉艺”。刘海粟招致保守人士的攻击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艺术叛徒”“教育界蟊贼”实可代表一般社会公众对刘海粟之认识,刘海粟后来所谓的“传统叛徒”和“世俗罪人”实从此演变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刘海粟此处提出“模特儿乃艺术之灵魂”这一激进命题,这一命题如若要成立,势必要召唤一种更加深层的价值观进行佐证。刘海粟称:
美术上之模特儿,何以必用人体?凡美术家必同声应之曰:因人体为美中之至美,故必用人体。然则人体何以为美中之至美?要解决此问题,必先解决美的问题。何为美?美是什么?此乃古今来所悬之一大问题,决非一时一人之力所可解答者。虽时历数千年,经贤数百人之探讨,尚未能有一确定之解答。虽然,多数学者之间,见解各异,要亦一共同之主点焉。共同点维何?即通常所谓美之要素:一为形式(Form),二为表现(Expression)。一切事物之所以成为美,必具此形式与表现也。所谓美之形式,乃为发露于外之形貌。美之表现,为潜伏于内之精神。故形式属于物,表现则属于心。心理学之术语,前者是感觉,后者是感情或情绪。人体乃充分备具此二种之美的要素,故为至美。
无疑,刘海粟的这一佐证在于美学理论本身,审美价值为人体模特之必要性提供合法性意义,在他看来人体为至美之物,实可在内之情感精神、外之形式状貌上共见,感觉与感情融合一体之对象,乃美术家之共识。然而这种刘海粟所认为的共识只能在西方绘画的语境中成立,本土绘画传统中并无人体写生之先河,身体之呈露在本土绘画之中并非美的或高明的对象,而是野蛮的象征。因此,这种观点本身也代表了刘海粟所自况的“叛徒”特征,即叛离中国艺术传统本身。
显然,刘海粟的这些辩解想要在保守的社会话语圈层中获得支持并不容易,更何况其间还有与传统美学和艺术观念之龃龉。于是,向异域文化寻求艺术偶像、获取精神支撑就成为必然之举。因此,他又写了《艺术叛徒》一文,将凡·高树立为自己的精神偶像。该文称:
非性格伟大,决无伟大的人物,且无伟大的艺术家。一般专门迎合社会心理,造成自己做投机偶像的人,他们自己已经丧葬于阴郁污浊之中,哪里配谈艺术,哪里配谈思想……伟大的艺人,只有不断的奋斗,接续的创造,革传统艺术的命,实在是一个艺术上的叛徒!
刘海粟十分自豪于“艺术上的叛徒”,显然是对之前社会诟病的一种回应。他又明确地提出了“革传统艺术的命”,显然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激进启蒙主义路线相合,在思想观念上他可谓鲁迅的同路人。此文中,他树立凡·高为艺术叛徒之首,称凡·高接受不了学院派的美术技法,故而叛离传统,且成为一名艺术的殉道者。最后他称:“狂热之凡·高以短促之时间,反抗传统之艺术……其画多用粗野之线条和狂热之色彩,绯红之天空,极少彩霞巧云之幻变,碧翠之树林,亦无清溪澄澈之点缀。足以启发人道之大勇,提起忧郁之心灵,可惊可歌,正人生卑怯之良剂也。吾爱此艺术狂杰,吾敬此艺术叛徒!”在刘海粟笔下,凡·高被描述为一个叛离传统艺术的殉道者,一个品格高洁、意志热烈和坚韧不拔的文化战士,其意义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仅只是一般启蒙意义,也寄予了一种超越性的价值意涵。
二、作为社会启蒙的艺术
艺术作为启蒙和救亡的武器,以及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是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思想的基本性质。这二者之间本来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联系: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现代思想者,他们对艺术之价值论的认识,总是先起于对民族危亡之思。在这种忧思之下,方兴起通过文艺以及教育启蒙社会、改造国民性之志向;此革新之志向既然屹立,则必成安居于旧时日、旧传统、旧文化中之俗流之敌,必须获得一种持之以恒、孤注一掷的生命信念,方可对抗俗世浊流,并获得思想和事业之结果。对产生艺术形上学思想的第二代思想者而言,最终一步是,获取不移之生命信念最终转变为对生命本身的信念。刘海粟亦不外于此进程。早在1912年,刘海粟与乌始光、汪亚尘等人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在《创立上海图画美术院宣言》中称:“我们要在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苦恼,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恰是艺术的价值所在,而“艺术的责任”在刘海粟看来,分为消极和积极的两点:为苦难之中的中国民众提供慰藉(“救济苦恼”)为消极含义,“惊觉一般人的睡梦”即积极的思想启蒙。
在1918年所作的《江苏省教育会组织美术研究会缘起》一文中,刘海粟对艺术的功能有了更加深入的阐述。该文开篇即称:
宇宙间一天然之美术馆也。造物设此天然之美术以孕育万汇,万汇又熔铸天然之美术,以应天演之竞争。是故含生负气之伦,均非美不适于生存,而于人为尤甚(如动物之毛羽,植物之花,必美丽其色;它若蛛网、蜂窝及鸟巢之组织构造,均含有美的意味)。
对艺术社会功能的认识总是来自对其起源和发展的认识,在刘海粟看来自然即美的艺术的来源,美的最初来源是自然,而美则是自然进化的结果,“非美不适于生存”则将美与生命发展的法则捆绑在一起,而生命之美首见于视觉之形式,故而美术之价值已与生命之价值相融合。继而刘海粟又勾勒了人类的发展史与美的艺术之发展史同步,从鸿蒙之初到现代,人类的发展与美之艺术的发展紧密相关,并称:“美术者,文化之枢机。文化进步之梯阶,即合乎美术进步之梯阶也。物穷则变,所穷者美,所变者亦美也。美术之功用,小之关系于寻常日用,大之关系于国家民性。”对美的艺术之性质的理解,为文化发展的核心;对其功能的理解,下关百姓日用之道,上达国家发展和国民性格。
美的艺术如此之重要性,而刘海粟反思本土文化传统显露出其批判锋芒:“吾国美术,发达最早,惜数千年来学士大夫崇尚精神之美,而于实质之美缺焉不讲,驯至百业隳敝,民德不进,社会国家因之不振。”“士大夫崇尚精神之美,而于实质之美缺焉不讲”,此语说中要害。正如其所言,中国传统重心性修治,重内在体验和内在超越,尤其是宋明心性之学兴起之后,士大夫一方面将文艺贬斥为“小道”或“玩物丧志”,另一方面是沉思体验及其技巧在士人之中的广泛普及,一种事关“精神之美”和内在体验的愉悦技术已然兴起,通过从佛、道二家处得来的静坐方法,儒家士人将沉思经验技术化和普及化,并在此过程中对外向的、视觉化的文艺审美活动加以贬斥,那些同样能够起到“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的文艺活动,也更侧重于精神体验或境界提升,如文人画、古琴等,莫不如此。的确,心性传统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深邃和立体,并造就了一种追求内在体验和人生境界的文艺品格,却对文艺类型和审美体验本身的多元化——尤其是刘海粟所说的建立在科学以及实用之肯定基础上的“实质之美”妨碍甚大。需要指出的是,刘海粟的这种认识,是在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美学思想论述之中均难以见到的,具有来自其现代美术家身份的卓见,上述诸人在强调审美活动的心灵品格或精神特性的时候,往往忽略视觉、科学和实用意义上的“实质之美”。
他进而称:“今旷觏世界各国,对于美育莫不精研深考,月异日新,其思想之缜密,学理之深邃,艺事之精进,积而久之,蔚为物质之文明,潜势所被,骏驳乎夺世界文化而有之。”作为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接受者、美育实践的开拓者,刘海粟充分认识到了审美教育的社会启蒙价值,认为西洋物质文明的发达,离不开对美育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使思维品质、学术能力和文艺事业同时发展,在文化积累的过程中奠定物质文明的基石。事实上,美育在中国现代时期,主要承担的正是思想启蒙的功效,而这种启蒙的主要的特性是针对人格教育的感性启蒙,然而刘海粟对美育尤其是对“实质之美”的重视,同样具有着眼于社会实践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理性因素。此外,刘海粟对美之艺术的功能性认识,也是十分全面的,这种全面的认识尤其在《致江苏省教育会提倡美术意见书》之中体现出来。他称:
窃维今之时代,一美术发达之时代也。西方各国之物质文明,所以能照耀寰区而凌驾亚东者,无非以美术发其轫而肇其端。盖美术一端,小之关系于寻常日用,大之关系于工商实业;且显之为怡悦人之耳目,隐之为陶淑人之性情;推其极也,于政治、风俗、道德,莫不有绝大之影响。
“寻常日用”与“工商实业”,均为美的艺术的实际社会功用,“怡悦耳目”与“陶淑性情”换言之即怡情养性,为美之艺术的传统美育功能,“推其极”则为广义的社会文化功能。显然,这里的阐释则更具有概括性。
刘海粟对艺术功能和价值的阐述,除了事关实用和实利之外,总是与美育的功能相结合。1919年11月,他率学生从上海前往杭州西湖写生,留下了《寒假西湖旅行写生记》一文,其中不仅再度提到美育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还自创了关于美育的新说法,即“无美感即无道德”。文中记载师生一行人在冬日西湖边写生,路人要么以为是测量局进行勘探,要么以为是上海来的画师画“月份牌”以赚钱,要么以为一行人绝非国人而是日本人,这些反映表现了当时一般社会民众对美术以及美术家本身的隔膜。对此,师生遂发如下一段感慨称:
周生曰吾国人对于美育知识之幼稚固不必论,而社会之轻视美术于此可证。故青年学子有志于此者甚多。辄为其父兄所阻,以余所知者已不少矣,先生将何以设法提倡之?余曰美感本是人之天性,故予创“无美感即无道德”之说。但我国向轻视美育,一时自难转移。但苟有人能提倡以正当之学说,表美育之效用,不数年间即可收效。盖爱美既为人人固有本性,苟非误用其美,即可为人尊重。
刘海粟的学生周伯华问其如何就美术之价值向一般社会公众进行启蒙,刘海粟遂提出其“无美感即无道德”之命题。尽管刘海粟本人除了此处外,并未见他在其他文献中提及,然而仅就此寥寥数语我们即可了解其思路。“无美感即无道德”这一命题的前提,在于“爱美既为人人固有本性”,若据中国心性文化传统之主流即人性本善,那么此本性即不可违逆而只可积极培育和顺势发展,返诸《中庸》可获其支撑,所谓“唯天下至诚可尽其性”,若违逆固有之本性则何以至诚?无以至诚又何来道德之基础?故而当守《中庸》所谓“率性之道”,进而修美术之教以顺“天命之性”。更何况,刘海粟已将美术之起源与人类之起源相合一,美感中当然含有对生生之肯定,而生生在儒道传统中为“天地之大德”,对此天地之大德之体验,以及由体验所生之感性化的德性范畴即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第一原则——“仁”,所谓恻隐之心不过是惜生爱生之心罢了。因此,尽管作为艺术家的刘海粟未能充分展开这一命题,然而这一命题毫无疑问是成立的。在乐观的刘海粟看来,从这种学说的普及出发,“不数年即可收效”。
这种面向社会进行美育启蒙进而彰显艺术价值的思路,即便到了国族危亡的特殊历史事件时,亦为刘海粟所秉持。1919年巴黎和会割让青岛等地给日本,遂引发五四运动,对此他刊登《救国》宣言称:
青岛问题失败,国人骚然,莫不曰:速起救国!速起救国!顾欲证明此二字不为无价值之空言,当以何事为根本解决?必曰:新教育,振实业,利民生,促军备、政治之改善。予曰:否!吾国之患,在国人以功利为鹄的,故当国者,只求有利于己,害国所不恤也;执社会事者,只求有利于己,害社会所不恤也;虽一机关一职务莫不如此。其人非不知爱国,非不知爱社会也,特以其鹄的所在,无法以自制耳。故救国之道,当提倡美育,引国人以高尚纯洁的精神,感发其天性的真美,此实为根本解决的问题。
作为蔡元培美育理论的信奉者和宣传者,刘海粟显然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美育救国论”。他认为实业救国也好、教育救国也好,都未能抓住最为根本的问题,这一最为根本的问题无疑在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早就已经意识到,甚至连戊戌派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信奉——无非他们所着眼的范围较小罢了。无他,正人心而已。而这个老生常谈的思路正是中国心性文化传统所打之深刻烙印,蔡元培那段从国家盛衰到外物印象的话正是明证;而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沪上炮声隆隆之时之所以可以对美娓娓道来,也无非是因为“谈美”可以“一新人心”。无疑,在艺术的实利价值与精神价值之间,刘海粟必须更多地强调精神价值,这也才能在救亡之急迫性面前获得发展艺术与审美事业的合法性论述。
1923年,在《艺术周刊》的“创刊宣言”中,刘海粟称:“我们确信‘艺术’是开掘新社会的铁铲,导引新生活的明灯,所以我们走上艺术之路,创造艺术的人生,组织这个团体。”“铁铲”表征着艺术之于社会的工具性价值,而“明灯”自然是社会启蒙的象征。艺术之于社会、之于新生活、之于救国的价值,与艺术之于革命的价值分享同样的启蒙逻辑。在1936年的《艺术的革命观》一文中,刘海粟称中国的革命从来没有彻底过,革命要想成功,首先要经历艺术的革命或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他说:
我不反对理科,不反对工科,也不反对职业教育,不过这些都是属于物质的,精神的也非要注意不可,做一个人,有时他的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一方面要解决口,一方面也要解决耳朵和眼睛,耳眼完全根据于情感方面的;换言之,是精神方面的。我们可以简单地明了艺术是什么东西了。故不仅是吃饱穿暖就算了。在这时,艺术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晶,表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同时表现一个民族的特性,凡是一个民族的强盛,一定先经过一番艺术的运动。中国也在走这条路。
此处,艺术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已被推上了极致,即成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前提。如果革命的目标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那么在刘海粟看来,艺术的革命才是最终的、最彻底的一场革命。
三、作为个体和社会之新信仰的艺术
现代艺术形上学的根本要义,是要树立起以艺术为核心的新信仰,艺术的超越性价值——亦即超越一般的愉悦耳目、怡情养性和社会实利——的价值正在此处。这种价值的树立和宣扬,对于本土而言,与西方相似,首先起到的是一个在传统价值失范、封建文化解体的时代,为无可皈依的人提供新的最高价值坐标的作用。而这种因信仰而产生的慰藉功能,首先是一批在思想、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勇敢反叛者自我激励、自我肯定的结果:无论如何,传统价值的解体本身是现代性的产物,尽管现代性从中汲取了养料;为克服解体之后的价值真空和虚无主义,新的信仰势必在那些叛离者、锤击者和摧毁者那儿重新建立起来。这种对艺术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内核即对生命本身的信仰。换言之,艺术形上学与生命形上学实为一体。
这种信仰在刘海粟那里,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发表于1922年的《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一文中,刘海粟再度回顾了使用人体模特的事件,并在此前“艺术的灵魂”这一判断基础上,给出了更加深入的价值依据。他先是称:“我们敢在这样尊崇礼教的中国,衣冠禽兽装作道德家的社会里,拼着命去做这一件甘冒不韪的事,实在因为与我们美术学校的前途关系太大。所以我们既然有了自己的认识,就当然根据自己的信条去做,任何社会上的反对,也就不在意中了。”此文的回顾,并无太多针锋相对的论辩气味。正如他所言,“既然有了自己的认识”,树立起了“自己的信条”,也就对社会上的反对之声不在意了。对于这一信条,刘海粟说:
我们要画人体模特儿的意义,在于能表白一个活泼泼地“生”字,表现自然界其他万物,也都是表的“生”,却没有人体这样丰富完美的“生”。因为人体的微妙的曲线能完全表白出一种顺从“生”的法则,变化得极其顺畅,没有丝毫不自然的地方;人体上的颜色也能完全表白出一种不息的流动,变化得极其活泼,没有一些障碍。人体有这种生的顺畅和不息的流动,所以就有很高的美的意义和美的真价值。因为美的原理,简单说来,就是顺着生的法则。
毫无疑问,此“生”即生命所带来之生气。刘海粟之所以认为人体为艺术之灵魂,全在于人体之曲线、颜色可表现出生命之气息和生气之流动,作为美术的绘画正是以线条和色彩表现生命之形式——美的原理就是“顺着生的法则”。
需要指出的是,刘海粟这里的“美术”,与王国维更早之时就已提到的“美术”意涵相同,也即一切“美的艺术”之总称,而非专指造型艺术。在发表于1923年2月《学灯》之上的《为什么要开美术展览会》一文中,刘海粟不仅指出了“美术”的概念及分类,而且还提出了美的艺术的本体性论断。他说:
美术是什么?从美学说,是人为美的一种,又可以叫做艺术美,人造物体的美,人为现象的美。以表现形式的不同,故又有空间美术、时间美术、两间美术、综合美术之别。从形象方面解释,又可别为抽象的与具体的美术。从感觉方面说,又可别为听觉的与视觉的美术。从空间美术、具体美术、视觉美术狭义的说,又可以分做纯粹美术与工艺美术,前者是非实用的,后者是实用的。
对于刘海粟而言,艺术的本体是从纯粹的美术中提炼出来的,因为工艺美术是受目的所支配的。他称:“纯粹的美术,是自由不受束缚的,不像工艺美术之有目的,为一定的目的所制约。通常就狭义言,则以绘画、雕塑为纯粹的美术,现在我们所要求表现的就是这一类。纯粹的美术,是生命的表现。换句话说:美术就是人生。”“自由不受束缚的”也就是超功利的、无目的的,刘海粟这种观念的产生,表明了到20世纪20年代,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普及到了艺术家之间。此处他又区分了狭义的美术也即传统的造型艺术。最后他提出一个命题,即“纯粹的美术,是生命的表现”。这是该命题的首次提出。
而在一个月之后的《学灯》杂志上,刘海粟又发表了《艺术是生命的表现》一文,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一个月前自己提出的新命题。该文开篇即称:
任何一种艺术,必先有自己的创造精神,然后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若处处都是崇拜模仿,受人支配,则他表现的必不是自己的生命。最高尚的艺术家,必不受人的制约,对于外界的批评毁誉,也视之漠然。因为我的艺术,是我自己生命的表现,别人怎见得我当时的情感怎样呢?别人怎知道我的内心怎样呢?肤浅的批评,是没有价值的。
此处,刘海粟将创造精神视为艺术表现生命的前提,与模仿和崇拜相对立。因此在他看来,艺术家保持自身的创造性,就是表现自身的生命特征,而秉持内在精神,即可蔑视一般的社会批评。他进而设问:艺术如何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因为艺术是通过艺术家的感觉而表现的,因感觉而生情,才能产生艺术,换言之,乃由吾人对现实世界的感受而产生的。”刘海粟的这一观点,乃当时已经流行开来的情感—生命表现说。艺术家创造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生命,实际上是通过表现其感受和情感来呈现的。“表现在画面上的线条、韵律、色调等,是情感在里面,精神也在里面,生命更是永久地存在里面。”他认为,艺术通过形式表现情感、精神等生命因素,而生命又因这种形式表现而永存——无疑,作为生成进程中的个体生命,通过形式创造,为个体之必然逝去的生命—生成之进程打上了存在的烙印,这正是现代艺术形上学的基本教义之一。
刘海粟又谈及对生生之美的感受,称“我常常会在看到一种自然界瞬息的流动线,强烈的色彩……如晚霞及流动的生物……的时候被激动得体内的热血像要喷出来,有时就顷刻间用色彩或线条把它写出来:写好之后,觉得无比快活”。自然界之生命美感激发了美术家自身的生命情感,当然这种摹写本身并非模仿而是创造。刘海粟进而检视传统,称有宋一代绘画开始鼎盛,然而宫廷画——“院体画”本身由于受帝王趣味的约束,并非自由生命的创造。从生命的创造和表现标准出发,他在中国传统画家中找到了后来为他一直推崇的人,他称:
明末清初,八大、石涛、石溪诸家的作品超越于自然的形象,是带着一种主观抽象的表现,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跃然纸上,他们从自己的笔墨里表现出他们狂热的情感和心灵,这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不受前人的束缚,也不受自然的限制,在他们的画上都可以看出来。在他们的画幅上虽一丝之隙,一分之地,都是他们生命的表现;即使极微妙之明暗间几为官能所不能觉察之处,亦有其精神存在。所以他们的作品经历许多年,经过无数人的批评,都被承认是杰作。且不期而与现代马蒂斯、罗丹等一辈人的艺术暗合。
“叛离传统”的刘海粟,对八大山人及石涛等人的肯定,并非存在矛盾,相反,以其“艺术表现生命”的标准出发,中西画法的区别已经被悬置,达到了一种在艺术形上学意义上的融通,因此马蒂斯、罗丹等人方能与本土画家相合。而刘海粟本人也开始重新估价传统,并非像以往那样呈现为彻底叛离的姿态。生命之源在自然界,而非对生命高度异化的现代都市,因此刘海粟肯定中西艺术家逃离都市、远离束缚的举动,在他看来,“与自然和谐”才能表现真实的情感、创造有生命的艺术品。刘海粟在将生命视为艺术的本体、将生命之表现视为艺术的目标之后,其艺术超越性的价值观才得以真正获得一个有力的基点:“由此观之,可知制作艺术应当不受别人的支配,不受自然的限制,不受理智的束缚,不受金钱的役使;而应该是超越一切,表现画家自己的人格、个性、生命,这就是有生命的艺术,是艺术之花,也是生命之花。”显然,艺术的超越性价值是与生命的超越性价值一体的:当艺术即生命即创造之时,艺术家也就在形上学的支撑下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在“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这一观念支撑下,刘海粟于1923年8月又发表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一文。该文说:
后期印象派乃近今欧西画坛振动一时之新画派也,狭义的是指塞尚、凡·高、高更三人之画法;广义的便指印象派以后之一切画派。与三百年前中国之石涛,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然而石涛之画与其根本思想,与后期印象派如出一辙。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二百年前早有其人浚发之矣。吾国有此非常之艺术而不自知,反孜孜于欧西艺人之某大家之某主义也,而致其五体投地之诚,不亦怪乎!
刘海粟对国内言必西方进行了批评,进而将后期印象派与石涛之间的联系,定位在表现主义之上。他说:
后期印象派之画,为表现的而非再现者也。再现者,如实再现客观而排斥主观之谓,此属写实主义,缺乏创造之精神。表现者,融主观人格、个性于客观,非写实主义也,乃如鸟飞鱼跃,一任天才驰骋。凡观赏艺术,必用美的观照态度,不以艺术品为现实物象,而但感其为一种人格、个性的表现,始契证于美。
用表现主义将后期印象派与石涛绘画进行会通,那么“表现主义”这一范畴已经脱离了西方绘画的言说语境,是借他人之酒杯以浇自己之块垒。于是,石涛本人是否符合西方表现主义的特征反倒成为其次,更重要的是表现主义诸原则提供了一个观照石涛、重新阐释传统绘画的现代性视角。在点出了技术上的也是第二个共通性原则“综合的而非分析”之后,刘海粟在第三个原则亦即艺术的本体性原则上凸显创造的重要性:“若能达艺术之本原,亲艺术之真美,而不以一时好尚相间,不局限于一定系统之传承,无一定技巧之匠饰,超然脱然,著象于千百年之前,待解于千百年之后,而后方为永久之艺术也。艺术之本原、艺术之真美为何?创造是也。”经久不衰的艺术品,必须具有创造性,而创造正是艺术的本原,艺术的超越性与创造的超越性再度相融为一体。
此文最后,基于艺术创造观,刘海粟又产生了一个艺术上的“冲决网罗主义”,他称:“吾画非学人,且无法,至吾之主义则为艺术上之冲决网罗主义。吾将鼓吾之勇气,以冲决古今中外艺术上之一切网罗,冲决虚荣之网罗,冲决物质役使之网罗,冲决各种主义之网罗,冲决各种派别之网罗,冲决新旧之网罗,将一切网罗冲决焉,吾始有吾之所有也。”需要指出的是,刘海粟这个“冲决网罗主义”,与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戊戌派战友谭嗣同在《仁学》中的“冲决网罗”无论在提法还是在行文上都颇为类似。所不同的是,谭嗣同“冲决网罗”依凭的是以“仁”为核心并试图汲取近代科学话语的道德形上学,而刘海粟则依赖的是现代以生命创造为核心的艺术形上学,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理论亲缘关系显而易见。
从“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这一观念出发,刘海粟逐渐将生命、艺术、美、人格相融合,最终使艺术走向了美与善、真相融合的超越性价值的顶峰,并被他视为一种现代性的新信仰。在发表于1924年的《艺术与人格》一文中,他称:“有生命的人,才配谈人格。生命就是美,就是人格。故物象必待赋了精神或生命的象征时,才能成为艺术。申言之,我们所谓美固在物象,但是物象之所以为美,不仅仅在它的自体,而在艺术家所表出之生命,也就是艺术家人格外现的价值。”当生命与美与人格相等同之时,美也自然就与善相。他进而称:“人格的价值,通常说也就是‘善’。这个‘善’的内容与‘美’的内容,本来是不相离的,因为它们都是表现自我的生命!有的人说艺术必具有劝善惩恶的内容,才是美。其实这只能说它是除去善之阻梗的一种手段,它的价值属于道德功利的价值,不是美的价值。因为并不是表现善心和善行的才可算艺术的美。”美与善相异但不相离,在生命和人格上实现了相融;同样在生命和人格之上,美、善与真最后实现了一体融合。在《艺术与生命表白》一文中,刘海粟称:“真的艺术家只是努力表现他的生命,他的信条是即真、即善、即美。”这种即真、即善、即美的融合境界的表现者,已抵达艺术超越性价值论之顶峰:
炮火烽烟弥漫了的中华,沉闷而混浊的空气绕围了我们。我们要凿开瘴烟,渴求生命之泉。我们要在黑暗之中,发出生命的光辉!试看古来许多伟大的艺人,他们在痛苦中不减其伟大,就是他们的生命成其伟大。从他们圣洁的心灵迸出他们真生命的泉流,造就他那伟大的艺术。他们是人、“神”境界的沟通者,他们是自然秘奥的发据者,他们是征服一切的强力者!
值得注意之处有三点:其一,“人”“神”境界的沟通者是从“美”加以言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康德美学思想滥觞的表述,即蔡元培所谓现象界与实体界之桥梁,当然此“神”境界在刘海粟处打了个引号,换言之艺术形上学并不通向宗教之神灵,而是通向最高的心灵境界;其二,“自然秘奥的发据者”言说的是真,艺术家被视为生命之真的发现者;其三,“征服一切的强力者”显然打上了尼采权力意志论的烙印,言说的是善。这三者的融合,正标志着在刘海粟这里艺术的超越性价值达到了论述的顶峰。既然已为顶峰,那么艺术的信仰就不再应当仅仅停留于一种个体的信仰,而是应该成为社会的信仰。在发表于1924年12月的《上海美专十三周年纪念感言》中,刘海粟提出要将对艺术的信仰代替一切的信仰:“今日中国社会之黑暗,已臻于不可思议之地步……人民无快乐、无希望,已失其中心思想信仰,日夕俯首于悲苦绝望之中,此中国之现势也。长此以往,国家永无宁日,人生失其意义。”“人民失其中心之信仰”,于是以何替代?“即以艺术之真理代兴一切信仰,使吾人借其生命之勇气而自振,由其纯洁之心灵而自慰;必使人人具美的意识,然后人人有真的人格。呼吸自由之空气,以伟大之精神创造伟大的时代,此亦所谓艺术革命也。”“以艺术之真理代兴一切信仰”,显然受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观念之影响。“以美育代宗教”命题如若要真正树立起来,所倚靠的绝非是社会进化论和科学主义,而是蔡元培因“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谨慎态度但未充分展开的部分,即将审美和艺术放置在超越性价值论的王座之上。于是,刘海粟的“以艺术之真理代兴一切信仰”这一命题,作为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命题更为激进的言说形式,不仅是刘海粟自身信仰的高亢表述,更构成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思想的最鲜明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