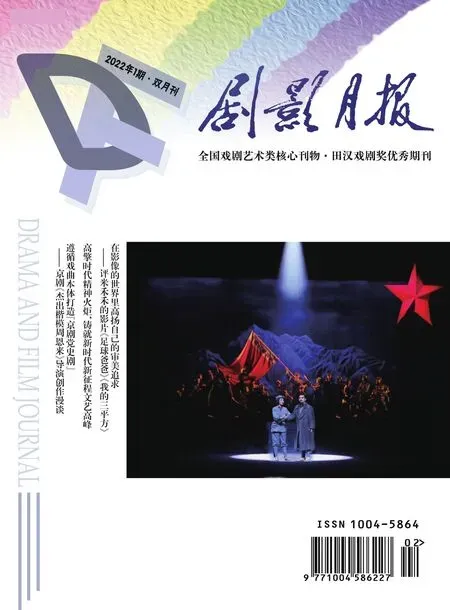恶所盛开之花
——《艺伎回忆录》中的人物形象与“意气”
■李想 刘竺岩
(李想系苏州大学艺术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刘竺岩系兰州大学文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电影《艺伎回忆录》改编自阿瑟·高顿的同名小说,它揭开了艺伎的神秘面纱,深入艺伎生活,不仅道出了她们背后的故事,还揭示了其神秘美感的来源。艺伎与普通妓女的区别在于,比起肉欲满足,她们更多是为提供给服务对象精神欲望满足而存在的。在精神恋爱中,氛围的营造极其重要,这造就了艺伎的神秘美感。影片中真美羽便是如此。她认为“我们营造一个神秘的世界,一切都美不胜收”。对艺伎来说,为给客人提供舒适的氛围,对其身体的“媚态”以及两性交往规则的训练必不可少。这种承载于身体及生活中两性交往的美感,随着现代西方“身体美学”的建立及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提出,逐渐受到重视。《艺伎回忆录》塑造的四位艺伎形象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她们的美。这种美如何产生?被称作恶所的“游廓”的审美价值如何体现?四位艺伎的不同结局究竟代表怎样的审美价值判断?对于以上问题,应在孕育艺伎文化的日本文化中寻找答案。
一、恶所之花:非善之地孕育意气之美
对日本人来说,“审美意识不仅停留在感性及美的世界中,更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规范存在于其中。”日本现代生活文化在江户中期到末期已基本完成。这种诞生于日常生活而非艺术的审美意识,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宗教和伦理,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讲,如果说中国人的生活以善为准则,西方人在自然界中追求真,那么日本人的生活就是对美的无尽探寻。
由于闭关锁国,江户时代维持了二百多年的社会稳定,长期休养生息让文化中心从乡村走向城市,商品经济繁荣。一些有钱的新兴市民阶层(町人)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极力摆脱土气(野暮),追求上品生活。总的来说,如果说平安时代的文化中心在宫廷之中,中世文化中心在名山寺庙与武士宅邸的话,江户时代的市民文化中心就在被称为恶所的“游廓”以及“戏院”中。《宽天见闻记》中“旅馆女招待和吉原町,均为世间的恶所”,表明在江户初期“游廓”即恶所的观念已然形成。虽然人们表面对恶所加以排斥,但实际由于对美的渴望使得“戏院”与“游廓”冲破了俗世伦理道德的禁锢,成为江户时代平民文艺的两大源泉。
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恶所中所体现的“性欲生活的美化”与我们所熟知的“男女恋爱的性欲生活伦理化及其产生的美化”有所区别。后者多体现为西方基督教处女崇拜的传统观念,符合西方伦理善的性质。而前者以性接触为假定,为传统伦理所不容,比起以恋爱为前提的西方男女关系来说,恶所中的男女关系仅仅将“恋爱作为将来的一种预想的归结,因此它只是某种程度上将恋爱加以剥离的‘性欲的美化’”。其对官能享乐的重视以及对性欲的审美化现象,在世界文化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出发于肉体,归结于灵肉合一的身体,寻求精神与肉体自由超越的审美思潮。”这种审美思潮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唯美追求的时代新风流行于整个江户时代。这种审美思潮被归结为“通”“粹”“意气”等一系列审美概念,其核心范畴是“意气”。
首先注意到这种独特文化现象的是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九鬼周造于1922 年留学欧洲,受教于柏格森、海德格尔。孤身留洋的他迫切想要欧洲人理解他家乡的文化。因此他运用海德格尔解释学、现象学的分析方法,将江户时代游廓中产生的文化现象挖掘出来,分析其构造,赋予其现代性,最终将其上升到美学高度。九鬼周造认为,“意气”是“东洋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大和民族对自己特殊存在形态的一种显著的表达”,是一种独特的日本审美现象。
一种有生命的哲学必须有助人们对现实的理解,作为恶所的“游廓”无疑是体现审美现象“意气”的核心之地。九鬼周造的理论无疑是剖析恶所之花惊心动魄的美的利器。
二、媚态之身:江户时代的身体审美
何谓“意气”?简单来说即为“通过理想性与非现实性来实现自我存在的媚态”。“媚态”的存在是意气的核心。这种“媚态”被九鬼定义为“一元存在的个体为自己确定一个异性对象,而该异性必须有可能和自己构成一种二元存在的关系”。因此两性间的二元关系与构筑的可能性是“媚态”存在的前提。
这里的关键词“两性”“二元关系”“可能性”缺一不可。也难怪九鬼周造认为“媚态”一般只在两性交往中才能显现,一旦“可能性”消失或者转为必然,两性间二元关系消失,“媚态”便荡然无存。可以看到这种论断本身就与传统伦理道德相背,“媚态”是一种身体审美,一种不依存于“真”“善”的唯美追求。这种追求排斥现实性与真实性,只是一种暧昧的理想主义。因此浮沉于“恶所”这种非善之地的艺妓们的唯美气质就可以理解了。
二元关系的构成使得“媚态”本身带有征服异性的假想目的,因此身体外貌对异性的吸引力必不可少。电影中,幼年的小百合与名伎初桃初遇于置屋,在阴翳的房间中,摇曳的烛光与天顶照下的少量日光,将初桃如火般明艳的和服映衬的格外妖艳,将初桃“性的魅力”完美表现了出来。初桃毫不掩饰的“媚态”使得初入邸园的小百合忘记了礼节,沉醉于其中。
初桃作为四位艺伎中“媚态”的代表,身形外貌极具美感。但这种如火焰般的“媚态”也昭示了其悲剧的发生。初桃是一名极受欢迎的艺伎,其妖艳姿态无疑向异性发出了致命的吸引信号。艺伎的职业使得每一个与她交往的男性都有着与其构成二元关系的可能性。原著中提及,邀请初桃参加宴会或者聚会需要提前半年至一年预约,这种求而不得的姿态反而使其更受欢迎。
与其受欢迎程度不同的是,初桃在她的恋爱中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正是其对感情的过分热切造成的。
影片中,初桃与男友在置屋偷情被小百合撞见时有着这样一段对话:
“请不要生我的气。”
“看看我们,就像偷东西的罪犯。”
“幸一,别……”
“这是一种耻辱。”
在这个雨夜,偷情被撞,男人仓皇而逃,满腹抱怨,女人爱意缠绵,拥吻不舍。她极力想维护住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其所不知的是,这种卑微的求爱正是两者关系崩塌的主要原因,即“越是沉溺于爱,越是落于俗套了”。
初桃与男友间的二元关系已经达成,可能性转为了必然,二元关系崩塌,“媚态”自然消失不见。作为艺伎——所有男性的幻想的存在,她与男友一周一次的幽会,破坏了其作为艺伎的神秘感。他们之间的二元关系也随着对异性征服的假想目的的实现而消失。难怪现代作家永井荷风在小说《欢乐》中写道:“没有比想要得到,而又被得到了的女人更可怜的了。”
留存于男女二元关系中的媚态,正是要维护两者之间合一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消失于合一或者分离之时,“媚态”也将消失于倦怠、绝望、厌恶之中。对初桃来说,她只是想有个人来爱她,但却因为过爱而走向分离。这与她所处的环境有着直接关系,恶所中浮沉的艺伎想在这里遇到一个真正理解她爱她的男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也正是发现了这一点,大火过后,初桃选择了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三、意气之眸:江户时期的道德理想
初桃爱情的幻灭与其“媚态”的消亡有着直接关系,当“媚态”消失于倦怠,艺伎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也就随此消亡。因此,为将这种“媚态”存续下去,意气的第二个表征——具有理想主义的“意气地”所带来的傲气与矜持必不可少。
“意气地”产生于江户时期町人文化的道德理想,这种理想在男性身上体现为纵横火场的“江户之花”的男人气概。在女性身上就体现为艺伎“倾城女不是金钱能买的,内心必须怀有意气地”与藐视街头流莺“轻易对客人动心”的清高姿态。这种带有理想主义的“意气地”正是一种经过升华的媚态,也是意气的核心。身怀“意气地”的艺伎往往能给人一种清高、矜持的美感,真美羽便是深谙此道的行家。影片中她教导小百合时这样说道:“你先专心学艺,音乐、谈话技巧才是吸引男人的正道,而不是在床上向他献身。”经过训练的艺妓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艺术品,在她教导小百合行走仪态时这样说到:“不能用一个眼神让男人驻足,就不算一个真正的艺妓。”
九鬼周造曾详细分析身体的“意气”之美,他认为唇齿、眼睛、脸颊等面部部位的张驰有助于“意气”的产生。例如眼睛,根据眼神流转的不同,通过低眉、飞眉、扬眉等动作向异性展示自身的“媚态”,这种流眄通过打破面部表情平衡,在张驰流转间变现对异性的关注。
不过仅仅如此还不足以称之为“意气”,“意气”的姿态必须在“媚态”的基底表现出“谛观”或者“意气地”的性格才行。这种性格表现在眼神中,就需要眼神在保持勾人的媚态的同时又能表现出无言的谛观与傲气来。
这一点上,小百合先天便具备这种条件,即她那双脱俗的灰蓝色眼眸。“你怎么会有一双如此不同寻常的眼睛。”田中先生在小百合发烧时惊叹道。“漂亮的眼睛”小百合第一次进入置屋时姆妈赞叹。“多么不同寻常的眼睛啊!我还以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呢。”真美羽如此说道,也正是这一双灰蓝色眼睛成就小百合的传奇艺伎之路。
与初桃火焰般炽热的感情并不相同,小百合的感情如水般含蓄。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始终隐藏着对会长的感情,并一直寻找与其构成二元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对爱情的矜持便转换为一种“意气地”的自尊,将其“媚态”存续下去。正是这种矜持使得男爵、会长、延、螃蟹医生等男性始终有着与其构成二元关系的可能性,为其着迷。但这种构成二元关系的“可能性”随着与螃蟹医生水扬结束、男爵竞争失败、延的放弃而消失。“意气地”的矜持与“媚态”间构成的平衡被打破,围绕在小百合令人着迷的神秘魅力便如初桃般消散。
值得注意的是,“媚态”的强度不会随着异性间的距离接近而减少,反而会随着两者二元关系的达成而增加,也就是说当两者距离达到最近,接近合一之时,“媚态”的强度就会达到最高。“我在天见的所为,是因为我对您的感情,会长。自从我还是祇园的一个小孩子,我这一生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为了能接近您。”电影结尾,小百合的告白使其“媚态”达到了巅峰,在这一刻,这朵出身贫苦成长与恶所的花朵终于绽放,绽放出了意气之花。愿望的达成使得小百合激动地颤抖,会长也为之着迷了。
四、谛观之心:佛教的非理想性
“你不能命令太阳下山,也不能命令雨停下来,男人只能把艺伎当成半妻,我们是他们夜晚的情妇,但一个小女孩吃了这么多苦,以无比的勇气,面对艰苦的人生,最后发现她的愿望终于实现,这难道不是幸福吗?毕竟这不是女王或皇后的回忆录,这是一个艺伎的回忆录。”影片最后的旁白,显示了小百合注入灵魂的真心遭到生活的磨练后所形成的心态。这种心态正是九鬼周造所挖掘的意气的第三个表征——“谛观”。“谛”是佛教用语,为真理之意。“谛观”是“諦観”的译词,“諦観”指的是一种经过红尘磨练最终看破红尘的心境。这种心境在美学上就是一种审美静观,九鬼认为这是一种“基于对自我命运的理解基础上的一种不执着与超然”的心态。
生活于恶所的艺伎常常会遇到爱情破灭所带来的痛苦。身怀“意气地”也只是这些可怜人与命运做的微弱对抗罢了,一旦动了真情,“意气地”带来的矜持与自傲便无法阻挡她们跳动的真心。净琉璃《十六夜清心》中的“清心先生啊,偶有相逢却又离去,你到底是佛还是鬼?”十六夜的感叹表明了这种红尘磨砺的痛苦之情。但生活需要继续下去,经过磨砺的艺伎们失去了对异性的信赖,形成了“浮世事事难遂愿,对此必须要谛观”的谛观之心,这种“谛观”之心与艺伎本身带有的“媚态”结合就转化成了独特的“意气”魅力。这种魅力“意味着命中注定的对自由的归依,意味着可能性的命题是由必然性所规定的”。理解这些便意味着看破了人生浮沉,真美羽以及成长了的小百合具有的成熟洒脱气质便由此而来。
因此,“谛观”的心态在年轻的艺伎身上很难找到,原著中“水扬”之后小百合与真美羽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命运并不总像晚宴的散场。有时候,它只是挣扎度日罢了。”
“可是,真美羽小姐,这太残酷了!”
“真美羽小姐”“你对男爵……感情深吗?”
“男爵对我来说是个好旦那。”
“是啊,那当然是,可你对他是否有对男人一样的感情?”
“男爵和我的关系对他很方便,对我很有利。如果我们的关系被感情束缚……嗯,感情会很快滑向嫉妒,甚至仇恨。……小百合,如果你想成功,你就得掌控男人的感情。”
很明显,对于常年在恶所磨砺的真美羽来说,她已经摆脱了对现实的执着追求,在妩媚的微笑、真诚热泪流过后的泪痕中获得了无所牵挂的洒脱与恬淡。而对爱情还有向往的小百合,只能再一次将其对会长的爱恋隐藏在心中。小百合无疑是幸运的,会长的垂青使得她最终脱离恶所,但对于艺伎们来说,这样美好的结局又怎是能轻易期盼的呢?
“意气”与其说是个人获得的,不如说是从恶所这个小社会中继承来的。“意气”作为日本文化特有的审美意识现象,“依靠道德上的理想主义精神(意气地)和宗教的非现实性(谛观)的‘形式因’,作为‘质料因’的媚态得以完成自我存在的实现。”可见“意气地”与“谛观”之心是艺伎之“媚态”存续的原因,一旦失去,“媚态”便荡然无存。因此,只有“媚态”而无“意气地”和“谛观”之心的初桃与连“媚态”都缺少的南瓜,自然在与小百合、真美羽两位意气达人的竞争中败北。
五、意气的凋零:东西方媚态之别
与尽显“媚态”的三位艺伎不同,南瓜的命运象征着艺伎职业的衰落。原著中对小南瓜的描写是这样的:“她身体很瘦,脸庞却是肉鼓鼓的,几乎呈滚圆形,所以在我看来她就像是一只西瓜立在一根棍子上。”
“意气”作为产生于“游廓”的意识现象,影响着大众对艺伎的审美判断,这种审美判断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南瓜圆圆鼓鼓的脸蛋看似非常可爱,但与小百合灰蓝色眼睛不同,她这个特征无助于“意气”的产生。如果说杨柳细腰的身姿是“意气”的客观表现的话,一张瘦长、显得潇洒的脸型更符合“意气”的要求。究其原因,除时尚外,是日本审美中特有的“秘”导致。“秘”即为看起来朴素,实则精致的审美意识。江户时期和服上的细小纹样就表现出了对“秘”的追求。这种对“秘”的追求表现在姿态、举止、长相上暗合“意气地”的矜持。九鬼周造认为,西方所钟爱的“狄俄尼索斯祭女的狂态”般腰部左右扭动的毫不掩饰的“媚态”与日本含蓄的“意气”相差甚远,他认为“意气”所表现的“媚态”是对异性若有若无发出的暗示。
在这里,“媚态”所具有的二元性构成了意气的质料因,它通过吸引异性打破了一元平衡,朝着二元性行进。然而作为意气之形式因的“意气地”“谛观”的“非现实的理想性”抑制了二元性,又让“意气”得以留存。真美羽的教导也正如九鬼的理论那样,艺伎的目光、姿态、微笑在表现出对异性吸引同时也要抑制形成二元关系的过分放纵。
一般来说,艺术要表现“非现实的理想性”时,会偏向于选择细长的姿态,这有助于表现灵魂的力量。如日本画家喜多川歌磨对艺伎这一包含男性幻想的女性,表现出了对窈窕纤细的无限追求。因此,在日本,如《抢夺吕西普斯女儿》般充满肉欲的丰韵身材被认为是“野暮”,也就是土气的。
南瓜的命运从开始或许已经注定,没有小百合天生媚骨的她,一开始就执着于成为艺伎,对爱情这种“非现实”“理想”的事物缺少追求。因此,越是执着就越是落于俗世,本就缺乏“媚态”的她,又缺少艺伎所特有的神秘光环,“意气”根本无法在她身上产生,给人一种“野暮”之味。最终和小百合竞争失败,落得靠出卖色相度日也在意料之中。南瓜的经历代表着一大批由于战争而失去容身之地的艺伎的结局。艺伎是长与恶所的恶之花,本就带有非善意味,当恶之花们失去了容纳她们的土地,又在现实中磨去了“意气”之心,当然就很难再开出美的花朵,只能成为单纯的恶了。这也是始终恪守“意气”之道的小百合、真美羽能战后重返恶所,南瓜与初桃再也无法当回艺伎的原因。
从电影《艺伎回忆录》四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对于出身于恶所的艺妓来说,一名优秀的艺妓,是有着严格的美学评判标准的。
从美学角度来看,“意气”作为江户时代的审美思潮,在艺妓、歌舞伎的影响下,作为町人文化的审美面向,逐渐成为了日本美学、文学的传统。日本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就偏爱描写艺伎的恋情,如《伊豆的舞女》《雪国》等,文风充满“意气”之美。
“意气”作为日本传统审美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与形态,直接影响到了现代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深受“意气”观念影响,艺伎的行为规范“艺伎道”也作为日本女性的生活典范融入现代日本社会之中。如今,“意气”这一审美传统已经从“游廓”“戏院”这一特殊社会中解放出来,褪去了其“情色”与“洒落”意味,作为日本民族自身存在形态的一种表达而存在。换言之,“意气”与“侘寂”“幽玄”“阴翳”等美学范畴一样,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根植于日本人血液之中。
在现代社会中,“意气”其实就是性感美与身体美的普泛化,本质上是以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审美为对象的审美化,极具“都市风”与现代性。因此《艺伎回忆录》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其所体现的审美意识,不仅作为日本特有的文化存在于他们的民族记忆中,而且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存在于当代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