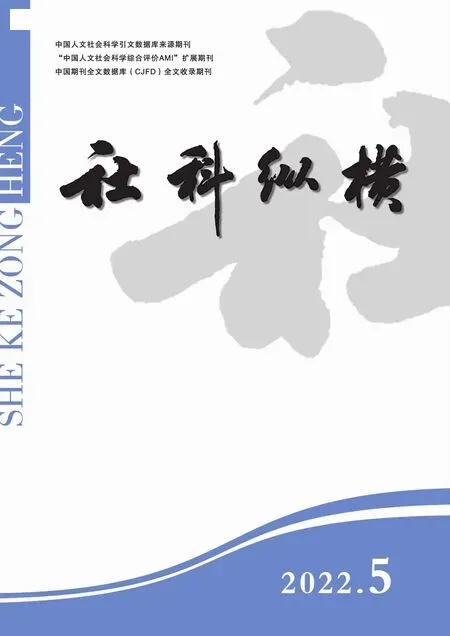收入对女性生育选择的影响研究
肖琴 王婷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3)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我国人口结构持续失衡,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攀升。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单独多胎”政策,并于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以期提高人口生育率。但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生育高峰,反而出现出生数和出生率的双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人口出生人数和出生率由2016年的1786万人和12.95‰下降至2020年的1200万人和8.50‰①,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引起了诸多学者的研究。研究表明,生育意愿是家庭中夫妻双方的“讨价还价”过程,只有在满足女性的利益需求情况下,女性才会拥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1],这意味着女性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起重要作用。而对于女性来说,生育二胎行为更是其效益和成本之间的选择[2],生育成本不仅包含了直接用于子女本身的抚育成本和间接用于子女的保健、咨询费用等,还包含了女性因为生育孩子而失去的可以增加收入机会的影子价格[3]。由于女性在孩子的生育和照料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大部分的工作,当女性认为生育孩子带来的效益低于女性工作带来的满足感,甚至不足以与生育的成本相抵扣时,女性会减少生育的数量;当女性认为孩子带来的效益超过工作的效益时,女性可能会增加生育的数量,甚至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文章基于贝克尔的孩子质量与数量理论[4-6],将女性收入作为女性工作效益的直观表达,研究不同阶段收入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
一、文献回顾
关于生育选择的决策问题较早受到了国外研究者的关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理论(Becker,1960;Becker,1974;Becker&Barro,1988)表明,孩子的效用与父母的效用呈正相关,父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消费,还取决于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家庭效用最大化是生育决策的最终结果。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探讨生育选择的影响因素问题,韩宇博认为女性工资收入水平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1],一般来说,高工资收入水平的女性群体具有更强烈的二胎生育意愿;周福林认为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会影响家庭生育行为,家庭规模的大小和家庭中女性的生育行为以及子女的数量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规模较小的家庭来说,大家庭中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较高,且家庭结构不同的女性生育行为存在着明显差别[7]。王军、陈蓉等发现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生育观念、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的高低、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养育孩子的成本等都会影响家庭中妇女的生育行为[3,8]。
其中,收入水平作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已经成为研究者们相继探讨的热点话题,但关于收入水平如何影响生育决策仍存在异议。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女性收入水平的提高,女性会减少生育数量。早期,Galor和Weil在贝克尔的质量—数量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研究劳动力市场工资性别差异、生育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女性的相对工资越高,生育率越低[9]。而后,熊永莲基于Galor和Weil的家庭决策模型,构建了一个家庭效用函数,从而得出我国生育水平低的原因在于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中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地区城镇化的发展[10]。王玥亦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家庭效用决策模型,进行女性收入变化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女性收入的提高会使家庭的生育率降低[1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女性的收入水平和生育子女数量呈“U”型曲线关系。Siegel通过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生育率、住房时间和性别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随着女性相对工资的上升,生育率会先下降,然后趋于稳定[12]。Jun和Taoxiong构建了一个三阶段重叠世代模型来探讨中国生育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影响生育选择的因素。结果表明,女性收入对生育选择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13],生育意愿会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到一定程度后,生育意愿会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关于女性收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U”型关系的研究,马启文收获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女性收入与生育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倒“U”型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收入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达到顶峰之后,收入与生育意愿负相关[14]。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大多数的研究都以调研数据为基础对收入如何影响家庭生育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虽然研究的结果会有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收入的变化确实会引起生育行为的改变。但较少有学者单纯从女性群体角度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女性收入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结合女性的行业性质与工作时间,将女性收入按照“家庭收入四分位数”进行划分,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下女性生育多胎的意愿。
二、家庭生育决策模型
基于贝克尔的孩子质量和数量替代理论建立一个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假设一个家庭中夫妻的效用取决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带来的效用,另一部分是夫妻其他消费的效用,分别有对应的单位成本[4]。其中,孩子数量的单位成本包括用于子女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同时假设,家庭通过调整孩子的数量、质量以及其他消费的选择来进行最大化效用抉择,其家庭效用函数为:

n为孩子的数量,q为孩子的质量,且同一家庭中每一个孩子的质量相同,C为其他消费,πn是nq的价格,πc是C的价格。家庭的效用同样分为两个部分,孩子数量和质量带来的效用和其他消费获得的效用,α和β分别为家庭中夫妻对孩子和其他消费的偏好,且α+β=1。
需要满足的约束条件:

其中,Y是总收入。
根据家庭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家庭效用最大化需满足:

C,q>0,n≥0,Y,π为常数
一阶条件为:

根据(4)—(7)式可以得到:

(8)和(9)式是家庭效用最大化情况下的最优解。(8)式说明,家庭中的偏好α和β直接决定了孩子的数量,质量以及其他的消费,即,家庭中如果更偏好于其他消费所带来的效用,那么孩子的数量就会减少,反之孩子数量增加。根据(9)式,无论家庭中夫妻的偏好如何,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同样根据家庭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探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是如何表现的,采用张新洁[15]关于效用的求解,可以将上述一阶条件简化为:

P代表边际成本或者影子价格。pn为孩子数量的价格,pq为孩子质量的价格。
根据(10)—(12)式,得到:

则有,当πn一定时,孩子数量的影子价格pn与孩子的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孩子质量的影子价格pq与孩子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假如,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较多并且孩子质量的影子价格pq也较高,则需要提高每一个孩子的质量的成本就会增多,于是在家庭质量总数一定的情况下,父母会将质量分配给更多的孩子,于是每一个孩子的质量降低。反正,当孩子数量较少时,每一个孩子的质量增加。
考虑到我国的传统家庭中,养育子女的任务主要由母亲承担,消耗的是家庭中母亲的大部分时间,因此我们假设在家庭中只有母亲的时间是具有生产性的,此时丈夫的时间不具有生产性,其收入可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那么家庭中的收入就主要取决于女性的收入[11],并且女性收入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的价格从而影响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选择。结合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中的女性会考虑在生育孩子和其他消费配置,从而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但从机会成本角度出发,女性生育多孩行为不仅会增加养育成本,同时会对自己的收入带来影响。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生育多孩是其获得的效用和成本之间的选择。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样本覆盖了全国25个省份,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采用2018年最新一期的调查数据,研究对象为20—50岁的女性,总共获得8361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介绍与描述统计
主要解释变量为女性工资性收入,将女性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于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分为四个群组:低收入组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女性群体;中等收入组是指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女性群体;较高收入组是指月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女性群体;高收入组是指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女性群体。
因变量是多胎生育选择。生育意愿为二元变量,将未生育和生育一孩赋值为0,生育二孩或多孩赋值为1。
控制变量为:
第一,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态、教育程度、健康程度,行业分类,城乡类型。将城镇女性、党员赋值为1,农村女性、非党员赋值为0。婚姻状况按照已婚/同居、未婚、离婚分别赋值为1、2、3。工作时间按照每周工作时间的长短分为三类,低兼职参与为每周工作时长小于20小时,赋值为1;高兼职参与为每周工作时长在20—35之间,赋值为2;全职参与为每周工作时长大于35小时,赋值为3。行业分类则按照2019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分为五类②:制造业赋值为1,教育行业赋值为2,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赋值为3,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赋值为4,其他行业赋值为5。此外,对样本受教育情况划分五类,核算方法是: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本科及以上=5。健康情况分为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不健康,赋值为1—5。
第二,家庭经济状况变量。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房产所有权以及房屋固定资产现值状况。
第三,社会保障情况。社会保障由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工作保险构成。此外,本文依据行政区域划分将个体所在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本文关注收入、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职业性质、行业特点与女性生育多胎的意愿,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着重研究女性不同收入水平下生育多胎的意愿,被解释变量多胎生育是一个二元变量,只有0和1两种取值(生育多胎取1,未生育及一胎取0),为二值选择变量。如果采用一般的回归计量方法,容易造成残差项出现异方差,从而导致回归结果不准确。同时解释变量多为离散变量和分类变量,因此需要采用离散选择模型[16],即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且Logit模型不需要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适合进行分析[17]。
计量模型为下:

该模型中,child为多胎的生育意愿,β0为常数项,βi为变量系数(其中,i=1,2,3,……,n),inc_i表示不同层次女性的收入;Xn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u代表随机干扰项。本研究以此为基准对全部样本进行Logit回归,为检验模型有效性,通过OLS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对城乡及地区样本进行异质性回归分析,以检验女性工资性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在群体中的差异。
(二)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检验不同阶段女性收入对生育多胎行为的影响,随后评估处于不同行业不同工作时间下女性生育多胎行为的不同,最后考察女性收入对生育多胎影响的异质性。
从表2显示的部分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女性收入与其生育多胎的意愿从低收入组和29.2%上升到中收入组的30.2%,而后下降为中高收入组的负向的14.0%以及高收入组的负向70.9%,表明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变量后,女性收入与多胎生育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随着收入的上升,收入与生育多孩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收入与生育多孩意愿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表明在对收入分层的情况下,显然中等收入女性群体和低收入女性群体会具有更加显著的生育多胎行为。对于中、低收入女性来说,此时生育更多的孩子所带来的效用大于自身收入带来的效益,女性会更愿意生育多胎,女性的生育意愿逐步增强。然而,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不断地上升。当生育孩子带给女性的效用与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相等时,女性此时的生育意愿最高。而后,随着收入进一步增加,对于女性来说,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逐步增大,生育多孩的边界效用递减,当女性从孩子中获得的效用低于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时,女性会减少孩子的生育数量,更多的是提高孩子的质量,女性生育多胎的行为减弱。
女性的工作时间同样会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女性群体的生育多胎行为,观察表2发现,低兼职参与的女性更愿意生育多胎,这可能与女性在照料孩子行为中承担大部分角色有关。从女性不同的行业性质可以发现,在众多行业中,处于教育行业的女性具有显著的生育多胎行为,原因可能是教育行业具有更多的假期且工作较为稳定,女性心理情绪较为稳定且工作压力较小,从而其更有意愿生育多孩。
从个人统计特征来看,婚姻状况对女性生育多孩行为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处于已婚或同居的女性,不论收入水平的多少,均具有正向的生育多孩意愿,而处于离婚或者丧偶的女性群体,其生育多孩的意愿是负向的,意味着婚姻状况的稳定性对于女性生育多孩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上升,妇女生育多胎的行为在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更加追求生活质量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考虑到生育多胎会对女性自身工作能力和地位的提升具有较大影响,女性往往不愿意作出牺牲。这部分隐藏的机会成本成了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巨大阻碍,逐渐在考虑经济成本时成为决定性因素。女性的健康状况也显著影响着妇女生育多胎,女性生育需要较长时长,且怀孕对女性自身健康状况要求较高,因此健康状况越好的女性,会有更明显的生育多胎行为。
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与女性生育多孩显著相关。观察父亲或母亲对家庭的照料是否会影响女性生育多胎行为,从表2中发现,父亲帮忙照料家务与女性生育多胎的行为并无明显联系,但母亲对家庭的帮助会显著增加各个收入阶层女性的生育多胎意愿。家庭人口规模在1%的水平下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得知生活在规模较大家庭中的女性群体,一般具有较为明显的多胎生育意愿。一方面,大家庭一起生活容易受到长辈“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儿童的照料以及经济压力得到缓解。家庭总收入与女性生育多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考虑到养育子女的经济支出和照料支持,在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情况下,女性可能更愿意付诸生育行动,满足生育需求。
(三)稳健性检验
根据回归结果,女性收入会影响其生育多胎行为,且呈现倒“U”型,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多胎的意愿增强,到一定程度后,收入越高,女性生育多胎意愿减弱。由于基准回归采用的是Logit模型,考虑到仅用单一模型进行估计,有可能会产生估计结果的误差,故进一步采用OLS估计法分析女性收入、教育程度以及行业性质对女性多胎生育行为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结果均在1%和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且与回归结果显著性一致,因此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四)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女性工资性收入对生育行为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将样本按年龄、城乡、和地区、进行分组,寻求女性收入对生育行为影响的动态演变。
首先,为了进一步探索女性收入与生育多胎的关系在不同年龄群体的差异性,本文按照女性的年龄将样本分为20—30岁、3l—40岁和41—50岁三个年龄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18],结果显示,20—30岁女性群体中,中等收入组与高收入组与女性生育多胎行为呈现显著关系,中等收入组群体更愿意生育多胎,而高收入组群体则具有更负向的意愿。3l—40岁年龄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呈现出与实证回归结果一般的倒“U”型关系。41—50岁年龄组则呈现出不同的趋势,随着收入的增高,女性生育多胎的行为减弱。
其次,按照女性的居住地类型将样本分为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地区女性收入与女性多胎生育行为呈现与全体样本相同的倒“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多胎生育意愿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城镇地区则随着女性收入越高,则其多胎生育行为随之降低。
最后,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女性群体相比中部和西南地区的女性群体会具有更显著的生育多胎意愿;中部地区女性随着自身收入的不断提高,生育多胎的行为逐渐减弱,西部地区整体来说显著度不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引入女性的工作时间与行业性质,分析不同阶层女性收入对其生育多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女性收入对其生育多胎行为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随着收入的增高,女性生育多胎的意愿先上升,而后下降。第二,工作时间的长短以及行业性质的不同会对女性生育多胎的意愿产生影响,低兼职参与和处于教育行业的女性会具有更强烈的生育多胎行为。第三,在有母亲帮忙照料的情况下,女性的生育多胎意愿是显著增强的。第四,女性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健康程度、居住地类型、家庭收入以及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等都会对女性的生育多胎行为产生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目前“三胎政策”的开放,为生育率水平的提高和生育个数的增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背景,但生育率的提高不再只是受限于传统的“传宗接代”,更多考虑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会网络、生育观念、生育孩子数量质量以及成本之间的选择等因素。因此,即使现在生育政策不断开放,生育率和生育数的成果也并不显著。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保持和扩大已具有一定生育多胎意愿的中、低收入女性群体的生育多胎意愿,积极保障这部分群体生育二孩的权益,加强生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如社区托育服务,以缓解家庭中女性的育儿压力,降低女性生育风险和成本,鼓励女性可以快速地在生育与工作中找到平衡,提高生育水平。
第二,提高较高收入和高收入女性群体生育多胎的意愿,对于这部分女性群体来说,工作带来的效益已经远远超过生育孩子带来的效益,因此,需要对这部分女性积极引导,通过再宣传和再激励,鼓励其在生育孩子的效益和成本之间进行再抉择,加大女性对生育孩子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同时,各地区应当结合本地的生育特征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如发放生育津贴、扩大夫妻双方的产假时间等,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等机构可适当增办孕妇工作区、休息区,以便这部分女性群体可以在妊娠安全期间选择适当参与工作,维持自身工作带来的效益和满足感,提高这部分群体生育多胎的意愿。
第三,保障全体女性的生育权益和就业权利,不仅要完善女性生育权益保障的社会支撑体系,还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就业、创业的保护,全面倡导女性的就业公平,加强社会监督,对具有性别歧视的企业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完善法律对女性平等就业权益的保护,创造一个有利于女性就业和生育的社会环境。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9年中国劳动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