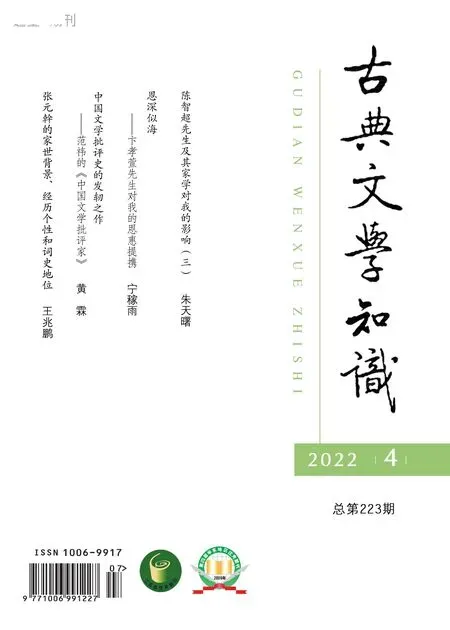恩深似海
——卞孝萱先生对我的恩惠提携
宁稼雨
在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上,曾有许多恩惠提携过我的学者,而卞孝萱先生则是这些学者中最令我难忘的前辈师长。他对我的鼓励提携和热情帮助,是我学术生命中最为珍贵的财富,也是我在学术道路上能够走到今天的强大精神支柱。老一代学者对于后学毫无保留的提携奖掖与坦诚襄助,在卞先生对我的关爱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结缘先生
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知道卞先生大名并向他问学。
1984年,我在南开师从刘叶秋先生攻读笔记小说专业方向硕士学位,已经是二年级。这一年,南开中文系为扩大南开文言小说研究的影响,决定召开一次以“古小说”为主题,以刘叶秋先生为会议主持人的全国古小说研讨会。作为刘先生的唯一弟子,我负责会议会务工作。其先期工作就是摸清学界研究情况,确定邀请人员名单。我当时正在准备写硕士学位论文,需要全面了解文言小说研究的前沿状况。当时,以古小说为主的文言小说研究还相当冷清,从各种出版物中能够检索到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数量很少。南开之外,能够查到本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中,卞先生就赫然在列,此外还有程毅中、方诗铭、段熙仲、周楞伽、郑学弢、侯忠义、吴志达、刘兆云等诸位先生。作为特邀代表,我都向他们发了邀请信,遗憾的是有些先生因故不能与会,其中就有卞孝萱先生。“文革”后,匡亚明校长就一直想把卞先生调入南京大学,但当时卞先生执教的扬州师范学院坚决不放人。嗣后中国民主建国会一纸调令,把卞先生调到北京中国民主建国会宣传部任职。南京大学又跟到北京,向“民建”商调卞先生,才获得成功。而南开这边的古小说会议时间,恰好与卞先生往南京搬家的时间冲突,因而无法与会。从先师刘叶秋先生到我,以及卞孝萱先生本人,都为此感到遗憾。但留下的遗憾却成为我后来继续向卞先生求教的起因。
1988年,先师刘叶秋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突然去世。其间我在北京待了一周,协助师母和家属料理后事。当时信息渠道远不及现在畅通,先师故去的消息学界很多人并不知道。回到天津后我很快给包括卞先生在内的先师故交老友写信告讣,并表达今后向卞先生求教学习的诚恳心情。卞先生接信后很快回信,对先师突然去世表示沉痛哀悼。他说:“刘叶秋先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无论是学问还是人品都非常优秀的学者,也引为知己同好;正因如此,我会像对待自己的晚辈学生一样来对待你,无论你有任何问题或需求,我都会尽量满足。”卞先生的殷殷话语让尚未从悲痛中走出的我十分感动,心灵上受到充分的安慰,并从此追随卞先生,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师生情和忘年交。
受益卞先生的精深学问
卞先生是学界罕见的自学成才的大家,文言小说研究成就卓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研开始,卞先生的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文言小说研究方面的成果,就一直是我的重要学习资源。除见诸各种报刊媒体的单篇论文外,从八十年代和卞先生建立联系后,我一直源源不断地得到卞先生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的签名赠书。诸如《元稹年谱》《冬青书屋笔记》《唐人小说与政治》《唐传奇新探》《郑板桥全集》等。这些学术成就对我个人的学术影响和指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文言小说作者、作品年代的考证。作为文史兼通型学者,卞先生文献考证功底深厚,撰有诸多学术考证文章。其中让我受益最多的就是那些关于唐代传奇小说的考证文章。从我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志人小说发展史论》,到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志人小说史》,再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对相关作者生平和作品年代的考订,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些研究工作中,既有我本人在掌握第一手材料基础上的创新发现,也有在广泛了解学界相关研究动态信息基础上的吸收借鉴。卞先生诸多关于唐传奇作者作品的考证,对我这方面的研究帮助甚大,诸如《〈纪闻〉作者牛肃考》《元稹年谱》《〈补江总白猿传〉初探》《〈长恨歌传〉新探》《〈开元升平源〉初探》《〈红线〉〈聂隐娘〉新探》《〈戎幕闲谈〉新探》《论〈虬髯客传〉的作者、作年及政治背景》等都是我学习研究时必备的参考论著,受益颇多。
其二是关于唐代小说内容的文化蕴含,尤其是政治文化蕴含。卞先生具有文史兼通的功底,因而他读唐代小说的一个独特优势,是能从常人作为艺术作品阅读的小说情节和人物言行中分辨出其中蕴含的唐代政治文化意蕴,从而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新鲜感和启发性。比如卞先生认为,唐代政局中党争问题在小说中留下很多痕迹,其中《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周秦行纪》《周秦行纪论》是共同围绕牛李党争主题,以小说进行政治人身攻击的典范;《玉泉子》则是作者借小说对牛僧孺本人暨全家进行丑化攻击的政治小说;而大名鼎鼎的《霍小玉传》则是作者蒋防为迎合元稹和李绅,以自己的政治对立面李益为原型,借谴责他在感情上的负心而影射攻击其政治变节。这些都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如他经过研讨分析,认为沈既济的《任氏传》和《枕中记》分别影射和取材于刘晏和杨炎;再如他联系柳宗元本人所写自喻龙女的《谪龙说》及历代相关评论,认为李朝威《柳毅传》乃为祝愿柳宗元走出政治困境所作等。
卞先生不但授人以鱼,还能授人以渔,以具体作品为例,传授演示如何在古代小说中发现作品政治寓意的具体方法。在《答问:怎样识别唐小说有无寓意?》一文中,卞先生以《义激》《唐国史补·妾报父冤事》《集异记·贾人妻》《原化记·崔慎思》四篇作品为例,从四位作者的不同经历背景中,找出同一故事原型在不同境遇作家手中的不同描写,从而彰显不同的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方法显然已经与西方学者提出的主题学研究、互文性研究等方法不谋而合,对我后来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对中国古代故事类型做文化分析的方法影响甚大。我每年给学生讲授“中国叙事文化学”课程中关于如何对故事类型进行文化分析时,卞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都是我强力推荐的必读书目。
卞先生这些研究成果让我如沐春风,如饮甘饴,醍醐灌顶,仅此而言,卞先生已是我一生学术经历中少有的几位重要学术引路人之一。
拜师卞门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我从硕士就读时起,心底就有个读博的愿望。但这个愿望一直磕磕绊绊,很久未能顺利实现。
最初的打算是,硕士毕业在南开工作后,在南开继续攻读在职博士学位。但这一计划因为各种原因,到我硕士毕业时就已经希望渺茫了。从客观上来讲,南开中文系虽然是国务院第一批授权的博士点,但当时申报的专业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导师是王达津先生。按当时教育部的学科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是两个并行的二级学科。也就是说,当时南开中文系,只有王达津一位导师能够招收文学批评史方向的博士生。但王先生自己有硕士生,校外也有许多慕名而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背景的考生。所以我也就不敢有这方面的奢望。在我硕士就读期间,南开中文系有个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室,由已故古代戏曲研究专家华粹深先生和古代小说资料学奠基人朱一玄先生以及宁宗一、鲁德才先生联手创办,加上先师刘叶秋先生的加盟,当时在该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本来希望以这个班底为基础,整合中文系古代文学其他方向的力量,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名义申报新的博士点。但随着先师的故去和宁宗一先生调离中文系,这个计划也基本成为泡影。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读本校博士学位的想法只好暂时搁置下来。代之以考博计划的,是我那几年苦心经营的几部学术著作:《中国志人小说史》《魏晋风度》《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等。
随着这几部书的陆续出版,我于1992年评上了副高职称。这是对我南开十年的鼓励和鞭策。与此同时,读博的愿望又在心底油然生起。由于卞先生的学术研究对我的深刻影响,几经权衡,我感觉无论是专业方向,还是人际关系,卞孝萱先生都是我最理想的导师人选。大约在1994年初,我给卞先生写信,表达了想报考他门下博士的愿望。卞先生很快给我回信,一方面说非常欢迎我报考,同时也善意地向我提出参考意见:“就个人条件资质来说,你没有问题;但目前读博还是有些现实困难,如脱离原单位,脱离家属,年龄也偏大等,都需要慎重考虑。一旦决定报考,你我双方,都要竭尽全力。”卞先生语重心长,坦诚相见。我完全明白他之所以全无推脱之意,完全是为我着想。所以也就慎重起来,暂时将此事搁置,并思考卞先生提出的几个问题能否有解决或缓冲办法。
就在我为此事踌躇不决的时候,经孙昌武先生推荐,我于1995年初到韩国高丽大学任教,为期一年。韩国的教学生活中,虽然上课多,但几乎没有其他事务干扰,自己能有时间做各种事情。其中考博问题仍然是我不肯放下的愿望和追求。我在韩国期间增加了与卞先生的联系频率,除了考博外,我们的通信还广泛涉及学术研究和学术环境等很多方面。卞先生对我有信必回,这让我这个后生晚辈十分感动和敬佩。经过一番斟酌,尤其是把卞先生提出的几个现实问题想好相关解决办法,我大致决定等回国后,就落实报考事宜。
1996年初,我回到南开,除继续中断了一年的工作外,开始进一步考虑报考卞先生博士的具体问题。1996年7月,我到卞先生的故乡扬州,出席由扬州大学召开的《儒林外史》研讨会。会后取道南京,专程去南京大学卞先生府邸拜访了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卞先生。他那魁梧的身躯,洪钟般的声音,渊博的学识和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一般的寒暄交流外,我主要就报考的相关情况请教了先生。先生告诉我,博士专业考试不会考那种死记硬背的书本知识,主要是考察文史研究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思维能力,所以无须做太专门的准备,倒是政治、外语这些公共课因为有硬性指标,需要有的放矢做好准备。卞先生的介绍让我精神上放松不少,也明确了备考方向。
回到南开,大约是秋季开学之后不久,南开这边的博士点情况却有了新的变化。鉴于孙昌武先生在唐代文学和宗教与文学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系里开始考虑重新申报以孙昌武先生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方向博士点。结果还没出来,又赶上教育部关于已有博士点可以就近学科增列博士生导师的工作安排。按照这个安排,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属于相邻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孙昌武先生也就按相邻学科,增补为南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方向博士生导师,并于1997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虽然是个好消息,但实际上也有点两难。一方面,我和孙昌武先生原是同一教研室(南开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多年同事,专业方向相近,而且私交甚好。我如果报考孙先生,更加方便。但另一方面,我已经和卞先生沟通联系多年,已经决定报考,不好爽约。于是,我就给卞先生写信汇报了这些情况。没有想到,卞先生很快回信,力主我报考孙昌武先生。他说:“你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学术基础,读博对你来说只是一次拓宽学术视野和提升境界水平的过程。这个目标在南京大学和在南开大学同样可以实现。而且,孙昌武先生的学术成就已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你可以从孙先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之前提到的几个现实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于我们之间,永远可以随时交流学术。”
就这样,我虽然很遗憾没能成为卞先生的嫡传弟子,但自认为是他永远的私淑弟子。
绵绵不绝的恩惠与友情
多年交往使我深深感到,卞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君子和师长。先师去世之后,他一再向我表示,会尽一切力量帮助我。卞先生是这么说的,也完全是这么做的。我们之间虽然没有成为名义上的师生,但我自认为卞先生对我的教诲恩泽,以及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师生关系,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人际关系财富。
从1991年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志人小说史》出版之后,每有新书出版,我都要给卞先生寄上求教。每次都能很快收到卞先生的手书回信,除了真诚祝贺,便是真正专家的点评,每每让我受教。1996年底,我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出版后,我照例给卞先生寄书求教,并且还斗胆请示先生可否写篇书评赐教。如此冒昧的请求,竟然也得到卞先生允诺。他写信说:“这部书填补了学术空白,非常有价值,书评一定写,但我目前年老眼花,很难通读全书;我让门生程国赋来通读一下该书,他主要搞小说,正好也是个学习机会,你们以后也还可以继续同行交流;他写好初稿后我来参与审订,署我们两人的名字。”我一个后生小子的冒昧请求,竟然能得到卞先生如此重视和悉心安排,感动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文章写好之后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题目为《资料翔实,考辨精当——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反响较大,对于拙著的宣传推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和程国赋兄的关系,也正如卞先生所预设的那样,已经成为学术同行和好友。
1998年,教育部做了一次博士点学科调整,原中国文学批评史二级学科合并到中国古代文学二级学科。这样,各校原来两个各自招生的单独学科打通,扩大和理顺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关系,无论是招生还是增列导师,都比以前方便顺畅。为纪念和庆祝这一盛事,南开中文系将原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三个教研室合并为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并于当年9月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工作交流会。参会人员均为各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很多学界大咖名流如约而至,欢聚一堂。我作为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承担这次会议会务工作。在发给各位博士生导师的邀请信中,我特别给卞先生写了一封信,盛情邀请卞先生莅临大会。卞先生欣然接受。这一年,卞先生虽然已是74岁高龄,但身体健朗,精神矍铄,兴致勃勃。会议第一天在校内举行开幕式,当晚移至当时的蓟县盘山宾馆继续开会。会后,大会组织游览盘山。我提前请示过卞先生,是否有兴致登山,卞先生兴致勃勃地说可以。登山那天,除了照顾大部队进程外,我和孙昌武先生全程陪同卞先生登上盘山南天门。一路上欣赏美景,畅叙友情,交谈甚欢。这是我和卞先生交往历史上最为幸福的时刻,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转眼到了2000年,经过三年学习和学位毕业论文准备,我完成了学位论文《士族之魂——〈世说新语〉中的士人人格精神》,并于6月顺利完成学位论文答辩。无论是答辩委员会,还是论文评审专家,都对论文给予较高评价。卞先生作为论文评审专家,评语中对拙文尤其青睐有加:
《士族之魂——〈世说新语〉中的士人人格精神》是目前很难见到的,下了大功夫的,学术价值很高的特优博士学位论文,具有方法新颖、气势宏大、结构完整、资料丰富、论证细密、表达清楚等优点。作者首次从精神史的角度,进行《世说新语》的研究。在对《世说新语》的内容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将魏晋士人的独立人格精神特征概括为:与社会意志分离的个体性、注重事物本质的精神性、超越实用功利目的的审美性。并将以上特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概括为:完成了从经济人格到文化人格的整体人格精神建构工作;人格精神独立是魏晋“文学自觉”的前提条件,为中国文化的滚动发展机制提供了范例。有理有据,可以成立。从论文反映出作者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念、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学风端正,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完全达到博士的学术水平,同意作者参加论文答辩。
卞先生对六朝文学和历史素有研究,不仅有论文多篇,而且曾经主编过《六朝文学丛书》。他凭借对六朝文学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准确把握住拙文的价值意义所在,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拙文的特点和价值,堪称慧眼独具。这个评语中的基本评价被吸纳在最终的答辩委员会决议中,成为我博士论文的专家定评。
学术良知与患难真情
一个人一生很难全然一帆风顺,遇到逆境和坎坷是难免的,关键是怎样面对逆境和坎坷。逆境和坎坷既是对本人的考验,也是对其周围师友的考验。好的师友能帮助当事人正确面对,走出逆境和坎坷。我一生遇到过两次比较大的逆境和坎坷,一次是“文革”期间遭遇家破人亡,一次是21世纪初遇到学术道路坎坷。如果说前一次是我的中学美术老师徐世政帮我走出逆境的话,那么后一次在众多善意相助的师友中,卞孝萱先生出力最多、影响最大,是我的命中贵人。
那段时间是我和卞先生通话通信最频繁的时段。卞先生一边了解相关情况,一边帮我分析引导。他对我说,从整个事件情况看,其中包含非学术因素和学术因素两个部分。非学术的因素可以通过非学术的途径去解决,学术的因素则需要用学术的办法来解决。同一位学者,同一部学术著作,学界产生不同学术评价和看法是正常的。既不能因为正面评价而视其为尽善尽美,也不能因为有负面评价而视其为一无是处,应该允许不同声音说话。卞先生还说,可以把他的看法公之于世,参与学术评价。
在当时那样的处境下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让我万分感动和激动。感动于卞先生用几十年的交往来践行先师刘叶秋先生去世后他要永远帮我的允诺,激动于卞先生在一些人避之不及的情况下,还能挺身而出,济人于危难。
我于1996年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该项目产生了两部书稿成果:一部是从文体和文化角度研究《世说新语》与魏晋文化的《传神阿堵 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部是从精神史角度研究《世说新语》中的士人人格精神的《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卞孝萱先生先后为这两部书稿作序。
卞先生在《传神阿堵 游心太玄》一书的序言《专、通、坚、虚》中说:
……在这篇序言中,我也用四个字——“专、通、坚、虚”来评述稼雨十几年的学术历程:
专 稼雨从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一直以六朝小说为其主要研究范围,已出版学术著作八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关于《世说新语》和六朝小说文化者约占一半,可见其专。
通 稼雨力求超越以往文学研究的某些框框,从文学与历史、哲学、文化学研究的结合上来思考和研究问题。例如对六朝小说的生成原理,他分别从诸子文章的“舛驳”走向,史传散文的“凭虚”流向,神话传说的社会化走向,诗赋文章的散体化倾向等四方面,对六朝小说的起源问题进行挖掘和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起源问题的认识。
坚 稼雨于1984年撰文,对“世说体”小说体制的形成渊源、体制特征及其思想文化蕴涵以及“世说体”小说的命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后继续钻研,提出系统看法。在这本新著中,对“世说体”的论述更为完善,体现了锲而不舍的精神。
虚 稼雨自序以“学无止境”为题,表现了不自满足的谦虚态度。举一个例子来说,关于魏晋士人服药的问题,他认为过去由于学力的原因,没有深入涉及魏晋士族道教神仙思想的重要内涵,是一个遗憾,在这本新著中着重予以考虑,并力求加以解决。
“专、通、坚、虚”四字是范文澜先生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用来衡量稼雨十几年的学术历程,可谓不谋而合。范老早年曾在南开大学执教,这也可以说是“流风余韵”了吧!范老还说过:“做研究工作,做了一辈子,也只能在知识海中取到一小杯水……但是,这一小杯水,必须经过辛勤的工作才能取得……任何一点知识,都是值得尊重的。”面对稼雨的新著,我衷心尊重,而他仍然心虚,并以这种心虚作为激发学问长进的动力,实在是难能可贵,我期盼着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陆续问世。是为序。
在这篇序言中,卞先生借用范文澜先生总结一生治学经验的“专、通、坚、虚”四个字来评价我的十多年学术历程和成绩,让我十分汗颜。但这是在当时境遇下,我从卞先生这样的大师那里得到的莫大鼓舞和鞭策。卞先生的良苦用心和鲜明态度,跃然纸上。
继为我的博士论文作出外审专家评语后,在博士论文的出版稿《魏晋士人人格精神》的序言中,卞先生又说:
……我之爱读《世说新语》,是从我到范文澜先生身边工作之后开始的。由于酷喜《世说》,对于研究《世说》的新人新著,自然也就十分关注了。稼雨就是我所瞩目的研究《世说》有成就的青年学者之一,《世族之魂——〈世说新语〉中的士人人格精神》就是我所欣赏的稼雨研究《世说》的系列著作之一。
……
稼雨画龙点睛地指出《世说》是“士族之魂”,其主要价值在充分展示了魏晋士人的人格精神,并体现了刘宋士人对它的认同。这是很正确的,也是很深刻的。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稼雨具体解剖了《世说》这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提出了怎样看待古代士人人格精神的特点及其演变发展的历史,魏晋士人人格精神对后代的影响等问题,很有启发性,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这本书中,稼雨对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数据的关系,结合得很好,由考立论,使人信服。书中谈到婚姻、服饰、饮酒、娱乐、服药等实际问题,但能以实论虚,实中见虚,归结到士人人格精神上来;而谈佛论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又不流于抽象,能虚中见实,立足于材料的分析。作者深知,作为精神史的研究,理论与考据二者缺一不可。缺少考据的精神史研究又会显得散乱。二者的综合运用,是此书方法论的实现。这对于文史研究的其他课题,也是可供参考的。
……在众多的魏晋士人品格、风度的论著中,稼雨之文,光彩夺目,摩挲书稿,老眼增明,故欣然而为之序。
该序进一步丰富拓展了论文评语的内容,将其覆盖到更为广泛的学术视野和背景上。除了卞先生的序,这部书稿还有前《文学评论》主编敏泽先生的序,两位学者没有相互通气,但学术评价角度和评价尺度几乎不谋而合,可见学问大家的学术眼光自有其默认的基本尺度和标准。
这篇怀念文章在我心里酝酿了十多年,终于得以一挥而就。愿以此向卞孝萱先生致以生命中最诚挚的敬意与最深切的缅怀。
壬寅三月于津门雅雨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