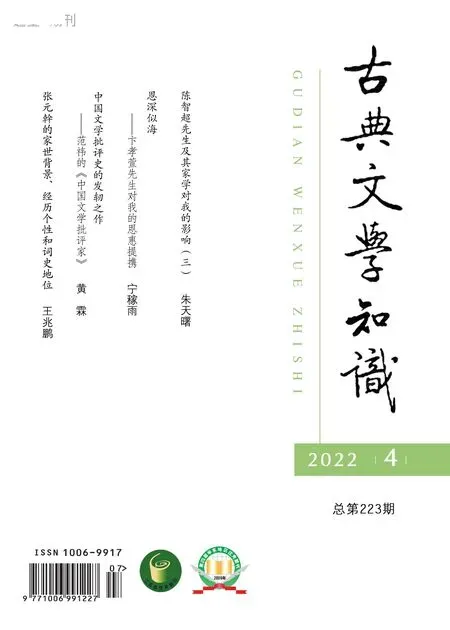沈德潜的“遇”与袁枚的“不遇”
陈圣争
一
当时可能谁也不会想到,乾隆四年(1739)会成为清代诗坛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此前诗坛仍笼罩在康熙诗坛的余风之下,此后则开启了乾嘉诗坛繁盛局面的序幕。因为乾隆诗坛两大教主式人物皆在是年会试中式,殿试后皆赐进士出身,朝考后皆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一个是沈德潜,“格调说”的代表人物,会试第65名,殿试后赐二甲第8名进士;另一位是袁枚,“性灵说”的主要倡导者,在诗歌创作上又是“乾隆三大家”之一,殿试二甲第5名进士。是年沈德潜67岁,而袁枚24岁,二人年辈几乎差了两代,但科举后则成为同年。
在以科名为重的时代,考中进士是进入仕途的最佳入场券,无论是大器晚成的沈德潜,还是少年得志的袁枚,这一年对他们来说都是幸运年。对于沈德潜来说,更是他的转运年,因为截至乾隆三年他已经参加了17次乡试。当他长期蹭蹬于科场时,即便再是老名士、诗文名家,也依然是乡闾愚夫村妇的笑柄,“当公偃蹇青衫,咿唔一室,里巷之士目笑而去之,甚者揶揄诋讪,摇手戒子弟勿复效其所为”;而平时交好的友人,“亦相顾太息,以为命也”。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从此发生彻底的改变。对袁枚而言,也极为幸运,至乾隆三年他已参加过4次乡试,此次联捷而中进士,可谓少年科甲而名重一时。
二人取中进士后,又幸运地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虽然袁枚的朝考诗因语涉不庄而差点落选,但在尹继善的力争下还是得以选为清书庶吉士(即以学习满文为主)。选入翰林院,这对考中进士的人来说是一种无上荣耀,因为一是人数少,二是出路广。在当时,翰林官员不仅是皇帝的“文学侍从”,还可考选御史,充主考、学政,放府道,甚至可以升转京堂诸官,有些官职更是非翰林出身者而不授。庶吉士虽非正式官员,但一般三年期满散馆考试后,一等者留馆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二等者多授为各部主事,末等者则多外放任各地知县或县丞,或再延长庶吉士的学习时间。
命运女神在这一年向他们都打开了幸运的大门。尤其对袁枚而言,他才24岁,年轻而才华横溢;且还有尹继善、鄂尔泰等众达官贵人相助,留馆对他来说犹如探囊取物。他本人也对个人才华极为自信。乾隆元年他去广西投靠叔父袁鸿时,巡抚金鉷一见大奇,目为国士,且逢人说项,甚至还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认为他是“奇才应运,卓识冠时”。这是袁枚第一次以才华征服了一位二品大员。参加博学鸿词时,一到京城初次见面便得到名士胡天游的不吝夸赞,“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并将他介绍给齐召南、商盘、杭世骏等前辈学者或诗人。这是袁枚又一次受到前辈们的推扬。选入庶常馆后,他更是自信心爆棚,自认为“我才较跋扈”,再经过与同人的砥砺,更加觉得元、白不在话下,更可直追徐陵、庾信。
然而,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乾隆七年(1742)四月十九日,庶吉士散馆考试,沈德潜为汉庶吉士,考诗赋;袁枚为满庶吉士,则考满文翻绎。四月二十四日,成绩公布,沈德潜考得一等第4名,袁枚则屈居末等。乾隆帝谕旨沈德潜、裘曰修等授为翰林院编修,袁枚、曾尚增等则以知县用。
二
俗话说“人生七十才开始”,此话于沈德潜犹如私人订制,乾隆七年,他恰逢七十,以翰林院编修开始踏入仕途。乾隆八年的一年之内,沈德潜连升四次,从正七品升至从四品——由翰林院编修擢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一岁之中,君恩叠稠”,让沈德潜既惊喜又惶恐,“不知何以报称,窃自惧也”。乾隆九年至十二年,又以从四品升至正二品(礼部侍郎),并入上书房教皇子读书。五年间升至卿贰,真是羡煞旁人!乾隆十四年,以原官致仕。乾隆二十二年南巡,沈德潜得加礼部尚书衔(从一品),让他老泪纵横地感慨“天恩优渥,蔑以加矣!”真的无以复加了么?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93岁的沈德潜扶病前往武进接驾,乾隆帝天语暖人,备问其病情及子孙情况,除赏赐物品、赐其孙为举人外,又加衔太子太傅(从一品),并改食正一品俸,让他再次深深感慨“君恩之高如戴履天地之高厚,而莫能报效者也”。除了对沈德潜厚以禄位之外,还诰封四代、赠封妻室、荫赐子孙。如此君臣相得的一段神话,连同为“二老”的钱陈群也羡慕不已,后人更是一再感慨“诗人遭际至于如此,古未尝有也”。
是谁在造就这段艺林神话呢?在一切都是帝王说了算的时代,功名利禄,只要皇帝想给某人,自是荣禄加身。钱陈群曾在《神道碑》中颇为隐晦地说“顾上所以裁成之者,亦复无所不至”,可见是乾隆帝故意要玉成这段佳话,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乾隆帝为什么要成就这么一位老名士呢?且众多老少诗人,又为何偏偏选中沈德潜?事实上,乾隆帝曾明言:“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早以诗鸣”,早到什么时候?康熙三十七年(1698)前后,尚为叶燮弟子的沈德潜,诗名已为王士禛所知。当时王士禛特地致书叶燮,说沈德潜已得其髓,并致书尤侗之子尤珍说“横山门下尚有诗人”。是以沈德潜可上接康熙诗坛,确为时辈难及。又据沈德潜本人记载,散馆时乾隆帝曾询问其姓名籍贯;留馆后轮班引见,乾隆帝还特地跟张廷玉说“沈德潜系老名士,有诗名”;作为现场见证人的袁枚也说,在散馆时乾隆帝就问谁是沈德潜,沈德潜跪奏,君臣这一问一答,令当场所有人都明白他已“简在帝心”;袁枚后来更将时间推至雍正初,认为时在潜邸的乾隆帝就已击赏沈氏之诗。
那么乾隆帝仅凭沈德潜有诗名就敲定他为代理人么?非也。有诗名,仅是充分条件;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两人诗歌主张的契合一致。他们最初论诗的契合点是“温柔敦厚”,后来乾隆帝更将这一传统的“诗教观”直接转化为世俗的“忠孝论”。乾隆帝曾说:“余虽不欲以诗鸣,然于诗也,好之习之,悦性情以寄之,与德潜相商榷者有年矣。”通过频年论诗,认为沈德潜名实相副之后才最终确定人选。
不过,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乾隆帝并非是以简单粗暴的谕令方式,而是设法让沈德潜感恩戴德地去主动宣传。他深谙文人的习性:一面盼着加官晋爵以光宗耀祖,一面要保持尊严和虚荣。是以乾隆帝在物质上厚以禄位,一再擢升沈德潜,并诰封四代、赠封妻室、荫赐子孙;精神上则极力地满足沈氏虚荣。他折节以和沈氏诗韵,让沈德潜觉得“君和臣韵,古未有也”;并一再主动赐诗、问候;甚至当沈德潜进呈诗集并“敢恃宠以请”题序时,他虽知“人臣私集自古无御序例”,但还是在小年夜熬夜为其写序,让沈氏更觉荣耀至极,“从古无君序臣诗者,传之史册,后人犹叹羡矣”。这一事件也将二人关系推向最高峰,一时朝野上下惊羡不已,如黄叔琳、汪由敦、蒋溥、梁诗正、嵇璜、董邦达、彭启丰等高层文士争相传颂这一奇闻,袁枚后来甚至将它写入《神道碑》中。沈德潜致仕时,乾隆帝御书匾额“诗坛耆硕”以赠,更是向士林昭告沈德潜是官方代表的诗坛大宗师。
乾隆帝的一系列行为确实产生了良好的效用,优渥的皇恩将一个几乎快绝望的“老名士”迅速打造成一代宗师,让沈德潜深深地觉得若不鞠躬尽瘁地涌泉相报真是耻为人类。但作为一介文士,他能做什么呢?唯有在做好文学侍臣的工作外,积极响应乾隆帝的诗学观念,并自觉地付诸行动,宣告士林,报答君恩。首先,他将个人书斋取名为“教忠堂”,其义不言而喻。乾隆帝还赐诗说“斧邱陈奠处,不愧教忠堂”,将“教忠堂”拈出就是暗示沈德潜要牢记“教忠”的深意。当他致仕离京时,乾隆帝更明言“汝回去,与乡邻讲说孝弟忠信,便是汝之报国”。这“忠孝”不仅是对行为处世、品格德行的要求,也是对写诗作赋的要求。其次,改变自己的诗风以附和乾隆帝。二人在探讨诗学之后,沈德潜开始渐渐地趋同乾隆帝的观念,连作诗都一改昔日诗风,“于向日所为壮浪浑涵、崚嶒矫变、人惊以为莫及者,自视若不足,且有悔心焉”。是以其后不仅经进诸作“原本忠孝”,甚至凡作诗,都是“以忠孝为本,以温柔敦厚为教”。最后是续选诗以导士林所向,在评语中将乾隆帝诗学观念贯彻其中。
其中,《国朝诗别裁集》(后世称《清诗别裁集》)一书用心最著,从序言到凡例一再申明选诗要“合乎温柔敦厚之旨”。除“温柔敦厚”是他们共同的主张外,由于乾隆帝反对绮靡浮华、坚决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沈德潜便在凡例中反复强调这两点。然而乾隆帝只是个人不为风云月露之辞,但沈德潜则变本加厉地放大到凡有言男女之情者,一概不录。沈德潜本以为如此煞费苦心而成的诗选,定会邀获圣眷。不过,却没想到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很明显的皇家忌讳:在诗选中他竟然敢直称慎郡王允禧的名讳,慎郡王是乾隆帝的叔父;且还有不少皇亲宗室皆直呼其名且未将皇室宗亲单列于卷首,皇家尊严何在?第二个错误也是最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首列钱谦益、龚鼎孳等人之诗,并选有钱名世的诗。钱谦益、钱名世等早被乾隆帝定为“不忠不孝”之人,在乾隆帝看来,“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是以乾隆帝大为光火,直骂沈德潜“老而耄荒”,认为此举是“非宿昔言诗之道”。二人亦师亦友的特殊君臣关系由此出现难以修复的裂痕。
三
同时的袁枚,则在庶吉士散馆考试后外放为知县。起初,在选为庶吉士后,袁枚对于留馆一事自信满满,更经常与裘曰修、金文淳等同人诗赋酬唱,砥砺诗文;但是散馆考试屈居末等而美梦破灭。又乾隆七年三月曾下诏推荐言官,留保、史贻直等皆以袁枚为荐,而事又不果,再次击碎了留京之梦。虽然知县与翰林院编修同为正七品,但在袁枚看来是“小谪”,从此“银汉隔红墙”,难再以诗赋报皇恩;而且其自信心严重受挫,灰心地感叹“生本无才甘外吏”;更觉得辜负了国恩及友人的期待,“既他公论偏怜我,黼黻终惭答紫宸”。
袁枚初官溧水知县,二个月后调为江浦知县。乾隆八年初,改官沭阳知县。县任事务剧繁,又逢旱灾,他既要监管赈务,又要管理河工,还要去征漕粮,忙得焦头烂额,急得疮疾复发。在他忙作一团时,同年裘曰修、沈德潜等却相继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沈德潜更是一年连晋数级,这让他作何想呢?在贺喜同年高升之余不免惆怅不已,“宦海烟波逐渐分”,深知自己从此与他们的差距日益拉大。乾隆十年时,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帮助下,他又从沭阳调为江宁知县。乾隆十二年六月,高邮知州员缺,尹继善等又将袁枚报升,但因户部咨查“欠漕项钱粮事”而被“照例停其升转”,高邮知州事又因此泡汤。而此时沈德潜已升为礼部侍郎,甚至连一同外放江南的同年曾尚增也升任广德州知州,他怎能不生出一番幻灭感?于是便心生辞官之意。乾隆十三年,他买下隋氏废园为辞官隐居准备,朋好们来贺时,就放言“异日将官易此园”。是年秋,多事烦扰,流言中伤、母亲生病、恩师移粤等,他便毅然辞官。其后往返于江宁、苏州,常住随园。乾隆十七年初虽一度入京补官,又因父卒丁忧,便于是年冬归随园。自十八年始,袁枚不复出仕,从此过着大隐于市的文士生活。
袁、沈二人本来同年进士、同选庶吉士,以年龄来说,袁枚有着绝对优势,以才华而言,恐更在沈德潜之上,但最终二人在仕途上若云泥之隔,诗学观念上更是分道扬镳。在袁枚看来,沈德潜以诗而遇是乾隆帝早就简在帝心;但袁枚为何就没有以诗遇知、以文章报国恩呢?在朝考时,他就语涉不庄;不过,以他的才智及诗才应该很快就熟稔应制诗的体制,却为何只能辞隐?这或许与他的性格、诗学理念有关。
虽然袁枚曾说他与沈德潜“乡会同年、鸿博同年,最为交好”,但实际情况或并非如此。在庶常馆时,袁枚经常与金文淳、裘曰修、沈廷芳等人雅集,而沈德潜很少参与。袁枚离京时,沈德潜随同人赋诗以送;在离京途中,袁枚作《怀人诗》中亦有沈德潜;当沈德潜升为侍读学士时,袁枚亦作诗为贺;但随着沈德潜的日益高升,而他依旧沉沦下僚,地位的差距越来越大,友谊也渐渐疏远,正如他所言:“进士同年较乡试少,故相亲亦倍焉。若同入翰林则更少,且更亲矣。然不数年,升沉顿殊。或为名位所移,异目相视,即阳为谦下,而阴实相疏者亦比比然。”这“阳谦而阴疏”的同年中是否就有沈德潜呢?据二人生平交际来看,极有可能。
二人关系若真如袁枚所言的最为交好,又岂在乎地位、年龄的差距?但实际上在二人的诗文集中提及对方者颇为有限。如果说二人皆为官时,一在京城、一在江南,交往少也说得过去;但袁枚于乾隆十三年底辞官,十四年归家,后长期往来于南京、苏州;沈德潜亦于十四年初致仕,六月就回到苏州;且二人还有着共同的朋友圈;然而奇怪的是,二人来往很少。乾隆二十二年,沈德潜游南京,并没去随园看望友人,惹得袁枚写诗询问:“何事蒲轮游白下,不来小住说沧桑?”乾隆二十三年两江总督尹继善招沈德潜游摄山,而袁枚亦曾于初冬陪游摄山;不过,沈德潜后来追和过尹继善和袁枚《侍宫保游栖霞作》诗韵,而袁枚似无回和之诗。但是在这年十一月袁枚到苏州小住时,沈德潜曾向他征诗以悼念薛雪外孙。二十四、五年间,袁枚曾就《国朝诗别裁集》选诗问题连写二札与之论诗,而沈德潜没有回复。二十八年夏,袁枚害疟往苏州求医于薛雪,沈德潜曾去探望,袁枚题诗扇以赠,沈德潜亦和诗以寄。乾隆三十年闰二月时,袁枚请吴省曾作《随园雅集图》,将沈德潜绘入其中。此后交际更少,直至乾隆三十四年沈德潜卒,袁枚赋挽诗并撰《神道碑》。由此可见,二人皆自乾隆十四年家居,二十年间的往来并非亲密无间,反而显得不淡不咸。
究其原因,除了年龄、名位的差距外,可能二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且各有各的生活交际圈子——各自经常有同人雅集或诗酒酬唱,却很少有交集。二人虽同为诗文名家,但在诗学观念上则“势如水火”——更确切地说是袁枚绝不屈己以从人,难以莸薰同器。
两人在诗学上有很多针锋相对处,如沈德潜标举唐音,而袁枚则认为诗无唐宋之分;沈德潜强调模仿,而袁枚则强调创新;沈德潜强调格调,袁枚强调性情;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一个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提倡“温柔敦厚”;一个突出诗歌的审美功能而提出书写“性灵”。这些大都只是二人平时的主张,并未正面交锋,但在沈德潜选刻《国朝诗别裁集》后,袁枚连写二信给沈德潜发表他对诗的见解——诗学史上所谓的“沈、袁之争”。然而,在这所谓的争论中,沈德潜实际上是缺席的,他没有回复,也无法回复。袁枚曾指出诗选中“诗贵温柔”数语有“褒衣大袑气象”,并曰“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褒衣”虽有二义,但袁枚所言“褒衣大袑气象”却意指沈德潜有人撑腰,是谁,显而易见。所以袁枚不敢口非,不敢公开地跳出来唱反调,只能私下反对。而面对袁枚的质疑,沈德潜无论回复是与不是,都会陷入两难之境,是以他只能选择置之不理,因为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诗学讨论。然而,这一诗选却又让沈德潜两面都不讨好:乾隆帝认为他做得不到位,甚至还有误差;而袁枚则认为他做得太过,完全是扯虎皮拉大旗。而且袁枚还将二信公开示人,虽然沈德潜缺场,但袁枚却至少公开地宣扬了“性灵说”。
此后他更借着多种途径,如雅聚、倡和、诗话、书信、授弟子等方式肆力宣传其诗学主张,好友程晋芳曾劝他删除集内缘情之作,袁枚则借机大谈特谈“性情”(《答蕺园论诗书》)。此外,他还多次对当时诗坛恶习——叠韵、和韵等现象提出批评,矛头更直指乾隆帝。虽然他也明白沈德潜坚持“诗专主唐音,以温柔为教……皆正声也”,但若不唱反调不足以发出声音。在“官位与诗名、政界与诗坛”几乎合而为一的诗坛,他既无法复制沈德潜的模式,也无法像盐官卢见曾一样时常雅集,甚至像盐商出身的汪孟鋗兄弟那样搞沙龙都难以持续。若踵续官方一套论调,在乾嘉众多人物中根本无法出声,其主张又岂会成为诗坛盛行的诗论之一?是以他不得不剑走偏锋地由“文章报国”转而以“诗赋名家”。不过,他至死前都在回想科场的荣耀,如在博学鸿词时他遇到了第一位贵人金鋐,庶吉士朝考时他又遇到了第二位贵人尹继善,是以也可以说科举改变了他的人生。
四
然而,人生之遇与不遇实难料,亦难定论。沈德潜生前虽占尽名位,风光无限,却随着卷入一系列的事件当中,不仅人被活活吓死,身后更惨遭“仆碑撤祠”。既能予之,必能取之,这一切都是乾隆帝在导演着,遗憾的是乾隆帝没有将这一场旷古绝今的文坛佳话演绎圆满。不过,这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伴君如伴虎”,倒有点类似“靡菲斯特”的契约:签订时间从乾隆七年始,甲方给予乙方世间的荣誉、地位,乙方则需要舍弃灵魂以报答甲方。但是这契约中甲方知道他该怎么做,乙方却没有具体条目规定该怎么做,是以一旦甲方觉得不满意,就意味着乙方毁坏了合同,那么甲方就会强有力地收回一切。因此乾隆帝一再强调是沈德潜辜负了他,他没有对不住沈德潜。然而名位之事是显性的,灵魂之事是隐性的,谁是谁非,如今都成为一堆故纸。只是悲剧的发生也多多少少与沈德潜自身有一定关系,不说完全咎由自取,但他若能更谨言慎行,固守他的本分,或许不至于身后酿成惨剧。
而袁枚二十出头即预博学鸿词,二十四岁中进士,早就声闻士林。他也想过侍奉玉堂,文章报国;而被外放知县后,他意识到梦想跟现实的差距,一度还生发幻灭感。当升迁一再受挫后,便毅然辞官,从此归隐于市。他对自己、对当时社会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在意识到仕途无望,踵续官方言论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便逐渐走向官方的对立面,提出“性灵说”,并不失时机地让沈德潜做了一回枪靶子。随着声音能量逐渐扩大,随从附和者日益增多,声势日益浩大而成为青年的导师,其诗学主张也成为乾嘉诗坛三大主要潮流之一。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推崇平民文学,曾经的那一套官方主张被扫进了故纸堆,袁枚其人其论在新文学中也更加闪耀出异代的光芒。遇与不遇,幸与不幸,又何可易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