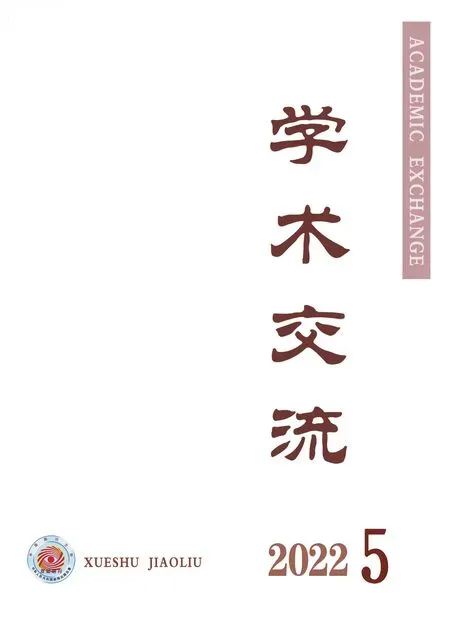《歧路灯》的“理治小说”价值
杜贵晨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清乾隆间问世的李绿园著《歧路灯》是一部小说。其异于“四大奇书”等小说的突出特点是为“使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的淑世效果而作。这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部化理学为故事,以故事讲理学的“理治之书”,即“理治小说”,是皇权时代士族阶层的教子宝典、治家龟鉴、救世良箴。
一、教子宝典
教子是李绿园预设的《歧路灯》主题。其以孝为本,第一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前半写孝,后半写教,表明《歧路灯》一书起于孝,承以教,为孝而教,把教子作为自己生命与家族延续火焰生光的“第一宗事”,成为全书叙事写人的真正中心,时时关照,处处提点,总结了历代教子最重要的经验:
其一曰寓爱于教,施教以严。《歧路灯》第一回开篇写谭孝移的独生子“端福儿已七岁了,虽未延师受业,父亲口授《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又自祖籍丹徒“千里申孝思”,因“夜坐,星月交辉之下,只听得一片读书之声,远近左右,声彻一村”,更引起他回家后急于延师教子。其后至第十二回谭孝移在对儿子死不瞑目的牵挂中去世,单是写谭孝移生前心思,用“教子”一词就有7次。而全书前后共十二回15次用到“教子”一词,除表明全书核心主题是“教子”以外,更是突出了父爱如山,深情似海,以及“教子”乃上关祖宗,中关自身,下关子孙的“第一宗事”。为此,谭孝移延师不吝登门拜请,不惜告病辞官,更无奈临终遗嘱以“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八字小学”,并托孤于友人与老仆等。他竭尽全力“教子”,虽然为的是“遗安”,但目的却是使儿子能成才自立,不坠家声,一生平安。此所谓“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乃古今一辙,贫富无二,值得今天每一个中国人再思、深思,永远记取。
然而,《歧路灯》写谭孝移的“教子”以“一掌寓慈情”起,当时王氏已为孩子辩护说“孩子还小哩,才出去不大一会儿”,至今多数读者,或以为粗暴过分,若在某些国家甚至就是犯法了。但是,纵有各种看法、对待的不同,却都必须承认,“一掌寓慈情”写出了中国或东方特色的“爱子”之心,一种家族主义价值观的“父爱”。其动机无疑掺杂了家族名声地位的利益,“打是亲,骂是爱”的做法也有悖文明,但由此突显谭孝移“父爱”的特征是一个“严”字,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谭孝移与夫人王氏之“母爱”失之于“宽”的对立。而娄潜斋作为塾师,从其赞同学生端福儿由大人带了去赶吹台大会,以及他又对谭孝移说“教幼学之法,慢不得,急不得,松不得,紧不得”等语看,是主张宽严有度的,也似乎更有道理。但是至谭孝移死后,谭绍闻学坏入了下流,乃又有潜斋道:“于今方知吹台看会,孝老之远虑不错。”(第十四回)就曲曲折折又回到了谭孝移“教子”以“严”的主张上来了。由此可见,《歧路灯》的教子之道,虽然不能说已经十分明确,但大体的结论是宁肯失之于严,不肯失之于宽。这个经验值得深思。
其二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歧路灯》写谭孝移请娄潜斋为塾师教子的想法说:“我想娄潜斋为人,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小儿拜这个师父,不说读书,只学这人样子,便是一生根脚。”(第二回)就是这个意思。但这样的“人师”如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娄潜斋中举去后,请到继执教鞭的侯冠玉、惠人也,都是“经”也不行,“人”也不行。固然做主请先生的王氏见识差,但孔耘轩替女婿请惠人也,也是找来找去找不着更好的,不得已凑合了。可见教子的关键在教师,延师之不易在“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为师之不易在“经师易做,人师难当”。那么,教师的选聘与尊严就成了教子的“第一宗事”了。《三字经》说“教不严,师之惰”,近世说教育的关键在教师,就都包含这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教育如果不是首先把教师的事办好,其他就都是舍本逐末,没有希望。
又从谭绍闻先后受学的四任塾师看,教师也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地位与责任,是学生父母教子责任的转移和替代。每一个做教师的,当思自己的工作来自学生父母的委托,并且自己也是为人父母,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以教子之心做好教学工作,这也是与山海一样大的责任。但为人师者,却真真切切,应该有为学生父母的样子与心情,有“化为春泥更护花”的责任心与奉献精神。反之,不好好教书,不能把家长嘱托代为教子的责任认真担当起来,误人子弟,甚至害人子弟,岂止沐猴而冠,实等同于“杀人”——谭孝移所谓“杀吾子矣”!
《歧路灯》写教子,不止写了谭孝移一家,还写了娄潜斋、王春宇等家;不止写了“教子”,还写了孔耘轩家“教女”。又,书中写谭孝移教子,虽然并不顺利,但历尽坎坷,谭家教子是“第一宗事”的家风坠而复振,毕竟世代相传,不仅谭绍闻改志后带儿子兴官一起读书上进,而且兴官的嫡母孔慧娘、继嫡母巫翠姐以及生母冰梅,先后也都注重教子读书。第七回《读画轩守候翻子史,玉衡堂膺荐试经书》写谭孝移“到大堂,看了匾额。孝移自忖道:‘先人居官之地,后代到此不过一看而已。这个不克绳祖的罪过,只有己心明白,说不出来。’”因此,一心只想教子读书成名,以干父蛊,别个并无良策。这段描写今天的读者可能讥笑,但看看每年“公考”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大概中国人仍不乏这种“大小是个官,胜似点水烟”——做官、做大官的谭孝移心态。
其三曰教求“功名”,更树“正人”。《歧路灯》写教子的人生道路与目标是读书做官,但并不首先和一味地强调做官,而是要求其“做人读书各宜努力”(第九十二回),连读书也是第二义的。至于具体操作,虽不过《三字经》中所列私塾教学的程序与内容,但强调“如此读去,在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时,自是经济良臣;最次的也还得个博雅文士。若是专弄八股,即是急于功名,却是欲速反迟……未有不坏事者”云云。这些话写教师、教材以及教学的目标,只需要换上新的说法就与时俱进,而“现代化”了。所以,最根本的是它讲“教子”的目标:“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云云,虽然以“经济良臣”为首要,但也并不一定做官。我们看书中甚至以“一发不认得字”的娄潜斋的令兄和低贱至奴仆如王中,以及“州上的一个皂役”(第七十二回),都可以被称赞为“正经理学”或“大理学”,就可以知道,《歧路灯》为“用心读书”所设定的目标,固然是做官、做大官好,但官不一定是人人能做和做得上的,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只要读书有了文化,是一个知书识礼的文明人,也就是没有白读书一场。这才是教子的正路和平常心,每一个做父母或教师的人,都应该从这里得到启发,把教育的目标定在提高学生安身立命的觉悟与素质上,培养应世处事造福家庭与社会的能力。这才是《歧路灯》教子主题的本质,也是其作为教子宝典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总之,读《歧路灯》,不要只看到它写谭绍闻败子回头以后家庭如何火焰生光,更不要心艳功名富贵,啧啧于结末的“洞房花烛”“金榜题名”。那即使有一定真实性也只是一个异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李白《行路难》诗中说:“多歧路,今安在?”多数人读了书,如程嵩淑、孔耘轩、张类村,虽然“都是些半截子功名,不满人意的前程”(第七十七回),其实就是好的。这些人能一生读书、著书,与书为伴,治身理家,为善乡里,有裨时代,为“老成典型”,不也是人生的成功吗?
二、 治家龟鉴
教子从来就不是请一位好教师就万事大吉了。教子是一个系统工程,“延师教子”作为谭孝移的“第一宗事”,同时也就是一个家庭事务中的“第一宗事”。古语“兴不兴,看后丁”。《歧路灯》中人物命名“绍衣”“绍闻”以及名不副实的“(张)绳祖”等,特别是给冰梅为谭绍闻生的儿子取乳名“兴官”,学名“篑初”,寓意也无非是教子乃一个家庭“上关祖宗,下关儿孙”的“第一宗事”。因此,《歧路灯》同时又是一部“家政谱”,堪称治家之龟鉴。
作为“家政谱”,《歧路灯》描写了多种多样家庭。这些家庭或兴或衰,或盛或败,或败而复兴,兴而能盛,各有因由。虽然“兴不兴,看后丁”,子弟教育培养是最后关键,但最后关键的关键,又反过来在于有一个好的家风。为此,《歧路灯》或正或反或侧,深入描写了各种治家的经验教训,而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曰以孝为本,积德成庆。上已论及《歧路灯》为书中老主人命名谭孝移,“谭”即“谈”,“孝移”字“忠弼”,即“移孝作忠”为朝廷辅弼之义。但书中写谭孝移及身作为,并未名副其实,而是作为书中描写的谭宅的活祖宗,代表了谭家一族的“根柢”,即“孝移”于“教子”的世代传承。这个道理即是书中写“孝移”的儿子名“绍闻”,族侄名“绍衣”的寓意。“绍闻”“绍衣”,取自《尚书·康诰》“绍闻衣德言”。绍,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曰:“继也。”闻,指旧闻。衣,同依,依照。孙星衍疏曰:“《学记》:‘不学博依。’依或为衣。言今之人,将在敬述文王,继其旧闻,依其德言。”又曾运乾《尚书正读》释曰:“衣,当为殷。……言今民将察汝之敬述乃文考,绍文考所闻殷之德言与否也。”文考即周文王。这是武王告诫康叔的话,大意是责成康叔要继承依照从文王所闻殷商之德为人行事。《歧路灯》第五十五回写程嵩淑道:“尊公名以绍闻,必是取‘绍闻衣德’之意,字以念修,大约是‘念祖修德’意思了。请问老侄,近日所为,何者为念祖,何者为修德?”就是从上述意思责备谭绍闻。由谭家两代三人的命名可知,《歧路灯》故事的核心是教子,教子的核心是孝,孝的核心是“绍闻衣德”,又集中体现于谭绍闻字念修的“念祖修德”。所以,这部书一切从“根柢”上说起,一切又都说到“根柢”上。其所传达的最重要经验,给读者最大的教训,就是要立一个好的家风,世代保持发扬下去。书中谭(谈)族是这样,写娄潜斋、孔耘轩等家庭也是如此。故尔这几家子弟结果都得了好处。而某些“门户子弟”,如夏逢若之由“门户子弟”沦为“匪类”之尤,即因为“他父亲也曾做过江南微员,好弄几个钱儿”(第十八回)的“根柢”不正,所以最后落了个发配极边的下场,可不慎哉。
其二曰勤俭持家,耕读继世。《歧路灯》所描写的社会众生,还绝对未至于有科学发明造福人类的思想,又多中下层人物,难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宏愿,所以多的是士商小康之家保家守业聊以卒岁之想。从而其治家的理念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如第十九回针对盛希侨如一把“天火”正在烧损自家的情形,写其祖上所遗手书楹联曰:“绍祖宗一点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曰读曰耕。”用意显然是对盛希侨这个败家子的讽刺,但也正是代表了作者对治家之道的基本看法。所以,书中写凡是“正人”的家庭,如娄潜斋父子读书应试,长兄与侄儿持家务农,书房院里,“一个十三四岁的家童,在那里学织荻帘儿;书房内高声朗诵”(第二回);孔耘轩家女儿慧娘“十一岁了,把家中一张旧机子整理,叫他学织布”(第四回)等等,即使王春宇弃儒经商,但由于勤恳加上精明,艰苦备尝后也终于发家。所以,勤俭特别是“勤”于努力做事的人,总是能到了好处。相反如张绳祖、夏逢若、王紫泥等人一味下流,结局则无不潦倒沦落。《歧路灯》大量描写这样的人生情景,使有家有子者读之,确为苦口良药,从而为“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歧路灯〉自序》)。
其三曰家和事兴,有容乃大。《歧路灯》写治家,同样卑之无甚高论的是一句“家和万事兴”。为此,书中最反对兄弟分家。第三十九回写程嵩淑讥刺就有“偏是那肯讲理学的,做穷秀才时,偏偏的只一样儿不会治家”的话,张类村道:“嵩老说不会治家,其实善分家;不会做官,却极想升官。”从而书中写得最多是父母去世而兄弟仍旧在一起过日子的家庭,如娄潜斋、孔耘轩,都是兄长主家,哥弟和顺的家庭。娄家更是耕读相兼,读书做官,把日子过得火焰生光。还有一位是第二回写陈乔龄提到的秀才黄师勉,“兄弟两个,有一顷几十亩地。他哥要与他分开,他不愿意,他嫂子一定要分。他哥分了大堤内六十亩地,他分的也不知在那个庄子上……前五六年头里,黄河往南一滚,把他哥的地都成了河身,他哥也气的病死了。这黄师勉把他嫂子、两个侄子,都承领过来养活,只像不曾分一般”,所以知道的人“都说他这宗好处”。反而惠养民字人也人称“惠圣人”,讲理学“坐的师位,一定要南面,像开大讲堂一般”,却顺从继室滑氏私积坐馆的酬金,与他忠厚老实在家务农的兄长分家,结果“得了羞病,弄得身败名裂,人伦上撤了座位”,成为秀才中“不会治家,其实善分家”的典型。反而第六十七回写张类村与他的侄儿张正心虽然已经析居,正心贫寒而张类村年老无子,眼见得将来张正心继承伯父家产。但当张类村与婢女生了儿子以后,张正心一力维护照顾堂弟,不使被妒妇所害,张类村夸奖他:“今日全得力的是这个舍侄。这舍侄前日取了一等第三名……全不像东院宋得明的侄子,只怕他叔得了晚子,他就过不成继。全不知亏损了自己阴骘,将来还想亨通么?”
虽然《歧路灯》不分家的主张未必总是可行,但是,它提倡“家和万事兴”的用心可嘉。为此,书中开出的良方:一是兄弟“每日同桌吃饭”(第二回),等于每天三次会议,相互无隐,事事明白。二是从外面挣得钱财回来,眼同开箱共见。第一〇八回写盛希侨的老婆说他娘家规矩:“俺家二老爷在福建做官回来,把皮箱放在客厅里,同我家大老爷眼同开锁,把元宝放在官伙里。我小时亲眼见的。”三是不听妇言。第三十六回议论说“处家第一,以不听妇言为先”,虽属偏颇,但是兄弟一旦各娶妻生子更难同宅一点,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后世家庭在兄弟同宅问题上很少知难而进的了。但无论是同宅还是析居,兄弟以至妯娌伯侄等家人的和睦,最重要的是相互宽容,有容乃大。所以,《歧路灯》写盛希侨虽然说过“俺家媳妇子不是人”,但是一面写他并不认真与媳妇争闹,一面又写他媳妇后来突然变得另一个人似的,忽然回心转意要善待小叔,一家和睦好好过日子了。但这与其说是盛希侨的老婆忽然醒悟,不如说是盛希侨一朝醒悟坚持兄弟合力一处,闺房内外有别,调停有方,使他的老婆也渐渐接受了一个兄弟妯娌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生活,愿意相向而行,和睦兴家了。
三、救世良箴
家庭是社会的分子,《歧路灯》写以教子为核心的“家政谱”,不可能只是一家或几家人过日子的话,而势必是一部社会小说甚至官场——政治小说。上述作者为《歧路灯》预设的主题说即表明这个必然的道理和实际的情形,从而书中教子——治家的描写自然延伸及劝世。但在李绿园看来,当时的社会实在太糟糕了。一方面“这满城中失教子弟最多”(第五十五回),另一方面“今日做官的……一心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第一〇五回)因此他的劝世又往往体现为愤世与救世的情怀,使《歧路灯》具有了救世良箴的特点。
其一曰家事优先,忠君意淡。《歧路灯》是一部教子书,写谭孝移以教子为“第一宗事”。加以居京候选中确实有了病,所以面君之后,即递了告病辞呈,回家准备继续其“延师教子”之事。固然因病重而死,事与愿违,但他毕竟把做官为朝廷尽忠,为天子“忠弼”的事,置于“教子”之后。虽然书中也充分描写了谭孝移告病的“隐衷”是由于朝政的黑暗,但如柏公所说:“我若有冯妇本领,就把虎一拳打死,岂不痛快?只因他有可负之嵎,又有许多伥鬼跟着,只有奉身而退,何必定要叫老虎吃了呢?”可见,《歧路灯》只为身家理正事,不为昏君做鹰犬的政治倾向,在古代长篇小说中是少见的。
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中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这段话揭示出中国历史循环的一个秘密即中国古代的国,历来是一家的私产,生死存亡总都是皇帝一家的事,其得与失都非百姓的,其论精当。但接着严复的话还可以继续说:天子以天下为己之一家,百姓亦以己之一家为天下。君臣上下以至于庶民,各以为“天下”之名而为其一家之利,则天下貌似一统,而实即所谓“一盘散沙”。于《歧路灯》写谭孝移父子出处的选择,可以见中国皇权社会皇帝与臣民关系的本质。第八十回写奴仆德喜顶撞谭绍闻道:“你穷是你穷了,与我们何相干?休要嘴打闲人。”
德喜对谭绍闻摔东西说这些话,不过寻常“家败奴欺主”而已。但皇权专制下家国同构,谭家父子为了自己的家而辞任皇帝家的差使,也仅是比德喜对谭家稍微委婉些罢了。总之,谭孝移不敢说不做皇帝的奴才,但是不甘心还要做太监的奴才。这在那时来说,比较做太监干儿子的,毕竟还是有些正气。
其二曰民命为天,不惜丢官。《歧路灯》写做官,以“实心爱民”为好官最高标准,第六十五回末诗云:“做官须用读书人,端的正心只爱民;猾吏纵然能舞智,玉壶原不映钱神。”因此我们看到,《歧路灯》写有不少好官,有诸多好的品质,即使有嫌游离枝蔓的“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第九十一回)和“季刺史午夜筹荒政”(第九十四回),也还是写入了回目中。这两个故事,一个讲谭绍衣平乱保护了许多无辜百姓的性命,一个讲季刺史在郑州大灾之年,冒了被撤职查办的风险开仓放粮,拯救一方饥民。这些人肯定愿意做官、做大官,但他们做官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百姓,甚至能够为了百姓不怕丢官,不顾自己的安危,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歧路灯》中这两位官员形象可谓当之无愧了。
《歧路灯》写“正人”,包括写官员中的“正人”即“好官”,绝无口口声声忠君报国的话头,也不唱舍己为人的高调,只是居官行政,处处为百姓着想,做好事,做实事,就可赢得百姓爱戴拥护了。如祥符县令荆公有“荆八坐”之称,并非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至今读来,尤其想到现实中许多告诉无门的人与事,便觉得这个形象虽没什么高大上,却无疑是老百姓的小确幸。由此可知,李绿园写《歧路灯》作为教子书、“家政谱”,总是一个用世情殷,一心只想世道好,只在“爱民”,可是他既手中无权,也想不出什么改天换地的办法,只能以小说为民请命,写一二以民命为天,不惜丢官的“好官”形象,做那个被质疑“天下还得有个好官”的时代的龟鉴,也算是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担当,尽了人间潇洒走一回的责任。我们应该感谢他。
其三曰针砭时弊,移风易俗。《歧路灯》作为“劝世文”,只好多写“老成典型”(第一回)“人样子”(第二回)“好官”(第九十四回)等正面形象。虽然也有意针砭时弊,揭发贪贿,谴责丑恶,但都集于下层官吏,尤其是吏役这个官场最低层群体,真正的官员尤其是大官,几乎没有一个不好。这应该也有作者主观上的原因。但从其借盛希瑗之口问“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看,实际上李绿园虽借《歧路灯》写出“好官”的样子,但他内心里才不相信祥符内外、官场与学界上下有那么多的“老成典型”和“青天大老爷”(第五十四回)呢!明显的体现不是书中写有董守廉那样的贪官,而是写最大的“好官”也只是不主动要钱而已。如第一〇六回写谭绍闻告终养回家,再到碧草轩,“开门一看,较之父亲在日,更为佳胜。原来谭道台离任,家眷要住此处,开封太守代交赎价,业归原主”,早就给谭绍闻赎回——岂不就是开封太守给谭道台变相送礼吗?
《歧路灯》的针砭时弊,更多是有意无意间掀动社会黑暗、机制溃烂的一角。如第五回“慎选举悉心品士”,满祥符县生贡中推出唯一堪为“贤良方正”又方便保举的就是谭孝移一人。这应该是周学正主持选举贤明公正的结果。但是,谭孝移能得此公正的基础,却是老门斗所说:“这谭乡绅是萧墙街一位大财主,咱的年礼、寿礼,他都是照应的。就是学里有什么抽丰,惟有谭乡绅早早的用拜帖匣送来了。所以前任爷甚喜欢他。”这才是谭孝移能得到保举的要害!但是看破不能说破,所以“东宿见门斗说话可厌,便没应答,起身向后边去了”。而谭孝移能保举成功,向各级衙门疏通关系,是娄潜斋主使王中等靠了“银子是会说话的”,从而作者回末诗感慨曰:“能已沉疴称药圣,善通要路号钱神;医家还借岐黄力,十万缠腰没笨人。”所以,写谭孝移是个好读书人,“老成典型”,当然不是针砭。但是,写谭孝移十分注重敬奉县学衙门才得到保举,用银子开路才保举成功,而且皆大欢喜,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就如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一般,才是对时弊真正的针砭,莫大的讽刺。在这个意义上,《歧路灯》不仅以露骨的揭发抨击见长,而且以似正而反之无意侧露的讽刺出色,是艺术上的一个成功。
又如,《歧路灯》写社会的溃烂,最严重的不是“娼妓百家转,赌博十里香”(第七十四回),也不是谭绍闻两次远出,不是遇盗就是遭劫,盗贼蜂起,而是官匪一家。第九十一回写“南边州县有了邪教大案”,前引第七十三回写劫匪谢豹对要杀德喜的魔王称道“这县的沈老爷,是咱的一个恩官”即是。诸如此类,《歧路灯》写针砭时弊,就是要唤起社会的注意,引出疗救的主意。但《歧路灯》对时弊针砭的效果,恐怕也只是一定程度上刺破了溃烂而已。不用说无法根治时弊的制度性原因,就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也未必治得好,更不用说昏君在上,贪官当道,从来只说不做,或者头疼治脚,脚疼治头,使之无可奈何。然而,可敬的是李绿园不是无可奈何而已,而是转以求助传统文化的某些兴建,以振衰起弊,敦励良俗。
其四曰珍重传统,振兴文化。《歧路灯》为敦励良俗,特别注重珍惜传统文化,思有以保守振兴。虽皆随笔为之,但总体量不少,兹以为全书的一大特征。一是显扬书法。第二回写娄潜斋为文靖祠题匾,“只见一面大匾,上放‘李文靖公祠’五字,墨犹未干,古劲朴老。两人赞叹道:‘笔如其人!’”第四回写周东宿为谭孝移题“品卓行方”匾额,“取出素用的大霜毫,左右审量了形势,一挥一个,真正龙跳虎卧,岳峙渊停。乔龄道:‘真个好!写的也快。’东宿道:‘恕笑。’又拿小笔列上两边官衔年月。”这些地方透露出作者对书法的爱好,也见出其对弘扬书法文化的美好愿望。 二是鼓励提倡搜集整理和刻印祖先或前人遗稿。书中不仅写了南北谭氏一族俱有家刻,而且第九十五回还写身居道台的谭绍衣亲对族弟绍闻说:“我们士夫之家,一定要有几付藏板,几部藏书,方可算得人家。所以灵宝公遗稿,我因亲戚而得,急镂板以存之。”又嘱咐道: “吾弟回家,定要在废筒败麓中密密找寻,或有一半片子手翰,书上批的,幅间写的,认清笔迹,虽只字也是咱家珍宝。贤侄也要留心。”
及至谭绍衣听说盛希侨祖上藩台公著作刻有藏板,便差人请至署中,督促盛希侨刷印藏板,并且助银三十两。这位达官百忙之中还不忘收集中州文献,以为能得前所未见中州名家之作,“也不枉在中州做一场官,为子孙留一个好宦囊”。如此等等,在别一种小说描写中实属罕见,而李绿园对保存文化的热心与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并不仅是或有寄寓个人著作传世之忧而已。
综上述论,《歧路灯》作为“理治小说”的价值有二:一是以理学为小说,理学成为小说的灵魂,扩大加深了理学对小说的影响。二是以小说演义理学,小说成为理学的载体。二者合体,共济于绿园所谓“正经理学”“教子”→“治家”→“救世”的目标。可以套用《歧路灯》写王中的两句诗:“漫嫌小说没关系,写出理学样子来。”李绿园是中国古代小说家中最大的理学家,理学家中最为优秀的小说家。《歧路灯》是宋代以来作为“理学名区”的中州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独特贡献!
——评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