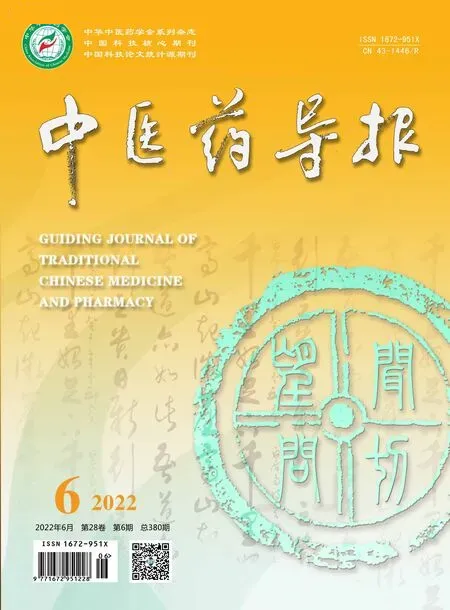中医药文化在日本传播认同的影响要素*
郑阳阳,张其成,梁秋语
(1.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029;2.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上海 201203)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深刻影响着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汉文化圈国家。最晚至夏朝,中国已经具备城市、文字、礼仪性建筑和冶金术这4个古代文明的标准[1],而日本具有善于向先进文化学习、实用主义的民族特点,以及地域上与中国相邻的地缘优势,使其更容易向中国学习古代文化。
中医药文化在日本传播,大致经历了全盘引进、发展本土医学、全盘否定和重新引进沟通4个阶段。其中,日本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催化了日本本土医学的发展;“渡来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的媒介作用为日本的中医药文化认同提供了前提条件;佛教、儒学、明治维新等影响贯穿日本的中医药文化认同历程。在不同历史阶段,日本主流文化的改变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1 历史上日本外交政策对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影响
日本的外交政策不仅受到中国的影响,也受到日本在不同时期国情的影响,在医事交流中呈现积极或消极的状态。
1.1 积极的官方外交与中医药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认同 隋唐时期和明朝,是日本积极主动与中国及周边国家建立外交的时期。公元607—874年,中日往来密切。公元608年,日本开始陆续向中国派遣使团。从公元645年开始,这样的外交政策促使日本全盘效法唐令制定《大宝律令》(701年),并制定了日本本土最早的医事制度《养老令·医疾令》。日本的医疗官职、医学分科、医学教育、救济制度等,几乎照搬了唐朝的医学教育模式[2]。也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开始提倡并重视佛教,将其立为国教,通过信仰共同宗教的方式来维护天皇的统治。
惠日为遣唐使节团成员之一,其在华学医数年,并带回《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书。此后,惠日又两度被遣唐,为中国医学传入日本之先驱。他的子孙世代承袭他的医业,被后世称为“难波药师”。其后也多有入唐使在中国学成(包括医学等)后回日本作出贡献者。
明朝建立后,处于室町时代初期的日本政府得知明朝建立,开始恢复与中国的官方往来。中日医药文化交流一改之前的颓势,贸易频繁,医籍和药材又开始大批量流入日本。来华学医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他们体会到中国经历宋元之后,医家纷呈的氛围,潜心攻读中医者众多。尤其是明朝中期,学术上的研讨更加深刻,日本对中医药文化的高度认同使得中日医学交流向成熟方向发展。
明朝传入日本的医学新浪潮,使得日本医家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主要是金元四家学说,尤其是李东垣、朱丹溪的学说,引领日本汉方医学走入独立创造时期。中国医家纷呈的氛围和程朱理学的盛行,吸引着大批日本人来华学医,并将不同医家的学说引进日本,为汉方医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后世派、古方派在这个时期产生。这个时期活字印刷术在日本的推广使得医籍更好地普及,针灸术、本草学、日本特色的茶道也都得到发展。
日本善于向先进文化学习的积极态度,使其学习吸收了诸多优秀的中医药文化;日本实用主义精神及其国情,使其在积极的官方外交中不会完全照搬所有的经验,而是在模仿与学习中做出改变与创新。
1.2 断交影响中医药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认同 日本历史上曾有3次与中国较长时间的官方断交。第一次官方断交后,日本对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学习,由与中国的直接交流转为以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百济为媒介转输。这次断交发生在公元479—600年。日本在政治上寻求中国的支持被拒后不再与中国交往,转而与百济更加密切地交流。百济先后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中国的典籍、文物通过百济传入日本,佛教也由百济传入日本[3]。
第二次发生在唐末至明初,日本在这次断交中衍生出“国风文化”,中医药文化也在日本的文化认同中沉淀出本土代表作。9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大陆地区的政局再次陷入混乱的局面,日本为防止受到影响,采取消极的对外孤立政策。此后,日本也从全面引进阶段的“唐风文化”过渡到消化吸收阶段的“国风文化”,《大同类聚方》(808年)、《金兰方》(866年)和《医心方》(984年)是“国风文化”在日本医药方面的体现。此时期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以民间贸易和双方僧侣为媒介进行民间交流,中医药相关的贸易也在此期间密切地进行着。但是政府方面的断交使得日本失去向宋朝学习的大好时机,日本中医药的发展也因此裹足不前。
第三次发生在明朝灭亡后,日本基于过往的经验,在官方断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向中国学习中医药文化。德川幕府的锁国令困阻了日本学者赴华学医之路,好在日本政府准许中国医生入日行医讲学。在这些中日诸医家的宣扬、推动和实践下,中医药文化在日本久盛不衰,并形成日本本土化的汉方医学流派,医学各科也得到发展,日本本土的汉医学发展进入顶峰阶段[4]。
日本官方针对中国的3次消极外交,导致日本的文化滞后于中国和朝鲜半岛,但对日本本土医药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一次消极外交时,日本通过百济转输中国文化,所获得的内容相对片面且大部分已经被朝鲜本土化。日本出于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积极地学习先进文化。第二次消极外交时,文化的同根相连,日本与中国及汉文化圈部分国家仍然保持密切的交流。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断交带来的缺失,但与隋唐时期相比,中日医药交流大幅减少。日本医学本土化初显,这些本土医著以整理、选录中国医籍部分内容为主,没有太大突破。第三次消极外交时,日本汲取之前的教训,即使在闭关锁国政策下,仍为中医药文化传日提供条件,日本本土医学得到质的飞跃。
2 中医药文化在日本传播认同的媒介
2.1 “渡来人”“渡来人”(とらいじん,toraijin)指主要从中国、朝鲜半岛迁移到日本的移民,通常是因国内战争频繁或随文化交流传播而移居日本。他们带来了当时先进的文化和社会生产力,中医药文化也随之传入。这些“渡来人”在日本颇受欢迎,日本人使之融入当地居民,并且积极地接受他们带来的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和先进生产力。“渡来人”的后代也渐渐融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徐福是早期“渡来人”的典型代表,他携众东渡,为日本带去汉字、中草药和水稻种植等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弥生时代的诞生,原始社会由此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
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大量中国人迁徙日本,为日本的医学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5]。公元563年,客居朝鲜的吴人知聪被带回日本,随行携带包括《明堂图》在内的164卷医药书籍,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日本的医学发展。
另一个在日本医药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渡来人”,是日本古代医学世家丹波(多纪)家族的祖先刘阿知。他率族人移民日本,带去当时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明的发展。其后代支流之一丹波氏家族在日本的医学地位世袭不衰,在汉方医药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丹波康赖的《医心方》是日本汉医的极盛之作,标志着日本汉方医学的独立成长,被誉为“本邦方书之府库”[6],《医心方》继承了中国编写大型医籍博而不杂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日本医家突出实用、务求实效、崇尚实体、讲求直观的特点[7]。《医心方》所引方书许多在中国已失传,可为现在研究已佚医书提供不可多得的资料[4]。丹波(多纪)家族在江户时期成为日本医学流派考证折衷派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丹波元简和丹波元胤、丹波元坚父子三人在医籍训诂方面达到了日本医药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训诂方法的运用还是训诂所得的结论都取得很高成就,对后人整理、研究中医文献具有借鉴作用[8]。
“渡来人”是中医药文化传入日本的先遣主力军,他们的子孙也在后来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活跃着,如公元608年遣隋使中的倭汉直福因、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等留学生和志贺汉人惠隐、南渊汉人请安、新汉人旻、新汉人广齐等学问僧[3]。由于多属所谓汉人、新汉人,他们懂得中国语言,善于向中国学习,对中医药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带动了日本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据《日本书纪》记载,药师惠日和倭汉直福因均为第一批赴中学医的遣隋使成员。他们学成回国后,向天皇奏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9]比如明朝时期中日通商,明朝灭亡后,大量儒者东渡,这些都促进了中医药在日本的传播。
综上,8世纪以前,以中国和朝鲜半岛为主的“渡来人”迁徙到日本,不仅推动了日本社会性质的改变,也对日本早期的医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其后不同朝代,尤其明朝以后中国的一些医家、学者移居日本,也推动着日本医学的发展。但就规模和日本认同中医药文化的程度而言,8世纪以前的“渡来人”迁徙更为突出。
2.2 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 在航海技术还不太发达的古代,朝鲜半岛为日本提供了更安全便捷的路线,成为了早期中医药文化传入日本的主要中转站。8世纪后,由于日本与当时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新罗关系紧张,遣唐使团的路线改由北九州横渡中国东海,从长江口登陆。
此外,朝鲜半岛作为引入中国文化最早、最广的地区,是日本早期学习中国文化的桥梁和窗口。佛教、针灸最早通过朝鲜半岛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百济亦有遣医博士、采药师到日本传授中国医学的记载。日本医学史著作中记载的“韩医方”即是通过朝鲜半岛获得的源自中国的医药知识。5世纪日本皇室也多是向当时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等国求医[10]。公元562年,携164卷医书的吴人知聪也是从地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前往日本。隋唐时期,新罗也作为一个重要媒介向日本转输中国的先进文化。
公元1392年,日本和朝鲜恢复了邦交,日朝医家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量中医古籍在日本和朝鲜的流传和习读,使得两国医家具备了扎实的医学基础。尤其是朝鲜医家对源自中国的方剂运用灵活,在日朝医话交流中提供了很多临床经验分享。山口忠居所著的《和韩医话》,记述了日本医家山口忠居与朝鲜通信使者围绕中国古籍、临床疾病治疗及药物人参等内容进行笔谈的经过,现被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11]。
3 不同时期日本主流文化对日本认同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3.1 佛教作为主流文化时期(公元552—1572年) 公元552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6世纪中叶,佛教成为了日本国教以维护天皇的统治,逐渐在日本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医学随着佛教的消长而发展变化着[12],僧侣兼医或作为中日医药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与医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甚而有“欲为医者必作僧侣”的说法。广泛存在于医家言论中的佛教之说,直到安土桃山时代才基本绝迹[13]。佛教慈悲为怀的理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日本社会救助机构的创立与发展,圣德太子创立敬田院、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得到日本各地的效仿,为穷苦疾患提供医疗。一些优秀的民间医家成为幕府御用医师后也会被赐予僧阶。
鉴真和尚是日本中医药文化认同史上举足轻重的僧侣之一,对中医药的文化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带动了日本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鉴真和尚6次东渡除携带经书外,都会携带药品随行。他精通医药,不仅带去不少中医书籍和中药,还把中药鉴别、应用的技术带到当时处在奈良时代的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曾多次为皇室治病,得到褒奖。鉴真和尚的东渡不仅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整顿了当时日本佛教的乱象,而且在医学、书法等方面都贡献巨大。他促使中医药文化在日本落地生根后,又结合日本本土的和药,开创出和汉医学。他的到来,使日本文化在这一时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奈良招提寺“奇效丸”发售至今,江户时代药袋上即有鉴真像及说明,今之药袋则印“开山鉴真大和上传方”,亦其传流悠长[4]。值得一提的是,《黄帝内经太素》至南宋时期亡佚,而当时鉴真和尚的东渡,使《黄帝内经太素》在日本得以流传。公元1823年日本学者在御宫仁和寺发现《黄帝内经太素》古抄本25卷,并返传回中国。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考证[14]。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僧医”,一些著名的日本医籍如《顿医抄》《万安方》《福田方》《类证辨异全九集》《大德济阴方》等均出自僧侣之手,针医的身份也以僧侣为主[15]。
3.2 儒学作为主流文化时期(公元1573—1868年)江户时期,契合当时统治者政治需求的儒学得到德川幕府的大力推广,成为日本官学。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儒学的昌盛、个人的追求和当时社会强烈的医疗需求,推进了日本医学体系由佛教医学向金元医学的转变[16]。儒医群体逐渐壮大,代替僧医成为日本认同中医药文化的主要媒介,日本儒医持着“儒志医业”的理念,在精神方面追求治国、平天下,以医为业,解决生存问题。
儒学是日本儒医群体学医的前提素养和道德指针,中国儒学与医学的同源性也增加了中医药在日本的传播优势。复古、折衷、考证等医学流派的产生和流派理论学说的形成,均与相关医家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及引领时代风尚的儒学思潮具有密切的关系[17]。
日本儒医的历史变迁也反映出汉方医学与儒学发展的同步性。江户初期儒学的繁荣带来中医学的引入和汉方医学的中兴,明治维新后儒学的颓败也伴随着汉方医学的衰落[16]。
3.3 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西化后 政治经济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而是紧密相关的。强势的政治经济条件,必然推进文化的强势传播。晚清时期,汉方医在日本也生存维艰,被强势文化代表之一的西医所排挤替代[18]。
3.3.1 奠定日本汉兰折衷派的西医学基础18世纪初,随着西洋医学传入日本后,其截断性治疗理论与古方派“万病一毒论”相合,被古方派传人山胁东洋迅速接受,并创立汉兰折衷派。汉兰折衷派理论上倾向西医,疗法仍多用汉医方药,遂成中西医汇通结合之域外先声。后有华冈青洲精研汉医古方,从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撷取精华而创麻醉新方“通仙散”,又自兰医处习得剖割之术。公元1805年华冈青洲成功以中药全身麻醉施行乳腺癌切除术,名震世界医坛[4]。其注重汉兰两个医学体系并重,授业行医,包容灵活,以效为念,在外科治疗方面颇有建树,成就了汉兰折衷派的创造力高峰。
3.3.2 逐渐完善的医学教育 曲直濑道三(公元1507—1594年)所创“启迪院”,是日本近代早期的第一所医学校,突破了师徒口传、受众者寡的格局,学生达800人。启迪院教学注重实际简练的医理讲解,注重医学伦理方面的教育,并首创“切纸”训导法,培养了一批有才能的医生。
江户时期日本官办医学馆“跻寿堂”是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中心。该校将《神农本草经》《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针灸甲乙经》《格致余论》等作为授课内容,兼讲针灸、诊断、生药及答疑课,并包含实习如诊断、配药、治疗训练等;举行“医案会”测试、“疑问会”答疑、“药品会”讨论药物等;另讲授儒学及诸子百家之书,重视学生品德培养[4]。
受西方建校教育影响,公元1780—1860年,医学院、医学部开办之势渐甚,重视医籍经典和中医各科教学,诊断、药案、本草教学兼备,儒学、道德教育与医学并重,是这些医学校的共同特点。这一时期日本中医教育方式的改变,亦已独立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教育模式。
3.3.3 全盘西化的医学制度 日本最初通过汉译西洋文化著作接触西方医学及西洋史、地理、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技术等知识。进入明治时代后,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结束的日本,施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明治维新。在引进欧美的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同时,对西方医学体系的引进和现代化医疗、卫生行政制度的建立,也使得日本汉医的传承岌岌可危。在公元1875年实行的医师开业考试制度规定,汉方医家也要通过西医考试才能行医[19]。医学考试内容为解剖学、生理学、外科学、内科学、眼科学、产科学、物理学、化学、药物学、临床实验等[20]。汉医陷入无法教习传授,后继无人的困境。所幸汉医传人尚多,亦有学习西医通过考试后研修汉方者,汉方医学得以一息尚存。
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日本民族,认为当时的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从部分认同西医学的内容到全盘接受,最终摒弃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全盘引进西方文化,从而导致日本汉方医学走向衰弱,只留下西医化的汉方药为主的传统医学。
4 结语
日本的中医药文化认同历史是中医药国际传播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日本经过消化吸收、结合本土特色,形成了日本特色的传统医学。文化的传播呈现由高到低传播的特性,中国古代文明早于很多国家,中国对中医药传播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民族自身包容开放、善于学习的态度使日本在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很好地吸收转化了中医药文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传统医学。而日本的实用主义精神,使其在认为中国文化落后时,不够理智地鉴别、撷取精华。
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医药国际传播中可以改进的部分,优化中医药文化走向国际的路线与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