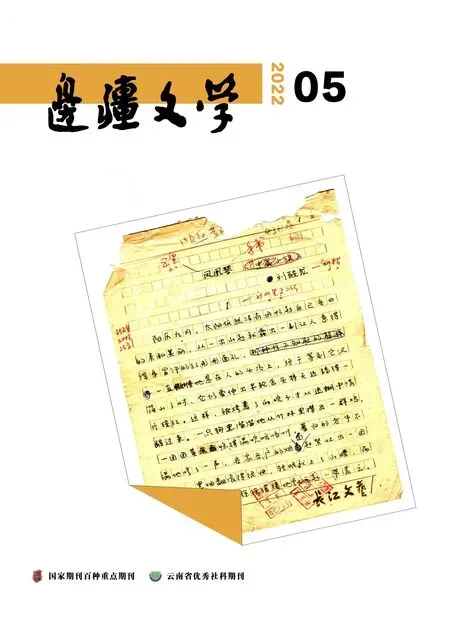我的命理,也正是一块木头模糊的纹理组诗
张二棍
莫测
蚯蚓蠕动着,路过
自己断掉的遗体,宛如路过
一座,事不关己的废墟。它没有停留
没有吊唁、超度、掩埋……
它还没有觉察,自己已经死了。也有
另外的可能,蚯蚓深知
不能怀着,下一秒生还的窃喜
去悼念那个
上一秒,罹难的自己
朽木
我的命理,也正是一块木头
模糊的纹理。我肯定是开裂的
朽木,转世而来
无人雕琢,无法成器
也想成为老爷们威风凛凛的惊堂木
也想做个木鱼,听哪位老僧
面授玄机 —— 太迟了
我身体里,早已浩浩荡荡
挤满了,你推我搡的白蚁
偷情,弑父,攻城略地……
它们把人间的坏事,一再做绝
而我,却充耳不闻,仿佛
只要包庇着这一切,就会皆大欢喜
就能无疾而终。我这块朽木啊
做不到,以命换塔。只能
一边,忍着钻木取火的疼痛
一边,凝望着自己纷扬的
碎屑,喃喃自语:
刮骨罢了,疗伤罢了
殆尽
几乎整个童年,我都不得不
活在阴森森的偷窥
与监视之中。我们的老房子
成为,这群好战分子
搏杀的疆场。而漏风的门窗
在这些强盗狭细的眼里,俨然是
可供大摇大摆,出入的平地
连破旧的衣柜都难免,被这些不劳
而获的土匪,常年霸占与征用
成为婚房、粮仓、庙堂……
有一次,我还看见一个小家伙
孤零零坐在门槛上,晃荡着双脚
啃食,母亲藏起来的糖果
—— 这些毫不见外的家鼠
在所有不可思议的角落里,出没
有时鬼鬼祟祟,有时光明正大
它们一定偷听过我的梦呓,也目睹过
母亲在灯下,惺忪着双眼缝补
旧衣的样子。它们打碎过姐姐的镜子
也私藏了,弟弟的羊骨玩具
……难道,正是这一群小小的
生生不息的家鼠,在冥冥中
参与,也组成了我们的生活
而现在,它们仿佛一群
再也无人豢养的孤儿,追随
无须赡养的母亲
远遁而去,甚至
连一丝丝痕迹,都消失殆尽
无奈
既不能给自己下达
任何通知、告示,更不能
律令和主宰。常常是
几近于哀求,我的灵魂
一次次,跪在肉身的阴翳里
仿佛一团无辜的
乱麻般,低声哭诉着 ——
放过他们和它们吧
忘了莫须有、不得不、无奈何
放过共犯和帮凶,宽宥
开枪的娃娃兵,年迈的毒贩子
怀孕的妓女,行窃的侏儒
……亲爱的灵魂啊,永远不懂
它栖身的这具肉体,虽然偶尔也战栗
但早已,断绝了愤怒,更阉割了
同情。亲爱的灵魂,给你看看这些
陈年的伤疤和新添的皱纹
你就明白,一个不惑之年的庸人
被千丝万缕的恐惧,与卑怯
紧紧捆绑着,早已配不上
冲冠一怒,也配不上释怀一笑
为母占卜
刚刚,我又在算卦的摊上
坐了一会儿。老来多福,且长寿……
母亲啊,算命的先生永不会知道
我是携带着一个亡者的生辰
来此。我愿意一次次
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点着头
把这些好听的话
既当成迟来的祝福
也当作永生的慰藉
空地
长风万里,吹拂着一片片
凌乱的生活垃圾。一粒粒玻璃渣子
闪闪发光,映射着一瓣瓣
碎掉而单调的天空。从远处运来的残枝
败雪,烂砖头,倾倒成
一堆堆末日景象……我毕生所学
也不足以将此地的破败
与凌乱,如实描述。骤起骤落的
鸦雀们,东奔西跑的野狗们
寻觅着各自的果腹之物
—— 人间用剩的一切,它们
又用来活命,争夺……
我毕生所为,也不过
如它们一样
撕咬着争夺,嚎叫着活命
造化
造化弄人,才生就了
这一副寒碜又凄凉的模样
我面孔黧黑,仿佛经受了无数场
风吹雨淋。我背影佝偻,仿佛遭遇过
无数个朝代的鞭挞,和压榨
看我的尊容吧,时而卑怯,如充军的
罪臣。时而恓惶,如马戏团落魄的
小丑。看我这一身衣衫,满脸风尘
孤零零一个人,就云集了诸多
你避之不及的穷亲戚、苦兄弟
我这枯槁的样子里,一定还
深藏着,无数人的影子:
我是我们逃荒落难的先人
无法给后人,留一方家园
我是我们失魂落魄的后辈
不能给祖先,立半间祠堂
末日
每一秒,都有古树为秋风所伐
而尚未成精的猢狲们
在大雨中,尖叫着向茫茫中散去
每一秒,漆黑的国家公路上
都有一辆刹车失灵的救护车
拖着长长的哭腔,碾压过
一双牵手过路的蜗牛。每一秒
都有鸦雀们的房倒屋塌
都有田鼠们的家破人亡
风起,是露珠的末日
雨落,是蚂蚁的末日
这宇宙中,哀乐从来不绝
每一秒,都有破碎、陨落、形神俱灭
每一秒,都是末日
是无数个,纷至沓来的末日
农夫颂
一个最憨的农夫,也永不会杀鸡
取卵,更拒绝驭鹿为马
在种与收的间歇里,就摆弄几株
好养活,却灯火般辉煌的
花花草草。生下的女孩子,也
跟着一株株花草,唤作
兰啊菊啊。最憨的农夫
也知道父母在,不远游。所以
种瓜种豆。种下高粱,酿新酒
种出桑麻,做新衣。最憨的农夫
会把几亩薄田,奉在心头
会教,牙牙学语的子嗣
在田地间摸爬着,认下
养命的五谷,与先人的坟头
一个勤恳的农夫,终生奔走在
油绿和金黄之间,把自己活成
晴耕薄田,雨读苍生的老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