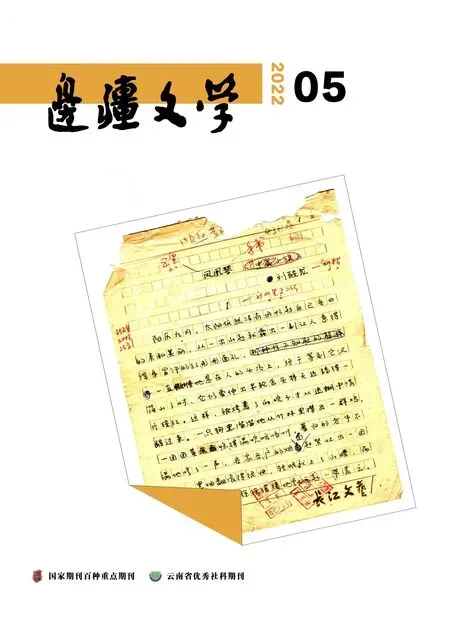靠山夜话 短篇小说
张世勤
储物间
小顾是我与靠山胜景楼盘接触后认识的第一个人。每次见面,我都会问一次她的名字,可总记不住,我于是喊她小顾。既然是置业顾问,喊小顾便错不了。小顾并不在乎我怎么喊她,她的心思全在推介楼盘上。反正不管我怎么喊她,她都是微笑,而且尽可能往微笑里加进适量的糖,甜甜的,招人喜爱。要推介楼盘,必须先推介好自己。这一点看来她懂。当我站到沙盘前时,我其实已经喜欢上了:依山而建,一面漫坡,六个层级,形成六个台地。每个台地六七座、七八座楼不等。六个台地,各自相对独立,又上下相互连通,错落有致,别有格局。住进来之后我见过她几次,每次见她,她都在忙着接听电话。有次,见她没接听电话,我问候她:还没结盘?她说,基本结了,只剩一个储物间还没卖出去。
有一天,妻子高兴地说,我又买了个储物间。我问为什么?妻子说,一些杂物扔了可惜,有储物间,周转后,攒攒可以卖钱。妻子说,人家都夸我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随后妻子将大小纸箱,旧报纸,破桌椅,攒了一个季度后卖出去,卖了将近三十块钱。第二个季度,卖出去了不到二十元。买这个储物间,共花去三万多块钱,我晚上睡不着觉时算了笔账,这么下去,单是要把本钱顶回来,差不多就得需要三百九十多年的时间。我便惊出一身汗!妻子见我一直郁郁寡欢,夜里常常睡不着觉,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最好别瞒她。
我说,咱们两人未来的日子可能会很长,我怕扛不住。
妻子根本没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但她没有再问。
纠纷
有一部分业主入住了,有一部分业主正在装修。装修公司有很多家。有个家伙我叫不上名字,看上去五大三粗,老实巴交,我心里喊他老庄,装修的“庄”。当初他曾跟我联系,我也有意让他来做。但妻子反对,说看上去不太靠谱。我说,还能有比我更不靠谱的?妻子说,跟你真有得一拼。
有一天,妻子让我去物业中心缴车位管理费,看见老庄急匆匆从外面进来。他向物业反映,他刚装修完一家,但联系业主时怎么也联系不上了。物业人员帮他打电话,电话通,却无人接。
这事惊动了驻地派出所,来了两位警员,敌奇户和展朱阁。老庄领着他们去房子里察看。其中一个警员打电话时,听到墙里面电话响。经过前后排查,原来是老庄装修时不小心,把业主给装进一面非承重墙里面去了。
后来,我问老庄,干嘛要这样?老庄说,没遇见有他这么抠的,一天到晚,把我指挥得晕头转向。他自己也没个设计,一会儿指挥砸,一会儿又要求补。我简直要崩溃了!那天我趁他睡午觉,干脆把他装修进去了。
据老庄讲,这业主有个口头禅,天塌下来有我顶着。老庄说,我应该把他装到承重墙里面的。
遇见熟人
遇见熟人。熟人不是人,是一棵树,一棵老柳树,它具体叫什么名我不知道,我只喊它老柳。靠山胜景最拿手的就是绿化,楼房与楼房之间,台地与台地之间很开阔,全做成了景观。在这些景观中,树木占了很大一部分。
那天在小区散步,竟然意外遇上了它。它原本生长在司息河岸边,高大魁梧,我读小学时,在它树荫下上过体育课,读中学时每周从它身旁经过,彼此已经熟悉到可以对话的程度。我感到很奇怪,我说,你怎么来了。老柳说,说的是呢,我也没想到老家会把我卖了。我说,老家可能也是好意吧,想让你进城风光风光。老柳说,我老远就认出了是你。我说,是啊,我们老朋友了,我本来还计划着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回去,肯定找你,再坐上你肩头,跟你说说春暖,话话秋凉。老柳说,你还敢往树杈上坐啊,忘记你的屁股了?老柳所说,是我小时候屁股曾被它划伤过,并留下了永久的疤痕。我自嘲道,是的,我现在的屁股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想在外面做个坏事都不敢,很怕被人记着。我看到老柳的情绪并不是多么高涨。老柳说,都说城里好,可我怎么总感觉在城里不如在乡下自在呢?并问我,你呢?我抬头看了看天,并没说出话来。老柳说,你还能想回去就回去,可我呢?我说,你是不是又想你身旁那棵树了?那棵大槐树,老槐!老柳说,不想。我问,怎么了?老柳说,老槐去年就被伐掉了,给村里过世的老陈头当了棺木。我说,看吧,你的命总归比它好些。我指指近处的一扇窗子,说,我就在那里面,你在外面,难得咱们这么近,没事互相看一眼,很方便。
后来有一天,我在五台地的一个景观区放风,物业上有几个负责绿化的人聚在那里闲聊。一个说,那棵新移植过来的大柳树,天天往下掉叶子,就跟流眼泪一样,这才几天工夫啊,朝向家乡方向扎出来的根,就已经长出去了几丈之长。
我一听,他们说的应该是老柳。我略感惊异又略带惊喜地问,有这事?
那人说,还好,被我锯断了。
当天晚上,我趁着夜色去悄悄看望老柳。在我细心给它包扎脚上伤口的同时,它也用树叶一遍又一遍地替我擦去脸上的泪水。
我们虽然仅仅一窗之隔,我经常看它在晚风中摇摆,但它可能并不知道我每每会在长夜中失眠。
我并不敢多拿眼光去看它。
它原本是一棵魁梧的树,可现在,站在新地方,必须得好几根木棒搀扶着才行。可能它还不明白,在城市它得借助外力才能站得住脚跟。
一个女孩找上门来
我叫不上她的名字。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也是只夜猫子,晚上睡得很晚。早晚倒没关系,关键是她喜欢裸坐在阳台上。当然,可能她也知道,这种行为自然还是夜深一点为好。
除晚睡之外,她还有一样爱好跟我一样,吸烟。但她吸烟的姿势比她裸着的身体更具魅惑。跟她的魅惑效果比,我根本就不配吸烟。
她一手托腮,身子前倾,烟头偶尔明灭。她可能并不舍得把小区完整的夜晚,无端烧出一个黑洞。客厅的灯是关着的,深夜中靠山胜景的灯火已经暗淡,但月色透出的微光,仍然足以把她的剪影幻成为最美的构图。因为她习惯了身子前倾,那么垂下来的两个胸就更为突出,更有味道。
蓝布牛仔,小白扣。黑小衫,露脐装,小蚉腰。肩上披着精心打理过的直发,两只胳膊像是瓷做的,其中一只的手腕上束着黑项圈。我打开门,不知道她要找谁。她说,我就找你。这更让我摸不着头脑。她说,我住你对面,你知道的。她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个大概。我说,小罗啊。她一边进门,一边问我,你喊我什么?我说小罗。她想了一想,然后笑了,说,你喜欢这么叫,也行。我是想,她既然喜欢夜裸,这么叫应该也合适。再说,我从来都记不住陌生人的名字,问了也是白问。
我们在阳台上坐下。在坐下之前,她从多个角度向对面望去。她望向对面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种姿势都很美。我说,我晚上睡不着。她盯了我半天,然后反驳我说,谁说夜晚就一定是要用来睡觉的?单纯用来睡觉岂不可惜?我的意思是想表达,我不是故意要去看她。她显然明白我的意思,说,我并不是怕你看,而是怕你拍。我马上申辩说,我没拍。她说,我看你有时两手举着,应该不是手机就是相机。我说,不瞒你说,我是假装手里握着一筒长焦望远镜,我已经习惯了想象,想象有什么就有什么。望远镜也是,我想象它是长焦的,可以看得很远,看得很清,而且我认真试过几次。这么说吧,我其实并不想看得太清楚,我认为还是不清楚会更美一些。我问她,你喜欢夜?她说,是的,你不是也同样喜欢吗?我说,我是因为晚上睡不着,我妻子说我是个病人。你今天来得倒是时候,她不在家。她说,你们的行动规律我很清楚,就是因为知道她不在我才过来的。我看着她,问,那么你来我这儿是……我在心里想她应该是来斥责我、揭发我甚至是起诉我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应该瞅我妻子在,她想达到的效果才可能更好一些。她倒岔开话题,问我对她的行为怎么看,什么感觉。我便实话实说,太媚惑。她说,你有烟吗?我说,有。我替她点上。她一边吐烟圈一边说,因为生活中感觉不到一丝一点的媚惑,所以我不得不把自己做成标本。我说,所以你便裸?她说,是的,尤其夜里。只有脱得一丝不挂,我才觉得轻松。她并且拿月亮说事,说,你见月亮什么时候穿过衣服,哪晚不是光溜溜的?我说,其实月亮有时也穿。啊?她望定我。我说,有时它会穿上几片云彩。她笑,说,看来月亮还不如我。我说,不如。我继续说,我其实也很想裸,只是苦于没有你这样的身材和姿色。这些年来,我甚至一直想做一个坏人,可一直做不成,这也成为了我苦恼的原因之一。你可否给我一些指点,我应该做哪些努力?她说,这可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说做就能做的。她说得很肯定,这让我心里充满了些悲伤。我说,我想自由。她说,我也是。
临走,她再次落实我是否拍过。她说,那是些忧伤的底片,我想还是自己保管为好。我说,可我真的没拍。
多出来的一个保安
我想跟老荆打听下这个女孩的情况,老荆竟不知道小区里还住着这么个女孩。我说,她吸烟,难道她房子里的烟火器就没报过警?我这么问,是因为我跟老荆相熟此前我一吸烟老荆扛架梯子就上来了,说,物业说你家烟火警报器又响了。每次,老荆把梯子从这间屋挪到那间屋,看一圈,说,并没什么问题。这么反复检查过多次后,烟火器无端报警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我跟老荆熟了。他显然并不姓荆,姓什么我问过,叫什么我也问过,可总是记不住,我就喊他老荆了,报警的荆。老荆也吸烟,他说,把客厅的推拉门关上,咱们到阳台上吸,不然又得报警。我问,咱们物业中心现在多少人?老荆一下瞪大了眼,这事你也知道?老荆的反应让我感到奇怪,因为我跟他没多少话题,不过是想找出个由头,好一起闲聊。问物业有多少人,也是因为我觉得靠山胜景的物业做得还是不错的。我问他,怎么回事?老荆说,真是怪,我们的全体人员会常常是晚上开,每次开,总是多出一个人。开始大家都没注意,但有人嫌开会无聊,为了耗时间就在心里默点人数,这一点不打紧,点来点去,总多出一个。有人悄悄把此事报告给了物业经理。经理不信,开会时他趁副经理讲话的空,在那儿点,确实,怎么点也是多出一个。但多出的这一个到底是谁,却怎么也找不出。经理的脸当时就被吓得煞白。经理私下给每一个人谈了话,让大家守住这个秘密,暂不外传,待查个水落石出再说,免得引起业主不必要的惊慌。我说,你们肯定是数错了。老荆说,怎么会是数错了呢?这时,窗外小路上有个保安开着巡逻车驶过。我说,还是开巡逻车好,一看就是那么回事,开巡逻车才配得上靠山胜景的品质。老荆说,是,保安们都开巡逻车。我说,可我见过有个保安一直是骑自行车的,而且车子还很旧。老荆一下又瞪大了眼,这怎么可能!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说,我晚上睡不着,除了坐在阳台上在那儿假装思考之外,有时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下楼,一个台地一个台地地胡乱转。每次都能碰见他骑辆破自行车,也在那儿一个台地一个台地地巡视。有一次,在五台地,我看到他连人带车一起翻到四台地去了,奇怪的是没有出现响声,也没听他发出惊叫。我想这怎么回事,赶紧下到四台地去察看。我并没能从树丛中找到那辆破车子,倒看到他已经走远了。我想追上去问问他受伤没有,但他走得很急,一直走到六台地,出了靠山胜景的后门,然后往山上去了。老荆听我这么说,把手头的烟一下捻掉,扛起梯子就往楼下跑。
为这事,老荆后来专门过来了一次,跟我说,查清了,多出来的人就是你说的那个。我问,他不是你们的保安吗?老荆说,是,但不是现在,过去是。这事发生在楼盘交房前,他那时还是属于工地保安,听说他是个很尽职尽责的人,靠山胜景的地形结构决定了当初工程作业面的复杂,土建时台地与台地之间不是悬崖就是深沟,不可能加栏杆,有天晚上他连人带车都翻下去了,等到早上施工时大家才发现了他。大家觉得后面的山风光很好,就把他抬到山上,埋了。大家都知道他对靠山胜景有感情,因为他一直说等楼盘开盘,他会第一个选房。他对拥有一座房子看得比命还重要。事实上,小顾给你说的只剩一个储藏间没卖并不准确,而是到现在还空着一套房子。我问,为什么要空着一套房子?老荆说,这事现在能回答了,原来还真说不清。开盘后,有一天夜里,售楼处忙了一天,正要关门,这时进来了一个人,说要选房。选好后,置业顾问让他第二天到财务缴定金,他说钱他已经带来了,想请她们代缴。既然客户坚持,她们也没多想,就留下了。但等到第二天,她们想替他缴财务时,才发现哪里有钱,昨夜放钱的地方这时候只残留着一撮灰烬。
我说,原来是这样。那么现在开会他还来参加吗?
老荆说,不来了。
为什么不来了呢?
老荆说,前两天,经理找了个晚上,带着几个人,专门上了趟山,给他烧了些纸,跟他说,现在小区一切都很正常,让他不用挂念,好好休息。小区有活动时,会主动来请他。
他叫什么,你们知道不?
老荆说,大家都喊他小保。
楼下储藏间里有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妻子一直没舍得卖,想起小保的遭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夜里再去楼下转时,我取出自行车,想体验一下小保的心情和感觉。骑着自行车,一个台地一个台地地转,感觉就是不一样,特别两个台地之间坡度较大,上行时虽然有些费力,但下行时就很拉风,感觉自己跟飞起来一样。我想跟巡逻车比比到底谁快,可是每次不等我靠近,巡逻车上的保安总是掉头就跑。
中药房
有个电话打进来,号码陌生。我接了。对方说,你预约的时间到了。我说,我没预约。对方说,是你妻子替你约的。
我问过后,终于弄清楚,对方是三台地的中药房。
之前,就听妻子多次说起,三台地的中药房很火爆。靠山胜景利用两个台地之间的落差,除六台地之外,每个台地都建起了一排商铺。这些商铺都成为了旺铺。中药房进驻时,并不被人们看好,但很快却经营得风生水起。
我不明白小罗来找我的事,为什么妻子会知道。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应当是小跑给妻子提供的情报。小跑,是我喊他时用的名字,他的真名叫什么,我没问,问也记不着。喊他小跑,是因为他在业主群里的昵称叫一路小跑。小跑是个很勤快的人,跟他的昵称一样,经常见他一路小跑。妻子认为我的病很严重,并且认为我所有严重的病症都是由睡不着觉引起的,如果继续往偷窥和偷拍方向发展下去,情况肯定会变得很糟。特别是听妻子说,物业经理专门找过她,让她劝劝我,晚上没事下楼转转不是不可以,但尽量不要骑自行车,时间最好也不要太晚。再就是,他们物业有时候晚上会开会,是内部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和部署业务工作,让我也不要随便去参加。如果有必要,物业会邀请业主代表参与。所以妻子认为我的确病了,必得赶紧医治才好。其实此前,我看过西医,也去过街上的一家诊所。记得在街上的那家诊所,我跟大夫说,我病得很重,经常浑身麻木毫无知觉。大夫很认真,对我周遭进行了检查,最后确准我的问题主要出在嗓子上。大夫说,你先前肯定遇到过很多需要你大喊一声的事情,但你一句都没有喊,时间一长就把所有神经都给憋坏了,所以今后你必须尝试着去大声叫喊,甚至是大声骂人。我说,我现在喊不出来了,而且也不想喊,骂人可以,但我可以骂自己吗?大夫说,你骂自己肯定不行。听大夫这么说,我俯在他耳朵上悄悄说,也许你说得对,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这些年我从来都是小声地说,没敢惊扰过任何人,包括我的读者。当然,我可能连一个读者也没有。我说,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大夫看看我,摊开处方签,板着脸,从身后找出了一部厚厚的文学评论著作,从中仔细往外挑拣着一些合适的词儿,开成了处方,并嘱我一早一晚按时服下。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脸色渐渐红润了起来,精神也比从前好了许多,有好几个夜晚我都没有再听见靠山胜景小区里的狗叫。但妻子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就诊,我的病情并不是轻了,而是在不断加重。我的话越来越少,总是长时间坐在阳台上发呆。那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也被妻子当废品卖了,听说卖了40 多元,比积攒一个季度的废品卖得还多。我越来越重的病情让妻子的眉头越蹙越紧,这让她更加坚定了去看看中医的想法。妻子的解读是,西医主要是治硬伤,而中医可以治软伤。此前,她就向我推介过,中药房里有个老中医坐诊,水平挺高的,自打他来后,他的瘦身大法让小区里的中年妇女们全都瘦了一圈。妻子的意思应该是他的医术高,无所不能,所以我的病他不仅能治,甚至属于手到擒来。
我去了三台地,进了中药房,老中医像模像样地坐在那里。我不想问他的名字,问了我也记不着,我喊他老钟,中医的钟。老钟一见我,就黑了脸,很生气地跟我说,你呀,再来晚一点就麻烦了。我问,怎么了?老钟说,还怎么了,一看你就是已经六十多岁的人。我说,这怎么可能,我才刚刚四十多岁,离五十还有好几年呢!老钟问,你是不是至少半年多甚至一年没有那种生活了?我说,是。老钟说,你也根本不想,对不对?我说,对。老钟说,这不就得了。我说,那可不是,你不知道,现在街面上刚刚新流传着至少三起关于我的绯闻,每一起都足够生猛和香艳,让我自己都十分艳羡,垂涎不已。老钟说,这正常,绯闻和你的实际情况肯定不会一致,一致就没有意思了。这才是生活的精彩!我说,我还一起也没摆平呢!老钟说,你为什么要去摆平呢?就让它们在外面绯着不是挺好?我说,总得有法治吧,你觉得中医有什么好法吗?老钟沉默了一会儿说,现在是给你的身体看病,咱还是不扯那么多。
飞天图
我提着一摞中药,从中药房里出来,感觉有些走不动,身子不由自主地晃了几下,好在有人把我扶住了。扶住我的人正是一路小跑。小跑说,怎么,你病了?我问他,我的年纪是不是很大了呀?小跑说,不大啊,怎么看你也是正年轻着呢。我说,你知道老钟刚才怎么说,他说我六十多岁了,各种器官严重老化,全身虚,再晚来一点他就是华佗再世,也调理不过来了。按他的说法,我只能精神矍铄地跟大家拜拜。小跑问,老钟?我说,嗯,就是里面的老中医,中医的钟。小跑说,他的话你听着就是,别当真,也别生气,遇见这院里的每一个人,他几乎都这么说。我说,我没生他的气。小跑问,那你是生谁的气?我说,我生中医的气。我担心好端端的中医,怎么会有这样的医师,中医迟早会毁在这些人手里的。
小跑很热情,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一直搀扶着我进了家门。他对我家不陌生,妻子跟他走得近,他也挺愿意跟妻子说长道短的,诉说自己的痛苦。他的一路小跑,并未给他换来业主们的赞誉,倒是因为热情愿揽闲事,经常与业主们发生纠纷,甚至有时会被业主骂得狗血喷头。我曾亲眼看到他不厌其烦地摆动一台地那九个石球墩。这些石球墩是为阻止车辆进入楼前空地而设,本来有提示牌已经够了,但指示牌根本阻挡不了。于是象征性摆上了两个,但仍然不解决问题。于是从两个增加到了三个,后来又从三个增加到了六个,后来干脆一长溜摆出了九个。其实违犯规定来回走车的就那么一两个人,同时也是经常投诉物业不作为的那一两个人。有次,其中一个人又走车,这次是因为拉了东西,因为又找物业专门批了通行条子,所以是可以通过的。小跑正从此路过,本来没他的事,他看业主不便,便停下来帮业主挪动石球墩。业主的小儿子凑在一边看热闹,石球墩一滚,正好把他的脚给砸着了,为此小跑不仅陪上了一个多月的工资,还失去了季度优秀员工的评选资格。
妻子对这些很看不惯,常常私下里安慰他,并帮他支些招数。妻子很无奈,因为她是业主,她也不便光明正大地站在物业一边。因为小区的主流舆论,物业永远是错的,属政治正确。
我让小跑进来坐,他也没客气。我们没在客厅,也没去阳台,而是直接去了书房。只要在书房里坐定,我能最快速度地恢复正常。小跑不吸烟,我点上自己吸。
小跑打量着我并不大的书房,然后发现了我书房里挂着的画,他说,这画真好。
小跑所说真好的画是一幅十二身飞天图,这是敦煌第282 窟里的一副图案。十二个女子,个个曼妙,她们头束双髻,上体裸露,腰系长裙,肩披彩带,身材修长,逆风飞舞,身轻如燕,天女散花。她们有的演奏腰鼓,有的演奏拍板,有的演奏长笛,有的演奏横箫,有的演奏芦笙,有的演奏琵琶,有的演奏阮弦,有的演奏箜篌。她们每一个都像是天地精灵,鲜美靓丽。每一个仿佛都身怀绝技,婀娜多姿。我曾三去敦煌,去那个看似荒凉但我却感觉是生机无限的地方,这幅画便是我第三次去敦煌时买回来的。
我把它挂在了书房。
自从有了这幅图后,我的梦突然多了起来,一会儿梦见昆仑山,一会儿梦见祁连山,一会儿梦见天山。那可真是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梦里的我不断在嘉峪关和玉门关之间进进出出,看到很多使臣将士商贾僧侣等等人头攒动。那段时间我特别忙碌,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在阳关,我竟遇见李白正在那儿写诗,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不错,写得好。只是在写出这两句之后明显发现他再没什么词了,我说,你让开,结果我没怎么费力就给他补上了霓裳曳广带和飘浮升天行这后两句。李白脸红红的,跟刚喝过酒一样,在那儿拍手叫好。总之,不止我的病情好转,我的生活和事业也都明显出现了腾飞的迹象。我感觉我已经通过敦煌打通了西域,通过藏经洞打通了天地,通过飞天女找到了自由,通过跟李白过招提升了酒量。
小跑站在画前,看得很仔细,看得很激动,说,真好。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懂画还是不懂画,但他说好自然有他说好的道理。
他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说,哎,你快看这个!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像不像小顾?他用手指着画中的一个人。
我凑过去,一看,还真像。我说,不瞒你说,我每天都要看一眼这十二身飞天图,却从来没发现里面还有个像小顾的。我问小跑,你跟她还有联系吗?
我这么问他,是因为热心的妻子曾用心用力地撮合过他们。在外人看来,他们的确很般配。据说,他们也曾热络过一阵,但后来分开了。
小跑说,我们已经很少联系了。
为什么?
这个楼盘结盘后,她又去了另一个楼盘。
我问,你怎么不随她去?
小跑说,我喜欢做物业,给业主们服务。
那么你们不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卖楼卖的。
这怎么讲?
小跑说,卖楼让她开阔了眼界,见识了人,特别是见识了太多的有钱人。应该是这吧,反正是她看不上我了。我问,你是不是心里还有她?
小跑虽然没回答我,但我想他心里应该是有的,不然他也不会从十二个难分伯仲的女子中,一眼就能看出里面有个小顾。说实话,那女子跟小顾并不是很像。
有一天,我坐在书房里,无所事事,默默出神,突然想起似乎好久没见小跑了。我起身想看看那幅十二身飞天图。这一看不打紧,上面竟少了一位。少的不是别人,正是小跑说的那个小顾。我问剩下的这十一个人怎么回事,她们却都不说话。她们倒是停止了飞舞,有的在吃李广杏,有的在吃敦煌瓜,有的在吃酒枣,其中有一个正从樱桃小口中往画外吐着阳关葡萄皮。
我第一时间去了物业中心,但反映情况后却没一个人理我,当然,我也看到他们确实都很忙,每人手里都有一摊子事。我给驻地派出所打电话,敌奇户和展朱阁两位警员很快就过来了。他们仔细看了一会儿画,然后说,你举报小跑偷了画中人缺少证据啊。我说他们谈过恋爱,警员说这不能证明。我说他心里一直还在记挂着小顾,警员说这也不能证明。我说小跑来过我的书房,专门评点过这幅画,警员说他是物业,去哪家都正常。我说但他认定画中那个人就是小顾,警员说这条线索倒值得参考。我说,更大的嫌疑是小跑辞职了,而且是突然辞的。他为什么要突然辞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警员说,这点我们已经了解过,他的确辞职了,但他辞职有别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业主们不能理解他。比如说你吧,他好心好意把你搀扶回来,你不是照样举报他犯了案吗?
看望老柳
天气已经到了深秋,我很喜欢这个季节,这个季节充满着金色阳光,风也绵墩墩的,充满着质感。但老柳是一棵树,它是否也喜欢,我拿不准。我想看看它,跟它拉个呱。
我们共同的话题自然是司息河,它在司息河边成长,我也在司息河边长大。司息河那可真是一条神奇的河流,从来没有人去过问过那些奔腾不息的河水它们到底从哪儿来,它们又将流向哪儿去。我所知道的是,有人用直钩在河水里钓鱼,有人用竹篮在河边打水,有人用河水织成了布匹,有人把细沙贩卖成了红糖,有人用布兜收集岸林中的晨露,有人用裸体储存树杈间的阳光,有人干脆搭起了爬满青藤的木屋,有人干脆捞起了河水中的月亮。甚至有个光棍汉,直接从河边背回来一大捆洗衣女们的笑声。村里,有人把河水弄到打麦场上,晒成了一方平地。有人把河水弄到鏊子上,烙成了煎饼。有人把河水弄到玉米地里,长成了红缨穗。有人干脆从地底下把河水引到自家院子里,长成了炊烟。司息河两岸的岸林那叫一个浓密,只是树木们只要发笑就会落光叶子,只要沉默就会发出绿芽。
我说,老柳你知道吗,村里人从来没想过有一天野猪会搬家,野鸡会去城里,野鸭会去别的地方下蛋,野兔会偷了长管猎枪后逃走。剩下的蚂蚱们在隆重纪念最后一个秋天,凡是像点样的树都忙着去找斧头。我跟老柳说,为了我们这次见面,我专门回去过一趟。自打你走后,河水就跟犯了糊涂一样,一会儿正流,一会儿倒流;一会儿长流,一会儿短流;一会儿左流,一会儿右流。后来从上游下来个浪头,到这儿后停下来,气喘吁吁地招呼其他水说,歇歇,先不流了吧。你想,司息河多么美的一条河啊,就这么说断流就断流了,大家伙感觉心里一点准备也没有。村里劲最大的那个人,你也认识,叫什么来着,反正我记不着他的名字,我都是喊他大力。有一天他喝醉了酒,一生气,把司息河给折断了,结果躲藏在里面的最后一批水,把整村人的梦都给淹了。有人说那不是水,那哗哗的声音听上去,有的像老人们的古话,有的像古人们的老话。村里的老调,就是那个爱做恶作剧的调皮鬼,这家伙用折断的河制作成了两个鼓槌,把牛皮一样绷紧的河床,擂得咚咚直响,那响声传到了千里之外,听到者无不感到惊心,都想知道司息河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有不少司息河的河水,从他们的眼睛里咕嘟咕嘟地流了出来。
老柳一阵沉默,我也不知道该继续说点什么。过了一会儿,我问老柳,你喜欢秋天吗?老柳说,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那么你感到孤独吗?老柳的树头在摇,枝条却一根根垂下,我不知道它是想表达自己孤独还是不孤独。我说,你如果觉得孤独,你就看看对面。
我知道,小罗这会儿是不会睡的。或许她也正在看着我们呢!我望向对面,看到她正一手托腮,身子前倾,烟头明明灭灭。这会儿,我倒很希望她能把靠山胜景貌似完整的夜晚,给烧出一个黑洞来,好让它向外流血或者冒烟。
小罗客厅的灯是关着的,屋里的灯全是关着的,静静的深夜中,靠山胜景的灯火也早已暗淡。但秋天夜晚的月色特别迷人,月亮撒下的银灰色微光,已经将她的影像制作成了剪影。她身子前倾,垂下来的胸布满光晕,清晰而又模糊,模糊而又清晰,特别好看,也特别动人。
老柳突然冒出一句,我好像听到有一条河正急急向这边奔来。
啊,是吗?我也学着老柳的样子,在仔细地听夜。
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没跟老柳说,这次回去,村里有不少人认为,那条河是我弄走的。
村人们能有这样的想法,我其实很理解。
阳台上那个人是谁
有天晚上,我起夜。从公卫出来时,突然看到阳台上坐着一个人,这让我很是一惊。我走过去,轻轻拉开通往阳台的推拉门,竟是老荆。他冲我一笑,坐!仿佛他是主人。我说,怎么是你?老荆说,我过来查看下烟火器,看你睡了,就没打扰你。我说,我家的烟火报警器不吸烟也报警吗?老荆说,也报。我问老荆,你是怎么进来的?老荆没回答我,却说,你都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骑自行车转悠。我笑了笑,说,自行车已经让我妻子给卖了。老荆说,有两个深夜看见自行车无人也自行的保安已经得了夜游症,不是他们的班,也每天晚上出来转悠。我说,我还以为最近你们人手多了,加强夜晚巡逻了呢!并问老荆,小保最近还来吗?老荆说,不来了,但也有人说,发现小区里有好几只野猫的眼神有点像他。这事物业上很重视,已经着手实施善待野猫计划,听说靠山胜景的好多老太太都已经自觉行动起来了,家里养狗的也储备起了猫粮。我说,我从荣成小镇买过小鱼,可野猫不吃。老荆说,我知道你跟三台地荣成小镇海鲜馆很熟,我看你经常往那跑,那个卖海鲜的漂亮小姑娘也挺愿意跟你聊天。我说,是啊,她说我跟小区里的其他人不一样,说话做事挺有意思的。其实,她愿意跟我聊天是因为我正在教她一项绝密技术。老荆问,什么技术?我说,这个不能告诉你。我只对黄花一个人讲。老荆问,那女孩叫黄花?我说,是的。第一次进店,我就问她黄花什么情况,她感到很惊讶,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我说,是大海告诉我的。她说,这个大海!原来大海是她一个闺蜜的哥。我跟老荆说,我认为她在这里时间待不长,她终究还是要回大海那边去的。老荆说,也许是吧。我说,不信你走着瞧。临走时,老荆说,外面有棵树好像老往这边瞧。我说,这没什么,因为我经常给它浇水。老荆说,没见你给它浇水呀。我说,是啊,可跟它说说话,说说雨天,说说河流,比浇水管用得多。我浇的是无源之水。
第二天碰见老荆时,我说,昨晚咱们谈得挺好,你什么时候再来啊?老荆说,昨晚?昨晚我去你那儿了吗?昨晚我早早就回家了。我说,哎,大半夜的,那我是跟谁谈的?老荆说,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跟自己在谈?
我仔细一想,老荆这话说得有道理。
一场大雪纷纷下
冬天来了,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铺天盖地。靠山胜景紧靠着青龙山,我决计躲开行人,爬上山去,去看看雪,看看天地。
作为一个中年人,我的时光早已经被一劈两半,一半还给过去,一半等待着未知的未来。
我说过,雨是液体的阳光,阳光是耀眼的雪,雪是心爱的女人,女人是风,风是少年,少年是我。我喜欢在雨中穿行,让一身湿漉漉的明媚,去把雪融化,任风将头发吹得凌乱。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颗心,自由自在地飞翔。心灵有多么自由,生命就有多么长久。这也是我选择购买靠山胜景新房的原因。
这应该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吧,它比往年来得都早、都大。雪一片一片落下来,像一个个美女,用手挡也挡不住,这个吻我,那个也吻我。按说这番情景激动的人应该是我,但我却发现她们在吻完我之后,一个个都选择了泪流满面。她们六角形的吻,晶莹洁白,透着冷冰冰的热气。我可以被融化,但她们却不可以被冻僵。
我站在半山腰上,看到茫茫原野坦坦荡荡,确实没有理由,去阻止一场大雪纷纷而下。这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被覆盖被收藏的季节。
我一直望向远处,等我向近处看时,我被吓了一跳,在距离我并不太远的地方,竟然站着一个人,一个雪人。我看她,她也看我。我仔细分辨,竟是小顾。确实是小顾。
我说,你……
她说,我……
我说,我没想到这会儿山上还会有其他人。
她仰起头,看着漫天的雪,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雪天确实适合一个人。
我问她,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但却说,你能把我再收到你那幅画里去吗?
我问,怎么了?
她说,我不想再在外面待了,没意思。
我说,你看这外面不是很纯洁吗?
她说,是很纯洁。但因为这是雪天。
我随口问,看来画的事小跑都给你说了?
她说,是的。
我说,有一件事很奇怪,我画上剩余的那十一个人后来也都飞走了。
她感到吃惊,怎么会这样?
我说,那天在书房,小跑一眼就从中发现了你。这说明他心里其实是有你的。我问他,今后你打算怎么办?他说他已经没有别的想法,只想等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成熟。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想了想,才知道他可能是想找个机器人。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孟姜女把爱情垒进了长城,祝英台把爱情埋进了坟墓,白娘子把爱情罩进了雷峰塔,牛郞织女稍微接些地气,但最后还是被扯到天上去了,这人间所剩的爱情已经不多,而且也都上了年纪,已经千年万年,他不想再指望了。
说完这些,我发现小顾哭了。
我说,我曾提醒小跑,与机器人的恋爱也许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看上去用一个小小的遥控器,就能掌握她身体的所有开关,她不跟你谈工资,谈住房,谈身份,谈地位,是挺好,很省事。但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们就这么过下去,有没有可能出现身份互换的那一天,你渐渐地变成了一架机器,没有了白天也没有了夜晚,而她却慢慢换上了人间的笑颜,生儿育女,柴米油盐,这可能是将来让你感觉难以承受的代价和风险。当时小跑说,我不想想那么多。
我和小顾两人一起下山,来时的路早已经被大雪掩没。我们走的肯定是一条旧路,但也完全像是一条新路。
我说,只要有爱,冬天就不会冷。
小顾补充说,但必须是真爱!所有打着爱的旗号的,都不算。
我说,我其实一直希望这世上的女子,都能清纯如花,她们浴晨曦,披晚霞。
小顾望着远处,呐呐地说,女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过了一会儿,小顾突然说,你快看那边,遍野桃花!
大雪时节,哪里还会有盛开的桃花!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一片雪野,苍苍茫茫,根本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说,对,还真是的,遍野桃花!
说这话时,我假装得很激动。
凶案
物业经理多次到家里来看望我,关心我的病情,同时也向我征求对小区物业管理还有哪些意见和要求。又一次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张108 身飞天图。我说,这是敦煌第427 窟里面的图案。经理忙着点头,是,是。我相信,他其实并不清楚这是哪一窟的图案,对他来说,只要我高兴就行。
确实,我有点高兴。
我仔细看了看这108 身飞天图,她们戴宝冠,饰璎珞,佩环镯,系长裙,绕彩带,同样是漫天散花。这些女人们让人爱,她们所代表的那段历史也让人爱。
经理说,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希望你这回能好好保管,加强防范措施,别再让她们跑了。因为物业人手少,一切靠物业,并不能完全照应得过来。
然后经理又说,好在,这回是108 个,人多,倒也不怕她们跑丢一个两个。
我说,真没想到,你能送这幅画来。
经理说,没什么,就是去一趟敦煌不容易,我们也是多次线上联系,最后还是托樊锦诗给买回来的。
我说,物业不错。
经理说,还是希望你多提意见。
我说,我就提一条吧。
经理并没想到我会真提,说,您说。
我说,你讲话时经常讲我靠怎么的,我靠怎么的,这样不好,不文明。
经理说,我看县区领导讲话都是说我县怎么的,或者我区怎么的,所以对靠山胜景来说,也只能讲我靠怎么的。
我说,我们靠山胜景能跟它们不一样吗?我们是什么小区!
经理连说,是,是。
经理走后,我把108 身飞天图小心翼翼地挂到墙上,决心睡个好觉,做个好梦。但一想起与小顾一起看雪时的对话,便再也睡不着。我重新爬起身来,看画。108 个女孩,从头看起,一个一个认真地看过去,看一遍需要不短的时间。上次小跑从12 个女子中,一眼就看到了小顾。受他启发,我后来从11 个女子中终于发现了里面有小罗,就是往画外吐阳光葡萄皮的那个。后来我发现,小区超市里的那个收银员女孩,荣成小镇中那个卖海鲜的女孩,中药房的女孩,理发室的女孩,幼儿园的女孩等等,她们都集中在画里面。除小罗外,我对荣成小镇中那个卖海鲜的女孩自然更熟悉些,因为我终于教会了她如何让冰冻的鱼重新活过来,这一招可不得了,让她的生意很是受用。她曾问我,这复活大法是不是老钟发明的?我说,你错了,这是大海发明的。这回她倒没说大海是她闺蜜的哥。
我一直对着画在看,连续看了好几遍,仔细查对后,竟没发现画里有小罗。12 个女子时里面就有小罗,多到108 个了里面竟没有,这讲不通。我突然想起,已经有三四晚上没有看到过小罗了,今晚她应该在。我匆匆走向阳台,向对面望去,对面却是一片黑黢黢的,仍然没有出现小罗媚惑的剪影。我越想越有问题,看看时间,已是凌晨两点,我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驻地派出所的电话。
值班人员问,什么事?
我说,报案。
什么案?
靠山胜景有个女孩失踪了。
她叫什么,住第几栋楼?
这我说不上来。
值班人员问,你怎么确定她失踪了?
我说,我认为是。
按正常敌奇户和展朱阁接到报案,用不几分钟就会来到现场。但这次没有。
早上,我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展朱阁,我说,小罗失踪了。展朱阁明白我说的小罗是谁,他问我具体什么情况,我说,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小罗,但最近三四个晚上一直没再看到过她。我记得她跟我说起过,她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我说你是租住何必要新装呢,她说租住也得搞得像点样,这样做起业务来,心情会好一点。重点是她联系的装修工是老庄,我担心老庄已经把她装进了墙里,她出不来了,你们得赶紧救她。不过这次到底是装进了承重墙还是非承重墙,我一下说不准。展朱阁说,我知道了。
又过了三四天,前面楼里的业主们纷纷反映楼道里充斥着异味,物业经理派两个保安前去查看。最后打开了小罗的门,发现小罗倒在地上,人已经遇害,血迹干了,但尸体已开始腐烂。
连着几辆警车开进了靠山胜景。案子很快告破,凶手不是别人,的确是老庄。
打架
弄清小罗死因的那天晚上,我书房里的书突然打起架来,弄出来的响声很大,把好不容易才睡着的我给吵醒了。
我走进书房,看到还没上架的书都在争先恐后地忙着上架,已经上架的书却都不愿意腾出位置。我的书房很小,但发生这样极不文明的骚乱还是第一次。
我狠狠敲了一下《喧哗与骚动》的头,说,一定又是你惹出来的事。《丰乳肥臀》告密说,本来,趁着夜深人静我们都在听《聊斋志异》,结果《老人与海》一不小心灌了进来。
这事怨不得海明威,我于是说了三个原则,一是鲁迅的,二是古典的,三是南美的,这三个不能动。
我的话音刚落,不在这三个范围的书,一跃而起,把整个书架全给砸烂了。
更为关键的是,等我回转身的时候,发现飞天图中的108 个美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部飞走了。
这时,我听到敲门声,这么晚了,会是谁呢?难道是出差的妻子回来了?不会这么快吧?
打开门,是敌奇户和展朱阁,两人走了进来,说,知道你睡得晚,就过来了。
展朱阁说,过来也是想向你道个歉,说实话,你早好几天就给我说了,但我并未拿着当事人。
敌奇户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得感谢你。没有你,案子不会破得这么快。
两位警员见我一脸木讷,问我怎么了?
我拉开了书房的门。除书架被书砸烂了以外,108 身飞天图下,散落着一地花瓣。其中还有一条她们没能带走的彩带,开门带起的风,吹得那条彩带独自飘舞。
难道她们就那么喜欢那些木构崖岩,那些莲花柱石,那些铺地花砖?当然还有那片千年荒野。难道她们就不怕被敦煌咽喉锁钥?我自言自语。我相信两位警员并未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但他们都在同一时间说,是这样。
我问了一句,老庄为什么要这么做?
展朱阁并未接话,而是说,楼下的垃圾筒都已经分类了,这世界已经堆积了太多的垃圾,其实人也是其中的一种,区别仅在于,有的可以分类,有的不可分类。
我很想知道小罗算不算垃圾,我向他们提出质询,敌奇户说,这要看你怎么看。
妻子出差
妻子因公外出从来没有过这么长时间。去年清明节物业组织业主在小区内植树,我和妻子一同栽下了一棵海棠,前几天下楼时,我发现它已经开花了。妻子是过完正月后走的,现在已经是满园春天了,妻子还没有回来。早年,我跟妻子都年轻气盛,经常争吵。如今随着年轮渐长,各种矛盾已经渐趋平和。我为此专门记过一篇日记,题目叫《夫妻》,是这么写的:从一天一次,到一周一次,到一月一次,到一季度一次,到一年一次的无休止分歧和争吵,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和平,已慢慢步入一年一次,一季度一次,一月一次,一周一次,一天一次的问候与呵护,难分与难离。这是一天,也是一生。它跟一天一样短,又跟一生一样长。
夜晚,没有了对面楼上小罗的剪影,日子仿佛更加难熬。有时候我为了节约时间,让时间过得更有价值,我会拿出大量的时间来确保让自己无所事事,甚至煞有介事地独自孤坐,假装自己很会思考,很能思考。很多时候我其实是用睁着的双眼,去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沉睡。
书房里的书我已经收拾停当,但画框里的飞天图一直空空荡荡,飞走的飞天女不可能再飞回来。但等我再次抬头的时候,忽然发现画框里孤零零地冒出了一个飞天女,胖胖的,对着我一直在笑。
这人怎么感觉这么面熟啊。定睛一看,我说,就你这体型也能飞!我把她一把扯了下来。落到地上后她还在笑,我嘟囔了一句,我终于知道那些曼妙女子为什么待不下去赶紧飞走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