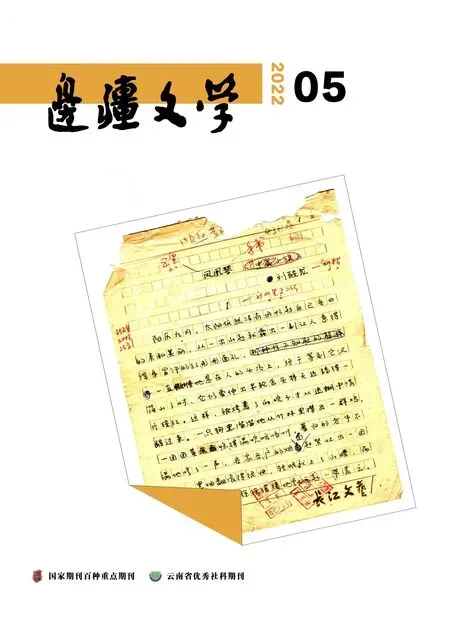鄱阳湖女人
米来
梅雨
立夏之后,青梅的果子还挂在树上,雨季就来了。在一个午后,或者是半夜,从遥远的地方滚过来一阵雷声。过了两天,雷声从湖面上踏浪而来。风伴着雷,湖水渐渐汹涌。嫩绿的柳树在风雷中伸展着柔软的肢体,以骄傲的姿态起舞。风儿摇晃着青梅的果子,丰满的桃子禁不住坠落到屋顶。树叶飒飒作响,扫落屋檐的一块旧瓦。风从缝隙里进来,穿过卧室的门,径直进入梦中,又从梦中坠入湖中。怕它碎了,用双手去捧,却捧了个空。醒来惊坐,耳畔风声、雨声、梅子坠落的声音不绝。恍然大悟,哦!梅子的季节到了。
第一场梅雨到来的时候,通常是下得热烈奔放。配合着风雷闪电,雨水像帘子一样盖下来,天空因此低垂,湖面因此广阔。黑色的屋脊在雨水中发出亮色,干涸的墙壁在雨中膨胀,树木在雨水中成熟,土地承接着人们承受不了的雨水,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奔淌。
一场雨水之后,天气忽然就闷热起来。水在空气里蒸发,雾一般的水汽袅袅升起。梅子渐渐成熟,从地上拣一颗起来,嫩绿的躺在红嫩的掌心。攥紧了拳头捏一捏,有些生硬。放进嘴里咬一口,酸涩异常。赶紧吐出来,可是满嘴的酸涩已经侵蚀到内心。于是把梅子用瓷坛装起来,撒上一把盐,再撒上一把糖。把盖儿封了,藏在床下,等待梅雨的过去。
也许是第一场雨下得太猛烈了,之后的雨水渐渐温柔起来。像雾一样的蒙蒙细雨,绵绵不绝地笼罩着天空。间或可以看见成形的雨线了,那雨水就像是从天空中垂下的挂面,清晰而又整齐。有时候起风了,铜钱一般的雨点砸在地面上,把青石板的路面也砸成密密麻麻的小坑。这梅雨的性格,既温柔又缠绵。她那种似乎无休无止的劲头,让人爱不是,恼不得。
泡桐树是梅雨最得意的作品,梅雨前的泡桐还是一棵幼苗,一场雨水下来,泡桐的叶子就肥大起来。泡桐贪婪地吸吮着雨水,它的身体因为雨水的滋润而粗壮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飒飒作响的雨声中,可以听见泡桐拔节而起的呻吟。清晨的时候,雨如果停了。满地的泡桐叶躺在地上,那肥硕的叶片上,依然凝聚着颗颗圆润的水珠。
北方来的人第一次经历梅雨,会惊叹自己被梅雨缩小了。衣袖比过去长了,裤腿边也拖到了地上。南方人在梅雨中出入,袖子裤腿一齐挽得高高的。女人倘若被独自羁绊在屋里,她会情不自禁的把指甲蓄得长长的,然后用那长长的指甲去抠门框。抠一下,门框留下一道痕,再抠一下,门框掉一块皮。当梅雨期过去后,门框就像是被耗子啃过一样,留下千疮百孔的痕迹。
竹木的房子,还有家具,都在梅雨中发潮变霉。桌子的榫头开始松动,木箱里的衣服发出腐烂的气息。这种气息在空气里弥漫,直到泡桐树开花了。一朵一朵的喇叭状的泡桐花砸到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没有人怜惜那洁白的泡桐花,只有几只蚂蚁抬着它在移动。泡桐花落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梅雨就要过去了。
这个时候,从床底下散发出一股酸酸的香味。人们记起了床底下的青梅,赶紧把坛子揭开,一坛青梅化作半坛水,半坛梅。梅子已经失去了翠色,那半坛水化作褐色的甘露,成为人们夏天解除酷暑的饮品。梅子熟了,梅雨终于过去了。
渔网
夏季的风,带着湖草的清香、带着湖水甜腥的气息,无声地弥漫着。赤脚的妮子,踩着被太阳灼热的湖沙上了岸。沙滩上印下一串脚印,摇晃的船儿把湖水推过来,是一汪汪小水坑。一级级台阶,是粗沙岩上开采的红石。沾着泥沙的脚板,在红石上跳跃。妮子身后的台阶,在热烘烘的气流下,顷刻只留下一抹细沙。微风吹过,细沙如雾一般升起。
湖畔的人家,盘踞在高高的红石台阶顶上。红石、青瓦和翠柳,组成一幅渔村图画。图画中的柳树,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的内容。一张张摊开晾晒的渔网,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妮子的说笑声从画面后传了出来,她捧了一把丝线,后面跟着拖了网架的女伴,三五一群地来到了柳树下。织小网的将网绳缠在网架上,织大网的将网绳绑在树身上。她们一手握盾,一手拿针。双目凝视着手中的渔网,两臂上下舞动。她们的眉眼在笑,她们的嘴巴在动,渔网随着她们的动作也在慢慢地伸长。
一个妮子织网,是一幅画。一群妮子聚在一起织网,则是一台戏。一把竹针,就像一条鄱阳湖里的鱼。织网用的丝线,就是鄱阳湖里的风浪。丝线有多长 ,波浪就有多宽。竹针在波浪里面穿梭,就像吐丝的蚕儿,渐渐攒成一张围困自己的大网。妮子将网针握在手里,有一种握住鱼儿的感觉。生活就像手中的网针,一不小心就会从手中滑落。可是定下神来,一切都握在手中。妮子的心绪,就像鄱阳湖的浪起伏,又像手中的渔网,错综复杂。
漫长的季节,是因为等待。经过一个季度休养生息,鱼儿肥了,水也干了。鱼儿从水面上露出脑门,仿佛在窥探织网的妮子。妮子的网已经织得很长很长,红石台阶的湖畔上,那一片一片的渔网,仿佛把渔村都给网住了。
渔夫把渔网接过来,数一数渔网的网眼,量一量网眼的尺寸。岸上的动物有多少种,水中的水族就有多少类。捕大鱼,用大网,捕小鱼,用小网。渔网的丝线有的细如发丝,有的粗如棉线。渔网还分捕网、放网、拉网、罩网等,各因捕鱼的需要而设。
渔网从妮子的手中完成后,到了渔夫的手中,还需要很多工夫。给渔网上瓢子,结甸子,还要上浆子。新渔网出湖,先要上浆。将几十斤鸡蛋,打进一个大木盆中。用勺子将蛋黄舀出,留下透明的蛋清。然后把新渔网放在湖中浸透,甩掉水分,然后将渔网投入装有蛋清的木盆当中。把渔网在蛋清中一上一下地来回摆动,一条渔网要摆动半天的时间,渔网才能均匀地将蛋清全部“吃”进去。渔网“吃”饱之后,要让渔网在木盆中休息一晚,让它“醒醒”神。第二天,再将渔网挂在太阳下晾晒。晒干后的渔网,才可以下水捕鱼。
妮子送走新织好的渔网,心儿就跟随着渔网上了船。听老一辈的渔人说,一条新渔网打的鱼,可以抵得上几条老渔网。尤其是浆得好的新渔网,撒到水里面,落水的速度就像刀切到水里面,无声无息。被网住的鱼儿,无论怎么使力,也挣脱不了渔网。于是她半夜里爬起床,推开后窗户门,面对着繁星和一湖波浪,她的心又是焦虑又是期盼。自己织的渔网是否均匀?网上的网结是否结实?那丝线没有用错吧。于是她一夜的梦,尽在鄱阳湖的风浪中起伏了。
赶集
前一天就相约了伙伴,做好了准备。箩筐整齐地摆在院子里,扁担竖立在门背后,绳子也圈成卷,静静地躺在箩筐边。男人照样喝了二两酒,倒头就睡,不久就发出很响的鼾声。女人在旁边推,却推不醒。心里笑骂:醒的时候像老虎,睡着了像死猪。心里有点憋屈,有点伤感。忽然抬头看见月亮,明晃晃的显得格外敞亮,越发睡不着。为啥赶集的日子,月亮就格外亮呢?只有十六岁才会问的傻问题,忽然又缠绕上妇人的心。
天还是麻麻亮,妮子就坐在梳妆台前梳辫子。站起身,长辫子垂到屁股下。坐下来,辫子就垂到地面上。把辫子绞了,留着它管啥用?影响干活呢。爹这样说。是呢,城里人也不兴留长辫子,嫌弃它土气,每天费事梳理不说,还浪费钱买洗发水呢。娘也在一旁帮腔。妮子不回嘴,咬住嘴唇,两汪泪却在眼眶里转。等到下到田间,爹娘果然没有看见妮子的长辫子。可是到了十五赶大集,妮子把头巾撤下,一头乌黑的秀发瀑布一样洒下来,把村前村后的眼睛都吸引了来。
鄱阳湖流域四十八村镇,七天一小集,半月一中集,整月一大集。小集集中在几个村,是一个小范围的交易;中集放在乡镇,是一个集生活用品大全的大交易;而大集则除了生活用品外,还包括商业交易和娱乐大全的聚会。除了附近几十个乡镇外,还有省府和外省市的轮船过来,因此时间都定在每月十五。
到了赶大集的这一天,人群从四面八方像流水一样涌来。湖泊交错的圩堤上,只见人们挑着担子,挽着篮子,推着车子往集市上赶;宽阔的马路上,摩托车、汽车、拖拉机的喇叭声响成一片;渡口的湖湾里,泊满了乌篷船和轮船。
穿西服打领带的,夹着公文包的,指挥着一帮人收购大豆和花生。穿长靴子的,戴胶皮手套的,趟着水在大声叫嚷收购银鱼;留着满脸胡子的,长了一身横肉的,则围着一群生猪、鸡鸭来回转。他们大多数是外来的商人,带着空车空船到集市上来收购他们需要的东西。来的时候干净整齐,走的时候满身的灰尘。
附近的居民在生活区摆满了摊子,卖馄饨小吃的、卖甘蔗水果的,卖金银手镯的,卖衣物布匹的挤在一起。那高高挂起的花布,在太阳的照耀下,哗啦啦抖动着,映红了一条街。那些从商业区出来,卖掉了粮食大豆或水产的乡民渔民,纷纷挤进了生活区。尝尝街边小吃,扯几尺新布,或者买个新彩电,高高兴兴的就回了家。
留下来的是一帮年轻人,他们要逛夜市。妮子到照相馆化个妆,描个弯弯眉,烫个波浪发,穿上唐人装,背后用一把大折扇做布景,留下一张十六岁的倩影。等到了人家来相亲,就用这张照片做诱饵。到了晚上,相熟的女伴一块去看露天电影,围着篝火吃烤鱼。
妮子一伙,后生一团,你往我这里扔骨头,我往你那里扔炭火。被砸着的妮子发一声叫,于是妮子们集体起来还击。烤鱼变成了手中的武器,烤鱼从妮子的手里飞出,像雨点一样砸到后生们的头上。后生们既不跑也不躲,只将衣服翻过来,罩住一个脑袋。到烤鱼砸完,那个惹祸的后生站出来,老老实实按照砸出烤鱼的数目跟老板去结账。
妇人还沉浸在半睡半醒的梦里,忽然男人的一声吼把她唤醒。坐起身,揉揉眼,太阳升到半空中了。男人把一切收拾停当,正在院子里抽烟。谁叫今天是赶集的日子呢?他就是在当年赶集的日子认识的她。
黄金
金碗、银筷、铁锅、铜壶、珍珠项链翡翠玉,是鄱阳湖女人一生的梦。尽管在现实中,她们首先考虑的是吃住行,但是只要有可能,这个梦就会从某个角落里冒出来。
娃儿在娘肚子里还没出来,娘就给他缝衣服鞋帽。鞋是虎头鞋,帽是老虎帽,老虎额头上总有一个金线锈的王字。一套红色的夹袄,用彩线和金绣一起,沿着纽扣的边沿,绣上象征吉祥的图案。娘将她所有的梦想,凝聚在一根绣花针和一根黄金线上。她用她的恬淡、从容、沉静,来传达她一个女人对生活强烈追求的愿望。
娃儿出生了,家里宽裕的,就给他打一个金项圈;家里不宽裕的,也给他打一对银手镯。项圈上,或者手镯上,挂几串铃铛。娃儿笑的时候,手舞足蹈,把铃铛摇得叮当响。娃儿哭的时候,举手踢脚,同样把铃铛弄得叮当响。娃儿爬动的时候,手脚并用,爬到哪里,哪里就一阵叮当声和笑声。
这个时候女人的笑,是无所顾忌、敞开心扉的笑。这个时候的女人,突然间接受了烈日下曝晒、风浪中搏斗的生活现实。她从过去那个含蓄、腼腆、胆怯的妮子,变成了一个勤俭、贤惠、耐劳的女人。
娃儿渐渐长大了,背起了书包,开始走出娘的视线。娘把虎头鞋、老虎帽,还有金项圈、银手镯收了起来,压在了箱子底下。娃儿是个男的,娘就悄悄地给他攒钱。如果娃儿考上了学校,就留着给娃儿做学费;如果娃儿要出门远行做事,就给他做盘缠;倘若娃儿哪儿也不去,继承爹娘的事业,娘就把积攒下来的钱,换成金项链、金耳环或者金戒指,留着给他做娶媳妇的彩礼。
如果娃儿是个女娃,娘也偷偷给她攒钱。无论她长大以后,是丑是美,有钱还是无钱,娘都要给她一份薄礼,一条赤金的项链,或者一块厚实的金元宝,或者是一对祖传的耳环,一个纯金的戒指。在女娃出嫁的时候,娘俩相对流涕。在娘的心里,娃儿从此像断了线的风筝,离她越来越远。那根断了的残线,依旧还缠在娘的心头。可系住女儿的那头,却只能在风中飘舞了。娘把对女儿的忧虑,化做一个行动,将一份薄礼压在女儿出嫁的箱子里。
娘这个时候依然有梦,只不过她把她的梦,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和耕耘。早晨的星辰,可以照见她的身影;深夜的月亮,经常伴随她的脚步。就在她挥舞锄头的瞬间,或者是在她摇动船桨的刹那,在强烈的阳光下,有一道炫目的亮光从她的手腕上闪了出来。
不用奇怪,在鄱阳湖的流域,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女人。她到湖边洗衣,双手在水中摆动时,有一对玉手镯也浸在了水里。她在灶台上做饭,握住锅铲的手上,有一只银手镯被磕得轻响。在大街上,集市中,金银铺子的前面,永远拥挤着女人。年老的,年轻的,她们将一双眼睛,深情地凝聚在一堆金银上面。
世界上有很多种颜色,可是金银的颜色最动人;世界上有很多动听的声音,也许金银的声音最动听。在鄱阳湖女人的心中,对于金银的梦想,一代一代的传承。或许这不仅仅是一个梦,如果把它比作梦,那么这个梦就是能够激发她们战胜磨难,直面生活的梦。
鄱阳湖的女人,爱金银,更爱生活。
夏夜
夏季的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那橘红的天色显得格外温柔。浅浅的湖浪,轻轻地向湖畔推来。落晖渗透到风里,撒到岸边竹楼的屋顶。竹楼里的门敞开着,穿堂风从屋里刮过,携带来清凉的气息。在竹楼里躲了一天的人,终于钻了出来。赤着胳膊的汉子,肩上搭一条毛巾,从自家屋后的石台上,高高地跃入了湖中。
穿了蜡染衣裙的女人,提着一只小木桶。她站在高高的石台上,用吊绳把木桶放入水中,看水中的汉子游过来,把水桶装满水。然后她缓缓地将水桶提起来,将铺有红石的地面一遍一遍冲洗。被烈日蒸烤了一天的红石,被清凉的湖水一浇,立刻腾起一阵青烟。当地面被湖水完全湿润之后,湖水就顺着地面往下流淌。
女人冲完地面,汉子就上了岸。冲洗后的红石,显得洁净而又清凉。于是人们把竹床搬到了屋外,并把小圆桌支了起来。女人端上几碟咸菜腊鱼,熬一锅南瓜粥。一家人就着湖水,伴着垂柳,在夕阳的风中用晚餐。
当夜幕低垂,满天的星星在天空闪烁。湖边的岸上,那一家一家的竹楼后,悬挂着一盏盏马灯。朦胧的灯火下,围着一位老人,在谈天说古。另一边,摆了几个棋阵,汉子们各自占据着棋阵的一角,相持不下。女人则抚摸着幼小的娃儿,轻轻哼着古老的催眠曲。
这个时候,有一点渔火在湖面上移动。当渔火靠岸的时候,有叫卖菱角的声音传来。正在假寐的娃儿一咕噜的就爬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女人用扇子拍打着娃儿道:哄了半天,原来是装睡。卖菱角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娃儿开始央求,女人用指头轻轻地戳一下娃儿的额头,嗔道:就知道你想着菱角,看样子不给你买你是不罢休的。说罢趿了拖鞋,就向渔火处走去。
卖菱角的是一对母女,看到来了人,妮子把草帽拉低了,罩住了半张脸。娘一边高声叫卖,一边笑迎着客人。买菱角的女人过来,看到筐中饱满的菱角,不禁嘴馋。拿一颗尝尝,咬一口,水汪汪的入口,甜糯糯的进喉。忍不住赞道:真是地道的菱角。卖菱角地笑道:本地南湖里采的,味道当然地道。买菱角的附和道:南湖里不仅菱角好,芡实和莲子也好。我就是南湖人,和你妮子一般大时,我经常去采摘的。卖菱角的母女一听,立刻和这女人亲热起来。她们唠起南湖,话题就没有完。到了最后,卖菱角的送了南湖女人一大兜菱角,南湖女人则邀请卖菱角的到自家去喝茶。
在喝茶的过程中,南湖女人站在自家石台上叫嚷了几声,附近的女人都围了过来。你一兜,我一篮,两筐菱角顷刻被卖光了。女人把卖菱角的送下船的时候,还附带送给妮子一块布,送给妮子娘一条头巾。
等到女人回到竹床旁,娃儿已经入睡,地上撒满了菱角壳。女人把菱角壳打扫干净,躺在清凉的竹床上,看着卖菱角的船儿远远的离去。柳条在头顶晃动,湖水轻轻地拍击着石台。屋檐上悬挂的风铃,在风中发出丁当声。女人仿佛枕在波涛上,进入了少年时的梦乡。
当夏夜悄悄流逝,当黎明静静来临时,晨霭还没有消逝。渔船还没有起锚,湖浪摇晃着船儿,鹭鸶站在船舷打盹。河岸上的柳树,依然在晨风中飞舞。早起的水鸟从水面上掠过,竹楼后的石台上,人们依然在竹床上熟睡。静谧的世界上,惟有风铃的响声与水鸟伴舞。
照相
鄱阳湖的妮子,长到十六岁的时候,或鲜艳如早晨的露珠,或饱满如夏日里的莲蓬,或淡雅如水面的菱花,或活泼如涌动的湖浪,或柔软如沙洲的湖草。朴实中透着纯真,活泼中充满灵气。为了留住这岁月的美好瞬间,妮子们往往选择了照相馆。
十六岁的生日,家里人没有人留意,可是妮子的心却兴奋。在几个月前,妮子就用织网的钱,偷偷地买了新衣裳。或者是高领的毛衣,或者是彩色的裙子。毛衣的颜色要鲜艳的,裙子的花色是新颖的。或许这种毛衣和裙子在平常不能穿出去,因为无论是上船或下地,这种衣裙都不方便。一件毛衣好几百,一件裙子也是好几百,那是妮子织了一个月网攒下的工钱,可是妮子一点也不心疼。
一生之中,能有几个十六岁呢?穿上最好的衣裙,配上娘藏在箱子底下的金项链,画一画眉梢,把粗壮的长辫子垂到胸前,轻抿红唇微笑,这是妮子对自己形象最美好的记忆。到了生日这一天,妮子比往常都起得早。爹娘有点诧异,但也不以为然,妮子向来勤快。等到爹娘上了船,或者扛着锄头下了地,妮子就轻掩房门,打一盆水,仔细地擦洗自己。
妮子换好了新衣裳,坐到了镜子前。梳头,化妆,左看右看,外面就有女伴叫唤。妮子假装很自然地开了门,心里却企盼同伴的惊羡。女伴们果然发出惊叹,因为妮子的衣裳确实好看。于是妮子们相拥着出了门,来到了照相馆。照相师一眼就看出了是妮子的生日,因为女伴们为了陪衬她,故意穿旧一些做绿叶。
妮子照完相,把新衣裳脱下来,照旧藏在箱子里。她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照片的出来。过了几天,女伴们忽然上了门,说照相馆里已经挂上了妮子的照片。妮子很激动,心里咚咚地跳,拽着女伴的手就往照相馆跑。照相馆的墙上,果然挂了一张扩大了的彩照。妮子站在自己的照片前,有点晕眩,又有点迷惑,怎么看都觉得照片不像自己。这时候的妮子,就觉得是自己被钉在了墙上。她想把照片要回来,可是又想让照片继续留在那里。妮子从此就像分裂成两个人,一个在照相馆的墙上,一个在她自己的身上。
妮子的照片吸引了很多人,从此就不断有媒人来上门。爹娘发现妮子与往常有些不同,她仿佛变成了一个空壳,失去了灵魂。爹娘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妮子的魂被钉在了照相馆的墙上。爹娘最后把照片要回了家,交到了妮子手上。妮子把照片抱在怀里,又把照片挂在自己的闺房,后来担心照片上了灰,又把照片藏进了箱子里。
妮子出嫁了,箱子里带着那张让她灵魂出窍的照片。后来她也生了妮子,妮子渐渐长大,娘的容颜却渐渐衰老。已经变成老妇的她,渐渐忘却了当年那张照片。当梅雨过后,妮子帮娘把箱子搬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发现了娘的照片。照片虽然已经发黄,可是依稀可以辨出和自己相似的轮廓。妮子仍然要问,这是娘吗?娘没有作声,可是内心却心潮澎湃。爹的眼角有了泪花,点点已经花白的头说,这是你娘十六岁的生日照啊!妮子突然感悟到岁月的痕迹,青春如花,朝花夕逝,自己原来在延续娘的过去。
女红
如果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夫妻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就建议男人娶南方的女子为妻。因为南方的女子,不仅克俭勤劳,而且在持家方面颇有特长。南方女子的五官,不仅本身秀色可餐,还是食色的制造者和鉴赏者。其中值得称道的,就是南方女子的女红。
初到南方的北方人,可能会抱怨南方的雨下得太多。可是南方的人却从不嫌雨多,尽管小溪、池塘、河道还有湖泊都被雨水灌得满满的。可是南方人还是笑着说,水带财,财水财水,越涨越旺。
并不是因为迷信,因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会变得丰盈起来。不说湖泊的鱼虾,也不说河畔的莲藕。单单是地里种的葫芦、南瓜、丝瓜、茄子、萝卜、地瓜,仿佛都储满了水分,一个个变得水汪汪肥胖胖。就连树上的叶子,架上的青藤,也变得翠绿粗壮,仿佛一拧就能拧出水来。
树上结的桃子、李子、杏子、梅子,红的红、青的青、黄的黄;架子上趴着的梨瓜、香瓜、西瓜,一个个把藤儿坠断;还有水中的莲子、菱角和芡实,也粒粒饱满。瓜果种得多的人家,就给有小孩的亲戚家捎信:让娃子放了假上我们家来,今年的瓜果吃不完呢!
西瓜吃不完,干脆就踩碎了,用箩筐浸到河里去漂洗。把浮出来的瓜瓤去掉,把沉淀到筐底的瓜子捞起来,晒干后炒瓜子磕。西瓜皮却舍不得扔,把它们剐得薄薄的,上了蒸笼蒸熟,再用纱布包起来,榨干水分。然后切成碎片,拌上香油、食盐、辣椒、香料,就是一道瓜皮名菜。
莲子吃不完更没关系,直接把它们放在太阳下曝晒,晒干后装起来。想吃的时候,把莲子放进石磨里走一圈,褐色的皮、白色的莲肉、绿色的莲心就分开了。莲子皮可以做枕心,莲肉可以生吃,也可以炒着吃炖了吃,莲心可以入药。红枣、李子、桃子、梅子也和莲子一样,如果吃不了,可以晒成干,也可以腌制成酱。西瓜、甜瓜和梨瓜,可以榨成果汁,当成饮料喝。
一般来说,男人是张嘴的,女人是动手的。除了摆弄渔船渔网,侍弄田地外,女人私下里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做女红。女红分为两种,一种是干的,一种是湿的。干的是指缝衣服,绣花草;湿的指晒干菜,腌制瓜果。女人之所以爱女红,不外乎两个字,吃和穿。一个满足于果腹,一个满足于裹体,本无可非议,可是她们偏偏要作出许多文章。
因为要做女红,所以女人的东西就特别多。比如绣花,不仅需要彩丝线、绸缎、绣筐绣架,还需要样图等等。而做湿女红,需要的东西不仅多,而且很占地。比如腌制瓜果,需要很多很多的坛坛罐罐。女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各种器皿。有人喜欢陶器,有人喜欢瓷器,还有人喜欢瓦罐。于是女人们变成了陶瓷鉴赏和收藏家,比如景德镇的青瓷,她们一眼就能分辨出自哪个年代;一个缺了口的瓦罐,她们能说出瓦罐出自哪个窑。
南方女人就像蜜蜂一样,春夏秋冬不停地忙碌着。春天绣鞋袜,夏天腌制瓜果,秋天下田地,冬天缝衣裳。偶尔的轻闲,会让她们想起青瓷上的美人图,还有腌制在坛子里的酸梅酱。忍不住用小指头蘸一蘸,放进嘴里舔一舔,酸溜溜甜丝丝。于是做一罐酸梅汤,装一瓶桃子酱,提一袋莲子干。酸梅汤给男人解暑,桃子酱给孩子解馋,莲子干送给婆婆清火气。女人最后空了手往回走,一边走还一边傻傻的乐。她在想什么呢?可能还是女红。
相亲
妮子和女伴们坐在院子里织网,正打打闹闹,忽然三姨婆来串门,妮子们立刻噤了声。有一个女伴冲妮子做了个鬼脸,妮子的脸腾的就红了一片云。她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恨不得自己的耳朵能飞进屋里,听听三姨婆和娘在说什么。
其实什么也不用听,三姨婆上门就是专为妮子来提亲。三姨婆走后,娘把妮子叫进屋。可是妮子用手把耳朵堵住,什么也不想听。娘知道妮子的心思,妮子不想听人家怎么说,她要自己先看看人才行。娘只好找个借口,带着妮子到沙洲上去割草。娘把口信带给了三姨婆,三姨婆立刻领会了妮子娘的意思。
娘在前边走,妮子在后面跟。这个时候,天边就响起一片大雁的叫声。大雁排成长长的一队,就像一条柔软的缎带,从远处飞了过来。领头的大雁扑腾着翅膀,将半个身子俯冲下来,接着又腾飞而起,发出一声高昂的鸣叫。仿佛经过排练一般,跟在它身后的第二只大雁立刻从队伍中分离了出来。第三只大雁依然紧随着原先的那只头雁,第四只大雁跟在了第二只大雁的身边。头雁的一个动作,在刹那间让一队大雁分为两列长队。两列大雁一会儿交叉成十字,一会儿汇成一个人字,一会儿又并行而飞。它们仿佛在用翅膀举行一个仪式,用飞行表达互相之间的依恋,用这种形式来倾诉难分难舍的感情。
妮子正弯腰割湖草,抬头就看到天空中的一幕。眼见一支大雁远离而去,另一支大雁在后面恋恋不舍地追赶。渐渐的后面那支大雁慢了下来,它们在空中盘旋,发出凄凉的低鸣声。大雁的叫声触动了妮子,想到娘把自己领到沙洲上来,就是为了要把自己嫁出去,禁不住眼泪婆娑而下。
妮子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像鄱阳湖畔的一棵湖草。娘下地,把她背着;娘休息,顺便给她喝一口水;当她开始走路的时候,就跟在娘的身后拔草;五六岁的时候,她就学会了洗衣做饭;等到她再大一点,她就会织网绣花上沙洲割草了。
三姨婆不是妮子的三姨婆,可是同村的人都叫她三姨婆,所以妮子也这么跟着叫。妮子第一次绣鞋垫,三姨婆就把她盯上了。妮子用白色的竹布做底,将帆布染成深蓝镶边。再用红、绿、蓝颜色的纱线,在鞋垫上锈一支荷花,荷花下是满塘的荷叶。三姨婆就抢过去看,一边夸她的手工好。妮子绣花的时候,远远看见三姨婆过来,就把绣框藏起来。三姨婆笑眯眯哄她道:给我看看,将来给你说个好婆家。妮子又羞又气,抢白道:谁让你说婆家?我一辈子不嫁人。
不嫁人是妮子一时的气话,没有人会把这话当真。想到娘一心要把自己嫁出去,妮子的心就有点凄凉。娘在身边开导她说:妮子大了,就像天上的大雁,总要单飞出去,过自己的日子。嫁人就像大雁找个伴,两只大雁一起飞,总比单飞要强。可是妮子认为,大雁是大雁,人是人。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对妮子来说充满了风险。
妮子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觉得有人在暗处盯着她看。她回过头去,却不见人影,只听唰唰割草的声响。湖草倒下的时候,就像一阵风刮过来,把湖草刮倒一大片。妮子有些吃惊,又有些痴迷,想看看割草的人是谁,可是湖草遮住了视线。朦胧中只看见一个模糊的背影,还有那镰刀的白光在舞动。
前边忽然听到三姨婆和娘说话的声音,妮子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割草的声音离她越来越近,妮子不由耳热心跳,不敢抬起头来。割草的人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干活,呼哧呼哧的喘气。两个人碰了头,互相看一眼,却又相互走了开去。
妮子本想停住脚,问问他的姓名,住哪个村……也许割草人也想停住脚,和她说说话。可是两个人都不知如何开口,就这么错开了机会。妮子这时候把不想嫁人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她希望娘和三姨婆能再给她一次机会,让她了解了解割草人。
湖草
湖草被人关注的季节,就是湖草成熟的季节。就像鄱阳湖畔的黄毛丫头,忽然长成红唇鲜艳的妮子,吸引了一双双后生的眼睛。湖草一片一片的铺开来,无边无际的样子,就像鄱阳湖绿波荡漾的湖面。一阵风儿吹过来,湖草连绵起伏。一种青悠悠的湖草的味道,从草根下散发开来,弥漫在湖畔的空气里。
其实,湖草刚刚从沙土里钻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她们。或许是在冬末的雪后,或许是在初春的细雨中。在潮湿的沙土上,忽然就冒出一丛丛鲜嫩的湖草。湖草挺立着矮小细弱的身子,隐藏在远离人迹的沙洲上。可是人们还是发现了她们,并且把她们加以分类,将其中可以食用的一种称之为蒌蒿。
湖畔的妮子都认识蒌蒿,她们挽着篮子,或者撑着船来了。把蒌蒿采摘回去,捋去叶子,去掉土根。把蒌蒿掐成一寸一寸的长短,用半肥半瘦的腊肉爆炒,再洒上一把红辣椒。红绿相间的蒌蒿下到盘子里,就一壶酒。家人围坐一团,或者招待客人,青悠悠的蒌蒿,伴着浓浓的酒香,成为鄱阳湖的一道风景。蒌蒿炒腊肉,也就成为当地一道特色菜肴。
蒌蒿的生命很短,过不了十天半月,蒌蒿就不再脆嫩了。这个时候的蒌蒿,又变回了普通的湖草。经过漫长的梅雨季节,湖水涨起来了,把沙洲上的湖草淹没。细小的湖草们,在水中轻盈地摆动。有些不甘寂寞的湖草,把修长的手臂伸出湖面,仿佛在波涛中起舞。这个时候的湖草,沉浸在梦一般澄澈的境界里。她的颜色是青翠的,她的身材是柔软的。她将她青春的美,全部展示给水中的鱼儿,天空中的白云。
夏季过后,湖水渐渐退却。湖草从水中露了出来,由于失去了湖水的滋润,她渐渐干枯。平常寂静的沙洲,忽然就热闹起来,妮子跟随着娘来收割湖草。娘割草的时候,手握磨得白晃晃的镰刀,身子弓下去。空气里一片镰刀的声音湖草断裂的声音。
妮子不喜欢这个声音,尽管她手里也拿着镰刀。当看到娘毫无表情地割草时,她的心就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娘曾经说过,妮子的命就像这沙洲上的湖草。湖草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不需要施肥,也不需要耕耘,更不需要呵护。风里雨里,沙里泥里,她们挣扎着生存。到了秋天,她们等待着人们收割。把湖草编成草帽、草筐、草绳、草鞋,或者把湖草变成一把火,用来取暖或烧饭。一年一年又一年,伴随着湖水的涨落,湖草一茬一茬地接着生长。
妮子想着湖草,心里就有一种委屈。于是她远离了娘,自己找了一块湖草地。她弯下身割草的时候,镰刀下得快,湖草却放得轻。她手里握着割下来的湖草,心里就涌起怜惜之情。仿佛是为了安慰湖草,她把湖草放下的时候,不仅动作轻柔,而且还像绣花一样,把湖草整整齐齐有规律的摆放。当沙洲上的湖草全部倒下时,在妮子割草的地域,可以看见用湖草码成的菱形,或者是五星形,或者像荷花形的图案。
娘抬起身子,用手臂揩掉额头的汗水时,就发现了妮子割倒的湖草。娘心里有些着恼,又有些伤感。着恼的是妮子在耽误时间,因为割湖草不是绣花。伤感的是妮子的举动,让她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她本来想责怪妮子,可是责备的话到了嘴边,最后又咽了回去。
当男人们撑着船儿,要把湖草收回家时,娘暗示男人把妮子割的湖草留到最后。可是妮子割的湖草还是被打成了捆,堆上了船。娘发现妮子的眼角,隐隐有了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