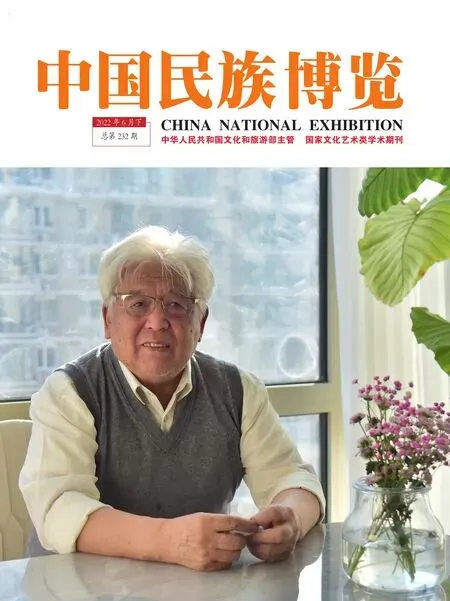现代戏剧传达悲剧性精神体验的三种途径
王东泽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一、悲剧、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戏剧文学在步入工业资本入侵的现代社会之后,呈现出独特的悲剧性审美特质。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到现代具有时期、特征、体验三种意义,本文所探讨的现代戏剧即借用“时期”层面来界定。卡林内斯库划分现代的时期即为“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现代悲剧”就是此种现代定义下的结果,一种作为在人类文明史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出现的戏剧类型,而非局限于仅具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戏剧作品。
悲剧一般内含于戏剧这一整体概念中,但悲剧的概念同样也是难以界定的,事实上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悲剧的争论也仍未停息。对此笔者只对部分观点进行阐释。总体上看定义悲剧有两种途径的尝试,一是文体意义上的悲剧,二是泛审美意义上的悲剧。亚里士多德定义悲剧毫无疑问是文体上的,将其界定为“悲剧是严肃完整的,对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摹仿,通过怜悯恐惧,受众情感得到陶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上符合这种程式并且使受众获得固定的审美体验的文体就是悲剧,包括主体必须受到不可避免的冲突,人性受到伤害,从而引起受众的悲壮怜悯或恐惧,最后精神得到升华。受众在阅读或观看悲剧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效应,感同身受此种结局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尼采独创性地引入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来理解悲剧,认为悲剧源自酒神精神,它破除以代表梦境状态,造型艺术的静态的日神精神的外观幻觉,与本体沟通,最后直视人生悲剧。这本身便与叔本华的哲学不谋而合,即认为人的存在即伴随着痛苦,而悲剧快感便是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它使我们暂时逃脱事态变迁,感到事物基础中的生命坚不可摧并充满快乐。这便是泛审美意义的而非文体意义层面的定义,因为它只规定了受众在审美过程结束后需要获得的心理感受,没有规定具体的文本程式和戏剧主人公必须受到损害并伴有悲剧结局的要求。石娉娉相似地指出存在广义上的悲剧概念。广义的悲剧是泛指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到的不幸、苦难、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性的结局。石娉娉讨论的广义的悲剧已经超越了狭义的悲剧,更接近常说的“悲剧性”,而且这种悲惨性结局不一定是主体被毁灭,且不一定伴随着双方激烈的冲突矛盾与斗争反抗。
沿着这一思路出发,若要对悲剧相关概念进行较为正确的分析,则应一分为二地从文体与审美两种层面进行判断。这样便有助于对“中国有无悲剧”等问题做出回应。首先要先分辨“悲剧”是作为文体还是泛审美范式来讨论。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悲剧,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同样有悲剧,只是中国古代的悲剧作品与西方的悲剧作品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从西方文体意义上的悲剧为模板在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搜寻,后者则是采取类似于石娉娉的广义的悲剧观点来看待此问题。于是单从文体意义上看待,就有了第一种观点。中国古代没有具有古希腊悲剧那种规模和范式的文学作品。而当我们把中国古代那些我们当下称为悲剧的作品纳入西方悲剧美学理论的范畴时,打破西方“悲剧”概念固有的封闭性, 我们就有了第二种观点。朱立元认为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便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悲剧观,其包含着人生价值观和宇宙观等不同的层面,如《诗经》《楚辞》以及《庄子》中,这些文本都有对于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表现出无奈和感伤的悲剧意识,都表达出对人生的终极结果的疑问,对于生死离合从审美角度上进行了把握和描绘。
至于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大抵也是由文体意义延伸到审美意义上来的,只不过两者的主体有所不同。悲剧意识是人的意识,不管悲剧是否发生,悲剧意识都始终存在,贯穿了人类发展始终。悲剧精神则是作为文体的悲剧带给观众或读者精神上的一种震撼,侧重于悲剧发生后,剧中主人公所彰显的一种契合悲剧特质的精神。石娉娉强调悲剧意识是一种忧患意识,“悲剧意识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如影随形的忧患意识,一旦出现了诱因,就会爆发。所以,悲剧意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人生悲剧感的一种体验模式,是一种自觉的痛苦”。她所理解的悲剧意识是一种自觉的同情,这无疑强调了悲剧带给人的精神感受。王富仁从文学的历史进程中阐释悲剧精神与悲剧意识。“在这里,有人类对自我存在的悲剧意识,有贯穿于这个神话故事的悲剧精神……司马迁建立起了自己的悲剧意识,他的悲剧意识并没有导致对人的悲剧精神的否定”。王富仁看待悲剧意识是对于个人,个体而言的,而悲剧精神是对整个人类而言。除此之外,王富仁提出了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在不同文学体裁中的表现,“悲剧意识可以在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强烈表现,悲剧精神则只有在叙事性作品中才能得到真正有力的表现。因为悲剧意识是一种没有长度和阔度的情感,而悲剧精神却必须在一种长度和阔度中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表现。小说和戏剧都是叙事性的作品,也都有可能表现悲剧的意识和悲剧的精神,但西方的悲剧主要是指戏剧中的悲剧,这是因为戏剧比小说更集中、 更单纯。它的悲剧也是更集中、更单纯的悲剧”。作为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虽然脱胎于古希腊悲剧,但在后期发展中定义发生了扩大,强调的是审美体验上的悲剧性,可以表现为悲哀、痛苦、同情。如果泛悲剧化,那么可以体现悲剧精神的体裁不仅限于戏剧,还有小说甚至是诗歌。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的悲剧意识一开始就与宗教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宗教意义上来讲,实际上西方悲剧崇尚的是一种牺牲。似乎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现代主义,西方的美学思想都在关注人本身生存的幻灭感。而中国古代宗教意识相对淡薄,悲剧意识与宗教意识没有直接联系。就结局而言,中西古代悲剧也大相径庭,古希腊悲剧所体现的是主客冲突及惨厉效果,这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比较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大团圆结局。中国古典戏剧往往借助天地神灵的力量来改变人在现实中无法改变的命运,从而表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念。
而当试图论述现代戏剧文学是如何使受众产生近似于古希腊悲剧那种怜悯、恐怖的莫名的悲哀时,会发现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都无法完全恰当地表称这种审美体验。因为这种体验往往结合了个人和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于是笔者使用“悲剧性精神体验”一词来指称美学意义上现代戏剧给予受众在阅读剧本或观看戏剧时产生的强烈的心理精神感受,并将之做以下定义,“悲剧性精神体验表现的是戏剧受众在阅读剧本或观看戏剧时面对自我的生存困境时,对自我人生、命运进行根本思考的一种身体性体验。”这个概念是立足于戏剧受众的立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包含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适合对题目的表达。
二、现代戏剧表达悲剧性精神体验的三种途径
宿命论是作为第一种途径出现的。人企图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最终仍陷入宿命的困局,这便是莫大的悲剧。人对于“命运”的无力往往是悲剧的根源所在,现代戏剧承袭古典戏剧,在对于“命运”的表现上把人在“命运”控制下的脆弱、孤独与渺小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的存在始终挣扎不出宿命。
中国新文学史上有曹禺的《雷雨》。其中“雷雨”作为神秘的第九个角色,始终贯穿全剧,从某种意义上说,造成了最后悲剧的发生。某种程度上的“雷雨”似乎可等同为古希腊戏剧中提到的“命运”。“命运”没有办法出场,但又和其他八个角色紧密关联,甚至一些人物的主要性格的建构就是为了“命运”的到达而服务。《雷雨》可看作对古希腊戏剧的致敬。人无法摆脱命运,如剧中对鲁侍萍的书写。《雷雨》是社会悲剧与命运悲剧的结合,两者组成了“宿命论”悲剧。从鲁侍萍离家那一刻起,第九个角色“雷雨”就已经粉墨登场,“命运”将一切矛盾和巧合拿捏得恰到好处。无独有偶,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在其戏剧创作中也对宿命论颇感兴趣,只不过奥尼尔思想中的宿命和巧合大多是与“海洋”有关。前期现实主义作品《安娜·克里斯蒂》就刻画了一个典型的被命运愚弄的水手长克里斯的形象,一生憎恶大海最终却又回归大海,甚至连女儿安娜的命运也要交付给大海。戏剧结尾表面上是大团圆结局,但深层次上更像是重复上一代人生命的轮回。作为象征因素的“雾”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仿佛告诉读者人生就如同在迷雾中航行,无法主动选择方向。奥尼尔对此种宿命观的书写并非是无意的。相反,这是作家对现代戏剧做出深刻理解之后产生的自然的行为。诚然,奥尼尔对于宿命论的审慎和偏爱也是源于古希腊戏剧,“用独立并且明确区别于我们称之为现实的戏剧的艺术来解释生活,也许能表达那种巨大的力量,而现实只是这种巨大力量的一个苍白无力的象征……简单地说,戏剧应该回复到古希腊戏剧的那种宏伟的精神”。同时奥尼尔在诸多古希腊悲剧诗人中尤其尊崇埃斯库罗斯,正是因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展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涉及诸神在内的一切人的赏罚和神秘的法则。正是欣赏自古希腊悲剧由来已久的命运观主题,加之对现代社会人的存在的深切体认,奥尼尔将宿命论作为自己戏剧创作的重要一环,目的即在于深刻而颇有洞见地展现生活的原貌。
悲剧性的荒诞书写是第二种途径。西方后现代主义戏剧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与阿尔让的《血喷》正是这类的代表。作品论述在后现代主义中人的存在受到质疑,在信仰丧失、语言贬值的大背景下,是现代戏剧表达悲剧精神的新方式。荒诞一方面是工业化模式下看清自身价值后的人的自嘲,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人的反抗理性主义、资本生产结构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戏剧的悲剧精神就等同于荒诞精神。荒诞精神内涵丰富,包含着语言的荒诞、情节的荒诞以及信仰的荒诞。在任何皆可疑的时代中,人不能成为人。在前工业社会,人更多地可以通过将客观本质力量对象化反过来肯定自身,但如今人们找不到可以将之对象化的客观实体,人的存在不再被肯定,人成为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在具有荒诞情节的现代戏剧中,主体的无力感、内容的片面化、形式的丑怪使得人获得悲剧意义上的怜悯与恐惧。在欲望横行的现代工业社会,悲剧在表面上丧失了传统的崇高与严肃,但于实在层面则更能引发“静穆与伟大”的审美体验。
贝克特对于悲剧性精神体验的传达,就是证明了“存在即死亡”的命题。当人身处现实社会却无法对现实说“不”的时候,就是人存在的巨大的悲剧。因为既然这样,为何不去选择死亡?在现代戏剧中,个人存在的死亡有三个方面的呈现。首先是语言的死亡。《等待戈多》中,戈戈和狄狄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企图用语言来填充虚无,结果语言也变得无意义。他们在戏剧开场时毫无逻辑的对话就表明,现代语言存在的意义只是填补无尽的时间,不作为有意义的沟通媒介。如狄狄和戈戈在等待戈多时的对话,似乎只是让对话不再停止,因为一旦停止对话,就会陷入更大的空虚。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对话,就丧失了意义所在。“戈戈:这倒是真的,你能肯定在这里吗?狄狄:什么?戈戈:必须等待。狄狄:他说在树前。你还能看到别的树吗?戈戈:这是什么树?狄狄:看样子是一颗柳树、戈戈:那树叶在哪里呢?狄狄:它可能枯死了。戈戈:浆液都没有了。狄狄:兴许还不到季节。戈戈;:它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灌木。狄狄:一种小灌木。戈戈其次是个人的死亡,但这种死亡与古希腊悲剧的个人死亡截然不同,它不像俄狄浦斯一样是肉体上刺破双眼式的惩罚,也不是精神上的伟大自省、勇担惩处,对抗命运的“自我放逐”,而是“被迫放逐”。贝克特把人放于二战后的工业发展和消费主义把人的生存空间压榨得所剩无几的现代社会,就是要人丧失主动,丧失自我。或者说,人唯一能做到主动可能就是被迫追求无意义。狄狄和戈戈的等待戈多的行为看起来是掌握着主动权的,实际上,这仍然是荒谬的被动等待。他们不认识戈多,不知道戈多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戈多的具体情况,甚至无法主动和他取得联系。他们之间唯一的信息传递全部通过小男孩,而小男孩显然是受戈多的操纵。而且,在戈戈狄狄和小男孩的对话中,小男孩都刻意回避使用描述性话语,而是以“我不知道,先生”或“是的,先生”这样的语言回答,架空了戈多的存在,令狄狄戈戈无法了解戈多,阻碍了主体认识的能动性,造成个人存在的死亡。最后是信仰的死亡。在被普遍异化的现代社会,上帝再也不能以博爱来拯救世人,既然“上帝死了”,那我们便拥抱魔鬼吧。信仰魔鬼的结果就是第三种死亡即信仰死亡。人的精神向低级、虚无和情色靠拢。《等待戈多》中对基督倾覆的描述非常醒目,首先是戈戈和狄狄同戈多,那种像一些评论家一样把戈多看作上帝的象征时的相约,这本身就是基督中神与人定下的契约精神,而结果却是神的缺席和毁约。其次就是拒绝忏悔,当狄狄在犹豫要不要忏悔一下时,戈戈反问“忏悔什么”“为出生而忏悔吗”。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只能继续,因为不需要进行忏悔。
现代戏剧中在消解信仰的强度上,阿尔托显然比贝克特更残酷。他在《血喷》中直接写道:“妓女:放开我!上帝!(她在上帝的手腕上咬了一口。巨大的血柱撕裂了整个舞台,在火光的闪烁中,教士在不停地手画十字进行祈祷。火光还在继续,所有人都死了,他们的尸体和残骸散落各处。只有少男和妓女贪婪地注视着对方,随后妓女跌入少男的怀中)”《血喷》里上帝被一个妓女反抗,甚至被咬出巨大的血柱,神的身份遭受彻底的质疑。上帝的鲜血意味着在如此荒诞异化的社会中,上帝和人一样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被工业碾压过的现代社会,信仰丧失本质主义的神圣光辉,人作为上帝的杰作,本来也应天性美好,善良纯真,但剧中的人物几乎都是肮脏、恶心,猥琐的,如“妓女像一片薄烤饼”“胸部已经干瘪”“肿胀的乳房”。
最后,现代戏剧通过元戏剧来传达悲剧意识,本质就是某种文体通过反对自身来获得悲剧效果,可以看作是文学形式自身的后现代化。可以说,在现代戏剧表达悲剧性精神体验的最后一个途径就是否定戏剧自己。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元戏剧这一形式自身就饱含着十足的悲剧性审美体验。宿命论和荒诞书写这前两种途径都是现代戏剧作为主体施加给人物或情节以悲剧性效果,相比较而言,现代戏剧传达悲剧性精神体验的第三种途径则更富有悲剧意味,它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一切四散后空心的状态达成和解。元戏剧有意暴露自身是戏剧本身,刻意拉远同观众的距离。如戏剧《阳台》第一场里,“伊尔玛:该说的都说完了。等戏演完了……”到第一场结尾“伊尔玛:很美,不过您必须走了。您把车停在路口了,电线塔旁边……(主教很快换上了日常服装,把他的教袍扔到一边)”以及最后一场警察局长对罗杰饰演自己的评价,“演得好,他相信已经被我灵魂附体了”。《阳台》彻底的“戏中戏”结构,在大阳台俱乐部中,人们希望通过演戏切换自己的身份,满足欲求,但“演戏的演戏”只会让观众自觉地从沉浸中脱身而更关注演员的动作和戏剧形式,也更容易引起观众对自身的反思,即反思自己是否也是置身于一种大舞台,为了演戏而生存。由此而来的对于生存的思考便直接地指向现代人的生存命运。可以说,让·热内的元戏剧比元小说更能起到怀疑自身的目的,很容易导致观众自觉地身份叠加,思考自己和台上演员的身份关系,形成看与被看的社会层面上的二元结构。如果说前两种途径是文本受众先在角色的身上发现了悲剧性因素后再引申在自我身上,那么,元戏剧《阳台》则直接让受众在现实层面激荡起悲剧意识,通过台上身份(演员)和台下身份(自身)的瞬间对照,通过“演戏”本身——只需要意识到这种形式,无需了解剧中人物是否有悲惨命运以及结局如何便进行自我反思,无需经历一次思维转换的过程,然后获得一种快乐,这边回归了戏剧最本质的功能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这比前两种途径更为高明。
三、结语
所述综上,现代戏剧在表现悲剧精神上手法是多样的,既有侧重于主题意义,如借用古希腊戏剧沿袭而来的“宿命论”传达悲剧性,也有现代社会的新的表达方式,如从文本内容层面带来悲剧体验的荒诞式写作和从文本形式层面通过反抗自身形式来达到悲剧体验的元戏剧。需要注意的是,悲剧性精神体验也只是众多现代戏剧所传达的阅读体验之一,此外,它也会从一种且从不同角度看,对于“现代戏剧表达悲剧性精神体验的三种途径”这一命题的回答也有不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