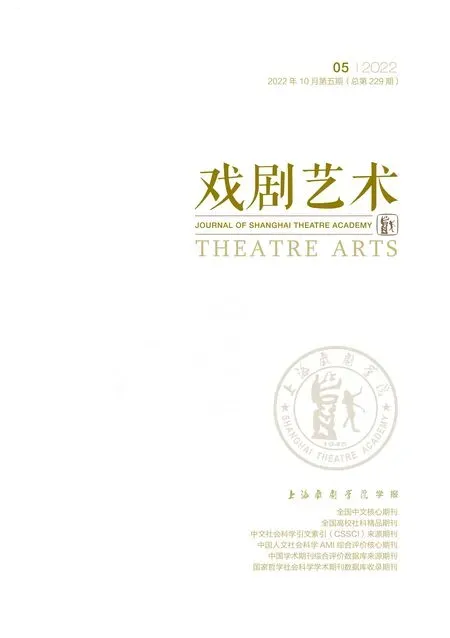田沁鑫戏剧作品中的“疾病书写”与“疗愈”
徐敏杰
疾病是人类非正常的生命状态,现代医学将疾病分为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两种,而在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层面,疾病则具有多重意指性。它“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政治事件,此外,还是一个经济事件”,疾病在此又具有隐喻性,就像癌症等同于死亡、食欲不振、失败;抑郁症等同于压抑、自残、不满或痛苦一样。如何从戏剧角度对疾病进行解读或意义上的升华,就进入了戏剧的“疾病书写”与“疗愈”范畴。从对个体身心的深入挖掘到对社会机制的多维度剖析,戏剧艺术的剧场性使其天然具有“社会公共论坛”性质,其“疾病书写”与“疗愈”范围涵盖了个体、群体、社会乃至国家的不同层面。在田沁鑫的戏剧作品中,“疾病书写”分为生理疾病、心理疾病和社会疾病三个向度,这种多视角、多维度的“疾病书写”在其早期戏剧创作中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和问题表达的一致性。其戏剧作品不仅提出问题,引发观众的思考,而且致力于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对“疾病”进行“疗愈”,“当美学和疗愈的元素彼此相依,再加上观众的见证时,便成为意图当下力量的升华。”本文截取田沁鑫前十年的戏剧创作为标本进行重点剖析和研究(1997—2007),以期在时代背景下探索其戏剧作品中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 田沁鑫戏剧作品中的“疾病书写”
田沁鑫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其戏剧作品往往由她本人兼任编剧、导演两项职责,从第一部作品《断腕》(1997年)至《驿站桃花》(1998年)、《生死场》(1999年)、《狂飙》(2001年)、《赵氏孤儿》(2003年)、《红玫瑰与白玫瑰》(2007年),其前十年的戏剧创作大多从历史题材切入或是名著改编,作品以史为鉴,借助历史题材的厚重和文本内容的深刻性反观当下社会,这种跳出当下对一些重大母题进行思考的思辨意识体现出田沁鑫对人、对民族、对国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以古喻今的人文关怀精神。
(一) 生理疾病书写下的隐喻性
生理疾病是传统病理学上的身体疾病,主要指“生物机体的生命活动和各个器官的功能紊乱、丧失直至生命的消亡等”。在田沁鑫的戏剧作品中,生理疾病的出现往往成为戏剧冲突的高潮点,它既推进剧情发展,又有隐喻性显现其中。《断腕》中,述律平的丈夫阿保机于征战途中暴病身亡,众大臣意欲谋反叛乱,其子却要在辽国游牧式的奴隶制度下推行汉族的“以儒治天下”,国家之乱在母子、群臣就殉葬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时达到高潮,为了保住她与丈夫共同创立的辽国,述律平先发制人,她说:“众位大臣,我会为阿保机的江山而活着,但是,我要用我的手陪伴灵柩,以示忠心。”话音刚落,自剁其手,这种后天形成的“肢体符号”隐喻了述律平生命的不完整(身体残疾、丈夫身亡、儿子远走他乡)。同样的隐喻手法在《驿站桃花》中得到再次运用,剧中汉武帝刘彻和司马迁的友谊在司马迁冒死为李陵求情时走向极端,司马迁一遍遍将刘彻推倒在地,刘彻一遍遍爬起追逐,田沁鑫运用肢体的“失衡—复衡”技术外显出两人摇摇欲坠的友谊,而刘彻在跌倒与爬起的肢体重复中颜面尽失,情急之下大问:“李陵是你何人?”司马迁只回答二字:“朋友。”至此,矛盾冲突达到高潮,刘彻下令对司马迁处以宫刑。宫刑又称腐刑,它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心灵的受辱,对受刑者来说,这种残酷刑法隐喻了权利自上而下的阶级压迫和统治阶层代表的价值评判对其道德层面的责罚,这种压迫和责罚造成了友谊的不对等。
现代医学将死亡定义为“生命活动的终止,也是机体完整性的解体”。至《生死场》和《狂飙》时,死亡成为田沁鑫所要表达的重要母题之一,它告别《断腕》和《驿站桃花》式的借古喻今,故事人物也从古代进入现代,且表现内容都是20世纪发生的真实事件而使其更具现实意义。话剧《生死场》改编自萧红于1931年创作的同名小说,其时代背景正值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人物的死亡在剧中随处可见: 赵三忍受不了增税杀地主却错将小偷杀死,麻婆给日本兵吃食反被日本兵奸杀,日本兵枪杀地主二爷,赵三摔死其闺女金枝的孩子,日本兵枪杀金枝及村民,人物的死亡变得无足轻重,它隐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国人生命的低贱、脆弱和不可控。死亡的隐喻意义在《狂飙》一剧中具有相同性质的体现: 田汉的妻子渝英年早逝,田汉在日本看戏时见到喜爱的女演员在台上为情剖腹自杀,莎乐美为了得到心爱之人的吻而不惜将爱人的头颅砍下,“戏中戏”将台上台下的死亡串联在一起,死亡的隐喻性成了田汉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一种极致追求,他将“五四”时期这种新浪漫主义推向极致和纯粹,而这种极致和纯粹也是田沁鑫的戏剧追求,二者的艺术驱动力由此达到了内在统一。2003年,田沁鑫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死亡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原驱动力贯穿戏剧始终: 赵朔杀死与庄姬通奸的赵缨,赵朔被迫谋反杀死晋灵公,屠岸贾杀害赵氏孤儿全家300余口,庄姬抽刀自刎,程婴因承诺赵家而将自己的儿子替死,程婴之妻自尽,韩厥和公孙杵臼为程婴义举感动而赴死,程婴和屠岸贾气绝身亡,剧中人物的死亡隐喻了权利的争夺和压迫,以及人物在面对压迫时的自我反抗。《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舞台上同时出现两个佟振保、两个红玫瑰和两个白玫瑰,故事结尾,佟振保和白玫瑰分别将另外一个自己捂死,红玫瑰也“埋葬”了过去的自己,“死亡”在此隐喻了主人公的外部肉体和内心情感在面对现实社会生活时由抗争走向妥协,由分裂走向统一。
(二) 心理疾病书写下的深层意指
心理疾病主要指精神疾病,它不同于肉眼可见的生理病变,而是“在体外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感知、情感、注意、记忆、行为、意识和智能等精神活动的异常,例如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热等”。田沁鑫运用蒙太奇手法(也称平行空间)在《断腕》的舞台上创造两个时空——臆想时空和现实时空,述律平在臆想时空中与阿保机展翅共舞,在现实时空中失去手腕,孤零零地坐在地上回忆着过去,此手法的重复运用外化了述律平的心理疾病——相思病。相思病是中国古代医生对精神性疾病的一种描述,常见种类以纯粹的单恋和自作多情居多,病症导致思想和行为的癫狂、抑郁乃至幻想等,严重者可以致命,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因对梦中出现的书生柳梦梅一见倾心,梦醒后茶饭不思、伤情而死,此亦为相思病所致。该病症具有深层意指性,它不仅是剧中人物的“心病”,更是田沁鑫自己失恋心结的外化,诚如田沁鑫所言,“《断腕》是我第一个戏,是我为了感情所做的”,戏上演了,等待的人却没来,戏里的述律平和戏外的田沁鑫产生了共情链接,心理疾病由此发生了重合。至《驿站桃花》时,田沁鑫已从个人情感走出,其心理诉求转向关于友谊、占有、自我、距离等社会问题的探讨。常年“皇宫牢笼”生活形成了汉武帝刘彻孤绝的人物性格,当他遇到司马迁这样一位追逐自由、放浪形骸于外的人时,其内心情感有了映射和寄托,他将全部友情寄托于司马迁,这种对内心喜爱事物的珍惜于刘彻而言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即只允许自己独占,不允许他人触碰,而占有欲一旦过头,就会触发新的病症: 强迫症。司马迁不堪刘彻的“强迫式友谊”,刘彻也不能忍受司马迁其他友谊的存在,这个历史故事“把现代人的孤绝心理集中在一个帝王身上展示,将自然情怀、宽容散淡集中在文人司马迁身上,两人的融合、崩溃、纠葛正寓示了现代人的种种矛盾、复杂的心理”,它意指现代都市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强迫性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带来友情或爱情的缺失。
至《生死场》时,戏剧焦点转向国民自卑性心理病症的探讨上,剧中的赵三和二里半是此种病症的典型代表,首先在地主二爷面前,两人是自卑的,其次是二里半的儿子让赵三闺女未婚先孕遭到全村人戳点,尤其是二里半,他的身体姿态总是躬背、哈腰、低头,这是自卑症伴随下的自信心不足,其心理上总觉得比别人矮一截,当其婆子被日本兵奸杀后,村里人对其唯恐避之不及的嫌弃态度加剧了二里半的自卑心理,此病症根源意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国民所受的阶级压迫和长期挤压下形成的畸形国民心理。同样的意指手法也体现在《狂飙》一剧中,田汉兼具浪漫主义气质和革命精神,如同他所创作的大量抑郁男性形象一样,这种抑郁气质也体现在田汉与其历任妻子身上:
渝: 林,喜欢看戏么?
林: 不喜欢,你呢?
渝: 寿昌喜欢,我就喜欢了。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田汉的两任妻子虽不喜欢看戏,却都不表露出来,田汉与林为纪念渝的病逝而结婚,但这段感情只维系两年便终结,田汉的第三任妻子维中也没办法与他产生情感共鸣,剧中一段对话揭示出两人间的隔阖:
寿昌: 维中,喜欢莎乐美吗?
维中: 我喜欢娜拉。寿昌,我给你买了件长衫。
寿昌: ……
维中: 喝口龙井吧。
寿昌: 不……
维中: 那,你跟我说会话吧。
寿昌: ……我有点累了,早点歇着吧。
彼此情感和思想的交流错位外化了主人公的心理疾病——抑郁性精神障碍,这与病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有关。田汉一生为戏疯狂,有一种痴迷和欲望的情感寄托在里面,他是理想主义诗人,其三任妻子却是现实主义女人,这种抑郁性精神障碍意指两个层面: 一是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二是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与彼此产生情感共鸣的知音。《赵氏孤儿》一剧中的主人公也患有此种病症,赵氏孤儿全家被杀却不自知,造化弄人,其父亲不是亲生父亲,其义父是杀其全家的凶手,小小的身躯承受不了如此的血海深仇,从16岁那年知道真相起,他便生活在巨大的痛苦、悲伤、挣扎和压抑中,孤儿的抑郁性精神障碍一下子被推至顶峰,然而有此病症的不止赵氏孤儿一人,几乎所有与他相关联的人物均是如此。首先是其义父屠岸贾,他与赵家有权利争夺,借“庄姬事件”灭赵家满门,而他却因战场之伤不能生育误将赵氏孤儿认作义子,多疑、嗜杀的性格下含混着孤寂与压抑。其次是将军韩厥和老丞相公孙杵臼,他们空有报国之志,然朝野混乱、报国无门。第三是庄姬和程婴之妻,庄姬的乱伦行为招致其情人和父王被杀,赵家满门抄斩,她的抑郁性心理因负罪感和保护不了自己孩子的无助感交互作用产生,后一点与程婴之妻无力护住自己儿子所产生的抑郁与绝望心理相同。第四是孤儿的养父程婴,他是所有人物中承受抑郁性心理最严重的一个,只因他诚信赵家,自己的儿子替死、妻子自尽、韩厥和公孙杵臼为之舍生取义……,身为一介草民,他背负晋国上下十几年“不义小人”之骂名,内心万般思绪却有口难言,压抑、孤绝的心理化作悲伤的形体,由内而外蔓延至整个舞台,然而悲伤的情绪和身体表现并不流于萎靡,因为他做的乃是诚信、忠义之事,其深层意指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核心——大义与大爱,这在演员悲伤却有骨力的身体语言中得到充分显现。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感知、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精神活动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病”。《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主人公均患此病症,他们每一个人都分裂出另外一个自己: 一个是世俗眼中的佟振保,一个是受困于内心欲望和声音的佟振保;一个是遵循三从四德的白玫瑰,一个是冲出家庭束缚寻求身心补偿的白玫瑰;一个是敢于追求爱情的红玫瑰,一个是只有在受伤后才会出现的理智红玫瑰。舞台中央的玻璃通道将舞台分成左右两个区域,一边住着白玫瑰,一边住着红玫瑰,这样的舞台布景具有隐喻和象征意味,“那宛如男人的心脏: 左心房和右心房,一个装情人,一个搁老婆;玻璃走廊是阴茎或者是阴道”,双重的人物设定和左右舞台布局构成了剧中人物内心分裂的外化。十年前,佟振保因为欲望选择了红玫瑰王娇蕊,当王娇蕊说她爱上了佟振保决定转嫁给他时,佟振保犹豫和退缩了,分裂型人格障碍在此显露出来,世俗眼中的佟振保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名声”和“妈妈的眼泪”,他对王娇蕊说:“你要是爱我,就要替我着想。王士洪毕竟是我的老同学。”奥尼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外部生活在别人的面具的缠绕下孤寂地渡过了;一个人的内部生活在自己的面具的追逐下孤寂地渡过了”,身心“分裂”的佟振保开始在外嫖妓寻求身体宣泄,回到家与白玫瑰则是零交流,发展到最后是要么不回家,一回家就摔东西、打老婆,就像他自己所说:“因为我空虚,我压抑。”张爱玲在其小说开篇便将故事的结局告诉大家:“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佟振保一直不知道,爱情和欲望是分不开的,一边是得不到满足的内心渴望,一边是家庭的责任和负担,在理智与现实,肉体与欲望的分裂中,这个男人失去了爱情。白玫瑰孟烟鹂也生活在分裂中,佟振保不爱白玫瑰,所以白玫瑰怎么做都是错的。在佟振保眼中,白玫瑰总是“人笨事皆难”,在小裁缝眼中,白玫瑰则是:“佟太太,您真年轻、真聪明、真漂亮,像您这么端庄的女人,我见的真少。”孟烟鹂在小裁缝身上得到了身心的尊重和爱,这在其丈夫佟振保那里是缺失的,但这也导致了她内心的分裂,两个白玫瑰互相扇着耳光:
孟烟鹂: 你就是个废物,振保都不爱你。
烟鹂乙: 振保为什么不爱我,我日复一日的守着振保,守着这个家,我非常努力的讨他喜欢。
孟烟鹂: 你越努力越紧张,越紧张越做不好。振保都去嫖妓了。
烟鹂乙: 你看见了?这与我无关。我再笨也是他老婆,是他老婆,是他老婆……
分裂的两个白玫瑰互相嫌弃,一个勇敢的追求“悦己者”,另一个却告诉自己不能再想丈夫以外的男人。红玫瑰王娇蕊的精神分裂是在她与佟振保分离时才表现出来,理智的红玫瑰告诉她:“你从来都不注意我的存在。你恋爱了,你痛苦了,分裂了,才看见我。”正如田沁鑫所说:“她一痛苦,就分裂成两个人,因为她知道爱了。”主人公的精神分裂症在此意指人们爱情的“缺失”和“不完整”,它即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
(三) 社会疾病书写下的隐喻性
在田沁鑫的戏剧作品中,社会疾病分化出“国家之病”和“国民之病”两种,它是隐喻性疾病的一大子题。《驿站桃花》的故事虽取材于西汉,但呈现出的内容却处处显现着现代国民的种种心理病症,剧中刘彻对于友谊的缺失隐喻了当今快节奏都市生活下人们内心情感的焦灼、封闭、孤独以及冷漠。《生死场》中,田沁鑫深入探讨了“国家之病”和“国民之病”,其病因皆与生死有关。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人民开始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这使“国家之病”日益加深,而“国民之病”则体现在人们的小农思想和对生老病死的集体麻木与冷漠上,当麻婆被日本兵强奸并刺死时,其丈夫二里半愣住了,他不敢反抗,一肚子窝火无处释放,最后只能对着死去的婆子狠狠打了一巴掌,村里人对他不仅没有同情,还化作一句句:“二里半,躲我远点!晦气!说屈你了?俩人弄死的,不是她招的咋的?”……冷漠、麻木的生存状态造就了那个年代的人们“乱七八糟的生,乱七八糟的死了”。“国民之病”还体现在赵三杀地主未成跪地求饶且对地主言听计从,村民得知赵三被地主赎回关心的不是当下赵三老婆之死,而是称赞地主多有钱,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利规训和自下而上的权力谄媚形成的“道德体系”和“权力体系”成为“国民之病”的根源所在,就像米歇尔·福柯所说:“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回溯千年,《赵氏孤儿》借古代晋国之事隐喻当今社会之疾,它融入了田沁鑫对当下社会的忧思,借戏剧之口呼唤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回归,如作者所言:“我做戏,因为我悲伤。悲伤于现今社会的混乱,私欲的弥漫,道德底线的几近崩溃,思想的覆灭,礼节的丢失。”至《红玫瑰与白玫瑰》时,故事的述说内容虽然是“张爱玲时代”都市男女面对爱情时的抉择,但时隔百年,它依然传达出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诉求,这是田沁鑫对于人性的深入思考和挖掘,隐喻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真爱的缺失和抉择间的失衡。
二、 田沁鑫戏剧作品中的“疗愈”
“医生”一词是指“掌握医药知识、以治病为业的人”。在田沁鑫的戏剧作品中,“医生”和“患者”的身份则是互为转化的,这种“医患”身份涵盖了剧中人物和田沁鑫本人,“疗愈”范围也扩展至三个维度: 一是戏剧人物的“疗愈”;二是导演视角下的“疗愈”;三是戏剧上演对观众产生的“疗愈”。
(一) 以“情”化“疾”
《断腕》中的疾病“疗愈”分戏里戏外两个维度,第一维度是戏里的述律平以断腕之举保全辽国统一,自我“疗愈”则发生在其孙子率兵攻打辽国之时,当时的述律平将辽国拱手相让,其目的有二: 一是她从其孙子身上看到了当年阿保机的影子,情感有了寄托,相思病获得了补偿,心结也开始释然;二是她不愿再看到辽国战乱分裂,将辽国交给孙子,也是她与阿保机爱情的另一种延续;第二维度是戏外的田沁鑫通过剧目上演得以情感宣泄和实现自我“疗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田沁鑫戏剧作品的最后点题: 导演为情做戏,述律平为情让位。戏里戏外,情感成为连接两位女性的纽带,这个情感也在观众群体中产生振荡,成为对疾病最好的“疗愈”。至《驿站桃花》时,被处以宫刑的司马迁没有就此沉沦,而是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创造力,他客观且公允地记录了汉武帝刘彻的丰功伟绩和行为过失,而刘彻在失去一生中的挚友后也悔不当初,他大声疾呼:“没有人理我,孤家寡人!司马,我一生中唯一的朋友!我把你丢了!丢了!”刘彻在寻求“疗愈”之法,也就是求得司马迁的谅解。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暮年之时,二人再次相逢于驿站桃花之下,恍惚中,他似乎得到了司马迁的谅解,这是疾病的最终“疗愈”,即唯有谅解和宽容才是友情最好的延续。故事结尾,帷幕从舞台上方缓缓降落将两人盖住,犹如两座坟冢,呈现出诗的写意和象征意味,它是多年后都归于尘土,是多年后的相互谅解,亦是多年后内心与自我的和解。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田沁鑫从“医者”角度触及现实生活,诠释了一出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她将问题抛给观众,是否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笼子里?是戴着面具的好人还是世俗眼中的好名声?扼杀自己的本性和欲望是对还是错?所有问题的最终归宿都回到对人性的探讨上,正如她本人所言:“我们想要展现给观众的也就是张爱玲作品中,平凡大众中的一人,他的情欲、爱情、生活压力,以及伴随他一生的家庭。”佟振保最终选择重新做个好人,白玫瑰对裁缝说:“你还是走吧,裁缝先生,我是这家里的主妇。”是理性战胜了欲望,还是理想屈从于现实?这里面有田沁鑫现实生活的映射,她学生时代有一个谈了四年的男友,性格上的摩擦使她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之时选择了停止,选择了另外一个走进她心里的人:“我挺痛苦,挺矛盾的。一面是社会价值观,一面是自我意识。想了想,觉得社会评价于我没太大关系,就选择了我认为的那场纯粹的感情。”田沁鑫说她喜欢红玫瑰,因为她哭过以后依旧往前闯,在闯的过程中遇到了对的人,受伤的心得到了“疗愈”,这正是田沁鑫带给我们的思考和给出的“疗愈”方案: 花有“情”才香。
(二) 向“死”而“生”
《生死场》于千禧年之际上演,它的上演既是一次警醒,也是一次回望,警醒于中国人民曾经遭受惨绝人寰的侵略和凌辱,回望于中国人民在面对生死时所展现出的顽强与坚韧。最后一幕村民的集体赴死(抗争),真实再现了早期东北民众在没有组织情况下的集体自发行为,它是民族的觉醒,象征了“国家之病”和“国民之病”进入自发“疗愈”阶段,从此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不当亡国奴!誓死抗争到底!”的吼声。田沁鑫不仅从女性视角触及那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女性的命运,更从“医者”视角触及国家生死和民族存亡的母题,尤其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直接传达出原著小说展示的中国农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生死场〉序》),故事对当今人们逐渐忘却和不愿提及的死,以及人们逐渐忽视和麻木了的生具有同样震撼和促人深省的精神效力,回望历史,百年沧桑,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和民族自省意识仍力透纸背,警醒深远。《狂飙》一剧中,安的出现给田汉抑郁性心理病症带来强烈的精神慰藉,她就是田汉苦苦寻找的“红色莎乐美”,然而安的回答却是:“莎乐美在战斗中,你要的颜色会随着中国革命红的耀眼!”从此,田汉的戏剧创作从纯粹的浪漫主义转向唤醒民众意识觉醒的现实主义,某种意义上,安就是田汉的“药”,“红色莎乐美”隐喻的狂飙与突进运动亦是当时中国所需的“药”,就像田汉在剧中的一段独白:“我写了《一致》这出戏,为了向统治阶级、压迫者和所谓的绅士开战!”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田汉身上那种为民请愿、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一直感动和激励着我们。拨开层层包裹,从《赵氏孤儿》的权力与阴谋、欲望与爱情、挣扎与杀戮等多重脉络中,我们看到了主人公的忠信、诚义、善良和隐忍,尤其是主人公面对死亡时体现出的大义与大爱,它是田沁鑫戏剧作品的最终立足点,作为“医者”,她从人性和道德角度出发“疗愈”人们的思想,通过主人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所呈现出的精神内里呼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这使其戏剧作品具有普世的社会现实意义。
结语
将戏剧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从田沁鑫起,对她创作产生影响的阿尔托便是其中之一。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她的“十年”戏剧创作既有残酷戏剧的表现形式,又有隐喻和意指性显现其中,从最初为情做戏的《断腕》到唤醒宽容之心的《驿站桃花》;从警醒国民的《生死场》到《狂飙》中的红色莎乐美;从呼唤仁义礼智信的《赵氏孤儿》到爱情探讨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其作品中的“疾病书写”与“疗愈”范围小至个体的七情六欲,大至国家的生死存亡,它超越了医学表征,饱含着田沁鑫对当下生活的真切思考和人文关怀。这些作品借助戏剧的宣泄与启迪功能赋予当下人们走出心灵困境的契机,由此在当代社会中产生持续的激荡和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