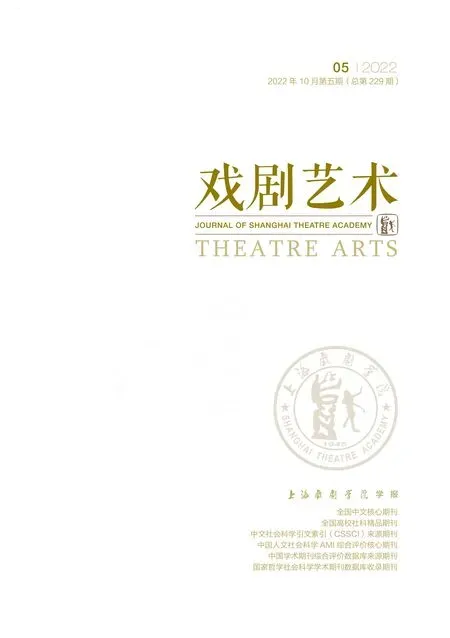论方旭对老舍小说的戏剧改编
——老舍作品的另一种舞台面貌
郭晨子
1951年《龙须沟》首演,1957年《骆驼祥子》搬上舞台(改编自老舍同名小说,编导梅阡),1958年《茶馆》亮相,毫无疑问,“老舍的话剧创作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以《茶馆》为代表,老舍把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话剧创作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中国话剧赢得了世界性声誉;而《龙须沟》《茶馆》等剧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艺术风格,又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在老舍作品“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的同时,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也定义了老舍作品的基本舞台面貌和美学格调。“现今学术界认可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就是建立在以焦菊隐为核心的艺术家群体艺术创造的基础上”,而“焦菊隐的导演创造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诗意的美学建构。他的理论框架和演剧体系是在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民族化这两大理论问题的思考与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得以确立的”。毋庸赘述,斯坦尼体系的现实主义和话剧民族化的自觉追求构筑了《龙须沟》和《茶馆》的舞台成就,然而,“老舍是多产作家,一生共写了一千多篇(部)作品,约七八百万字。”对照他的创作年表,《骆驼祥子》《龙须沟》和《茶馆》固然是他成熟的巅峰之作,却未必代表他作品的全貌和全部价值。在将老舍更多的小说,特别是他早期的喜剧小说搬演上戏剧舞台时,该如何传递文学原作的风格与特质呢?
2011到2019年,作为编剧之一、导演和演员,方旭先后改编上演了老舍小说《我这一辈子》、《猫城记》、《老李对爱的幻象》(改编自《离婚》)、《二马》、《老舍赶集》(改编自老舍四篇短篇小说与两篇散文)和《牛天赐》(改编自《牛天赐传》),在舞台上呈现出不同面向的、尤其对戏剧界而言些许陌生的老舍作品。这六部戏打破了北京人艺演剧体系对于老舍作品的垂范,无论对研究当下的改编策略,还是对戏剧从业者更深入地研究和体味老舍,都是极具价值的。本文将在梳理老舍小说创作的基础上,分析老舍小说的喜剧内核及其在舞台上的转换,聚焦于方旭导演的舞台手段,对剧场化的改编一探究竟。
从小说改编戏剧的角度来看,《骆驼祥子》在话剧改编之后,又被改编为京剧(1998年)、曲剧和歌剧(同为2014年)。世纪之交,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演了《正红旗下》(编剧李龙云、导演查丽芳),2005年和2006年,北京人艺先后出品了《开市大吉》(编剧何冀平、导演顾威)和《我这一辈子》(编剧、导演李六乙),2011年,国家话剧院演出《四世同堂》(编剧田沁鑫、安莹,导演田沁鑫)。除短篇小说《开市大吉》之外,考察上述小说的写作和发表时间——《骆驼祥子》连载于1936年,《四世同堂》完成于1944年到1950年,《我这一辈子》出版于1947年,《正红旗下》(未完成)写作于1961和1962年——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面貌与老舍本人的戏剧创作《龙须沟》《茶馆》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如对弱者的关爱和同情,对黑暗势力的谴责,外敌入侵时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连同其现实主义的手法和主旨,皆是属于“人民艺术家”的。但老舍进入旺盛的创作期肇始自《骆驼祥子》问世之前的十年,《老张的哲学》(1926年)、《赵子曰》(1927年)、《二马》(1929年)、《小坡的生日》(1931年)、《猫城记》(1932年)、《离婚》(1933年)、《牛天赐传》(1934年),以及1934年到1936年的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构成了他作品的另一系列,构成了“另一重”的老舍。这一系列作品曾长时间受到遮蔽,在方旭的改编之前,更没有受到戏剧舞台的垂青,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文体的要求——戏剧体戏剧。作为舶来品的话剧自1907年进入中国以来,占据主流的始终是亚里士多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脉络的“戏剧体”(Drama)文体。以“摹仿说”和“行动说”为基石,戏剧被定义为“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并且“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行动”的整一性决定了情节的整一性,人物的意志和激情构成行动的、也是情节的动力。因此,当小说改编为戏剧时,在戏剧体(Drama)文体的范畴内,意味着要将小说的叙述转化为戏剧的行动。问题在于,老舍的创作,是否以行动性/情节性见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他的小说来看,《小坡的生日》结束在梦境的醒来,似有头无尾;随后的《大明湖》在“一·二八”战火中付之一炬,他仅从中抽取片段后来写成了《月牙儿》,意图在以“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牛天赐传》的情节多半在小说的后三分之一处急转直下,往往是奔向结尾的不得已的仓促手段,况且,猫城遭侵略而覆灭,牛家因革命暴动而破产,所借皆外力,《老张的哲学》中阻止恶行的孙守备、《赵子曰》中推动赵子曰改变的李景纯、《离婚》中让老李下定决心离开京城机关的丁二爷,都是外人。外力和外人的作用,如同古希腊戏剧中的机械降神,可见,情节在本质上并不构成老舍小说叙述的动力,甚至是其短板。而在他的戏剧创作中,他表示,“我以为剧本就是长篇对话,只要有的说便说下去,而且在说话之中,我要带手儿表现人物的心理。这是小说的办法,而我并不知道小说与戏剧的分别。”“听说戏剧中须有动作,我根本不懂动作是何物。”“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而舞台上需要的是‘打架’。我能创造性格,而老忘了‘打架’。”老舍在检讨自己的剧本缺乏戏剧技巧时,仍然坚持“过重技巧则文字容易枯窘,把文字视为故事发展的支持物,如砌墙之砖,都平平正正,而无独立之美。我不愿摹仿别人,而失去自己的长处。而且,过重技巧,也足使效果纷来,而并不深刻”。在多篇关于戏剧的创作谈中,老舍反复讲到,他是用写小说的方式创作戏剧,他能够抓住的是人物和语言。事实上,老舍剧作的代表作《龙须沟》和《茶馆》都是群像式的描摹,作者自称,前者“不一定有个故事,写一些印象就行”,后者“人物多,年代长,不易找到个中心故事”。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情节都并非老舍作品的魅力所在,从他的小说中确立和厘清动作性无疑是困难的,或者说,以戏剧的行动法则来结构老舍的作品,反而会丢掉其最可宝贵的特质。是以,单纯的戏剧体(Drama)文体,是难以应对也并不适合老舍的小说改编的。
其二,时代的要求——正剧。狄德罗提出了正剧的概念,即一种介于悲剧与喜剧之间的“严肃喜剧”或“市民悲剧”。由于种种原因,正剧始终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占据主流。《茶馆》之外的老舍本人的大量戏剧创作,也都属于正剧的范畴,如《女店员》《红大院》《青年突击队》等等。“另一系列”的老舍小说则是喜剧的,并且极有可能是黑暗喜剧或至少带有黑暗喜剧的因子。如带有幻想外壳的《猫城记》,以猫城譬喻古老的中国并以猫城的灭亡为结局,用种种夸张的手法讽刺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对社会现实和国民性的批判毫不留情。以至于1951年出版《老舍选集》时,他在自序中写道,“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感冲淡了正义感”。他明确表示,《猫城记》“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在正剧的统领/统摄下,“幽默感”与“正义感”是冲突的。正剧竖立和巩固权威,以宏大叙事理所当然地消融个体的存在,以近乎无条件的信仰取代怀疑,而喜剧思维的特征则是“怀疑论的哲学态度”“狂欢式的思维定势”和“超越感的心理机制”。喜剧具有消解正剧秩序的能量,当戏剧服从国家叙事的需要时,《猫城记》式的喜剧的笑声难免会刺耳。评价老舍的小说创作,王德威论述,“说老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写实小说家当然不算错,但是我们往往因此忽略了他的喜剧天才,使他成为鲁迅以次,所谓‘正统’写实主义的最佳临摹者之一罢了。事实上,笔者以为真正使老舍突出于其他‘五四’小说家之上的,并不在于他对社会百病模拟式的揭发,倒在于他能‘苦中作乐’,将并不好笑的故事点染成喜剧/闹剧的叙述”,直至他自身“对这种笑声所暗示的颠覆内涵颇为不安”。正剧的殿堂岂能容忍喜剧的捉弄,更不允许喜剧的颠覆。
戏剧体(Drama)文体与正剧是一体的,文体的突破和喜剧精神的张扬都难以一蹴而就,这是改编老舍早期喜剧小说的难度所在,方旭一系列老舍改编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松动的,首先是戏剧体(Drama)文体。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度兴起“布莱希特热”,尽管布莱希特对陌生化效果的阐释中误读了中国戏曲,但中国戏曲中的确存在的“叙述”成分又是和叙述体戏剧的手段一致的,“叙述”在中国话剧中的出现,不仅是对布氏体系的实践,也包含着对民族戏曲演剧方式的借鉴。
2010年,方旭开始筹备独角戏《我这一辈子》的创排,同年,王翔编剧、林兆华导演的《老舍五则》首演。次年,《我这一辈子》首演,稍后方旭接受邀请参加《老舍五则》的演出,这两部改编自老舍小说的戏剧一改之前的“北京人艺演剧体系”的老舍作品面貌,突出地表现在叙述体的建立。
在方旭的戏剧经历中,2010年和史可合作演出的《收信快乐》启发了他做独角戏的念头。《收信快乐》完全依赖两名演员朗读写给彼此的信件刻画出长达四十年的人生经历,是一出借助书信为载体完成的叙述体的戏剧,而以第一人称写就的《我这一辈子》在方旭的解读中,“就是一个老警察的个人独白”,可以说,“独白剧”是叙述体戏剧的极致方式。第一人称写就的小说转换为舞台上的独白,极大地发挥了老舍的语言魅力,带来了时间跨度和时空转换的自由,同时让方旭发现,观众非常接受这种演绎小说的方式。
同样,在方旭参演的《老舍五则》中,老舍创作于1934年和1935年的五篇短篇小说《柳家大院》《也是三角》《断魂枪》《上任》和《兔》被搬上舞台,或安排叙述人,或借鉴中国戏曲的自报家门,“叙述”在场。
此处要厘清的,不是“叙述”和“动作”的定义,而是两个概念的纠缠。西方戏剧的范畴中,亚里士多德正是摒弃了“叙述”而以“动作”定义了戏剧,戏剧体(Drama)文体范畴下的小说改编戏剧中,“改编”要完成的恰恰是将小说的“叙述”改为戏剧的“动作”;而布莱希特的出现,以重拾“叙述”创造了不同于亚氏的戏剧体系,“叙述”也是现当代戏剧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于原创,“叙述”直接关乎创作者对演出样式的确定和戏剧结构的选择,而对小说改编戏剧而言,“叙述”则是把双刃剑,戏剧舞台上的“叙述”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读小说”,而是要将小说叙述转化为剧场语汇的叙述。老舍自称的在舞台上“用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还是在戏剧体(Drama)文体的范畴中,和建立叙述体文体不能等而视之。
在独白剧的尝试之后,方旭的老舍小说改编中,主要运用了两种方式“叙述”,一是增加歌队,一是在增加歌队的基础上,由扮演者同时担任自身的叙述者,与此相关的,是一人分饰多角的剧场化手段。
“歌队作为一种特殊戏剧人物,首先带来的是对一出戏的美学定位。比如布莱希特,非常明确地界定其歌队,是要使其戏剧获得一种叙事剧的体裁。以歌队和其他手段建立幻觉主义舞台场面之后,布氏宣布,舞台上不是再现真实地生活,而是在讲述真实的生活。”歌队的运用直接确立体裁感,具体地看,《猫城记》的首尾,扮演小说人物/剧中角色的演员扮作盲人,两位盲人为决定走什么道路而争执不休,乍一看,令人联想起《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喋喋不休的话语堆砌了毫无意义。结尾时两位盲人再度出场,再度重复开场时的台词,形成了一个死循环。眼盲而争论道路的方向,他们具象化也隐喻化了小说中所概括的,猫人的最大特点是“糊涂”。这两个人物是小说中所没有的,与剧情亦没有关联,他们如同两位说书人,是角色所分身出来的歌队。《二马》的开场,一组英国绅士在读报,借由他们,交代出小说中描写的英国人对黄皮肤们的偏见,铺设了主要人物出场的背景,在实际作用上,近乎歌队的议论。《老李对爱的幻想》中出现了现场乐队,一人演奏笛或箫,另一人拉胡琴,两人不仅和演员搭话,场次转换之间也交代暗场戏的情节发展,以乐队的方式完成了歌队的任务。《老舍赶集》索性以老舍的两篇小品文作了开场和结束,开场时的《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类似于戏曲中的“副末开场”,直接和观众建立交流,结束时的集体朗诵《我的理想生活》如同老舍先生的直接倾诉。
到了《牛天赐》,方旭称在剧本改编阶段遇到了难题,“改编中非常犯难的一点是,老舍先生的作品经常喜欢夹叙夹议,往往议的部分比叙的部分好看,但议的部分又很难从剧中人物的嘴里说出来。情急之下,我就把牛天赐家门口的门墩儿激活了”。在他的直觉中,“议”比“叙”好看,也就是说,相对于牛天赐及牛家所经历的所有事件,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事件更加直抵作品的内核,转换到戏剧舞台上,意味着主人公和歌队缺一不可。如何在《牛天赐》中创造出歌队呢?方旭将牛家的门墩化为一个人物,既有机地融入剧情,又实现了歌队中歌队长的功能——与主人公牛天赐对话。
或分身有术,或增加角色,或将乐队纳入演出的有机整体,开场确立的叙述体戏剧的样式和观众建立了契约,这是非幻觉主义的、非戏剧体(Drama)文体的演出。随之而来的,是在表演过程中,扮演者在扮演角色之外也担任自身的叙述者。《老李对爱的幻想》中,老李的苦闷是独白式的,是直抒胸臆的叙述,而他所经历的场面,如小赵为出老李太太的丑而组织的饭局,也完全依赖“叙述”而并不“表演”出来。《牛天赐》中,为了让主人公的自我叙述更加成立,从襁褓中的弃婴,到童年、少年时代的牛天赐,都由扮演牛天赐的演员和体量由小变大的木偶同台演出。扮演牛天赐的演员,在扮演不同阶段的牛天赐的同时,间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视角打量和评价牛天赐,随时跳进跳出。偶的使用,既是剧场语汇之一种,又合理化了牛天赐的叙述者身份。
叙述体的建立决定了舞台美术的风格,《猫城记》中叠放的纸盒子,《二马》中垂吊的各式帽子,《老李对爱的幻想》和《老舍赶集》中变形的屏风,《牛天赐》里作为背景的夸大变形的人偶轮廓,都在消弭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属于当代戏剧的符号系统。
独角戏《我这一辈子》是方旭改编老舍小说的起点,之后的五部作品皆是喜剧。如前文所述,以《龙须沟》《茶馆》为其剧作代表作,以《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标志其小说创作成就,作为“幽默作家”的老舍之前并未登上舞台。对老舍的幽默,一度评价不高,认为有两重性,一重是过于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说得严重一点,有点类似北京‘京油子’的‘耍贫嘴’)”,另一重以《离婚》为分水岭,认为老舍就此找到了幽默的健康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意味,谑而不虐”,并且“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离婚》的文学成就毋庸置疑,也是老舍本人最为满意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离婚》之后,他进入了《骆驼祥子》和《月牙儿》的写作,他的“幽默”已告一段落,而《离婚》之前,被方旭搬上舞台的《二马》《猫城记》和没有搬上舞台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以及他转向长篇写实小说《骆驼祥子》前的最后一部喜剧小说《牛天赐传》,是否过于“耍贫嘴”了呢?不同于上述常见的两分法,王德威非但肯定老舍的早期喜剧小说成就,而且认为以“讽刺喜剧”论及还稍嫌温和,索性称老舍想要制造的是闹剧,而闹剧决不等于低下。“作为一种叙述形式而言,‘闹剧’指的是一种写作形态,这一形态专门揶揄倾覆各种形式和主题上的成规,攻击预设的价值,也以夸张放肆的喜剧行动来考验观众的感受。它通常强调一连串嘉年华式狂欢的事件,其中身体的动作(相撞、滥骂、揶揄、容貌丑化等等)暂时压过了理智和情绪的控制。闹剧行动的‘主使者’是小丑。他们或以可笑的被害者姿态出现,或以喜剧的攻击者姿态出现,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经过丑角激越的行为,闹剧也暗示了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意识形态,如巴赫金(Bakhtin)所称,是以‘堕落’的方式在想象中‘瓦解’既存的秩序。”如王德威所言,巴赫金的闹剧定义未必“尽然适用于”老舍喜剧小说,那么,“嘉年华式狂欢的事件”、小丑的出场和主使、“以‘堕落’的方式在想象中‘瓦解’既存的秩序”,是否更适用于方旭的老舍改编?尤其是在《牛天赐》一剧中。
《牛天赐》中的人偶同台,使得“我”常常化作“他”,“叙述”的牛天赐时刻揶揄着“动作”/扮演的牛天赐,这种间离戳破了生活的表象,貌似正常的一切有了荒谬的色彩。而小说原作中围绕牛天赐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在导演处理中“嘉年华”化了。“洗三”(第三场)一场,天赐的真实反应与众人合乎礼数的态度迥异,坐在舞台右侧的门墩儿又拆穿着众人台面儿上的话,这种反差引得观众哄笑。舞台后方垂吊的孩子面庞般的装置上,投影出三姑六婆嘀嘀咕咕的身影,他们当面表示祝贺,背后议论天赐是私孩子,紧接着偌大的蓝绸子覆盖主要演区,众人合力抖动,舞台中央的天赐孤立无援。迎接新生儿来到人世间的仪式中,主角新生儿是被动的,成人世界是虚与委蛇的,而类似的仪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抓周”(第四场)一场,亲朋好友高举竹竿,上面吊着各种象征未来前程的道具,各种“诱饵”包围天赐,竹竿之长和牛天赐及周岁偶在体量上形成对比,与其说是他抓周,不如说是成人来“钓”他上钩。而在天赐养母、养父先后离世的场面中,葬礼上都充斥着亲戚们势利的算计。声势浩大的种种仪式夸大了各色人等的表演感,牛氏夫妇表演为人父母,人偶合一的牛天赐表演他是一个初来人世的孩子,亲友们表演祝贺与悼念,他们表演得越真,维系人际交往的感情就越假,舞台上放大了这种悖论。
天赐渐渐长大,他的教育问题成了养母的一块心病。养母坚持请私塾先生,没想到请来的要么是根本不会教书的账房先生,要么是只知道体罚学生的老古板;养父把他送到新式学堂,新式学堂除了变着花样收费,就是同学之间的恶意攀比;回到家中继续设家塾,这回的老师是满脑袋不切实际浪漫想法的新青年……天赐的求学经历成了不断变奏的诙谐曲,他时而是“可笑的被害者”,时而是“喜剧的攻击者”,而每一位老师都是漫画式的人物。各式教育的种种弊端层出不穷,教育的庄严感、严肃性和等级秩序在笑声中荡然无存。
《牛天赐》也继续沿用了方旭以男演员反串女性角色的特色。“全男班”的演出特色是从《二马》开始确定的,《二马》中的温都太太、玛丽,牧师夫人,《老舍赶集》中《创造病》《邻居们》的女太太们,《牛天赐》中的牛太太、奶妈纪妈,全都是由男演员扮演的。《二马》中,男性社会所推崇的女性矫揉造作的气质和英国文化中的社交表演合二为一,性别反串的表演凸显了既是异域的又是异性的“不自然”;《牛天赐》又是另一种情形,牛太太和纪妈均是丑扮,类似戏曲中的彩旦,牛太太在家中有几分跋扈,凌驾于牛先生之上,她对培养一个“官派”儿子的向往与性别无关,而是出于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这是一个失去了女性特征的女性,是牛家的权威;纪妈扔下自己的孩子出来做奶妈是令人同情的,但她身上又有着喜剧固定类型角色“乡巴佬”/乡下人的特质,是受人愚弄的,对牛天赐来说,她近乎巫婆和丑怪,令他既恐惧又无从抗拒。这类女丑由男演员扮演,轻松而出彩。性别本身包含了表演/规训的成分,男性演员对女性的扮演,陌生化了这种性别表演和规训,突显其滑稽可笑。
台词方面,台词的有机重复和对白的相声化贯穿始终。《牛天赐》一剧的多组人物关系中,如牛天赐和养母、和养父、和纪妈(奶妈)、和四虎子(小力巴)、和前后两任家庭教师、和学堂的老师同学们、和门墩儿,各有各的“暗号”,即有机重复的台词。如养母的“暗号”是“官派”,她心心念念要培养一个官派的儿子。“官派”一词是人物的标签和基调,更代表人物的意志,而儿子没有也不大可能“官派”起来了,养母却已经作别人间,台词中的一遍遍强调,带来了机械重复的喜剧效果,重复中,现实一步步背离了初衷,而那初衷,也渐渐变得虚妄。
依托小说语言,老舍的文字一旦改成台词,不少对白接近了相声。《牛天赐》中,全剧开场的一段对白如下:
门墩儿 要不是卖落花生的老胡,这小子可能早就没了命。即使天无绝人之路,而大德曰生,那也得碰对了机会。机会可以左右生命,这简直无可否认,特别是在这天下太平的岁月。他遇上老胡,算是个机会,还得算是个不赖的机会。
牛天赐 不对,不是我遇上了老胡,是老胡发现了我。我刚生下来几个钟头。这时候要是就会说话打招呼,不见得是好事。万一我一开口把老胡吓跑了,那我只有等死了。
门墩儿 人是可以努力!但是不能过火。
牛天赐 人是可以努力!但是不能过火。这话听着有点意思。
这段建立了叙述的对白中,对话的双方门墩儿和牛天赐有意无意地形成了捧哏与逗哏的关系,捧哏重复和发展/逗哏的语言,两人合起来的语言效果像一段绕口令,在“机会”“老胡”“努力”“过火”几个词中反复缠绕,近乎两个声部的重叠和第二声部对第一声部的模仿与发展,突显的是语言的趣味和游戏性。
此外,《牛天赐》一剧的表演还用到了方言和京剧表演程式,化妆方面门墩儿和牛天赐面部敷以白粉等显豁的喜剧手法。
传记通常是献给英雄的,“小英雄”牛天赐的成长历程是反讽性的,在此过程中,既存的秩序渐渐坍塌。舞台上的《牛天赐》使用剧场化的手段放大了小说的喜剧性,相类似的事件/场面在模进中不断升级,具有了狂欢化的样态。
结语
与后期创作得到的肯定和荣誉相比,老舍的早期喜剧小说一度被遗忘了。从独角戏《我这一辈子》开始,方旭在八年间先后创排了《猫城记》、《二马》、《老李对爱的幻想》(《离婚》)、《老舍赶集》和《牛天赐》,将“另一重”的老舍搬演到舞台上。以观众的接受而言,“陌生”往往是第一感受,人物、主旨、情调都和舞台上常见的《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式的作品大相径庭,而“陌生感”很快在笑声中消除,继而油然升起的,是对老舍先生的叹服。创作于1926—1936年间的这些小说,犀利、准确地批判了国民性,恰恰是这一重的老舍在时光荏苒中被陌生化了,重新出现时,更具喜剧的效应。“……‘喜剧创造距离’。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再来看世界,则世界的滑稽性与荒谬性就更清楚了。”套用叶廷芳对迪伦马特的论述,在时间的距离下再来看老舍早期小说,他所描绘出的世界的滑稽性与荒谬性就更清楚了。
值得讨论的是,在老舍的写实主义巨著中,是否依然有喜剧的影子?《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一文中,王德威指出,这部小说“对人生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后面”,有某种凄厉阴森的“喜剧”力量,贯穿祥子厄运的,是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用,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祥子一次次厄运的降临也几乎到了机械重复的程度,“如同卓别林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倒霉鬼那样,骆驼祥子最后演出的是一出阴森滑稽剧。”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充满眷念地书写着北平的种种旧时风物,而不断出现的,是各式人物的各种死亡,或忍辱或窝囊或疯狂或无辜或是莫名其妙做了替罪羊,死亡的频繁出现是乖张的、悲剧的,也有可能是“以喜剧形式来表现悲剧主题的黑暗喜剧”,“黑暗喜剧是由绝望的悲剧主题和滑稽的喜剧形式互为表里的悲喜剧,或喜悲剧;是对灾难、死亡、恐惧、虚无等黑暗景象所作的幽默思维”。是以,《骆驼祥子》或《四世同堂》,都存在着区别于现有改编的极大可能性。
摆脱正剧体裁和戏剧体(Drama)文体的束缚,方旭的老舍改编系列成功地立在舞台上。文学改编于戏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学和戏剧观念都业已发生变化的当下,以剧场化的思维和现代意义上的悲剧观或喜剧观面对小说,重新焕发小说原作魅力的同时,戏剧舞台的面貌也得以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