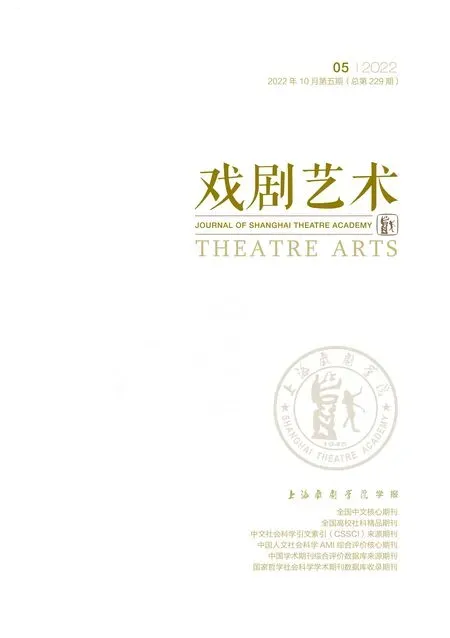沉浸性: 表演在后现代语境的另一种探讨
沈嘉熠
一、 问题的提出
表演艺术一直以来隐藏在戏剧/影视艺术中,作为表现叙事的手段而存在。
亚里士多德最早定义了戏剧和表演。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这里“人物动作表达而引起怜悯和恐惧的情感”可以看作表演作为艺术最初的“元话语”,因此表演最初的核心任务是与观众共情。
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表演多以研究演员表演为主,围绕着文本和角色展现表演技巧。表演的艺术性来自演员融合或抽离角色,引发观众不同的体验。对20世纪表演理论有着重要影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等实践和理论都很辉煌,表演游弋其中,稳固的叙事逻辑有着至尊地位,能折射文明的理性,进而表达人类的思考。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社会文化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差异边界逐渐模糊,艺术创作内在的消费性、偶发性逐渐优先于原本的主体性、逻辑性。表演亦从戏剧中跳脱出来,成为一种独立呈现的多元表达;或者说戏剧(Theatre)的审美核心从“艺术创作”延展为“交流事件”。表演的核心任务也从与观众共情转向使观众沉浸。
无论学科研究的发展,抑或艺术实践的延伸,无不使表演呈现出模糊、弥散、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等后现代主义属性,表演生成多元的沉浸性“幻景”,这恰恰契合后现代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的特质。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艺术正以一种或多或少游戏的、或多或少媚俗的方式,开始挪用久远的或不太久远的所有形式和所有作品……它是对自身文化的戏仿,也是一种复仇的形式,其特征就是彻底的幻灭。”波德里亚认为进入20世纪,艺术就已经死亡。可是,表演艺术在一个维度的“死亡”却走向另一维度的“重生”。
艾瑞克·本特莱(Eric Bentley)曾提出了最经典且简炼的戏剧公式——“C看A演B”。如此,可认为戏剧因表演而呈现于观众眼前。当然他也指出,随着后现代文化的不断渗入,“戏剧”会从文本(Drama)到剧场(Theatre)进而转向为演出(Performance),研究范式重心也发生转移,表演从观众观看延展到观众“沉浸”。
沉浸性是一种表演文化的新趣味,其审美特质重塑了表演、剧场与观众的关系。它将叙事文本埋藏在被剪碎的时间线和行动线里,更强调观演双方沉浸于自身的情境而共同演绎完成,其特质是一种幻与戏的结合,双方各层次的交流、主体与客体在整个过程中不停地转换。它不拘泥于线性叙事,为即时性想象和偶发性打开可能,故表现出深刻的沉浸性特质。
沉浸性表演把本特莱的“C看A演B”的公式转换成本研究所讨论的“C和A一起演C+和B”,观众在“观”“演”中承担“C”与“C+”的双重身份。在沉浸性表演中,“看”升级到新的维度,他们沉浸在另一个戏剧性情境中扮演和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自己。沉浸性表演不仅呈现在沉浸戏剧(Immersive Theatre)中,更在各类蕴含戏剧元素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如主题公园、戏剧疗愈、各种媒介中有表演呈现,甚至存在于大型线下游戏中,如密室逃脱、剧本杀等。
这些沉浸性表演让我们看见的是观众离开幽闭的剧场,进入开放多元的空间,它的背后意味着表演的审美特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介入到表演环境中的体验者和驱动者。社会情景的变化和渗透,技术力量提供的可能性及其干预,使得表演的本体价值和意义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螺旋上升。
本研究将以观众为主体展开讨论,以身体感知、时空关系、观演的“看”与“被看”等三个重要的维度阐释沉浸性表演是如何发生的。本研究继而结合中外相关“经典”案例,以分析表演艺术传统的“崇高地位”是如何被消解的。沉浸性如何透过观众而回旋于当下多元的表演文化场域中?沉浸性表演的后现代文化特质是怎样隐喻当下社会文化变革的?这些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
通过实地观察、体验、参与若干沉浸性表演,本研究认为: 表演作为艺术的幻觉已经溢出表演叙事之外,而弥散在演员与观众之间,使观众沉浸于表演之中,从而使表演的沉浸性呈现出感知 (Perception)、幻觉(Illusion)和凝视(Gaze)三个维度的美学特质。
二、 沉浸的身体感知
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幻觉如何向真实不断趋近,从视听感知开始。1787年,欧洲出现了全景画(Panorama),这种巨大的圆形画作让观者只站在一处,便能看到绘有一座完整城市景观的油画设计,试图给予观众最大限度的真实幻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不断地制造跨媒介的真实幻觉。比如,4D电影除了戴上眼镜感受3D影像效果外,还在座位周围装上传感器,配合画面一起给观众带来“浅尝辄止”的风吹雨淋等体验,以此激发观众的身体感知,使他们尽可能进入情境中去。
这种“沉浸”虽有身体的参与,但基本立足于外部技术(数字的或机械的)。我们不妨称其为“接受式沉浸”,以区分下文即将要讨论的“沉浸性表演”: 前者是被动的视觉或身体感受,观众没有主动参与,与表演的关系是割裂的;而沉浸性表演中观众的身体和意识则要主动地感知,并参与/推进表演。
“感知(Perception)”实际是持续的瞬间积累,是人们对信息的主动选择。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认为“感知是一个生成之中的知觉”,它被认为是后现代艺术的重要特质。沉浸则是人们在感知过程中全身心投入的状态,既具有当下的身临其境,又具有自我觉知其虚构性的交错。
“沉浸”(Immersion)在感知层面增加了时空的维度。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认为沉浸的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下,参与到某项活动中的人们是如此投入,以至于忽视了周围的一切。”当人们在某个时刻建立起沉浸性,他的思维、身体等方面的感知都融合起来,对时间的理解和感知也会随着沉浸的空间而变化。
沉浸性表演中,观众的沉浸从意识层面进阶到身体层面:“我们以往不曾认识到,为能表达它自己,身体应该在分析之后也变成思想或其指示我们的意向。其实,在显示、在说话的正是身体。”身体感官和精神活动的关系是相互交错的,只有触摸时才能感受到被触摸,只有看见时才能感受到被看见。观众的身体被浸没在戏剧叙事的情境里,参与表演的同时也被表演所淹没。
当下热门的沉浸式戏剧便体现了沉浸性表演的审美特质。例如,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在全球多地不断上演: 每一个角色的表演路径都是固定的,从特定的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如此循环往复。“观众可以铆定一个角色,跟着他/她的时间线和行动线循环;也可以随意地捡起另一个角色的时间线头,跟随新的行动线。”观众在不断地追寻和奔跑中探索各种不同的体验,在戏剧所创造的真实空间中寻找戏剧情境中的时间、氛围,甚至是气息。
马晨骋主导了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的引进,他曾提及: 上海的《不眠之夜》前不久进行了5周年庆祝演出,到场的很多忠实观众分别在五年间体验了100遍、200遍、300遍、400遍,最多的一位观众已经看了580遍。他们纷纷表示来《不眠之夜》不一定是看戏或演员。在这种戏的空间里,他们找到瞬间的迷失感。观众甚至热衷于看房间,周围布景、道具、服装等都是切切实实的,但它们整合的是纯粹的虚构。观众迷失在幻境里,既是观众又是表演的另一个主体。
从某种意义上看,沉浸性表演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媒介,是人与戏剧叙事,以及自我和他者之间交换的媒介。它的审美特质和传统戏剧不同,人们一旦进入其间,即与其产生交换。表演引发观众最初始的感知是视觉(Sight),在沉浸性表演中,视觉是可触摸的(Tactile)。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当我们观看艺术品乃至普通对象,尤其是印象深刻的东西时,我们会陷入一种可触摸的交流,因而我们才能够与其沟通。这样的交流在戏剧空间中重叠迂回,观众沉浸于此,从视觉开始,到达身体。
观众的沉浸性感知来自身体的两个层面: 一是观众身体触摸等直接感觉(Sensation);二是观众身体产生的直接感觉与身体感知(Perception)相关的行为。《不眠之夜》中,当观众在邓肯国王书房里随手拿起书桌上的信件时,他们的手对剧中信纸的感知,不仅包含了触摸书信的感觉,而且包含了触摸戏剧的感觉。观众的手嵌入戏中,成为他们沉浸到表演的一个通道。“外在的”身体和“通过身体被感知到的”那部分作为同一个身体被给予。当观众离开沉浸空间时,通过身体触摸到戏剧的那部分感知就消失了。
观众在沉浸式戏剧中产生多维的感知,进而滋生沉浸性的新意义: 一是颠覆性的演出空间给观众带来的现场感,二是与演员的互动为观众建构的存在感。
表演最初让人产生共情,但当与日常消费方式连接在一起时,二者互相笼罩,互相隐藏,观众不可能发生单向的共情,而是沉浸的体验。他们在观看与表演中游弋,他们是驱动者,他们的身体和“看”的过程都因表演而被消费,并形成共生共促的参与。
三、 迷失的戏剧时空
沉浸性表演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蕴含戏剧叙事的、交错的时空关系。当表演抛开原来的剧本(Drama)土壤而迈向事件(Event)时,它便浸润在弥散的、去中心化的氛围中。人们不再追逐戏剧冲突与核心人物,而迷失在蕴含戏剧叙事的情境中,但主体是在观众与演员之间交替转换的。
观众与演员融合在戏剧情境的幻境里,暂时忘记物质的时空。例如,在《不眠之夜》的演出中,观众在剧场的酒吧里一边喝酒一边看剧中人物一边以参与叙事的方式与演员互动表演;在迪士尼乐园里,游客/观众成为迪士尼故事的一员,当人们戴上迪士尼特色的小头饰、小道具时,他们的表演甚至比乐园中的演员还要投入。
沉浸性表演的发生是时、空、观、演的集合,生成一个向心的场域,包含其中和附近发生的所有一切,必须打破和违反所有表演的传统,消除核心冲突和人物,更像一次迷失在故事中的狂欢,其主旨在于“消减隔阂,把观众改变成作为共同参与表演的关联”。
这种沉浸式审美并不是在后现代文化浸润下横空出世的,它的精神可以追溯到古老而神秘的印度,那里有一种“幻-戏”(maya-lila),即宗教戏剧“罗摩利拉”(Ramlila)。这是一部连续31天的戏剧,故事来自古老的传说,从印度历9月到10月,每年有上千部罗摩利拉在印度北部上演,最著名的是印度教圣地罗摩那迦城(Ramnagar, 直译为“罗摩之城”)。每到演出月,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沉浸式剧场,戏和生活充分相融,城中的居民、游客和演员都一起生活/表演于传说中的罗摩王城中,他们的生活和“罗摩王与罗刹王的战争”混杂,游客们和演员们一起吟唱剧中的长诗《罗摩衍那》,和演员们共同表演那个想象中的世界。人们会建造或拆除一些临时性的布景,而城里永久性的建筑、花园、池塘等则一直使用着它们在剧中的名字。进入演出月,许多街道、寺庙和池塘便摇身一变,从平淡无奇的去处变成罗摩利拉的舞台。同一空间具有多层联想和含义,戏剧和表演在观众之间流动、交叠、迷失。
无论在古老的“罗摩之城”还是在当下的迪士尼乐园,空间都是既有“幻”又有“戏”。观众身处于“另外的时间和地点”,但这种“另外”对观众并非未知,他们反而穿梭其中,游刃有余,他们才是真正的驱动力。
例如,在沉浸式音乐剧《疯狂约会》中,一位幽灵要拯救主人公的爱情,扮演幽灵的演员随机选择一位男性观众并直接坐在他身上,抢过他的手机并拨打后面将上场的女演员电话。这种突如其来的时空交错会让观众吓一跳,但他往往会很快适应并和演员合作完成沉浸性表演。再如《不眠之夜》中,观众跟随麦克白夫人进入卧室,他们可以随意地坐在沙发上或靠在躺椅上,甚至可以坐在床边,欣赏她与麦克白先生的表演;有些观众甚至会坐在国王邓肯书房的一角,翻一翻书桌上的书,闻一闻边上的半杯苏格兰威士忌。这里,观众的身体作为驱动主力,颠倒了日常生活空间,在沉浸式时空中,他们意识中的禁忌和幻想被各自的身体实现。
沉浸式戏剧中迷失的时空还呈现一种混杂化(Hybridization): 生人和熟人、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专业演员和普通观众都聚会到同一时空。在这种戏剧体验的“间隙”,人们的身体在“同一时间身处两处”。观众的迷失与沉浸是“身体化”的主体性审美过程。他们的身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不断的互动,而表演由互动构成,颠倒于故事的景观中。这种沉浸的迷失不仅存在于物质时空中,更存在于精神的建构中。
四、 凝视: 沉浸中的“看”与“被看”
沉浸性表演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凝视。
沉浸性表演场域是弥散的、去中心的,叙事是碎片的、不可表达的,观众游走其间似乎更易迷失。然而,观众之所以能够沉浸,是因为他们不仅在观看,更是在凝视;观众的外部时空转换是松散的、交错的,而他们表演的内在意识是专注的、有叙事核心的。
在沉浸性表演中,凝视是观众“C”与“C+”的勾连,“看”不仅是看见,他们的“看”与“被看”也是相互辩证的,意识和身体一起思考和感知。
约翰·杜威(John Dewey)指出,“纯粹的认识是纯粹的凝视(Beholding)、观看(Viewing)、关注(Noting)”。“看,也是感知;看,就已经在思想”,既针对现象世界,也可通往理性境界。
传统表演,无论是剧场还是银幕,人们在观众席观看表演,意识可以入戏出戏,但身体无法移动,没有“被看”,也鲜有“凝视”。
如今观众的注意力早已被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电子信息过度吸引,传统戏剧和表演的外在生产方式被电子工具轻而易举地替代,因此人们的身体性感知和沉浸的“心流”则愈显珍贵。
沉浸性表演中,观众的视觉和身体会与戏保持距离,但这种距离没有接近与疏离,它超越三维空间。这是因为,观众与演员之间有彼此身体的厚度,由此构成戏剧的可见性;而这不是戏剧与观众之间的障碍,而是它们的交流通道。“我是在可见的中间的,同时我又是远离它的: 这是因为可见的是有厚度的,由此它自然注定要被一个身体去看。”
这种复杂的“看”与“被看”形成“凝视”(Gaze):“我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却四面八方被看。”拉康(Jacques Lacan)说:“‘凝视的前存在’(The Pre-existence of a Gaze),即主体在向外观看的同时也被另一个东西(但不是另一个主体)所注视,主体总是处在来自另一个领域的目光包围之下。”尼采诗意地隐喻:“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沉浸性表演的情境不是深渊,也钻不出恶龙,但观众的凝视被沉浸式戏剧包裹,形成统一的“理想空间”。他们的“看”并不仅限于作为客体对表演主体的看,他们与演员同为主体,戏剧的空间和他们的想象形成交互的空间。在那里他们与表演相互呼应、交换、聆听;在那里他们“看”与“被看”。
沉浸性表演的命题是“看”和“感知”融合,建立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感官理解。观众和演员彼此既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演员之于观众是可见的,而观众之于演员是可述的,两者相互渗透、相互驱使并相互虏获。观众和演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整个沉浸性表演的空间是个积层交错的、越界表达的场域,呈现着观众与表演之间、可见与可述的力量交汇。
沉浸性的隐喻不仅是“看”与“被看”的交叠,而且还有表演性。
这里所说的表演不是传统戏剧中的表演艺术(Acting),而是以非叙事性和体验性为特征的后现代表演(Performing): 这是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指出的弥散并存活于各处的后现代表演,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不稳定叙事或创造叙事的形态。
沉浸性表演弥散在观众与演员之间,观众的沉浸有“演员”的部分,他们占据演员的领地,他们的身体、行动构成了表演的一部分。观众与演员形成层叠的交互关系,他们站在沉浸场域中间,与演员不是单一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因戏剧叙事内核而存在的不稳定且不间断的交流关系。观众把“此时此地”的表演移情到毫无关系的“彼时彼地”,他们沉浸的当下,仿佛都是真实的,而他们一旦离开,则立即变得虚假。观众们在《不眠之夜》国王邓肯的书房里,随意地拿起书桌上的书信,或者他们走向《疯狂约会》的吧台,点一杯爱情主题的鸡尾酒,这时,观众移情到了“表演”。如果观众在沉浸性表演之外还拿起同样的书信或点同样的鸡尾酒,就会意识到那只是道具而已。
在这种重叠的运动中,观众的移情表演既不为他们的观看提供证据,也不向他们传达有助于理解的信息: 它以沉浸性覆盖于整个戏剧(相同或者不同、在场或者缺场、真实或者想象),从而迫使观众和创作者与超越视觉领域之外的、但仍然弥漫在戏剧中的东西达成一致。
沉浸性表演中蕴含了多重自我关系:“我”看到了自我本身,并介入甚至替代,就好像它是另外一个自我。“我”意识到这个替身——让第三自我感觉到与另外两个自我的亲密关系,朱光潜曾提及这种几何式的进阶“内省”就是后现代的。观众在“看”戏的同时意识到另一个自我沉浸于戏的当场,它正在表演。
结语
不少戏剧理论研究把20世纪欧美戏剧的变迁理解为从“舞台艺术工作”到“交流事件”的转变,认为是“戏剧范式的重心转移”,这一范式重心转移的“一个重要转向便是从演出者的叙述与阐释转向为观众的接受与解释”。观众不仅在接受和阐释,更在表演与创作,“所有沉浸性表演事件都涉及参与者在表演体验中对自身存在的认可,在表演形式上转向为完全沉浸,观众作为参与者塑造自己的‘叙事’旅程”。在这个旅程中,尽管以推动戏剧叙事为主体的表演艺术被摧毁,但表演的快感被栽植在参与者/观众的身体里,成为一切参与者的表演事件,不需要被沉浸性场景之外的任何一个他者所“核定”——这便是后现代艺术中的体验性和游戏化特质。
在一个更宏大与广阔的意义层面,沉浸性表演更蕴含着人们对艺术感知的自我增生和自我更新的力量,这是后现代文化由内而生发的力量。后现代语境中,现实主义艺术正逐渐消亡,但表演却在沉浸中激发新的魅力。沉浸性表演中观众作为驱力的主体,冲破身体走到了前台。
后现代艺术成为一种姿态,一个陈列柜,美学注满在整个社会机体内,它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主题公园。在这个“主题公园”中,艺术的幻觉便是存在的现实,那些原本需要距离和空间进行反思的艺术审美往往被沉浸所颠覆,被消费的是观众与艺术的关系本身。这种行为不是一种单纯的、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他不再反思自己,他沉浸其中并在其中被消解。”消费者/观众不会把沉浸中的表演性自我与现实中的自己混淆起来,前者只是他们在沉浸空间的一种镜像。他们在与看戏时的那个自我的镜像“游戏”“玩耍”。观众看戏有表演的意味,他们同时也在消费,观众在剧场餐厅中消费的不仅是一份美味佳肴,而且是一种戏剧所营造的特定艺术情境。观众在消费的同时也在表演,或者说观众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消费。
沉浸性表演发生之初,也许人们看到了“先锋戏剧”的身影,也感受到消费文化的痕迹。然而先锋也好,消费也罢,其背后蕴含的都是人们内心对当下文化与艺术的感知,挖掘的是人们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以及与人类精神和情感的关系。
观众无论在台下看表演,还是与演员一起在表演中沉浸,都是生命有机体对艺术的知觉,以及对自身经验和想象的洞察。“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人生如戏,你在戏中,“风景”和“看风景人”并不存在,但“你”与它们之间凝视的瞬间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