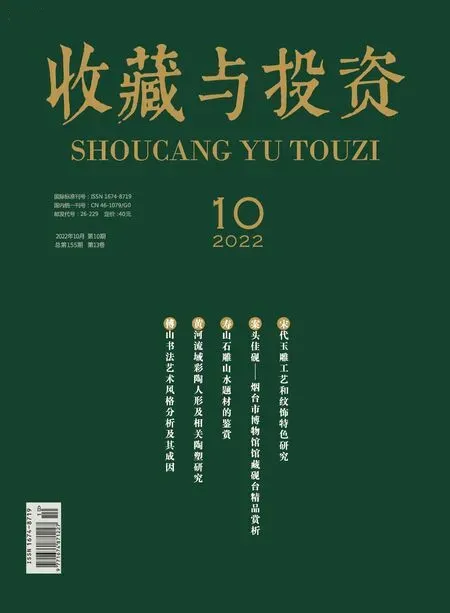诡形怪状 任情肆意
——张旭狂草艺术分析
刘佳佳(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张旭,号称“张颠”,世称“张长史”,他作为在唐朝时期颇具盛名的书法家,在当时就已经被誉为“草圣”。张旭工书法,精通楷法,但是以狂草最为出名,也最受推崇,多见于诸家诗文。张旭的狂草艺术显示出书法审美的“形”与“意”层次:“形”的审美是书法审美中最基础直观的部分,张旭将旷达洒脱之情寄于狂草艺术,其狂草艺术之“形”彰显出极致的变化之态,但仍处在汉字的结构框架之内,最终达到整体和谐之美;透过表象形式可以窥见“意”的审美层,张旭的笔墨挥洒中蕴含着纵逸狂放之情与动态之美。
一、张旭狂草“形”与“意”形成背景
在中国书法史上,唐朝是无法逾越也不可逾越的一个时代,“大唐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历史与文化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稳定的社会使人民追求精神生活,促进了艺术文化的发展。同时唐太宗钟情书法,还将文字学知识和各种书法演示纳入科举考试之中,“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1]。必须要两者兼及才能书科及第。除科举考试外,书法也是考核与任官的必要条件,因此促进了书法在唐朝的发展。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与创作者主体性的审美取向是密不可分的,作品独特性显示出对象本身的特征,对象的特征和创造者的主体性相互联系。中国古代诗、画、书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张旭的诗歌中蕴含其审美取向,传世的诗歌仅有十首,其中,《全唐诗》收录六首,《全唐诗拾补》中收录四首,其诗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张旭在进行创作时将目光投向自然,追求清新脱俗、闲适淡雅,这使得他在书写时呈现狂草的极致自由之势。
张旭处于整个社会崇尚书法的氛围之内,加之唐朝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时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张旭钟情于自然万物,自然在他心中引发自由洒脱之感,于万物中体悟书法,其狂草中的“形”与“意”在受唐朝影响的同时更是其审美取向的结果。
二、张旭狂草的“形”—外质审美
张旭的狂草有其鲜明的特点,汉字在线条中建构所具有的空间性,决定了书法艺术的空间性。张旭在狂草中将较为稳定的空间造型打散,使得字形得以突破。但无论其形如何使空间造型改变,整体的均齐依旧存在,同时字的整体框架结构不会因狂草字形的变化而从狂草艺术中消失。
(一)形—变
杜甫在《饮中八仙》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2]草书艺术对于楷书稳定的框架结构和字字独立之形进行了突破,张旭的狂草艺术在此基础之上又对于章草与今草之形也有所变化。章草与今草都表现出“字字区别”的态势,字与字之间区别仍分明可辨,张旭的狂草则更多为牵上引下,字与字之间相互勾连,一行无所间断。刘延涛在《草书通论》中称:“狂草者,草书中美艺品,创始张旭,由狂僧怀素得名,而以诡奇疾速为其特征!”[1]诡形怪状是张旭狂草最为明显的特征。
张旭的《古诗四帖》是诡形怪状极致的书写,以其屈伸变化之势最为突出。对于草书的书写,其他书法家一开始的书写都略显严谨,但张旭不被拘束。《古诗四帖》开首即为狂草,“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十个字可以说字字连而不断,两诗句形成一笔书,到“车”字的末尾以枯笔为收笔,停顿之后再另起笔锋进行下一句的书写。“芝”字顺峰落笔,几经曲折,极具张力,然后引笔顺势而下至“北”字,上紧下松,整体的和谐仍存其中。“登天”二字与“泉”字其形在简化的基础之上,线条奇肆,形虽变神依存,篇尾“隐”字顺承“仙”字右落之笔,弹性的伸展可以由此窥见。“隐”的右旁空间虽小,但笔画盘踞之中,形折而不乱,如神龙腾天潜渊之势,至“不”顿字笔势结束,笔结意不结,之后又另为起笔,“别”字以环绕成圆的态势现于纸上,如龙盘踞之势,气势昂扬,“可”字上屈下伸,上部曲绕使态势较为紧,上部空间笔画被压缩,下部得以伸展,顺意延长,“其书非世教”左旁屈右旁伸,“世教”二字又上伸下屈,形成对比,“其人必贤哲”是完全的伸展态势。短短几行就蕴含了多样的屈伸变化,可以说态势的屈伸在张旭的狂草中随处可见,但其狂草中字态的伸展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在字形简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赋予字形变化的态势。
张旭的狂草将外形框架进行最大限度的突破,运用变形、夸张手法,字形跌宕起伏,使字形随心而变,无论是字构、线条还是笔法,都具有舞动之感,不为前人拘束,以无法为有法,“如神腾霄汉,夏云出嵩、华,逸势奇状,莫可穷测”[5]。
(二)形—不越矩
书法是以文字为载体而存在,它对于汉字的“音”与“义”有所摈弃,但汉字的“形”对于书法来讲是不可分离的。书法虽脱离文字之后其形虽仍具有美感,但书法的实用功能就丧失了,人们在面对不可完全识别的“书法”时,对于其美的欣赏在失去可参照物时就丧失了一部分。狂草能够最大限度地摆脱汉字框架结构,但狂草终究不能脱离一切,汉字第一形式的框架性依旧在其中。
姜夔在《续书谱·草书》中云:“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5]。”以张旭的《古诗四帖》为例,《古诗四帖》中的“仙隐不别可?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其书写连绵如山,体势飞动,字字皆无法辨识,而其仍不逾矩。“字之梗概”可见于其中,仙隐二字,“仙”字疏而“隐”字密,二字之间虽有所牵连,但整个方块结构仍存,“隐不”二字,以“不”字之上笔画作为“隐”字之下笔画,使得二字相连,但是“不”字内部又是连中有断,使得二字“同中有异”,二字各具体势,“不别”二字,“不”字的收尾细轻而“别”的起笔粗重,二字的区别也是一眼可辨,“别其”二字也是上字收尾轻细而下字起笔粗重,同“不别”二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书非”连笔与点画之笔具有粗细变化,于流动之间见其形,“世教”二字则连笔处较粗,但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人”“贤哲”皆是连而不断,其密疏布局,框架仍可见。张旭的狂草不仅是线条的艺术,更是点画的艺术,点画的运用使其更增变化之势。“下”由三点构成,犹如坠石,“雨”字将两点半包围其中,“应逐”“登天”在连续的线条结构之中加以点画,起画龙点睛之笔,无论狂草如何使得字形变化,其框架与点画都仍可见。
狂草在对字形框架突破上作了最大的尝试,将书法向自由方向最大限度地延伸,但整体仍处于汉字的框架结构之内,丰富的线条韵味与诡奇的形态变换相互依存,同时张旭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把握恰到好处,流动的时间在线条与节奏之中得以体味,在有限的空间之中构建无限的韵味,内美外美皆寓其中。
三、张旭狂草的“意”—内质审美
书法是由线条所汇聚而成的艺术,书法、绘画与音乐之中的线条,虽都具表情达意的功能,但书法表情达意的功能更上一层楼,书家细微的情感变化都可映于线条变化之态中。蔡邕在《笔论》中曾加以论述:“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5]
篆、隶、形、楷因受到法度约束更强,因此抒情性就会被削弱。张旭的狂草以无法为法,洒脱之情映照在其笔墨中,从字的疏密大小之变可以感受到张旭情感的变化。《古诗四帖》开头即是狂草,可以体会到张旭情绪的欣喜之感已经生发,此后情绪不断激越上涨,至“齐侯问棘花……南宫生祥云”,其字形大墨浓,情感激昂至极,狂放自由之态更为凸显,至“一老四五少”情绪略有舒缓,至最后“必贤哲”戛然而止,但书尽而意无穷,情意仍留于其中。
“中国的书法本是一种类似于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有形线之美,有情感和人格的表现。”[4]书家或疾或缓的运笔中蕴含着丰富的节奏韵味,将笔墨挥洒于纸上,浓淡润枯更不相同,这一切赋予书法以音乐的节奏感。张旭在狂草的书写中通过运笔的疾缓、点画的轻重、结构的疏密将节奏加以表现,行行之间的间隔并非整齐划一、整篇不变,字与字之间并非字字分离。或缓或快的运笔使得狂草具有连绵不断的势态,字字相连为常态,使书法节奏更具有连续性。缓时,如潺潺流水;疾时,如瀑布倾泻。正是这种缓急变化,加强了狂草的节奏意味。《肚痛帖》大小字穿插其中,参差错落中又具有整体和谐性,第一行“忽肚痛不可堪”六字,前三字浓墨粗笔,厚重稳定,忽然之间,后三字轻笔连绵,顺势而下,极具艺术夸张的形式美,用笔飞动流畅,变化莫测。张旭在自由肆意之下所书狂草,其体势的平衡被打破,书法的静态空间也随着打破,其 “形”表现出回环往复的态势和线条的飞动变化,时间的动态美在张旭的狂草中得以充分体现。
张旭在狂草中以无定法为法,意欲达到法度的极限与无定的极限。其落笔书写之时,笔墨自由奔放,随胸臆自然而发,线条具有流动美,在狂草中可以体会到张旭的诗酒情怀及其豁达的生活态度,体味其奔放激昂的生命体现,形意相存。张旭将这一切寓于狂草之中,在节奏中流动,在字里行间流淌,奏出对自由灵魂的赞歌,体现出生命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