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脉络※
——从《饿乡纪程》到《赤都心史》
〔日〕铃木将久
(东京大学 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日本 东京 1130033)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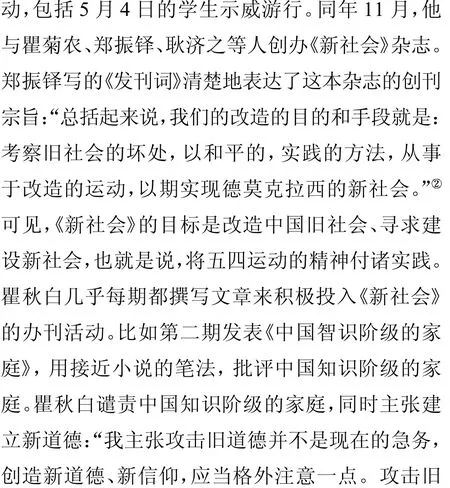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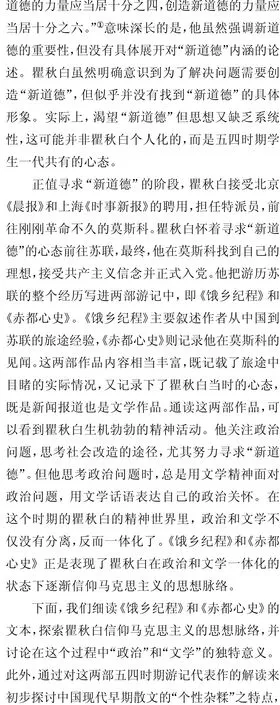

一、以文学的方式走向共产主义:《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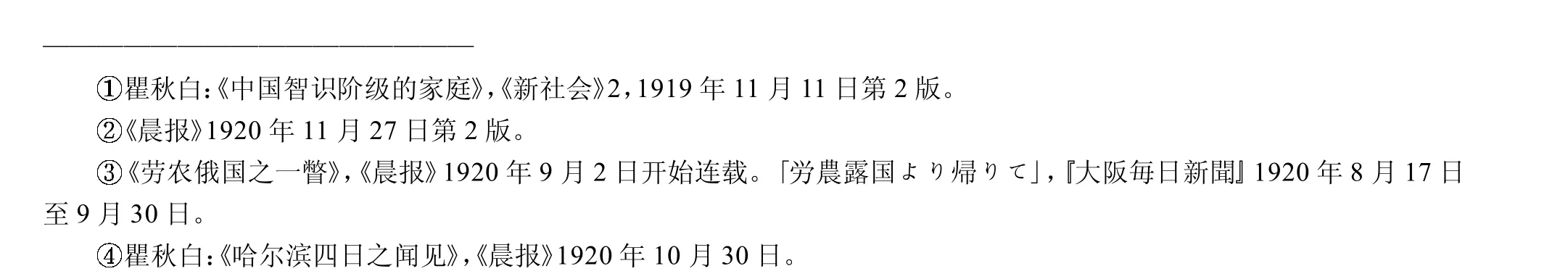

问题的思想意识。应该说,瞿秋白去苏联肩负了双重任务:一个是作为记者进行海外报道,另一个是作为五四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探求。这两种任务虽然没有正面冲突,可以同时追求,但方向上迥异。这两种意识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瞿秋白彼时的精神状态。《饿乡纪程》就表现了瞿秋白的这一内心张力。
这首诗表达了瞿秋白当时当地的心情。他不仅为了担任记者,而且为了解决自身“待解”的问题,即他一直思考的社会问题,不顾困难前往“无涯”的饿乡——苏联。紧接着这首诗,他这样写道:“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将来’里的生命,‘生命’里的将来,使我不得不忍耐‘现在’的隐痛,含泪暂别我的旧社会。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他一方面强调去苏联决不是简单的决定,说自己忍耐隐痛,但另一方面同时说明,是为了求“中国问题”的解决而去俄国。这种意识在他从北京启程之前已然萌发。值得注意的是,在刚刚离开北京不久,他就在哈尔滨已经用文字写下自己的心情。也就是说,他几乎在开始记者工作的同时,已开始生发寻求解决中国


在此意义上,《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表现出瞿秋白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整个脉络历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部作品记下了瞿秋白逐渐信仰共产主义的每个阶段的心理波动。而在他决定加入党组织的时候,他从共产主义者的立场重新整理自己思想的变迁过程。比如,上述的新诗《无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写这首诗的日期,瞿秋白必定是在哈尔滨期间写的。但即便如此,把这首诗放在《饿乡纪程》的开头部分,让它代表《饿乡纪程》的整体基调,是由1921 年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瞿秋白构想出来的。他在《饿乡纪程》中重点描写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的旅途经验,而在《赤都心史》中重点叙述莫斯科的见闻,这个分工也意味着,借助时间的推移,把他自身从尚未信仰共产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逻辑推进关系加以了说明。《饿乡纪程》为阐述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建立了论述框架,《赤都心史》则深入展开论述,阐明了选择共产主义的核心理由。应该说,这两部作品既表现了瞿秋白自身的思想脉络,又显示了他参加共产主义的一个路径。它用文学作品的方式向五四青年知识分子指出走向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二、自然描写、俄罗斯文化和感受现实:《赤都心史》体裁的选择
《饿乡纪程》中,瞿秋白有意强调研究共产主义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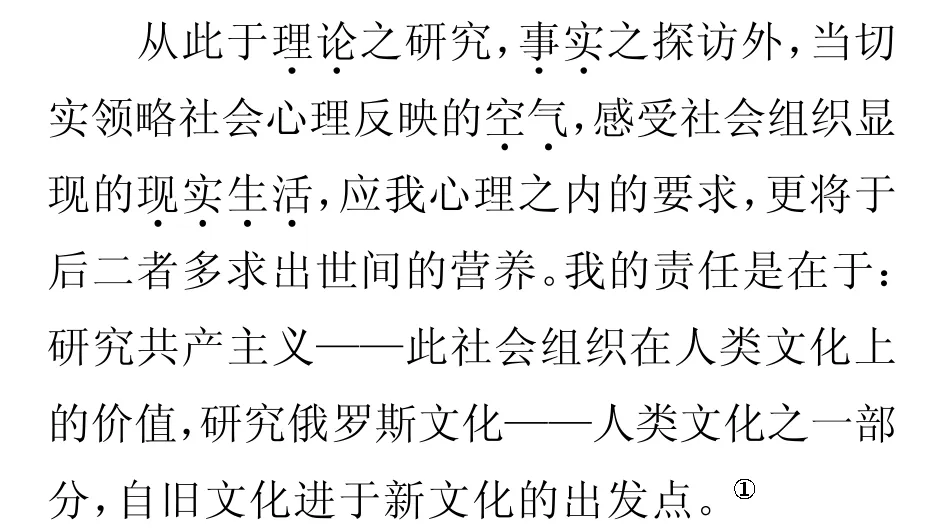
瞿秋白没有否认理论和事实的重要性,他肩负着记者和思想探求的双重任务,理所当然地重视理论和事实。但同时他还强调需要领略“空气”,感受现实。他似乎主张只有把理论、现实和空气、感受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较完整的理解。他在前往莫斯科的旅途上,目睹苏联远东地区的现实生活,尤其注意领略“空气”,感受现实,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接近共产主义思想。瞿秋白强调“空气”和感受的重要性,显示出瞿秋白的特点。而他主动接受记者身份,亲自踏上苏联的土地,也来自这种意识。因为瞿秋白感到仅从文字上理解共产主义理念是不够的,须要致力于感受现实,以获得更完善的理解。如上所述,记者身份和思想摸索的张力构成瞿秋白的精神世界,其实瞿秋白需要这种张力:有了记者身份,才可以深入现实感受社会的空气;有了思想基础,才能找到深入社会的切入口。瞿秋白的双重任务以及双重任务之间的张力,与他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有密切关系。
上述引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谈起自己的责任时,并举了共产主义和俄罗斯文化研究。他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相当重视俄罗斯文化,甚至可以说,他强调“空气”和感受,也与他致力于研究俄罗斯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为什么他如此重视俄罗斯文化?他所谓的“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饿乡纪程》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仅仅提出以领略“空气”、感受现实、研究俄罗斯文化等为核心的思考框架而已。到了《赤都心史》他才全面展开自己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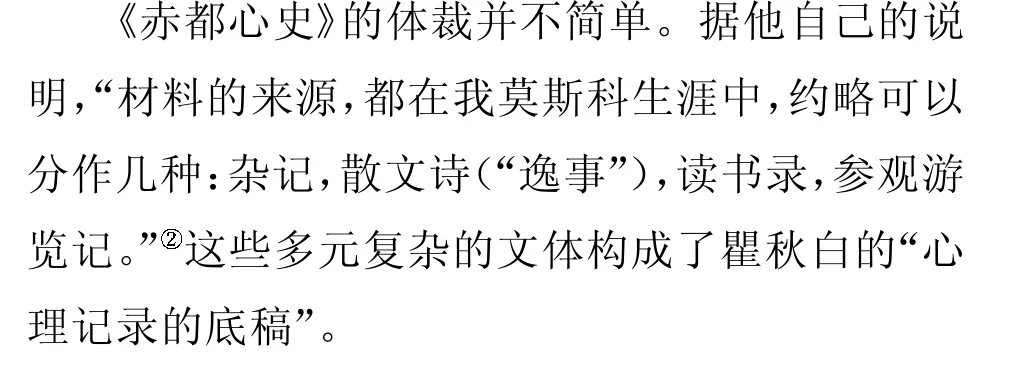

《赤都心史》第1 节《黎明》叙述了他对俄罗斯文化的观察。开头部分他居然用美文写道:“沉沉的夜色,安恬静密笼罩着大地。”他的美文立刻引出俄罗斯新文化的讨论:


瞿秋白似乎主张“文化”是在经济地位的根本之上出现的,即把文化当做建立在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这种理解基本上符合共产主义的理论。瞿秋白遵循共产主义理论的文化理解,深入探索俄罗斯文化,发现无产阶级文化的“新芽”,预言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会打破已开始动摇的资产阶级文化。从资产阶级文化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想法,也符合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也就是说,瞿秋白基本是以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展开叙述。饶有兴味的是,他居然继续用美文来配合表达这种共产主义理论的观点。瞿秋白的美文可以归结于他的文人趣味,因为他从小就受到传统教育。不过,如果考虑到瞿秋白致力于把自己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写清楚,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指示出路,这种美文或许又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的趣味,也会表示当时中国对“文化”的理解。瞿秋白用描写自然美景的文笔让读者感受俄罗斯文化的气氛,由此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俄罗斯社会的意义。
《赤都心史》的体裁中,较多的是参观游览记。瞿秋白四处周游,写下不少参观游览记。比如他拜访了清田村的托尔斯泰故居。瞿秋白原来敬仰托尔斯泰,在这个记录中,他不隐藏心中的兴奋。参观一整天后,在记录结尾,他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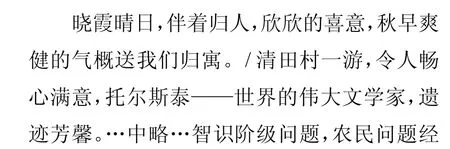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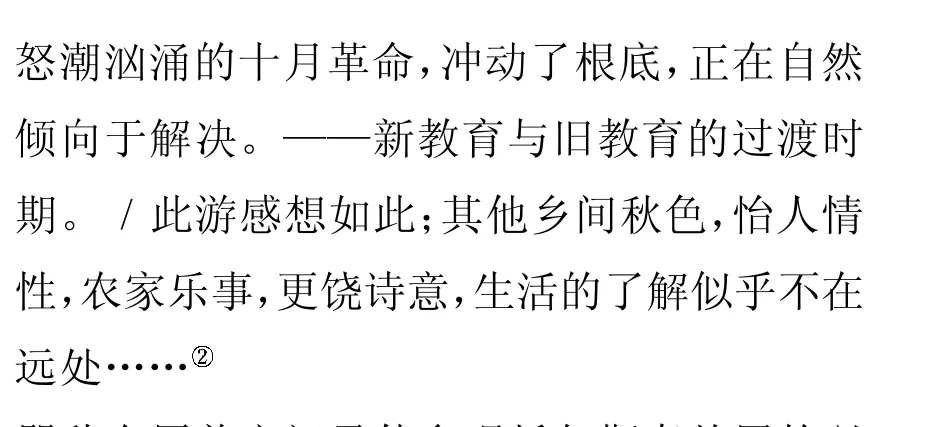
瞿秋白用美文记录他参观托尔斯泰故居的兴奋,他似乎陶醉于仰慕很久的托尔斯泰故乡清田村。同时可以看到他注意十月革命推动了社会的过渡。瞿秋白总是用美文叙述社会的变革。重要的是最后一句“生活的了解似乎不在远处”。在他看来,这种一边欣赏自然风景一边观察社会变革的心情,离生活不远。瞿秋白在游览清田村的时候,体会到“生活”的存在。
在此可以看出瞿秋白叙述《赤都心史》的基本方法。参观清田村托尔斯泰故居的游记显示出他的叙述方式至少包含如下三个因素:第一他很兴奋地赞扬自然环境的美丽,第二他观察到俄罗斯文化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变革,第三他通过自己的观察感受到生活。他重视自然环境、感受现实,也致力于研究文化,由此说明接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些因素连接在一起,使得他不仅在理智上而且在情感和身体的层面上坚信俄罗斯社会出现共产主义的道理。


三、《俄国文学史》的写作与“多余的人”之再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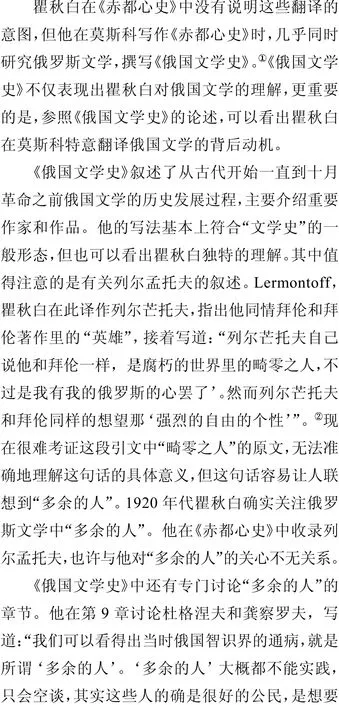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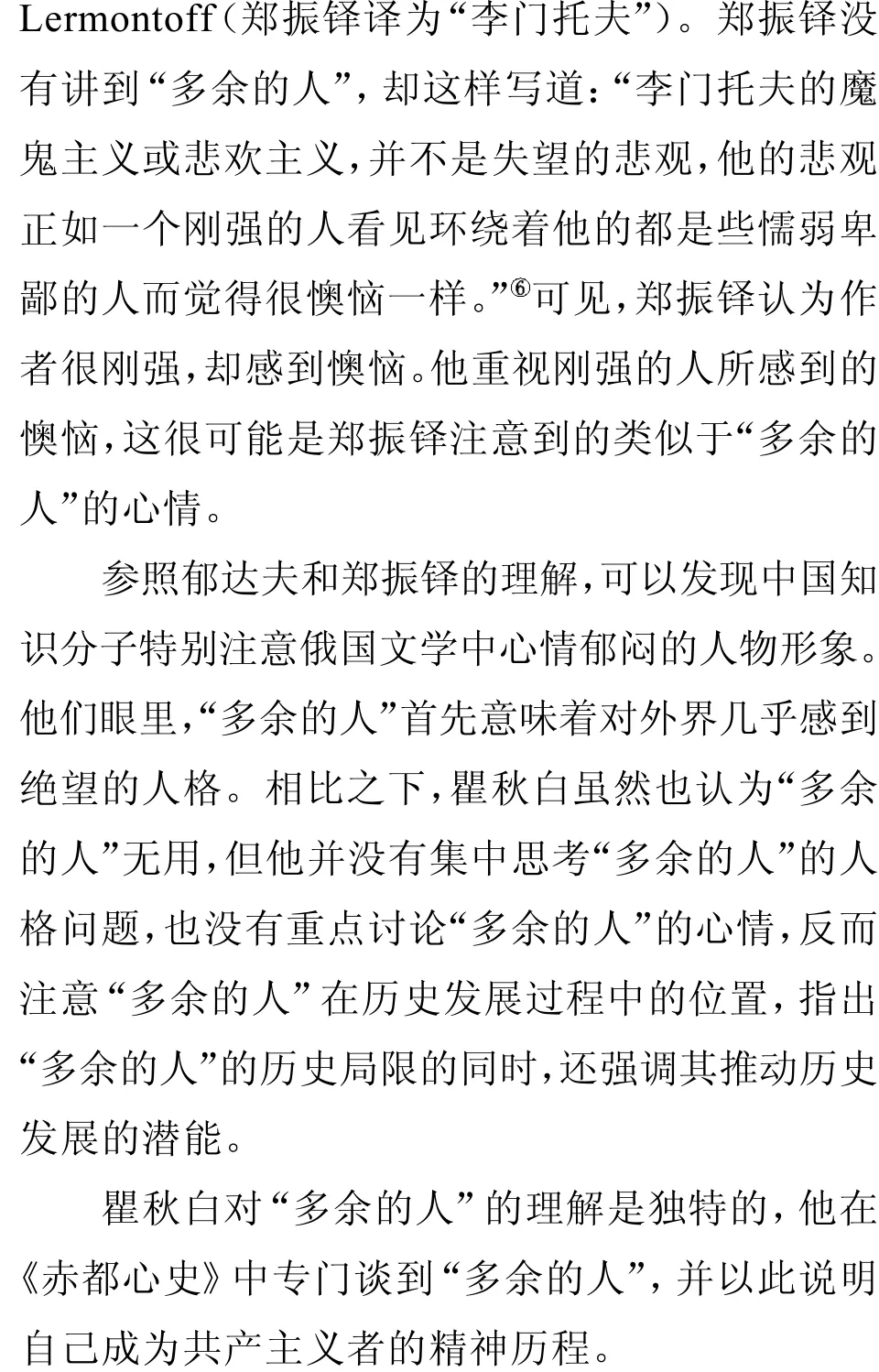
四、“多余的人”的自我命名与“共产主义者”的身份选择



就在此时,他在高山疗养院写了《中国之“多余的人”》。这篇文章首先叹息自己的病情,其次进行自我反思,同时批评中国社会“不助个性”,然后总结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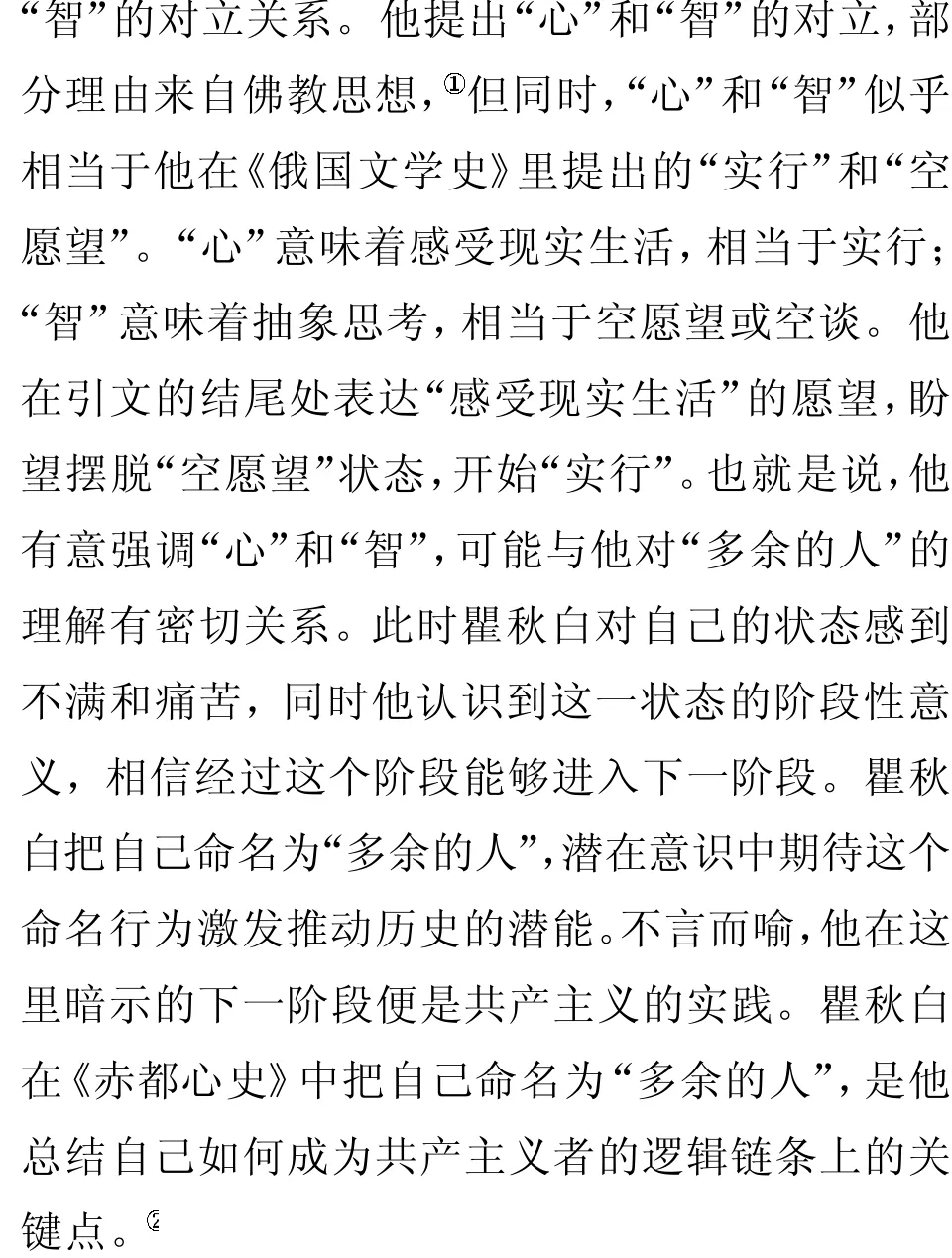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表现他从五四知识分子走向共产主义者的丰富复杂的精神脉络。他带着记者的任务去莫斯科,观察苏联社会。他观察苏联社会时,有意感受现实,重视文化,由此体会苏联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逻辑。瞿秋白的特点是,他并没有把这些观察用新闻报道式的文章表达出来,而是再次回到自我,把自我的问题和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加以思考。这种思考的关键点,便在于他对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对“多余的人”的理解。瞿秋白根据他对“多余的人”的独特理解,对自我进行解剖,阐明自己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精神脉络。他的文章既包含了对俄罗斯社会的感性观察,又表现了自我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复杂连接,因此能够让读者领会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在此意义上,《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无疑是瞿秋白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产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史上,这两部作品又成为中国现代早期的代表性散文作品。在构建中国现代散文的意义上,这两部作品也担任了重要角色。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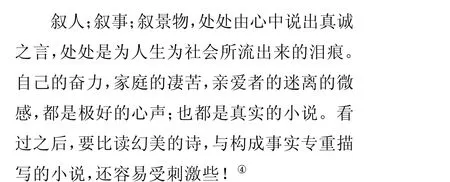

王统照强调瞿秋白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之言”,蕴含强烈的感情。他捕捉到了瞿秋白内心丰影响。王统照似乎特别提出了“读者”的问题。王统照认为,读者阅读文学性文本,尤其接受瞿秋白的情感表现,从而渐渐理解瞿秋白的政治信仰。王统照的理解实际上表露了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读者也没有把文学和政治区分开来,而是把两者放在同一个空间里加以理解。总而言之,王统照的书评体现了当时的文化形态。无论是瞿秋白的文章还是读者的阅读习惯,都没有把文学和政治分离开来,反而在重视个人情感的延长线上,接受和理解政治信仰。瞿秋白和读者共享这种文化形态,因此瞿秋白的文章在有力说明自己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精神脉络的同时,也自然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散文。反过来讲,在这种文化形态下,中国现代散文得以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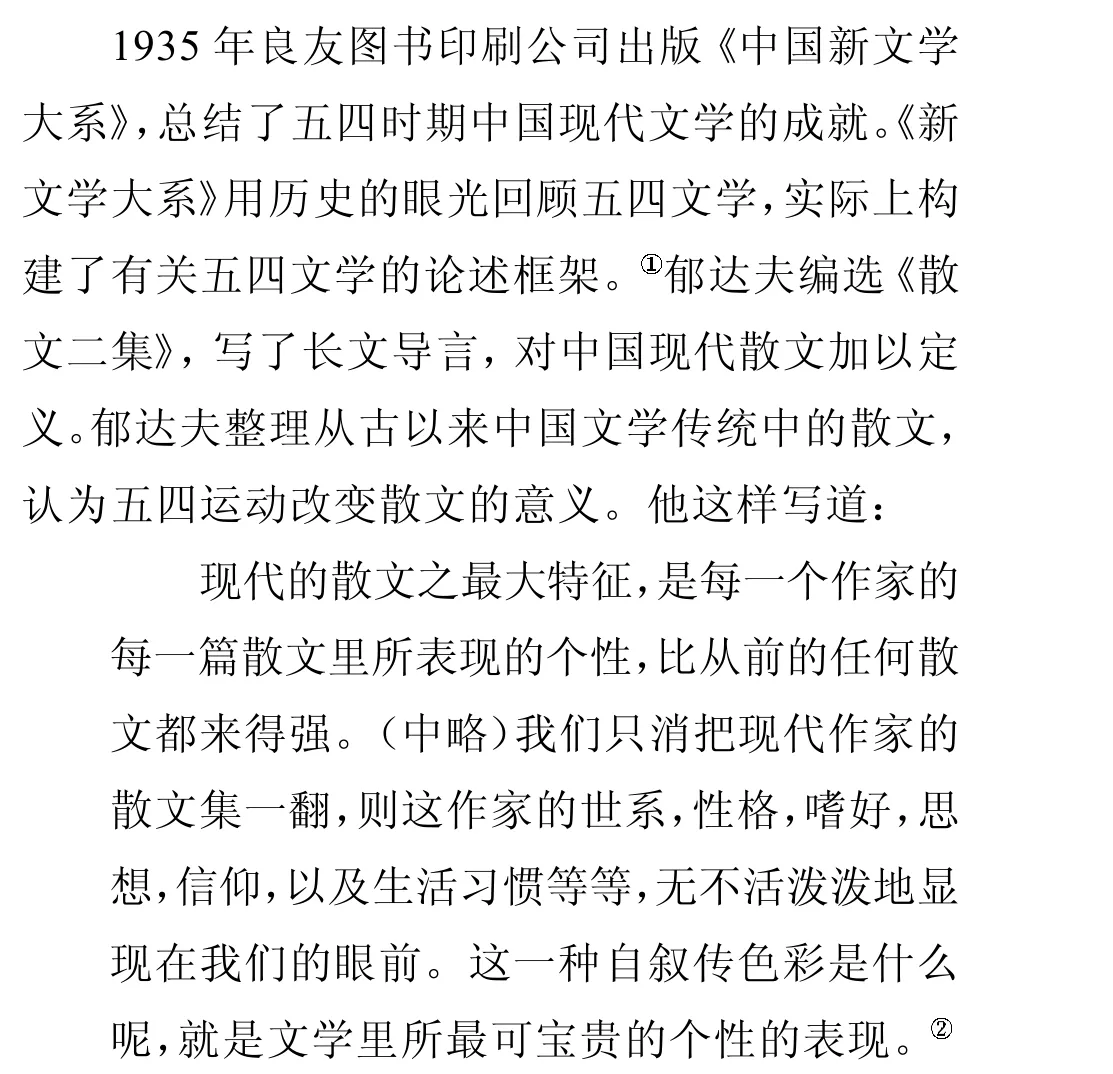

郁达夫概括从古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五四时期打破传统,建立起了以个人为核心的新的文学观念,这种理解本身不无道理。但如果考虑上述情况,郁达夫的理解也许有所偏颇。其实,强调个性很符合郁达夫自身的文学观念,他在这篇导言中的富浓烈的情感活动。在王统照的书评里,瞿秋白不是发表客观报道的新闻记者,而是表达自己心声的作家。王统照强调瞿秋白的文章所蕴含个人的感情,这其实是五四时期共通的文学课题。众所周知,五四文学的目标之一是“人的文学”。如何在新文学上表现“人”,表达人的感情,无疑是新文学的课题之一。瞿秋白和王统照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青年,认真探讨了这种时代课题。
王统照的书评可能因为只讨论《饿乡纪程》,没有谈及瞿秋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整个思想脉络,因而主要讨论瞿秋白面对社会问题的苦恼,仅仅暗示瞿秋白追求的方向而已。但如上所述,《饿乡纪程》是瞿秋白选择加入共产主义组织之后加以整理的,阅读《饿乡纪程》不难看出瞿秋白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把王统照提出来的瞿秋白文本中继承了五四文学课题的一面和王统照暗示的瞿秋白文本所暗含的共产主义方向结合起来,就浮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五四文学的“人的文学”的追求,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道理之间并不矛盾。至少瞿秋白和瞿秋白的好友们觉得,走五四文学的道路,就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在文字上力求表现个人的情感,和阐明自己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精神脉络,两者之间也没有矛盾。瞿秋白的文章中,表现感情的文学和阐释政治信仰的文字是共存而不可分离的。恰恰因为他用文学的方法表现了个人问题,因此能够进入从自我出发探索社会问题的精神脉络,也因此能够呈现政治信仰的发展历程。政治信仰也恰恰因为是根据个人的情感而建立起来的,因此显得稳定有力。文学和政治并没有区别开来,反而构成了互助的关系。
王统照的书评还提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他指出瞿秋白的文章表达情感,因此获得真实性,更让读者受刺激。瞿秋白的文章具有感染力,对读者产生叙述也来自他自己的文学爱好。更重要的是1935年中国文学界广泛流行的对散文理解。当时周作人的散文和林语堂的小品文受人瞩目,引发了一些争论。在1935 年的这种情况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本身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个体性和政治信仰已没有天然的连带关系,不再是1920 年代的文化形态了。郁达夫的理解反映出从1920 年代到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对散文理解的变迁。
但即便这样,还可以注意郁达夫论述的细节。郁达夫所说的个性其实还包含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郁达夫似乎承认五四时期出现的“个性”容纳了杂糅内容。个性的杂糅性正是五四时期文学的特点之一。虽然1930 年代的散文理解中瞿秋白的作品没有适当的位置,但回到五四时期的历史现场,瞿秋白的散文也正好证实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丰富杂糅性。就此意义上,用文学的方法叙述瞿秋白精神脉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给后世留下了五四特定时期中国新文学开端期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