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刘勰的文心与佛性
李建中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今天这个隆重的赠书仪式上,面对三千多万字的《星云大师全集》,我想到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刘勰。讨论“文心与佛性”,不得不从我最熟悉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说起。我在大学任教四十余年,记不清读过多少遍《文心雕龙》,更记不清讲过多少遍《文心雕龙》。每每谈到刘勰的生平行迹,我总是会以“始于寺庙,终于寺庙”来概括其一生。青年刘勰依沙门僧祐十余年,《文心雕龙》即撰写于此时期。到了人生暮年,刘勰削发为僧,皈依佛门。我一直认为,刘勰这一生,是同时生活在三个世界里——文的世界、儒的世界和佛的世界。其中“佛的世界”之于刘勰的意义,和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星云大师以及佛光山有诸多相通之处。
一、上定林寺与佛光山
首先,我想来谈谈两个既异时异地却又彼此相连的空间——千年前刘勰生活的上定林寺与今天的佛光山。
2000 年我第一次参访佛光山,初到便为其所震撼:整个佛光山宛若一个佛教的帝国。佛光山不仅仅是一个供信徒参拜祈愿之处,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生活栖居之处。生活在那里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一切井然有序。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这也让我联想到了刘勰与上定林寺。上定林对于年轻的刘勰来讲,是帮助他解决了人生的三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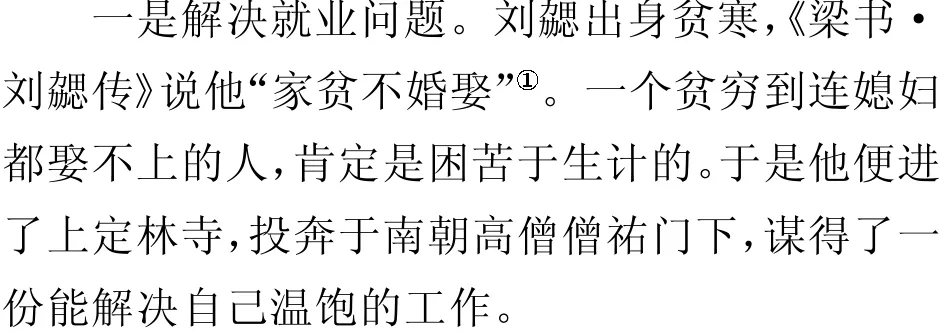

我曾向我们学校一位任职于政协的老师提过一个建议,建议他开政协会议时提交一份提案:多建一些寺庙,以缓解我们大学生就业压力。这句话听来像是一个玩笑,但我是认真的。当年我们一行人初到佛光山的时候,接待我们的就是一位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她和今天在座的同学们一样,穿着打扮并无二样。她告诉我们这就是她的职业,佛光山就是她工作的地方。她领着我们参观了佛光山,从她的讲解中可以感受到她是非常熟悉和了解佛光山以及佛教文化的。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人间佛教”,看到了这位台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如何在星云大师的世界里发挥着自己的专业特长。她以此为本职工作,与那些出入于现代写字楼的白领并无差别,与当年在上定林寺依沙门僧祐的刘彦和更无差别:既是自食其力,也是自得其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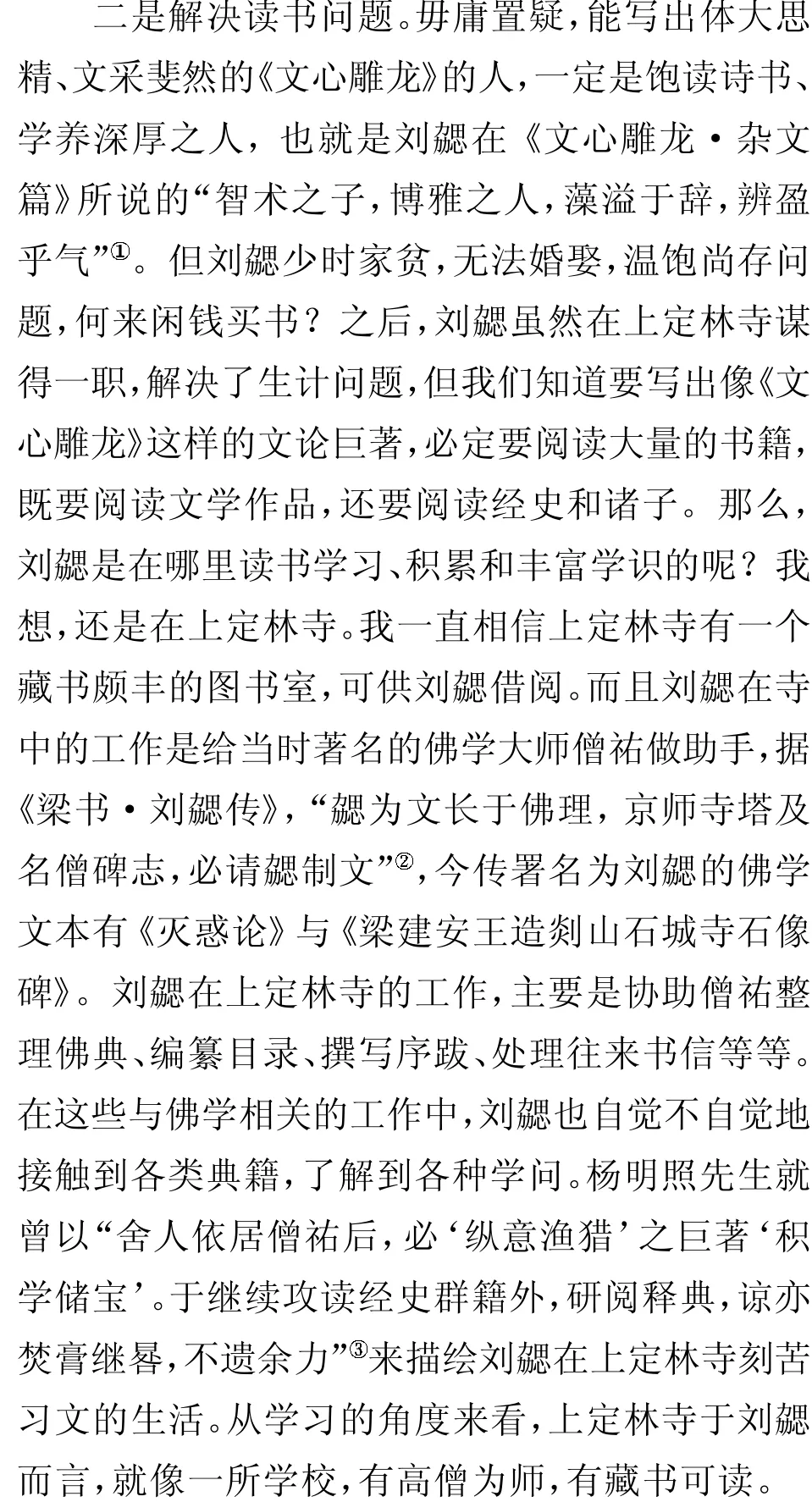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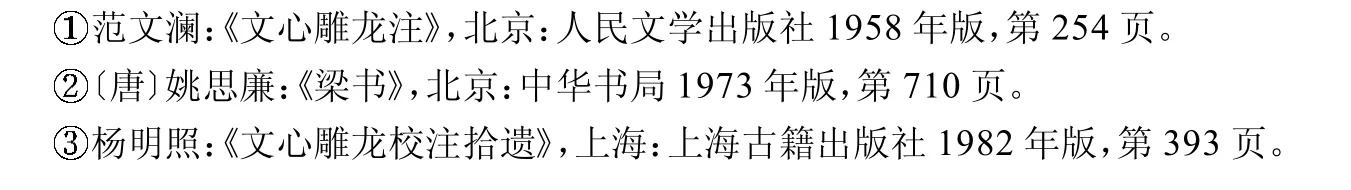
佛光山也是如此。佛光山也是藏书丰富,高僧云集,俨然是一所佛教界的高等学府。佛光山本身就办有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涵盖了所有阶段的教育。佛光山于各种层次,以各种形式来办学育人,尤其是为许多和刘勰一样清贫而好学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读书学习的平台。这既是佛教走向人间的体现,也是佛教精神的弘扬。
三是解决社交问题。前面谈到,刘勰一生同时生活在三个世界,其中“儒的世界”是建功立业、经世济民的世界。年轻时代的刘勰,其志并不在桑门而是在魏阙,他并不甘于一辈子在上定林寺伴着暮鼓晨钟和青灯古卷。他也希望自己能遇一伯乐,受其重用。而刘勰出身贫寒,又如何识得当时的权贵之士呢?是上定林寺给他解决了第三个问题。当时的南朝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从文士到武将,信佛者众多,达官贵人、鸿儒俊彦经常出入寺庙,著名的寺庙,比如上定林寺就相当于一个高级沙龙。在这个高级沙龙中,刘勰自然也有机会结识当时的达官显贵,为自己日后的仕途做好铺垫,打下基础。
佛光山也是一个高级沙龙,也是一个名流交往之处。佛光山以它博大的爱吸引着各阶层的来访者,自然也包含各个领域的社会名流。当然,我们不一定就要以一种谋求功名或“终南捷径”式的心态去看待这种“沙龙”功能。换言之,正是因为星云大师提出了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人间佛教”,所以佛光山才能对众生有着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人文可以化成,人间佛教也可以化成:化成一个大同世界。
刚才来会场时,我在电梯里面与妙海法师相遇,法师递给我她的名片,名片上“妙海法师”的法号后面写着三个字——“二当家”。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如果说,“妙海法师”的法号给人一种超凡脱俗、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二当家”三个字又机智幽默地消解了这种距离感,让人体味到一种人间的烟火味。我想这也是“人间佛教”的一种味道吧。不把佛教抽象成形而上的东西,而是让佛教贴近凡人生活,给人以亲切与欢喜,给人以既“妙”且“凡”、“凡”中见“妙”、“妙”“凡”一体之感。这正如当年的上定林寺,既实实在在地帮助寒门刘勰解决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又实实在在地为文论家刘勰以一己之文心精雕文龙提供了“妙凡”之助。
二、“字字无佛”抑或“通篇有佛”
上定林寺与佛光山,在时空中相互穿越;上定林寺撰写《文心雕龙》的刘勰,与佛光山写下千万言巨著的星云大师,在精神层面更是相通的:既有文心亦有佛性。我觉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体现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内涵,与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有诸多可通约之处。
刘勰生活在一个崇佛的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是笃信佛教的。我们知道晚唐杜牧有两句很有名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根据汤用彤先生的考证,南朝时仅仅是建康就超过了四百八十寺,京城内外寺庙的总数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所以在这样一个佛学很盛的时代,青年刘勰不可能不受到佛学的影响,尤其是他自己还有在寺庙生活十多年的经历。
然而,在《文心雕龙》大量的理论范畴和术语之中,我们又很难找到与佛学相关的概念。如果硬要从关键词(术语、概念、范畴、命题)上找佛学的痕迹,那也就是《论说》篇里面谈到玄学论著的时候曾说道:“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但是刘勰这里所说的“般若之绝境”不是在讨论佛学,更不是在讨论文学理论或者说佛教诗学,而是在讲僧肇的一个玄学命题:“非有非无论”。因为这段文字的前面谈到西晋玄学,就是元康玄学的“有无之争”,裴頠和王衍,刘勰就说,这个“崇有”和“本无”都有偏颇,正确的道理其实就是僧肇的“非有非无论”,也就是“般若之绝境”。刘勰在这里用的是佛学词汇,但讨论的却是玄学问题,是西晋元康玄学论争的一个例证。换言之,刘勰使用“般若之绝境”这个带有明显佛学痕迹的命题,不是要阐释佛学思想而是要解答玄学问题,因此不能据此来判断刘勰《文心雕龙》里面有佛教思想。所以一直以来,龙学界关于《文心雕龙》到底有没有佛学思想是有争议的。
我以为,从字面上看《文心雕龙》是“字字无佛”,但就其内在理路而言《文心雕龙》则是“通篇有佛”。如果说儒、道思想以一种有言之教的方式影响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的言说方式,那么佛学思想则是一种无言之教,是刘勰融通于文心之中的一种无言之说。因为生活在寺庙之中,又以僧祐为师,关于佛的一切于他而言都是习以为常。佛学文化和思想已经深入到刘勰的精神骨髓之中,潜藏在他的思维和灵魂深处。而这种潜在的东西,往往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去产生影响,并不需要通过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在《文心雕龙》中我们看似找不到任何佛学的痕迹,但是你只要用心去读,你就会发现,大到篇章结构,小到字里行间,都是能读出一种若有若无的佛学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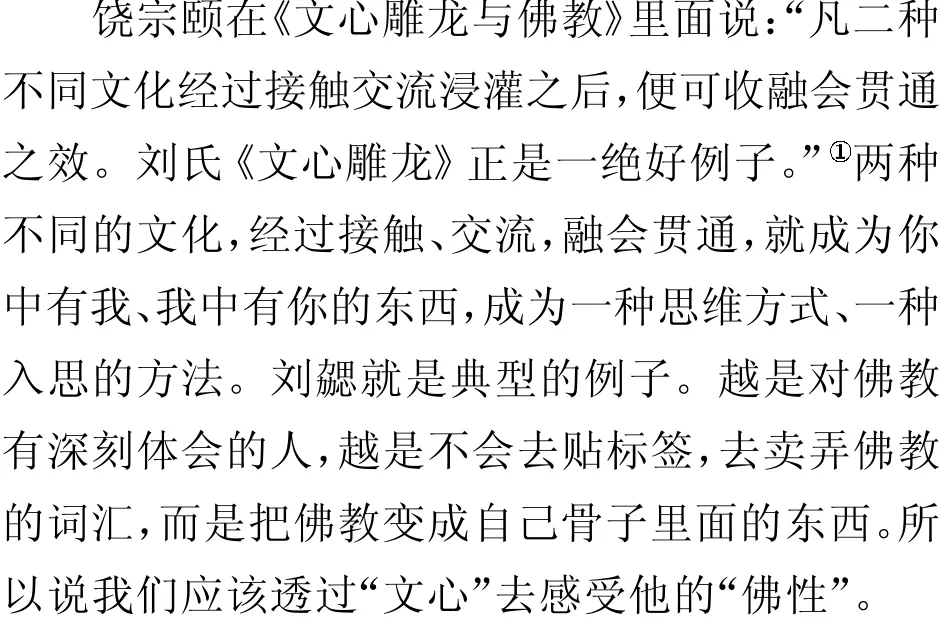
说到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这种无言的佛性,我又不禁想到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曾提出当今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就是“失语症”。“失语症”本来是一个医学词汇,简单来说就是指本来会说话的人,后来丧失了语言功能。曹顺庆教授借这个词用来形容文学理论研究,他认为当前的中国文论研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我们在表达和解读文学时都是在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比如形式与内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旦离开了西方的文论话语,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说话,就会变成一个得了失语症的“哑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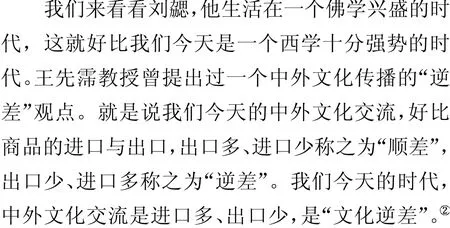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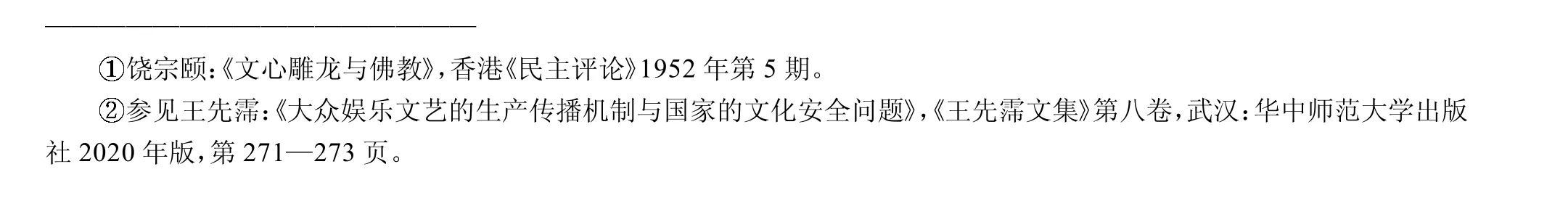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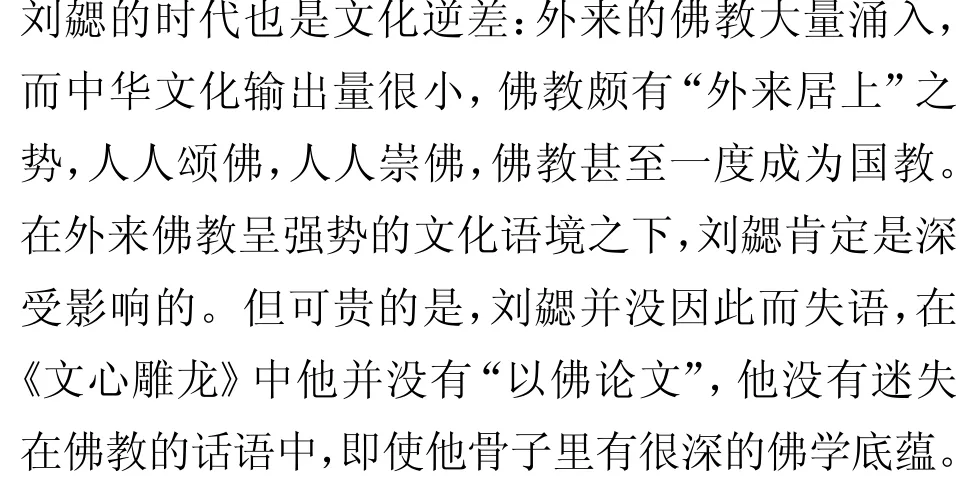
同处“文化逆差”的当下中国,如果说谁人不受外来文化影响无异于痴人说梦。任何时代,只要不是夜郎自大,不是闭关锁国,本土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以及中外文化相互交流自然是大好事。问题是,如果这种影响和交流只是停留在术语和概念的浅表层面,则既不能得“佛性”之精髓又无助于本土之“文心”。就当下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而言,太多的论文和论著,热衷于搬运甚至堆砌西方哲学和文论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或一厢情愿或削足适履或强拉硬扯式的施之于本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其结果或者是隔靴搔痒,或者是水土不服,或者是强制阐释。
置身于当下的中国文化语境,回望1500 年前南朝的刘勰,不禁感慨万千。青年刘勰的大环境(南朝)和小环境(上定林寺)都是很佛学的,但刘勰并没有失语,更没有崇佛或者佞佛,而是既能“振叶寻根”式的守护文化根柢,又能“观澜溯源”式的海纳万川之水;既能“释名章义”式的诠解本土文论之名,又能“敷理举统”式的铺叙诸家文化之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心雕龙》的“字字无佛”与“篇篇有佛”,刘勰的“佛性”与“文心”的完满融和,有着重要的现代启示和当下意义。青年刘勰对华夏文明的深情和大爱,对本土文化及文论关键词的深刻理解和深度阐释,是很值得我们深思考并借鉴的。只有在创造性转换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只有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才能真正走出“失语”之困境,改变“文化逆差”之窘途,开创“文化复兴”之新局。
三、“文心”深处见“佛性”
再回到文心与佛性这个话题上。既然说《文心雕龙》是“通篇有佛”,那么这种“佛性”又潜伏在“文心”的哪些方面呢?
刘勰深受佛学影响,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文心雕龙》的体系性。在刘勰之前和刘勰之后,做文学批评的人很多,有的文学批评家的水平并不比刘勰低。比如,钟嵘就比刘勰更有才气,读钟嵥的文章,能感觉到钟嵥是个大才子,《诗品》写得既灵气飞扬又自然天成,真正是寓目则书,妙手著春。相比之下,《文心雕龙》则略显雕琢。可是才气超过刘勰的钟嵘,作为文论家的地位却在刘勰之下,原因就在于《诗品》的体系性没有达到《文心雕龙》的高度。也就是说,在刘勰那个时代,或者在他前后的人,才气之大,思想之深刻,文字之优美,超过刘勰的大有人在,但是著作之体大精深,理论之自成体系,却无人能与刘勰相媲美。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人能像刘勰那样精通佛教。进一步说,没有人能像刘勰那样,把佛教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真正的融会贯通,并天衣无缝地应用到自己的文学理论之中去。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有点像陈寅恪先生。陈先生精通西学,在国外读了很多大学,他用文言文写的文章中也有西方的东西,但中西文化在陈寅恪的文章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所以说,仅仅从《文心雕龙》的体大精深,我们就可以看出佛学对刘想的影响。
首先,从其理论结构的体系来看。一个佛学的经典大体上有三个要素:界品,问论,论末附偈。界品就是门类、种类。佛学经典的“界品”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里面显示为文体论。从第6 篇《明诗》到第25 篇《书记》全部是文体论,相当于佛学的界品。“问论”就是在一问一答的辩难之中来彰明佛理,特别是禅宗,善于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文心雕龙》第26 篇《神思》以下,都类似于佛教的“问论”。佛学著作有论末附偈,刘知几《史通·论赞》里讲:“篇终有赞,始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在每一篇的后面有一个“赞”,这个“赞”是偈语,也就是佛理诗,我们知道六祖惠能就是以他的一篇偈语出名的。佛教著作的篇终有一个偈语形式的赞,这就是《文心雕龙》“赞曰”的来源。前有界品,中有问论,而且每一篇都有赞即偈语,这就是佛学经典的组织方式。先秦诸子也有一些哲学论文有较强的思辨性,比如《庄子·齐物论》里面就有很抽象的哲理。只是《庄子》一书像《齐物论》这样思辨而严谨的篇章并不多,除了内七篇,外、杂诸篇都是随心所欲、随人俯仰之“卮言”,远没有达到《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系统性和谨严度。
其次,从其书写的体系来看。佛教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带数释。佛教的一些关键词都是数词后面跟名词,如三世、三界、三法、三宝、三藏、四谛、五蕴、八戒、六十四戒、三百六十六戒、十二因缘,等等。为什么使用数字呢?因为数理化的表述使得要表达的内容层次清楚,条理畅明。所以佛教经常用一些数字的东西,大到对宇宙世界的划分,小到它的一些很细节化的戒律,都用数字来表示。刘勰整理过很多佛典,阅读过大量的佛经,佛教的一些方法对他有很深的影响,自然成为他书写的方法之一。饶宗颐把这种带数释的方法分成三种:单层,双层,多层。单层的如《知音》篇的“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宗经》篇的“体有六义”等;双层的如《体性》篇中先说“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然后又对八种风格的具体内容作了阐述;多层的则如《练字》篇中,第一层先谈选字的四个问题“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然后进入第二层对各个问题进行阐释,在阐释中又通过举例说明进入到第三层,三层过后刘勰再以评价进入到第四层。可以说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书写中,佛学思维方式及言说方式融通为一种精确的数字表达。
再者,佛教的融通还体现在刘勰对“文学”这一中国文论核心关键词的解释上。我们常说章太炎先生“以文字为主”的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是一种泛文学观.他认为“凡著竹帛者”都可以进入“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文”的学问就是“文学”。这种文学观已经很大了。可是刘勰的文学观比太炎先生的文学观的范围还要大。他认为什么是文学呢?其实细读《文心雕龙·原道》篇就可以发现,在刘勰看来,天有天文,地有地文,人有人文。而天上的太阳、月亮、云彩可以是文学的对象,地上的山川、草木、虫鱼可以是文学的对象,而关于“人”的一切(文字、语言、体貌、精神、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等)自然更是文学的对象。“文”是无所不包的,“文学”是无所不有的。
综合而论,刘勰潜于“文心”的内在“佛性”,恰是与佛光山“人间佛教”的佛理相通相融的。人间佛教所强调的就是佛法应该走入人间,佛法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要落实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上,只有这样佛法才有意义。与文心中的佛性一样,都体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力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书写中体现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与星云大师以及星云大师包融其中的文学创作精神相暗合,二者都是极其圆融极其透脱的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