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中被背叛的女人:张爱玲《封锁》对莫泊桑《羊脂球》的多重反转
〔日〕藤井省三
(东京大学 文学部,日本 东京113-8654)
一、《封锁》——发生于反转之城上海的反转爱情
1937 年7 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虽在首战中浴血奋战却仍不敌日军攻势。11 月上海、12 月南京,1938 年10 月武汉、广州等从沿海到内陆的主要城市均已被日军占领。美英法所有主权的上海租界区相对于广大的沦陷区来说俨然成为一座孤岛,但随着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上海租界也最终被日军接管。从1941 年底到1942年初,日军借口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连续在南京路、浙江路等闹市区和闸北、杨树浦等居民稠密地区实行封锁,严禁市民出入。刘惠吾所编《上海近代史》中有如下叙述:


1943 年11 月,张爱玲(Eileen Chang,1920—1995)以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为背景,在《天地》月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封锁》。故事发生在因日军突如其来的封锁措施而长时间滞留原地的电车里,讲述了一等车厢中银行高级会计吕宗桢向大学英语助教吴翠远搭话而生出情愫,由此二人坠入情网,然而随着封锁的解除,吕宗桢却弃吴翠远而去。
滞留原地的电车内,两人之间的感情急速升温。吕宗桢抛出一句“我打算重新结婚”,其后又改变主意,说:“我不能够离婚。我得顾全孩子们的幸福。我大女儿今年十三岁了,才考进了中学,成绩很不错。”不由叹道:“我年纪也太大了。我已经三十五了。”对此,吴翠远回应道:“其实,照现在的眼光看来,那倒也不算大。”当吕问她“你……几岁?”时,她低下头去,回




二、《羊脂球》中反转的报纸琐闻




如前所述,《羊脂球》和《封锁》的情节框架相同,都讲述了在因外国占领军而长时间滞留原地的车中,男性觊觎车中女性的故事。《羊脂球》中,以妓女羊脂球为首的所有人物都表露出了对普鲁士军的憎恶。而向妓女投射的感情,不仅包括占领军军官的欲情,更包含了为求再次启程而希望妓女献身的马车上同乘者们的丑恶又滑稽的利己心。
与此相对,许是因为《封锁》执笔和发表于日军占领上海时期,作品中并没有涉及人物对日本军的憎恨。但是,对女主人公吴翠远产生想法的男性不是日本军官,而是和吴相同的上海人,以及吕宗桢在封锁解除后马上忘却自己先前爱的告白,这两点都体现出该作与《羊脂球》的决定性差异。《羊脂球》中的贵族和资本家在妓女牺牲自己而满足占领军官的淫欲之后,非但没有忘却此事,反而对她的妓女身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厌恶。如此看来,《封锁》中存在着对《羊脂球》两重、甚至三重的反转。不仅如此,给予张爱玲这一反转构想的正是《羊脂球》里马车再次启程后紧接着的那一节。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因妓女的献身而得以再次启程的一行人,在马车中完全无视她的存在,一边暗暗地背地里议论、一边吃着自备的食物。而四五天前,逃出普鲁士军占领下的卢昂城的第一天,因路面积雪、车轮损坏致使他们深夜才到达多特的旅馆。一路上,妓女分明拿出自己储备的三天量的口粮和葡萄酒与同伴们分享,让他们免于饥饿。但是到了重新出发的那天,没有一个人分东西给她吃。悲哀的妓女羊脂球因屈辱寂寞和饥饿而抽泣……
熟悉《封锁》的读者,从这个充满欺骗卑劣的车内餐会描写中,想必会注意到以下一节的内容。


奶酪上颠倒印着的“琐闻”究竟是什么?对于笔者的疑问,法国文学研究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广播大学教授野崎欢作出了解释:
小说此处提到的“琐闻”,应是报纸的“栏”的标题(即用来表示新闻报道的类型标题)。实际是在报道“社会新闻”,用“琐闻”(faits divers)作为标题。将记录市井杂闻的多篇报道刊登在一起,是当时新闻报纸的风格。
因此,包裹乳酪干的是新闻中最粗俗的“社会新闻”,而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闻。从这一点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讽刺,即《羊脂球》故事本身刊登在“琐闻栏”(或许连“琐闻栏”都登不上),不过是不值一提的人生片断罢了。
初读太田先生的新译,虽认为是一部精心译就的好译本,但是否真的有必要在“琐闻”两字上加着重号(原文并未采用斜体而是加了括号)呢?依我拙见,译文中“琐闻”二字是否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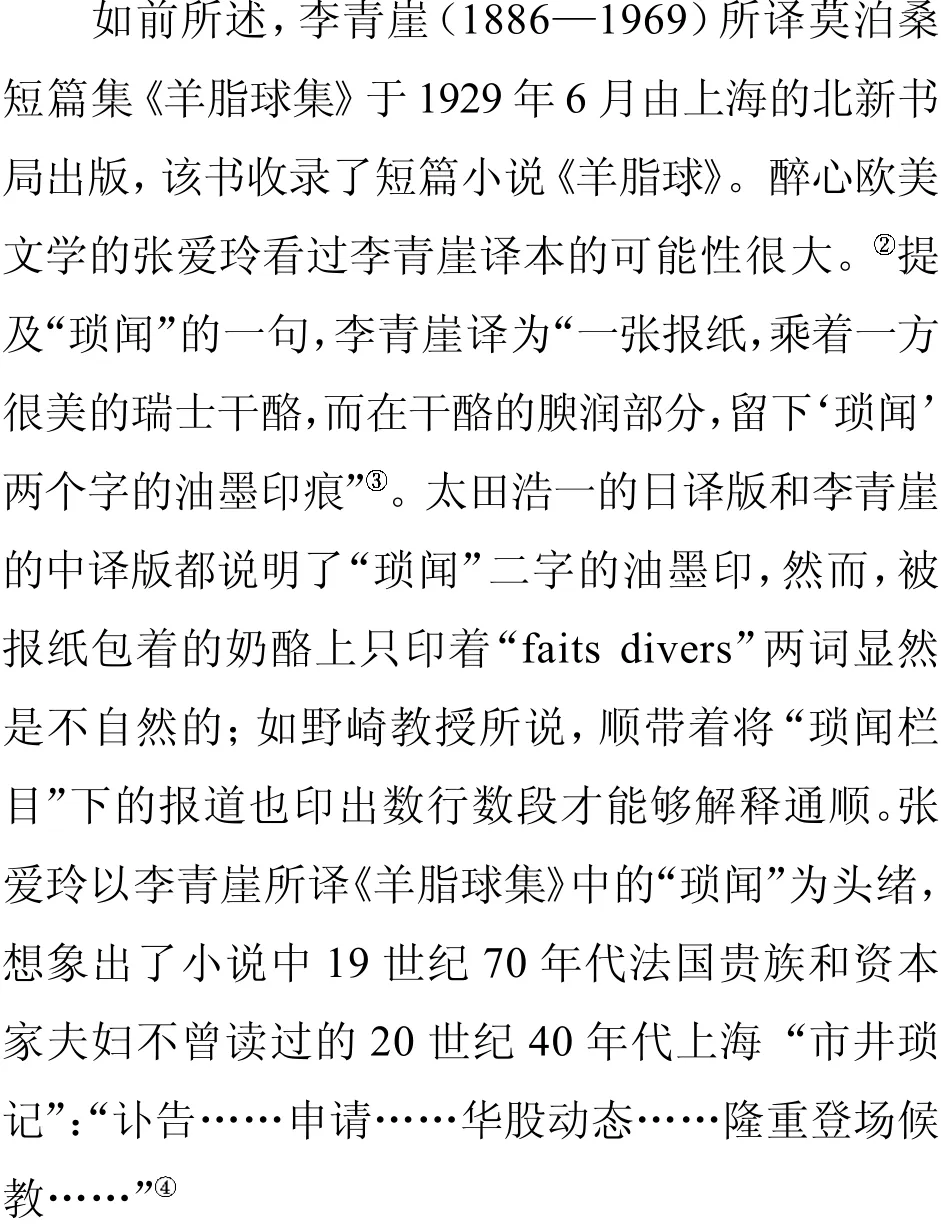
三、《封锁》对《羊脂球》的三重反转
莫泊桑的《羊脂球》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反转——面对占领军仍有强烈的自尊及爱国之心、富有同胞之爱的妓女遭到贵族及资本家们的背叛而陷于凄凉境地。反印在瑞士奶酪上的报纸琐闻栏目,正是对妓女反转的悲惨境地的隐喻。
张爱玲构思《封锁》时,不仅从《羊脂球》中有关奶酪上反印着报纸琐记的情节中获得灵感,还对其情节构造进行了多次反转。第一次反转恐怕是为了逃避日军检阅,防止小说被禁发,作者在小说中隐去了封锁的主谋者日本占领军的身影。全文谈及日军的只有“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这一句。这一句描述带同一起回头看向卡车的男女主人公的脸“异常接近”,起到了“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效果,发挥了让“他们恋爱着了”的作用。叙述者利用日军短时间的登场,将其转化为恋爱剧情里的大型催化工具。作者借此向读者明示了小说《封锁》和《羊脂球》一样以外国军占领下的城市为舞台,暗示了两篇作品间的影响关系,并用叙述技巧躲开了占领军的检阅。
第二重反转是上文所提到的“老实人”吕宗桢突如其来的人格变化,并且该反转循环往复着进行——吕宗桢由于十分厌恶妻子的外甥而做出车中调情的轻浮举止,虽然在外甥离开后立马变回“老实人”,但他还是在和吴翠远的对话中陷入爱河,只是封锁解除的同时就将此前情话抛诸脑后。这一系列不断重复的反转和《羊脂球》中贵族、资本家一以贯之的狡猾与歧视心理形成了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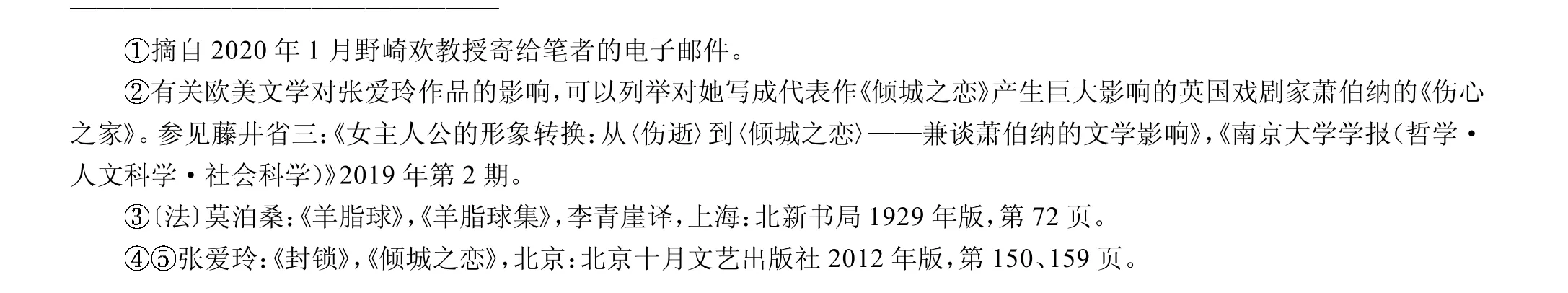
张爱玲受《羊脂球》启发的同时,在《封锁》中实现了对该作的三次反转。凭借这三次反转,作者描绘了不合情理的封锁背景下一段短暂而耀眼的恋爱美梦,也向熟悉莫泊桑的读者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不正当行为。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发生的一场不合情理的美梦,《封锁》不单是一部恋爱小说,还潜藏着反战和爱国的主题。就其表现的多样性和情节的多属性而言,《封锁》称得上是张爱玲文学的代表作。
《封锁》从头至尾将舞台设置在电车中,小说始于对电车司机的描写,并在他的怒骂声中走向结束。《羊脂球》将舞台设置在主人公们同乘的马车和同住的旅馆两个空间里,小说中也写有一个马车夫。两相对比,前者中电车司机的存在感要强烈得多。以下是《封锁》的开头和结尾:
(开头)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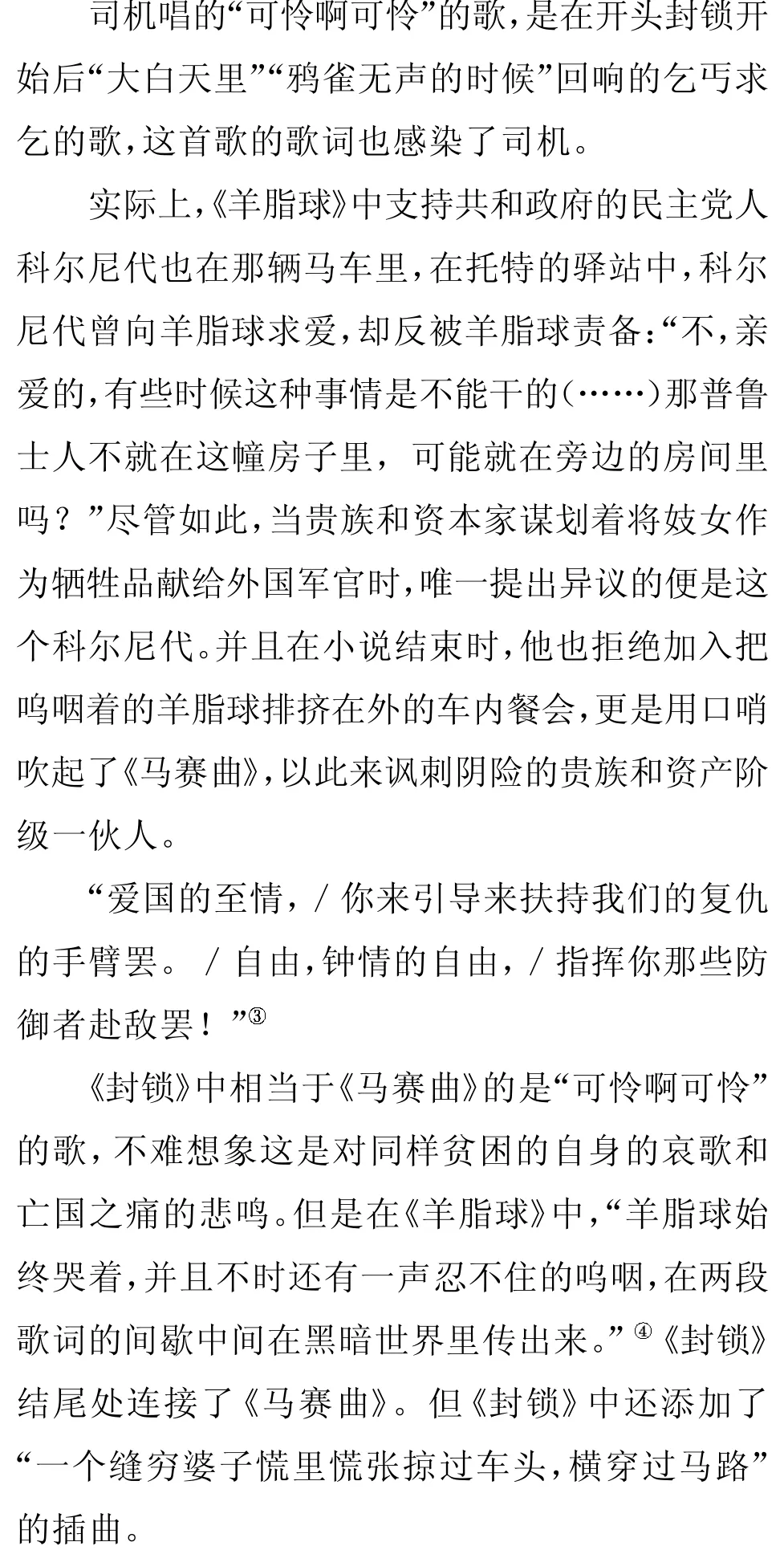

四、电车前横穿马路的老婆子——鲁迅《一件小事》的影子
张爱玲为何不将《封锁》的故事结束于“可怜啊可怜!”的歌声中,而是新加了一位“缝穷婆子”作为第四重的反转呢?看到这位在有轨电车前横穿马路的老婆子,应该会有不少读者联想到鲁迅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1912 年12 月发表)。在“大北风刮得正猛”的北京,“我”搭乘人力车去上班,车子撞到了一位突然在车前横穿马路的“衣服都很破烂”的老婆子。“我”甚至怀疑这是老婆子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满身灰尘的车夫却对老婆子温柔以待。“我”被其坚定的善意所打动,反省了自身对他人的不信任,发出了如下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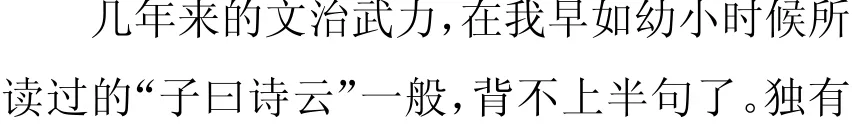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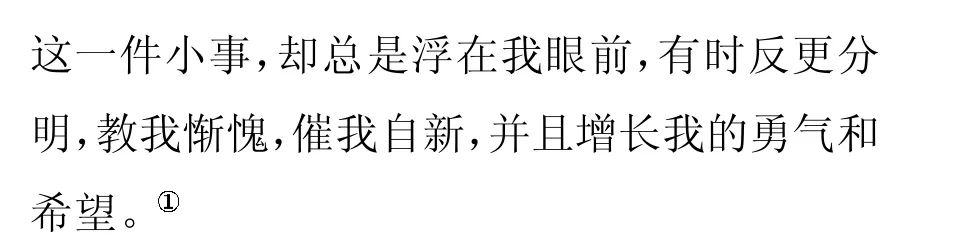

关于《一件小事》,笔者认为“以这些世间常有的事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中,鲁迅想表达的是,自以杂志《新生》(日本留学期间创办的文艺杂志)为阵地发起的文学运动开始以来,始终流淌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对世间万物不灭的希望。”不过,许是张爱玲对该作抱有别样的看法,例如,不管是在“大北风刮得正猛”的北京,还是在“太阳滚热地晒在背脊上”的上海,老婆子都像是目睹了一场“不合情理的梦”。她也由此产生了上述诸如此类的悠远遐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