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与刘基之交往及心态述考
黄仕忠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275)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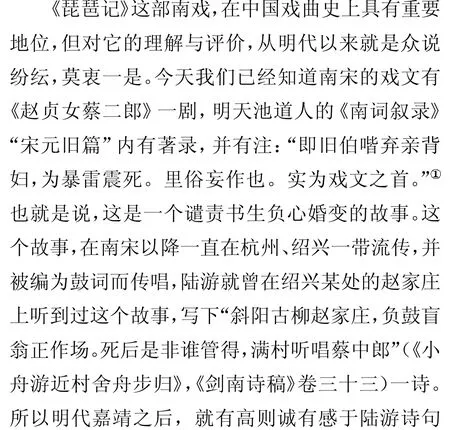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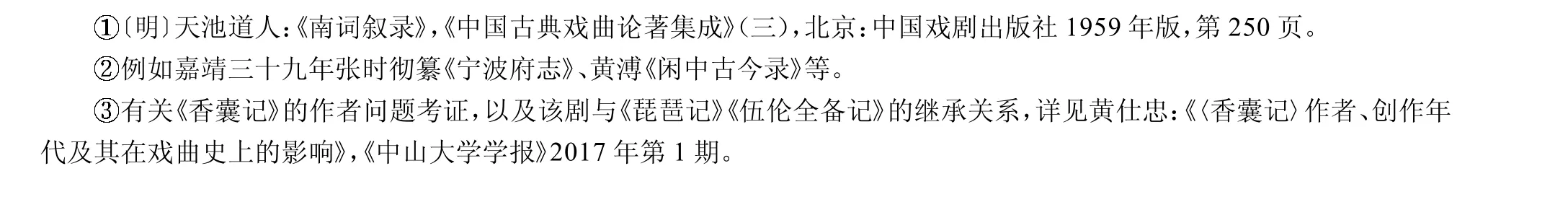
我对刘基没有研究,但对刘基的友人高明(字则诚)及《琵琶记》曾作过专题的研讨。所以本文主要谈谈高明与刘基的交往,以及他们在元末这一特定时期的心态变化。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才留意到《琵琶记》,通过反复的阅读与不同版本的比对,从渊源最早的版本的整体观感出发,去寻找“作者原义”,进而从晚明的修订版本的比较中,体察早期版本可见的那种“原义”,是如何通过句词的调整而被消解和忽略的,又通过增加哪些表述,让另一些意义得以凸显和固化,从而试图将“作者原义”与读者理解、接受过程中的“理解义”和“引申义”区分开来。古人称“曲无定本”,明代人的改动,代表了明人的认知与明代演剧及观众的需求,但毕竟与作者原本要表达的内容有其距离。同时,我又从高则诚本人的经历、遗存的诗文中寻找其思想变化的痕迹,并将它们与剧中所表达的意蕴结合起来考察,寻找两者之间的关联之处。结果,我得出了一个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结论:高则诚撰写《琵琶记》的初衷,是要说明为官一途是充满忧患的,蔡伯喈的遭际,实际上是一幕因为赴试做官而导致的悲剧!也许,高则诚本人不一定有我所说这样明确的“创作动机”,要用《琵琶记》来表达这个“主题”,但我确信在《琵琶记》中无疑倾注了高则诚个人的这种感受。
我的解读方式,是把剧中人物、历史人物、剧本作者这三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第一,剧中男主角蔡伯喈,是历史实有的名人,但宋代南戏中的“蔡二郎”,最初可能并不是历史上的蔡伯喈,据学者推测,其中可能经过了由二郎而中郎再附会到蔡中郎这样一个过程。高明在至正五年(1345)以《春秋》中进士,他是一个精通历史的人,对于《后汉书》中的蔡伯喈应当是非常熟悉的。而《琵琶记》的核心故事,可以说与历史人物毫无关系,例如汉代没有科举状元,蔡伯喈有叔伯兄弟,并非孤身。如果单纯是为了翻案,高明便没有必要去写一个蔡伯喈科举中状元的故事。但他改变了原有故事的线索与结局,一定有潜在的想要表达的内容,只是高明本人没有直接作出说明,甚至也无法直接言说。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再平心静气地看《琵琶记》,发现蔡伯喈最初其实为了在家中尽孝而无意于功名。但因为社会一般观念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以,他父亲认为尽管只有一个儿子,但只要儿子取得功名,自己已经一把年纪,死也甘心。邻居张大公来劝,以为国家有事,正当作为。只有净扮的蔡婆,用调笑的口气,说到可能的不良结果。而蔡伯喈自信取功名如拾草芥,结果也确实如此。只是既入官场,便当尽忠,便不再由自己掌握命运,在皇帝和丞相的“好意”下,蔡伯喈赘入相府,便无了自由,时刻处在夹缝之中:
【二犯渔家傲】思量,幼读文章,论事亲为子也须要成模样。真情未讲,怎知道吃尽多磨障?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凰。三被强衷肠说与谁行?埋冤难禁这两厢,这壁厢道咱是个不撑达害羞的乔相识,那壁厢道咱是个不睹是负心的薄幸郎。
【雁渔序】悲伤,鹭序鸳行,怎如乌鸟反哺能终养?谩把金章,绾着紫绶;试问斑衣,今在何方?斑衣罢想,纵然归去,又怕带麻执杖。只为他云梯月殿多劳攘,落得泪雨似珠两鬓霜。
【渔家喜雁灯】几回梦里,忽闻鸡唱。忙惊觉错呼旧妇,同问寝堂上。待朦胧觉来,依然新人凤衾和象床。怎不怨香愁玉无心绪?更思想被他拦挡。教我,怎不悲伤?俺这里欢娱夜宿芙蓉帐,他那里寂寞偏嫌更漏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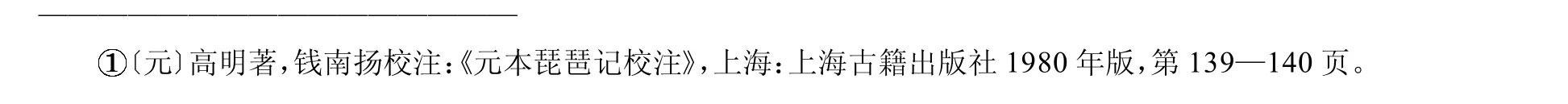
戏曲的构思充满了“假定性”,这样的假定,便是这部“戏”的构建基础,虽然未必能够与“生活的逻辑”无缝贴合,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尽力表达的意思。牛丞相到底是怎样限制着他,官场的情况是怎样地让他觉得不自如,剧中只是通过表现他的犹豫、软弱,表现他在夹缝中的两难处境,来暗示、衬托。也有人批评这类描写还不够具体、缺乏真实,但中国传统的“戏”的构思,并不能用放大镜来看,而应去意会。
无论蔡伯喈的心境是怎么样的,最后的结局,终究是父母双亡,他本人并未能完成孝养与送葬的责任与义务,他无法面对别人的质问,也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谴责。
按戏中的“设定”:父母年过八十,自己成亲两月,无叔伯兄弟,家中离京城又十分辽远,这让独子蔡伯喈不能放心远行。他一旦赴京,家中的灾难便难以避免。后人大多会质疑这样的设定不符合“生活逻辑”、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符合空间实际距离,却很少从作者的角度考虑,为何置这么明显的“漏洞”于不顾。试想作者何尝不知道这些,但“戏”需要假设,必须在假设的前提之下,故事才能得以展开。虽然在“现实主义”成为对文学的主流要求时,那种质疑便抑制不住地要冒出来,不过放到今天玄幻小说、穿越故事盛行的背景下,人们已经充分接受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对内功心法作假定的前提下展开的故事,也大约能够理解高明的处理及苦衷了吧。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就可以理解,可以体悟到,根据蔡伯喈在剧中的表现,《琵琶记》所讲的就是一个因追求功名而导致的悲剧性故事。
更重要的是,在动荡末世,功名或为忧患之始的观念,我不仅从《琵琶记》、在高明的诗作中明白地感受到了,还从他的友人刘基的经历中,看到了共同的倾向。既然如此,高明所抒发的便不仅是他个人的境遇,其实也隐寓了元代末年元蒙统治濒临崩溃的背景下,在大动荡的时局中,士大夫们何以自处的问题,表达了这一拨人共同的心声。
在1980 年代中期,我做这样的解读,说功名为忧患之始,做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但到了今天,大约会有很多人认同我的解读了吧。
我认为,高明所针对的是他所处的那个特殊的时期,只是这个时期在不到十年间就结束了,朱明王朝迅即取代元蒙统治,社会重新走上正轨,并且更多地承接有宋一代的儒家正统,人们便再难以体会高明在元末时期的良苦用心,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二
《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字则诚,一字晦叔,号柔克,又号菜根道人。浙江温州瑞安人。温州别称东嘉,所以后人也称他为高东嘉,或尊之为东嘉先生。所著有《柔克斋集》20 卷,在清初尚存,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著录,此后散佚。今人胡雪冈、张宪文辑校有《高则诚集》,收录他存世的诗文与戏曲,稍称完备。
高明大约生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前后,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岁末(若依公历,当在次年一月),享年约54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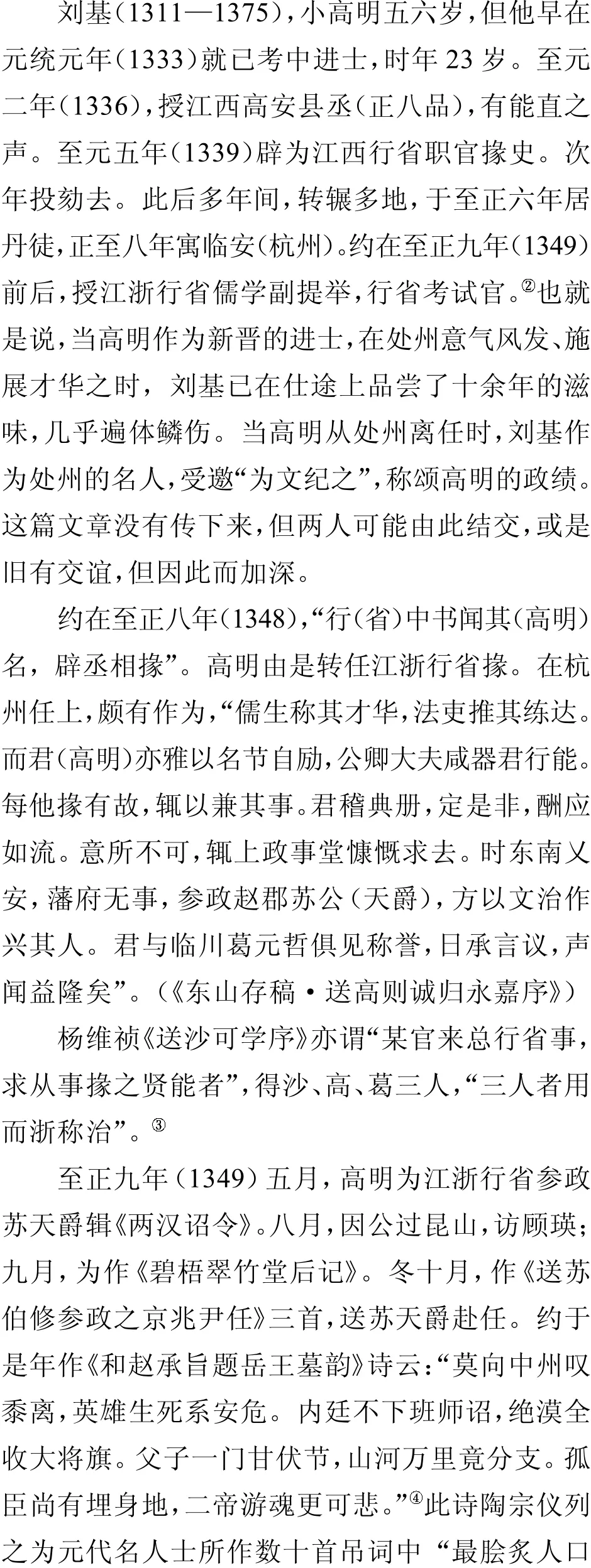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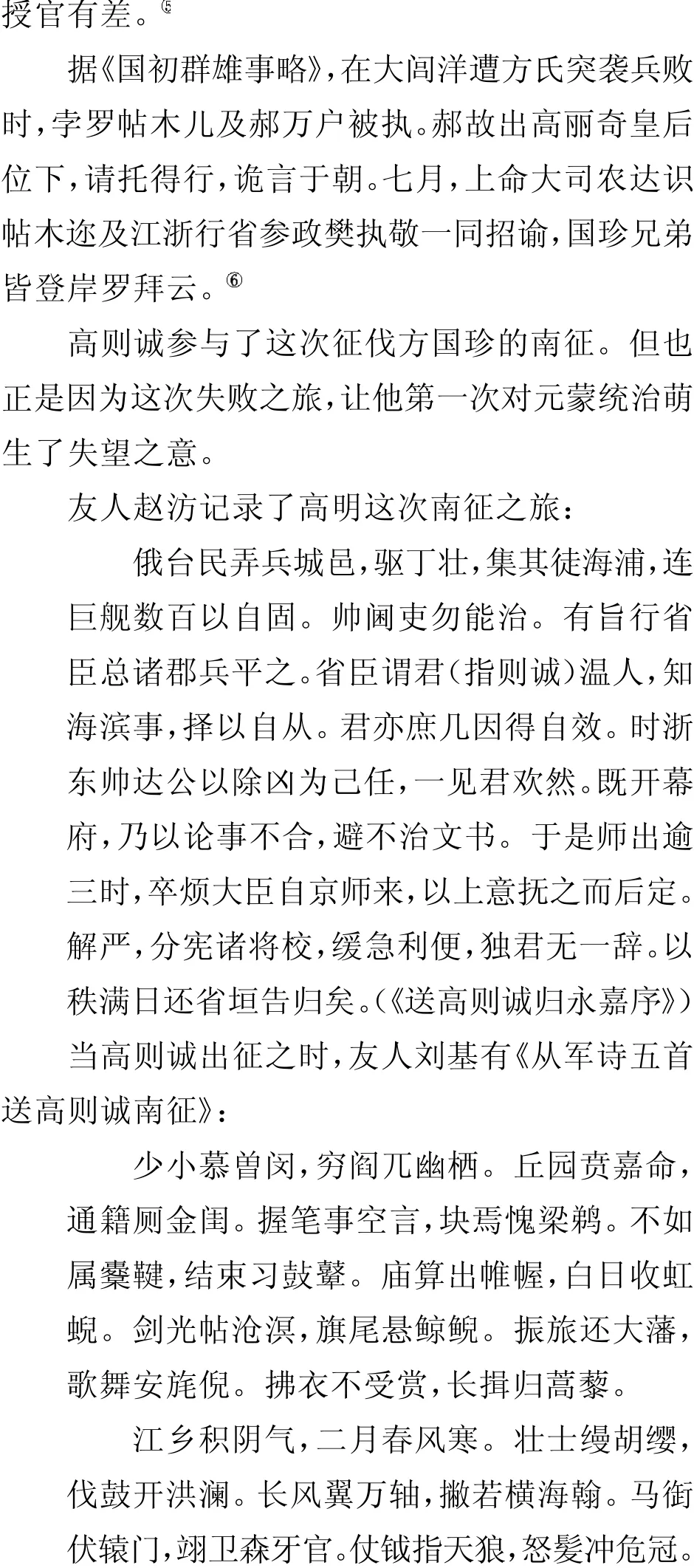



从“二月春风寒”,可知出征时间在本年二月。“用兵非圣意,伐罪乃天讨”“牧羊必除狼,种榖当去草”“抚绥属有望,世世为尧民”,刘基希望除首恶而抚百姓。高则诚所思所想,当与刘基相近。但“既开幕府,乃以论事不合,避不治文书”,可知高明在幕府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高明秩满还省垣日,交游之士以“儒者虽临事不见用,卒能究所守以自旌别为君贺”,以作宽慰。饯别时,高明“笑谓座中曰: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虽然,余方解吏事归,得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城、雁荡诸山,俯涧泉而仰云木,犹不失吾故也时。”(《送高则诚归永嘉序》)公开表露功名宦仕为忧患所系,对自己往日鄙视前辈关于功名“为忧患之始”的看法作了忏悔,并萌生退隐之念。但归隐亦非易事。其乡人即说:“今中原多故,圣天子贤宰相一旦惩膏粱刀笔之敝,尽取才进士而用之,则如吾高君者,虽欲决遁山林,亦将不可得者。”(《送高则诚归永嘉序》)
约至正十二年(1352),高明改调浙东阃幕四明都事(或称“庆元路推官”),“四明狱囚事无验,悉多冤,明治之,操纵允当,囹圄一空,郡称神明。”(弘治府志、嘉靖县志)是年二月,方国珍复叛。高明的好友刘基被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参赞军务,与元帅纳邻哈剌谋筑庆元(宁波)城,以拒方氏侵扰,并且在征剿方国珍的过程中,陷入困境。
据《诚意伯刘公行状》:
方国珍反海上,省宪复举公(刘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公即与元帅纳邻哈剌谋筑庆元等城,贼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谕方冦,复辟公为行省都事,议收复,公建议招捕,以为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斩之,余党胁从诖误,宜从招安议。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镇抚,以公所议请于朝,方氏乃悉其贿,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台俱纳之,准招安,授国珍以官,乃驳公所议以为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罢帖里帖木耳左丞辈,羁管公于绍兴。公发忿恸哭,呕血数升,欲自杀,家人叶性等力沮之。门人穆尔萨曰:“今是非混淆,岂公自经于沟渎之时耶?且太夫人在堂,将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气疾。是后方氏遂横,莫能制,山冗皆从乱如归。(下册,第776 页)
刘基的建议,与送高则诚南征诗所说相则:“建议招捕,以为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斩之,余党胁从诖误,宜从招安议。”即是主张“斩首行动”,除首恶,抚余党。如果元军听从刘基的建议,结局便是不同。方国珍兄弟深知此举击中要害,遂重赂刘基,但刘基“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镇抚以公所议请于朝”,方氏兄弟乃先行派人从海上乘船到燕京,行贿于“省院台”,因朝中各级官员为之说情,元帝乃“准招安,授国珍以官”,反过来颠倒黑白,“乃驳公所议以为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罢帖里帖木耳左丞辈,羁管公于绍兴。”此事对刘基的打击十分巨大,“发忿恸哭,呕血数升”甚至“欲自杀”,幸被家人劝住。


三
至正十五年(1345)前后,高明转任江南行台掾,治所在绍兴。因而与羁管于绍兴的刘基有交集唱和。绍兴所辖范围,包括萧山、诸暨、嵊县、新昌、上虞等地。刘基在绍兴三年中,足迹遍历诸县,而所作诗文亦多。其中在萧山与友朋交往,有不少诗文,交往的有任伯大、包与善、贾性之等人。
这里主要想通过刘基、高明与萧山任氏的交往,来看《琵琶记》初创于萧山的可能性,进而探讨这一群具有共同志向的人,他们对于元末时局的忧思,是否会影响到《琵琶记》的写作。
刘基文集中收有《萧山任氏山堂》一首,称“珍重主人能爱客,衰颜聊复为君酡”(下册,548 页),又有《怡怡山堂记》,称“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别业之所也。……伯大之子元与予善,邀予游而请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上册,149 页)。大略可见他与任氏的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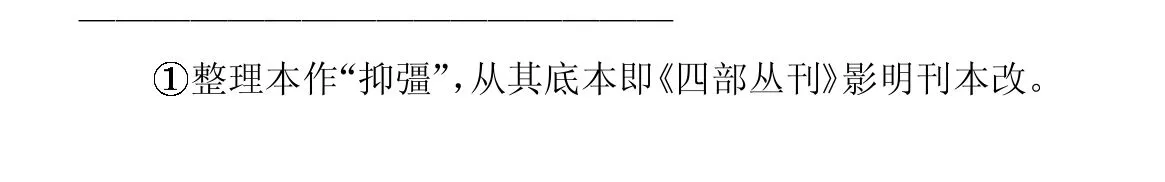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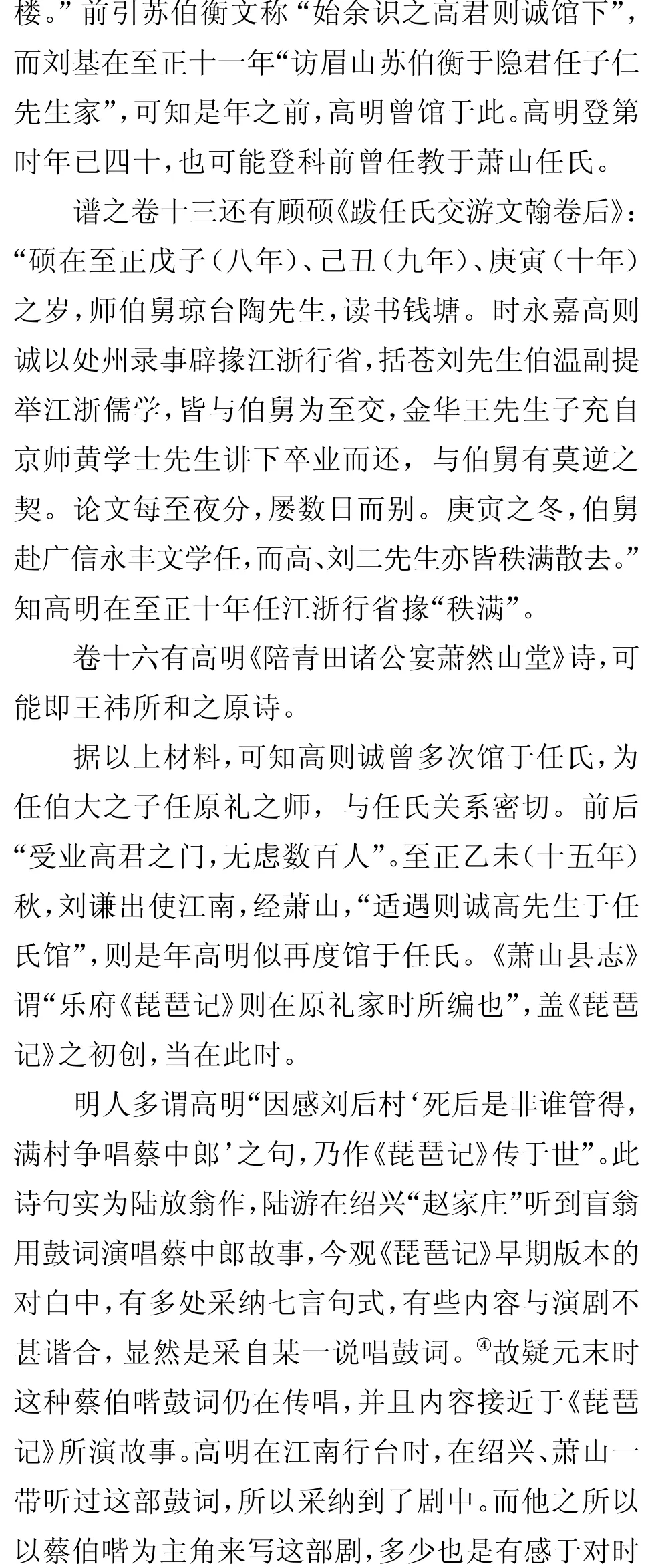





陈麟在至正甲午(十四年),以《易经》贡春官,乙科得中,授予承事郎庆元路慈溪县令(戴良《元中顺大夫秘书监丞陈君墓志铭并序》)。从陈麟的情况,大略可以想见高明在鄞县时的处境。
刘基因力主惩首恶,不愿接受方氏贿赂,故为方国珍所陷,而被羁管软禁于绍兴三年。高明因为南征方国珍,论事不合,避不治文书。他们两位都对方国珍没有好感。这是高明不愿辅助方国珍的原因。刘基在至正十六年二月才得以撤销羁管而返回青田,在隐居三年后,决意投奔朱元璋,遂开辟了新的空间。
高明在仕途上没有经历刘基这样巨大的创伤,但始终未得重用,从江南行台辗转而为国史院典籍官(从七品)、福建行省都事(正七品),最后则未能脱离方氏的势力范围。他虽然号称“隐居”栎社,其实时时在方氏的看管之下,从对陈麟“国珍时时遣人侦之”,可以作印证,此期间还被迫为方氏撰《余姚筑城记》等文,所以内心无限的郁闷宣泄于《琵琶记》一剧中。剧中人蔡伯喈的无奈,多少有着高明自身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