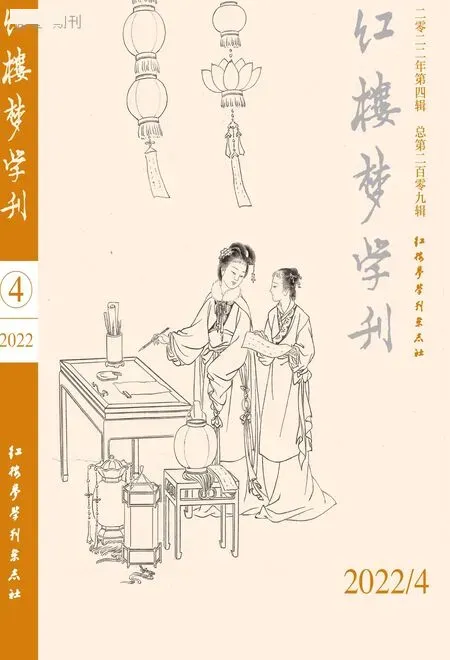“对手方”“中国心”与钱穆批评《红楼梦》
何建委
内容提要:通过《中国文学论丛》,钱穆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与“文心”,包括评论《红楼梦》。他对《红楼梦》整体上持批评态度。这与他始终将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视为“对手方”密不可分。而他这样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发掘“中国心”——中国传统文学有别于西方文学的特性。鉴于此,借助“对手方”视角,考察钱穆对《红楼梦》的批评,探讨其得失及启示,进而窥探背后的文化史意义,显得尤为必要。
钱穆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中国文学论丛》是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结集。对比西方文学,钱穆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与“文心”,与王国维、鲁迅等人盛赞《红楼梦》不同,钱穆对《红楼梦》整体上是持批评态度的。钱穆批评《红楼梦》,与他始终将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研究者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视为“对手方”密不可分。
“对手方”原是经济学范畴的概念,“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首先将这一语词用于人文学术领域,系指学术著述的接受者。他认为,‘对手方’也直接或间接参与专业知识的建构,故学术接受者本身也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因此,“对手方”也可指“学术研究活动中观点互歧、彼此争锋竞逐的对立方”。树立“假想敌”,围绕“对手方”,贯穿了钱穆学术研究的始终。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历史研究方面,钱穆的“对手方”有梁启超、顾颉刚。在清史研究方面,钱穆将梁启超视为“对手方”,针对后者《清代学术概论》,撰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启超视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人不同,钱穆认为黄宗羲也有开山之功。此外,在其代表作《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分析了近世史学三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的得失。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的代表分别是梁启超、顾颉刚。不言而喻,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对手方”就是革新派、科学派。
树立“假想敌”,围绕“对手方”,不仅体现在钱穆的历史研究当中,也体现在他的文学研究当中。而在文学研究方面,钱穆的“对手方”有王国维,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事实上,钱穆阐发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包括对《红楼梦》的批评,始终以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王国维,特别是质疑传统文学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对手方”。而他将这些人视为“对手方”的重要目的,便是一反这些人对传统文学的臧否,进而发掘“中国心”——中国传统文学有别于西方文学的特性以达到为“传统文化”招魂之目的。鉴于此,考察钱穆对《红楼梦》的批评,参照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的相关评述,探讨钱穆批评的得失及启示,进而窥探背后的文化史意义,显得尤为必要。
钱穆对《红楼梦》的内容、思想性评价不高。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一文中,他批评道:
《红楼梦》仅描写当时满洲人家庭之腐败堕落,有感慨,无寄托。虽其金陵十二钗,乃至书中接近五百男女之错综配搭,分别描写,既精致,亦生动。论其文学上之技巧,当堪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伯仲。然作者心胸已狭,即就当时满洲人家庭之由盛转衰,一叶知秋,惊心动魄。雪芹乃满洲人,不问中国事犹可,乃并此亦不关心,而惟儿女私情亭榭兴落,存其胸怀间。结果黛玉既死,宝玉以出家为僧结局。斯则作者之学养,亦即此可见。籍其晚年生活,穷愁潦倒,其所得于中国传统文学之陶冶者,亦仅依稀为一名士才人而止耳。其人如此,则其书可知。较之满洲人初入关之纳兰成德,相去诚逖然远矣。
在这里,钱穆虽然肯定了《红楼梦》的描写“既精致,亦生动”,在文学技巧上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水平堪当,但他认为《红楼梦》“无寄托”,仅仅书写“儿女私情亭榭兴落”,反映“当时满洲人家庭之腐败堕落”而已。因此,在钱穆看来,通过《红楼梦》,可以看出曹雪芹“心胸已狭”,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非常有限,仅仅是“一名士才人”,其境界尚不如纳兰性德,其作品在内容上、思想性上更无法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提并论。批评《红楼梦》之余,钱穆顺带批评了《儿女英雄传》。他认为:
继之有《儿女英雄传》,亦为满人文康作品。书中主人侠女十三妹,似乎针对着大观园中十二金钗之柔弱无能。而何玉凤张金凤同嫁安骥,亦似针对薛宝钗之与林黛玉。故其书亦与《红楼梦》同名金玉缘。而文康与雪芹同是家道中落,其处境亦相似。殆文康心中,只知一曹雪芹,乃存心欲与一争短长,其人之浅薄无聊又可知。即以此两人为例,而此下满族之不能有前途,亦断可知。
关于《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的关系,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已有详细论述。鲁迅说:“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即《儿女英雄传》乃不满《红楼梦》之作,“欲与一争短长”。在鲁迅看来,《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多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满族人,文康是满洲镶红旗人,曹雪芹出身于正白旗包衣世家;且“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然而,鲁迅认为,《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由于一“为理想,为叙他”,一“为写实,为自叙”,“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在鲁迅眼里,《儿女英雄传》虽然“骥又有妻曰张金凤,亦尝为玉凤所拯,乃相睦如姊妹,后各有孕,故此书初名《金玉缘》”,虽然“多立异名,摇曳见态,亦仍为《红楼梦》家数也”,但其主人公“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由此可见,钱穆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与鲁迅有一定的不谋而合之处。他们看法不同在于,鲁迅虽然提及曹雪芹与文康的满族人身份,但并不像钱穆以他们的民族身份而否定他们的著作。当然,他们的最大不同在于,与钱穆整体上批评《红楼梦》相比,鲁迅则整体上肯定《红楼梦》。
与钱穆整体上否定《红楼梦》类似,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陈寅恪亦是整体上否定《红楼梦》。陈寅恪在出版于20世纪50年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
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寅恪读此类书甚少,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
可以看出,与钱穆认可《红楼梦》的描写精致、生动不同,陈寅恪认为,相比西方小说,《红楼梦》等作品的“结构皆甚可议”。同时,与钱穆认可《水浒传》等小说的结构不同,陈寅恪并不认可《水浒传》等小说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批评中国传统文学名著的参照标准是西方小说。然而,对于鲁迅、钱穆否定的《儿女英雄传》,陈寅恪却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在陈寅恪看来,“反红楼梦之作”的《儿女英雄传》却“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除此之外,陈寅恪认为《红楼梦》的细节多有失实之处。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对《儿女英雄传》情有独钟的原因在于:《儿女英雄传》具备陈寅恪所强调的“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庭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这个判断的全部因素,而且均以理想状态描述”,“这部小说中描写的讲人情、重气节的时代气息,唤醒了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回忆”。
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托命之士,钱穆批评《儿女英雄传》作者“浅薄无聊又可知”,且以他和曹雪芹为例,“亦断可知”“此下满族之不能有前途”,而陈寅恪却盛赞《儿女英雄传》结构胜于中国四大名著,欣赏其中浸淫的“吾国旧日社会关系”的理想状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非常耐人寻味。不难得知,钱穆的论述本质上是因人废文,基于曹雪芹与文康的民族身份,进而否定了他们的著作;而陈寅恪却因自身身世飘零而沉浸在传统社会的理想状态,进而推崇《儿女英雄传》。
钱穆不仅在内容上、思想性上否定了《红楼梦》,而且从悲剧的角度否定了《红楼梦》。他在《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剧》一文中批评道:
近代国人又好言《红楼梦》,以为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然贾家阖府,以仅有大门前一对石狮子尚留得干净,斯其为悲剧,亦仅一种下乘之悲剧而已。下乘悲剧,何处难觅。而且在大观园中,亦仅有男女之恋,非有夫妇之爱。潇湘馆中之林黛玉,又何能与寒窑中之王宝钏,以及韩玉娘、薛三娘诸人相比。贾宝玉出家为僧,亦终是一俗套,较之杨四郎虽同为一俗人,然在杨四郎尚有其内心挣扎之一番甚深悲情,不脱俗,而见其为超俗。贾宝玉则貌为超俗,而终未见其有脱俗之表现。衡量一国之文学,亦当于其文化传统深处加以衡量。又岂作皮相之比较,必学东施效颦,乃能定其美丑高下乎。
近代国人,乃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也。王国维在其著作《〈红楼梦〉评论》里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其大宗旨如上章所述,读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红搂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由此可见,钱穆指出了王国维将《红楼梦》视为悲剧的西方理论资源。鉴于他认为“西方文学以悲剧为贵”,钱穆视《红楼梦》“仅一种下乘之悲剧而已”,无疑是对王国维论述的釜底抽薪。换言之,他并不认同王国维的相关论述。
与钱穆不同,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这一论述是持肯定立场的。在《柳如是别传》著作中论述陈柳情事时,陈寅恪指出:“‘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理斯多德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陈寅恪所言“亚理斯多德论悲剧”着重点是“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这与陈寅恪看重的柳如是之“春日酿成秋日雨”词句“追溯悲剧成因的句意的意象”略同。而王国维视《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一方面认为其符合叔本华“第三种之悲剧”的定义,具有美术意义上的目的与意义,一方面,符合雅里大德勒《诗论》之谓,具有伦理学上的目的与意义。由此可知,陈寅恪虽然并没有完全理解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但他却赞同其观点,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著述阐释当中。
事实上,钱锺书也不认同视《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的观点。1984年,钱锺书在再版《谈艺录》之际,批评道:“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此非仅《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为然也。”在钱锺书看来,王国维并未真正理解叔本华的“悲剧”观念,且其借助叔本华哲学评介《红楼梦》多是“附会”,“不免作法自弊”。不过,与钱穆认为鉴赏文学作品要从“文化传统深处加以衡量”不同,钱锺书则认为“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不可直接“等为一家”,不能直接援引西方哲学等方面的观念以阐释中国文艺作品。在此意义上,钱锺书既不同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也不认同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更不认同钱穆对贾宝玉出家与杨四郎出家之比较。
当然钱穆并没有完全否定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价值,而是认为其有着一定的价值,突破了红学中泛滥的版本考据,在他看来:
考据工作,未尝不有助于增深对于文学本身之了解与欣赏。然此究属两事,不能把考据来代替了欣赏。就《红楼梦》言,远在六十年前,王国维《观堂集林》提出《红楼梦》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此乃着眼在《红楼梦》之文学意义上,但此下则红学研究,几乎全部都集中在版本考据上。
钱穆对考据派的微词是一贯的。他不仅对文学研究的考据派颇有微词,而且对历史研究中的考据派多有微词。可堪玩味的是,对于考据派特别是古史辨派,不仅鲁迅在《故事新编》当中多有讥讽,而且钱锺书在《围城》中也多有讥讽。此外,钱穆也认同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文学不应有隔”之观点。
若细读《中国文学论丛》,则会发现钱穆阐发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包括他对《红楼梦》迥异于王国维、鲁迅等人的认知,始终有着他的“对手方”。换句话说,钱穆始终以西方文学为靶向,主要以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王国维、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为“对手方”。与此相应,钱穆阐发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批评《红楼梦》,也是每每针对西方文学而发,针对“对手方”的观点而发。
在《中国文学论丛》的再序里,钱穆坦言:“民国初兴,新文学运动骤起,诋毁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甚嚣尘上,成为一时之风气。而余所宿嗜,乃为一世鄙斥反抗之对象。余虽酷嗜不衰,然亦仅自怡悦,闭户自珍,未能有所树立,有所表达,以与世相抗衡。”由此可见,新文学运动是钱穆的潜在假想敌,是其“对手方”。而他编辑出版《中国文学论丛》,阐发他自己以前所闭户自珍、仅自怡悦的“旧文学”的价值,则显然是“与世相抗衡”——与新文学运动代表人物相抗衡。这些在《中国文学论丛》著作中,比比皆是。在阐发中国传统文学价值时,他说若“照近代流行观念,把文学分为活文学、死文学两种”。而“活文学、死文学”恰恰来自胡适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比较《三国演义》《包公案》与《红楼梦》高下时,钱穆痛心疾首地说:
今人则于民族文化传统排弃不遗余力,尧舜孔孟首当其冲,轻加抨击。而远自诗骚以来,三千年文学尤所厌鄙,藏之高阁,下再玩诵。即不施全面攻击,亦必正其名曰古典文学,以示区别。文学则必为现代的、通俗的、白话的、创造的。古典性的则必为贵族的、官僚的、封建的,陈腔滥调,守旧不变。即如《三国演义》《包公案》诸书,亦属白话通俗的一种创造,一如今人所提倡,而亦仍加区别,一概不登大雅之堂。其所提倡,则惟曹雪芹之《红楼梦》。论其白话通俗,亦未必驾《三国演义》与《包公案》之上。而特加重视,则无他,以其描写男女之爱,更似西方耳。今日国人提倡新文学,主要意义亦在创造人心,惟求传入西方心,替代中国心。于中国旧传统则诟厉惟恐其不至。近代最先以白话新文学擅盛名,应推鲁迅,为《阿Q正传》,驰名全国。
这里“现代的、通俗的、白话的、创造的。古典性的则必为贵族的、官僚的、封建的”来自陈独秀1917年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众所周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章,宣告了新文学的开始。
通过钱穆的这番话可知,他将新文化运动否定中国旧传统、鼓吹新文学,视为“惟求传入西方心,替代中国心”的结果。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大肆宣扬西方文学,提倡“现代的、通俗的、白话的、创造的”文学,否定“贵族的、官僚的、封建的”古典文学,过于在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而忽视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观,遮蔽了《三国演义》《包公案》在白话通俗方面的创造。在此基础上,钱穆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重视与高度肯定《红楼梦》,与国人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密不可分,与“国人提倡新文学”密不可分。他的批评“近代国人又好言《红楼梦》,以为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以及“惟待西化东渐,人心变而高捧此红楼一梦,认为如此境界,始是人生”,皆是明证。也就是说,在钱穆看来,20世纪以来中国重视与高度肯定《红楼梦》,是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王国维将其视为“悲剧中之悲剧”的结果,是“西学东渐”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受西方文学影响国人重视“西方心”包括重视男女之欲望、人生之苦痛而忘记“中国文化之传统理想”的结果。
事实上,《红楼梦》的影响超过《三国演义》,并非开始于西学东渐。从乾隆年间而非“西学东渐”或新文化运动后,《红楼梦》在文人中的影响已超过《三国演义》。也就是说,《红楼梦》在文人中的影响超过《三国演义》,并不是钱穆所言是国人重视“西方心”忘记“中国心”的结果。同时,由于“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亦有人不满于《红楼梦》的儿女情长,期望文学作品能够“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反《红楼梦》的《儿女英雄传》正是这样的产物。不过,一定意义上,《红楼梦》正如钱穆所言,确实有别于中国许多传统小说。在叙事方式、故事发展上,“《红楼梦》的故事几乎是不往前走的”,“这跟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差别很大”,与钱穆所推崇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的差异也很大。相比《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故事发展的线索非常明晰”。相比中国古典小说“描述的是一个行动的世界,人们通过行动完成一个事件”,讲究的是“有头有尾”,《红楼梦》的“叙事没有明显的时间刻度”。《红楼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失去了行动性”。此外,《红楼梦》的内容和主题有着丰富性。
正是有了“假想敌”,有了“对手方”,钱穆便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核心论旨方面,与王国维公开立己,与鲁迅公开立异。众所周知,王国维揭示《红楼梦》“悲剧中之悲剧”,不仅借此强调了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而且借此阐发了其在美学、伦理学上的价值。这在中国20世纪学术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文学研究的“范式革命”。而鲁迅评价《红楼梦》为“人情小说”,具有“悲凉风格”等,不仅有着鲜明的学术创新,而且自始至终有着史家眼光与文学史意义。而钱穆则将《红楼梦》贬低为“下乘之悲剧”,认为其不过是“儿女私情亭榭兴落,存胸怀间”名士才子之作,皆与王国维、鲁迅的评价截然不同。可见,尽管他们所讨论的对象相同,但观点迥异、旨趣相殊则十万八千里也。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将他们视为“假想敌”“对手方”,目的并不是为了公开树敌,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公开立异上。而是为了批评他们以“西方心”代替“中国心”,是为了批评他们将中国文化之传统理想“尽抛脑后亦惜更无高文妙笔以挽转此厄运”。也就是说,钱穆的根本目的是,凸显长期被“西方心”所遮蔽的“中国心”,找寻失落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理想。在他看来,“非切实了解其文字与文学,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内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欲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独特与优美,莫如以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为之证”,“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看重中国传统文学“深透其民族之内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重要性的钱穆,认为与西方文学以叙事长诗、剧本、小说为三大骨干不同,诗与史是中国文学的柱石。在他的文学理念里,“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诗者,中国文学之主干。诗以抒情为上。盖记事归史,说理归论,诗家园地自在性情”。在这理念指引下,他认为“小说戏剧之在中国,终为文学中旁枝末流,而不得预于正统之列”。因此,在他看来,文学与时代互相成就,文学与人生可以互换,文学既要反映时代,也要表达人生。因此,中国文学作品,不仅要在乎“技巧与风格”,更要在乎作家的“生活陶冶与心情感映”,作品的伟大有赖于作者的崇高人品与精神。与此相应,他认为,作为内倾性之文学的中国文学“必以作家个人为主”,作家个人“必具有传统上之一种极度自信”,进而在文学作品中,达到“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的境界,而“此种境界与精神,亦即中国文化之一种特有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大成就、大业绩。换言之,在他眼里,最高境界的文学,需要作家在“向往理想上之崇高标准”的前提下,对于本人生活“有亲切之体味”,且“在其内心,经验了长期的陶冶与修养”,最终作品“所抒写”、所“旁见侧出”,才“能使读者亦随其一鳞片爪而隐约窥见理想人生之大体与全真”。与此相应,他认为“中国文学家最喜言有感而发,最重有寄托,而最戒无病呻吟”,“作家远站在人生之外圈”“仅对人生作一种冷静之写照”,以及“作家远离人生现实”“对人生作一种热烈幻想之追求”,皆不足取。
不难看出,他的文学观,有着明显的儒家本位,有着明显的理学色彩。这种文学观,要求文学在追求上要秉承“文以载道”,要讲究圣人之道,要求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在思想上要富有“教诲性感化性”。在内容上要侧重写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人伦之爱而非男女之爱。与此相应,他很难认同《红楼梦》的思想性与内容,并不认可《红楼梦》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地位。与此相应,他认为,《西厢记》谈不上中国文学之上选,《金瓶梅》谈不上是“文学”,写男女之爱的《红楼梦》比不上《三国演义》。
由上述可知,树立“假想敌”,与“对手方”公开立异,对于钱穆而言,并不是为了公开树敌,而是为了追寻“中国心”,而是为了发掘与彰显中国文学、文化之传统境界和理想。也可以说,树“敌”与立异,是钱穆将个人学术生命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其阐发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之微言大义的必由之路。客观上,无论是与史学研究上的“对手方”争论或对话,还是在文学研究上的争论或对话,都很大程度促进了钱穆思考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之特性之价值的深入,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钱穆在史学研究、文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精进,都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碰撞,有利于学术的良性竞争与发展。
同时,钱穆对《红楼梦》的批评虽多有偏颇之处,但却不乏启示。即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如何对待西方包括其文学观念这个庞然大物,如何不将中国文化之传统理想“尽抛脑后亦惜更无高文妙笔以挽转此厄运”。19世纪以来,面对西方这个巨大的客观存在,中国的学者始终探讨何以西学中用,始终探讨与西学的对话与交流,这既包括“中学”“西学”的体用之争,又包括王国维对西学发出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之疑问,又包括鲁迅的“拿来主义”,更包括钱锺书的中西“打通”,以及王元化的“不以西学为坐标,要以西学为参照”。而探讨中国传统文学之特性之理想,亦是20世纪中国学者的不倦追求,这既包括梁漱溟的努力,又包括新儒家的探索,更包括1997年提出“文化自觉”的费孝通的探讨。他们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学之特性之理想方面,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换言之,钱穆通过批评《红楼梦》,树立“假想敌”,与“对手方”公开立异,启示在于,直接援引西方文学观念以阐释中国文艺作品是否可行,以“西方心”——西方文学的核心观念代替“中国心”——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与境界是否可行,以及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关于新旧文学的划分标准是否妥当。
不可否认,钱穆在树立“假想敌”,与“对手方”公开立异的过程中,在追寻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与境界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过于强调了中西之别、新旧对立,比如处处反对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观点,否定其认可的著作,进而轻视与误读《红楼梦》,否定新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这些限制了他的视野,使他忽视了中西文学、新旧文学共同共通的“文心”,进而使他的文化观、文学观缺乏包容性或开放性。毕竟找寻被新文化运动遮蔽的“中国心”,追寻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与境界,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心”,而应该是为了找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实现中国文化、文学的“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使得“现代性”在突破了“传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而这个过程,就要共时性地充分吸收与借鉴吸收西方文明、西方文学的优秀经验,参照西方,打通中西,通过现代的方式“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使得“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同时,由于过分注重儒学本位、注重文学的教化价值与干预现实,钱穆的文学研究很有可能位移到外部研究以及社会学批评,从而偏离文学本身,缺乏足够的审美,存在一定片面性。换言之,钱穆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批评,则也可能会割裂文学作品,是“局部窄狭之追究”,以丰富的内涵,换取以“自己塑造”的文学理念,虽寄情于先民文化精神,但却对现代人之一往情深漠然无视,进而无法对先民文化精神进行全面关照。
① 孔定芳《学术“对手方”与钱穆的清学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7辑。
②③⑦[12][13][14][15][17][18][19]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63、169、170、148、159、189、184、1、15、40、41、43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6页。
⑤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50页。
⑥ 谢泳《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江淮文史》2014年第4辑。
⑧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14、15页。
⑨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0页。
⑩ 刘梦溪《陈寅恪与〈红楼梦〉》,《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
[11] 钱锺书《谈艺录》(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348、352页。
[16] 李洱《熟悉的陌生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1、72页。
[20]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