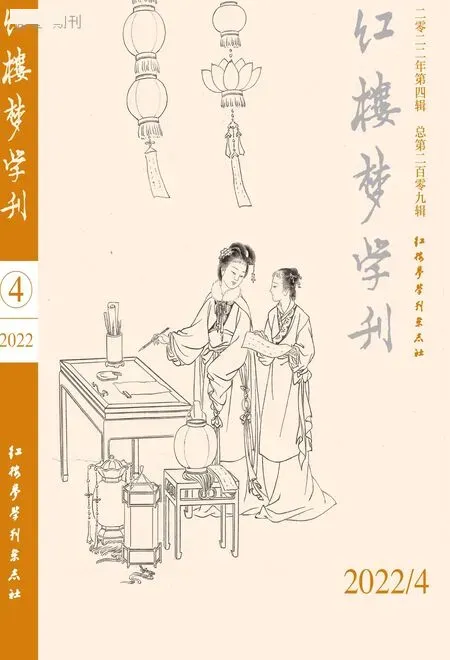俞平伯红学观之“怨而不怒”说刍议
许 飞
内容提要:俞平伯关于《红楼梦》风格的“怨而不怒”说,是在红学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巧借儒家经典诗论拈出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著名观点。它是一个美学概念,认为《红楼梦》具有含蓄蕴藉的总体风格,表面平静,内藏血泪,感染力超强。此说是俞平伯以文学的眼光进行《红楼梦》研究的一项有益实践,与他本人的艺术气质息息相关,也是新时代红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项学说植根于传统审美理念的丰沃土壤中,合乎《红楼梦》文本的实际状况,是理解《红楼梦》的一把金钥匙。
李太白飘逸奔放,杜少陵沉郁顿挫。每个作家作品都具有其总体风格。关于《红楼梦》,俞平伯曾经拈出“怨而不怒”四个字来对其风格予以概括。对此,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有人赞同中有保留或反对时有补充。由于题旨比较紧要,我们不揣谫陋,也来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怨而不怒”说:由来与遭际
查“怨而不怒”源出先秦史籍:“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国语·周语》)这是讲为人处世的基本行为规范。作为社会一员的人,在冲动易怒的关键时刻要善于调节情绪,以便与他人维系一种相对平稳的和谐关系。后来“怨而不怒”演化为诗学概念。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其中“可以怨”是讲诗可以表达负面情绪,可以抨击丑陋现象。南宋朱熹训以“怨而不怒”四字,见《论语集注》卷九。朱熹显然是主张文学作品尽可“怨”,但要有所节制。再往后“怨而不怒”常常与“哀而不伤”或“乐而不淫”并举,变为中庸原则的一项操作指南,从而在诗文批评方面广泛运用起来。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西汉司马迁《屈原列传》云:“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卷八四)近人陈寅恪《无题》说:“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这就是指俞平伯早年提出“怨而不怒”说并撰成《红楼梦辨》,此说源自儒家经典。元人李继本《傅子敬纪行诗序》云:“无名氏之十九首,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其风人遗音乎?”明人赵统《杜律意注》评骘杜甫《晓发公安数月憩息此县》云:“尾句是自叹其漂流无所抵止,极怨也。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之谓杜诗。”清人谢堃《春草堂诗话》云:“诗可以怨,怨而不怒者,上乘矣。”类似的例子颇多,不胜枚举。既然如此,各体文学创作自然会受到很大影响,小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诗可以怨”和“怨而不怒”也必定有所了解。
俞平伯最早将“怨而不怒”引入红学领域。1923年春《红楼梦辨》发端,1952年秋《红楼梦研究》继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一以贯之。
俞平伯还将《红楼梦》与其他小说进行了扼要对比,认为《水浒传》词锋犀锐,《金瓶梅》涉嫌诽谤,《儒林外史》牢骚满纸,唯独《红楼梦》“怨而不怒”,所以在神采上《红楼梦》比其他小说要更为卓荦。至1952年9月《红楼梦研究》修订再版,俞平伯仍坚持并重申此说。
“怨而不怒”是一宗诗教观念。在俞平伯看来,它不仅可以隐括《红楼梦》的艺术品格,还兼有教化的成分在焉。他希冀读者能够通过此一风格察觉《红楼梦》的深层涵义,那就是忏悔情孽。“情场忏悔”说是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另一著名观点,该说旨在劝世与教诫,即劝诫世人从情执中解脱出来。这与他之前话及色空观念及反照《风月宝鉴》是分不开的。
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是催生《红楼梦》“怨而不怒”说的学术土壤。俞平伯到后来质疑曹贾互证,其前奏曲即“怨而不怒”说伴随着新红学孕育而生。追根寻源,沿波讨源,此说直接来自他的镜子说。俞平伯称许《红楼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现实世界的人生百态。俞氏镜子说又源于胡适的自然主义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自然主义即镜子,晶莹剔透,平淡无奇。可以讲,俞平伯的《红楼梦》“怨而不怒”说原本属于胡适自传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俞平伯作为新红学主将的闪光点之一。没有胡适的及时督促引导,该项风格论便不会呱呱坠地。
俞平伯总结出“怨而不怒”说,与他自身的文士气质息息相关。“怨而不怒”的主体特征是许怨不许怒,这是俞平伯偏好中庸的文人雅士情趣的一种自我暴露。它属于比较典型的东方文人格调,提倡中和美,要求舞文弄墨须做到温柔敦厚,一如儒者对中庸之道的竭力尊崇。孔子的理念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等。俞平伯讲《红楼梦》“怨而不怒”是对应中庸之道,宣传中和为美,推重艺术创造上的克制、抑制、节制、控制,这是圣贤意识的必然归宿。
俞平伯对于“怨而不怒”说的系列论述,从1954年秋季起招致了一些严厉驳斥,几乎持续不断。批评者包括白盾、李希凡、蓝翎、田锺洛、端木蕻良、聂绀弩、何其芳、王达津、程千帆、林焕平、刘绶松、李易、王瑶、何家槐、周汝昌、王若水、刘衍文、石灵、郭豫适、崔西璐……到1980年以后,裴晋南、刘扬忠、石昌渝、李广柏、韩泰伦等有所辩解。
石昌渝打抱不平说:“‘怨而不怒’曾被人误解为作者没有爱憎立场,作品没有倾向性。……俞平伯所谓‘怨而不怒’实在指的是含蓄,这含蓄既是文章的风格,又是作者的个性。”此议平实,切中肯綮。
俞平伯过去的那些黯淡遭际,眼下已成遥远的红尘史迹,何必过分纠结纠缠?唯误解应该澄清,“怨而不怒”说的红学本旨理当加以阐明。
二、“怨而不怒”说:红学本旨
俞平伯颂扬《红楼梦》“怨而不怒”,这首先是一个美学概念。他认为“怨而不怒”呈现出来的是含蓄之美,是蕴藉的修辞手段,它使得作品具有幽深悠远的审美情韵。他曾指出:“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含怒气的文字容易一览而尽,积哀思的可以渐渐引人入胜;所以风格上后者比前者要高一点。”这是讲含蓄及“积哀思”不仅是一派文本风貌,更可上升为一种美学境界。在俞平伯眼里,蕴藉是一种理想的美的形态,此类文学作品依之而焕发出令人着迷的艺术魅力。恰如刘勰《隐秀》篇所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彩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文心雕龙》卷八)《红楼梦》能够给人带来某种强烈美感,每每可意会不可言传,在一定程度或极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曹雪芹采用了这种“积哀思”式含蓄手法。
咸丰至同治中,安徽旌德的愿为明镜室主人江顺怡(秋珊)在其所著的《读〈红楼梦〉杂记》中谈到:
《红楼梦》,小说也,正人君子所弗屑道。或以为好色不淫,得《国风》之旨,言情者宗之。明镜主人曰:《红楼梦》,悟书也。其所遇之人皆阅历之人,其所叙之事皆阅历之事,其所写之情与景皆阅历之情与景,正如白发宫人涕泣而谈天宝,不知者徒艳其纷华靡丽,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人生数十寒暑,虽圣哲上智不以升沉得失萦诸怀抱,而盛衰之境,离合之悰,亦所时有,岂能心如木石,漠然无所动哉?缠绵悱恻于始,涕泣悲歌于后,至无可奈何之时,安得不悟?谓之梦,即一切有为法作如是观也。非悟而能解脱如是乎?
又有满洲巨公谓《红楼梦》为毁谤旗人之书,亟欲焚其版。余不觉哑然失笑。……《红楼》所纪,皆闺房儿女之语,所谓有甚于画眉者,何所谓毁?何所谓谤?
俞平伯诠释“怨而不怒”时简要征引过这两段文字,赞许江氏“这两节话说得淋漓尽致,尽足说明《红楼梦》这一种怨而不怒的态度”。《红楼梦》的确不毁不谤具体个人或特定群体(例如旗人),却依然“字字看来皆是血”即“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这正是源于《红楼梦》超越性的精神旨归,它要揭示的是人生皆苦,暗合了释迦牟尼的“四谛”之苦谛。三界如火宅,小说是催人产生出离之心的“悟书”。
俞平伯把“怨而不怒”当作一种审美体验的主观感受,同时也把它当作臧否得失的一把尺子。“怨而不怒”对他而言是理想状态的艺术美,同样也是价值判断的客观标准。他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在审美韵味上不及前八十回,缘故便在于续书过分直白浅露,缺乏蕴藉的神秘美感。
俞平伯以为,发泄与含蓄是文学作品截然迥异的两种境界,后者比较高超而前者略嫌低端。他还将《红楼梦》与《水浒传》作了一番对比,强调尽管施耐庵与曹雪芹“都是文艺上的天才,中间才性底优劣是很难说的”,但“我们看《水浒》,在许多地方觉得有些过火似的”,而“《红楼梦》底风格偏于温厚,《水浒》则锋芒毕露了”。于此甭提《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之类谴责小说,《海上尘天影》《九尾龟》《九尾狐》之类嫖界教材更等而下之了。俞平伯执拗地宣称,在艺术风格上《红楼梦》明显是胜过《水浒传》一筹的。
须知“怨而不怒”基本前提的“怨”,是一种否定,这跟《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致的。分歧之点仅在于表达方式,怒还是“不怒”,直露还是含蓄,激烈还是收敛。明人江盈科《雪涛诗评》说:“唐两人罢官,各题小诗。……二诗用意虽同,然有怨而怒、有怨而不怒,可以观矣。”持此衡量,对俞平伯“怨而不怒”说的某些攻讦便属无的放矢,是误会或曲解了俞氏的红学观点。譬如贬斥此说无视《红楼梦》所闪耀的批判现实主义光辉,对俞平伯确乎有欠公允。有的批评者不改初衷。白盾称《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气壮山河,《渔光曲》和《汉宫秋》如泣如诉,于是尖锐质问“怨而不怒”说:“这之间,能划出等级吗?”我们不可混淆雄壮与婉约的美学界限,不可将两者割裂对立起来。雄壮也可以含蓄,婉约也可能放肆,唯“怨而不怒”更容易形成委宛萦曲的文章笔调,这倒是事实。《水浒传》尽可雄壮,尽可激烈,尽可怨而怒,俞平伯也热情夸奖施耐庵伟大,是世所罕见的文学天才,同曹雪芹在伯仲之间,一时难分轩轾。只是俞氏个人更欣赏《红楼梦》言筌无迹式“怨而不怒”,就是不疾不徐、不矜不盈、绘声绘色、娓娓道来,认为那样的“怨”更具情感支配力、思想穿透力、理论说服力、精神吸引力、灵魂震撼力、道德感召力及艺术感染力,由此庶几乎实现纸上世界的风云变幻乃至乾坤挪移。“怨而不怒”并非软弱无骨、脆嫩无筋或怯懦无胆,含而不露往往举重若轻,笔挟雷霆,力拔山兮气盖世。此即晚唐司空图所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己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诗品·含蓄》)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妙玉、李纨、秦可卿、甄英莲、晴雯、花袭人、贾雨村、刘姥姥、尤二姐、尤三姐、鸳鸯、司棋、紫鹃、芳官……处处含“怨”却不简单告诉你断语,让你自己去辨别思考。旁的姑且莫论,单单扬钗抑黛与扬黛抑钗就令红学史热闹非凡了。倘怨而怒,曹雪芹像焦大似的动辄骂出底里,结果可想而知,无非在张南庄《何典》之外再多出一部《鬼话连篇录》来。《何典》成书于嘉庆朝,去《红楼梦》未远,以嬉笑怒骂、汪洋恣肆而为鲁迅所青睐,却不能跟《红楼梦》媲美。《红楼梦》确具“怨而不怒”风致,而且此法是格外成功的。
“怨”的本能反应是怒,直线反应是怒,即时反应是怒,却竟尔“不怒”,这一戛然顿挫转捩当中包孕着沉默、回味、咀嚼、内省、沉淀、权衡、辨析、斟酌、擘划、反诘、哽咽……曹雪芹俨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念。“怨”意味着惊骇、苦恼、追问、求索……“不怒”则意味着忍耐、冷静、窕邃、厚重……于是蚌病成珠,柟蹙成锦,修辞效果定然差不到哪里去。
对曹雪芹而言“怨而不怒”既有迫不得已的一面,威胁来自文字狱(怨而怒容易凝成政治碍语,时人“避席畏闻文字狱”),也有欣然笑纳的一面(“怨而不怒”容易提升翰藻水平,即“淡极始知花更艳”),诱惑来自士林趣味及艺术规律。南宋魏庆之《古诗之意》云:“诗之为言,率皆乐而不淫、忧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孔子所以有取焉。”朱熹《跋东坡书李杜诸公诗》云:“然其言怨而不怒,独百世以俟后贤而不惑,则其用意亦远矣哉!”诗文如此,小说怎能例外?由宋至清“怨而不怒”已成四字箴言,也便意味着它代表习惯、风尚、规矩乃至规律。
俞平伯的“怨而不怒”说昭示出《红楼梦》的总体风格,一言以蔽之,含蓄蕴藉。含怨,字里行间血泪斑斑;含怨,表面上波平浪静。其实静水流深,包藏在内核的悲忿犹如滚滚岩浆。不怒,火山未喷涌;不怒,读者能感知,因为大地分明在微微颤抖。南宋姜夔曾指出:“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按“怨而不怒”即怨而不露,怨而有力,格外有力,力大无比,力大无穷。为什么?因“怨而不怒”可以充分调动每一位严肃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让历代读者都积极参与到阐幽探赜之中,从而超额完成即无限触及“怨”的丰富指向,有广度也有深度,有分量也有质量。这正是曹雪芹的高明处及《红楼梦》的卓越处,正是俞平伯“怨而不怒”说的红学本旨。
三、“怨而不怒”说:红学价值
审美主体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本属自然。俞平伯除了拥有学者的身份以外,也冠有闲适派散文家兼新诗人称号。对于美的观察,他抱持着艺术家自身的主观倾向。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以鉴赏为基准,认为婉约胜于雄壮,他的这种审美偏好在诗词品藻中多有显露,《唐宋词选释》多选婉约派,另著《读词偶得》侧重花间词和后主词,《清真词释》则专取周邦彦(美成),这原也无可厚非。实际上,婉约和含蓄是一组不同的审美概念,“怨而不怒”可以同时兼备这两种歧异的解读方式。俞平伯重在揭橥《红楼梦》含蓄的美学价值。他感觉“怨而不怒”带去了微妙的蕴藉美,使得《红楼梦》一举攀登上珠峰之巅,又幻入庐山云雾里,在古代小说领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艺术高度。
俞平伯心目中的《红楼梦》艺术风格固属“怨而不怒”,但这仅仅是创作手段。曹雪芹选用缱绻旖旎的文学语言,花娇月媚、如诗如画、葳蕤潋滟、如醉如梦,终究是为了“情场忏悔”。这就是悟书说,暗合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鼓吹的解脱说。而这一写作主旨,长久以来被清代风靡的史书说、情书说、淫书说、邪书说、谤书说遮蔽了起来。于是乎俞平伯写道:
我因此想到高鹗补书底动机,确是《红楼梦》底知音,未可厚非的。他亦因为前八十回全是纷华靡丽文字,恐读者误以为诲淫教奢之书,如贾瑞正照“风月宝鉴”一般;所以续了四十回以昭传作者底原意。
这就很清楚了。俞平伯觉得,正因高鹗把握住《红楼梦》的创作主旨,辛勤续成了悲剧结局,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曹雪芹的后世知音。其中“纷华靡丽”文字也就是“怨而不怒”节奏,不仅无涉诲淫教奢,恰恰相反,它是作者为了警世醒世而精心设计的,即小说开篇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读者正照风月鉴,目睹的是“纷华靡丽”及诲淫教奢,反照则见劝惩私欲、忏悔情孽,这才是《红楼梦》的深层旨义。如此一来,俞平伯便将“怨而不怒”引入到文学功能的范畴中去了。却原来,暗暗隐藏在“怨而不怒”背后的,居然是儒家文学传统所倡导的诗教理论,是“文以载道”、是“温柔敦厚”、是“思无邪”等古时正统的文学功能论。《红楼梦》所载之道主要既儒亦释。乾嘉两朝钱塘陈文述(元龙)的《秋日杂感》说:“骚人逸兴攀淮树,怨女愁根托海棠。参透情禅思学佛,香南雪北两鸳鸯。”又《秦淮杂咏》云:“画舫新编有盛名,倚云高阁最多情。情禅参透《红楼梦》,曾识吴门高玉英。”不愧是袁枚的衣钵传人,陈文述选用“情禅”二字标举《红楼梦》所载之道,相当恰如其分。既为“情场忏悔”,那么曹雪芹就是在“怨”他自己,怎么怒得起来?只好缠绵悱恻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起来。即此望去,俞平伯的“怨而不怒”说,在逻辑上起码是自洽的,没有破绽洞开。
俞平伯定义《红楼梦》的总体风格为“怨而不怒”,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它是俞平伯治学过程中偏向文艺视野的一种集中外现,是他不断倡导使用“文学底眼光”去研究《红楼梦》的自然流露。郑重捧出属于文学考证和审美范畴的“怨而不怒”说,是他借用缪斯的双手耕耘红学园地的一次重要实践。《红楼梦辨》梓行两年后,俞平伯撰写随笔《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道:
我们可以说,一切事情的本体和他们的抄本(确切的影子)皆非文艺;必须它们在创作者的心灵中,酝酿过一番,熔铸过一番之后,而重新透射出来的(朦胧的残影),方才算数。申言之,natural算不了什么,人间所需要的是artificial。创造不是无中生有,亦不是抄袭(即所谓写实),只是心灵的一种胶扰,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角逐。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俞平伯注重文学创作对现实生活的加工淬炼,同时鄙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一一对应的机械比附。这也跟他在《〈红楼梦辨〉底修正》中检讨自己将曹家与贾府合并起来的做法遥相呼应。
曹贾互证将小说情节与现实中的人、事、物、理划上等号,是补史小说观的拙劣表演。俞平伯悟到这种做法模糊了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根本界线,和索隐派猜笨谜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换了个底面罢了。与蔡元培、胡适、顾颉刚、李玄伯等单纯的文史类学者有差异,俞平伯是学者,也是新文学作家兼诗人,还醉心昆曲,他是作家型学者或诗人型学者,他所珍视的是作品本身及其经营过程。新旧红学家都将《红楼梦》当作文献史料,他却再三强调那是一部虚构小说。既然《红楼梦》是文学作品,那么历史考证便不应是红学唯一的可行之法。要进行文学解剖,就不能没有对作品的鉴定赏析。俞平伯宣扬“怨而不怒”说,是他重视艺术鉴赏的突出动作之一。在这里“怨而不怒”指画的是《红楼梦》蕴藉含蓄的风神之妙,以及此种美学趣味对小说整体审美趋向的深度濡浸。王维《送邢桂州》:“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王右丞集》卷八)香菱学诗时对林黛玉感慨说:“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的尽,念在嘴里,到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是的。”曹雪芹正是要锻造出这种绵远醇厚的阅读效果。一个小小的薄命女,一介卑贱的侍妾,竟具备此等绝世才情,竟不免一连串凄怆坎坷,竟难逃早早夭折返故乡,更加惊才绝艳的林黛玉也泪尽而逝,我们还想要求作者怎么“怨”呢?曹雪芹确实“不怒”,但这“不怒”比怒目圆睁、怒火中烧、怒发冲冠、怒气冲天、怒不可遏、怒骂无状来得更有力量。“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怨而不怒”说真可谓知味解味之言,它的横空出世,是俞平伯将《红楼梦》看作小说也就是文艺作品的具体反映。
从某种意义上讲“怨而不怒”说也是弥补新红学先天不足的一副良方。它的问世标志着新红学开始铺设文学研究轨道,终将跟史学方法(以自传说为代表)分道扬镳。在新红学成长为显学以后,使用科学方法,替代旧红学猜谜式套路,这固然是红学发展的巨大进步。然而,新红学将《红楼梦》视为谱牒史料的做法势必会作茧自缚,画地为牢,逐渐形成本身发展的学术桎梏,使其抱残守缺,日趋僵化,终将裹足不前,难以为继。新红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另辟蹊径,“眼前无路想回头”,这便需要新红学家们以“文学底眼光”和艺术鉴赏法去对待《红楼梦》,也就是更换角度,刮目相见。作为美学范畴的“怨而不怒”说应运而生,无疑是一粒宝贵的红学种子。
新红学当然需要小说理论研究。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有关发泄与含蓄文字在审美体验上的初步比较,便带有明显的艺术赏析成分。而在《红楼梦研究》中,俞平伯更删掉了前引“《红楼梦》底目的是自传,行文底手段是写生”云云,而保留发泄和含蓄的学术、技术、艺术对比。这便将《红楼梦》研究引渡到了文学考证即美学鉴赏的时空维度,有关“怨而不怒”说的审美情趣也因而瞬间放大,光彩照人。对于新红学自身来讲“怨而不怒”说的脱颖露锋,牛刀小试,更是诱发其进一步完善与革新的一桶催化剂。这当然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理论源自作品,反过来又能指导作家创作。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一大弊端是失语症,所以人们大声呼唤本土声音,反复提倡建构文艺理论的东方话语体系。《红楼梦》是本土的,“怨而不怒”也是本土的,两者珠联璧合,属于标准的东方话语。更何况,俞平伯此说按头制帽,量体裁衣,看起来是很合身的。“怨而不怒”说可以加深对《红楼梦》的词章理解,可以点拨对《红楼梦》的艺术研究,也可以启发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其价值相当厚重,已非红学所能限量。
结语
从《红楼梦》开篇对才子佳人小说及艳情小说的辛辣嘲讽中,从全书对庄子、屈原、陶渊明、杜甫、王维、李商隐、《西厢记》及《牡丹亭》等作家作品的热情赞赏中,读者不难体会到,曹雪芹特别善于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与教训。在他生活的时代,圣训“诗可以怨”已传播两千多年,而作为文艺理论术语的“怨而不怒”也被正面肯定了五百多年,明末清初的言说尤其频繁。“怨而不怒”既可以左右诗文创作,自然也就可以规范戏曲小说。于此《红楼梦》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光辉的范例。倘讲曹雪芹惨淡经营《红楼梦》的时候,主观上便具备了此种艺术追求,当属虽不中(尚无实证)亦不远之论,那么俞平伯的“怨而不怒”说,可谓神会曹雪芹之意了。宋诗:“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
俞平伯关于《红楼梦》风格的“怨而不怒”说,是在红学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巧借儒家经典诗论拈出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著名观点。这项学说强调《红楼梦》基本的艺术特征是含蓄蕴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感染力超强。它植根于传统审美理念的丰沃土壤中,大体上合乎《红楼梦》文本的实际状况,可以讲是理解《红楼梦》的一把金钥匙。古语云,金针度人,慈筏妙在,正可移来一用。
① 陈寅恪《无题》,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89页。
② 李继本《一山文集》,四库全书本,卷四21ab。
③ 赵统《杜律意注》,清骊山集刻本,卷一1b2a。
④ 谢堃《春草堂诗话》,道光春草堂集刻本,卷一1b。
⑤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见《评红楼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2页。
⑥ 石昌渝《俞平伯和新红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⑦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⑧ 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见一粟《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5、208—209页。
⑨⑩[16] 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7、85、124页。
[11] 江盈科《雪涛诗评》不分卷,宛委山堂刻说郛本,采逸篇2a。
[12] 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参看白盾《〈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评俞平伯的〈红楼梦底风格〉》,《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2日。
[13] 魏庆之《诗人玉屑》,四库全书本,卷六2ab。
[1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涵芬楼影印明刊本,卷八四9a。
[15]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清历代诗话本,3a。
[17] 陈文述《颐道堂诗外集》,道光增修嘉庆丁卯刻本,卷七24a、卷九15b。
[18] 俞平伯《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见《俞平伯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