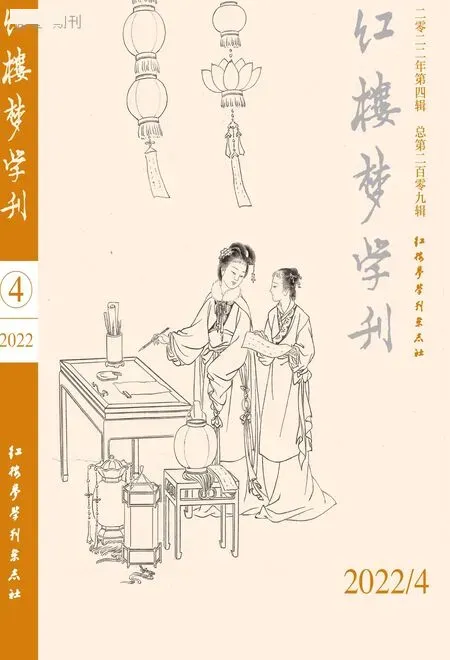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
梅新林
内容提要:红学史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红学史,而应臻于全球视域中的世界红学史。鉴于长期以来既有红学史研究视野、理念、体系与方法存在的种种缺陷,本文提出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这一论题,并重点归纳和申述了如下意见:一是全球视域中“重写红学史”旨在将本土红学史引向世界红学史,具有基于学术而又超越学术的多重意义;二是全球视域中“重写”而成的世界红学史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停留于内容上的简单综述与体例上的“附加”地位;三是全球视域中的“重写”世界红学史主要取决于国别红学史的夯实根基与洲际红学史的重点突破;四是全球视域中“重写”的关键问题是跨语言的困境,必须有赖于不同语种学者的协同攻关方能完成;五是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特别需要引入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并与数据库建设和数字化平台相结合,助力重绘世界红学史地图。
经典既是民族文化独特的价值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红楼梦》自1794年传至日本之后,在迄今为止的200余年海外传播中,相继以34种语言出版了155个不同篇幅的译本,其中有18种语言36个全译本。与此同时,从海外诸多语种的《红楼梦》文本翻译,到各种中国文学史论著对《红楼梦》的介绍评述,再到一系列相关论题的专题与比较研究,红学业已成为一种跨区域、跨语言、跨文化的世界性学术,成为中外文学对话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成为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并能够“走进去”的重大课题,充分彰显了中国文学—文化经典的深厚底蕴、独特魅力与精神价值。所以红学史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红学史,而应臻于全球视野中的世界红学史。鉴于长期以来既有红学史研究视野、理念、体系与方法等方面存在的种种缺陷,本文试图聚焦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的这一论题,拟从“重写红学史”之需求、意义、定位与实践提出相应意见与建议。
一、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之需求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亦有一代之学术史,这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对学术理念、路向、范式的不同理解,都需要对特定时代的主要学术论题作出新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写学术史”既是一种即时性学术思潮的反映,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学术创新活动。不同时代“重写学术史”的依次链接与推进,即是最终汇合成为学术通史的必要前提。然而,这里所论的“重写红学史”,除了上述的普遍性内涵之外,主要基于矫正与拓展既有红学史研究的双重需求。
回顾《红楼梦》问世以来红学史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先后大致经历了以下六个重要环节:
第一个重要环节是《红楼梦》问世之际“一芹一脂”的“作者批评”与“读者批评”。《红楼梦》开篇即云:“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一发端于《红楼梦》创作的“作者批评”可以视为红学史之先声。与此“一芹”的“作者批评”相比,“一脂”的“读者批评”更具红学批评之内涵与性质。按照徐恭时的推测,曹雪芹约于乾隆六年(1741)开始创作《红楼梦》,约至乾隆十六年(1751)经过“十年辛苦”,在悼红轩里著成《红楼梦》稿本,脂砚斋亦于此际开始评点《红楼梦》,乾隆十九年(1754)再评,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评,乾隆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759—1760)四评。徐恭时又引陈庆浩《脂砚斋评语研究》按八种版本加以统计,共有6472条评语,除去各本相互重复者(包括文字略同的)外,计为3920条。就这些评语的形式而言,有回前总批或韵文、回后总评或韵文、双行批语、行间夹批、眉批、特批等。其中存在问答之批,或云某些注释系“一芹”之笔,但难以找到确证。然而不管如何,脂砚斋的“读者批评”已属于典型的小说评点,也是开创红学史的学术起点,脂砚斋堪称为第一位红学家。
红学史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晚清光绪年间“红学”的命名。据1918年《文艺杂志》第8期所载光绪举人均耀《慈竹居零墨》云:“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谈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尽管朱昌鼎所言“红学”本出自戏称,但自此方有“红学”之名行世。又据1919年刊行的李放《八旗画录注》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由此可见,晚清京朝士大夫研读《红楼梦》风气之盛,而且“红学”之名已从戏称逐步转化为一个具有专学意涵的学术概念。张云《晚清经学与“红学”——“红学”得名的社会语境分析》以“红学”一词缘起为案例,联系晚清社会政治现实,特别是今文经学在当时政治生活方面的实践进行社会语境的分析,认为从中不仅能够读出经学的衰微、小说观念的变迁、晚清时局的动荡对士人阅读取向的影响,亦可读出“红学”出现于偶然中的必然性。
红学史的第三个重要环节是20世纪初的“新红学批评”。先是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连载于《教育世界》第76—81号。此文主要引入叔本华哲学重新阐释《红楼梦》的意义与价值,在第五章《余论》中集中批评了索隐影射和自传说:“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提出研究者要了解文艺本身的特点,而不能把小说创作中某个人物形象与实际生活中某一个人混为一谈。就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创新观点与批评功能而言,实已开启了“新红学”之先声。然后至20年代初,“新红学”的“三驾马车”——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同时开创了“新红学批评”。从胡适《红楼梦考证》批评“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提出“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到俞平伯《红楼梦辨》中《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提出“大家都喜欢看《红楼梦》,更喜欢谈《红楼梦》;但本书底意趣,却因此隐晦了近二百年,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然后重点批判“猜谜派”与“消闲派”的误入歧途,强调此文旨在“祛除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底谬见”,再到顾颉刚《红楼梦辨序》将以往红学研究的局限与根源作了归纳:“浮浅的模仿出于《尚书》之学,尖刻的批评出于《春秋》之学,附会的考证出于《诗经》之学”,并率先确认“新红学”的命名,谓“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于是以“新红学批评”为红学研究划出了一个时代——一个从“索隐红学”走向“科学红学”的新时代。
红学史的第四个重要环节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红学史学术论文的问世。追本溯源,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红学史学术论文是雪岑连载于1915年3月2日、3月16日、4月16日成都《四川公报》增刊《娱闲录》第16、17、19期的《红学发微》。文中开篇《弁言》有“欲穷流别,请次章目:哲理中之《红楼梦》;节记中之《红楼梦》;钩稽中之《红楼梦》;文艺中之《红楼梦》”云云,可见此文所谓“红学发微”之构架。作者于该刊第19期标明“未完”,然在第20期以后直至29期,不仅第一章《哲理中之红楼梦》未见续载,而且《节记中之红楼梦》《钩稽中之红楼梦》《文艺中之红楼梦》三章全部未载,所憾是一篇未竟之稿。至1937年5月,阿英《红楼梦书话》刊于《青年界》第11卷第5号;1938年9月1日,白衣香《红楼梦问题总检讨》刊于天津《民治月刊》第24期;1944年2月15日,杨夷《红学重提》刊于《民族月刊》第1卷第3期;1948年6月14日,习之《红学的派别》刊于北平《新民报日刊》。这些均为比较成熟的红学史论文,其中白衣香《红楼梦问题总检讨》具有比较典型的学术史论范式,习之《红学的派别》则拓展至红学流派研究。自此之后,每当红学史的重要节点,总有相应的学术论文问世,诸如林以亮(宋淇)刊于1972年2月《香港所见红楼梦研究资料展览》的《新红学的发展方向》;余英时刊于1974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2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潘重规刊于1974年7月《幼狮文艺》第40卷第1期的《红学六十年》,以及大陆学者的“红学”三十年、四十年……七十年系列论文,都在红学界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红学史的第五个重要环节是20世纪中叶之后红学史学术专著的问世。先是1960—1961年,郭豫适为华东师大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题研究与评论”课程教学的需要而编印《红楼梦研究简史》讲义。后经陆续增补、删削和修改而成《红楼研究小史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红楼梦》问世以来第一部红学史研究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次年,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续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韩进廉所著《红学史稿》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述两书的接连出版,一同开启了红学研究专史著作的新阶段。
红学史的第六个重要环节是21世纪之初中外红学史的初步对接。在红学史研究领域,张庆善、梅新林先于2001年在《红楼梦学刊》第3辑发表《让历史启思未来——关于〈红学通史〉编纂的构想与思考》,讨论和提议按照“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启示未来”的三结合原则编纂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2005年,陈维昭以个人之力所著《红学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具有两大鲜明特点:一是强调“纵横贯通”;二是强调“解释学立场”。关于前者,按照陈维昭在《绪论》所言:“从‘纵’的方面看,它以自‘红学’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为考察对象;从‘横’的方面看,它要把每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及海外(台港地区及其他国家)的《红楼梦》研究现象纳入视野。”此为率先将海外红学纳入红学史的研究范域之中,具有开拓性意义。再至2010年,李广柏所著《红学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下册设立第十六章“台湾、香港地区的红学”与第十七章“《红楼梦》在国外的流传及国际红学”,专题探讨台港地区与国外红学的发展历程与主要成果。以上两种红学史著作的出版,标志着21世纪之初中外红学史的初步对接。
由上六个重要环节可知,200余年来的红学史研究经历了从评点到研究、从论文到著作、从专史到通史、从本土到世界的演变。然而与本土红学史研究不同,海外红学史研究乃至中外红学史的有效对接,毕竟存在着跨语言、跨文化的重大障碍,单靠一人之力的确无法完成,所以特别需要充分吸纳从事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专家学者一同参与世界红学史研究。令人可喜的是,王丽娜、胡文彬、李绍年、姜其煌、孙玉明、张惠、高玉海、唐均、闫敏敏、陈宏薇、江帆、王燕、冯庆华、吕世生、王宏印、吴珺、谢依伦、高源、王琳等众多学者参与了海外红学的介绍与研究,并有一批重要论著相继问世,相信通过中外红学史的有效接轨,可以为全球视野中的“重写红学史”铺平道路。
二、全球视野中的“重写红学史”之意义
全球视野中的“重写红学史”,即是从本土的红学史走向世界红学史研究,并一同纳入全球视域中的“大红学史”体系之中。因而,本质上是基于本土——世界两个维度的红学史对话,具有“互观”“互补”“互鉴”“互融”之重要意义。
1.“互观”之意义
相同的《红楼梦》,不同的红学史。这是《红楼梦》在海外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在此,我们固然要重点关注那些有关《红楼梦》与世界经典名著的比较研究成果,诸如以《红楼梦》与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法国中世纪诗人特雷蒂安·德·特洛亚的长诗《帕西法尔》、英国女作家莎拉·司各特的小说《千年圣殿》、萨缪尔·理查生的小说《克拉丽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以及20世纪赛珍珠的《大地》、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与11世纪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17世纪朝鲜金万重的《九云梦》等进行的比较研究。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学术体系中的互观与对话,也就是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学术。李广柏谈到他于1993参加在北京香山举行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参加会议的中国内地学者提交的论文,大都是运用‘新批评’方法的,意在跟上国际潮流;而来自欧美的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几乎都是运用中国传统的考证方法作各种史料的考证,大概是欧美学者觉得到中国来开会应当入乡随俗。真是令人大跌眼镜!”由此可见中外红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源流关系以及明显的时空差。鉴于长期以来海外红学史被排除在整个红学史书写之外,而海外红学史本身研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与局限,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强对海外红学史的系统梳理、总结与研究,以便为中外红学史的“互观”提供新的学术基点与起点。
2.“互补”之意义
在20世纪的红学史叙述体系中,大致分为以考据学为主潮的新红学、以社会学为主潮的当代红学以及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红学的“三段论”,尽管中外学界对“新红学”存在不同的评价,但最终都难以撼动“新红学”的学术创新价值与地位。而就以社会学为主潮的当代红学而论,主要借助20世纪50年代的“批红运动”,即通过对现代“新红学”观念与方法的彻底清算,最终确立以社会学为主潮的当代红学传统。从中外红学史的发展曲线来看,上述三个阶段经历了一个合—分—合的演变过程,与本土红学的社会学—政治学主潮相对应,当时更趋多元发展的欧美批评界则以“新批评”为引领,所以也出现了诸多以“新批评”应用于红学研究的论著,诸如珍尼·诺爱尔(Jeanne Knoerle)由美国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评介》(1972),卢先·米勒(Lucien Miller,又译作卢西恩·米勒)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中小说的面具:神话,模仿和人物》(1974),普拉克斯(Andrew Plaks,又译作浦安迪)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1976),等等,皆为“新批评”应用于红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客观而论,由于《红楼梦》博大精深的容量与内涵,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新批评,都适合于红学研究,也都有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何况学术研究的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批判的武器,同时也取决于武器的批判。而就社会学与新批评而论,一重“外部研究”,一重“内部研究”,彼此正好构成内外对比与互补。
3.“互鉴”之意义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经典,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所以中国学者对于《红楼梦》的文化认同与深刻感悟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在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方面,海外学界更处于不断新变的前沿地带,所以在学术创新方面往往走在前列,但又不乏牵强附会或隔山望牛之憾。就此而论,身处欧美的华裔学者诸如夏志清、余英时、余国藩等则更能取其长而避其短。从夏志清《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余国藩《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等重要论著,皆可充分印证这些著名华裔学者同时兼具中国文化修养与西方前沿理论之长,所以彼此“互鉴”的意义与作用更为显著。历史地看,中外红学研究的“互鉴”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当代西方红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受到新红学尤其是胡适“自传说”的影响:赛珍珠同意曹雪芹的主题是讲述他自己生活的故事;史景迁、布兰道尔、帕兰得里都相信这部小说包含了许多自传性材料;夏志清、余英时、周策纵、余国藩也多认可《红楼梦》的“自传性”独特价值。彼此从不同方向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超越。进入新时期之后,大陆学界为突破当代红学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的局限,积极引进西方新理论新方法应用于红学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文化学、神话原型批评、心理学、美学、性别批评、后现代主义、比较文学、叙事学、阐释学、新批评等等,促进了传统红学研究范式的变革,激发了红学研究的新活力,拓展了红学研究的新空间。新时期“红学学术范式实践表明,时代精神、外来理论和学术创新是红学学术范式演变的核心动力、学理依据和内在要求;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外来理论的本土转化和文学研究的本位性则在红学学术范式演变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为红学研究结出新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值得认真总结和吸取的教训。与以往自发“互鉴”所不同的是,当今中外红学界可以更为自觉也更为从容地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互鉴”,相信这样的“互鉴”才能取得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4.“互融”之意义
比较之下,“互融”的重要性与难度系数都在“互观”“互补”“互鉴”之上。尽管海外红学史已逐步引起本土红学界的重视,而且在陈维昭《红学通史》、李广柏《红学史》等著作中,也都已将海外红学史内容纳入其中,但主要还是借助和引录既有研究成果加以综述,难免有泛泛之谈、深度不足的缺陷。而另一方面,这些被引录成果的学者主要分布在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由这些领域进入《红楼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跨界研究,则又往往缺乏对于红学研究尤其是红学史研究的深厚积累,其中也有一些如孙玉明、张惠、高玉海、唐均等学者,多能打通彼此之间的壁垒。基于全球视野中的“重写红学史”跨界研究的内在要求,一方面需要红学界更加关注海外红学研究,并不断提升从“互观”走向“互补”“互鉴”“互融”的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从事《红楼梦》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红学尤其是红学史研究,至少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中强化红学史意识。当然,比较可取的是跨界研究中的通行补救办法,就是组织两支队伍开展合作攻关研究,以实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之最大效应。
如果说中外红学史“互观”之意义是为“重写红学史”打开了新的视界,“互补”之意义在于中外红学史的“物理反应”,“互鉴”之意义在于中外红学史的“化学反应”,则“互融”之意义应臻于中外红学史的“生物反应”。
三、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之定位
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无疑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需要对其加以明确的学术定位。这里拟重点提炼为“时间—空间”“文学—文化”“传播与—接受”三重维度加以讨论。
1.时间—空间维度
时间和空间本是一切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当然也是学术史研究定位的两个基本维度。所以,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如何定位的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时间—空间”维度。其中的时间定位,需重点关注海外红学史中诸多“第一”的时间节点,比如乾隆五十八年即日本宽政五年冬,公元1793年12月25日,中国王开泰的“寅贰番南京船”从浙江乍浦港出发,1794年1月10日抵达日本长崎,所载货物内有图书,其中包括“《红楼梦》九部十八函”。《红楼梦》由此走出国门、传入日本,也是《红楼梦》在亚洲传播之始;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专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译的汉语语言教材《中文会话及凡例》在澳门出版发行。书中的会话第五篇与会话第二十五篇均选取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里宝玉和袭人对话的英文翻译。这是《红楼梦》最早的外文——英文翻译,也是《红楼梦》在欧洲传播之始;关于《红楼梦》在美洲的传播,据黄安年《1870年前〈红楼梦〉刻本在美宾州被发现》载:1999年,路德康教授在题为Asian Pioneer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Chinese Cutlery Workers in Beaver Falls,Pennsylvania,in the 1870s(《美国东部亚洲先驱:宾州水獭瀑布市刀具厂的中国工人》)的论文中提到有一本华工留下的《红楼梦》,于是作者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该市历史协会,并与妻子吕启祥最终确认1870年前《红楼梦》已经通过美国华人劳工传至美国了,此为《红楼梦》在美洲传播之始。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红楼梦》以34种语言翻译出版了155个不同篇幅的译本,各种中国文学史论著、“百科全书”对《红楼梦》的介绍与评述,以及一系列专题或比较研究的相关时间节点,这些时间节点的依次排列组合,具有学术编年史的重要价值。其中的空间定位,则需重点关注海外红学史的空间流向与区域分布。唐均《〈红楼梦〉译介世界地图》在这方面作了新的探索。作者搜集了中国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中已知的《红楼梦》译本基本信息,以所绘制的地图形式展示了《红楼梦》在东亚、西北欧、东南欧、北美等地蓬勃发展的空间传播态势。尽管此文主要聚焦于《红楼梦》的“译介世界地图”,但可以由此进一步拓展至《红楼梦》传播乃至红学研究史的“世界地图”。“文学地图之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关键在于时空轴心的转向与重构,即从以‘时间’为主导转向以‘空间’为轴心,以空间流向引领时间流程,所以文学地图的时空重构,首先体现在通过切割时间、重组空间的时间—空间化。”同样,海外红学史的学术地图也应注重时空定位,追求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的相互交融,而逐步臻于时空互化的境界。
2.文学—文化维度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是一部文学经典,但同时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结晶,因而是一部文化经典。所以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如何定位的第二个核心要素即是“文学—文化”维度。这里所言“文化”维度主要包括文化的包容性、主体性、变异性等不同指向。既然《红楼梦》是文学经典与文化经典的复合体,那么,作为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史也就远远不能局限于文学研究史,而是从文学进入到文化的形态与精神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红学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或者更确切说是二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历程与命运的一个缩影。此为红学文化包容性的主要特点之所在。关于红学的文化主体性,主要意指各个民族译介和阐释《红楼梦》的不同价值取向。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重点探讨了母语文化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认为母语文化对译者翻译文化观和翻译思维模式同时产生影响,而译者的翻译文化观和翻译思维模式对译者的风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译者的翻译文化观是显意识的,而译者的思维模式则是潜意识的。母语文化是译者的第一文化优势,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译者会潜意识或显意识地发挥自己的母语文化优势。另有李晓姝《东方主义视野下的〈红楼梦〉王际真译本研究》、唐均《〈红楼梦〉翻译中的东方主义问题撼拾》则探讨了西方《红楼梦》译介中的“东方主义”问题,认为即便是华裔学者——不管是受“东方主义”的浸润还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似乎都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潜在影响和束缚。关于红学的文化变异性,则主要意指不同时代文化思潮变迁之于红学研究的影响。张惠《红楼梦研究在美国》总结美国红学研究第一个特点,即是追随学科发展与理论更新,不断将新的观念、方法引入《红楼梦》研究。影响美国红学各个时期的理论思潮不同,如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社会学与哲学,70—80年代的人类学和叙事学,80—90年代初的统计学与修辞学,以及90年代之后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这是因为美国学界崇尚“科际训练”(Multiple Discipline),往往将各门各派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哲学、历史、人类、考古、心理、社会学等应用到红学研究上。尤其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率先踏入《红楼梦》研究的建筑、疾病、服饰等领域,试图综合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以及用统计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病理学、电脑、电视等种种方法和媒介进行研究,对红学发展的可能性做出全面尝试。尽管这些文化学术思潮与方法论的更替在欧美之间具有同频共振性,但在视野较宽阔、思想自由的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美国红学界特别善于提出一些问题,这些疑问也许是因为了解不够而产生,也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但它们可以启发灵感,刺激我们用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要之,在“文学—文化”维度中,“文学”一维指向《红楼梦》的文本译介与阐释,而“文化”一维所蕴含的包容性、主体性、变异性,则同时标示着红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3.传播—接受维度
传播学重在研究传播主体、受体、内容、媒介、效果以及通过传播而建立一定的关系。广义的传播学包括了传播与接受两个层面,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则多有重心落点之不同。就《红楼梦》的“传播—接受”双重维度观之,主要体现在译介、评述、阐释以及系列专题研究等方面。第一个层面即《红楼梦》的译介,乃是海外红学史研究的基础。注重从传播的维度看待《红楼梦》的译介,谢依伦《〈红楼梦〉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与李大博《海外译本与〈红楼梦〉海外传播的关系探析》具有“点—面”不同取向的范本意义。李文认为,海外传播是《红楼梦》文本价值重构的重要途径,也是红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通过全面梳理《红楼梦》海外译本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而阐发《红楼梦》在译介过程中所要着力关注的三大领域,即文化、美学、人学,并力图以此为《红楼梦》的海外传播提供全新的视角。谢文以1820—2018年近两百年为时间轴线,尝试还原和呈现《红楼梦》的传播主体、信息、途径、受众,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然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并参照世界红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未来的红学研究的拓展提建议。第二个层面即《红楼梦》的评述,乃是海外红学史研究的起点。主要呈现于海外中国文学史有关章节以及“百科全书”条目对《红楼梦》的评述。关于后者,姜其煌在所撰《〈红楼梦〉在欧美百科全书中的反映》中扼要论述了欧美百科全书中反映和评价《红楼梦》的变化与进展,从19世纪的空白,到20世纪前期评论的进步,中期的充分肯定,再到70年代以后“研究的深入,评论的准确,探讨的细微,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就是说,欧美整个学术界对《红楼梦》的认识,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与海外中国文学史有关章节的书写,集中代表了欧美学界对《红楼梦》的整体认知与价值评判的历史变迁。第三个层面即《红楼梦》的阐释,乃是海外红学史研究的重点。张惠《百年美国红学之路——范式、意义、不足与启思》一文认为,海外红学中,美国红学的成就独树一帜、成果斐然。回顾百年美国红学发展史,其研究分期、学术范式、所用版本、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但可与西方文论相结合,亦可开拓出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方式。美国红学的活力和发展,不但与中国红学密不可分,也对中国红学颇有启思。其中成果最为显著、最为丰富、也最具特色的是借助西方各种理论与方法对《红楼梦》进行意义重释,而且在夏志清、浦安迪、李惠仪、斯科特、裔锦声、余国藩等学者身上同时交织着多重理论的使用,只是因为他们文中的某种理论特别突出,不仅与自己所处时期的思潮合拍,而且出类拔萃足以秀出同侪,因而他们成为各时期理论思潮影响的代表。第四个层面即《红楼梦》的专题研究,乃是海外红学史研究的深化。这些专题研究广泛分布于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之中,具有学术创新的独特价值,但同时也容易引发新的争议。兹以美国学者卢西恩·米勒《为旋风命名:曹雪芹与海德格尔》为例,作者旨在对“通灵宝玉”同为“命根”与“祸根”的神奇合一提出新见,于是借用海德格尔关于人的生存概念观察,认为黛玉的觉察是很有见地的,宝玉本不该借一个非人的客体来自省。然而,从他的生命、他的实际情状的前定关联的观点来看,他又势必如此。这对他的“沉沦”,即他“沦入”与黛玉的爱网步步相悖。在实在的最深层次上,即形而上的(领域和石头的劫运)层次上,她是他的“对头”。确乎,当“通灵宝玉”果真失落,宝玉陷入痴呆状时(第九十四回),黛玉倒为之庆幸(第九十五回),实指望那“金玉良缘”之命就此受挫。而当她被自己的“沉沦”(她钟情于宝玉)和他对被抛状态的抗争所左右时,她自身也就融入了烦虑不安的弥漫性现身状态。所以黛玉不得不在梦幻中与宝玉亲近,而一旦梦觉,却又彼此疏离,无法沟通。直到二游太虚幻境得一僧一道点化后,终于从机械地遵从与玉石的一种确定关系中获得了自由,并且超越了实际情状与沉沦。此类专题研究,既需要海外学者去寻找与开拓,也需要本土学者去发现与总结,相信随着海外红学研究的深入与中外红学研究的交流,必将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四、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之实践
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需要由微观而宏观、由局部而整体、由分散而集成加以逐步展开,从而形成国别红学史、洲际红学史、比较红学史、世界红学史四个不同序列。
1.国别红学史
此为全球视野中“重写红学史”的根基所在。在既有成果中,以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张惠《红楼梦研究在美国》为代表,具有开拓性意义。孙著以时间为经,将日本红学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不仅比较准确地勾勒出了红学在日本的产生与发展趋势,而且对日本历代学人有关《红楼梦》的翻译、注解、评论和研究成果作了扼要的评述。张著主要对1960年起迄2000年止美国汉学界的《红楼梦》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并通过对这40年美国红学的研究成果的整理及其得失的总结,触及了相关的红学重大问题及其学术前景。首先,本书梳理了美国红学的方法、成就和影响,考察美国红学的学术价值及其在《红楼梦》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考索了《红楼梦》研究在美国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在传播过程中体现了怎样的特征,参与其事的学者构成;再次,就美国红学的特点、专长、不足以及和中国红学的交流做出了研究和判断;最后,总结了美国红学的贡献和启示意义,可以为我国红学研究提供重要借鉴。以上两书皆为国别红学史的成功尝试,具有先导与示范意义。而在重要论文方面,则日本伊藤漱平《漫谈日本〈红楼梦〉研究小史》(《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姜其煌《英美红学》《俄苏红学》《德国红学》(载姜其煌《欧美红学》,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张惠、王妍卓《美国红学史的学术史反思》(《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张惠《百年美国红学之路——范式、意义、不足与启思》(《光明日报》2022年1月3日),姚军玲《〈红楼梦〉在19世纪德国的译介和批评》(《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5辑),韩国崔溶澈《红楼梦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中华书局2018年版),谢依伦《〈红楼梦〉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但总体而论,目前的国别红学史研究还未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已经问世的国别红学史研究的论著毕竟为数有限,有的论文还停留于介绍性的文字,离学术史的内在要求之间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国别红学史这一根基还需进一步加以夯实。
2.洲际红学史
即以洲际地理为空间单位,重点分为亚洲、欧洲、美洲三大版块。《红楼梦》最先传入日本,此后亚洲的红学研究也是以日本为中心,以韩国为次中心,同时还流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但目前的亚洲红学史研究还没有从国别走向洲际,尚无亚洲红学史论著问世。关于欧洲红学史研究,目前同样未曾出现独立的学术论著,姜其煌《欧美红学》作为最先问世的欧美红学专著,因其研究重心在欧洲,庶几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作者借助自己精通欧洲多国语言之长,广泛收集了英、法、德、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红学资料,大致勾勒了“红学”在欧美中的发展历程与主要成果。周汝昌在《欧西〈红楼梦〉研究得失之我见——姜其煌著〈欧美红学〉序言》中指出:“像姜先生,精通很多种西语,却没有不屑于红学的意思,竟然为了介绍西方的红学状况而投入了这么多的工夫,写成这部品种独特的新著,以飨国人,填补了一个多年来无人肯填能填的红学空白,这不是一件小事。不但在红学史上,即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应该大书一笔的篇章节目。”从本书的著述宗旨与体例来看,作者并非要撰写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红学史,所以欧洲红学史还有赖于精通欧洲主要语种的学者承担这一学术使命。至于美洲红学史,与上述亚洲、欧洲红学史有所不同,主要集中于美国,同时波及加拿大。所以《红楼梦研究在美国》的作者张惠可以在此基础上著成美洲红学史著作。
3.比较红学史
按照英国波斯奈特(Hatcheson Mcavlay Posnett)《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所论“比较文学”的规范:“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则比较红学史研究需要同时思考如何确立空间单元、拓展学术路径、搭建交流平台等等。先说如何确立空间单元。其中最大的空间单元当然是中外红学史比较,姜其煌《欧美红学》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从主题内容、社会意义、艺术技巧和语言等方面对欧美“红学”和中国“红学”进行比较,并试图勾勒出“红学”如何随着西方中国“红学”的变化而变化。其次的空间单元是洲际之间的比较。通观亚洲、欧洲、美洲红学史,彼此同中有异。亚洲的红学重地是在东亚日本、韩国和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皆处于汉文化圈,具有汉文化共同体背景下独特的价值取向与研究传统;欧洲红学广播于英、俄、法、德、意、西、荷、瑞、保等十余个国家,在西欧与东欧之间,明显存在着两大文化版块、文化传统中的分野;北美的《红楼梦》传播起步相对晚近,红学研究史相对年轻,但最为丰富多彩,也最具学术创新活力。当然更为可行的是不断拓展非对称单元的多元化比较,籍此将比较红学史逐步推向深入。次说如何拓展学术路径。尤其需要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以及跨界研究的综合集成。比如中苏学者普遍注重《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彼此在理论与方法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1954年,苏联学者L.D.波兹德涅娃(L.D.Pozdneeva)在《论长篇小说〈红楼梦〉》中指出:“中国文学中的最伟大艺术家曹雪芹,创造了一部巨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实际生活。他揭示了统治阶级的最主要代表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的崩溃和中国封建家庭内部的矛盾。”“曹雪芹的这种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以前很多世界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所具有的矛盾,这种矛盾丝毫不会降低《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因为这部小说现实主义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充满于实际生活中的那些矛盾。小说作者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表现了‘下层’对封建社会压迫的反抗。除此之外,他的民主主义立场还表现在他在小说中面向人民,使用人民的语言写作,从而创造了一座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丰碑。”1959年,苏联汉学家O.菲什曼(O·Fishman)在刊于苏联《外国文学》杂志第4期的《红楼梦》(Son Krasnom Tereme)中认为:“《红楼梦》的伟大和力量,在于它勇敢地批评了封建制度,真实地揭露了被当时生活环境所扭曲了的人的悲惨命运。”O.菲什曼还特别关注到了“不同的时代产生了对《红楼梦》的不同评价。1911年辛亥革命时,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对满洲侵略者的讽刺。1919年文学革命时期,《红楼梦》被认为是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散文杰作,但它的社会意义遭到忽视。1954年以后,小说则被看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而不是作者爱情故事的自传”。这些观点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红学颇为相近,并对中国红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彼此可以展开综合性的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与跨界研究。又如美国红学界最具求变求新的鲜明特点,总是不断将新兴理论与方法引入《红楼梦》研究,从注重外部研究的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权主义以及注重内部研究的叙事学、修辞学、新批评等等,正好似“你方唱罢我登场”,红学研究几乎成了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试验场”。其中有的理论源地在美国,但更多的源自欧洲。所以在源地欧洲与引入的美国之间以及欧洲源地的不同国别之间,都可以展开综合性的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与跨界研究,如此追本溯源,显然有助于比较红学史研究的深化。再说如何搭建交流平台。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即是1980年6月16日周策纵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持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这是红学史上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首次单独为一部中国小说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极大拓展了《红楼梦》的国际影响,促进了中美两国红学界的接触、联系和交流,成为红学研究正式走向世界的标志。应该说,这样的会议之于比较红学史的效应与意义当非单纯的论著之可比。
4.世界红学史
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的最终成果是编写世界红学史。一个饶有意味的参照系是:1991年,比利时比较文学界的何塞·兰伯特在《寻找文学世界地图》一文率先提出绘制“文学世界地图”的构想。而后同是比利时籍的学者西奥·蒂汉即以此为基点,在所著《绘制世界文学地图》一文追溯和反思了世界地图“投射”于世界文学地图绘制的种种影响,演绎并比较了几种世界文学地图,重点分析了非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学者对世界文学格局的“重新定位”,最终提出以“椭圆”系统为单位、永远处在“流变”互通中的“完美”世界文学地图模式。蒂汉在文中结尾特别提出“逐步将世界文学地图扩展为世界文学历史地图集”,实际上是旨在强调将“空间”形态的“世界文学”扩展和转化为“时间”形态的“世界文学史”,以期实现全球空间观融入世界文学史观的变革。而在世界文学史编撰实践方面,则有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的先行创新。然后于201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中文版。全书8卷16册,近1000万字,几乎涵盖了全世界各个有文明记载的民族和区域,论述所及包括欧洲之外的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一些我国学界闻所未闻的、资料罕见的特定区域的文学创作,无论在篇幅规模,还是在时空跨度上,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学史研究工程。编撰者尤其注重采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以揭示世界各民族文学文化流播、传承、发展的规律和不同特色,并配有1000余幅珍贵的资料性插图,由此构成某种“图—文”互释的效应,有助于拓展我们原有的世界文学眼界和概念,继而更新我们对于世界文学的想象和图景,遂有“绘一幅力求完整的世界文学地图”、“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著作”之誉。对于世界红学史的研究与编撰而言,无论是何塞·兰伯特与西奥·蒂汉所提出的“绘制世界文学地图”的设想,还是俄罗斯科学院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的问世,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何况世界红学史毕竟只是由一部经典名著孕育与激发的专书学术史,其学术容量与难度系数远在《世界文学史》之下。就此而论,世界红学史虽然工程浩大,也的确超出了个体学者的能力,但完全可以通过协同攻关取得成功。
概而言之,一是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旨在突破既有红学史研究的局限,将本土红学史引向世界红学史,具有基于学术而又超越学术的多重意义;二是全球视域中“重写”而成的世界红学史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只是中外红学史的简单相加,更不能停留在内容上的简要综述与体例上的“附加”地位;三是全球视域中的“重写”世界红学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时期持续不懈的努力,主要取决于国别红学史的夯实根基与洲际红学史的重点突破,这两项工作要先行提前谋划与布局,然后才有足够的学术成果支撑世界红学史的编纂;四是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的关键问题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严重制约,尤其是跨语言的困境必须有赖于不同语种学者的通力合作、协同攻关方能完成,别无其他捷径可走;五是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特别需要引入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并与数据库建设和数字化平台相结合,助力重绘世界红学史地图。从一定意义上说,“重写红学史”即是重绘世界红学地图——不管是实体性的还是隐喻性的红学地图,都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实现视觉化、集成化、虚拟化,并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与“虚拟地理环境”(VGE)为媒介,系统绘制与立体展现集大成的世界红学地图,以期为全球视域中的“重写红学史”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籍此不仅可以超越纸质地图的种种缺陷,而且会收到数智赋能、迭代升级的理想效果。
①[16] 参见宋丹《〈红楼梦〉最早抵日时间的再确认》,《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2辑。
② 关于《红楼梦》译本的统计,主要涉及文献依据与统计口径等问题,所以难免有所出入。此据唐均《〈红楼梦〉译介世界地图》(《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期),统计时间截止2016年。
③ 引文据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④ 徐恭时《红雪缤纷录》(下),阅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568、574、576页。
⑤ 参见王正《松江才子朱昌鼎世系生平杂考》,《红楼梦研究辑刊》2012年第5辑;詹健《关于朱昌鼎的几项补考》,《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秦基琛《早期“红学人物”朱昌鼎的新资料考释》,《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5辑。
⑥ 张云《晚清经学与“红学”——“红学”得名的社会语境分析》,《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
⑦ 胡适《红楼梦考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初版《红楼梦》卷首。
⑧ 顾颉刚《红楼梦辨序》,载俞平伯《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7页。
⑨ [美]葛锐《英语红学研究纵览》,《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3辑。
⑩ 李广柏《红学史》下,广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41页。
[11] [美]夏志清《〈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台湾《现代文艺》第27期(1966年2月)。
[12] [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2期(1974年6月)。
[13] Anthony C.Yu,Rereading The Stone: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Chamb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美]余国藩《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中译本由李奭学译,台湾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
[14][22][27] 参见张惠《红楼梦研究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270、273页。
[15] 梅新林、曾礼军《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的演变及启示》,《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4辑。
[17] 黄安年《1870年前〈红楼梦〉刻本在美宾州被发现》,《人民政协报》2018年5月7日。
[18] 唐均《〈红楼梦〉译介世界地图》,《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期。
[19] 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04—905页。
[20] 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1] 李晓姝《东方主义视野下的〈红楼梦〉王际真译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13年;唐均《〈红楼梦〉翻译中的东方主义问题撼拾》,载唐均《红学·迻译·文化西行》,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5—402页。
[23] 李大博《海外译本与〈红楼梦〉海外传播的关系探析》,《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7第5期。
[24] 谢依伦《〈红楼梦〉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25][32][35] 姜其煌《〈红楼梦〉在欧美百科全书中的反映》,载《英美红学》,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8、1—9、95页。
[26][36] 张惠《百年美国红学之路——范式、意义、不足与启思》,《光明日报》2022年1月3日。
[28] [美]卢西恩·米勒《为旋风命名:曹雪芹与海德格尔》,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期,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4—145页。
[29] 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30] 张惠《红楼梦研究在美国》。
[31][33] 姜其煌《英美红学》。
[34] 苏联学者L.D.波兹德涅娃(L.D.Pozdneeva)时任莫斯科大学语言系东方部中国语文教研室主任,其《论长篇小说〈红楼梦〉》(0 Romane〈Son v Krasnom Tereme〉)首刊于1954年王力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语法概要》俄译本卷首。邢公畹将此文为中文,刊于《人民文学》1955年6月号,用以配合当时开展的批判“新红学”运动。1955年作家出版社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收录此文。文中主要观点对当时中国红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都有广泛影响。参见姜其煌《英美红学》,第92页;李广柏《红学史》下,第734—735页。
[37] [比利时]何塞·兰伯特《寻找文学世界地图》,转引自[比利时]西奥·蒂汉《绘制世界文学地图》,殷国明、刘娇译,《江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38] [比利时]西奥·蒂汉《绘制世界文学地图》。
[39] 参见颜维琦、曹继军《绘一幅力求完整的世界文学地图》,《光明日报》2014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