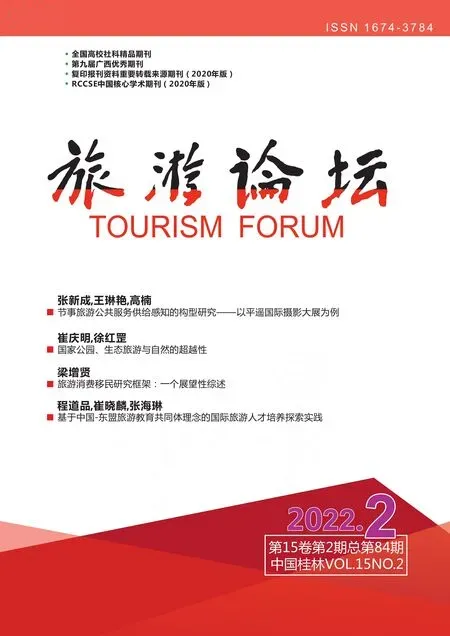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与自然的超越性*
崔庆明,徐红罡
(1.华南师范大学a.旅游管理学院,b.华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006;
2.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广东 珠海519082)
0 引言
现代世界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正日益影响着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应对环境危机,中国提出具有标志性、创新性和战略性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工业革命加大了对化石燃料的使用,随着各种技术的发明,加快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扭转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掠夺关系。资本主义对利润、积累的本质追求,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对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也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对自然资源的无尽开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体系上促进根本性的变革,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模式;同时还需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语境,探索解决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改革之一。党的十九大确定“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标。2019年6月颁布的相关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建立由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组成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其中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保护地类型。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抓手,国家公园建设既要体现生态文明,反思工业文明人与自然关系,也要显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基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构思生态保护工作。
关于国家公园建设,我国已经出台了具体的政策文件,学术界也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分析国家公园相关文件和文献,勾勒出我国国家公园试图构建的人与自然关系。现有文献对国家公园的讨论主要从自然作为物质的视角,主张在国家公园内禁止大规模的生产活动,限制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注重对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这是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影响而推出的政策措施。
与之相比,国家公园作为自然空间所具有的超越性意义在现有文献中极少讨论。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超越性(transcendence)是指超越物理/物质层次的存在或体验,往往与精神的、道德的、美学的、宗教的体验相关。物质性与精神性是事物的两个基本方面。自然不仅具有物的客观特征,也具有超越性的意义。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除了会造成物质层面的环境问题之外,还会导致人的精神异化。人与自然的疏离对人的身心福祉、环境态度和情感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自然空间具有精神疗愈的作用,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能够满足异化的城市人对自然绿色空间的精神渴求。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然的精神意义还具有文化特征。中国人对自然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建构和想象,这进一步影响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游实践,对保护地的建设也有重要影响。本研究认为应该根植于中国传统,挖掘国家公园的文化、精神等超越性的内涵。
1 国家公园与物质的自然
1.1 自然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从目前出台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主要是为了保护具有高生态价值的自然,体现在对自然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强调上。2019年6月出台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为“指导意见”)对国家公园下了明确的定义:“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域或海域,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同度高。”这一定义,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将保护对象限定为不受人为影响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景观、自然遗产等。
何思源和苏杨认为,强调自然原真性需要将生态系统恢复到一个健康状态,使其“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通过自然过程进行自组织”。生态完整性则指“生态系统支持和维持一个生物群落的能力,该生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多样性和功能组织可与区域内的自然生境相媲美”。这两点都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组成、功能和更新,人类及其活动被视为潜在的干扰因素。
保护自然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并不意味着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就不能够利用。关于如何保护和利用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现在主要衍生出如下三种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
1.2 三种自然观念
1.2.1 自然主义
2017年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对国家公园的定位是:“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最严格的保护这一要求,使得很多人和地方产生杜绝开发利用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的想法,试图摒除一切人类活动对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的影响。
生态保护领域对待自然资源有两种基本态度:保护(preserve)和保育(conserve)。前者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是不利用(no use),后者则认为自然资源可以合理利用(wise use)。杨锐认为,国家公园最严格的“保护”对应的英文应该是“preserve”而不是“conserve”,唯其如此才能够称得上是“最严格”的保护。这种拒绝利用的保护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即认为生态系统有其自发的演化过程,人类活动与自然过程相对立,人类影响应该被排除在自然生态过程之外。自然主义自然观认为存在纯粹的、质朴的、未经人类沾染的自然,自然主义保护注重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巩固。
然而自然主义保护观只部分地运用于国家公园体制之中。按照最新国家公园的分区管理规定,原则上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限制人为活动。核心保护区就是自然主义原则被充分运用的自然空间。在现有的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中,这一原则已被付诸实践。例如,从2018年9月起,普达措国家公园关闭碧塔海和弥里塘亚高山牧场,进行环境整治;碧塔海原是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核心景区,是自然资源和景观最好的区域。三江源在建设国家公园之前,就已经开展生态移民工作,将生活于生态脆弱的核心区的农牧民迁出集中安置。根据规划,到2010年,青海省需要对三江源18 个核心区的牧民进行整体移民,计划涉及牧民55 774人。生态移民或者生态恢复工程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对原始自然的破坏、利用和干扰,恢复重要生态系统应有的功能组织和自我更新能力。
1.2.2 有限工具主义
苏红巧等认为,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并不意味着杜绝对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的利用。中国建设国家公园需要考虑的特殊国情。正如沈国舫院士指出,中国人口众多,保护地范围内以及周边分布着大量社区,居住着大量居民,特别是中东部地区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国家公园建设需要考虑这些居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不能够“采用极端的环境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绝对化的保护也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国家公园具有公益性特征,需要对公众开放,让公众平等获取进入绿色空间、与自然接触的机会。
因此,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内可“划定适当区域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扶持和规范原住居民从事环境友好型经营活动,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支持和传承传统文化及人地和谐的生态产业模式”。这一制度和空间安排允许有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态产业,其中发展生态旅游是重要方面。但是,国家公园里的旅游发展方向不是大众旅游和过度开发。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主任张鸿文在报告中声明:“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其核心目标就是保护我国重要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不是为了搞旅游,更不能搞大开发”。国家公园旅游应该采用绿色发展模式,以低门票和公益性为主要特征,注重提升游客在生态旅游中的环境教育和深度自然体验。
对一般限制区的规定显示了对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以实用的态度将自然视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福祉的工具。但是,这里的工具主义又是有限度的,不提倡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而是在生态保护前提下合理利用。
1.2.3 原始主义
在国家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中,还隐含着另外一种自然观下的人与自然关系。因为保护地范围内人口稠密,所以生态移民工作压力大,有些原住居民并不能够及时从核心区域中搬离。对于这部分人群,“可以设立过渡期,允许开展必要的、基本的生产活动,但不能再扩大发展”,即允许一部分原住居民在核心保护区内从事基本生产活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这是一种原始主义的自然观,认为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较小,是一种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对自然往往采取大规模开采和剥削式使用,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无限生产,并创造市场需求,鼓动人们无节制消费,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而原始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也不盲目追求消费,只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小。因此,在无法满足自然主义保护原则下,原始主义生产方式在核心保护区内被允许保留一段时间。
1.3 自然作为物质空间
上述三种自然观念体现了我国国家公园政策主要将自然视为生态空间或物质资源。自然主义、原始主义和有限工具主义的取向表明我国国家公园尽量避免开发、开采、破坏物质的自然。这些策略是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超越。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物质使用。从狩猎-采集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现代工业文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规模越来越大、利用方式越来越复杂、转化出来的物质商品也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工业革命对化石燃料的发现和使用,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用自然资源。诺贝尔奖获得者Paul Crutzen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称为“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认为人类活动已成为影响地球环境最主要的力量。Steffen等发现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地球进入一个“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阶段。全球的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GDP、海外直接投资、水资源使用、交通、国际旅游等)与地球系统指标(如碳排放、氮排放、地表温度、热带雨林损失等)都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意味着我们正将各种自然资源快速转化为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增长。“人类世”下的社会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生态负效应。虽然罗马俱乐部早在1972年就提出增长具有极限的警告,但是世界各国的“增长瘾”(growth addiction)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无法彻底改变“增长瘾”及其造成的生态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增长、利润和积累的内在追求,使得其生产方式必然对自然资源产生掠夺。资本“不断尝试着超越自己强加给自己的限制……每一次数量上的增长都将成为新的界限,这一界限马上又被转变为一个新的障碍”,这种对无限增长的本质要求,对于自然资源来说是一场灾难。同时,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污染又对环境造成破坏,污染物无法转化为自然养分,或者重新转化为自然物质。奥康纳认为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自然既是一个“水龙头”,也是一个“污水池”;“水龙头”可能会放干,污水池也可能被塞满。为了消化过度生产出来的商品,实现经济增长,资本主义提倡一种无限消费物质商品的生活方式。人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消费、占有商品,人的需要被市场创造,是虚假需要。资本主义围绕商品生产和物质消费造就的物质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环境保护的重大挑战。因此,Moore认为,与其说地球进入“人类世”不如说地球进入“资本世”(Capitalocene),真正对自然资源产生剥削利用关系的根源在资本主义,而不是早就存在的人类29。
国家公园建设力图在某一空间范围内,逆转上述工业活动和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无限的工具主义使用。自然主义的保护应该是现行国家公园政策最终要达到的理想效果:国家公园成为动植物天堂,极少甚至没有人类的干扰。生态保护充分借鉴现代生态学、生物学、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成就,将保护建立在科学认知自然的基础之上。自然主义的取向恰当地响应了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的需要,既不把自然当作“水龙头”,也不把自然当作“污水池”。同时,国家公园建设政策还考虑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国情。我国自然保护地周边存有大量社区,需要解决这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在目前阶段允许有限的工具主义和原始主义的取向。历史上美国为了营造没有人为干扰的国家公园荒野区,强行迁徙等行为。中国国家公园采取不同的路径,不盲目追求建立荒野区,这响应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情境解决生态保护问题的宗旨。
综上所述,我国国家公园现有政策和学术讨论很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但主要是从自然物质性这一视角出发。自然要么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要么作为个体的动物植物,是需要保护的物质对象,是需要防止人类为了经济增长加以开采利用的物质资源。生态旅游作为发展路径得到认可,主要是因为生态旅游产业被认为对环境影响较小,是有限度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方式。
2 生态旅游与自然的超越性
2.1 旅游与超越的自然
自然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还是人类主观建构的对象,被人类赋予超越物质之外的多重意义。从狩猎-采集文明对自然的畏惧和崇拜,到农业文明对自然的适应和敬畏,再到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最后到后工业文明时代提倡对自然的尊重,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赋予自然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现代人对自然景观的精神向往,以及自然/生态旅游活动的流行,是在现代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工业发展加速了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迁往城镇居住生活并谋求生计。1600年之前城镇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2016 年城镇化人口已占到54%,到2050年居住于城镇的人口预计将达到总人口的64%。如此大规模的城镇化不但影响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还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和情感。居住在城市中的人能够直接体验自然的机会越来越稀少,这种现代人与自然的疏离也被称为“体验的消亡”(extinction of experience)。自然体验从日常生活中的消亡促使人们对自然景观产生了浪漫主义品位和精神需求。
工业-城市系统对自然的破坏从18世纪开始就影响着人们对自然态度的转变。例如,英国工业革命造成城镇化、环境污染以及乡村破坏,使得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人提倡重新认识自然的美和崇高。19世纪美国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也强调自然的超越性价值,主张人与自然建立联系,通过自然体验获取自由、精神和道德感。无论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还是美国的超验主义都是在反思工业主义中重新认识自然在精神、道德和审美层面的重要性。对自然的浪漫主义想象为自然旅游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浪漫主义对旅游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人们感知什么是美的和值得赞颂的,进而改变和扩大了人们在旅行中的观光清单”。
自然还被认为是工业文明的“解毒剂”。马克思早就指出现代工作会造成人的异化,对人的肉体和精神会产生负面作用。现代劳动分工将工作细分为越来越狭隘的任务,劳动者工作内容趋向单一,对其工作内容缺乏自我掌控。劳动者被化约为机器上带有自我意识的零件,其创造力和工作意义在单调中被逐渐榨干。休闲具有康复功能,能够缓解工作带给精神和肉体的压力,让人在自由时光中重拾自我。而与自然接触的休闲体验被认为对人的身心健康福祉大有裨益。英格兰峰区国家公园被传统工业城镇(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利兹等)包围,从19世纪开始峰区就是工人的重要徒步休闲空间。各个工业城镇逐渐成立规模庞大的漫步者协会,到20世纪工人阶级徒步旅行和漫游达到狂热的程度。美国国家公园的荒野保护初衷之一也是为美国人逃离城市生活提供公共度假地。在当今已完成工业化的社会中,工厂劳动带来的异化减少,但服务和知识型劳动带来的异化在增加;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工厂依然有着普遍的异化现象。因此,现代自然/生态旅游的重要动机依旧包含逃离城市中乏味的日常生活和追求健康。对于城镇居民来说,自然依然具有精神疗愈意义。
王宁认为理解旅游体验有两个基本视角:逃避主义和补偿主义。逃避主义认为旅游是“一种(暂时)逃脱日常生活的异化和千篇一律的休闲活动”;补偿主义则认为旅游是对“日常生活局限性的偿还、对‘平凡生活’的仪式性反转或对非凡体验的加强”。自然的超越性充分体现在这两个视角之中:一方面繁重单调的工作导致的精神异化使得人们想逃离日常生活,去往绿色的自然空间寻求精神的疗愈;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特别是城市中自然体验的消亡,促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疏离,发展出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品味,自然/生态旅游能够补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不能体验到的自然的审美、崇高、道德等。
2.2 中国生态旅游中超越的自然
随着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生态旅游活动也越来越普遍。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对生态旅游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休息、缓解压力、追求自然美也同样是中国生态旅游的重要动机。因此,与西方国家一样,自然也是中国人追寻精神疗愈、审美、道德等超越性体验的空间。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自然的超越性意义具有文化特征,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和民俗等文化紧密关联。中国对自然具有特殊的文化建构和想象,并在现代生态旅游活动中充分显现。
从人与自然的本体关系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哲学中的天人相分。张岱年认为天人合一中的“天”具有广大自然界的含义。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观和思维模式,不把自然与人类截然分开,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在联系互通。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的很多自然景观带有人文影响,并不刻意强调将文化因素排斥出自然之外,例如黄山“迎客松”即赋予植物以特定的文化含义。多种人与自然互动的实践模式都折射出天人合一思想,比如风水、山水等等,并历经千年历史留下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既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自然观念和环境实践,又继续影响着中国人在当代生态旅游中对自然的态度、观念和体验。
山水文化集中体现中国人对自然的文化想象,并从古至今塑造了中国人在自然中的旅行体验。山水文化既体现了古人的隐逸逃离,又表征着古人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建构。山水文化兴盛于魏晋南北朝,魏晋名士在政治上不得意,便逃逸于山林江海间娱情冶性,还创造大量山水画、山水诗、山水游记、书法等文学艺术作品,塑造了接下来整个中国对自然的审美取向。自然山水成为古代士人游乐寄情、抒怀咏志的重要对象,自然的精神、情感维度在山水文化中得到发现、强化和传承。
现在的风景名胜区体现的主要是中国的山水文化,区域内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融为一体。谢凝高认为中国自然景观往往带有丰富的文化意象、宗教意义、历史事件、传奇故事、艺术审美价值等。这些人化的自然景观(humanized nature)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逐渐形成,并在现代生态旅游中成为重要旅游吸引物。有关自然山水、名山大川的传统哲学、艺术、传奇等知识处处体现在中国中小学基本教育中,内化为每个人的一部分,例如提到中秋的月亮,很多人都会想起无数有关的诗词歌赋,提到庐山就会想起李白的诗歌等等。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风景名胜影响着中国人对自然和旅游的双重想象。
中国人去自然景区旅游,往往带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像是去一个历史文化中心朝圣,那些带有文化意象的名山大川更容易吸引中国游客。喻学才认为中国旅游文化有“重人”的传统,衡量风景名胜知名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与历史上的名人是否发生过关系。有些山水从自然奇观的角度来看并不出众,但如果曾有历史名人游览过此地,或者在此地有文人墨客的题咏,或者有历史事件、传说故事发生在此地,那么这个地方就能够成为旅游热点。田晓菲将这种旅行方式概括为“今/昔模式”,通过追思古代事件、人物、诗文来体验今日之景观,“通过时间来体验空间”。现代游客会通过古诗词来体验与之有关的自然景观。Yu和Xu发现三峡古诗词能够提升三峡自然景观的游客吸引力,增强游客的审美体验,因此中国人对自然的凝视是一种诗意的凝视。文学经典同时能够唤起游客观看自然时的道德感,例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依然能够得到岳阳楼现代游客的道德共鸣。中国山水“比德”的文化传统在今天的游客体验中仍然能够得到继承。中国自然游客对自然景观附着的文化、传说、故事更有共鸣,而对地质过程、动植物知识等解说不感兴趣。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旅游体验中的延续性并非一成不变。山水画、山水诗和摩崖石刻等高雅文化对当代旅游者的影响式微,大众游客在自然山水中很难准确识别或联想起具体的诗画,只能大致想到最出名的那些诗词或者山水画意境;而通俗文化依旧具有很强的影响,特别是附着于自然景观上的传说故事、民间信仰、好运口彩等附会依然能够引起游客兴趣,并影响游客的行为。
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然不仅仅代表生态过程或物质资源,还具有丰富的精神、道德、审美意义。这些对自然的文化想象从古至今影响着中国对自然的实践,在很多自然保护地中还留下了物质遗存。
3 国家公园与超越的自然
现有国家公园的政策旨在建设一个基于自然物质性的保护地,需要保护纯粹的、原始的生态系统,尽量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容许满足基本需求的原始主义生产活动和有限工具主义的绿色发展方式如生态旅游。本研究基于中国本土生态旅游的研究成果,认为国家公园建设需要考虑生态旅游的超越性,即在保护自然的客观、物质维度的同时,还需考虑自然的文化、精神维度。下面我们从三个角度讨论此观点。
3.1 自然的超越性能够促使国家公园的保护思想与保护对象达成内在统一性
目前国家公园试点划定的范围内,包含以前多种类型的保护地。例如长城国家公园试点区整合了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八达岭-十三陵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和八达岭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部分区域;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包含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九曲溪生态保护区。整合不同类型的保护地使得现有国家公园试点不得不协调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保护哲学。国家公园的建设目标是保护自然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在此保护观下,人造景观作为生态系统的对立面,不在保护范围之列,甚至是需要清除的人类干扰。但某些试点范围内包含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具有很高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人文景观,其本质上不属于生态系统。按照现有的目标,这部分文化景观未被纳入保护范畴,造成国家公园保护目标与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相互矛盾。大部分国家公园试点还包含风景名胜区,这些风景名胜区内也多少会有人化的自然景观,其中一些属于国家级和省级的文化遗产,也需要遵循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定。如果要恢复自然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否意味着将这些文化的自然景观再次生态化? 因此国家公园建设要协调其保护哲学与保护对象达成统一,必须考虑自然的超越性。
3.2 自然的超越性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内在地要求中国国家公园建设,需根植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走中国道路。中国文化赋予自然的超越性意义,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互动模式,它不但影响着现在国家公园内的部分物质遗产,还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何思源、苏杨、王蕾等的最新研究发现,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游客首选的是自然中的文化体验,这说明游客对国家公园内自然的超越性建构依然延续传统。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2018年城市化率达到59.58%,城镇常住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7.7亿。如此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对绿色空间有着极大的需求,城镇居民需要足够的自然空间作为缓解精神压力、逃离日常生活的休闲地带。国家公园能够很好地满足城市人口对自然的精神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赞同将国家公园内的自然景观都改造为人文景观或者完全按照游客的休闲需求建设旅游设施,而是认为应该考虑保护国家公园已有的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自然景观;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
3.3 考虑自然的超越性还能帮助国民建立起对国家公园的认同
“指导意见”除了要求国家公园“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之外,还要求国家公园“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同度高”。关于我国国家公园如何代表国家象征以及如何赢得国民认同,尚没有具体研究。19世纪的美国相较于西欧国家还处于文化自卑阶段,美国知识精英将荒野挖掘为美国相对于欧洲国家的“独特性”,继而构建国家认同和国民自豪感。我国国家公园的生态价值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可以通过国民教育,让人们认识到这些生态价值进而产生认同和自豪感。但是,除了科学路径之外,我国还可以将文化路径作为补充方案来塑造国民认同,人化的自然景观也可以成为国民认同国家公园的来源之一。中国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景观具有极高的独特性,这些景观是中国人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并内化到身体里的知识,与中国人有着亲密的情感联系。以国家公园内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然景观为基础,塑造国民认同应该具有天然的亲和性。
所以,从国家公园保护工作的内在统一性、国家公园路径的中国特色性以及国家公园的国家代表性和国民认可度来看,我国国家公园都可以将自然的超越性这一维度纳入考虑。从中国文化本位视角出发,对中国的山水文化、自然的文化遗产以及生态旅游研究已经非常多,但尚缺乏将这些已有成果与国家公园建设这一在新时代中的新目标、新任务相结合的研究。
4 结论
国家公园建设是响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工程。本研究通过分析已出台的国家公园政策文件以及国家公园相关文献,发现国家公园现阶段注重保护的是纯粹的、未受人类干扰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状态。这种自然观下人类被视为自然的对立面,衍生了三种自然观念:自然主义态度、有限工具主义态度和原始主义态度。这三种态度都将自然视作物质空间和实体资源,从物质层面反思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无止境的自然开发方式。
本研究认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还应考虑自然超越性这一维度。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具有独特的精神、审美和道德意义,在历史中长期影响中国人与自然的互动,并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不但成为当代旅游者的吸引物,还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看待自然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精神追求。同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也会导致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异化,需要绿色空间作为逃避日常生活和压力的精神疗愈场所。自然超越性视角能够基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将特有的自然与文化一体的景观融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自然超越性视角还能够为现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出现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学理辩护,为构建国家公园的国民认同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