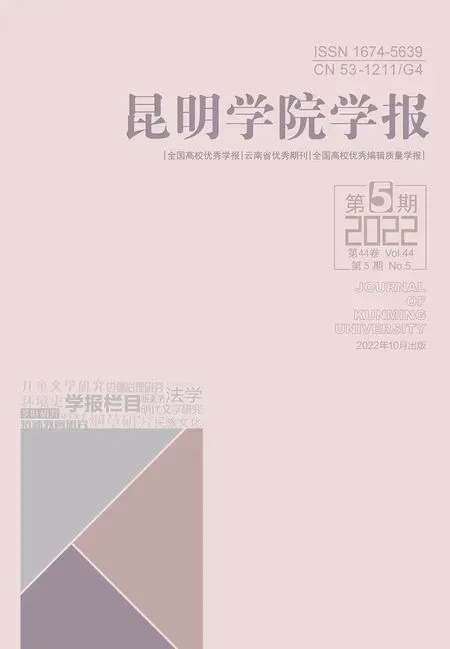现实与理想的“错位”
——《儿童世界》封面女童形象的现实化想象(1922—1941年)
钟佳晨
(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8)
民国时期的儿童读物,是伴随着现代社会转型及思想解放运动而兴起的。儿童作为“未开化”的小国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儿童世界》创刊前,虽已出现各种以儿童为内容的读物,但基本上依旧遵循“成人本位”,仍从成人的角度去看待儿童的世界。自《儿童世界》创刊后,“儿童本位”[1]的思想开始得到真正的践行。作为儿童文学运动的主要阵地,该刊物不断开拓创新,在内容形式和编辑理念上皆有所进步,每月销量达十余万册(1)数据来源:《儿童世界》1931年第28卷第9期中广告所述。,受到儿童读者的极大欢迎。本文即以《儿童世界》封面中的女童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封面男童形象和成人形象作为必要的参照,并适当结合内容分析方法(2)本研究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中的内容分析方法,从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探析。,从女童外在形象、活动环境呈现和男女童玩具选择等几个方面,探寻民国时期儿童刊物中女童形象的性别建构问题。
一、 《儿童世界》封面中“儿童相”的呈现
《儿童世界》作为民国时期专为儿童创办的期刊,该刊物封面理所应当的是以儿童形象为主导的。这其中,学龄前女童形象又占据了主体地位。参照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在视觉传播中,图像符号往往比文字更易被大众接受。[2]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图像符号的自然化以及表征方式的直接性。因此,对《儿童世界》封面女童形象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透过一个既独特又具有直观性的视角,更为全面地认识民国时期女童形象的建构特征及其意义所在。
(一)封面人物形象分布:封面女童形象占主体
本研究将以《儿童世界》1922年至1941年间出版的所有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在对该期刊封面逐一检索后得出如下结论:除去1940年,其他年份均未中断,获得19年间总共出版的525期(份)样本。经筛选,剔除与本研究无关的封面(例如有部分期数的封面已被撕毁、看不清等)后,最终确定本研究的总样本数为452份。其中以成年男性形象为封面的有20份,以成年女性形象为封面的有15份,只含男童形象的封面为54份,只含女童形象的封面为98份,男女童共为封面的有112份,性别特征不明显以及“精灵儿童形象”的封面数为28份,以家庭场景为封面的有22份,社会化景观(含科普知识、外国奇观、时事介绍等)的封面数为67份,只含婴幼儿封面数为3份,其他封面数为33份。该刊物在1932年1月第29卷3期停刊,同年10月复刊,由此后改为半月刊,此前为周刊。
本次研究将只含女童形象的期刊封面作品作为主要分析样本,将只含成年女性形象、只含成年男性形象和男童形象的期刊封面作品作为比较样本。笔者对上述期刊封面作品逐张浏览后发现,封面人物的年龄、穿着、发型,以及所处地域、环境和所玩玩具等指标可以从人物图像上直观判断。在指标数量统计前,已将无法判断的样本剔除本研究样本范围外。为了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整个过程按随机抽取的顺序对样本进行浏览。根据需要,对每一位人物形象从以下几项指标进行分类和编码。
1.年龄:分为婴幼儿、少年、青年和老年四类。(3)我国对年龄分段的最新标准为:0~6岁为童年期,7~17岁为少年期,18~40岁为青年期,41~65岁为中年期,66岁后为老年期。
2.穿着:分为西式洋裙/连衣裙、布衫/中式旗袍、西式短/长袖、童子军服以及未知五类。
3.发型:分为波浪卷、黑色直短发、黑色直长发、盘发(发髻)、后脑勺梳小辫戴帽子以及未知六类。
4.人物所处环境和地域:分为城市家庭、大自然、农村家庭(包括乡村劳作)、公共场所(学校、户外等)以及未知五类。
5.活动种类:分为汽车、骑马等刚性活动;洋娃娃、厨具等柔性活动;读书、艺术活动以及其他五类。
此外,本文研究的时间变量最终确定为三个时期:1922—1927年(共213期);1928—1934年(共201期);1935—1941年(共111期),如图1、图2所示(4)图1的样本数为35份,图2的样本数为152份。。

图1 以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为封面的数量统计

图2 以男童和女童为封面的数量统计
这是综合重要历史节点及搜集整理某时期集中出现某一类型封面形象后确定的,其原因为:第一,郑振铎、沈雁冰等人于1921年发起并成立文学研究会,而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儿童文学运动,《儿童世界》作为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运动的主要阵地,在儿童文学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学研究会……尤其是1927年以前的文学版图包括其中的儿童文学版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国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文坛各个流派出现新的分化与组合。”[3]又因《儿童世界》始刊于1922年,因此可以认为,1922年至1927年不仅是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运动的黄金时期,更是《儿童世界》刊物的初步成长时期。该时期的封面形象主要聚焦于精灵形象、婴儿形象和男女童形象。第二,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赢得国际承认,新政府的成立必然要推动“新国民”生活的变革。1928—1933年间,《儿童世界》封面作品主要集中于对家庭观、生活方式以及女童形象的描绘。第三,在童子军运动的推动下,1934年国民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其实质为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并为抗战培养“童子军”。
通过对图1、图2的统计可以发现,从数量来看,《儿童世界》封面人物形象整体呈现出女童>男童>成年男性>成年女性的排列特征。封面中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只是零星的出现,主体以儿童形象为主,尤以女童形象居多。从时间段来看,封面女童形象在1922—1927年占比达到最大。因此,本文对女童形象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儿童本位”的形象化呈现:学龄期女童占主体
王人路曾在《儿童读物的研究》一书中谈及,“凡是供给儿童阅读的书籍,都是要经过一番文学化。”[4]因此,他给儿童读物下的定义是:“儿童读物是供给儿童阅读的书籍,有活泼的思想,有动人的情感,有奇特的想象,用艺术的文字和图画,把他表现出来,而且能使普遍的儿童懂得且感兴趣的。”[4]可见,儿童读物的传播和发展需要考虑到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在内容选择上多以启蒙教化为主;在文字编辑和图画选择上,多被美化和理想化以适应儿童的观看方式。因此,儿童读物具有隐晦性特征,正是基于该特征,儿童读物更具备深入挖掘的空间。
年龄是人物形象的生理方面体现,封面人物的生理形象能够反映出该儿童读物的受众对象。郑振铎将《儿童世界》杂志的读者定位为“初小二、三年级及高小一、二年级的程度相当”[5],“根据当时的学制来推算,大概是9至14岁的儿童”[6]。读者群的年龄分布与该时期封面人物形象的年龄分布是否较为一致?哪个年龄群体更占封面主体地位?图3是本研究的数据结果统计。

图3 《儿童世界》封面人物形象年龄统计
从图3来看,在年龄的分布上,少年形象(学龄期(5)本文将儿童成长历程细分为三个时期:婴幼期(0~3岁)、学龄前(4~6岁)、学龄期(7~14岁)。)出现较多,与主编郑振铎将《儿童世界》的读者群定位为“初小、三年级及高小一、二年级”(7~14岁)基本相符。再结合图1、图2可发现,《儿童世界》的封面人物形象多为学龄期的女童形象。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封面中男女青年形象数量在不断增多。郑振铎曾说过:“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馆的知识一样。”[7]因此,1934—1941年间,《儿童世界》封面增加了身着军装的青年形象,并大量刊登战争实事、军人作战场景的实物照片。此时的儿童不再停留于生理和心理上的“儿童”概念,而是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上的“国民”概念。《儿童世界》刊物紧跟时局发展步伐,旨在培养知晓“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小国民”形象,儿童不再囿于家庭,而是被成人赋予了能够参与到社会的、追求独立自主的“小国民”的期待。但在该时期具有政治意义的“国民”形象却更多指向于男童和成年男性形象,如此一来,封面中为何要花大量的版面展示女童形象呢?这需要重点考究。
二、现实与图像的“错位”:“中西杂糅”与“阶级分化”下的女童形象建构
《儿童世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主要发行于民国时期最为繁华的城市——上海。因此,该封面中的女童形象整体呈现出囿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黑色直短发+连衣裙+小皮鞋”式的女童形象。这一形象正是受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与现实中的女童形象相差甚远。对民国时期女童形象的总体特征及其成因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封面女童形象。
(一)外在形象的呈现:“黑色直短发+连衣裙+小皮鞋”式的女童形象
衣着搭配是人物角色形象的表现,封面人物的外在形象能够反映出该时期社会化性别角色的情况。作为儿童,父母是他们性别社会化的第一任启蒙者,他们按不同的性别角色标准来塑造孩子的社会性别,主要表现在衣着和发型两个方面。在对封面人物形象进行初步筛选后,本研究将人物的衣着分为西式洋裙/连衣裙、布衫/中式旗袍、西式短/长袖、童子军服和学生装五类,实在无法辨别的归为“未知”类。社会性别的塑造需要符合社会性别认同和性别期待。从封面人物的外在形象的统计入手可以发现期刊中大量出现女童形象的原因。那么《儿童世界》封面中女童形象的整体风貌如何?该封面女童形象的塑造是基于知识分子想象还是现实描绘?笔者将从该杂志封面女童形象的衣着和发型两方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见图4、图5)(6)图4、图5的样本都为98份。。
从数据来看,随着年代更迭,女童在衣着和发型上的变化较为微妙。本研究并未对封面男童的外在形象进行统计,原因在于经笔者对只含男童的封面人物作品进行逐张浏览后发现,男童形象搭配较为统一:多以立领或圆领的汗衫短裤、童子军服、西装小皮鞋或学生装的形象出现。即男童人物的外在搭配较为单一、单调。

图4 《儿童世界》封面女童形象衣着统计

图5 《儿童世界》封面女童形象发型统计
从不同时期来看,前期(1922—1927年)的女童形象多身着中式旗袍,头扎蝴蝶结,而后这一形象逐年减少,多以连衣裙、蝴蝶结和小皮鞋的形象替代。封面作品中还较多地出现了西方儿童的形象:金黄色卷曲的头发、灵动的大眼睛和华丽的蓬蓬裙,若是仙子还会拥有一对蝴蝶般或蝉羽般透明的翅膀(7)见1922年第2卷第7期、1922年第3卷第1期。。但整体而言,民国时期女童主要以黑色直短发、连衣裙、小皮鞋,有时还头戴一顶小帽子的形象出现。这一形象是“中式风”和“西式风”的杂糅,黑色直短发是民国时期学生形象的“标配”,而小皮鞋和连衣裙却是“舶来品”。这种“中西风”杂糅的儿童形象在《儿童世界》封面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综上描述,本文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其一,1922—1934年间,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国内陆续掀起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西方“儿童本位”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冲破传统道德规范的重要武器。表现在图像叙事上,《儿童世界》作为中国期刊史上最早的儿童刊物,其封面女童形象多为西化的中国女童形象。这一形象与现实中的女童形象之间是否相似呢?笔者在对比《儿童世界》中刊登的读者真实照片后发现,现实中的女童形象与刊物封面所呈现的女童形象相差甚远。现实中的小读者大多身着旗袍,束马尾辫。这就不得不怀疑该杂志对女童形象的描绘是不是基于西方世界而建构出来的虚拟形象。在这些建构的图像下,女童具有极大的个人自由和空间,她们的童年是美好、快乐、自由、平等和友爱的,她们没有悲伤和苦难,更没有当时中国人民苦难的影子。“郑振铎在创办《儿童世界》之初就强调该刊总体上是力求满足儿童的一切需要,但绝不迎合现行社会里各种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心理和家庭的旧习惯”[8],编者在选择当时较为流行的“中国故事”时显得非常谨慎,同时对于其他国家有适合于中国儿童的作品,他都会尽量予以登载,这或许是绘者和编者心中较为美好的童年模样。他们不仅旨在培养儿童正确的民族观,还希望让儿童建立起新的世界观,使儿童具备世界性格局和视野。
其二,虽然《儿童世界》封面女童形象出现的频率相较于男童形象偏多,但是该刊物所刊登的读者照片多为男童形象(见图6(8)选自《儿童世界》1929年第23卷第9期“读者照片”一栏。、图7(9)选自《儿童世界》1923年第6卷第3期“爱读本刊者照片”一栏。),女童形象几乎没有。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有二:第一,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和由此掀起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儿童从作为大人的“附属品”到“儿童本位”思想占主导;妇女从丈夫的“附属品”“失语者”到开始拥有话语权。因此封面上的女童形象逐渐增多,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儿童形象——女童和男童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同等自由。第二,女性的发型、衣裙、帽子等变化相较于男性,其表现形式更为多样,这也是封面女童形象出现较多的主要原因。但若从刊登的读者照片来看,女童的照片极少出现,这也可看出该杂志期待的女童形象与现实的差距。总体而言,《儿童世界》封面刊登的女童形象为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兼具完美性和典范性的理想形象,其虽与现实形象相差甚远,但却体现了当时的知识精英对儿童的深切期盼。《儿童世界》作为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儿童刊物,对当时儿童与成人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图6 读者照片
(二)活动环境的呈现:囿于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女童形象建构
活动环境能够反映出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活动环境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是人物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的体现。杂志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方式,其借助隐喻或转喻的方式传达着意义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那么,知识分子所塑造的是哪一阶层的女童形象?女童形象和成年女性形象在整体风貌上是否存在一致性?笔者将以图8、图9的数据(10)图8样本为98份,图9样本为54份。进行分析并解释。[1]

图8 《儿童世界》封面女童所处环境和地域统计

图9 《儿童世界》封面男童所处环境和地域统计
本研究将封面人物的所处环境分为城市家庭、农村家庭、大自然和公共场所四个部分,实在无法辨别的归到“未知”一类。划分标准主要为:城市家庭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家庭特征为主,农村家庭以中国底层家庭的样貌为主,公共场所以少植被的水泥地和高楼建筑面貌为主。
从图8、图9的数据统计中可以发现,女童的活动环境多为大自然或家居环境;而男童的活动环境多为公共场所、农村家庭和大自然。正如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所提倡的“自然教育”“儿童期是感官发展”[9]的教育理念,大自然是调动儿童感官发展最好的老师。首先是《儿童世界》封面中的女童形象在衣着、发型的塑造上具有明显的西化特征——深黑色齐肩短发、连衣裙配小皮鞋的形象。这一形象多出现在户外活动中,如学校组织的郊游、看电影、参加舞会等;其次是女童形象出现在拥有圆桌台灯、小宠物的新式家庭中。笔者通过检索民国时期上海家庭的照片发现,封面中的女童形象多为当时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女童形象,即这一形象是在“中西杂糅”和“阶级分化”下的建构品,而对于绝大多数贫苦家庭出身的女童形象依旧是“长袍/布衫+布鞋”搭配。
值得注意的是,封面中还出现了零星的新型女性形象,这些新型女性形象的塑造给民国时期女童的成长培养提供了新的方向。女性在公共场所中出现的频率增加,在该杂志中女性的温柔、贤惠、善良、慈爱等特质和男性的勇敢、主动、冒险、刺激等特质得到了少许的颠覆如图10(11)1927年第19卷第6期封面。。又如图11(12)1931年第28卷第14期封面。中呈现的成年女性形象:一头干练的短卷发,身着女式西装,左手提着挎包,右手夹带报纸,似乎匆忙奔走于学堂途中。再图12(13)1933年第30卷第2期封面。中的女飞行员形象和图13(14)1932年第29卷第2期封面。中三位女青年的形象,她们身着上衣和裤子,均为短发造型,正以“冲锋陷阵”似的气势抛雪球,这一气质一般多用于描绘男性形象。

图10 《汽车比赛》

图11 《到学堂去》

图12 《向天空飞行》

图13 《雪人》
从上述四幅封面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呈现出干练、独立的形象特征可以看出,这些零散的、刚性的女性形象萌芽反映了该时期女性地位的缓慢上升,体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力倡男女平等观的良苦用心。但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这些零星出现的新型女性形象,作为“星星之火”却不足以燎原,女性多处于家居环境,而男性多奔走在公共场所,性别角色分工依旧显著存在。女童形象整体依旧参照着“囿于家庭”的温柔好静、善良慈爱的“贤妻良母”式新型成年女性形象进阶。
三、“模范形象”的塑造:洋娃娃与“贤妻良母”型的未来角色定位
玩具作为儿童的至爱,陪伴着儿童的点滴成长。“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10]玩具的制作和选择反映出社会对儿童的性别期待,儿童的性别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建构起来。其中男童多与刚性活动(如开汽车、骑马等)联系在一起,而女童多和柔性活动(如洋娃娃、小动物等)共同“出场”。模范女童形象与“贤妻良母”型的未来成年女性形象无缝衔接。两性的社会角色在玩具的分类中被生产和再生产,直至最终符合社会对两性的性别期待。
《儿童世界》封面中的儿童活动,可以大致分为刚性活动、柔性活动、读书、艺术活动及其他五个类目。其中刚性活动主要包括野外冒险、竞争、远行(玩具汽车、竹马等包含在内)等。柔性活动主要包括玩洋娃娃、荡秋千、吹泡泡、逗小动物、织毛衣、浇花、洗衣服、手工等活动。那么,《儿童世界》封面的女童形象在玩具选择中将表现出怎样的性格气质?女童形象又朝着怎样的成长角色发展呢?以下是本研究的结果呈现与分析(见图14、图15)(15)图16样本数为54份,图17样本数为98份。。

图14 《儿童世界》封面男童游戏种类统计

图15 《儿童世界》封面女童游戏种类统计
从图14、15可以看出,女童多以玩洋娃娃、荡秋千、保护小动物、做家务、吹泡泡等柔性活动为主;男童的兴趣点多在开小汽车、射击、爬树、打球、赛跑等刚性活动上。从人物的衣着发型、行为举止和活动种类可以看出人物的性格倾向,男童和女童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男童主动,女童主静;男童顽皮冒险,女童温柔持家。周作人说过,“玩具是为了小孩儿做的,但因此也可以看出大人们的思想。”玩具的设计和分类必然体现着大人对小孩的性别期望,并迎合了社会对男女的性别认同,由此形成的性别刻板印象将在儿童的成长中根深蒂固。
在中国古代婴戏图中,儿童的游戏多为推枣磨(16)参见宋代李嵩的《秋庭婴戏图》。、泛舟、爬树等;玩具多为拨浪鼓、小鸟、风筝、不倒翁、竹喇叭等。[11]男女童在游戏和玩具上几乎没有明显的性别区分,因而性别概念在儿童期也较为模糊。随着民国时期西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洋娃娃、小汽车、足球、射击”等舶来品大量涌入,儿童虽然作为一个暂未被“社会化”的群体,但其性别社会化(17)性别社会化是指人们将其所在社会的性别规范内化的过程。性别社会化的内容涉及性别期望、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社会通过各种手段教化个体有关性别规范和相关的象征意义,个体同样加入这一过程中,学习和使用性别规范。[10]却伴随着西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儿童玩具的涌入而提早至儿童期,对儿童的未来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男女童在玩具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趋向。从儿童喜欢的玩具来看,洋娃娃就如同女童的宠物、伴侣或“孩子”一般,她们在洋娃娃的“陪伴”下成长,在这过程中慢慢学会了温柔、呵护和慈爱,她们在社会中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如图16)(18)1924年第11卷第4期封面。。

图16 《哭后》
“在儿童生活中,游戏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游戏是儿童理解、拖延、超越生活的方式”[12]而成人对儿童的期望也倾注在儿童玩具上,这便是社会对女童的性别期待。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曾说过:“在每天无数的小活动中,我们社会化地再生产着——亦即制造和再制造着——性别。”[13]“两性的社会角色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学习、领悟和效仿;同时两性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在社会化过程中被生产和再生产。”[13]玩具作为儿童接触最多,也最喜爱的小物品,在两性社会角色的分类中被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导致了性别刻板印象的生成和固化。《儿童世界》封面女童形象整体朝着新时代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模范形象进阶。这是特定时代的发展要求,也是时代的局限。
四、结语
《儿童世界》封面女童形象的塑造打破了当时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从当下而言,该杂志的儿童形象塑造却是性别刻板印象形成的开端。封面中女童多以黑色短发,身着连衣裙和小皮鞋,手拿洋娃娃的形象出现,活动内容以柔性活动为主;男童以身着汗衫短裤、童子军服、西装和小皮鞋形象出现,活动内容以户外冒险类刚性活动为主。这是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其源头可溯源到清末民初西方文化的介入开始,因此,《儿童世界》可视为现代儿童形象形成的初始缩影。性别角色作为一整套文化期望的集合,规定了性别成员应有的言行举止、外在穿着以及应当采取的行为方式。《儿童世界》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儿童刊物[14],了解其封面女童形象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民国时期女性国民形象的建构。该刊物在民国时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启蒙读物”,其封面中所塑造的女童也因此被当作“模范形象”而备受推崇。儿童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所接触的日常玩具和实践活动,都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不同时代的“模范儿童”形象。《儿童世界》封面女童形象,实可谓现代社会中性别刻板印象和角色定位逐步形成并日益固化的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