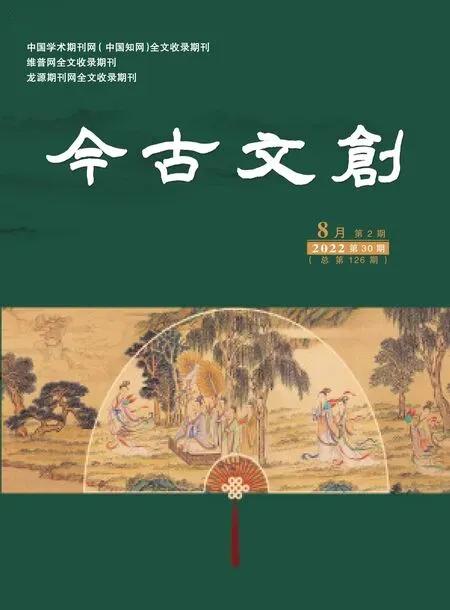广州话止摄字今读研究
◎胡智轩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一、绪论
按照对《广韵》读音的拟测,止摄开口字韵母为*i,止摄合口字韵母为*ui。广州话支脂之微韵无法作为分开讨论的条件,按不同声组止摄开口字ei、i二分,合口字ɵy、uɐi二分,此外有部分例外。
二、止摄开口字今读ei类
中古止摄广州话今读ei的有帮组、泥组、见、溪、群、晓母开口字。在1782年《分韵撮要》中上述所有字都位于“幾纪记”韵,并与知组、章组、疑、影、喻母开口字同韵,可知当时读音仍然为i。由i裂化为ei为近代广州话一大演变趋势,1841年裨治文《广东方言读本》在序言已有提及:é pronounced as a in may, lay, and as ei in neigh. 1855年湛约翰《初学粤音切要》中帮组泥组率先裂化,而见组仍未脱离*i韵。1856年卫三畏《英华分韵撮要》提及见组字的裂化。
这类字中与灰韵、齐韵相混的例外比比皆是,此外还有开合相混例。
(一)止灰相混例
黴 正读mei21,异读mui21。mei21对应《唐韵》武悲切,表“物中久雨青黑”义。《广韵》虽有又切“莫佩切”,义为“点笔”,然不但意义与“黴”迥异,去声的读音也与平声的“黴”有别,因此不能视为异读来源。mui21的读音受“梅雨”“霉雨”讹变而来。“霉”为后起字,始见于《正字通》。共同语止开三唇音字与灰韵字很早就合流了,“眉”“梅”《中原音韵》同为齐微韵梅小韵,但广州话两组字读音至今仍不相同,“梅”“霉”同而与“黴”有别。因此在表“物中久雨青黑”义时表义更具直观性和形象性的“梅”“霉”覆盖了本字“黴”,完成字形替换的同时连带着为“黴”新增了一个外源的mui21的异读。
(二)止齐相混例
祕 正读pei33,异读pɐi33。pei33对应《唐韵》兵媚切,徐锴《说文系传》:“祕之言闭,祕不可宣也。”
俾 读音有pei35和pʰɐi33。pei35对应《唐韵》并弭切,表“使、从”义。pʰɐi33见于《集韵》:“毗至切,鼻去声。俾倪,衺视貌。通作睥睨。”
泌 正读pei33,异读pɐi33。
糜 正读mei21,异读mɐi21。mei21对应《集韵》忙皮切,mɐi21对应《广韵》靡为切。
荔 读音为lɐi22。《广韵》有力智、郎计二切,力智切*li表荔枝义,按反切及广州话今读规律应读lei22,且“荔枝”古音和广州话今读皆为叠韵可为旁证;郎计切*liei表香草义,lɐi22的读音对应这条反切,且 “薜荔”古音和广州话今读皆为叠韵可为旁证。然而现在的状况是音义错配:以表香草义lɐi22的读音表荔枝义,而荔枝义理论上的读音lei22又不存于广州今读。明人方以智《通雅》云:“荔本为马蔺、薜荔,合溪、敬甫俱云从刕,三刀茘乃协也。其实无此字,但以力得荔音,以附离为义也。”可以得知:上古“荔”仅有表示香草的一音一义。古籍“荔枝”原本写作“离支”,不知自何时始换用“荔”而逐渐完成对“离”的覆盖。白居易《荔枝图序》云:“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那么字形换用过程完成的时间应该就是白居易其时及稍后的共同语止齐合流完成的时间。于是“荔”新增止摄读音,一字对应二音二义,音义各自配对,无所牵连。最后大概是荔枝使用频率高且香草义多弃本名用俗称,表香草义的“荔”遂淹没不彰,中古两个“荔”完成合并。绝大多数地区的粤语今读都是“荔”“离”有别的,虽然字形也受共同语影响而混淆,但是读音的差别仍可窥见“荔”并非“荔枝”本字的事实。
由此可见,齐韵和止摄有的方言合流了,有的方言仍然走上两条不同的演化路径。但是数量众多的异读也使我们不能否认广州话存在一个止摄与齐韵合流的层次。这个层次发生在支脂之微合并之后,止摄合一与止齐合流先后作用于早期粤语,处于两层作用之间的粤语在止摄字的读音上并不完全规律。受止齐合流层次影响较深会使单音字读同蟹摄细音,受此影响程度较浅则为本读ei、i的字输入异读ɐi。
(三)齐撮相混例
裏 读音有lɵy13和lei13。《分韵撮要》“裏”凡三见:“裡,幾韵,理小韵。表裡”“裏,诸韵,吕小韵。内也”“裡,诸韵,吕小韵。表裡,亦内也。”由此可见“裏”在近代有*li和*ly两种读音。后来,li裂化为lei,ly裂化为lɵy。“裏”“里”有别的现象集中在广州及香港、澳门、佛山及粤北等受广州话影响较大的地区,但在大部分的粤语区“裏”“里”是无别的。因此很难以语音上的条件来说明这种差异,只能推测是一种自源变化。
这或许与《分韵撮要》的音系性质有关。作为一本通行于广府地区的、供人致函修书的韵书,很难不让人相信它具有以省城话为音系基础,夹杂郊区及附近各县特点的综合性质。从作者的身份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黄锡凌认为1782版作者是顺德周冠山,而1885版《增辑字音分韵撮要》在序言前标明作者为南海伍殿纶。从历史沿革看,南海县和顺德县和省城关系密切,至今仍与番禺并称“南番顺”。粤语区止开三读y的现象大量存在于佛山。
尽管出现的条件是精庄组字而“裏”不属于此列,或许是使用频率过高导致过度类推的结果。这个佛山地区的读音反过来扩散到广州,后港澳政府以广州音为官方语言继而接纳了这个音。韶关在抗战时期涌入大量广府人口,作为强势方言广州话几乎推平了原先的粤北土话层,时至今日韶关各区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精庄组读y的字。
履 正读lei13,异读lɵy13。《分韵撮要》只有对应lei的读音*li而没有对应lɵy的读音*ly。新增的合口读音或许是受同义词“屦”kɵy33(*ky)的感染作用影响使得韵母由齐齿变撮口,但是“屦”实非易字,又或者是和“屡”字形相混而带有lɵy音,也可能是“裏”通过词汇扩散形式将撮口读音带到“履”,只是时间在《分韵撮要》之后,故韵书本身没有体现出来——不过目前仅有此例,这种扩散力度之弱似乎不太可信。
还有可能是北方官话层次的影响。官话“履”直到《五方元音》仍然仅有*i读音,在《国音常用字汇》*li已经变为又读而liu为正读,其中变化过程不知道起于何时及因何缘由。官话有一些*i→*y的例子,如轩、剧、薛、略、削等,最难说明的是合口作用究竟本自何方。又或许如上文所述,官话可能亦将“履”和“屡”字形弄混,给“履”新增“屡”音。
三、止摄开口字今读i类
中古止摄开口精、知、庄、章组及疑、影、喻母字广州话今读i。《分韵撮要》“几纪记”韵和“师史四”韵存在对立,前者如上所述仍读舌面元音*i,后者按共同语及粤语次方言应读ɿ。这部分仍然和蟹摄相混的最多。
(一)止佳相混例
舐 正 读sai13,异 读 有si22、sai35、lai35、lim35、lɛm35。《广韵》“俗‘舓’字” ,“舓”《唐韵》“神旨切,音士”,因而理论上的读音为si22。sai13和sai35读同佳韵,却不见于韵书,而闽语、赣语、客语都有韵母读ai的。
或许可以怀疑ai的读法是上古支部二等残留。共同语很早失去该读音,因而中古以降的韵书失收的同时这个音却保存在南方各大方言之中。从人口迁徙与今天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ai读音自北往南数量递增的趋势。自张九龄挖通大庾山,越来越多的移民经由韶关进入广东东北部再扩散至珠三角,也将客赣方言的ai读法带到粤语。随着后世南方方言日益被官话层次冲刷,南北方言分界线节节败退,可以看到吴语已经没有ai的读法;闽语、客语、赣语也仅保留零散的ai韵母,相对靠北的赣语点,如长江南岸的九江湖口、庐山星子甚至有ʂʅ的读音;粤语则绝大部分读ai。
至于lim35、lɛm35则 是“舔”tʰim35的口语 读 音。lai35估计是受sai13和sai35影响,经历ʦ→s→ɬ→l音变完成从擦音到边音的转变,与lim35和lɛm35关系似乎不大。中古的擦音上古往往读为塞擦音,如心母字“赐”“伺”国语和粤语都有塞擦音读法。
玺、徙 读音为sai35,理论上应读si35。
国语精组止摄字韵母几乎都读ɿ,唯独“玺”“徙”二例韵母为i,因而可以猜测:这两个字脱离了精组字的演变趋势。《切韵指掌图》时代精组字从*si往sɿ演变,具有相同语音条件的它们没有与主流共同演变。当舌面元音舌尖化的作用完成之后,它们仍然保留*si的古读,《中原音韵》“璽、徙、枲、洗、屣”五字同属齐微韵洗小韵*i可为证。而音变规律是有条件性的,当一定音变规律作用结束之后,它们便不能再受到同样音变规律的作用。直到18世纪它受腭化作用影响,以离散式音变的方式从舌尖辅音s变为舌面辅音ɕ,在国语里与齐韵开口字合流。
国语的今读可以证实这两个字在音变上的滞后性,而非“玺”“徙”等字为避讳“死”而先于“死”发生例外音变。今天粤语区仍然有“玺”“徙”韵母读i的地方,如宁明、北海、融水、宜州、蒙山、武宣、浦北,而绝大多数地区二字韵母不是ɐi就是ai。在所有的心母止摄开口上声字脱离“死”*si之后,“死”在音韵系统内再也没有同音字。它并非因避讳而发生的例外音变,而是一种声韵共同配合作用下的规则音变。除了舌尖化,中古精组止摄三等字还有一条声母腭化的音变道路,两条音变规则先后作用,导致同一韵部产生两种语音形式。
(二)止齐相混例
蚁 读音为ŋɐi13,理论上应读ji13。
毅 ŋɐi22,理论上应读ji22。与“蚁”同理。
早期粤语先后经历止摄合一层和止齐合流层影响,有一部分止摄字读同蟹开三四。此三例皆疑母字,不受止摄规律影响而受止齐合流层影响,疑母则不再脱落,遂与“倪”“诣”等齐韵字同音。 “蚁”在粤语区大致有如下演变链:ŋi(高明)→ŋei(江门)→ŋɐi(广州)
筛 读音有sɐi55和si55。此字先秦不见,始见于《汉书》。此字中古二读,支韵所宜切,亦作“簁”;佳韵所佳切,亦作“籭”。上古支部分化为中古的佳韵、支韵和齐韵。si55源于支韵;sɐi55虽源于佳韵却与齐韵同韵。
使 正读si35、si33,异 读sɐi35。si35和sɐi35在《分韵撮要》之前的韵书看不出任何区别。按卫三畏《英华分韵撮要》,“使”虽有二读,但是读si2是和不吉利的词(即“死”)同音。
驶 正读sɐi35,异读si35。与“使”同理。
(三)i、ei二读例
死 正读sei35,异读si35,理论上应该读si35。
四 正读sei33,异读si33,理论上应该读si33。
肆 正读si33,用于“放肆”“食肆”等词;异读sei33,用于表示数字“四”的大写。
上述三例属于回避同音字变读。先前说到“玺”“徙”的例外读音并非出于避讳,而“死”*si→sei的音变则是因避免与后起同音字同音而变读。近代广州话tʃ系并入ts系,在两组塞擦音合并进行中而“死”未变读时,有些率先与“死”合流的tʃ系字产生了*si之外的读音,如“驶sɐi35、使sɐi35”等字选择变韵,而“矢ʦʰi35、豕ʦʰi35”等字选择变声。两组塞擦音合流后“死”与原本不同音的“史、屎”等字同音。因为新并入的原tʃ系字短时间内不可能先后或同时进行声母上的tʃ→ts及韵母上的避讳变读两种音变,所以反而是给“死”新增sei35的读音。按语音演变的常例,广州读ei的上声字只能从帮、泥、见、晓四组字来,因此广州话“死”就没有同音字了。
以“四”为声符的“驷”字仅有si33一音,可见 “四”读sei33同样不具备语音上的分化条件。在广府人看来“四”“死”二字仅有去上之分,同样具有不好意头,继而“四”及以“四”为声符的“柶”“泗”也新增sei33的读音,这种作用又连带可用作大写数字的“肆”多出sei33一读。至于除“四”“肆”外其它的心母字并不会带有不好意头,大概是数目字日常生活使用频率极高,但凡和序数、数量、日期有关的事物都需要避开。
四、止摄合口字今读ei类
中古止摄非组与帮组同读ei。例外如下:
疿 正读fɐi33,异读fɐi35、fɐi22、fei35。
费 读音有pei33和fɐi33。
肥 正读fei21,异读fɐi22。
上述三例微韵合口唇音都有ɐi的读法。如前所述粤语存在止摄读同蟹开三四的层次。以开例合且同为唇音,道理是一样的。从地域分布来看可以推导出pʰui→fui→fi→fei→fɐi的音变链。
五、止摄合口字今读ɵy类
中古止摄合口字泥、精、知、庄、章组读ɵy。以开例合,可以构拟出中古的合口形式是*ui。在波乃耶1888和1897两版《简明粤语》ui和öü的不同注音中可以大致看出音变过程:韵尾i使韵腹u往前往低先至ʊ再到央化为ɵ,韵腹u将韵尾i圆唇化为y,遂与遇三泥精见晓组、灰韵端精组和祭韵合口合流。这类字没有例外。
六、止摄合口字今读uɐi类
止摄合口字见系今读uɐi,与祭韵、齐韵合口见系合流。例外如下:
彙 正读wɐi22,异读wui22。
与“黴”受“霉”影响同理,此例通过字形替换连带以新字形读音覆盖旧字形读音。“彙”“匯”在简化过程中因都有聚集义而被合并为“汇”,而“汇”“匯”音同而与“彙”有别,换用字形的同时以“汇”的读音覆盖“彙”,因而“彙”新增异读。“黴”“彙”同为微韵字,“霉”“匯”同为灰韵字,官话方言两韵皆归齐微韵梅小韵,致使广州话少部分微母合口字产生同声组的灰韵异读。
七、结语
止摄字的广州话今读与古音类对应关系总体来看是十分规律的,四类主要的读音中i是古读,ei、ɵy、uɐi都是高元音两折化的结果,ɵy、uɐi除止摄外亦见于遇蟹等摄。例外音变数量较少,产生的原因包括合音、感染、避讳、形混、借字及层次叠加等等,有的展示了不同读音的不同来源,有的展示了不同的历史层次,有的则是讹误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