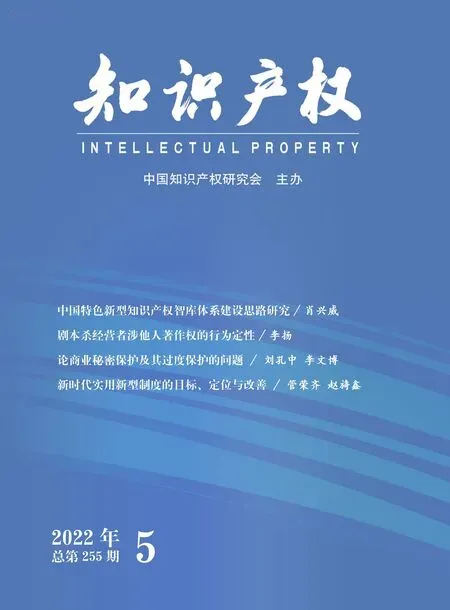论我国《著作权法》中出租权规则的协调和完善
张伟君
内容提要:2020年《著作权法》第39条第2款已经明确录音录像制品中的作品著作权人是享有出租权的,虽然这与第10条有关作品出租权的规定以及第44条第2款的表述并不协调,但是这个规定其实是合乎法律逻辑的,不仅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国立法遵循国际条约的需要。为了减少法律规则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冲突,并且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因为目前出租权规则缺陷而带来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应该对著作权人享有的出租权作出更为合理和协调的制度安排。
一、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有关出租权的变化及引发的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改之前并没有赋予著作权人出租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一书的说明,2001年《著作权法》是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第11条的要求对出租权作出的规定。根据2001年《著作权法》第10条的规定,出租权是指“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因此,“享有出租权的是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和计算机软件”。于是,主流观点认为,音乐作品、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在我国并不享有出租权;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权可以用来禁止未经许可制作的任何作品复制件的出租。
在邻接权保护方面,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虽然也没有赋予音乐作品表演者或者文字作品的朗读者以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但令人意外的是,却赋予了录音录像制作者出租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这个规定依然与《TRIPS协定》有关。根据著作权法释义一书的说明,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一些工作组成员对中国保护版权及相关权利的法律与《TRIPS协定》的一致性表示关注,提出《著作权法》的修改应与《TRIPS协定》第14条的规定相一致。为履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2001年《著作权法》按照《TRIPS协定》的要求,增加规定了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出租并获得报酬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此后任何人要出租录音录像制品,都要取得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并向其支付报酬。
因此,在2001年《著作权法》的框架下,就录有音乐作品或文字作品的录音录像制品而言,只有录音录像制作者享有出租权,而作者和表演者均不享有该项权利,当然也无法从出租录音录像中获取报酬。2020年《著作权法》第39条第1款有关表演者所享有权利的第5项规定,新增了“许可他人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但是,对于这个规定的解读,存在不少争议和困惑。
首先,关于这次修改为何要赋予表演者这项权利,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在几乎不存在录制品的出租市场,不会因为没有赋予表演者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制品的权利而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以下简称WPPT)的要求相违背,也无根据《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为表演者规定出租权的义务,因此,“如果”立法者意识到了我国并无这个义务,2020年《著作权法》为表演者规定的出租权涵盖表演的视听录制品原件或复制件的出租,就是立法者的主动选择,并不是为了与条约相符。但是,上述观点中对我国立法者主观“意识”的假设,可能是不成立的,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副主任石宏博士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重要内容及价值考量》一文明确指出:“近年来,我国相继加入了一些与著作权保护相关的国际条约。为了将有关国际条约中规定的义务落到实处,回应国际关切,这次修法作了以下修改……(三)增加表演者许可他人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文提到,WPPT第9条规定了表演者的出租权,《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第9条也规定了表演者的出租权,“为了强化对表演者权利的保护,并与国际条约接轨,本次修法增加规定了表演者的‘出租权’,即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可见,究竟是立法机关对国际公约的要求作出不同解读,还是立法机关额外赋予了表演者出租权,尚未可知。
其次,关于出租录有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是否须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也存在疑惑。2020年《著作权法》并没有对著作权人享有出租权的客体范围进行调整,因此,即便《著作权法》赋予了表演者出租权,而录音录像制作者本来就享有出租权,也不能认为著作权人(特别是音乐作品和文字作品)必然也享有出租权。正因为如此,2020年《著作权法》第44条只是规定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录像制品须同时取得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的许可;但是,就出租录音录像制品而言,并没有规定须同时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而仅须取得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的许可。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2020年《著作权法》第39条第1款新增了表演者的出租权后,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第2款的表述,并没有像第44条第2款那样排除出租录音录像制品须著作权人许可,而是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第5项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被许可人以第3项至第6项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既然出租录有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还须著作权人许可,这里的著作权人显然包括被制作成录音录像的音乐作品和文字作品的著作权人,那么,从这个规定来看,我国《著作权法》其实已经赋予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之外的其他作品(比如文字、音乐作品)以出租权。2020年《著作权法》为何作出如此前后不一致的规定,究竟是因一时疏忽而忘记了对第39条第2款同步进行调整,还是刻意为之——目的就是允许文字和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也享有出租权,同样不得而知。
上述因法律规定的前后冲突而带来的法律解释上的争议,恐怕难有一致的结论。值得讨论的是,从立法论而言,我国《著作权法》是否应该赋予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等专有的出租权呢?本文认为,撇开在当下我国出版物出租市场几乎消失的情况下出租权的赋予是否真的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无论从法理上来说,还是从国际公约的要求来看,在表演者和录制者都享有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租权的情况下,我国《著作权法》不赋予作者(著作权人)同样的出租权,是不应该的。对此,试作以下分析。
二、保护邻接权人利益却不保护著作权人利益违背了《著作权法》的基本宗旨
只要表演者表演的是一个尚处于著作权保护期内的作品,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录有该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就应当取得该被录制的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许可。虽然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等邻接权是独立于著作权而存在的,但是,因为著作权法首先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在一般情况下,就对作品、作品的表演、作品的表演录制品的同一个使用行为而言,无论是复制(对作品进行录音、录像;制作录有表演的录制品;翻录录有作品的表演的录制品等)、发行录有作品的表演的录制品和公开传播录有作品的表演的录制品,原则上都必须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但是,是否须得到邻接权人的许可就不一定了。各国著作权法都赋予了著作权人最广泛的专有权利,而邻接权人享有的专有权利往往不如著作权人广泛。显然,这样的制度安排体现了著作权法的首要目的在于鼓励作品创作和保护作者权益,一般来说,对著作权是强保护,而对邻接权是弱保护。
以我国《著作权法》为例,表演者迄今为止依然不享有对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公开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录音制作者也只是在2020年《著作权法》修改以后(新增的第45条)才获得了机械表演和广播录音制品的报酬请求权(依然不是专有权利)。唯一的例外是,对出租录有作品的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情形,我国《著作权法》却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著作权人不享有出租权,邻接权人却享有出租权,在2001年《著作权法》中是如此(只有录音录像制作者享有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租权),在2020年《著作权法》中依然没有改变(虽然增加了表演者对录有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租权)。
对此,笔者也曾撰文提出过质疑:立法还是应该尽力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既然《著作权法》已经赋予录音制作者出租权,并准备赋予表演者出租权,那么理所当然也应该赋予音乐作品作者出租权。这也是著作权国际公约的要求,因为音乐作品作者在录音制品上享有复制、发行、传播等各项专有权利,当然也应该享有出租权,否则有违《TRIPS协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CT)的规定。连表演者、录制者都对录音制品可以享有出租权,却独独不给予音乐作品作者出租权,道理何在?既然音乐作品作者在录音制品上可以享有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却独独不能给予其出租权,道理何在?
三、国际公约对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著作权人赋予专有出租权的要求
(一)我国是否可以“自行决定”拒绝将出租权赋予录音制品中的作者
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出租权仅仅限于影视作品和计算机软件,而没有就出租录有作品的表演的录音制品(以及录像制品)赋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出租权,是否违反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TRIPS协定》和WCT的要求呢?结合上文分析来看,我国立法没有赋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出租录音制品的权利,显然是因为《TRIPS协定》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对此,许超先生也有详细的分析:录音制品涉及多种权利人,包括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的制作人。众所周知,作者和表演者的贡献处于上游位置,制作人的贡献应当位于末端。如果只赋予制作人出租权,而制品中包含的作者和表演者却不享有出租权,是否不合逻辑?《TRIPS协定》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的出租权“原则上适用于录音制品制作者,适用于成员域内法所确认的录音制品的任何其他权利持有人”。从这项规定可以看出,录音制品的出租权首先是赋予制作人的,至于是否赋予录音制品涉及的其他权利人,例如作者或者表演者,则取决于这些权利人是否被“成员域内法所确认”,即由缔约方域内法自行规定。
上面提到的《TRIPS协定》第14条关于出租权的规定是该条第4款的第一句,英文原文的相关表述为: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1 in respect of computer programs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nd any other right holders in phonograms as determined in a Member's law(第11条关于计算机程序的规定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应适用于录音制品制作者和按一成员法律确定的录音制品的任何其他权利持有人)。那么,如何理解这里的“按一成员法律确定”?更确切地说,“按一成员法律确定”到底是由国内法来确定究竟哪些人属于“录音制品的其他权利持有人”,还是国内法在确定哪些人是“录音制品的任何其他权利持有人”之后,还可以进一步确定这些人是否可以享有录音制品的出租权?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与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对此作出解释:根据一成员的国内法,出租权应该既适用于录音制品制作者,也适用于由该国内法确定的在录音制品上的其他权利持有人。如果该国内法并没有决定在录音制品上还有其他的权利持有人,那么,依据第14条,该成员仍有义务将出租权授予录音制品制作者。从该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录音制品上到底存在哪些权利人,各国并不完全统一,因此,这确实是可以由一国国内法决定的。比如,在我国,一个录音制品上其实并存着三个权利人(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而在美国版权法中音乐作品和音乐录音(sound recording)可以享有版权保护,却没有规定音乐表演可以享有版权。但是,无论如何,按照《TRIPS协定》的规定,如果一国国内法已经明确录音制品上的权利人是哪些人,那么出租权就应该全部适用于任何一个权利人,国内法并不可以对各个权利人厚此薄彼。所以,本文认为,虽然按照《TRIPS协定》的规定,不排除在有的国家作者不被认为对录音制品享有权利或者录音制作者可以享有比作者更多的权利,但是,因为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在一个录音制品上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都是权利人,所以如果我国《著作权法》按照《TRIPS协定》的要求应该赋予录音制品出租权,立法也实际上已经赋予了其出租权,那么,出租权就不应该仅仅赋予录音制作者,而应该同时赋予作者和表演者。
上述理解也可以从两位德国学者莱因伯特和莱温斯基对《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一句以及与WCT第7条第1款的关系的分析中得到印证。根据他们的分析,《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一句关注的是录音制品制作者以及 “按一成员法律确定的录音制品的任何其他权利持有人”的出租权问题,从第14条的标题来看,很明显,制定这一条款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理有关作者的权利问题。但是,他们也承认,也有人认为,根据这个规定,作者也可以享有出租权,只要作者被认为是 “录音制品的权利持有人”,甚至他们对这个观点的合理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他们认为,首先,确实(indeed),“录音制品的任何其他权利持有人”只能从作者,例如音乐作曲者和歌词作词者身上去找,在《伯尔尼公约》和国内立法中,作曲者和作词者对使用有他们作曲或作词的唱片,是享有法定权利的。因此,尽管“录音制品的任何其他权利持有人”这一术语的概念不是很明确,但是作曲者和作词者可以被认为是录音制品的任何其他权利持有人。其次,上述观点也为《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的缔约历史所支持。制定《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一句的目的,是为了要求已经给予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作者以其他所有权利的《TRIPS协定》的所有成员,也必须给予这些作者以出租权。如果对这句话的解释使得这些作者不享有出租权,则这句话提及“其他权利持有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此外,即便说《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一句并没有赋予作者出租权,但是,WCT第7条第1款关于出租权的规定与《TRIPS协定》第11条明显不一样——享有出租权的主体明确增加了“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作者。对此,莱因伯特和莱温斯基认为,尽管如上文所作解释,WCT的这一规定其实已经被涵盖在《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一句,但是这一规定构成了“TRIPS plus”,至少在法律的透明度和清晰度上是如此。换句话说,WCT第7条第1款已经对于《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一句话中没有明确的“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作者也应该享有出租权进行了明确。我国作为《TRIPS协定》和WCT的成员,应该履行公约义务,赋予“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作者出租权。
为了确认对两位德国学者的观点的理解是否正确,2020年8月1日笔者特地发邮件就如何理解上述“由国内法决定”的含义咨询了该书的作者之一莱温斯基教授。8月3日莱温斯基回复邮件,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并强调这是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一直以来的观点。而且,她认为中国有义务赋予在录音制品中体现的作品的作者以出租权,因为作者在录音制品上是享有出租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
(二)“减损测试”例外是否允许我国不赋予著作权人对出租录音录像制品的专有权利
在1994年4月15日《TRIPS协定》生效前,出租属于发行行为的下位概念,权利人不能禁止他人出租合法购买的录音制品,结果使录音制品的复制品的发行数量明显下降。于是,一些国家立法征收出租业的版税,这样,即使权利人无权禁止他人出租录音制品的复制品,也能够多少降低损失。但是,通过征收出租版税降低权利人损失的只有少部分国家(甚至美国都没有出租版税制),在一些国家强烈要求下,《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一句首次赋予录音制品独立于发行权的专有出租权。不过,《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二句又允许成员不规定录音制品的出租权,但是要符合两个前提:第一,在1994年4月15日一成员在录音制品的出租方面已实施向权利持有人公平付酬的制度(a system of equitable remuneration);第二,录音制品的商业性出租不对权利持有人的专有复制权造成实质性减损(the material impairment,即所谓的“减损测试”)。在符合这两个前提的条件下,则可维持该制度。
且不说我国是否可以满足第二个条件,因为在1994年4月15日之前,我国并不存在出租付酬制度或者出租业的版税,不存在拒绝规定录音制品出租权的可能性,所以在我国加入WTO之前的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时,当然就赋予了录音制品出租权。WCT关于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出租权的规定中,第7条第3款有关“减损测试”的规定与《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二句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国也不能依据“减损测试”的规定而否定对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出租权的保护。
但是,我国《著作权法》还将出租权也赋予了录像制品,而《TRIPS协定》并没有对录像制品作出规定。这是否就超越了《TRIPS协定》的要求呢?因为录像制品与电影作品具有表达形式上的相同性,有的国家也对两者并不加以区分,所以我们可以从《TRIPS协定》对电影作品出租权的要求来加以分析和回答。根据《TRIPS协定》第11条有关电影作品的出租权的规定,一成员对电影作品可不承担此义务,除非此种出租已导致对该作品的广泛复制,从而实质性减损该成员授予作者及其合法继承人的专有复制权。这就是电影作品出租权的“减损测试”,即,如果满足“减损测试”,一国可以不规定电影作品的出租权。
那么,《TRIPS协定》规定“减损测试”的背景是什么呢?在20世纪90年代《TRIPS协定》谈判的时候,市场上主要是模拟录像带,由于复制技术原因和图像质量问题,将出租的录像带进行家庭私人复制的行为不是很普遍,复制权也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在模拟技术时代缔约方事实上就没有义务授予电影作品以出租权(比如美国版权法就没有赋予电影作品出租权,笔者注)。然而,在数字环境下(如出租DVD),上述结论可能要发生变化了,一个拥有DVD碟机的家庭,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拥有一台录像机或其他的录制机器,因此这个家庭就可以将两台机器相连进行复制,这种新的私人复制将会损害复制权。回想一下,我国在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的时候,正是DVD碟机大行其道的时候,也确实会发生私人制作复制件的情况,所以,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拒绝赋予电影作品出租权,甚至直接同时赋予了电影作品和录像制品出租权,应该也是考虑到了当时我国音像制品产业的实际状况。
总之,按照《TRIPS协定》的要求,既然我国《著作权法》应该赋予也已经赋予了录音制品和录像制品出租权,那么,也应该赋予以录音制品或录像制品体现的作品的著作权人出租权。这才是合乎《TRIPS协定》和WCT的要求的。
四、美国版权法也赋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对录音制品的出租权
在上文提到的莱温斯基教授回复笔者咨询的邮件中,她也承认:对于是否应该赋予录音制品中的作者(著作权人)出租权,是有争议的(I kn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is question),所以,这也是《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一句为何采用如此复杂表述(即,由成员法律决定的在录音制品上的任何权利持有人)的原因。她认为:这是妥协的结果,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并不想赋予作者出租权,所以,那些国家可以对“由国内法决定”这个表述作出不同的解释。
确实,如莱温斯基教授所言,美国版权法中不存在独立的出租权,出租权被包含在发行权中,并且适用“首次销售”原则,即一旦作品的复制件合法售出,就不再受发行权控制,也就不能禁止合法售出的复制件的出租。因此,美国是不愿意将出租权普遍地赋予所有作品的权利人的。特别是,美国版权法没有赋予也并不希望电影作品享有出租权,所以《TRIPS协定》第11条关于作品出租权的规定的第二句话中才会有这样的除外:“一成员对电影作品可不承担此义务,除非此种出租已导致对该作品的广泛复制,从而实质性减损该成员授予作者及其合法继承人的专有复制权。”有观点指出,《TRIPS协定》第11条第二句的这种起草方式,就是把美国排除在外了,因为关于授予电影作品以出租权在美国是有争议的,但它又同时尽可能地让更多的国家规定这种出租权。
但是,与对待电影作品出租权的态度相反,美国版权法并不否定音乐作品的作者对录音制品享有出租权。早在《TRIPS协定》谈判之前,美国版权法就承认,尽管有首次销售原则,但在录音制品和计算机程序上享有出租权。对禁止未经授权出租这些作品,美国版权法规定了若干条件和例外。就录音制品而言,录音制品的所有人必须是在未经该录音制品所包含的录音(sound recording)和音乐作品(musical work)的版权所有人授权的情况下,为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商业利益,以出租(rental)、租赁(lease)或借阅(lending)或具体出租、租赁或借阅性质的任何其他行为或做法的形式进行的。这里明确提到了要取得音乐作品版权所有人的授权这个条件,说明美国版权法并不否定音乐作品的版权人对录音制品的出租享有权利。所以,即便按照美国国内法,音乐作品作者是享有出租录音制品的专有权利的,并不受首次销售原则的约束。当然,《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第一句中刻意增加“由成员法律决定”的表述,或许也是为了满足美国版权法对录音制品出租权所设定的各种条件(比如为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商业利益)罢了。对于由美国主导的《TRIPS协定》来说,为了满足美国的需要而作出这样含糊的表述也并不奇怪。
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欧盟,录音制品上体现的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出租权,就更不是问题了。欧盟1992年通过的《出租权和借阅权指令》对于除建筑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以外的所有种类的作品,都确立了准许或禁止借阅的专有权。这项规定当然也适用于了音乐作品。正如莱温斯基教授所言,这是欧盟一贯的立场。
总之,即便《TRIPS协定》中存在对出租权的种种限制,欧盟国家依然明确作品的作者对录音制品享有出租权,哪怕对版权人享有出租权向来持消极态度的美国版权法(比如规定电影作品不享有出租权)也依然规定无论是音乐作品还是录音的权利人都应该享有录音制品出租权,而并没有“依据本国法”决定不赋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出租权——可见,如果采用这样的制度安排,对著作权人来说恐怕是很不公平合理的。因此,从著作权国际规则的要求来看,《TRIPS协定》第14条第4款的规定中,无论是第一句“由成员法律决定的录音制品上的任何权利持有人”的表述,还是第二句成员可以不赋予录音制品专有出租权的例外规则(保留原有报酬规则),都不应该成为我国《著作权法》不赋予录音制品中的著作权人出租权的国际法依据。相反,我国应该按照WCT第7条的规定明确赋予以录音制品体现的作品的著作权人以专有的出租权。
五、明确美术和文字作品等享有出租权是我国司法审判和文化市场的现实需要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因为我国目前并不存在成规模的作品载体出租市场,没有出租权也不会对作品的发行和权利人的利益造成什么影响,因此出租权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有没有出租权无关紧要。本文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我国《著作权法》将出租权从发行权中分离出来后,却没有规定文字、美术、音乐等作品享有出租权,已经给我国法院审理一些涉及出租盗版作品复制件的纠纷案件带来了困惑。
在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发行” 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因此,发行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出租行为,虽然依据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出租合法售出的作品复制件不会侵权,但出租盗版的作品复制件,就会侵犯发行权。但是,2001年《著作权法》将出租权规定为独立的专有权利后,发行权中的发行行为仅仅是指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转移其有形载体的所有权的行为,这样对于出租盗版的文字、美术、音乐等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著作权人既无法依据出租权来主张——因为只有影视作品和计算机软件享有出租权,也无法依据发行权来主张——因为发行行为不包括出租。再加上《著作权法》第59条中“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文字、美术作品,即便出租者无法证明其出租的文字或美术作品的复制件有合法来源,似乎也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更加不利于打击通过出租盗版的作品复制件而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比如,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审理的涉及出租“黑猫警长”美术作品的非法复制件用于展览而产生的侵权纠纷一案中,被告世盟公司向被告欢歌公司租赁了黑猫警长模型用于公开展示,因为被告世盟公司展览的美术作品是非法复制件,所以被判侵犯展览权。但该非法复制件是展览者通过租赁获得的,这时,因为出租者并没有授权世盟公司实施展览行为(不侵犯展览权),出租行为又不属于发行权控制的行为(不侵犯发行权),出租美术作品也不侵犯出租权,也没有证据证明出租者自己实施了非法复制行为(不侵犯复制权),于是,似乎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追究出租者的法律责任了。事实上,该案二审判决在否定被告欢歌公司侵犯了展览权后,维持了一审判决(不侵犯复制权,也不侵犯发行权,更不侵犯出租权)。但是,在这样的案件中,如果仅仅追究展览者的侵权责任,而让出租者逃脱任何法律责任的追究,明显不公平也不合理。
再比如,虽然剧本杀经营者向玩家提供盗版剧本的行为明显属于商业出租行为,但这种行为是否侵犯剧本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在业界众说纷纭。首先,剧本杀玩家表演剧本的行为并不侵犯公开表演权,正因如此,经营者也不会因为向玩家提供剧本让其表演而侵犯公开表演权。其次,因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明确区分发行权与出租权,而剧本杀经营者只是临时转移剧本复制件的占有给玩家,剧本显然又不属于享有出租权的视听作品或者计算机软件,于是剧本杀经营者向玩家提供盗版剧本复制件的行为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就既不侵犯发行权,也不侵犯出租权。所以,要规制这种行为,就存在“无权可依”的尴尬,理论上虽然不排除用复制权来控制这种行为的可能,但实践中也会存在争议和困难。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即便我国目前市场中出租文学或美术出版物的商业活动并不是太普遍,但也并非不存在。而一旦发生此类著作权侵权纠纷,往往因为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赋予文字、美术等作品的出租权而使得出租者可以从此类行为中获取商业利益却逃脱法律的制裁。
本文认为,立法是否应该赋予著作权人某项专有权利,虽然确实要看该权利所要控制的作品利用行为是否到了严重损害著作权人利益从而必须采取立法行动的程度,但是,立法也应该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预防性。因为出租行为对著作权人享有的发行权的损害是必然存在的,事实上很多国家的著作权法(包括德国法和美国法)都是以发行权来控制出租行为的,只不过有的国家对所有作品规定了出租行为不适用发行权一次用尽的例外(如德国《著作权法》第17条第2款),这样即便出租合法售出的作品复制件也依然受发行权的控制,有的国家只对少数作品规定了不适用首次销售原则的例外,例如美国《版权法》第109(b)(1)(A)条规定的录音制品和计算机程序。但是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著作权人或者版权人都可以依据发行权去禁止作品的非法复制件的出租行为。
而我国《著作权法》既然采取了发行权和出租权分别规定的模式,如果我们未用出租权来禁止所有合法售出的作品复制件的出租,那么就应该像发行权那样,让出租权也可以适用于所有作品——但是原则上应该适用首次销售原则,只是将某些特定类型的作品(比如被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文字或音乐作品、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作为不适用首次销售原则的例外,从而使著作权人可以控制这些特定类型作品的合法复制件的出租。这样的规则才能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不至于在面对那些出租盗版的作品复制件的行为时陷入缺乏权利依据而难以禁止的尴尬。甚至,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旦出现商业性的出租活动(不论是合法复制件的商业出租,还是非法复制件的商业出租)无疑会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我国《著作权法》不妨像欧盟那样赋予除建筑作品和实用艺术品之外的全部作品专有的出租权。这样,一旦在市场中产生对某类作品的复制件的商业性出租,就不再需要借助兜底的其他权利来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了。
六、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无论是赋予录音录像制品中的表演者以出租权,还是赋予录音录像制品中的作者以出租权,均是包括《TRIPS协定》、WCT、WPPT以及《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在内的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要求。因此,虽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出租权并没有明确适用于录音录像制品中被录制的作品,但是根据2020年《著作权法》第39条规定,如果表演者许可他人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那么,被许可人(出租者)还应该取得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这事实上已经明确:录音录像制品中的作品著作权人是享有出租权的。虽然这样的规定是否体现了立法者的真实意思尚有疑问(毕竟这与《著作权法》第10条有关出租权的规定以及第44条第2款的表述并不协调),但是,既然立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这个权利,而且这个规定其实是合乎法律逻辑的,不仅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国立法遵循国际条约的需要,因此,我们在法律解释上不如顺水推舟,承认我国《著作权法》已经赋予录音录像制品中的作品著作权人的出租权,是更为合理的。事实上,我国《著作权法》中早已存在类似的立法技巧,就录像制作者享有的广播权而言,我国《著作权法》在第44条第1款关于录像制作者权利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赋予录像制作者广播权,但是,在第48条中又明确电视台播放他人的录像制品,应当取得录像制作者许可,并支付报酬——这其实就是赋予了录像制作者专有的广播权。
当然,为了减少我国《著作权法》中有关出租权的法律规则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冲突,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因为目前立法对出租权规定存在的上述不足而带来的法律适用困境,在我国《著作权法》将来进行修改的时候,应该对著作权人享有的出租权作出更为合理和协调的制度安排。本文建议,在不对“发行权-出租权”分离方式作出改变的情况下,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的规定可以修改为:“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的权利;但是,除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中的作品外,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所有权已经获得著作权人同意而转移的,著作权人不再对其享有出租权;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这样的规定,一方面,使得著作权人可以直接依据出租权对任何一类作品的非法复制件的出租者进行打击,不至于落入无权可依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可以与《著作权法》第39条第2款的规定相协调。当然,《著作权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就应该作出调整,可以修改为“被许可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同时取得著作权人、表演者许可,并支付报酬”。最后,《著作权法》第59条的规定也应该作相应修改,对于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不能仅仅限于“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作品的复制品,其实,提供任何一个作品(尤其是文字、美术作品)的复制品出租的人,如果不能证明其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该复制品往往就是出租者自己非法复制的,即便无法证明是出租者自己复制的而难以认定其侵犯复制权,出租者也应该承担侵犯出租权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