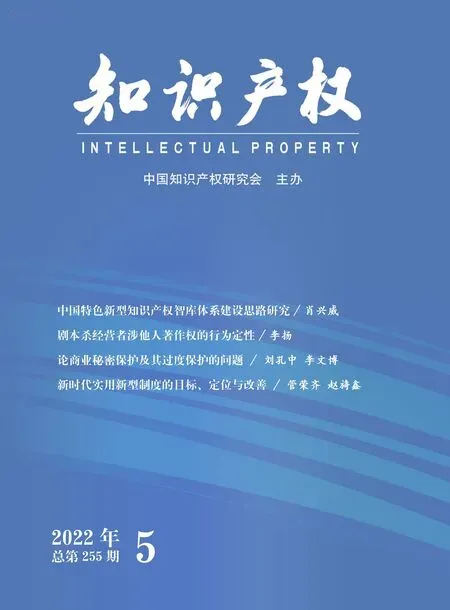剧本杀经营者涉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定性
李 扬
内容提要:因剧本杀行业快速发展以及巨大利益驱动,其中的著作权问题已经开始凸显。解释论上,剧本杀经营者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的行为构成“他项权”控制的行为。立法论上,应将发行权控制的行为由出售、赠与两种转移作品复制件所有权的行为扩张至互易、出借等行为,将出租权保护的作品由视听作品、计算机程序扩张至所有作品,从而控制所有盗版作品的发行和出租行为;但为了防止出租权妨碍视听作品、计算机程序以外作品的自由流通和利用,著作权法应当规定其他作品著作权人享有的出租权仅能控制盗版作品的出租。表演作品,是指通过动作、声音、表情再现作品,包括口述和表现作品。公开表演作品,是指在向公众开放或者半开放的场所向不特定人或者家庭及其正常社交圈以外的人表演作品。应当根据手足论(工具论),将剧本杀经营者利用剧本杀玩家直接表演剧本杀剧本的行为,规范地评价为直接表演剧本杀剧本的行为。
一、引言
剧本杀起源于英国的谋杀之谜(Murder Mystery Game)真人角色扮演游戏,也被称为“脚本杀人”游戏(Script Homicide),2013年随英文剧本杀Death Wears White传入国内而开始在国内兴起,2016年因为芒果TV推出的明星推理真人秀节目《明星大侦探》在国内热播而开始在全国流行。剧本杀的基本玩法是:剧本杀玩家在剧本杀经营者指派的游戏主持人的主持下抽选各自的角色剧本;剧本杀玩家各自研读自己抽中的角色剧本,了解和熟悉故事背景,进入所扮演的游戏角色;剧本杀玩家在游戏场景中搜索案件线索并交流讨论;剧本杀玩家梳理得到的案件线索,讨论推理案件发生的过程;剧本杀玩家推理、还原出案件真相并投票选出凶手;剧本杀主持人公布真正的凶手,并回答游戏玩家的疑问。由于进入门槛低,剧本杀行业在我国迅猛发展,产值短期内快速提升。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剧本杀行业用户研究及标杆企业案例分析报告》统计分析,2020年中国剧本杀市场规模已达117.4亿元,预计到2022年中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将增至238.9亿元。
从类型上看,剧本杀可分为线上剧本杀和线下剧本杀。线上剧本杀通过APP和小程序进行游戏,剧本杀玩家可以自己组建队伍,也可以随机匹配,通过虚拟空间对话找出凶手。线下剧本杀又有圆桌剧本杀与实景剧本杀之别。圆桌剧本杀是剧本杀玩家围坐在现实中真实的圆桌旁,通过现场对话等方式找出案件线索,侦破案件找出真正的凶手。实景剧本杀则是构造出一个案件的真实场景,剧本杀玩家进入现场进行搜查取证和讨论,还原案件真相,找出凶手。线上剧本杀和线下剧本杀的同步发展,满足了不同剧本杀玩家对时间、地点、价格和共同游戏参与者的不同需求。
从产业链看,剧本杀涉及上游的内容创作、中游的内容发行、下游的内容渠道。上游的内容创作主要是剧本和美术、音乐等其他元素的原创或者改编,涉及剧本、美术、音乐等创作者或者改编者的权益。中游主要涉及发行方、销售平台和展会等,是上游创作者与下游剧本杀门店联系的纽带。下游主要涉及线上APP和线下剧本杀门店,是剧本杀消费的主要出口。由于沉浸式体验、满足社交需要等优点不断得到肯定,剧本杀已经与传统游戏、影视、文旅、民宿、KTV等产业结合在一起,使传统文娱旅游行业更加趣味化、年轻化,并带动了旅游、餐饮、民宿等相关行业的消费。
基于行业快速发展以及巨大的利益驱动,剧本杀行业中的著作权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且预计会呈多发趋势。从已经发生的案件和舆论讨论的焦点看,剧本杀经营中涉及的著作权问题,除了剧本杀剧本的著作权归属和未经许可在剧本杀剧本中直接使用他人美术作品是否构成侵权等理论上并无争议的问题之外,主要还是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剧本杀经营者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的行为在著作权法上应该如何定性。二是剧本杀玩家的行为如何定性,剧本杀经营者主持玩家沉浸式体验剧本杀的行为在著作权法上如何定性。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关系著作权人权益的保护边界,也与剧本杀经营者、剧本杀玩家、APP技术服务提供者、剧本杀实体门店经营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实有探讨清楚的必要。
二、剧本杀经营者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的行为定性
(一)三种观点及其评析
剧本杀游戏受到市场青睐之后,剧本杀剧本盗版问题逐渐成为行业内的一个痛点。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剧本杀经营者购买盗版剧本后在不同时间提供给不同剧本杀玩家反复使用再收回的行为,也就是出租或者出借剧本杀剧本的行为,在著作权法上应该如何定性。至今为止,学术界出现了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并未赋予著作权人“购买权”“阅读权”以及除视听作品和计算机软件作品以外的出租权,同时由于剧本杀玩家的行为不属于公开表演行为,剧本杀经营者不属于表演组织者,因此剧本杀经营者购买盗版剧本出租或者出借给剧本杀玩家使用的行为并不构成侵害剧本著作权人任何著作权的行为。对于剧本杀经营者使用的盗版剧本,只能由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依据2020年《著作权法》第58条的规定,予以没收,或者应权利人的请求予以销毁。第二种观点认为,剧本杀经营者如果无法举证证明其提供给剧本杀玩家的盗版剧本杀剧本的合法来源,则应当推定剧本杀经营者为盗版剧本杀剧本的复制主体,其提供行为侵犯剧本杀剧本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如果剧本杀经营者提供了盗版剧本杀剧本的合法来源,则权利人可以向源头追索,追究盗版剧本杀剧本源头提供者的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向公众提供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合法制作的复制件的行为,都构成对著作权人发行权/出租权的侵害。据此,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出租盗版图书的行为在著作权法上也将会被评价为著作权侵权行为,因而不会出现某一行为在著作权法上被评价为不侵权,却受到刑法规制的奇特现象。
本文认为,上述三种观点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在现行法框架内,就解释论而言,只能暂时将剧本杀经营者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行为,即出租或者出借的行为,定性为《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即“他项权”控制的行为,并根据《著作权法》第52条第11项(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追究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就立法论而言,则需要适当扩张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权控制的行为和出租权保护的作品范围,以制止出借、出租盗版作品的行为。
第一种观点虽然看到了我国著作权法未赋予著作权人“购买权”“阅读权”以及除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作品以外的出租权的事实,但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该观点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理论上缺少根据,在实务上无法操作,因此无法令人信服。既然被盗版剧本杀剧本的权利人不享有任何著作权法上的权利,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商家也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实体法上无任何请求权基础的剧本杀剧本权利人如何能够启动民事救济程序?连民事救济程序都无法发动,人民法院又如何对盗版剧本杀剧本进行没收,或者应权利人的请求予以销毁?第一种观点显然也注意到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行为可能损害剧本杀剧本权利人的利益,但其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着实难以实现。
第二种观点从举证责任分配的独特角度,将无法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合法来源的剧本杀经营者推定为复制行为主体,并追究其侵害剧本杀剧本著作权人复制权的责任。相比于第一种观点,其在理论解释上不存在特别的违和感,实务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该种观点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著作权法上的解释依据。虽然《著作权法》第59条第1款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该条并不适用于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经营者。其一,从我国著作权法制定和历次修改背景看,《著作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的“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应当是指《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规定的应当取得出版许可证的出版单位或者印刷许可证的印刷业经营者,而非指任何从事复制行为的主体。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经营者并非《出版管理条例》规定的出版者,也非《印刷业管理条例》规定的印刷业经营者,不能适用《著作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若扩大《著作权法》第59条第1款的适用主体范围,虽严格保护了著作权人,但会加重一般复制行为主体的举证责任,导致打击面过宽。其二,即使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经营者属于《著作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的“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适用的也只能是“合法授权”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而非针对复制品发行者和出租者规定的“合法来源”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据此,即使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经营者无法提供剧本杀剧本的合法来源,也不能直接得出该经营者就是盗版剧本杀剧本的复制者及侵害了剧本权利人复制权的结论。相反,即使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经营者提供了合法来源,假如该经营者未能进一步提供得到权利人的“合法授权”的证据,也难以免除侵害著作权的责任。其三,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经营者是否为复制品的发行者,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使该经营者就是复制品发行者,且不能证明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那么其侵害的也是发行权,而非复制权。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经营者并非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则无需讨论,即使其是出租者且不能证明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侵害的也是出租权而非复制权。总而言之,为了追究剧本杀经营者提供盗版剧本的复制侵权责任,保护剧本著作权人的利益,而对《著作权法》第59条第1款的适用行为主体作扩张解释,将造成举证责任在原被告之间的不合理分配,不适当地扩大著作权法的打击范围,并不可取。
第三种观点从效果上看,可以彻底解决剧本杀经营者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行为定性和责任追究问题。但该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了我国《著作权法》立法者已经将发行权与出租权分割并举且界限分明的立法事实。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6项,发行权,指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可见按照我国著作权法,发行仅包括出售和赠与两种转移所有权方式,出租、出借、互易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均非我国著作权法上所指的发行,亦不受著作权人发行权的控制。由此可以导出两个解释论上的重要逻辑结论。一是发行权既可以控制出售、赠与正版作品的行为,也可以控制出售、赠与盗版作品的行为。二是对于出租、出借、互易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不论该原件或复制件是正版还是盗版,著作权人都欠缺行使发行权的法律依据。又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7项,出租权,指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可见按照我国著作权法,仅有视听作品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享有出租权,文字作品等其他作品著作权人均不享有出租权。由此也可以导出两个解释论上的重要逻辑结论。一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出租权,既可以控制正版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的出租行为,也可以控制盗版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的出租行为。二是出租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以外的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不论该原件或复制件是正版还是盗版,著作权人都欠缺行使出租权的法律依据。
立法使用的术语有明确含义且内涵和外延确定的,不应也不能进行扩张解释。综合上述阐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体系框架下,出租、出借、互易文字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不论是正版还是盗版,既不受著作权人发行权控制,也不受著作权人出租权控制。具体到本部分讨论的问题,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的行为,不论是有偿出租还是无偿出借,因剧本杀玩家使用后经营者将收回剧本,不存在转移盗版剧本杀剧本所有权的行为,因此既不侵害剧本杀剧本权利人的发行权,也不存在侵害其出租权一说。第三种观点将出租、出借解释为发行的一种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剧本杀经营者向剧本杀玩家提供(出租或者出借)盗版剧本杀剧本的行为应受著作权人发行权/出租权的控制,实属立法论上的观点,与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出发进行文义和体系解释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恐难为已经养成从法条出发严格解释法律习惯的我国司法者在司法实践采纳,适用前景并不乐观。
(二)解释论和立法论途径
本文认为,对剧本杀经营者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行为的定性,有两种思考途径。一种是解释论途径,一种是立法论途径。下面分述之。
解释论上,只能无奈地将剧本杀经营者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行为,认定为《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他项权”控制范围内的行为。
首先,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的复制件在市场上的流通,不论以出租、出借、互易还是别的方式流向市场,不论是否转移复制件的所有权,都已经超出了著作权人第一次许可复制并上市流通的复制件数量,减损了著作权人本可以获得的市场交易机会和经济收入。尤其是在同一个侵权复制件可以在同一营业地点反复出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确保著作权人创作的激励,有必要使出租、出借、互易等导致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的复制件流向市场的行为处于著作权人的控制之下。在著作权其他子权利无法发挥剧本杀剧本创作激励者这一角色的情况下,“他项权”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其次,如上所述,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框架内,无法从解释论角度将出租、出借、互易等导致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的复制件流向市场的行为,解释为著作权人发行权或者出租权(除视听作品和计算机软件外)控制的行为。在此情况下,通过“他项权”规制出租、出借、互易盗版剧本杀剧本等行为,是最为稳妥、最少争议的方式。
最后,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关于“他项权”的规定,虽然在世界著作权立法中独一无二,受到有违著作权法定原则等批评,但就法律适用而言,这种著作权权项开放性的立法模式,反而可以适应利用作品手段随科技变化而变化的需要,规制现实中已经出现而著作权其他子权利无法规制的损害著作权人利益的行为,弥补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其他子权利界定过于狭窄导致的难以适应现实需要的不足和缺陷。
剧本杀经营者向剧本杀玩家提供盗版剧本杀剧本的行为,无论表现为免费的出借行为还是有偿的出租行为,由于从盗版剧本上市流通之日开始,就超出了著作权人预定的作品复制件流通数量,不论经历多少流通环节,也不论采取出借、出租、互易等何种具体流通方式,著作权人的权利都不应当用尽,每个环节的行为都应当受著作权人“他项权”的控制。
立法论上,有必要将发行权控制的行为,由销售、赠与两种转移所有权的行为,扩大到出借、互易等其他转移或者不转移所有权的行为,将出租权的对象扩及所有作品范围,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出租、出借、互易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向他人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定性及其规制问题。
首先,复制与销售、赠与、出租、出借、互易等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流通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复制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进行,且复制件有流向市场的可能性,不控制销售、赠与、出租、出借、互易等行为,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发行权规定为一种独立的权利,为著作权人追踪发行第三人未经许可复制的复制件的行为人提供了便利和灵活性。当然,未经许可销售、赠与、出租、出借、互易作品复制件,也超出了著作权人预定的流向市场的复制件数量,将会减损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
其次,《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虽仅在第14条保护电影作品发行权,《TRIPS协定》第11条虽仅规定成员至少应赋予计算机程序和电影作品出租权,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CT)第6条已经规定至少应当赋予著作权人以销售或者其他转移所有权的方式发行其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专有权利,WCT第7条亦已规定至少应当赋予计算机软件、电影作品、录音制品以出租权。由于国际条约或者公约仅是对成员国内法的最低要求,我国扩大发行权控制的行为范围,扩大出租权保护的作品范围,并不违背这些条约或者公约的刚性规定。
最后,从比较法上看,美国《版权法》第106条(3)条采取广义发行权概念,著作权人专有以出售、其他转移所有权的方式、出租、租赁、出借方式将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进行发行的权利。德国《著作权法》第17条第1款也采取广义发行权概念,著作权人专有向公众提供或者交易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28条之一虽然采取狭义发行权概念,规定著作权人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专有以转移所有权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权利;表演人就其经重制于录音著作之表演,专有以转移所有权之方式散布之权利;但其第87条第1款第6项却规定,明知为侵害著作财产权之物而以转移所有权或出租以外之方式散布者,或明知为侵害著作财产权之物,意图散布而公开陈列或持有者,视为侵害散布权的行为。该条中的散布则采用其第3条第1款第12项规定的广义散布概念,即指不问有偿或者无偿,将著作之原件或者复制件提供公众交易或者流通,包括出租、出售、互易、出借等行为,发行权实际控制的行为已经扩及出借等行为。其第29条规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专有出租其著作之权利,表演人就经其重制于录音著作之表演,专有出租之权利,出租权的保护对象包括所有类型的作品和表演。日本《著作权法》第26条规定,电影作品作者享有发行权,包括通过有偿或者无偿的方式向公众转让或者出租电影作品复制品的权利;第26条之二规定,除电影作品以外的作品作者享有转让权,即通过转让其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第26条之三规定,作者享有通过出租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可见,日本著作权法虽然将电影作品和其他作品的转让权与出租权分开规定,但并未改变所有作品都享有转让权和出租权的实质。总而言之,虽然上述制度模式有所差别,但至少销售或者出租盗版作品的行为无一例外将侵害发行权或者出租权,因而不会出现著作权制度面对向公众提供盗版作品的行为束手无策的结果。这样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不过,考虑到国际公约关于出租权保护客体的最低要求,以及不妨碍作品复制件自由流通和利用,从而确保公众获取文化科学知识的利益,著作权法应当规定,视听作品、计算机程序以外作品著作权人享有的出租权,仅能控制盗版作品的出租行为,而不及于正版作品的首次出租以及转租。
三、剧本杀经营者主持玩家沉浸式体验剧本杀剧本的行为定性
剧本杀经营者除了向玩家出借或者出租剧本杀剧本外,还存在主持剧本杀玩家沉浸式体验剧本杀和提供游玩场所等行为。一种观点认为,剧本杀玩家体验剧本杀的行为仅是在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并不构成对作品的表演,即使有玩家的行为构成表演,面对的仅是共同参加游戏的几个朋友,难言面对“公众”进行表演。由此,剧本杀经营者也不属于“表演组织者”。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剧本杀玩家和剧本杀经营者的行为呢?要准确定性剧本杀经营者的行为,先得讲清楚什么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作品行为”。
(一)表演作品行为
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9项规定,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可见,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表演包括现场表演和机械表演,表演的作品类型没有限制。惟查《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并未发现有条款对“表演作品”和“公开表演”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任何界定。这种立法模式虽极大增加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但也为法律解释提供了广阔空间,可谓忧喜参半。
何谓“表演作品”?美国《版权法》第101条规定,表演作品是指直接或者借助装置或方法,朗诵、表演、演奏、舞蹈或者演出作品;涉及电影或者其他录像作品时,指以连续方式展示其图像或者使人听到伴随的声音。可见,该法上的表演包括了视听作品的放映。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第1款第3项规定,表演,是指通过具有戏剧效果的演出、舞蹈、演奏、歌唱、背诵、朗诵或者其他表演方式再现作品的行为(包括虽不再现作品但具有文艺性质的类似行为),包括表演作品和表演非作品的行为。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表演权之外,日本《著作权法》第24条还规定了口述权,即作者享有的公开朗诵其文字作品的权利。所谓口述,则是指以朗诵或者其他方法口头传达作品(表演中的口头传达除外)(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第1款第18项)。可见,日本《著作权法》将口述从表演中分离了出来,与美国《版权法》不同。德国《著作权法》第19条第1、2、3款分别规定,朗诵权是指通过个人表演而使公众能够听取语言作品的权利;演出权是指通过个人表演而使公众能够听取音乐作品或者在舞台上公开表演作品的权利;朗诵权与演出权包括在个人表演的场地之外通过屏幕、扩音器或者类似技术设备使朗诵与演出可公开感知的权利。法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作品含义更广,第L.122-2条规定,表演是指通过某种方式尤其是下列方式将作品向公众传播:公开朗诵、音乐演奏、戏剧表演、公开演出、公开放映以及在公共场所转播远程传送的作品;远程传送,是指通过电信传播的一切方式,传播各种声音、图像、资料、数据及信息;向卫星发送作品视为表演。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3条第1款第9项规定,公开演出,是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弹奏乐器或其他方法向现场之公众传达著作内容;以扩音器或者其他器材,将原播送之声音或者影像向公众传达者,亦属之。该款第6项规定,公开口述,指以言词或其他方法向公众传达著作内容。其他方法,指以录音或者录影使影像再生向公众传达著作内容,但不包括公开播送和公开上映之情形。
一些国际公约或者条约在规定何谓表演者时,也间接规定了表演作品的行为样态。《保护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广播组织罗马公约》(以下简称《罗马公约》)第3条第1款将表演者定义为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以及其他将文学著作或者艺术著作予以表演(act)、歌唱(sing)、演说(deliver)、朗诵(declaim)、演奏(play in)或者以其他方法(otherwise perform)加以表演之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以下简称WPPT)第2条(a)款则将表演之行为样态新增“表现”(interpret)。《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第2条(a)款亦规定,表演者系指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以及对文学或者艺术作品或者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进行表演、歌唱、演说、朗诵、演奏、表现(interpret)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表演的其他人员。
综合《罗马公约》、WPPT、《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以及前述国家和地区的著作权制度规定可以发现,虽然它们都或多或少列举了表演作品的各种方式,但都并未揭示出表演作品行为的本质。本文认为,现场表演是指直接或者借助辅助设备以声音、动作、表情或者其结合,直接或者间接再现作品的行为,基本要求是将思想、感情等通过外部的动作、台词、表情等表现出来,直接诉诸观众或者听众的感官,通常应当给人以审美享受。机械表演则是指借助录音机、录像机等技术设备将上述表演向现场公众进行传达的行为。
歌唱、演说、朗诵主要是通过声音再现作品,有时候也辅之以一定表情或动作。演奏主要是通过手脚的动作和乐器的声音再现作品。哑剧主要是通过动作和表情再现作品。戏剧表演,主要是通过声音、动作和表情的结合再现作品。表现(interpret),按照牛津词典的解释,起码包括以下四种含义:诠释、说明;把……理解为;口译;演绎(按照自己的理解演奏音乐或者表现角色)。可见WPPT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所说的表现,不但包括了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的对作品进行口述的行为,而且包括对作品进行解释、说明、口译的行为。口述是通过口头语言未有任何表演成分地直接、单纯再现作品的行为,不同于有表演成分的朗诵,相当于通过语言和声音进行的复制。但由于未形成有形复制件,所以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我国并未规定独立的口述权,但完全可以根据WPPT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规定,将口述归于表演行为。
通过声音、动作、表情或者其结合直接再现作品,是指再现作品时,虽然有自己独立的理解和感觉,但并未改变现有作品的独创性表达。歌唱、演说、朗诵、口述、演奏属于通过声音、动作、表情或者其结合直接再现作品的行为。通过声音、动作、表情或者其结合间接再现作品,是指再现作品时,除了有自己独立的理解和感觉之外,常伴随改变现有作品的独创性表达。戏剧表演和表现中的解释、说明、口译,除了加上自己的理解,由于表演的客观需要,通常会增删、改变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进行二次创作。通过声音、动作、表情或者其结合再现作品,无论是否增删、改变原作品表达,均属于对原作品的表演。
根据上文对表演作品行为的解读,就不难理解剧本杀玩家的行为定性了。具体而言,剧本杀玩家通过声音读出抽选的剧本台词,属于通过口述方式表演剧本杀剧本的行为。即使剧本杀玩家在阅读台词后,仅根据自己对台词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相互提问或者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要这个过程中再现了剧本杀剧本的剧情,不论剧本杀玩家是否有二次创作的成分,仍然属于通过阐释、说明等方式表演剧本杀剧本的行为。认为剧本杀玩家根据自己抽选的角色剧本,再用自己的语言相互提问或者表达自己关于剧本杀剧本内容想法的行为,不属于表演剧本杀剧本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二)公开表演
表演权控制的行为以公开表演为要件,与复制权控制的复制行为不同。在私人领域内从事复制行为,若复制件存在向外部流出和扩散而损害著作权人利益的可能性,则也受复制权控制,除非是为私人目的的复制,且复制件未超出私人目的使用领域流向外部。与此不同,除非对表演进行了录音录像,否则表演一结束利用作品行为即结束,不存在向外部扩散而进一步损害权利人利益的危险性,因而在非公开场合进行的表演,为表演权所不及的利用形态。此外,公开表演,具有公开表演的目的即可,实际是否有观众或者听众在所不问。
何谓公开表演?与表演作品一样,我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也均未进行界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著作权法》第10条第1项规定的“公之于众”,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条件。德国《著作权法》第15条第2款规定,作者享有以无体形式公开再现其作品的排他权利,特别包括朗诵权、演出权与放映权等。同条第3款规定,公开再现是指针对大多数公众成员的再现。与利用作品的人及与以无体形式可感知或者已获得作品的人不存在人身联系的人,属于公众。可见,按照德国《著作权法》,可能仅在相互陌生的两个人之间再现作品就构成公开再现,而在数百人参加的婚礼中的再现,不构成公开再现。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第5款规定,该法所称的公众,包括特定的多数人。韩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32项规定,公众是指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多数人。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3条第1款第4项规定,公众指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数人;但家庭及其正常社交之多数人,不在此限。根据这些规定,不存在争议的一点是,在不特定人面前进行的表演,属于公开表演,不论事实上是否有观众或者听众。
需要探讨的是,在向公众开放的场所,或者在超出家庭及其正常社交关系的相当数量的人可以聚集的场所表演作品,是否属于公开表演?举例而言,在卡拉OK经营店的包厢里演唱歌曲,是否属于公开表演?在此情况下,包厢是私密的,参与演唱的,也限于家庭或者熟人,明显不属于在不特定人面前演唱歌曲,似乎应当得出客人演唱歌曲不属于公开表演的结论。假如这个结论正确,则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均无权就其管理的词曲作品向卡拉OK经营店收取任何使用费。这显然与现实不符。该问题应该如何解释呢?
美国《版权法》第101条的规定及其适用的相关案例可以为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思考的方向。美国《版权法》第101条对于公开表演或者展示作品进行了如下定义:(1)在对公众开放的场所,或者在超出一个家庭及其社交关系正常范围的相当数量的人的任何聚集的场所,表演或者展出作品;(2)利用装置或者方法向第(1)项所指地点或者向公众传送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作品的表演或者展出,无论公众是否可以在同一地点或者不同地点以及是否可以在同一时间或者不同时间内接收到表演或者展出。
在Columbia Pictures Indus.Redd Horne,Inc.案中,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就上述条款的适用作出了解释。该案中,被告开设了两家店铺,共设有85个私密小隔间,每个私密小隔间可以容纳二至四人。被告在两家店铺的前部准备了视频播放设备和各种包含原告电影的影像带。顾客选择好希望观看的电影以及私密小隔间并支付相应费用,进入小隔间后,关上房门就会激活置于店铺前部柜台的信号。被告营业员收到信号后,就会在店铺前部的视频播放设备上播放影像带,影像会传送至顾客私密小隔间的电视上供其观看。私密小隔间只租给分组的个人,分组虽然没有限制,但陌生人并不会为了填满一个私密小隔间而被强行分在一组。被告向希望利用其设施和服务的任何公众成员开放。原告指控被告在其店铺中的私密小隔间展示或者放映录影带的行为,构成未经授权的公开表演行为,侵害了其享有的公开表演权。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认为,按照美国《版权法》第101条规定的公开表演的定义,两种表演满足该定义。一是在对公众开放的场所进行的表演,二是在对公众半开放的场所进行的表演,这取决于听众的数量和人员组成。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同意地区法院关于被告的店铺而非私密小隔间才是向公众开放的场所的结论,因此认为没有必要讨论是否向半公开场所进行表演的问题。关于公众的组成,法院认为在私密小隔间的展示或者播放与在电影院展示电影并无显著区别,公众中的任何成员付费都可以观看电影,被告提供的服务本质上与电影院提供的服务相同。按照美国《版权法》第101条的规定,该案中的场所是被告的两个店铺,而不是每个店铺中的私密小隔间,仅仅因为在私密小隔间观看电影并未改变被告店铺是向公众开放场所的本质事实。被告的营业活动构成公开表演的结论完全符合上述第二种公开表演的定义,公众中的成员在不同时间观看表演的事实不会改变公开表演的法律后果。美国Nimmer教授就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公开表演的定义进行的评论,很好地诠释了上述判例对公开表演所作的解释:“如果某个作品的相同复制件被公众中的不同成员在不同时间反复表演,即构成公开表演。”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罗明通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顾客在KTV包厢演唱歌曲的公开表演性质:“KTV包厢成员虽为特定,但出入人员为不特定人(例如服务人员),性质上属公众场所,故于该场所演唱,性质上属公开演出。”
结合上述规定、案例和学者论述,本文认为:向公众开放的场所,是指公众中的任何成员付费或者不付费,于相同或者不同时间均可进入的场所;于该场所进行的表演,不论是否反复进行,即为公开表演,是否实际有听众或者观众则在所不问。据此,在向一般公众开放的公园、楼堂馆所、采取会员制才能进入的半开放场所等进行的表演,属于公开表演自不在话下。在向公众开放的游乐园、卡拉OK店、音乐室等场所中的包厢、密室、分隔间进行的表演,由于包厢、密室、分隔间等私密场所是公众中的任何成员在不同时间均可出入的场所,于该场所进行的表演,也属于公开表演。否则,游乐园、卡拉OK店、音乐室等经营者利用他人作品,哪怕是侵权作品供公众中的任何成员在不同时间进行表演以营利,著作权人都将束手无策。即使抛开著作权法,放任这种现象的存在,也与人们朴素的正义观不相符合。
剧本杀玩家如果是在剧本杀经营者于同一时间内向公众中的任何成员开放的场所进行体验,属于公开表演剧本杀剧本当无疑义。即使剧本杀玩家在剧本杀经营者提供的经营场所内设的私密空间表演剧本杀剧本,由于私密空间是任何剧本杀玩家于不同时间均可付费进入的场所,于不同时间在该私密空间进行的表演即使无观众或者听众,亦属于公开表演。将剧本杀玩家在向公众开放的场所中内设的密室或者独立空间中表演剧本杀剧本的行为作为非公开表演行为处理,是静态、孤立地看待公开场所和剧本杀玩家行为的结果。
(三)剧本杀经营者还是剧本杀玩家属于公开表演行为的主体
剧本杀玩家的行为属于公开表演剧本行为,已如上述。惟玩家基于个人娱乐目的表演他人剧本,且未获报酬或者有营利目的,行为落入2020年《著作权法》第24条第1款第1项和第9项限制与例外范畴内,将剧本杀玩家认定为表演行为的主体,剧本著作权人无由向其主张停止侵害或者损害赔偿。由此即使认定剧本杀玩家使用剧本杀剧本的行为属于公开表演行为亦无法追究剧本杀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从而放任剧本杀经营者利用玩家表演剧本杀剧本行为营利而著作权人利益受损的状态存在。这相当于将一部分公开表演市场交给了剧本杀经营者,于激励剧本杀剧本创作极为不利,进而导致市场失灵。
为了维持剧本杀剧本创作激励,防止市场失灵,本文认为,有必要引入手足论将剧本杀经营者拟制为公开表演行为的主体,并追究其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责任。手足论,又称机关论或者工具论,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当某主体将他人直接利用作品的行为作为自己利用该等行为的手足或者工具时,应从法规范的角度将该利用行为主体评价为实施著作权控制范围内行为的直接主体,并将其作为被告追究法律责任。所谓一定条件,一是指管理支配性,二是指营利目的性。管理支配性是指,利用行为主体对他人直接利用作品的行为进行了管理和支配。营利目的性是指,利用行为主体将他人直接利用作品行为作为营利的手段,从他人直接利用行为中获得利益。
手足论来源于刑法中的间接正犯理论及其司法实践。间接正犯是指利用不成立共同犯罪的第三人实施犯罪。间接正犯并无实行行为,仅是利用第三人的实行行为,实行行为的第三人只不过是行为人的“没有灵魂的工具”,尽管从外部看行为人没有具体实行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支配了导致犯罪结果产生的原因,因此可以视为行为人将第三人当作工具实行了犯罪,是犯罪行为的主体。间接正犯主要表现为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犯罪、利用精神病人实施犯罪、利用他人无罪过行为实施犯罪、利用他人合法行为实施犯罪、利用他人过失行为实施犯罪、利用有故意的工具实施犯罪(包括在目的犯的情况下利用有故意无目的的工具实施犯罪和在身份犯的情况下利用有故意无身份的工具实施犯罪)等形态。将他人作为实行犯罪的工具之所以应当作为间接正犯追究刑事责任,是因为利用者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在手足论之下,利用者的行为样态主要表现为,利用他人合法利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实施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尽管被利用者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是合法的,但利用者行为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被利用者行为的合法性,而取决于幕后操纵行为是否经过了知识产权人许可,是否直接因此获得了经济利益。在幕后操纵者未经知识产权人许可,利用他人合法行为实施知识产权控制的行为,且直接因此获得了经济利益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人的经济利益将因此受损,因而应当被规范地评价为直接侵害知识产权人利益的行为。
手足论的侵权构成不同于帮助侵权和教唆侵权的侵权构成。帮助侵权、教唆侵权,均以被帮助者、被教唆者的利用行为构成侵害著作权行为为前提,帮助者和被帮助者、教唆者和被教唆者存在主观意思联络,且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手足论,并不以他人直接利用作品行为构成侵害著作权行为为前提,即使直接利用作品行为构成著作权限制和例外范围内的行为,利用行为主体的行为亦可成立侵害著作权行为。按照手足论,利用行为主体和直接利用作品行为主体之间并无意思联络,相互之间并不承担连带责任,而由利用行为主体独自承担侵害著作权的责任,直接利用作品行为主体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手足论下利用行为主体的责任,也不同于雇主责任。雇主责任以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受雇人所为行为是履行雇佣合同的职务行为,手足论下利用行为主体承担责任,并不以其与直接利用作品行为主体存在雇佣关系为前提,直接利用作品行为并非履行和利用行为主体之间任何合同规定或者约定义务的行为。
日本最高裁判所在1985年的“猫眼俱乐部案”中,开创了在日本具有重大影响的“卡拉OK法理”,该法理的实质就是手足论。该案中,经营卡拉OK店的被告未经原告日本音乐著作权管理协会同意,为来店顾客提供由该协会管理歌曲的卡拉OK伴奏磁带,供顾客在其他顾客面前演唱。在此过程中,被告准备了卡拉OK磁带和选歌单,被告营业员负责操作卡拉OK装置,有时还陪客人一起演唱。原告指控被告侵犯了其管理歌曲的演奏权。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卡拉OK店为顾客准备了卡拉OK装置和曲目,为顾客操作了卡拉OK装置,顾客只不过是在服务员劝诱下,在卡拉OK店所准备的曲目范围内选择了曲目并进行演唱,顾客的演唱实质是在卡拉OK店的管理支配下进行的。同时,卡拉OK店将顾客演唱作为营业政策的一环,以此酿造良好氛围,招揽顾客前来演唱并消费进行营利。基于这两个原因,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应当将卡拉OK店认定为演奏行为的主体。卡拉OK法理诞生之后,因其严厉性在日本理论和实务界备受争议,但对日本地方裁判所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地方裁判所在此后的类似案件中,都适用管理支配性和利益性两个要件将非直接利用他人作品的行为主体规范评价为直接利用作品的行为主体,并追究其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责任。
按照手足论追究利用他人直接利用作品行为的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虽然相比帮助侵权论、教唆侵权论、替代责任论更为严格,但对于我国而言,却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手足论,将对直接利用作品行为具有管理支配关系且具有营利目的的服务提供者,评价为直接侵害著作权的主体,对于强化著作权保护,打击著作权侵权行为,净化著作权空气,激励作品创作和传播,都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剧本杀经营者的行为,完全符合手足论的两个要件。一是管理支配性要件。线上剧本杀主持人一般由机器人替代,剧本杀玩家完全按照经营者预设的标准化流程和指示操作,剧本杀经营者完全管理和支配了剧本杀玩家的表演行为。线下剧本杀经营者首先为剧本杀玩家准备了剧本杀剧本,其次为剧本杀玩家配备了主持人。剧本杀游戏正式开始前,主持人会主持剧本杀玩家抽选并分发各自的人物剧本,讲解剧本杀具体玩法和剧本杀剧本大纲,某些搜查过程和特殊道具或者信物,以及对于找出案件真相有重大关系的物品。剧本杀游戏正式开始后,主持人会引导剧本杀玩家进行案情分析,掌控剧情推进过程和节奏,并会逐渐引导剧本杀玩家找出正确的答案,最后公布案情真相并回答剧本杀玩家的疑问。可见,通过线下主持人的主持,剧本杀经营者对剧本杀玩家的行为进行了管理和支配。二是营利性要件。剧本杀经营者直接针对剧本杀玩家的游戏行为,也就是表演剧本杀剧本的行为收取了费用,具有营利性。总之,剧本杀玩家表演剧本的行为不过是剧本杀经营者进行营利的一种手段,名义上是剧本杀玩家在表演剧本杀剧本,实质上是剧本杀经营者在表演剧本杀剧本,剧本杀经营者才是剧本的真正表演者。
结语
剧本杀游戏在我国尚属新事物。剧本杀经营涉及上中下游各种不同市场主体的利益。建立良好剧本杀游戏业态,尊重和保护该业态活水之源——原创剧本创作者的利益是关键。在现有著作权法规定可资利用的情况下,应当首先充分利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解释法律规则,而不是通过立法论创设规则,以保护剧本杀剧本创作者的利益。在解释侵害著作权行为时,将侵害行为等同于或者限定于直接利用作品行为,会使将直接利用行为作为侵害著作权工具的行为逍遥法外,并使著作权人利益受损,扭曲作品创作的激励机制。本文提出的手足论,从理论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解释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