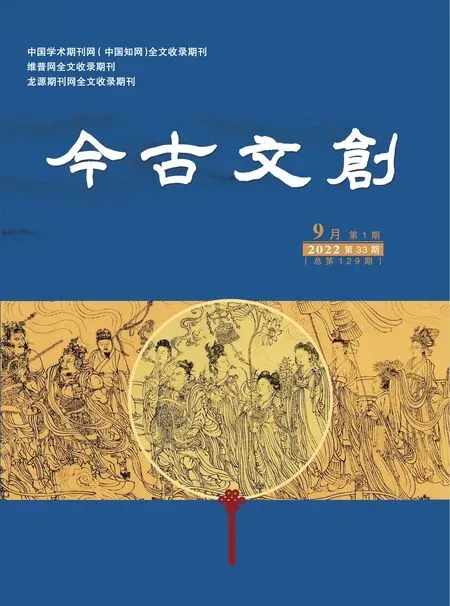浅论天下概念的跨文化意义
◎鲁文静
(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4)
一、天下概念的主要内容
(一)天下体系:起源与动机
“天下”是赵汀阳教授自21世纪初开始不断完善的一个哲学概念。所谓天下,意即“普天之下”,不仅是一种指代地理方位的原始观念,更表达了一种宇宙论层面的对世界的关怀。“天下”这一观念源远流长,古已有之;1943年罗梦珊先生从此发挥,把“天下”建立为一种中国式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天下体系”。而这就是在赵汀阳教授以前的、关于“天下”的简明概念史。
2001年,赵汀阳教授为欧洲跨文化研究所的一项有关帝国的课题撰写了两篇论文,在这两篇论文中,赵汀阳教授论证了一种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政治体系,而这种体系被赵汀阳教授命名为“天下体系”。在此,天下这一概念完成了从政治学走向政治哲学的进程:赵汀阳教授所谓的天下体系,不再是一种宇宙论关怀或者政治意义上的构想,而是一种新的世界制度哲学的概括。
有关诠释哲学意义上的天下体系的动机,赵汀阳教授在著作中是这样表达的:“今天中国正在重新成为大国……是在进入一种新的政治经验……当今中国正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必须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对于世界的意义。”诚如赵教授所言,当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大国的位置,假如关上门来,封闭自身,固然可以过得很好,但还是不免在参与全球话题、负起全球责任等等方面产生许多遗憾。因此,想要加入全球讨论,势必需要自己的一项核心主张;而对于中国而言,这一主张的政治哲学部分很可能就是天下体系。由此,天下概念从常识中抽离自身,走向政治哲学,就具有其思想上的必然性了。
(二)关于核心概念“天下”的分析
理解天下体系只是分析其中所蕴含的跨文化意义的第一步。毕竟,尽管天下体系已经进入了哲学讨论,但它毕竟还是从纷繁的政治现象中抽象而来的。那么,应该如何从一个关于政治制度理想的概念中提取出一种跨文化意义来呢?在此,或许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返回天下体系中的“天下”概念。如前所述,天下体系是在一项关于帝国的研究中提出的;由此,天下体系中与“帝国”不同的“天下”概念含有对现有帝国概念的否定,是对当前世界的世界体制的反拨,因此是新的世界制度哲学的核心。所以,从天下概念出发,分析其中对当今世界制度的不合理之处的否定,以及对未来世界制度地从理性层面的构思,或许就能为人类文化的未来找出一种跨文化意义上的可能性。
有关天下体系中的天下概念,或许可以定义如下:天下概念所关涉的是一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利用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资源,从全球视角提出的关于正义的理论(即天下体系)。有关这一定义,主要可以从“世界制度现状”和“文化传统背景”两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从世界制度现状方面而言,当今世界仍然是一种“非世界”。尽管在世界上,全球化已经使任何本属于某一地区的问题引起世界范围的反应,例如越南因为新冠疫情工厂停工,美国就要买不到耐克球鞋,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了:我们的世界仍然处于一种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时代,仍然缺乏一种能够代表全球的世界利益,更不要说出于维系世界利益的需要而推行的世界制度,以及全人类所公认的价值体系了。由此,在遇到重大问题,或者相互利益、权利产生纠纷时,世界秩序会迅速走向混乱,人类看不到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的共同基础。
其次,从文化传统背景方面而言,中国乃至其背后的东亚文化圈流行儒家文化,这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完全异质的文化形态。儒家文化强调对人的德性进行发掘,以求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理想;而西方文化起于古希腊世界对世界本源的物理学追问,追问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怀有对理性的追求。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具有一种无神论的背景。中国文化讲求经世致用,关注此岸世界,并不热衷于追求彼岸世界的安宁;而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影响,是一种一神论的文化形态。东西文化交流时,文化传统往往成为障碍。
通过以上两个角度可以看出,人类世界的确具有建构一种新世界秩序的需要,而这种新秩序必须能够保证控制不平等、提供全人类交流合作的平台。假使世界继续处于混乱无序的“非世界”状态、不能找到共同的利益和公认的价值,那么全球化所指向的包容、合作、和谐等理想的世界状态就永远不能成为现实。而“天下”概念所关涉的正是基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资源、针对现实需要所提出的哲学构思:天下是一种无外世界,也即一种全人和谐共处、四海一家的乌托邦。换言之,天下中所包含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构想。正因如此,一种跨文化的意义才可被推导出来:假如天下体系成为现实,那么一种不同于帝国体系的、有利于人类间相互交流和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的跨文化形式也就具备了制度基础。由此,关于天下概念的跨文化意义的思考才真正得以引出。
二、审视跨文化:一种新的生命角度
(一)基于新世界制度的跨文化
在进一步讨论天下概念的跨文化意义之前,首先需要廓清的是天下概念所对应的“跨文化”究竟是什么。
在赵汀阳教授的著作中,有这样一个关于跨文化的定义:跨文化意指通过将本国文化传统与其他文明的文化传统加以比照,由此吸收其他文明之文化的可取之处,改变对本国文化的固定观察视角,从而构建出一种基于普遍的人类视角的、关于本国文化的新知识,从而实现全人类间的相互理解。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了:这种作为人类理想的、普遍的、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何以可能?
通过分析可知,天下概念所对应的跨文化过程最终要实现的是一种文化的共可能性,即取消了解异质文化的特殊目的,使所有文化能够汇集到同一个公共平台中。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分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各个主体需要跨越彼此之间的隔阂,参与到真正平等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中去。但是,各个主体间的隔阂如何跨越呢?在《一神论的影子》中,赵汀阳教授分析了这一问题的关键:要想各文明相互跨越隔阂,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形成交流理解的“聚点”;就好比一个城市中最具特色的地标建筑,人们在相互约见却又忘记商量具体地点时,第一反应是到地标建筑附近等候。但是,就目前的世界现状而言,这样的“文明的聚点”实际上并未形成。具体而言,各文明间具有“不可共享利益的冲突”,而且缺乏能够共享的传统、历史与经验。由此,跨文化要求达成“心的一致”,然而却往往导致“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文明的合取”。
结合以上关于天下概念本身的分析,可以大致明白其中的原因:目前世界并不具备一种能够代表全球的精神上的一致性,因而也就无法调解物质层面的相互冲突;而物质层面的冲突不调解,精神层面的一致和交融就无法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赵汀阳教授也曾对此表达过关切:在西方世界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存在一种“一神论的影子”。以往西方世界试图把自身的经验与传统借助强权强加给其他文明;然而,尽管对于历史事实而言,这一过程或许为落后国家带去了先进经验,但却是以泯灭落后国家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假如这种做法的基础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也是一种强迫式的普遍主义,它并不基于各个文明的自愿与自主,反而更像是被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扭曲的对话形式。
所以,只有克服了强迫式的普遍主义,才能迎来一种平等普遍主义。调和世界冲突的世界制度能够为平等普遍主义提供基础,而平等普遍主义作为替代性的思想原则,能够引导人类走向平等交流,从而实现价值的汇聚。平等普遍主义或许能够为找到跨文化的“聚点”提供帮助。
(二)从生命角度出发看“平等普遍主义”
从宏观上看基于新世界制度的跨文化,可以得到一种替代性的平等普遍主义,作为这种跨文化形式走向现实的思想原则;但更进一步,人类还需要一种视角去发现这种平等普遍主义在现实中的可能性,即对于现实中的每个个体而言,一种全新的世界制度所带来的文化交流的新形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或许选择一种生命视角,更有助于揭示其中的现实必要性。具体言之,平等普遍主义的可能性背后是世界生命的普遍相似性。由此,世界生命的这一特性就是跨文化的基础;跨文化的价值在于世界生命价值,而要想确立跨文化的意义,关键在于确立世界生命的意义。
如前所述,当下世界缺乏一种共同的制度基础,因而也就不具备形成共同精神的可能;除了已经论及的制度原因外,不能形成世界共同精神的原因还在于世界生命的意义缺失。世界生命的意义缺失,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下世界中生命普遍处于持续的动荡状态中。
在生命哲学中,关于生命有这样一个论断:生命之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动荡不安。具体言之,生命并非一个静止不动的客体,而是一个永远处于一种动态过程中;这样的动态过程也并非就是持续向好,而是根据具体的环境不断改变,生存境遇也会变化。由此,生命过程的确就像一条河流,不断地与未曾经历过的新状况遭遇,“动荡”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从此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动荡与当下世界生命最新的遭遇是不同的:当下世界生命所遭遇的动荡,并不是一种自身生命过程之特点的体现,而是一种生活的主题。当下世界生命的生存境遇就是动荡的,生活的主题也是动荡的。世界生命需要面对的是一种系统性的持续动荡。
在此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既然世界生命的意义缺失之原因包含了系统性的持续动荡,那么,这种意义缺失是否应该被包含在制度原因之中?或许看起来制度缺乏和生命意义缺失是同一回事,但实际上此二者之间有所区别:假如把世界生命的意义缺失视为制度原因引起的后果,那么这就取消了生命的独立性,把生命意义的合理性归为制度的合理性,实际上是进一步消解了世界生命的意义。进一步的,跨文化的新形式也就成了合理制度的附属品,仿佛新的世界制度一旦形成,就会附赠一个新的跨文化形式。然而制度仅仅是一个基础罢了。无论对于生命还是跨文化都应该持这种态度。
实际上,尽管生命之流的重要特征是动荡不安,但生命的意义却正是在于自主地在不确定的生命之流中追寻一种确定的生活方式。例如,人们经受挫折是为了更好地克服自己的缺点,或者积累处世经验,以更好地参与同类型的活动,获得稳定的结果;人们从事生产是为了获得收入,以便开展稳定的日常生活。在文化方面也是这样,古往今来人类开展过许多文化交流活动:例如数字的发明和传播;例如日本派遣使者来到唐长安城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例如在宋代以前,中国有许多人已经精通各种异国语言,等等。文化相互交流,也是为了取得审视本国文化的新视角,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追求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
通过以上关于生命的各种分析,可以看出世界生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普遍相似性。而当下世界生命的持续动荡正是西方强迫普遍主义所导致的一种后果。由此,跨文化的新形式具有一种现实必要性:通过平等普遍主义的跨文化交流,能够通过强调世界生命的普遍相似性,重新确立起世界生命的意义,进而走入世界精神的发现之途。
(三)生命视角下的跨文化的必要性
当下世界生命的持续动荡究竟能够在哪些方面看出呢?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就实现了对当下缺乏共同制度和精神的世界的病理诊断。由此,也就从生命角度说明了的跨文化新形式的必要性。总的来说,世界生命的持续动荡是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困境所引起的并发症:在逐渐走向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对话精神日渐丧失,无论是在个体与个体的层面,还是在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的层面。跨文化的必要性就在于对相互对话的重新倡导。
具体而言,目前世界生命的持续动荡是这样的:
1.新冠疫情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冲击
自2020年起,新冠疫情在世界持续肆虐;假如有一天新冠疫情终于得以平息,那么在抵抗它的过程出现的各种突发状况将形成全人类共同的创伤记忆。除此之外,新冠疫情也给世界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本雅明·布拉顿在《真实的复仇》中提道:由于西方政治腐败、管理失当,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分裂,所以当新冠疫情暴发时,西方必定以自己的脆弱性直面新冠疫情,由此,以往的正常生活和秩序必然中断。
2.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特征的加速现象
在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核心人物之一哈尔特穆特·罗萨的著作中,有一种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加速”现象被论及:在当代社会中,尽管技术已经十分发达,但个体的生活节奏也相应地被加速,原本用于再生产的时间反而被更多的生产活动填满,以追求所谓“更高质量”的再生产;由此,个体不得不加入一种竞速逻辑,参与压力越发增大的竞争,否则就会产生如同坐在平滑的斜坡上逐渐下滑的生命体验。这样的生命体验背后是对世界生命之生存意义的否定:已经参与了定量的生产,却不能因此获取等额的报酬;并且,个体生存的意义完全依附在参与生产加速的过程上,除了加速,别无生命价值的其他体现。
以上几个层面只是世界生命的持续动荡的部分体现。但是,其共同点是明确的:当下世界生命“想要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中追寻一种安定的确定性”的活动秩序被打断了,只剩下绝对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体本身缥缈无依的生存形式。在这样的情形下,生命之动荡就成了个体生活的绝对主题。由此,实现异质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也就具有了必要性:在裂隙渐密的现代社会中,因世界生命的普遍相性,亟须转换看待自身文化的固有视角,以发现自身文化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并且,世界也亟须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世界文化”,以引导人类渡过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危机,走向光明的未来。在建立世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平等普遍主义的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交融,是满足以上需求的其中一条路径。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赵汀阳教授提出的“天下”概念,揭示出这一关于世界制度的哲学构思中所隐含的一种跨文化意义:当下世界生命而言,立足于生命之流的不确定性而开展对安定的确定性之追求的活动秩序被打断了,生命意义被迫依附于绝对的不确定性之上,个体的生存形式变得缥缈无依。在这样的情形下,生命之动荡就成了个体生活的绝对主题。天下概念的跨文化意义也正体现在此方面:新的世界制度呼唤世界在其他方面的改变,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光明未来。基于世界制度基础和生命的普遍相似性的、平等普遍主义的跨文化交流正是对世界生命状况的一种回应。通过以上分析,不仅可以发现天下概念之跨文化意义的现实必要性,还有助于借助生命角度,进一步理解天下概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