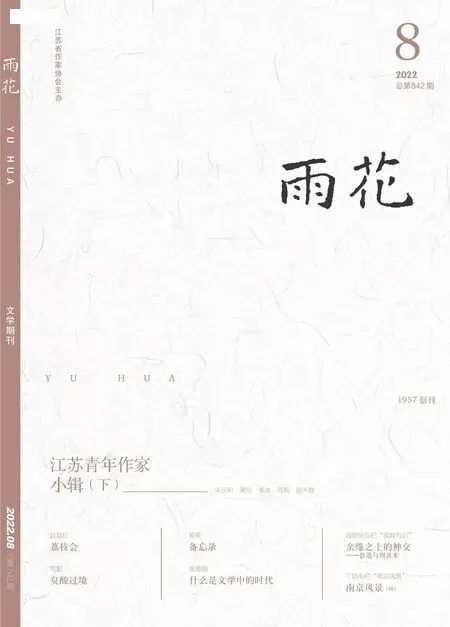往事森林
朱天蔚
草地上的旧汽车
习惯每天早晨醒来做的第一件事,
是喝一杯温开水。
我已经摆脱胃药有段时间,
我的状态很好,我想保持。
我的身体比衣服珍贵,我的衣服
比房子珍贵。我的车子,那台遗留的
〇六年产的起亚,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
去见了我父亲。它的残骸停在楼下的草皮上。
之后,我没有再买车子的打算。
有些地方车子没办法去,比如小巷子、田埂。
有些事情驾车做不了,例如散步。
每天下午放学,
孩子们钻进旧车子里
操控他们的新玩具。
他们坐在我曾经坐过的地方
把玩方向盘,握在我
曾经握过的地方。一个孩子说,
“长大以后我也要
买一辆汽车。”
新旅馆
十月,尤加利树比夏天时更修长。
边防工人散落在山顶,山腰上。
越南的山雨飘过来,像上帝用
薄荷叶和水泥调一杯
越式鸡尾酒。
傍晚,我从爱店峙浪乡乘车赶来
支援前线。同事们被雨淋湿
回到公寓里。这是我的新旅馆。
当晚越野车在群山之间穿梭
夜里山雾涌动。
我有一丝快乐,并想起
应该忘记一些事情。
往事森林
阳光在我归家之前光临我的屋子,
像一位熟识的客人。
我推开房门的时候,
它已经坐在了椅子上。
空调没关,静寂地吹了一整天,仿佛
在迎接我的归来。还有什么事情
比这还让人愉快的。
我们缓缓地交谈,分享桌子上的
红茶和饼干。记忆里
我许多房间大体都糟糕。
墙上腻子在掉落,脚下是粗糙的水泥。
整个夏天,只有一台笨重的电扇
卷着滚烫的风。我也曾在一间
铁皮围成的办公室里度过冬天,
把衣服裹在身上,在墓碑般的夜晚
汲取你梦里的体温。
人们总是低估自己的过去,
我未曾想过可以逃离炎凉。
但此时的房间里少了一缕发香。
回忆如野草,在地板上丛生。
我在房间里踱步,每一步
都迈入往事的森林。
地铁
地铁忽停那一霎——
一万匹野马穿过我的身体。
待我重叠的身影恢复平静,迈上列车
随着这条运输灵魂的暗涌
奔腾在城市下方,
每一个站台
成为一座水火山。
暴雨
七月末的夏天,
先是河南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
罕见到可以看见各种机械
和人类的遗体
在水里游泳。
然后
汛情漫延到了广西。
然而只是连绵地下,
并没有
考验城市排水系统的打算。
我还在餐厅里读布劳提根,
期待着可以把鱼钩扔向
马路中央。
餐厅角落的那对男女还是没提分手
他们在等什么呢?
雨都已经
下过了,
该说的都已经
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