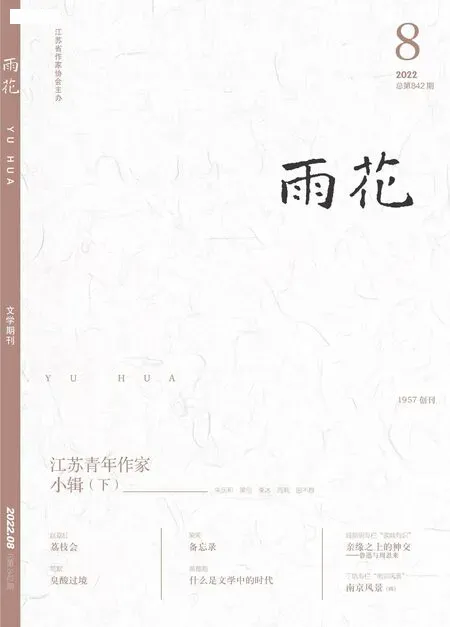拈花寺
刘 畅
阳光照在门檐,光影切割窗口,爸妈的老屋留给哥哥,再回来时,没有居留之所。台阶上开着童年时的太阳花,心中喊声大师父,女尼抬起头——当年玩耍的女孩,如今面孔陌生的妇人,烟尘在光柱里翻飞旋转,愿望捎至虚妄之地,无人识得旧时影。
这是2018年回淮安写的一段文字,像是梦。
淮安市淮安区,故称“楚州”。小学三年级时,我家由东长街淮安师范附属小学南搬至莲花巷,莲花巷三百余米,东起东长街,西至南门大街,蜿蜒曲折。莲花巷有古拈花寺,大人们不说寺,说“庵”,庵里住着“尼姑”。童年的我好奇拈花寺的名字,觉得神秘。拈花寺开着的门露出内里的一角,我走进去,无人阻拦。院里四间屋,正屋门头有石刻“拈花寺”三字,屋顶小瓦层叠,檐角卷翘,涂过白石灰的青砖墙面留有干涸的雨迹,墙角处,白石灰脱落,露出斑驳青砖。
蝴蝶翻飞于草尖,于寂静中增加颤动,老太太走进院中,她戴黑树脂镜框老花眼镜,留二道毛发式,头发又白又厚,靠耳边的头发用铁丝夹夹住,穿月白斜襟衫,黑裤子。你是哪家的?刘家的。莲花巷7 号刘厂长家的?老太太认识我爸,她默许了我在院子里玩耍。回家问爸爸,爸爸说老太太是大师父。大师父六岁随母亲来拈花寺,是拈花寺真正的出家人,其他的有的是半路出家,有的是居士。爸爸还说,拈花寺原本不只四间屋,东边居委会的社办厂也是拈花寺的。我好奇拈花寺为何只剩下几间屋,爸爸说因为特殊的年代,接着就沉默不语。
拈花寺成了我童年的乐园。下午或放学路过,只要拈花寺的门开着,我就溜进去。拈花寺的花草长得蓬勃,鸡冠花、晚饭花、太阳花、月季、指甲花、一串红点缀着院子。鸡冠花是杂花,它们卫士般站立,花冠如充血的鸡冠,我好奇地伸手捏,扒出鸡冠花黑色的花籽,将花籽撒在地上,再留点花籽用纸包着放进口袋,回家后撒在院子里。花籽掉进土里,过些天,冒出花苗,花秆长硬,浅黄的、玫红的花变成橙黄色、酒红色,在墙角下密密麻麻。晚饭花在暮晚时开放,长在有阴凉遮挡的地方,一开一大片,像一群多嘴的小姑娘,明艳,娇嫩。我在花瓣上掐出指甲印,将花瓣搓揉成泥,再摘下新鲜的花朵,拉出花蕊的长丝,挂在耳朵上当耳环。晚饭花会散发出清幽的香味,不能养在室内,不然会引起神经兴奋,睡不好觉。太阳花日出开花,日落闭花,有重瓣和单瓣,颜色有妃红、白、淡黄、紫。太阳花趴在地上,一副弱小、任人踩踏的样子。我掐断太阳花脆嫩的花茎,挤出汁水,手指留下草木的腥味。月季有白的有红的,花瓣层叠,花秆带刺,带有天然的尊贵气质,我不敢摘月季。院子里还种着青菜、辣椒、茄子、丝瓜、葱、蒜等菜蔬,在我眼中,它们呆头呆脑,没有观赏价值。院子里没养鸡,出家人不吃荤。蝴蝶翅膀有绢丝质地,手指触碰到,留下白粉。蜻蜓鼓着眼睛,振动着有网状斜格纹塑料纸般透明的翅膀。蚯蚓钻进泥里,断开后还能继续生长。石头下藏着扁扁的灰色虫子,令人头皮发麻。有种臭虫,手指碰上后,难闻的味道洗都洗不掉。在花园里无所事事,孤独充盈饱满,我反复咀嚼头脑里冒出的话语和句子,自我探究,自问自答,自得其乐。
说到花园,我六岁时,爸爸带我去南京,住建邺路招待所。招待所花园里长有冬青、雪松和野花,爸爸外出办事,我在花园玩耍。有种小白花,花茎含有白色的浆,我摘下花茎,白浆冒出来,留在手指上,我紧张得要命,怕有毒。招待所厨师老王家的孙子陪着我,他有乌黑的大眼睛,脾气好,在花园里陪着我。这是我最早的关于异性的感知,现在想来,所谓的爱和温暖,无关物质和欲望,而是陪伴。我家院子里也种有太阳花、一串红这类杂花,我时常蹲在院子里,看花,看墙角的蚂蚁。蚂蚁排着队,连成一条长线,忙碌不休。我好奇蚂蚁从哪出发,到哪里去。经过观察,我发现蚂蚁从墙角的裂缝里跑出来,排成队,前往厨房的地面,去运送一颗饭粒,或者去某个地方运送一条昆虫的腿。它们被神奇的力量驱使,挥舞着小爪子,抬饭粒时几只蚂蚁配合,只看到饭粒在动。我便恶作剧,将水倒在蚂蚁的队伍中,蚂蚁大军被冲散,待水退去后,它们又另辟道路。我好奇为何蜻蜓低飞会下雨,它们飞得靠近地面只有五十公分,有时一只,有时两只,交叉飞行,像天空中翱翔的战斗机。蝴蝶的白粉是否有毒?麻雀站在电线上会不会触电?头顶的天空为何总是没有内容?偶尔一道云彩的轨迹划过,是飞机留下的印痕吗?比天空还高的地方还是天空吗?淮安之外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的人是否和我们一样?我在一道无形的墙之中,看不到更远。
拈花寺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名叫小平。她的脸有点长,眼角朝上,眼珠鼓鼓的,扎麻花辫,穿红褂子、草绿色裤子。大师父收养她,出钱供她读书,我背书包上学她也上学,我放学她也放学,她放学回来和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做作业,玩耍。因有小平,我更有了去拈花寺的理由,我们碰见了,格外高兴。她趴在桌子上做作业,我蹲在院子里看花,留意眼中的点点滴滴。
寺院里还住着两个老太太,她们老来孤单无依,带着余钱和衣物来到拈花寺。老太太穿深蓝斜襟褂、小脚裤,嘴巴瘪着,发髻插不住银钗,她们容身于几间旧屋,一餐一食依靠双手的劳作,她们的身影如同维米尔油画中的人物。我也是画中人,旁观者,在画面偏左的位置,我这样想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当作画家。在拈花寺,做饭做针线种菜打扫是功课,烧香诵经念佛也是功课。案头香炉里,几支香绵绵呼吸,哪天断一根,故事便有转折,接着又续上去,继续燃着、活着。傍晚,拈花寺传出木鱼声、念诵声,在花园里玩耍的我忘了回家,抬起头,走进屋里。老太太打开经书,念几句,敲几声木鱼。天黑了,老太太取下煤油灯灯罩,拧动棉线,划根火柴,点燃灯芯。点了灯,气氛就不同了,灯不怎么亮,但很温暖柔和。火关在玻璃罩里,视线有了焦点,没被灯光照到的地方有大片的阴影。房梁下吊着的竹篮里放着锅巴,盖着纱布。晚饭是稀饭就大头菜,锅巴当作零食和点心。蝙蝠在屋檐下飞,老鼠在屋角跑,猫趴下脊背,瞪圆眼睛准备扑上去。屋外,花草窸窸窣窣,虫鸣让暮晚更静,天上的月照见亘古的寂静。
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落实宗教政策,社办厂用地归还拈花寺。拈花寺重建是件大事,大师父筹集资金,辛勤操持,每笔善款、每块砖、每根木料、每顿素斋,都一一过问。有一次我放学来到拈花寺,看到大师父肩扛一根圆木,木头又粗又重,大师父的背都被压弯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手更粗糙了。她像蚂蚁一样和工人们一起背木头,不知疲倦。我惊讶,这哪是老太太干的事。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拆掉原本的几间旧房、危房,重建大雄宝殿等房屋三十余间,山门前有两座石狮镇守,门洞上刻有“古拈花寺”,大雄宝殿左侧墙上刻有拈花寺的简介,我得以了解拈花寺的历史。拈花寺建于清朝初期,原本占地两千余平方米,有大雄宝殿、山门殿、禅房、僧房,因战乱被毁大部,殿宇、经卷、法器毁损,日渐衰落。而拈花寺的起源、历史和现今都和女性有关。中国最早依戒律出家的女性是净检法师,生逢乱世,丈夫与父亲相继在乱世中离世,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如乱世飘萍,有缘得高僧点化,于是抛却三千烦恼丝,一心要做一个度化众生的比丘尼,挑起教化众生的重担。拈花寺开山祖师佳慧也是一名女性,她自小爱好诗文、书法,经常到隔壁老太太家聆听佛法,父母想把佳慧许配给好人家,佳慧却一心想出家。她为研习佛法,乔装为僧在金山寺挂单,一天,有贵人来寺进香,看到墙上的对联字迹娟秀,像女子所书。佳慧听说书法露了破绽,匆忙离开金山寺回到淮安楚州,在楚州古城创建拈花寺,依据佛法中“拈花微笑”的典故,以“拈花”立名。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拈花”二字妙不可言,“摘”花,“持”花都显粗野粗糙,唯“拈”,配合手部精细的动作,大拇指、食指拈起一朵鲜花,姿态优美,动作、情境来自想象,来自凝神时的遐思。
院子里成排的长凳显示仪式的热烈隆重,大殿里木柱漆着红漆焕然一新,木鱼换成大个的,羊皮鼓立于鼓架之上。拈花寺重建后成为淮安市佛教协会所在地,大师父被任命为淮安市佛教协会会长。在释迦牟尼佛像低垂的目光与虔诚的梵音中,大师父剃掉头发,头顶烙上戒疤,她披僧衣,戴佛珠,恢复法号“了僧”。“了”有一了百了之意,透露出生命苍凉的底色。厨房里冒着香油炒热的热气,圆桌上放着青菜黄豆素鸡木耳香菇藕粉圆各式素斋,我看着一道道菜,好奇,但没有品尝的欲望。在山门处,我挨着买香烛的香客的肩膀,看到站在柜台后的小平,她长高了,头发在脑后扎起。她没再读书,走出寺院嫁了人。我看了她一眼,她看了我一眼,玻璃柜台将童年的小伙伴隔开,她和大师父一样,童年时在拈花寺,现在又回到寺院,她低下头继续干活。柜台里的香烛有发财香、平安香、状元香、全家福、许愿香、还愿香,每一种香都对应着俗世的愿望。
晨钟暮鼓,在跟着录音磁带听港台流行歌曲、欧美摇滚乐的同时,我也被拈花寺的诵经声吸引。梵音响起,如水波连绵,具有神秘、撼人的力量,我顾不上吃饭,推开家门,来到寺院。大殿里,大师父身披袈裟合掌念诵,二师父、居士列队其后。女居士年龄不大,满头青丝,眼帘低垂,我看着她的脸,想从中读出内容,在我想来,来寺院里的人大都生活不太顺心,年轻的女子则更令我好奇。来拈花寺挂单的老太太皮肤白皙,神色安定。有个老太太头发花白,后背佝偻,脑袋垂在胸前。老太太是老姑娘,父母离世,她带着米油、衣物来到寺院。夏天热,老太太哼哼,没人过问她,后来没再看见过她。我妈忧心地对我说,你不会照顾自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后怎么办?寺院里来了二师父,二师父身高一米七,肩宽,肤白,一只眼失明,我害怕看到她那只灰蒙蒙的盲眼。二师父五十岁,头顶也有戒疤,相比大师父,二师父精明,能说会道,嘴巴不饶人。有次我和同学去淮师浴室洗澡,看到二师父,澡堂里没有遮挡和避讳,二师父脱下僧袍,坐在浴池里,蒸腾的热气包裹着她,二师父除了脸部、脖子、手这些暴露在外的部位皮肤有点粗糙,身上的皮肤很白皙,乳房如同年轻女子般洁白饱满,我们暗暗吃惊,她穿上僧服时,我们忘了她是女性。
山门殿居中供奉的泥塑穿金的弥勒佛,自在地坐在莲花台上。泥塑穿花金的四大天王,各持兵器,脚踩小鬼。泥塑彩绘的哼哈二将,手持金刚杵,目眦尽裂。大殿里的释迦牟尼佛、观音,各有各的姿态。立于大殿,抬头看释迦牟尼佛像,发散的思绪集为一束。我边走边看,殿前花盆里种着月季,院子里的水泥地,扫帚一扫就扬起灰尘。案头供着苹果、香蕉,花盆里插着塑料花,经书是新的。古人说“一人不进庙”,拈花寺建于居民区,左右前后都是居民的房子,有着浓浓的烟火气,寺里都是女性,她们除了着僧衣,和普通人家的女子没什么不同,这是拈花寺的特别之处。拈花寺里的旧佛像、经书、法器等均损毁,所剩的是大师父们日常使用的。厨房里,居士围着灶台做饭,小花猫在大殿的屋角下晒太阳,寺院里没有荤腥,如何养得住猫?厨房里的青花瓷罐用来盛盐或者食物,画有彩墨人物的茶壶用来喝茶,都是生活所需。有外地学画的画友来淮安,我带他到拈花寺,他看见厨房里的青花瓷罐,眼睛亮了,和大师父说出三百元买,大师父说不卖。他说拿新的换,大师父摇头。他悄悄和我说,我拿走也没人知道。我吓了一跳,拈花寺的门总敞开着,有人来也不多问,的确有顺手牵羊的机会,民间隐藏有好物,拈花寺也有旧物件,我害怕他哪天来拿走大师父的青花瓷罐。淮安是座古城,仅莲花巷所在的楼东社区,就有秦焕故居、罗振玉故居、杨士骧故居、朱占科故居,百年前的豪宅多少存留些遗珍。小学同学罗红梅,爷爷奶奶是大地主,她家对门是罗振玉故居。她家三进院子,清缝起墙、小瓦现顶、檐口连角。到她爸爸这辈时,一进院子破败,屋角漏光,用来做厨房和餐厅;二进院子用来居住,地面铺青砖,条案放有青花瓷瓶,瓶子里插着鸡毛掸子。她奶奶梳发髻,穿斜襟褂、小脚裤,细长的眼睛也像鸡毛掸子,一派老式的威仪。再远点的淮安季桥镇出土过元青花双耳兽缠枝牡丹纹罐,器形高大,完好无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拈花寺的青花瓷罐色彩浓艳,有卷草和莲瓣纹。再回拈花寺,没再看到青花瓷罐,而美,留在时间里。
有历史积淀的地方,垃圾都是有价值的。有次我在寺院山门前看见猫在吃饭,猫碗是只破碗,碗口缺损,碗身描绘着缠枝花卉、蝙蝠,釉色莹润,设色淡雅。我看碗的图案好看,悄悄拿家里的碗换了猫碗,拿回家后画了张油画,名为《瓷器》。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淮安,画被家人放在院子东边的走廊,雨淋日晒后损坏,被当作垃圾扔了,现在想起还很心痛。碗被我带到南京,放在新买的房子里,公婆来住时,嫌碗是破的,给扔了,这是我的猜测,也许被人拿走了,就像我当年从拈花寺拿走它一样。拈花寺里还有一只描绘着一支红花,外壁施绿釉的清代粉彩碗,碗身裂了条缝,用铁钉补起,放在厨房角落里。绿底配一支红花,色彩浓烈,图案抽象简约粗犷,和法国野兽派绘画大师马蒂斯的绘画作品《舞蹈》相近。马蒂斯出生的1869年是同治八年,清代的瓷器色彩明艳,图案多为写意花卉植物人物,和崇尚现代抽象审美的野兽派画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彼时,欧洲的画家们也向东方式的审美学习。随着时间的消逝,拈花寺里的旧物不见踪影,再过几年,眼中所见,皆是超市里出售的价格便宜没有美感的流水线产品。
每逢十九香会,莲花巷挤得里外几层,善男信女们带着供奉果品,寿包寿桃寿面,厨房里的寿面锅一夜都不熄火,我只是看,没品尝过。穿梭于寺院,用眼睛摄录,拈花寺不再是童年时的乐园,而是属于大众。在拈花寺,大师父于我是亲切的。在寺院帮忙的居士看见我,眼里露出疑问,我不多言,如有人问,便说住在莲花巷的,对方不反对,也不表示欢迎。寺院院子里,有成捆地燃烧着的香,也有三支一束插在香炉里的,香灰堆积。人还没走近,热气、烟迎面扑来。善男信女匍匐在大雄宝殿的拜垫之上,我也跟着学。朝功德箱里头投放零钱,师父便敲钟鸣响,仿佛愿望得到回应。拈花寺里声音高亢、变化,来自佛事仪式。拈花寺侧殿的“往生莲位”存放着过世的普通在家人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有老人,有年轻女子,寺里会为他们举行超度法会。放焰口源自《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阿难尊者于林间习定时,夜见焰口鬼王,焰口鬼告诉阿难,三日后,你就要命终,堕入饿鬼道。阿难听后,赶忙跑到佛陀座前哀求救度。佛陀为阿难讲说焰口经,并教示阿难召开无遮大会,召请对象上至前王后伯,下至伤亡横死之流,道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普济精神。
通常,放焰口与丧事结合在一起,也有为活人消灾的,在重大法会时,也会放焰口。放焰口仪式由男性担任,往往需要十几个人共同完成,他们居住在乡村,平时忙农活,有佛事时到寺院,披袈裟,戴毗卢帽,戴佛珠,在佛案两侧相对而坐,案上放着法铃、戒尺、香炉。和大师父平日的诵经不同,焰口里的唱腔变化多样,词句优美繁复。他们一边唱颂一边翻动着经书,累朝帝主,历代侯王,九重殿阙高居,万里山河独据,西来战舰,千年王气俄收;北去銮舆,五国冤声未断。呜呼!杜鹃叫落桃花月,血染枝头恨正长……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唱腔伴以“呜呼”“唯愿”的感叹声,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唱到激越处,如江河流淌,或众声齐颂,或来回呼吁,木鱼、铙钹、手鼓等物器轮番鸣响,我立于门侧观看、聆听,屏住气息,心提至嗓子眼,又沉沉落下去。
斋主焚香叩拜,法师将案上作供品的糖果抛撒出去,众人争抢,以表功德圆满。过后,法师在唱颂声中烧纸扎的房子。纸扎的四合头的房子有门有走廊有窗,有的有二层楼,屋檐有龙,屋内外有人,仆夫,院子里有牲畜。我津津有味地观看,感叹精致的手作竟要烧掉,岂不白费了手工,可人们乐意这样做。在近年的国外艺术展上,中国艺术家制作库房展出,造型朴拙,在西方艺术语境里独树一帜。烧库房时,法师用竹竿将火头向下按,将纸房纸人慢慢烧掉,燃烧的灰烬在空中翻飞,然后落回地面。
1988年我入学淮安师范学习美术,立意画画,不知是否和童年时的“看”有关。学习绘画,绕不过拈花寺,拈花寺的花花草草,库房扎纸艺术,通过画面、文字、语言、经验去认知,通过想象去创造,通过想象沟通和对话,这也是艺术的功用。淮安师范在莲花巷斜对面,从家到学校步行十分钟,我在拈花寺转悠,看到感兴趣的就画下来。我画过拈花寺的大殿,寺院的外墙是灰色的,大殿的走廊有红漆立柱,这张水粉画被幸运地保存下来。有一次,我在拈花寺看到一个年轻的女香客,脸圆胖,眉眼周正,黑发齐耳,穿无袖红连衣裙。我从家里搬来画架,拿来颜料、调色板,找张凳子,让她坐在山门前,从门廊折进来的光让她的脸半明半暗,我用一上午画她的半身油画肖像,现在想来,我当时大胆,不知寺院的礼仪。我能在拈花寺任着性子,和大师父的宽容有关。虽然经常去拈花寺,我从没向大师父请教过佛法,唯一的一次,淮安师范的美术老师让我带他到拈花寺,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淮安师范,嫌淮安地方小,总想到南京。大师父手拿经书,说好好的离什么家,在单位好好工作,在家孝顺父母,教育孩子,当教师就把教师的工作做好。美术老师问,要天天烧香吗?大师父说想到就烧,有时间就读读经书。大师父朴实的话语让我觉得佛法并不遥远。
大师父当上淮安市佛教协会会长后,每年也会走出山门,到各地名山古刹交流。有一年,大师父从五台山回来,带回一个十八岁的比丘尼。大师父年龄大了,她想拈花寺后继有人。一天下午,我来到拈花寺,在大殿旁的侧院里,看到树荫下有人在晒被子,被子被掀开一角,一个陌生的穿灰色僧服的年轻女尼站在树下,她和我年纪相仿,脸庞圆润白净,干干净净。在拈花寺看到的都是老太太,第一次见到年轻的女尼,我按捺不住好奇和激动,回学校后告诉了同学陈娟。陈娟来自苏北农村,她文化课成绩好,本可以读重点高中,她看镇里的玻璃店画玻璃画可以挣钱,中考时填了师范美术专业。陈娟和我来到拈花寺,见到女尼,陈娟站在我身边笑,眼里透出亮光。笑了一阵,我们互相介绍,女尼说她叫慧洁。慧洁让我们去她住的小屋,我们暗自高兴,这可是第一次走进出家人居住的房间。屋里干干净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床单是新的,可见大师父对她的关照和喜爱。慧洁从书桌的柜子里拿出影集,影集里有她和师父的合影。我好奇女尼怎么可以和师父合影,她说那是方丈。寺院里等级森严,规矩多,比丘尼看到方丈要合掌致礼,侧立于路边。佛门弟子按受戒律不同,分出家五众和在家两众,这解了我的惑,我明白了拈花寺为什么有比丘尼,还会有男性出家和在家人来做法事,有的是剃度过的,有的留着头发。说到放焰口,慧洁说她的师兄在广州放焰口,一天能挣好几千,挣了钱就寄给家里,也给自己买东西。我好奇,出家人也挣钱?慧洁说广州那边的人有钱,不在乎多花钱,比丘尼中有读书识字的,真能讲说者比较少见,有能登台讲解经律的,则很受欢迎。影集里有张照片,白雪覆盖山石,慧洁穿棉僧服戴棉帽坐在石头上,她身边的人被剪掉了,留下一个轮廓。我好奇为什么剪掉,慧洁说那人不在了,我不便多问。问她这么年轻为何出家,她说山区人家生活贫穷,女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在山里只能和父辈一样,同村的几个女孩都出家了,她只能通过出家离开大山,改变命运。我好奇慧洁为什么到淮安拈花寺这个小地方的小寺庙来。她说当时年少,不知天高地厚,妄自菲薄,向往着去大城市。慧洁说大师父想她留在这里。我们没把慧洁当作比丘尼,只把她当作同龄的女孩,不明白大师父的良苦用心,就像不明白父母的用心。
慧洁的到来惊艳了拈花寺,来拈花寺的香客更多了,香客会带来吃的用的。有个女香客,来到拈花寺,从袋子里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用欣赏、怜爱的目光看着慧洁,问寒问暖。慧洁微笑着,表现得不卑不亢。她们殷切地希望慧洁留在拈花寺,慧洁不仅年轻,而且是从五台山来的,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她们期待慧洁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她们可以时常来和慧洁说说话,她们在俗世被击打得破碎的心便也有了依托。我和陈娟没课时常来拈花寺找慧洁。有一天,慧洁外出理发,我们和她一起去理发店。她背着布袋,身穿灰色僧袍,脚穿僧鞋,我们跟在她身后,感到特别骄傲,不同凡响。走进东长街的小理发店,慧洁的神情变得严肃,她坐在理发椅上,目光低垂,年轻的男理发师恭恭敬敬为她剃发,理发后,她付了钱,向理发师合掌致谢,理发师合掌回礼。我们被她给镇住了,她更美更端庄了。
师范学校的外地学生住宿舍,我每晚回家住。陈娟的经历有点特别,她说起她的家,她爸爸家暴,经常打她妈妈,她小时候就讨厌男人,认为男性是女性痛苦的根源,她想独立生活,包括精神层面,她一边想早点谋生,一边苦苦思考、寻找精神出路,她一方面无法依靠家里,另一方面,在外处事又不够圆滑,所以难免受到挫折。同一宿舍住她对面床铺的她的同乡,性格温和,学习好,听话,很得老师的喜欢。陈娟不听话,有几次,她没回宿舍,后来干脆在学校对面的巷子里租房住,房子小得只够放一张床。快毕业时,陈娟很少在学校,后来干脆住进拈花寺,自然也为了省点钱。大师父是宽容的,但也对陈娟有了意见,说她每次来,寺院的山门都关起来了,她还不走。陈娟住拈花寺,和慧洁住同一间屋子,屋里只有一张小床。每次进寺里,我只走走看看,陈娟则要讨论一番,说些我听不明白的话,她将慧洁当作听众,她需要有人倾听。作为美术专业的学生,我们乐于尝试和探索,乐于接受新的潮流和思想。有一次陈娟提出,和同学轮流做人体模特画素描,在女同学租的屋子里,戴深度近视眼镜,身材圆圆胖胖的女同学脱掉衣服,陈娟说这才是西方古典油画里人物的体型,她赞美女同学像鲁本斯画中的丰满强健的女子,具有生命力和母性美。轮到我时,陈娟也许是故意气我,说我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代表,生长在温室里,禁不住风吹雨打。陈娟脱掉衣服,她皮肤白白的,身材偏瘦。对初学绘画的学生来说,画人体有难度,学校里没有人体课,人体素描要到大学里才有。我们在纸上认认真真地画下一些不成样子的线条,然后又侃侃而谈,聊审美聊绘画流派聊所能想象到的外面的世界。我想起陈娟第一次看见慧洁时不好意思的笑,现在想来竟有意味。我们师范毕业后,慧洁也离开了拈花寺,没人知道慧洁为何离开,但我知道和陈娟有关。我们聊天时,陈娟向慧洁讲述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拈花寺在大师父眼里弥足珍贵,他人只是过客;拈花寺轻若烟尘,只有日常的琐碎、朴素的情感,无法获取更多。年轻的慧洁和我们一样,耐不住小地方的寂寞,忍受不了信息的闭塞造成的精神的困顿,想到更广阔的地方放置思想和灵魂,也许还想改善经济条件。我后悔不该带陈娟来拈花寺,如果她不来,不住进拈花寺,慧洁会走吗?我无法得知。
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去拈花寺,在院子里走一走,烧一炷香,在大殿里拜释迦牟尼佛,看看观音的脸,寻找没有答案的答案,再踏上回程的路。曾去过名刹古寺,但在我心中,拈花寺是不一样的存在,它大隐隐于市。在拈花寺停留,焦虑的心情得到缓解,心思变得清明。虽只是暂时的慰藉,无法阻止信息的洪流将心灵撞击为碎片,无法阻止青春时代的热情逐渐减退,但我想拈花寺是懂我的,再回拈花寺,在侧殿的香案上看到大师父了僧的黑白照片,她和莲花巷里普通的老者没什么不同,在她的脸上,写着过往的艰辛和未曾言说的凄苦,我的耳边响起大师父的话:你们工作、生活好好的,出什么家呢?她是否知道,有个当年的小孩因她的缘故,一次次回到这里。
站在拈花寺二楼侧殿回廊东望,寺院的屋檐挨着居民的屋顶,前后左右,房屋、院落高低错落,燕子停在屋檐,天空是那么蓝,站得高了,望得也远了。2005年,淮安籍普法大和尚返乡捐资,翻建大殿,新建法堂、“佛手拈花”石雕、“知恩图报”九龙壁,在莲花巷东入口处建起牌坊,并由普法大和尚书写了寺名“拈花寺”。现任拈花寺主持来自连云港,我不再相熟,但我回淮安还会去拈花寺,台阶上开着童年时一样的太阳花,心中喊声大师父。烟尘在空中翻飞,无人识得旧时影。
拈花寺也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了烦恼,每次烧香,香的味道和烟尘随风飘进居民的院子里。有的人家不在意,有的人无法忍受,比如我妈妈,她对气味过敏,忍受不了香的味道,只好关上窗。但飘在院子里的烟味无法阻挡,她只好将洗过的衣服用竹竿晾在房间里,有段时间,房间里挂满衣服和床单,她嫌洗过的衣服还有味道,反复地洗,疲惫不堪,让家人不胜其烦。
2021年,淮安老城区拆迁,凡是和历史、文化有关的建筑都拆了重建。嫂子在家庭群里说,淮安天妃宫、老图书馆拆了,拆到新文街西头,六珠居委会拆了,新安学校附近拆了,老山阳村旅社拆了,儿童医院、楚州医院搬了,老城区已是空壳。嫂子说,期待莲花巷也拆,哪位施主来扩展拈花寺,把莲花巷这片给拆了,拆了买别墅,嫂子发了个大大的笑脸。妈妈说,拈花寺前后左右都拆掉是不可能的,除非拆西边董家的那一片,南边的工程量太大。令我感到惆怅的是,如果莲花巷拆了,“家”在哪里,曾经的乐园还寻得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