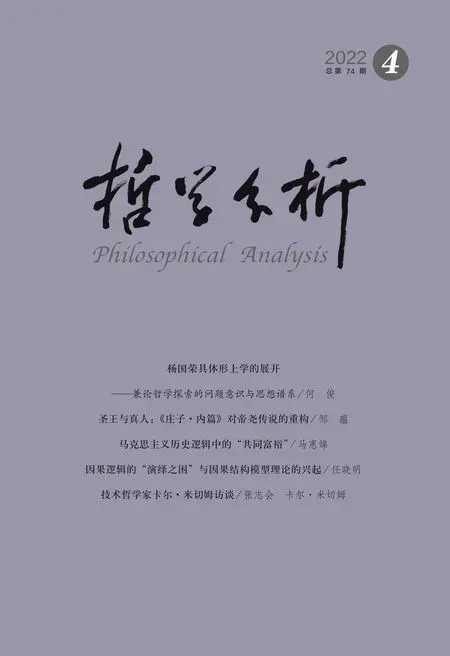杨国荣具体形上学的展开
——兼论哲学探索的问题意识与思想谱系
何 俊
纯然的客观世界先于人的存在,但这一纯然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却又因人的存在而“存在”。因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世界,即便仍然是纯然的客观世界——尽管这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它的存在仍然成为不同于作为纯然的客观世界而存在的存在。究其根本,一切因为人。人使得纯然的客观世界成为具有功能与意义的世界,并且这样的功能与意义是呈以不断延伸的状态的;与此同时,作为纯然的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也获得自身存在状态的展 开。
这原本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由于人的独特性——人是具有精神性的存在,并且其精神同样处于不断延伸或充实的状态,因此人对于自身从纯然的客观世界中分离出来,进而观察与施为于作为对象存在的纯然的客观世界时,人如何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基本性的预设前提。宋儒陆九渊以他著名的两个命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第一,“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第二,“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确认,但由于这一确认非常明确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尤其是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根本特征——心——获得了标示,因此这一确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与处理提供了富具开放性的空 间。
只是,尽管在标示心体存在的思想家那里,心与事几乎是同步展开的,但是,也许是因为心的向度要比事的向度更具有主体性的特征,或者是更具有主体的自由度,事的向度总是牵扯许许多多的羁绊,有许许多多的条件,因此心的向度很容易成为思想者青睐的世界。何况,追寻自由终究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最高理想。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创造性追求的哲学家,杨国荣教授的哲学探索也是由心体的打开开始 的。
一、心学的剖析
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宋明理学研究破冰之初,作为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杨国荣就以他的博士论文《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赢得学界瞻目。对此书的最大特点,杨国荣的导师冯契先生在序中指 出:
由对王学体系的内在矛盾的揭露,进而说明王门后学的分化,着重考察了志(意)知之辩的演进,李贽把王学引向异端,黄宗羲完成对王学的自我否定,并在“历史的余响”的标题下讨论了王学在中国哲学近代化中的双重作用等。这一系统的有条不紊的考察,比较好地贯彻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因此许多论断显得很有说服 力。
基于这一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将阳明学作为一代思潮加以研究,在着眼点上就必须很大程度上与仅仅研究阳明思想本身有所不同。前者的研究,必须在阳明思想中找到一条能将阳明思想与其后学联贯起来的线索,而且王阳明作为整个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条线索还必须能使阳明学可以被摆在思想史中加以解 释。
杨著于首章“王学的兴起”中首先通过对朱嘉、陆九渊思想的简要阐述,勾勒出他们各自的思想建树及理论上的难题,从而引出阳明学中的一贯线索乃是阳明思想中所存在着的个体意识与普遍天理这一内在二重性的结论。杨著以为,这一内在二重性来自王阳明对朱熹、陆九渊各崇天理与吾心的理论弊端的认识,而谋取此对立两面的融通则促成王阳明在理论上的建树和对朱陆思想的超 越。
接着,杨著在第二章“王学:王阳明的思辩体系”里以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而缜密地阐释、分析阳明思想。作者指出,构成阳明思想的主要是良知与致良知说,其中良知是阳明思想的基石,致良知是对良知的贯彻、落实。作为天理与吾心的合一,良知蕴含了双重性;良知作为先验之知,当其与后天之致相联系构成致良知时,致良知中便又有对立而求融通的两面;阳明一生注重“事上磨炼”,其致知工夫,具体上是展开于践履(行)的过程之中的,因此,致知过程实际上便成了知与行的合一并进。基于这种阐释,杨著较前人更确切地把握住了王阳明思想的本质,合理地揭示出其内在矛盾,从而科学地判定了王阳明思想的积极作用与 局 限。
由对王阳明思想体系的阐释,杨著分别于第三章“致良知说的分化”、第四章“志(意)知之辩的演进”中对阳明后学的分化进行了讨论。由于王阳明思想中所包含的二重性注定其演变不可能表现为单向的进展,故而在才智性情歧异不一的王门后学处,阳明思想必然遭到不同的理解而被加以诠释。对于王门后学的分化,前人作有多种解释,但杨著由于从王阳明思想的内在二重性出发来观察王门后学,因而使得他对王门后学纷争的阐释成为当时最为细密、合理的解释,足可备一说。除了对王门后学的分化作出阐释以外,杨著还在第五、六章中通过分析李贽、黄宗羲对王学的改造,从一个侧面,两个典型人物身上对晚明社会思想的发展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看法。总之,在阐释阳明学这一思潮方面,杨国荣当时的研究实已提出了超越于前人的新释 义。
此外,研究前人的哲学思想,阐释是基础,与之相应展开的理论上的细微分析则是不可或缺而犹见力度的工作。杨著于此方面,可谓相当精彩。王阳明本人立教,强调的是明心见性,事上磨炼,于文字甚是轻视,其思想亦即形式上的体系,要于细微处分析,研究者除了要吃透王学外,还必须具有相当的理论素养。杨著的优点在于:其一,所有的分析都从宽广的理论视野出发,这不仅使分析细微而深入,而且使所得论断具有富有启迪的理论意义。譬如在阐释王阳明良知(心)的双重规定的过程中,杨著指出在王阳明“在心禀受于天(得于天)的前提下,将吾心与理融为一体”的思辩形式中,包含着一些理论上的新建树,“首先是普遍的道德规范(作为当然之则的天理)与个体的道德意识的合一”。其次是“先验的知识条理(天赋的普遍之理)与自思合一”。再则是“一方面扬弃了(作为主体意识的二重属性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的抽象同一,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克服了二者的分离”,使二者统一的具体规定“以普遍观念在主体认知、评判过程中渐渐展开(具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 的。
其二,在借助西方哲学来分析比较阳明学时,不是以草率的态度、粗陋的手法给王学简单地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而是力求通过理论上的印证加深对王学的认识。这样的工作在整本著作中有许多,如对阳明良知中所含先验之知识条理的分析,对阳明致知过程中的主体认知结构的分析,对王艮自我的分析等等。从对王学的认识来说,这样的工作无疑是促进了分析上的深刻,而就中外哲学之比较研究来看,显出相当的功 力。
我重述杨国荣通论心学中的深入阐释与精细分析,首先意在表达,杨国荣对于心体的分析与认知自始即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展开的事实;其次意在强调,虽然他后来在心学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而且在哲学理论上开始进入自觉的探索与创造,但其学术视野、思想方法,以及具体的分析模式(我姑且概之为“二重性分析建构法”)可以认为是基本一以贯之 的。
二、立心于事
不过,正如杨国荣在《王学通论》中所分析与梳理的那样,如果限于心学,则即便是在阳明本人,其心学的建构中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二重性,至于基于心学而展开的思想,直到熊十力,这种内在二重性也未能消除。另一方面,我也曾通过对王门后学的讨论,指出王门后学由于在良知工夫的落实上封域于意识,几无不流归禅学。泰州学派强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原本足以开出新境,但惜未能真正在“事”的视域作出真正的思想透视,而只是流于表象的活动,故最终没有转出新的思想,而只表征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而不被列入“王门”。概言之,心学不能只论心,必须有赖于事的视域打开,才能真正建立“具体的”形上学,否则只是“抽象的”形上学。这里所谓的“具体”与“抽象”,乃取用黑格尔的概念,抽象意谓着贫乏与肤浅,而具体则是丰富与深刻。杨国荣在哲学上的探索,从心学开始,中经不同论域,诸如政治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思考,晚近回到事的视域,以建构他具体的形上学,这便是他在《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中所做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最新成 果。
《人与世界:以事观之》除去“自序”“导论”与两篇“附录”外,共六章。首章论事与现实世界,揭明现实世界不等同于本然的存在,现实世界因人的活动,亦即事而形成,并因此而获得意义,故因事而成的现实世界既是事实性的存在,又具有价值性的规定。次章论人因事而在,揭明人的本质在于其实践,亦即事的展开,人通过事的展开建构了社会关系,同时赋予其意义。第三章从事的视域看存在与生成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揭明存在与生成不是独立的,而是相合的,这种相合性恰恰根植于事。第四、五章由事与现实世界的讨论,转向心物关系以及知识论的分析。在第四章中,杨国荣指出,“仅仅囿于‘心’或限于‘物’,往往难以超越思辨之域而达到对两者内在意义以及相互关系的真切理解,唯有引入‘事’的视域,才能把握‘心’与‘物’的不同内涵并扬弃两者的分离”。从中我们足以看到杨国荣早年开始的心学研究所形成的认识在其中的作用与意义。心物关系自然衍生出知行关系,并聚焦于事。第五章是基于第四章的一个深入,无论是心物关系,还是知行关系,最终都导向事物之“理”。“事中求理”与“由理发现事”是此章的主旨。第六章论事与史,乃是将单个的事置于时间之流中加以讨论,从史的角度理解事的意义所在,同时从事的角度理解历史的真实性。整个讨论圆满而充分,其最终所确立起的思想逻辑,大概可由最后的两篇附文获得表征,即从人与世界关系中的感受出发,从而在认知、评价、规范相统一的意义上理解人类的认识并落实于具体的形态,即以事观 之。
为了更进一步凸显杨国荣早年博士论文就开始逐渐形成的思想方法,即前文所概括的“二重性分析建构法”,请举具体的论述以为呈现,且以最后一章,第六章“事”与“史”为例。在此章的引言中,杨国荣就非常娴熟地通过两句古诗将事与史的二重性挑明:孟浩然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把“事”中的“史”点出;李贺的“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则将“史”坐实于“事”之上。换言之,当人们面对纷然杂陈,朝夕变化的种种事相时,唯有深具历史意识,方能把握其中的意义,否则种种事不外是毫无意义的存在;而当以历史的眼光去透视现实时,如果不能落实于从经济、政治、军事领域到文化领域方方面面的具体事上时,历史虽千岁亦随风 飘。
在此下的“‘事’以成‘史’”一节中,为了更深入推进“事以成史”的讨论,杨国荣对“事”又进行了“个体性的活动”与“类的层面”的分析,即“宽泛而言,作为人之所‘作’,‘事’既表现为个体性的活动,也展开于类的领域。在个体的层面,个人所做之‘事’的延续构成其人生过程;在类的层面,人‘事’的代谢则呈现为前后赓续的历史演进过程”(第199页)。由此,杨国荣对两个层面的“事”逐次展开分析,并且将这种分析置于中西哲学的比较视域中进行,一如其在早年博士论文中所呈现的风格。比如,杨国荣通过举证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概念,以及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第199—200页),指出“对个体领域之‘事’与类的领域之间的关联,一些哲学家往往未能给予必要的关注”(第199—200页)。然后,杨国荣对“事”与“史”的关系作出他的充分论述,即在各种可能性的维度上,对“事”与“史”的关系进行说明,以表征“事以成史”的核心判断。在这一表征的过程中,无论是涉及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诸如日常言说与网络支付等等,还是关乎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诸如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二重性分析建构法”获得娴熟而一贯的使 用。
对于一个富具创造性探索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成果实际上由两方面构成,一个自然是他的思想内容,这往往为所有人所关注,另一个则是他的思想方法。由于思想方法常常隐遁于思想探索的过程与思想成果之中,容易被忽视,或难以获知。所谓“鸳鸯绣好与人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既是在述说不轻易传授方法,但也完全存在着另一种广泛存在的可能,即作为方法的金针,即便在原创者那里也未必有高度的自觉。杨国荣曾就他的哲学研究方法作有“思”与“史”并重互涵的说明,在某种意义上,思史并重与互涵也是“二重性分析建构法”的一种具体使用,但也因为只是一种具体使用,故作为杨国荣的哲学方法论而言,我以为“二重性分析建构法”更具有普遍的理论价 值。
三、象山心与事的印证
在阐明了杨国荣的方法以后,为了更具体地彰显杨国荣《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的哲学内涵及其意义,我试取象山心学处理心与事的关系,进一步来佐证杨国荣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对象山心与事思想的阐释,来补充杨国荣的论 述。
在本文开头即引入的象山两个基本命题中,除了宇宙与主体的关系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获得确认以外,象山心学的认知格局中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即事与心的问题,亦即少年象山援笔所书的另一段话:“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 事。”
依据发生认识论的原理,人的认知格局主要是通过人的活动而获得形塑的,所谓人的活动,便是象山所讲的事。事实上,活动不仅在认知格局最初形成时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而且在此后的认知中始终起到持续的作用,因为认知格局是在持续扩充并得以固化的。而且凭借着“吾心即是宇宙”的开端,象山的“吾心”就把自身显示为宇宙存在的根据;不是宇宙作为矢量性存在的根据,而是宇宙作为人化了的存在的根据。这意味着,宇宙既被理解和表述为客体性质的存在,又被理解和表述为主体性质的存在。实现这一理解与表述的,显然不能限于心本身,而必须通过心所要面向的事情,亦即活动,即事。换言之,无论是理解心,还是确立心,必须使心面向事情;作为主体性表征的心体,它的存在也在于它所面向的事情本 身。
如何清楚地阐明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心的体会,本身具有语言难诠之处;另一方面,心面向的事情虽然是具体的,但由此事情反过来表征心体,即由个体性的经验求得普遍性的认识,并不是必然能够实现的。但是无论如何,象山仍然是选择了由心面向的事情的揭明,使人对“心之体”获得真切的理解。最经典的案例便是象山对杨简(1141—1226)的教导。在《象山先生行状》中,杨简追忆道: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简安得而知之?惟简主富阳簿时,摄事临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阳,又获从容侍诲。偶一夕,简发本心之问,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以答,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 不通。
象山门下主要有两部分弟子,一部分是以家乡为主,即槐堂诸儒,象山学派的门庭张大主要靠他们;另一部分便是浙江为主,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象山心学的思想传衍主要靠他们,杨简是甬上四先生之首。杨简小象山两岁,却早象山为进士,象山举进士那年,杨简恰在临安,故得与象山相识,并有所讨教,但真正执弟子礼,则缘于象山回江西经过杨简任职的富阳时所经历的问学,即《行状》所述。这件事情无论对杨简,还是对象山,似乎都非常重要,不仅杨简在《行状》中专门追忆这件事,此前也是经常举此例,而且象山《年谱》中有更详细的记录,此外其他文献,如《宋史·杨简传》 《宋元学案·慈湖学案》中都有述及。实际上,在象山学派内,杨简问学这件事情表征了象山心学的核心思想,即通过心面对的事情而对心体获得确 认。
其实对于这件事,前引《象山先生行状》所述过于简略,并不能完全使局外人明白。前引《行状》,主要是说明杨简本人对此的重视。真正要讨论这件事,还是以《年谱》的记载更为亲切。《年谱》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34岁条 载:
四明杨敬仲时主富阳簿,摄事临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阳,三月二十一日,先生过之,问:“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对曰:“简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凡数问,先生终不易其说,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讼于庭,敬仲断其曲直讫,又问如初。先生曰:“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觉,始北面纳弟子礼。故敬仲每云:“简发本心之问,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答,简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
在这个详尽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杨简数问“如何是本心”,象山总是答以孟子的四端之说。象山的讲学水准非常高,不仅清晰,而且能切人心。朱子任南康守时,曾邀象山至白鹿洞书院讲座,象山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朱子尝以亲身感受对人 曰:
这是子静来南康,熹请说书,却说得这义利分明,是说得好。……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
但他面对杨简的数问,却只是答以孟子的四端之说,而且杨简明确声明,四端之说自己“儿时已晓得”,象山仍不作任何阐释。显然,象山明白,本心之问不是一个语辞可以解决的问 题。
尤其需要指出的,杨简的问题是“如何是本心”?而不是“何为本心”?如果是后者,那么杨简的本心之问更近乎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问题,其解答可以与主体无关;而前者,则与主体密切相关,因为所谓“如何是本心”,预设的追问并不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认识问题,而更是一个主体如何成其为主体的问题,即如何使主体确立起本心。因此,对于饱读了经典的杨简来说,象山任何的阐释都只能是以往知识的重复,不可能真正启动杨简的本心去面对事 情。
海德格尔指出,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使得主体性构成了哲学的坚固基地之后,“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虽然海德格尔的分析是针对着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致使哲学转变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从而使得哲学在展开为科学的意义上走向终结,因此必须重新来思考“思”的任务,完全是在现代语境中的追问;但是对于象山心学的理解仍然具有启发。象山 曰:
古之所谓小人儒者,亦不过依据末节细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许浮论虚说谬悠无根之甚,……终日簸弄经语以自传益,真所谓侮圣言者矣。
在象山看来,“终日簸弄经语以自传益,真所谓侮圣言者”,正仿佛海德格尔所谓的科学对哲学的终结。象山对朱子的不满,根本原因也正在朱子热衷于“终日簸弄经语”,而不务实学。他在给朱子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 出:
尊兄当晓陈同父云:“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气力为汉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今亦欲得尊兄进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学术,省得气力为“无极”二字分疏,亦更脱洒磊落。古人质实,不尚智巧,言论未详,事实先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者,以其事实觉其事实,故事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周道之衰,文貌日胜,事实湮于意见,典训芜于辨说,揣量模写之工,依仿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以子贡之达,又得夫子而师承之,尚不免此多学而识之之见。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无疑。……尊兄之才,未知其与子贡如何?今日之病,则有深于子贡者。
因此,回到杨简的“如何是本心”之问,象山始终没有就孟子的四端之说再作进一步的阐扬,而最终因断扇讼的判决开悟杨简,决不是一种随意的教学权宜之策,而完全是基于他的思想的抉择。象山要使杨简的本心从经文及其繁杂的解释中摆脱出来,让本心直面事情本身,从而本心得以呈现相应的是非判断。杨简由断扇讼的是非曲直判定,进而省悟“此心之无始末”“此心之无所不通”,心之体终于获得确 立。
这个案例表明,如何是本心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需要言语分辩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如何摆脱言语所带来的遮蔽的问题。只有揭去这样的遮蔽,本心才能面向事情本身,本心所具有的四端才能自然展开,作出判断。象山曾就义利问题出一策问,亦可以佐证他的思想。策问 曰:
圣人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凡圣人之所为,无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载尧、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时,禹平水土,稷降播种,为当时首政急务。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有它过,而孟子何遽辟之峻,辩之力?……辟土地,充府库,约与国,战必克,此其为国之利固亦不细,而孟子顾以为民贼,何也?岂儒者之道,将坐视土地之荒芜,府库之空竭,邻国之侵陵,而不为之计,而徒以仁义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为然耶?不然,则孟子之说亦不可以卤莽观,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为无用,仁义为空言。不深究其实,则无用之讥,空言之诮,殆未可以苟 逃也。
历史表明,凡圣人之所为就是为天下谋利,而孟子作义利之辩,仿佛是违背常识,故“世以儒者为无用,仁义为空言”。象山以为,世俗之蔽在于对孟子之说作了“卤莽”理解,只有深究其实,才能消除儒者无用、仁义空言的讥诮;而这个所谓的“实”,便是面向事情本 身。
不过,为什么当面向事情本身时,“如何是本心”的问题就得以解答了呢?当然,可以认为象山对杨简四端之心的回答本身就隐含着答案,因为四端之心内含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自我判明。但是,为什么这一内含着四端之心的本心在必须面向事情时,这样的自我判明才得以呈现呢?由象山对杨简的说明,“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似乎可以推知,当本心面向事情时,事情本身具有着某种道理,足以使得本心所隐含着的是非明辩力作出判明。《语录》曰:
有行古礼于其家,而其父不悦,乃至父子相非不已。遂来请教,先生云:“以礼言之,吾子于行古礼,其名甚正。以实言之,则去古既远,礼文不远,吾子所行,未必尽契古礼,而且先得罪于尊君矣。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如世俗甚不经,裁之可也,其余且可从旧。”
父子发生冲突,盖因儿子固执于死了的古礼,而未能面向事情本身。而象山引导其面向事情本身时,行丧礼之实重在哀而不在礼,就能使人作出合理的调适。换言之,当本心面向事情时,存于事的理与存于人的本心会相合无 间。
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象山心学的格局中,关于心与事的问题,象山是通过使本心面向事情来实现本心的自明与确立的,而理在事中,理与心为一,则是相应的两个基本思想。关于理在事中,《语录》第一条 曰:
“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先生常言 之。
可见这是象山的核心思想。唯此,象山以为,因吾心而人化了的宇宙,无处不是道的呈现,人只有因一己之病才会与道相隔;道总在宇宙中,也总在圣人的活动中。《语录》接着前条,续 曰:
道在宇宙间,何尝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圣贤,只去人病,如何增损得 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虽见到圣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 理。
唐虞之际,道在皋陶;商周之际,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责者,皋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为欲传其道。既为武王陈《洪范》,则居于夷狄,不食周粟。
关于理与心为一,同样讲得极清楚。在与人的书信中,象山 曰:
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如是则为仁,反是则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怵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者,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而逊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
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
可以说,只有明确了道在事中,心与理为一,“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才真正获得了落实,才真正与“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一起,构成为象山心学的格 局。
当然,本心虽然必须在面向事情中获得确立,但心并不能纠缠甚至沉溺于事情中,否则便使心失其“本”。象山 曰: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见得端的后,常涵养,是甚次第。
然而,人心往往适得其反,逐物而难返。象山 曰:
人心只爱去泊着事,教他弃事时,如鹘孙失了树,更无住处。
只是,这已属于象山心学中如何发明本心所必须关心的问题,此处不再延伸开去 了。
四、问题意识与思想谱系
至此,我们足以确信杨国荣在《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的“自序”中所指出的:
中国哲学中“事”这一概念,可以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表述广义的人类活动及其结果,而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则似乎难以发现同样的概念。……“事”这一中国哲学的概念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中国哲学中存在着其他文化传统所缺乏的观念表达形式,这些表达形式有助于推进对世界以及人类生活更为深广的理 解。
换言之,我想指出的是,杨国荣最新的哲学探索表征了他希望从中国哲学的概念形式来推进哲学思考,这当然可以说是他一直来的努力,但《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一书显然呈现得更为充 分。
只是,在充分肯定与彰显杨国荣的哲学探索的同时,许多年来也不免存有内心的疑问:哲学探索的问题意识究竟源于什么?思想新创如何接续学术谱系?这两个问题侧重略有不同,但彼此又具密切关联。前者重在问题意识,后者重在学术接续;问题意识的发生与学术本身的知识呈现有时会存在一定的间隔,或显与隐的区别,但本质上又是具有内在关联的。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曾兴起过创造体系的热情,但终因流于肤浅而消歇;而这种肤浅究其实质,也正是问题意识的苍白与学术谱系的无源。90年代起,学术界渐归趋学术本位,在知识园地上作深入耕耘,结出丰硕成果。近年来,也许是以为90年代以来的知识耕耘已累积到足以有所思想突破,或不甘于知识耕耘的清寂,哲学界似乎又重兴创造体系的热情,使得上述问题再次凸显。前文已述,杨国荣的哲学探索既非起于近几年,更非追步时流,而是已经历年,卓多建树。照理,我不应以上述问题来反思他的最新研究。但是,也许正因为杨国荣的哲学探索具有显著的标杆性,因此,由他的新著来提出上述问题的思考,或许更具意义,同时也是更表达对杨国荣工作的敬 意。
20世纪80年代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宋明理学研究兴起,对于催破固化了的学术研究与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这些研究虽然呈以哲学史的研究,但无疑都富涵着时代的问题意识,同时又具有着学术研究自身的内在动力。但是,当学界将学术研究的兴奋点转向所谓的体系建构时,这些建构的问题意识,以及学术研究自身的内在动力,又究竟是什么呢?我在高度称誉杨国荣的《人与世界:以事观之》后,专辟一节来阐扬象山哲学的相关思想,一方面是为了以古证今,彰显古今哲思的共同性,另一方面也希望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脱离了哲学史的接续,这样的共同性也意味着今人的哲学探索可能流于形式。尤其是众所周知,当象山在阐明他的本心面向事而确立的思想时,他不仅是充满着时代的问题意识,是针对着朱子学知识主义膨胀的现实而展开的,而且象山的思想阐扬始终是接续着孟子思想来进行的,在传承中实现创造,这是思想脉络的连贯,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嫁接。换言之,当我们体会一种真正的哲学创造时,我们总是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创造在现实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的思想脉络两方面的绾合之力,正是这种绾合之力构成了新的哲学创造的内在动 力。
事实上,传统中国哲学如此,现当代哲学也同样如此。请各举中西方哲学一例以见之。先举哈贝马斯为例。哈贝马斯以他的批判理论为标志,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但是,正如研究所表明,哈贝马斯虽然是以批判理论为标志,但他的理论既是对当代德国和欧洲的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并进而引领时代潮流,从而对现实产生深刻的直接影响,又是接续着欧洲哲学的思想谱系而展开的推进。其中,就哈贝马斯对欧洲哲学思想谱系的接续与推进,由于批判理论是他的思想标识,因此容易被置于亚里士多德—斯宾诺沙—马克思的序列中来加以理解;事实上,哈贝马斯也同时接续了詹姆斯—杜威—皮尔斯的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以及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的德国阐释学传统,因而才通过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了他的重建而非历史的方法,向前作出巨大的推进。再举陈来为例。陈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一直以来定位于哲学史研究,但近年来也在哲学体系的创构中有所探索,最显见的便是他的《仁学本体论》。对于此书的具体思想,已溢出本文主题,这里只是指出,陈来提出的仁学本体论最为凸显的问题意识是针对着李泽厚的情本论的,而其学术谱系则可以理解为是对整个孔孟程朱儒学传统的接续;而背后深层的现实回应无疑是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掘发与话语重 建。
以此为参照,杨国荣哲学探索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谱系显得有点隐晦。这并不等于说,杨国荣没有自己相关的阐述。从浅近的角度讲,他曾有意识地梳理过现代中国哲学中的金岳霖—冯契思想脉络,以智慧论为聚焦,从深广的角度讲,他的著作中呈以广谱性的思想对话,不问东西古今。然而,从接受者的立场看,杨国荣的哲学创构更近于哲思的自我展开,论题在这样的自我展开中迁延,方法在这样的自我展开中成熟。不仅难以在学术思想的谱系上把握到他的思想聚焦,更难以体会到他在问题意识上的针对,最主要的收获只能集中在他的思想的自洽性 上。
当然,高度自洽的思想建构同样是哲学家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当我们接受到杨国荣哲学探索的这一特性时,已然是一个巨大的收获。事实上,哲学本身便是以它的独特性而彰显其在整个知识世界中的意义,哲学自身更当以多样性的探索与呈现来表征自己的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的疑问不免有所多余,或近乎苛责。正如前文已述,由于杨国荣的哲学探索及其创造在当代中国诚为标杆,因此从各种角度提出必要的疑问,不仅是对当代中国哲学是有意义的,也是对杨国荣的工作深具敬意的表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