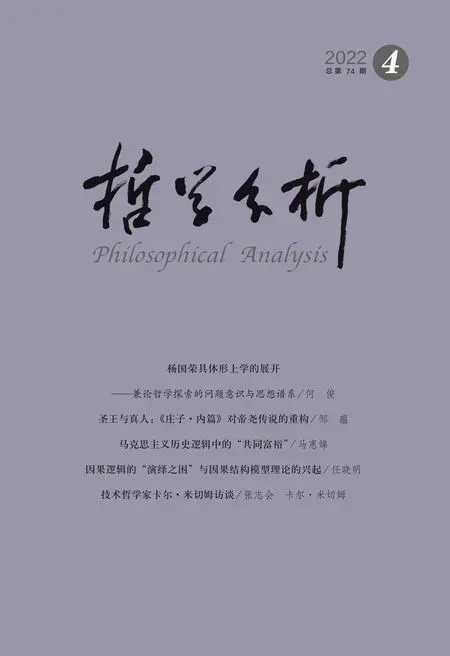圣王与真人:《庄子·内篇》对帝尧传说的重构
邹 蕴
通常来讲,在先秦儒家的思想谱系中,尧舜时代被视作一个至高的圣王时代。作为儒家重要思想来源的《尚书》,其首篇《尧典》以尧的德行和事迹作为后世君王学习的范本。孔子则把尧比作天,以“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赞颂尧的德行高远和功绩卓著。《中庸》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见孔子将尧舜视为圣王理想的源头。孟子更是感慨“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他借助尧舜死后世道的崩坏来反衬尧舜时代的昌明……这些过往的儒者或是基于上古的神话和历史,或是经过重新诠释,都不约而同地把尧舜的时代描绘成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至德之 世。
不过,庄子笔下的尧舜就没有如此光辉灿烂,反倒多了几丝彷徨不宁的气息,尤以内篇中的尧为甚。在《庄子》中,虽然尧舜常常并列出现,但作者对尧的描述和铺展则更多一点。《庄子·内篇》中有五则难以解释的政治寓言都与尧有关,并且尧都是其中的关键人物:第一则是《逍遥游》篇著名的“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第二则同是《逍遥游》篇的“尧见四子”的故事;第三则是《齐物论》篇的“十日并出”章,尧因征伐小国而不释然;第四则是《人间世》篇借助尧、禹攻伐小国的事例来探讨圣人与名、实的关系;第五则是《大宗师》篇“意而子见许由”章中许由对尧的批判。这五则故事的文本语境看似不相关,但实际上都通过“尧”这一人物折射出庄子对圣王理想的深刻认 识。
遗憾的是,庄学界关于《庄子》中尧的形象的解释难有圆满之论。经过笔者整理,相关解释约略分为三种:其一,部分研究打破了《庄子》内外杂篇的分界,无视尧在内篇与外杂篇系统中形象的巨大差异,进而将尧在《庄子》书中出现的篇章和段落同等对待;其二,绝大部分致力于《庄子·内篇》中尧的相关研究都只是以五则寓言中的一两则(尤其是“尧让天下于许由”章和“十日并出”章)作为论述的中心,而鲜少全面剖析上述五则寓言并深入挖掘五则寓言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三,当前的解释方向主要局限于两种,即要么认为庄子否定尧,要么认为庄子推崇尧,二者均未立足于庄子哲学的整体基调,最终没有跳出“誉尧而非桀”的是非论 辩。
鉴于当前研究的这些缺憾,笔者以《庄子》书的思想基础——《庄子·内篇》当中尧的形象——为研究中心,并将与尧相关的五则寓言视作一个相互阐发的整体,在庄子哲学的总体基调中去理解尧在《庄子·内篇》中的深层寓意。此外,《庄子》全书“寓言十九,藉外论之”,这五则故事都是基于上古历史和神话传说改编而成。如果将尧作为线索,并厘清这五则寓言和尧舜传说之间的异同,这将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庄子改编神话传说的用意。如此一来,我们不再拘泥于一两则寓言,而是把五则寓言融通地理解,那么尧在《庄子·内篇》中支离破碎的形象也可能趋向完 整。
通过分析这五则寓言,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则和第二则寓言同出于《逍遥游》,且都关乎对天下的治理,适合放在一起讨论。第三则和第四则寓言都牵涉尧的武力攻伐相关问题,也可以对勘。第五则寓言借助许由对尧的批评引出了“天人关系”这个更根本的问题,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解读关乎庄子对尧的整体态度,因此我们在前四则寓言相互发明的基础上,用第五则寓言来统摄全篇,最后揭示出尧在《庄子》中的整体哲学寓 意。
一、“让天下”——心系天下的治理者
我们先看《逍遥游》中的两则故 事: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 之矣。”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 焉。
尧禅让帝位于舜是尧舜传说中最为核心的情节,也是尧最重要的政治功绩之一。这两则寓言既是对“让天下”传说的改造和深化,也是对儒墨共同称颂的“禅让说”的回应。儒墨两家作为战国诸子中的“显学”,对尧舜禅让之说推崇备至。《墨子》有云:“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唐虞之道》更是竭力颂扬:“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庄子及其后学则对甚嚣尘上的“禅让说”颇为警惕,从第一则寓言中的许由到《让王》篇的子州支父、善卷、石户之农等,《庄子》塑造了一批不受天下之让的“逃王高士”,这个“逃王”群体拒受天下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保身求道,可见《庄子》“剽剥儒墨”的力 度。
先看第一则寓言,庄子把尧禅位的对象由同为圣王的舜换成了隐逸的高士——许由。尧形容许由的德行如日月的普照和雨水的浇灌一般广大,相形之下,自己不过是微小的火把和水流,哪还有资格占据着天子之位?尧于是要把天下让与许由。许由认为天下已经被尧治理好了,尧为治天下之“实”,自己如果接受天子之位,则只配有治天下之“名”。“名者,实之宾也”,许由不会为了求名而失去“鹪鹩巢于深林”的逍遥自在。此处很可能是借助许由暗讽尧好禅让之名,来隐晦地批评与庄子同时的魏惠王,他当时禅让惠子不过是为了窃尧舜之名,却无尧舜之功德。接着,许由道出了更深层次的拒受天下的原因:“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同于尧所代表的方内之圣王,许由在此处代表了方外之隐士,他们之间就如同庖厨和巫祝一样泾渭分明,正所谓《大宗师》所言“外内不相及”。因此,许由走的是方外之路,对治理天下没有任何兴趣,即使尧把天下拱手让与他也没什么意 义。
再看第二则寓言的第一句:宋人到遥远的越国去兜售殷商时期流行的发冠,到了越国才发现河网纵横,越人断发文身,根本不需要戴什么发冠。宋人和尧类似,以为其他人都会稀罕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章甫”和“天下”),结果却发现对方(越人和许由)根本不需要(“无所用之”),也不感兴趣(“予无所用天下 为”)。
我们再回到第一则寓言的对话情境,不难看出,尧在禅让天下之前并不理解许由的立场,只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天下人都会像他一般钟情于天下的治理,殊不知,天下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同理可推,宋人也以为天下人都像他们一样需要束发戴冠,直到进入一个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江湖世界,才意识到还存在另一种生活方 式。
在第一则寓言中,尧虽然谦逊大度,几乎要把自己最重要的天下让位于许由,但归根结蒂尧还是以治天下为意,他仍然关心天下能否在德行最好的人那里得到治理。如果说第一则寓言的许由还让尧心系天下,未能实现逍遥,那到了第二则寓言的第二句,尧所见的人物变成了由四岳转换而来的四子,这些方外神人却让尧忘记了原本重要的“天下之民”和“海内之政”,以至于恍惚间丧其天下。从第一则的“让天下”到第二则的“丧天下”,为何出现了层次上的跨越?我们不妨作出推测:许由和四子虽同为方外之人,却是有境界的高下之分。如果仔细推敲两则寓言,可以发现:四子是沉默的,他们很可能就是第二则寓言前文中“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游》)的神人。通常情况下,《庄子》中的“至德之人是默不作声的”。许由却一直在为自己“一枝及满腹”式的自足辩解,可见其执着于独善其身,未能忘己。并且,《庄子》中拥有至高权力的君主通常在遇到至德之人以后方才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更何况姑射神人的“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逍遥游》)。因此,姑射神山的四子在境界上要高于许由,只有见到四子这样道行高深的神人,才有可能让尧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那对于尧这样在人伦的秩序中已经达到顶峰并且功德圆满的圣王来说,还有什么局限性可言呢?笔者按下不表,我们需要继续释读第三、四则寓言才有可能给出答 案。
二 、“除四罪”——好名求实的攻伐者
第三则寓言出自《齐物论》篇的“十日并出”章,第四则出自《人间世》篇的第一个问对,在这组故事中,尧都以攻伐小国的形象出场,讨论的问题也都关乎“名实之辩”,对勘有助于解释两则寓言中含混不清之 处: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 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
关于第三则寓言舜劝说尧的含义,历来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以郭象(“夫日月虽无私于照,犹有所不及,德则无不得也。而今欲夺蓬艾之愿而伐使从己,于至道岂弘哉!”)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尧的德性遍照万物,又岂能容不下蓬艾小国的存在,故而以舜劝阻尧放弃攻伐来使尧释然;另一种是以朱文熊(“宗脍、胥、敖即共工、欢兜、三苗之转音。尧不释然,故未之除,舜之诛放,亦行所无事也。”)为代表的解释方向,认为舜是从正面论证尧攻伐三国的合理性,让尧心安理得地攻伐三 国。
笔者认为,要廓清第三则寓言的解释方向,不能孤立地看待这几句话,而应当将其放在《庄子·内篇》论及“尧”的整体语境中,尤其要结合第四则寓言中尧的形象来 看。
在第四则寓言中,尧和禹这些人间世的圣王以“攻丛、枝、胥敖、有扈”这类蓬艾小国的形象出场,并且在“用并不止,求实不已”的过程中导致“国为虚厉,身为刑戮”的惨况。庄子称这些圣王为“皆求名实者”,也就是既好名,也求实之人。“名”和“实”是《人间世》开篇第一个问对中出现的一组概念,“名”可理解为价值理想,“实”即是对这套理想的实现。孔子正是在教育颜回放弃出使卫国的过程中,插入了关于“好名”者和“求实”者的论述。庄子借孔子之口以比干、关龙逢的悲惨遭遇警示颜回,劝他不要再做“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的好名者,这是以自身的贤德反衬出君主的恶劣,最后反倒招致君主的猜忌和杀害。孔子以“好名者”的故事影射执意要去劝说卫君的颜回,“好名”,指的是颜回不顾身份的卑微和处境的艰险执着地要向暴君进谏的决心(“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如果说比干、关龙逢乃至颜回代表的是徒有理想却没有能力“求实”的有德无位者,那么尧、禹这些圣君代表的就是能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的有德有位者,所以他们是“皆求名实者”。通常情况下,君主总是先有“名”(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再去“求实”。既然第四则寓言讲的是尧的“求实不已”,那么第三则寓言就可被顺理成章地解释成尧的“好 名”。
我们回到第三则寓言,就能用前文所总结的第二种方向来解释,舜用“十日并出”的譬喻一针见血地戳中了尧灵魂深处的“好名”之心:既然尧的德性比十个太阳的光芒还要广大无边,那处于蓬艾之间的卑弱小国又岂能一直处在蒙昧落后的状态,尧有什么理由不去教化它们呢?因此,在舜的点醒下,尧由攻伐三国产生的不释然之心就转化为匡扶天下的决 心。
如此解释,舜的劝说不仅给尧的武力攻伐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从而和第四则寓言中尧“求实不已”的坚定形象贯通起来,而且也符合《庄子》中舜比尧“更倾向于武力征伐”的形 象。
通过第三则和第四则寓言的互证,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这番人间世的普遍境况:忠厚贤良如关龙逢、比干亦不能逃离“名”所设下的陷阱,他们舍生忘死追求“名”所代表的政治秩序,最终为“名”所害;尧和禹这样千古一遇的圣王也是在“名”的驱使下,无休无止地征服天下,让天下苍生“国为虚厉、身为刑戮”,终究无法避免生灵涂炭、不得安宁的悲剧。因此,庄子不无严厉地反复强调:“名”是人间世的凶器,它让人的欲望不停激荡、人的德性不断贬损,以至于让人“行名失己……亡身不真……役人之役,适人之适”(《大宗师》)。所以,“名”不是根本的可取之道(“非所以尽行 也”)。
然而,“名”和“实”却是构成政治生活的必要因素。政治秩序的实现总是先由掌权者的政治热情开启,再依凭一系列的名目、礼法、制度来完成,这个过程就是由好名之心的撄动逐渐被强化为对现实的不停追逐,也就是有心朝着“名”这个目标不断进于“实”的过 程。
即使是尧这样象征治世典范的圣王也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步骤完成了由“名”进于“实”的人伦秩序的建构。尧的政治德行以及他“‘由个人至天下’的实践步骤构成了后世儒家实践论的标准程序”,可见累世之圣贤都是以“皆求名实者”为终极目 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古历史和神话传说中,尧总体上都被叙述为人文秩序的缔造者,却较少以武力攻伐的形象出场,而庄子在第三、四则寓言中却塑造了尧暴力刑戮的形象,这种形象源头何在?如果我们放眼典籍中尧舜之于周边少数族裔的举措,就会发现存在一个“除四罪”(共工、欢兜、三苗、鲧)的情节单 元: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孟子·万章上》
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荀子》
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大戴礼记·五帝德》
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
这四段引文或是将“除四罪”归于舜(《尚书》 《孟子》),或是将其归于尧的行为(《大戴礼记》),或是归于尧舜共同的行为(《荀子》 《史记》), 主体的含糊不清是神话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很常见的一个特征,但不论其归属者是谁,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尧舜传说中很早就存在“除四罪”这样一个母题,而历代典籍对于“除四罪”不同版本的叙事可被看作一个母题的异型。《庄子》也不例外,作者通过叙述尧之攻伐三国把尧舜“除四罪”这个神话母题改造成了尧之除三罪:《齐物论》篇中尧“伐宗即放驩兜,伐脍者,流共工也,伐胥敖者,投三苗也”,《人间世》篇中尧攻“丛、枝、胥敖即宗、脍、胥敖也”,这种把“鲧”排除出去的尧之除三罪模式一直延续到《在宥》篇中所说的“尧于是放欢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 夫”。
综上分析,《庄子》使用“藉外论之”的寓言把尧改造成不断征服天下的攻伐主体,“求名实者”的圣王特征在尧的身上得以凝结。尧形象的重构让我们明白:“即便人间政治达到最高的可能,依旧固有其本身的限度”,这也正回应了第一和第二则寓言中尧的局限性在何处——尽管让天下于许由这个行为表明,尧不再以“治天下”之名自居,但他还是关心天下的治理,仍旧执着于理想的政治秩序(名)能否借一个更高明的治理者(许由)来实现(实),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尧还是好名求实的。只不过,尧作为方内的治世典范,他需要通过方外的神人(四子)才有可能意识到其政治的局限性(窅然丧其天 下)。
三、“单均刑法”——施行礼法的教化者
如果说,前四则寓言是围绕“名”和“实”勾勒出了尧治理天下的整体图景,那么第五则寓言则是以“躬服仁义”“明言是非”提炼出尧之治理的具体方式。和第一则寓言类似的是,在第五则寓言中,尧和许由也是以立场相互冲突的一对人物而出现,不过尧这次是间接地出场,借由意而子和许由来转述他的教化方 法: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许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意而子曰:“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捶之间耳。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许由曰:“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大宗 师》)
尧在此则寓言中被许由形容成一位“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的治世君王,由“黥”(墨刑)和“劓”(割鼻子)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尧舜时期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尧和刑罚的联系古来有之:春秋时期以“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来概括尧的功绩主要在刑罚领域;根据《尚书·尧典》中“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尧舜时期的刑罚体系已经相当完备;“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大法官皋陶正是从尧时期开始掌握断狱和司法大权,并且神话传说记载他有一只能够公正裁断人事纠纷的神兽——獬豸。以上这些记述都说明很早就存在尧、舜、皋陶立法执法这样一种叙述母题,后世的作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个母题进行了各式改造,庄子则运用尧和刑罚之间的种种联系把尧塑造成用礼法度数治理子民(“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的君 主。
理清尧的象征意味就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则寓言,即:意而子拜访许由,希望许由能教授自己一些本领,但很快就遭到了许由的嫌弃,理由是尧已经用“仁义”和“是非”这些人为的标准把意而子自然朴素的面貌改造(黥、劓)得面目全非,意而子已经远离大道、往而不返了。换言之,许由把意而子当前的面貌看作一种已完成的、不可逆转的状态。面对许由的质疑,意而子的回答是“吾愿游于其藩”,“藩”的意思是“边界”。这句话说的是,意而子不以“方之内”或“方之外”的范围限制住自己,虽然“躬服仁义”是对自然面貌的消解,但尧所传授的人文教化却也不是终极的状态,没有必要因此停滞不 前。
接下来,意而子举无庄、据梁、黄帝的事例劝服许由,同时勉励自己: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炉锤之间”的工夫去掉教化所带来的负面损害(“失其美”“失其力”“亡其知”),也就是通过进一步的修炼回返到天机自然的境界(“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不同于许由的质疑(“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所暗含的“自然—教化”的单向进程,意而子的回复则展现了一种“自然—教化—自然”的循环进程。这种回环往复的观念贯穿于《庄子》全书:《逍遥游》中的“鲲化鹏”故事展现了“一个从‘道’之整全到‘道’之分离再回归于‘道’的环形过程”;《大宗师》中的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显示出生死相续的循环流动;《寓言》篇在解释卮言时提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可见万物流变的循环;《至乐》篇则描述了一个“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的物物相生的链条……所以《庄子》认为,从“道”的运动到生命的链条都呈现出一种回环往复、旋转不息的结构,意而子的立场正与这种循环论相符合,且超越了许由所代表的单向静态结 构。
《应帝王》篇最后一个“浑沌”的故事,可以和这则寓言形成互证。在《应帝王》的结尾,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恩情,将其日凿一窍,七天之后,浑沌被凿七窍而死。浑沌的神话原型很可能出自《山海经》中的神鸟帝江,此怪兽面目模糊,没有七窍。在庄子的改写下,倏忽二帝自作主张地把帝江质朴浑成的面貌破坏得支离破碎,这种破坏(“凿”)与尧对意而子的损伤(“黥、劓”)非常相似,二者都是人为地改造浑然天成的自然状态。尽管《应帝王》篇乃至《庄子》内七篇以“浑沌之死”作结尾,但结合《庄子》的循环论,死亡并不是终点,只不过是 “永恒生命”中的一个节点。“七是循环数字之极,七日浑沌死,但七日也来復”,浑沌经历了死亡,也会迎来新生。浑沌之死、尧对意而子的改造、意而子有修复教化之伤的可能,这些情节都暗示着在“道”循环往复的运动中,死亡(除旧)和新生都是必不可少的环 节。
面对意而子与时俱化的态度和工夫修炼的决心,许由原本嗤之以鼻的语气也缓和了许多——从先前认为意而子完全不可能学道,转换到一种开放的态度(“未可知也”);从开始拒收意而子入门(“而奚来为轵”),到最后愿意为意而子讲述大道的核心精神(“我为汝言其大略”)。通观这则寓言的整体基调,意而子尽管承认了尧对自然的破坏(“虽然”),却不认为尧的教化是对自己修道的阻碍;意而子虽然不认同许由所主张的线性时间观,但虚心向许由求教。意而子对尧和许由双方观念的超越,再次证明了在此则寓言中,他才是庄子的代言人(“两忘而化 其 道”)。
借由意而子的言行,我们看到,庄子并没有否定尧和许由的任何一方——尧所代表的“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的教化之路和许由所推崇的“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的自然之路都在“道”的循环流转中得以保证。如果说许由之路代表的是“天”(方外),尧之路代表的是“人”(方内),那么意而子在“天”与“人”之间婉转流变的态度则指向了《大宗师》开篇所阐发的宗旨——“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何谓“真人”?下一节将作具体的阐 述。
四、圣王·神人·真人
在《庄子》书中,“真人”一词首次且集中地出现于《大宗师》篇(但真人的形象在《大宗师》之前出场过)。《大宗师》著名的“真人四解”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古之真人游走于方内和方外之际的自由图景:“真人一解”(“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讲述的是真人安之若命、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真人二解”(“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则通过真人的作息、饮食、呼吸等身体状态的刻画揭示了一种“本真的生活方式”;“真人三解”(“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展现了真人道通为一、随任大化周流的自适面貌;“真人四解”(“其状义而不朋……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以真人的体相和形貌特征为中心来揭示真人处理天人关系的智慧。通过这“四解”,我们可以看到,真人既进入了高妙超然的齐物境界,又不与人间尘世相脱离,这正合于意而子的志向——“吾愿游于其 藩”。
回顾第一节的论述可知,除了“真人”这种人格范式,庄子还讨论过“神人”。和真人类似的是,《逍遥游》中所描述的神人也是得道之人(“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只不过神人向来居于方外(“游乎四海之外”),不与方内世界打交道(“孰肯以物为事”)。这也难怪《庄子》中的神人不直接出场,而是出现在接舆、连叔、南伯子綦等人的传奇叙述中。这些神人或是居于远离人间、纤尘未染的姑射山上,或是化身为荒郊野外、可结驷千乘的不材之木——“神人以此不材”(《人间世》),或是与习俗观念所认定的不祥之物——“牛之白颡……豚之亢鼻……人有痔病”(《人间世》)——享有共同的价值。神人的事例和“尧见四子”的寓言一样,都开启了一个与人伦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外世界,同时开启的是与方内价值(有用、天下、材、祥)相对立的方外价值(无用、丧天下、不材、不祥)。换言之,神人崇尚的价值在世俗世界一文不值,而人伦社会所唾弃的无用之物在方外世界反倒被奉为至宝。结合前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尧作为有德有位的圣王可谓是方内价值的集大成者,而神人则是方外价值的典范,可见圣王与神人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人格范式。与此同时,在庄子的笔下,尧一生汲汲于天下秩序的建构而不知停歇,直到遇见以四子为代表的神人,竟舍弃自己毕生追求的价值理想。这说明神人在得道的程度上高于圣王,让圣王意识到自己在德性上的亏损,并向往另一个全生全德的方外世 界。
方内与方外、有用与无用的对立在圣王和神人两种人格的呈现中表露无遗,直到真人的出场才消解了二者的冲突。尽管同是得道中人,但真人不同于神人的地方在于,真人并不纯然栖息在方外之地,而是与世俗世界存在自然的联系。例如:《德充符》篇的哀骀它不受死生、存亡、穷达、贫富的影响,是一个臻于至德之境的人,同时他还能随遇而安、与物为春,甚至让身边的男女长幼都被他感化;《大宗师》篇的孟孙才也是真人人格的具体显现,他虽已齐同生死,但并不贬低丧礼,他为母亲居丧期间依然“人哭亦哭”、随缘自适;在紧随其后的“意而子见许由”寓言中,意而子也秉持着同样的处世观,他虽然向往许由所师法的神人之道,却并不对尧的礼法教化持以鄙薄的态度,而是平和地面对神人(“天”)和圣王(“人”)的差异。真人之所以能等量对待方内与方外,在于他以“道通为一”的视角看待宇宙万物,即方内世界和方外世界在“道”的观照下,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别。相较之下,神人的眼光却充斥着对方内世界居高临下的评判,“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逍遥游》),这分明是一种不屑一顾的孤傲,正如神人的代言人许由对圣王的教育嗤之以鼻一样,这些不都是庄子竭力批评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吗?显然,神人还未抵达“莫若以明”的境界,可见其修道的境地尚不如真人圆满。《天下》篇对庄子思想的概括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正是对真人不即不离风貌的写照,所以真人才是庄子最崇尚的理想 人 格。
理解了庄子的真人观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冷静地看待两类理解《庄子》思想的传统观点:一类是以郭象为代表的“游外冥内”说,也就是在方内适性而为才能实现充分的自由,隐逸于方外反而不能“实现性分所具的社会性潜能……难以真正实现自身的适性逍遥”,在这种观点的统领下,就会得出:尧这样充分实现社会性潜能之圣王正是逍遥游的典范,因为他以无为而治的方式保证了自己和天下秩序的自由;另一类是以荀子、司马迁等人为代表的虚无避世说,持这类说法者大体都认为庄子学说“蔽于天而不知人”,即倡导人们过一种远离尘世的隐逸生活,甚至由此延伸出庄子“坏法乱伦……欲天下而不理……欲绝圣贤,使天下各止其知”的“废庄说”,换言之,这种立场包含着一种认识,即尧作为仁义礼乐观念的代表被庄子所弃绝。前一种观点认为庄子主张方内才能实现自由,这样就导向对尧形象的推崇;后一种则认为庄子要归于方外的虚无之境,从而引出对尧作为方内圣王的否 定。
显然,上述两类观点都不符合《庄子》的真人观,真人既达到了玄同万物的廖天一之境,又不与世俗社会相脱离,故而能在方内和方外“两行”其道,而不是二者择其一。这样一来,庄子对尧的整体态度也渐趋明朗——虽然庄子借助尧的圣王形象揭示了人伦世界的不完满,但这样揭示的目的并不是将方内生活予以否弃,而是导向对整全之道的求索,同时,这个道与世俗生活不相分 离。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运用庄子的循环论和真人观来回应开篇提出的问题:不同于先秦儒家对尧的称颂,庄子诚然没有建构起一个光辉灿烂的尧形象,而是运用诸多神话传说重构了尧的圣王形象。值得强调的是,庄子重构圣王的目的不在于解构人伦生活的价值,而是让我们认清方内世界的局限,从而牵引出更为博大的“道”的本体论。换言之,庄子在批评尧的同时,并不纯然否定尧,而是正视尧在道的流转中的合理性。真人尽管是比圣王和神人更为理想的人格范式,然而真人在方内与方外游走的形态也印证了,庄子之意并非取消圣王和神人,而是要接纳和衔接两个世 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