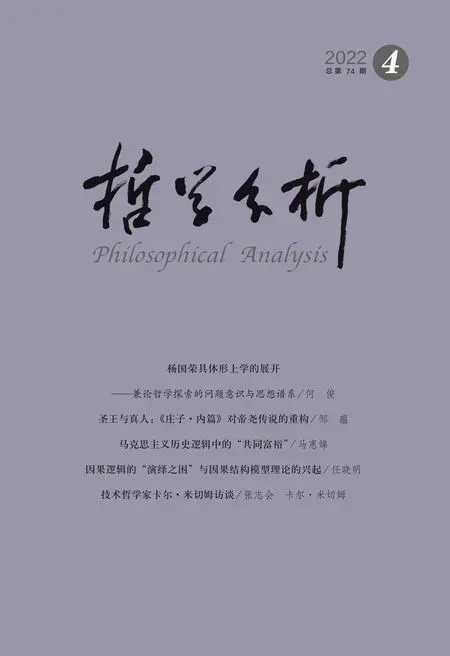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访谈①
张志会 卡尔·米切姆
一、从哲学与技术学会到哲学、工程和技术论坛
(以下简称“张”):您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作为我在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我想对您进行一次采访,以增进中国学术界对您的了解。
(以下简称“米切姆”):一直以来很高兴了解你和你的工作,特别是你关于三峡工程的研究。我很荣幸接受你的采 访。
:您的教育经历是怎样的?
:我的学术生涯非同寻常。我的学习经历前后共三十年,大学学习跨越的年度远远超出了常人,之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了哲学和文科研究的双学士学位,并在那里继续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几年后在纽约市的一所耶稣会学校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我博士毕业时已经和老友罗伯特·麦基(Robert Mackey)编辑了《哲学与技术》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1972年)。后来,在身为布鲁克林理工大学(后更名为纽约大学工学院)校长的土木工程师、工程师哲学家乔治·布利亚雷洛(George Bugliarello)的襄助下,我成为该校终身教授。
1978年,也就是哲学与技术学会(SPT)成立的那一年,您当选了第一任会长,后来您又担任学会期刊《哲学与技术研究》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的副主编。这是技术哲学制度化的重要一步。您是怎么参与的?
保罗·杜宾(Paul Durbin)是创建SPT的重要推动力。在我们通信的过程中,杜宾想出了召开会议的主意。他邀请我帮助组织1975年在特拉华大学召开的第一届美国哲学技术会议。我邀请了几个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尔伯特·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n)。
您也参加了工程和技术哲学论坛(fPET)的建立吗?它与SPT有何不同?
我参与了fPET和SPT,但fPET的建立必须归功于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的非裔美国机械工程教授塔夫特布鲁姆(Taft Broome)。布鲁姆相信工程师和工程学在技术哲学界过于边缘化,工程哲学是有必要的,是帮助工程师了解自己的一种方法。工程师出身的布利亚雷洛在1973年组织了一次技术哲学会议,哲学家杜宾在1975年组织了一次哲学家参加的技术哲学会议,其贡献者几乎没有重叠,这一事实反映了这两个团体和利益之间的分离。
那么SPT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可能是1977年,至少是非正式的。通过一个类似的特别投票过程,我被推选为SPT的第一任主席。1980年的一个晚上,科学哲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以技术史学会(SHOT)和科学哲学协会(PSA)的章程为范本,起草了SPT学会章程。新的细则规定任期为两年。与此同时,布利亚雷洛在从芝加哥搬到布鲁克林理工大学担任校长后,把我带到这个大学,帮助他建立一个新的哲学和技术研究中心。这为1983年在那里组织第二次SPT国际正式会议提供了一个平台。
布鲁姆最终得到了美国国家工程院的支持,成立了一个小型工作组,并于200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组织了一次哲学与工程研讨会,10至15位学者受邀参会,我是其中之一。同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举行的SPT的2007年工程哲学特别会议上,我们中的一些人提议将WPE与SPT合并。然而,布鲁姆强烈感觉到需要有工程方面的独立性,次年,伦敦皇家工程学院主办了第二届WPE(2008年)。
2008年WPE大会决定,对fPET进行适度调整,决定每隔一年在偶数年举行一次会议,作为对在奇数年举行的SPT会议的补充。2010年,我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主持了第一次fPET会议。李伯聪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北京主办了2012年国际fPET会议。
二、从哲学到技术伦理学
您更喜欢“哲学和技术”还是“技术哲学”?
我和罗伯特·麦基写的两本关于技术哲学的书到已有50年的历史了,我认为哲学和技术研究是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领域的主要贡献。当时STS通常被认为是历史、哲学和科学技术社会学的一种互动或跨学科的结合。
我更喜欢“哲学和技术”而不是“技术哲学”。我不同意唐·伊德(Don Ihde)和约瑟夫·皮特(Joseph Pitt)关于这一点的看法,而更强调哲学需要在更平等的基础上与技术合作。当时,政治哲学和伦理问题是与技术有关的最突出的哲学问题。在1998年的专题讨论会上,我又一次介绍了技术与政治以及公众参与技术科学决策的必要性。在这个话题上我的观点不断演变——特别是在一个公众参与已成为反对欣赏专业知识的武器的社会里。
您如何看待伦理、政治和更普遍的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
技术哲学带来了逻辑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伦理的和政治的哲学问题,影响了人工制品的制造和使用。这些问题之间的特殊平衡在哲学的相关区域内会有所不同,例如科学哲学或艺术哲学。因此,任何对技术的哲学评价,都部分地由它自身与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平衡来定义。
这实际上反映在我20世纪70年代的两本关于哲学和技术的书中。1972年和1973年的两本书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伦理和政治批判”,但这两卷也包括关于概念分析、认识论、宗教观点和形而上学的部分和文章。我认为,即使是在强调社会关注所驱动的伦理时,哲学和技术研究也必须让哲学的其他分支承担起责任。
所以对您来说,技术伦理只是技术哲学最突出的方面,反映了技术作为社会问题的突出性。
对。这也有助于将技术的伦理讨论置于20世纪70年代哲学“应用转向”的背景下。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哲学家开始对尝试将哲学应用于任何有争议的社会问题感兴趣。尽管这一运动通常被称为哲学中的“应用转向”。《当代哲学中的应用转向》 (The Applied Turn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1983)提供了一种关于转向的概述,但应用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伦理学。虽然原则上应用哲学包括应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但实际上公共政策和伦理问题是前沿和中心问题。《哲学与公共事务杂志》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2年创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正义战争、堕胎和刑事处罚的问题是早期问题的重复主题。即使在1984年出版的《应用哲学杂志》上,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也比本体论、认识论或美学更为突出。
然而,在应用伦理学的这些发展中,人们未能认识到许多这样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经历了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突变。核武器和其他先进技术武器的制造,扩大了战争何时合理的问题。随着公共卫生和医学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开始询问有关节育的问题。先进的救生医疗技术激发了人们有关对如何定义死亡的疑问。在标准应用伦理学中,许多问题的技术层面并不总是得到充分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末起,您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关于伦理与技术(1989年)、军事科技研究有关的伦理问题(1989年),以及关于世界工程伦理(1992年)的著作,您还发表了关于计算机伦理和生物医学伦理的文章,出版了有关工程伦理的合著(2000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您编辑了四卷本的科学、技术和伦理百科全书(2005年),并获得了国际世界技术网络(WTN)伦理奖(2006年)。
我对所有这些论题的兴趣是试图揭示当今道德和政治与技术的结合方式。1996年,我和伦纳德·沃克斯(Leonard Waks)合著了一篇文章,对这一普遍观点进行了论证。文章首先指出,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善后》 (After Defect,1981)一书中,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当代哲学界对核武器、堕胎和医疗保健的反思的不足,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新的伦理挑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科学进步带来的变革技术。我所出版的《技术中的思考伦理》 (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 1997)一书也试图提出同样的观点。
三、技术哲学的政策转向
现在我们来谈谈您所说的技术哲学的“政策转向”。您在2012年北京的fPET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工程政策的演讲,试图扩展科学政策的概念。后来的会议上又多次提到这一话题。
:我对“政策转向”一词的使用源于与罗伯特·弗罗德曼(Robert Frodeman)的合作,2001—2002年他担任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客座教授。他曾在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并担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的教员。我们讨论了“政策”的概念,以及它与“道德”和“政治”的区别。
“政策”是一个奇怪的词,也是一种模糊的现象,我从20世纪90年代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伊万·伊利奇共事时起就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伊利奇认为这只是“uniquack”的另一个例子,并称之为“阿米巴词”,改编了他的朋友乌韦·波克森(Uwe Poerksen)关于“塑料词”的概念(2004年)。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否定的,我与弗罗德曼的合作促成了《今日哲学》杂志的一期主题为“走向科学政策哲学:方法与问题”(Toward a Philosophy of Science Policy: Approaches and Issues, 2004)的专刊。此前一年,我和弗罗德曼与科学政策研究者罗杰·皮尔克合著了一篇关于“人文政策”的短文。
那您对“政策”的意义有什么看法?
:对于皮尔克,一位科学政策领域的领军学者和实践者来说,政策只是一个决定——不多不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描述。事实上,我们可以谈论“政策决定”而不是经济、政治或道德决定,这表明政策是与之不同的。
科学政策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为了政策的科学(science for policy)和为了科学的政策(policy for science)。这一区别通常归功于科学政策顾问哈维·布鲁克斯(Harvey Brook)。前一类型将科学应用于政治决策,以便将政治转化为政策,以科学评估取代决策或直觉。例如,想要提供安全饮用水的政府需要利用科学研究来提供有关污染物水平的知识,并设计有效的净化不纯水的工艺。后一类型寻求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次)为科学的支持和治理建立指导方针。一个政府应该在科研上投入多少资金,如何最有效地投入?应利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建立科学对政策对科学的反馈循环。
现在,在对科学政策的描述中可以注意两件事。第一,它与工程和科学一样重要。医学和安全饮用水系统的设计都是工程的形式,甚至比科学还要多。第二,政策在为行动提供指导方面与道德相辅相成。伦理学关注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政策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扮演特殊角色的群体或个人提供了更为普遍的指导。保险单并不是靠猜测或个人保险代理人的个人喜好来写合同,而是根据统计分析来指定合同的参数。医生有道德义务不伤害他人,但是,对于什么是危害,需要至少部分建立在对各种治疗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像我们这样的世界里,科技创新可能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危害。
简言之,在工程技术领域,仅靠伦理道德是不够的。工程设计和技术使用中的道德行为准则需要建立在结果论、道义论或美德伦理推理的基础之上。道德推理需要得到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所说的政策科学的补充。
弗罗德曼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仅仅从技术伦理的角度来思考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单个工程师和技术使用者的责任。任何技术伦理本身都将趋于软弱——如果不是无能的话。道德应当得到政策的补充。
那么政策转向是伦理学应用转向的另一个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是。但伦理学的应用转向往往仍然集中在个人责任上。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1982年的著名文章《医学如何拯救伦理学的生命》 (“How Medicine Save the Life of Ethics”)认为,高科技医学的伦理难题将伦理学从语言分析的云雾中带出来,处理临床中的实质性问题。然而,应用伦理分析往往与个别病例和患者相关。仅凭偶然性是不够的。生物医学伦理需要补充制定生物医学伦理政策,并最终通过法律。埃里克·费舍尔(Erik Fisher)的一篇文章试图对这个话题进行更多的思考,至少是描述性的思考。
我还要指出,政策转向的概念在环境伦理学和哲学中发挥了作用。让我引用弗罗德曼的话:“环境哲学的政策转向意味着从哲学家为其他哲学家撰写哲学论文,转向进行跨学科研究,并与公共机构、政策制定者和私营部门合作开展项目。尽管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些步骤,但在环境哲学家群体中,政策转向基本上仍未实现。完成这一转变有助于更好的决策,有助于在哲学和政策的交叉点上发现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并为哲学毕业生找到新的就业前景。”
有趣的是,2006年在帕萨迪纳举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学会(4S)年会上,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一个关于实验室研究的小组会议上呼吁增加与政策相关的STS研究。
在我看来,实验室研究的问题在于它们不是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他们把STS分析和哲学带进实验室,但只带着自己的STS分析和哲学问题。这是一个片面或单向的交叉学科。在一个更强大的双向交叉学科中,哲学将受到与其相互作用的科学或技术的更深刻的挑 战。
随后,弗罗德曼和他的同事用“场域哲学”这个词来命名我认为的政策转向的另一个方面。在同一次会议上,我与弗罗德曼一起提议召开一次小组会议,主题是“跨学科领域的实地实验:新方向:科学、人文、政策”,明确将两者联系起来。
您说的“后工程”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工程师在关注职业道德时,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已经参与政策之中,因为他们对将所有责任都交给工程师个人的道德规范表示不满,并且没有考虑到工程实践的社会背景。为了提出工程伦理学教学的认证要求,并试图为那些作出与企业或政府雇主不一致的伦理判断的工程师提供专业的组织支持。认证要求是一种政策,旨在建立在良好工程实践所需的经验知识和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工程教育研究的整个领域都试图取代关于如何最好地教授工程的直觉,包括教授工程伦理学。
在讲英语的美国工程环境中,职业道德重要性的增强意味着一种新的工程形式,我称之为“后工程”。这“意味着”既有趣又刺激。讲古典英语的工程学并没有让伦理学在这个职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只是假设工程是好的,总是好的。随着伦理学成为工程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也是有争议的因素,一种新的工程形式正在出现。“元工程”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术语。
基本观点是,随着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工程化,越来越依赖工程,工程不再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接管了一切。麻省理工学院前本科教育系主任罗莎琳德·威廉姆斯(Rosalind Williams)的一段有见地的回忆描述了工程的“扩展性解体”:“在工程正在消失的意义上,不存在‘工程的终结’。如果有,类似工程的活动正在扩大。正在消失的是,工程作为一种连贯和独立的职业,其定义是与工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与物质世界以及与功能性等指导原则的良好关系。工程学诞生于这样一个世界——它的使命是控制非人类的本性,而这一使命是由强大的机构权威所定义的。现在它存在于一个混合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自主的、非人类的本性和人类产生的过程之间不再有明确的界限。”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工程和非工程之间也不再有任何明确的界限。工程就像现代性一样,已经超越了自身,进入了后现代或元现代的状态。
四、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您对应用转向和政策的论述自然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怎么办?这些其他的“转向”和经验转向之间有关系吗?
:我想是有的,但经验转向的支持者可能不同意。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是作为变革论据的一部分而构建的。它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我说这不是批评,只是想认识到,在某些方面,这既是一种修辞,也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凝聚文化资本的努力。对于“应用转向”和“政策转向”这两个术语也可以这样说。
“经验转向”一词多义并不总是被人们所欣赏。正如您所知,它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荷兰哲学家——特别是特温特大学的汉斯·阿赫特胡伊斯(Hans Achterhuis)和图代尔夫特大学的彼得·克罗斯(Peter Kroes),他们的兴趣略有不同。碰巧的是,我在1998年春天去了荷兰,拜访了蒂尔堡大学的勒内·冯·肖伯格(René von Schomberg)、特温特大学的阿赫特胡伊斯、代尔夫特大学的克罗斯。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我所认为的“双重经验转折”。
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1998年4月在德尔夫特大学举行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研讨会”的标题中。克罗斯在他的纲领性介绍中指出,由于技术哲学一直是无效的,它需要经历三个方面的重新定位:(1)从用户阶段到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2)从全局分析到局部分析;(3)使用实证案例研究。克罗斯和安托妮·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编辑了该研讨会的会议记录卷,并作为哲学和技术研究的主题期刊出版(2000年第20卷)。这卷的第四部分是关于“伦理学和经验转向”,包括“工程师的伦理学:从职业角色责任到公共共同责任”,这是我与冯肖伯格(von Schomberg)合著的。那篇文章是应用伦理学的一种实践,尽管我们没有这样称呼它。
为了强调他的观点,阿赫特胡伊斯区分了芒福德、海德格尔、约纳斯、艾吕尔、阿伦特和伊利奇(Ivan Illich)等人所谓的“经典技术哲学”,他们的想法“更多地被使现代技术成为可能的历史和先验条件所占据,而不是被伴随着技术文化发展的真正变化所占据”。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技术表现自身的多种方式”。阿赫特胡伊斯因此对古典哲学家的成就和他们的发现表示赞赏,即技术不仅仅是应用科学,更是一种生命形式,一种“系统”(艾吕尔)或“巨型机器”(芒福德)。他认为,“把这看作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激进的转折点,这是经典技术哲学的伟大功 绩”。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克罗斯—梅耶斯和阿赫特胡伊斯的著作,只有一个共同的贡献者——来自特温特的菲利普·布雷(Philip Brey),他与工程师克莱夫·戴姆(Clive Dym)合著了一本关于克罗斯—梅耶斯的工程设计语言的研究,并单独撰写了一本关于休伯特·德雷弗斯的阿赫特胡伊斯研究。在阿赫特胡伊斯描述的哲学家中,没有一个在克罗斯那里得到重要的对待。很明显,这里有两个经验转折点。
然而,阿赫特胡伊斯提出的已经发生了的三个特征,作为经验转向的关键,事实上与克罗斯的三个方案建议中的两个相呼应。阿赫特胡伊斯将美国的技术哲学家描述为:(1)打开了人工制品社会结构的黑箱(“克罗斯1号”的另一个版本);(2)不看技术的吹捧,而是看技术的多样性(类似于“克罗斯2号”);(3)欣赏技术和社会的共同进化。阿赫特胡伊斯的第三个关键特征实际上似乎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的成就有一些共同之 处。
:您认为克罗斯和梅耶斯的经验转向和阿赫特胡伊斯的经验转向不一样,阿赫特胡伊斯更欣赏经典技术哲 学。
没错。另在1998年的同一个春天,在荷兰语版的经验转向书出版后,他与他的老朋友伊万·伊利奇就如何在全新的科技人类环境中生活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客厅对话”。我要说的是,阿赫特胡伊斯与克罗斯不同,他并没有简单地背离经典哲学,而是想补充经典哲学。
同时,我也不完全同意阿赫特胡伊斯对经典技术哲学和经验转向的描述。例如,经典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就机械钟等细节如何体现现代技术作了大量的研究。经验转向哲学家鲍尔格曼不仅思考特定的技术,而且试图阐明贯穿整个现代技术的“设备范式”。此外,我认为,将前经验转向哲学家解释为专注于“先验条件”是不够的。艾吕尔和伊利奇,至少,如果不是更关注现代技术的文化后果,也同样关注任何先验的前提条件。
:关于阿赫特胡伊斯和特温特大学,我想知道那里的教授彼得—保罗·韦贝克(Peter-Paul Verbeek)的技术哲学和他在中国越来越知名的调解理论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韦贝克实际上在技术哲学方面建立了另一个荷兰学派。韦贝克在阿赫特胡伊斯攻读博士学位,尽管此后他与伊德在促进后现象学项目方面进行了更密切的合作。韦贝克的《事情是怎么做的》 (2005年)一书借鉴了阿赫特胡伊斯对经典技术哲学的描述,详细地批判了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工作,为他的调解理论奠定了基础。然后,正如您所注意到的,他为他所谓的技术中介理论作了一个纲领性的论证。在这方面,他做了一些有趣的研究,但我还是认为“调解”更像是一个修辞品牌,而不是一个全新的思维轨迹。在伊德的领导下,技术哲学的后现象学无疑是在蓬勃发展。
代尔夫特经验主义转向学派承认特温特经验主义转向学派吗?
在某种程度上。特温特对“经验转向”的使用与代尔夫特经验转向的编程方式不同。当韦贝克提出研究计划时,他要么与伊德的后现象学(工具化而非意向性的现象学)结盟,要么与他自己的术语“中介理论”结盟。正如代尔夫特经验转向哲学家们基本上忽略了阿赫特胡伊斯、韦贝克和伊德一样,因此,后现象学家和中介理论哲学家对代尔夫特学派的研究并不十分重视。
:那么,在近20年的时间里,荷兰代尔夫特(TU Delft)的经验转向发生了什么变化?
:代尔夫特经验转向学派已经非常成功地在技术哲学中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和论证的话语共同体,这是以前不存在的。经典技术哲学,如加塞特、海德格尔和艾吕尔所发现的,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哲学——哲学是一种邀请,邀请人们注意或关注一些被忽略的东西(哲学是对技术生活世界的解构,重新使用一种突出的方法论称谓)。它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学术讨论的话语共同体,一个成员可以竞争来提炼概念和澄清问题的研究项目(就像分析科学哲学那样)。加塞特、海德格尔和艾吕尔希望更像诗人,帮助我们看到和体验我们原本忽略的现实——基本现实是现代技术如何在人类生活世界的连续性中引入了断裂、撕裂或突变。代尔夫特学派对这种大背景意义上的哲学并不特别感兴趣。
为了纪念克罗斯的退休的马尔滕·弗兰森(Maarten Franssen)等人而编写的《关于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he Empirical Turn)没有提到阿赫特胡伊斯,这正证实了这些观点。同样,阿赫特胡伊斯也认为书中几乎没有提及经典技术哲学家。然而,有趣的是,亚当·布里格尔(Adam Briggle)(弗罗德曼和我的另一位同事)发表了一篇关于“技术哲学的政策转向”的文章。
“经验转向之后”系列提供了对代尔夫特经验转向计划的范围和成就的最好的单一介绍,以及我所说的“技术分析哲学”的现状。正如编辑们在导言中所写的那样,经验主义转向成功地引导了读者。
对技术的哲学研究,从对技术这一普遍现象的广泛抽象反思转向解决与“技术的工作方式”或“正在形成的技术”直接相关的哲学问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主要关注的是工程师的工作。因此,它的主要信息之一是敦促将重点转向技术工件的设计,而不是他们以后作为实践的组成部分的职 业。
但是,回到你关于应用转向、政策转向和实证转向之间关系的问题,实证转向可以被描述为渴望深化应用转向,尽可能地纳入政策转向,并且以比过去更具实证稳健性和分析严谨性的方式去做。特温特学派比代尔夫特学派更了解政策转向的实质内容——如果不是术语的话。接替阿赫特胡伊斯担任特温特哲学系主任的菲利普·布雷使用了“预期技术伦理”一词,其目的是提供政策建议。但是,政策转向也许是STS研究的特征,而不是哲学研究的特征。应用转向和实证转向是针对个人决策的,而政策转向是针对政府决策 的。
最后,再次强调一下我已经说过的,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相关的课程是目前哲学和技术研究中最强大的话语群体。它成功地将哲学和技术研究转变为技术哲学,在更广的学术界赢得了尊重。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工程和技术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这个论证话语社区的贡献者,或者在未来从中会汲取什么。
所以您会认为经验转向已经取代了经典的技术哲学吗?
一点也不。在哲学中,一种方法或一种学派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所有其他的方法或学派。最近,意大利哲学家阿戈斯蒂诺·塞拉(Agostino Cera)对经验转向提出了一种挑衅性的批评。塞拉主张区分经验转向中的两个时刻:一个是合法地将海德格尔的技术神秘主义视为“事件”,一个是随后非法地拒绝所有与技术有关的本体论思考。经验转向哲学家经常指责经典哲学家表现出技术恐惧症。然而,塞拉认为,他们的技术癖已经变成了一种对技术的恐惧症或“对技术的任何本体论意义的先验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