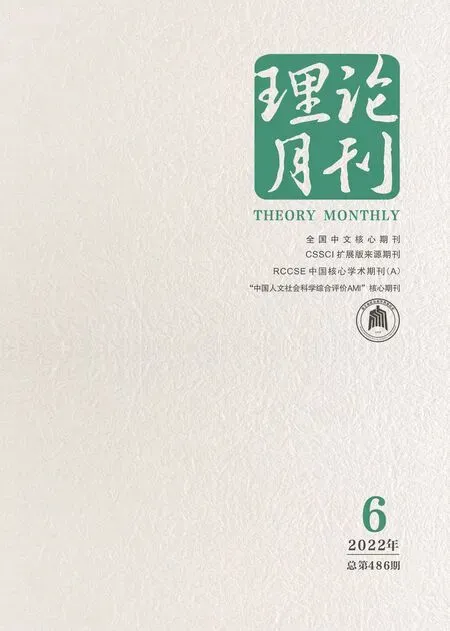反宗教主题与休谟的《人性论》之谜
——评保罗·拉塞尔对《人性论》的反宗教解读
□曾 允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在《人性论》中,休谟似乎表现出两种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层面:一方面,休谟试图将实验推理的方法运用于精神科学中,从而建立一门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另一方面,《人性论》中又包含诸多怀疑论的成分,它们似乎不可避免地给休谟的人学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内在矛盾使学界对《人性论》形成两种分裂的解读:一种是由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和詹姆斯·贝蒂(James Beattie)开启,并由T.H.格林(T.H.Green)和T.H.格罗斯(T.H. Grose)发展的怀疑主义解读。他们强调《人性论》的破坏力量,认为休谟将洛克以来的经验论立场贯穿到底而走向怀疑论,最终标志着经验论的彻底破产。另一种则是由康浦·斯密(Kemp Smith)提出的自然主义解读。他更强调哈奇森等人对休谟的影响,并集中关注《人性论》中积极的建构部分,认为休谟是要在自然主义框架内通过对人性的剖析建立一门有关人的科学。
这两种解读对当代的休谟哲学研究具有深刻影响,并使学者们就如何把握《人性论》的核心主题展开了长久争论。例如,巴里·斯特德(Barry Stroud)追随康浦·斯密,强调休谟在《人性论》中表现出的积极取向,并对休谟的自然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挖掘;而罗伯特·弗格林(Robert Fogelin)则强调,不应低估《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成分,并重提和发展了传统的怀疑主义解读。鉴于两种解读之间的长期争论,大卫·诺顿(David Norton)、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和霍华德·孟斯(Howard Mounce)等人认为,调和《人性论》中的这两个层面是不可能的。他们据此宣称,《人性论》的主旨是多维度甚至分裂的。由此,如何理解休谟在《人性论》中的整体计划和核心主题,尤其是如何处理其中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成了围绕《人性论》的一个“谜”(riddle),并引起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Popkin)、韦 恩·瓦 克 斯 曼(Wayne Waxman)、保罗·斯坦尼斯特里特(Paul Stanistreet)和唐·加勒特(Don Garrett),以及国内的张连富等众多学者的关注。
正是在此背景下,保罗·拉塞尔(Paul Russell)提出了一种“反宗教解读”(Irreligious Interpretation)。他指出,《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都服务于反宗教这个核心主题。他试图以此统合两种主流解读之间的分裂,从而解决《人性论》之谜。这种新的解读为学界处理休谟的《人性论》之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那么,拉塞尔这种以反宗教为主题的解读具体是如何展开的,特别是它如何处理《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层面之间的矛盾?这种解读具有哪些优势,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它能否成功解决《人性论》之谜,或是带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正是笔者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拉塞尔对《人性论》的反宗教解读
拉塞尔的反宗教解读的目标是要解决《人性论》之谜。为此,他在批评现有主流解读的基础上,从历史语境中挖掘出休谟潜在的反宗教动机,提出反宗教是贯穿《人性论》的核心主题,并通过对《人性论》三卷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加以论证。
拉塞尔提出反宗教解读的直接原因是对现有解读的不满。他认为,《人性论》并非分裂或混乱的,而是有着统一的主题和完整的计划。因此,他不赞同诺顿等人所持的“《人性论》是多维度的或分裂的”观点,而是相信《人性论》之谜是有可能解答的。不过他也指出,传统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解读由于两方面的局限而难以解开这个谜:一方面,主流解读仍囿于怀疑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传统二分法中,但这两种解读都由于自身侧重点的不同而难以涵盖《人性论》的全部内容。例如怀疑主义解读更强调《人性论》对近代哲学,尤其是经验论的破坏作用,却低估甚至忽视了休谟想要建立的“人的科学”的积极层面;自然主义解读则相反,它为了突出《人性论》中的积极面而有意弱化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倾向。在拉塞尔看来,两种解读的截然二分使它们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中。现实情况是,《人性论》同时包含两个层面,只强调单一层面的两种传统解读都是“断脊的”(brokenback)。另一方面,拉塞尔指出,传统解读都默认《人性论》中有关宗教的内容微乎其微,它在主题上并未以反宗教为导向,而且休谟为了避免冒犯正统而有意阉割了与宗教有关的内容,直到后期著作中才把研究延展到宗教问题。拉塞尔对此并不赞同,他将这种观点称为“阉割的神话”(the myth of castration),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对《人性论》的反宗教解读。
概言之,反宗教解读强调休谟在《人性论》中的目标是批判“宗教的哲学和道德,以对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世俗的、科学的理解来取代它们”。这一使命内在地包含两个层面,即树立作为形而上学基础的关于人类本性的自然主义观念,以及为建立世俗道德而展开的对神学教义和原则的系统性的怀疑主义攻击。因此,反宗教是贯穿《人性论》的整体计划的最终指向,只有从它出发,我们才能完整理解休谟的哲学体系,统合其中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两个层面,最终解决《人性论》之谜。
为了论证这种反宗教解读,拉塞尔首先从对休谟的早期批评中挖掘《人性论》的反宗教倾向。拉塞尔指出,在《人性论》发表后不久,里德就批评休谟试图从观念论传统中发展出一种系统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因为反对神性存在而带有反宗教倾向。贝蒂对休谟的敌意则更加明显,他认为休谟的哲学直接指向无神论,会破坏道德的根基。拉塞尔发现,里德和贝蒂等人都注意到了霍布斯对休谟的影响,并将休谟放在从霍布斯到斯宾诺莎和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ins)的近代无神论传统中加以批判。这条以往被忽视的线索给了拉塞尔启发,他据此强调休谟与霍布斯在反宗教动机上有直接关联,并将《人性论》与霍布斯的《法律要义》(The Elements of Law)的整体相似性作为证据。他指出,在这两本著作中,休谟和霍布斯在立场上都坚持以经验论和自然主义为基础,在方法论上都强调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性。而且,他们都将人性分为知性和情感两大部分,并以对人性的这种划分来规划各自著作的结构和内容。拉塞尔相信,这种相似性,尤其是对人性的共同理解和著作内容的对应性,表明休谟深受当时无神论的代表人物霍布斯影响。
在肯定休谟潜在地带有反宗教的动机之后,拉塞尔通过考察《人性论》三卷内容来进一步论证反宗教是贯穿《人性论》全书的核心主题。他指出,《人性论》第一卷的任务是对作为宗教及其相应的道德体系的基础的形而上学展开怀疑主义攻击。在对第一章的观念理论的阐释中,与强调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论哲学对休谟的影响的传统理解不同,拉塞尔更注重霍布斯与休谟在观念理论上的相似性,并基于霍布斯用经验论原则质疑有关上帝的观念或知识这个事实,指出休谟的观念理论中也暗含着对上帝观念的怀疑论倾向。而对于第二章,拉塞尔指出,在休谟时代,时空观由于与神学相关而成为热点问题。英国著名神学家萨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就从牛顿主义出发坚持绝对时空观,并将它看作上帝存在的先天证明的关键。而休谟时空观的核心观点是质疑绝对时空,因此,他的潜在目的是反驳克拉克的神学观点。对于第三章的因果性理论,拉塞尔批评传统解读所主张的休谟的因果性理论与神学无关的观点。他指出,通过因果性理论,休谟不仅反驳了以必然性推理(观念的关系)为基础的有关上帝的先天宇宙论证明的合法性,而且也质疑了以或然性推理(事实的关系)为基础的后天设计论证明的可靠性。同样,拉塞尔认为,休谟在第四章中对外部世界、灵魂和自我等内容的考察也与神学问题相关,休谟的潜在目标是要反驳上帝全知全能以及灵魂不朽等神学教义。
拉塞尔指出,在《人性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休谟将自己的反宗教主题进一步延伸到自由意志和道德领域。关于第二卷的自由意志理论,拉塞尔强调,休谟对自由和必然性的探讨与神学教义相关。他指出,休谟在自由与必然性理论上一方面表现出与霍布斯类似的决定论观点,批判基于人类具有灵魂和主动性能力而区别于惰性的物质存在的神学观点,认为人类的生活与外在物体的运动具有同样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另一方面,他特别指出休谟强调必然性对道德的必要性,这不仅与当时的无神论者柯林斯的观点相近,而且为休谟建立一种不依赖于宗教的世俗道德(secular ethics)奠定了基础。关于第三卷的道德学,拉塞尔指出,它与17—18 世纪神学家与无神论者对道德根基的争论密切相关,并认为休谟通过调和霍布斯与哈奇森的道德理论来具体阐述世俗性的道德是如何可能的。按照拉塞尔的看法,一方面,休谟强调道德具有自主性而不依赖于宗教,我们能够以人类的自然本性(human nature),尤其是同情等能力为基础建立道德体系;另一方面,休谟通过反驳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等人所持的无神论必然会破坏道德根基的观点,强调抛弃神学根基的世俗道德是一种“有德的无神论”(virtuous atheism),并不会导致道德败坏。
由此,通过对《人性论》三卷内容的解读,拉塞尔不仅反驳了传统解读中主张该著作与神学无关的“阉割神话”,强调反宗教才是贯彻《人性论》的核心主题,而且指出只有从反宗教主题出发,我们才能在整体上完整理解《人性论》的各部分及其关联性,进而解决休谟的《人性论》之谜。一方面,《人性论》是仿照霍布斯在《法的原理》中的相似计划来规划的。这个计划的基础是他们共同具有的对人类本性的自然主义的和必然主义的观念,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提出一种对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之基础的世俗的、科学的说明。另一方面,为了建立世俗道德的大厦,休谟不得不清理地基,对威胁这样一个计划的神学教义和原则展开系统的怀疑主义攻击。因此,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和表面上不相关的怀疑主义论证,事实上都与他对基督教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反驳密切相关。
二、反宗教解读的特征与优势
作为一种有关休谟《人性论》的新式解读,反宗教解读表现出区别于传统解读的特征。这些特征使拉塞尔相信,它不仅更符合休谟写作《人性论》时的历史语境,而且能更好地解释《人性论》各部分的内在统一性并调和其中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从而解决《人性论》之谜。
在阐发和论证《人性论》的反宗教解读时,拉塞尔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方面,他区分对《人性论》的反宗教解读的强立场和弱立场,并强调只有在强立场上的反宗教解读,即把反宗教看作《人性论》唯一的核心主题才是正确的。他曾用“反宗教的刺猬”(irreligious hedgehog)和“哲学上的狐狸”(philosophical fox)来比喻强弱两种立场上的反宗教解读。后者虽然承认《人性论》包含反宗教倾向,但认为它只是休谟哲学众多维度之一而非核心主题,而且是其中较为次要、休谟有意淡化的一个方面。拉塞尔反对这种弱立场上的解读,指出它实质上仍是传统解读中“阉割神话”的延续,不仅会破坏《人性论》各部分的统一性,并因此难以统合休谟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而且还会造成休谟前后期著作之间的断裂,即他在后期的《人类理智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中都表现出明显的反宗教立场,但在早期的《人性论》中却缺少这一重要主题。拉塞尔认为,必须把休谟看作专注反宗教目标的“刺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休谟思想在前后期中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为了论证这种反宗教解读,拉塞尔在方法上也表现出显著特征,即他专注于挖掘休谟与同时代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人性论》中以往被忽略的文本细节,然后通过结合历史语境分析它们的潜在含义来展开论证。例如为了论证休谟对当时哲学与神学之争的关注,以及他的潜在目标是反驳以克拉克为代表的神学家和护教者,拉塞尔借助休谟与亨利·霍姆(Henry Home)的来往信件对两人的私人关系进行了考察,并留意到了休谟曾将《人性论》赠予与克拉克关系紧密的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等人这样的细节。他还注意到,休谟在《人性论》的上、下两册的扉页上分别引用了塔西佗(Tacitus)的警句(“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和路庚(Lucan)的警句(“爱好严肃的德的人应当时常研究什么是德,并且要求贤淑的典范”)。而这两条警句在当时的思辨无神论者圈子里是具有潜在的反基督教意义的,通过分析科林斯等思辨无神论者对这两条警句的使用,拉塞尔强调休谟不仅知道自己的学说是非正统和有争议的,而且也清楚这种争议性根源于后来里德和贝蒂等人所批评的潜在的无神论倾向。
拉塞尔相信这种立场和方法上的特征使得反宗教解读在对《人性论》的理解上具有传统解读所缺乏的独特优势。首先,通过挖掘历史语境和文本细节,他相信反宗教解读更能还原休谟所处的历史语境。拉塞尔指出,传统的怀疑主义解读和自然主义解读要么把休谟置于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论传统之中,要么强调沙夫茨伯格和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论传统对休谟的影响。但它们都只是从哲学传统出发考察休谟的思想来源,而反宗教解读则结合了更为宏大的历史语境,尤其是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视角出发,强调了当时苏格兰和英国思想界的无神论者与神学家之间的争论对休谟的影响。例如,当时爱丁堡大学的校长威廉·威沙特(William Wishart)曾明确批评休谟的《人性论》,并详细列出六条“罪状”,而休谟对此作了详细回应。拉塞尔认为,只有从更宏观的历史语境出发,结合休谟的反宗教目标,我们才能理解里德和贝蒂等人为何会在攻击休谟的怀疑论时都指责他带有无神论倾向,并对休谟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之间的争论作出合理解释。
其次,拉塞尔还相信,通过在强立场上将反宗教视为《人性论》的核心解读,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人性论》内在的统一性。他指出,由于彼此的截然二分,传统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解读都侧重于分析《人性论》中能够为自身立场提供支撑的内容,而这种立场上的偏颇使它们对《人性论》中某些重要内容的理解并不透彻。例如,关于第二卷中的自由与必然性问题,拉塞尔批评传统的两种主流解读既没有意识到休谟探讨这一问题时的反宗教动机,又没有意识到该问题在《人性论》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他指出,自由与必然性问题是休谟将第一卷中的因果性理论进一步运用到实践领域中的结果。通过对因果关系的自然主义解释,休谟不仅反驳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先天和后天证明,而且将人类与自然的其他部分放在同一个因果链之中。这为他在第二卷探讨自由意志问题时将人类置于一种没有上帝的必然主义框架中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他还指出,在探讨自由和必然性问题时,休谟不仅将上帝从自由意志的领域中驱逐出去,而且强调必然性对道德的必要性,尤其是必然性在道德责任认定中的作用,这又为他在第三卷中建立一种不依赖于上帝的道德体系奠定了基础。
最后,更重要的是,拉塞尔相信反宗教解读能够比传统解读更好地解决《人性论》之谜。要解决《人性论》之谜,必须打破传统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解读之间的对立,并调和《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处理休谟的怀疑主义倾向带来的破坏性作用。拉塞尔相信,从反宗教主题出发,我们不仅能够实现两个层面之间的调和,而且可以对休谟的怀疑主义倾向作出合理的解释。以道德问题为例,拉塞尔批评传统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解读,认为它们只分别抓住休谟道德理论中的部分特征。例如,里德批评休谟由于承认人性自私而带有霍布斯伦理学的影子,而斯密则强调休谟通过同情理论继承和发展哈奇森等人的道德感理论中的仁爱理论。但休谟的伦理学中同时存在这两方面特征,而两种解读又是截然二分和对立的,所以传统解读无法统合对方,并难以完整把握休谟的道德理论。而反宗教解读强调,休谟伦理学的核心在于提出一种不依赖于宗教的道德理论,并表明这种世俗道德并不会导致道德败坏。为此,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休谟一方面要通过怀疑主义破除传统基督教道德,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种以人类自然本性为基础的世俗道德。这两方面的任务最终指向的都是反宗教目标,为此休谟同时吸收了霍布斯和哈奇森的伦理学观点。因此,不同于将休谟的理论置于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自私与仁爱等一系列二分中的传统解读,反宗教解读能够从更高层面统合这些二分,从而更好地解决休谟的《人性论》之谜。
三、反宗教解读的潜在问题
作为一种解决《人性论》之谜的尝试,拉塞尔的反宗教解读在历史语境和文本分析上有独到之处,而且他对休谟时代的无神论者与神学家之争,尤其是霍布斯等无神论者对休谟的潜在影响的挖掘,以及对《人性论》中以往被忽视的文本的关注等,都对休谟哲学研究有着启发意义。但反宗教解读在主旨立场和论据方面存在问题,这使拉塞尔所声称的反宗教解读的优势,尤其是在处理《人性论》之谜上的优势显得颇为可疑。
首先,拉塞尔的反宗教解读的立场过强。如前所述,他区分对《人性论》的反宗教解读的强立场和弱立场,并强调只有从强立场上的反宗教解读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人性论》的主旨和目标。而为了论证这种反宗教解读的强立场,拉塞尔主要通过诉诸里德和贝蒂等人对《人性论》的回应加以证实。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早期回应并不只支持这种强立场解读,而且同样适用于弱立场解读。从文本上看,《人性论》中直接涉及宗教问题的内容甚少,在其中休谟本人对宗教的态度也较为温和,因此弱立场上的反宗教解读或许更为合理,即休谟在《人性论》中并没有以反宗教为根本指向,休谟在《人性论》中的整体计划和最终目标另有所指,只是他的观点蕴含对宗教的破坏力量,所以才被同时代带有护教倾向的学者们所批评。这种弱立场上的反宗教解读不仅能像拉塞尔的强立场解读一样解释为何会有人指责休谟的《人性论》中具有无神论的潜在倾向,而且也更能与文本保持一致,即休谟在《人性论》中并没有过多探讨宗教问题,而且没有明确表露自己的宗教立场。
拉塞尔显然意识到《人性论》文本对自己的观点不利,所以他强调休谟为了避免指责和迫害而将其反宗教立场“隐藏”起来了,并试图通过外部论证来揭示这种潜藏的反宗教立场。但这些论据是存在问题的。具体而言,由于缺少文本上的直接证据,拉塞尔只能诉诸休谟的其他文本以及休谟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来间接论证自己的观点。对于《人性论》的某些文本,例如对于扉页上两条警句,拉塞尔只能从外部进行确证。但问题在于,这些并不构成反宗教解读的直接证据,只能为他的猜测和假设提供一些旁证。拉塞尔本人对此也有自觉,所以更多时候只把这些证据视为一种暗示。这是拉塞尔的反宗教解读在论证方法上的一大疑点。
其次,拉塞尔所声称的反宗教解读相较于其他解读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也是可疑的。例如,在阐述反宗教解读有利于把握《人性论》的内在统一性时,拉塞尔以自由和必然性问题在《人性论》中承上启下的作用进行证明,以此突出反宗教解读相较于传统解读的优势。但从整体上看,反宗教解读的一大问题在于忽略了休谟对情感的探讨,而这对于完整理解休谟在《人性论》中的计划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根据休谟在《人性论》的“通告”中的说明,前两卷中对人性中的知性和情感两大部分考察“单独构成一系列完整的推理连锁”,他的计划是在完成此任务之后,再将得到的人性原则运用于道德等实践领域,即在第三卷中“对道德、政治和批评等题目加以考究”。因此,对人性中的情感能力的自然主义考察是休谟力图建立的人性科学的两个必要根基之一。但由于情感论部分并不包含明显的反宗教内容和倾向,拉塞尔为了自己的解读需要有意或无意地省略了此部分。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拉塞尔对《人性论》的历史语境和思想渊源的分析中。拉塞尔虽然承认休谟的思想有多方面的渊源,但为了突出《人性论》中的反宗教主题,他更强调霍布斯等无神论者对休谟的影响。但问题在于,他为了突出无神论者的影响弱化了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论传统以及哈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传统对休谟的影响。例如,哈奇森等人对休谟的影响被拉塞尔局限在道德领域,而为了打破将休谟置于英国经验论哲学发展脉络中的传统做法,他不仅弱化洛克等人对休谟的影响,甚至因为洛克的宗教立场与休谟存在冲突而在一定程度上将洛克置于休谟的对立面上。应当看到,休谟的思想渊源是多方面的,不同传统对休谟的影响在程度上可能有差异,但一种合理的解读应当尽可能地把这些渊源纳入进来。为了突出《人性论》中的反宗教主题,拉塞尔对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作了取舍。因此,反宗教解读虽然突出了以往被忽视的无神论传统对休谟的影响,但它并未像拉塞尔声称的那般,在历史语境和思想渊源的挖掘上具有更大优势。
最后,拉塞尔所声称的反宗教解读在处理《人性论》之谜上的更大优势也是可疑的。在批评传统解读并论证反宗教解读在处理《人性论》之谜的优势时,拉塞尔预设了传统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解读的截然二分,并批评它们只抓住了休谟哲学中的单一层面。但这种观点包含着对现有解读框架的误解。虽然在早期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解读中确实存在拉塞尔指出的过于强调单一层面的问题,不过这两种解读的当代代表人物已注意到这一点,并试图在自身框架内调和《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例如,怀疑主义解读的当代代表弗格林虽然不满自然主义解读过分强调休谟哲学的积极层面而低估甚至忽视休谟的怀疑主义倾向,并因此着重揭示和分析《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倾向及其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或否定《人性论》的自然主义层面。相反,弗格林承认休谟哲学是在自然主义框架下展开的,并试图对这两个层面进行调和。与之类似,自然主义解读的当代代表斯特德也意识到必须协调《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倾向与自然主义计划之间的关系,而且他相信在自然主义的整体框架的前提下,休谟哲学中的这两个层面是能够得到调和的。所以在当前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解读中并不存在拉塞尔所批评的只局限于单一层面的问题。
因此,虽然拉塞尔的反宗教解读在对历史语境、思想渊源和特定文本的分析方面有独到之处,并且对《人性论》和休谟哲学的研究有重要启发,但并不像拉塞尔本人所认为的那样,在把握《人性论》的内在统一性和处理《人性论》之谜上具有独特优势。
四、解决《人性论》之谜的可行道路
作为解决《人性论》之谜的一种新尝试,拉塞尔的反宗教解读虽存在前述问题,但这种大胆尝试为我们处理《人性论》之谜带来了重要启示。通过反思这种新解读的得与失,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估现有的主流解读,并为《人性论》之谜的解决寻找一条更可行的道路。
首先,必须严格区分《人性论》中并存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与关于《人性论》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种解读。前两者是休谟本人在《人性论》中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哲学倾向,即有关人性科学的自然主义计划和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怀疑主义倾向;而后两者则是后世学者针对《人性论》的两种不同的解读,它们是在理解休谟的核心主题和整体计划时所采取的不同框架。在《人性论》的两个层面与两种解读之间确实存在关联,因为两种解读分别以《人性论》中的两个层面作为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个层面可以等同于两种解读。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两种解读的当代代表人物都看到了两种解读与两个层面之间的区分,并试图从各自框架出发解决《人性论》中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的矛盾。因此,拉塞尔之所以会误认为现有的两种主流解读只抓住了《人性论》中的单一层面,并批评它们无法解决《人性论》之谜,根源就在于他没有严格区分《人性论》的两个层面和两种解读。
其次,必须坚持从统一主题出发,来协调《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在处理《人性论》之谜时,拉塞尔敏锐地抓住了休谟哲学中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冲突,并由此主张要通过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来统合双方。具体而言,拉塞尔认为《人性论》的怀疑主义的任务是对宗教展开系统攻击,从而为树立人类本性的自然主义观念扫清障碍,并最终建立一种不依赖于宗教神学的人性科学和世俗道德。因此,他的思路是从反宗教的核心主题出发,把《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分别视为休谟哲学中的破坏与建构层面,并强调破坏只是手段,休谟的最终目的还是建构,这正是两个层面的关联性的体现。拉塞尔的思路是正确的,他的问题是试图在原有解读框架之外再添加一个第三者,即反宗教目标来完成此任务。但正如前述指出的,这样的一个第三者面临着立场过强、文本支持不足和解读方法可疑等问题,并且相较于现有主流解读也没有明显优势。
最后,必须在肯定《人性论》在整体上具有积极取向的基础上,对休谟的怀疑主义倾向作出恰当定位。拉塞尔肯定反宗教的核心主题和目标使《人性论》在整体上表现出积极取向,但他也意识到如何协调这种积极取向与休谟的怀疑主义倾向是一大关键。为此,拉塞尔强调《人性论》中存在两种怀疑主义,即温和怀疑论和极端怀疑论(皮浪主义),并颇有创见地提出对二者的一种“动态性”(Dynamic)理解,认为皮浪主义最终必然会走向温和怀疑论。具体而言,拉塞尔强调皮浪主义只存在于哲学沉思领域而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休谟指出皮浪主义的极端性必然会使得它走向自我否定(“一个地道的怀疑主义者,不但怀疑他的哲学的信念,也怀疑他的哲学的怀疑”),并因此放弃自己的极端立场而转向温和怀疑论。这种温和的怀疑论本身是休谟为达成反宗教目标的必要构成部分,它的作用在于暴露知性的弱点和局限,使人们不再沉迷于神学体系和假设,而是将目光转向对人性的自然主义研究。因此,在《人性论》中承担破坏作用的怀疑主义倾向同样能被看作是具有积极取向的。
基于这三点启示,我们可以对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种解读作出准确评价,并为《人性论》之谜的解决寻找一种更可行的思路。一方面,在区分《人性论》的两个层面和两种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肯定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种解读仍具有合理性,它们并不存在拉塞尔所批评的只局限于单一层面的重大缺陷。与反宗教解读相似,主流的两种解读也试图从一个统一的主题和框架出发,来统合《人性论》中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层面。虽然两种解读在选定的主题和框架上有分歧,例如怀疑主义解读将休谟通过怀疑主义摧毁传统哲学体系视为《人性论》的核心主题,而自然主义解读则将核心主题理解为休谟在自然主义框架下展开的人性研究,但它们都坚持在自身框架内调和休谟不同的哲学倾向,而且都没有像拉塞尔那样,试图借助一个可疑的第三者来完成这种统合。另一方面,基于拉塞尔的启示,通过对比两种主流解读,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主义解读是解决《人性论》之谜的更可取的道路。其一,自然主义解读更有利于肯定《人性论》在整体上的积极性的建构取向,并由此更好地统合《人性论》的各部分内容。相较之下,怀疑主义解读虽然在解释休谟《人性论》第一卷的认识论对现有知识体系的质疑方面具有优势,但是休谟在《人性论》第二、三卷的情感论和道德学中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怀疑主义倾向,因此它难以将这些内容统合到自身框架中。其二,在肯定《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框架的前提下,我们能够更好地将《人性论》的两个层面视为破与立的关系,并通过对休谟怀疑主义倾向的“动态性”理解来看待休谟哲学中破坏性的一面。当前的主流解读也正是以这种思路来处理《人性论》之谜的。例如,在对休谟的因果性理论的分析中,自然主义解读的代表斯特德承认其中的怀疑主义倾向,但强调这种怀疑主义最终导向的是对因果性的自然主义说明,即将它的根基最终要追溯到想象力上,并由此把因果性信念看作一种以人类本性为根基的自然信念。在怀疑主义解读的代表弗格林这里,他也承认休谟的整个计划是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认为休谟通过对因果性的怀疑来表明这一问题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是无法解决的,而这也使他有理由转向关于人类心灵如何构造信念这一事实性问题。这种对共同框架的认可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主义解读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五、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对拉塞尔的反宗教解读作出整体评价:一方面,拉塞尔将反宗教树立为《人性论》的核心主题的做法是处理《人性论》之谜的一种新尝试,而且它确实可以在历史语境、思想渊源和特定文本的研究上带来启发;另一方面,拉塞尔对现有的解读框架存在误解,加之他的反宗教解读还面临着种种问题。因此在《人性论》之谜的处理上,反宗教解读并不具有拉塞尔所声称的更大优势。尽管如此,反宗教解读依然为我们处理《人性论》之谜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区分《人性论》的两个层面和两种解读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回到休谟的自然主义框架,将他对人性的自然主义研究视为《人性论》的核心主题,并通过对怀疑主义倾向的辩证理解来协调它与休谟的自然主义计划之间的关系,是解决《人性论》之谜的一条更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