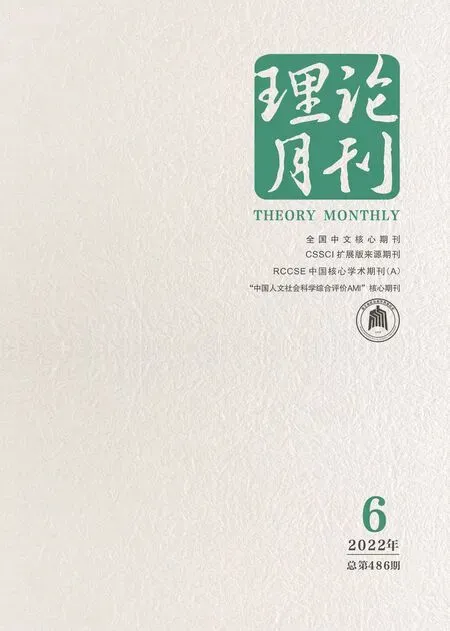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现实和理论逻辑
□郭国祥,王钰涵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来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关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它的论证意义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为过。自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论证就一直存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它的阐述角度就更加新颖多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进行了新的阐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来到中国并能扎根中国大地,这又是我们阐述七一讲话要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本文力求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三个维度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历史逻辑
(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民族救亡运动需要新的思想引领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封建社会保持了相当时间的稳定状态,整个社会在巨大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封闭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国门,封闭而稳定的生态遭到了破坏。中国从此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但是,中西方之间的交流是以中国受剥削和压迫为基础的,并不是平等意义上的往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它也将现代性的元素带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一元化的中国社会被混沌复杂的局面所取代。现状是,封建势力依然庞大,但新兴的资本主义也正在萌发;旧的统治机器依旧支配社会的同时,也日益受到帝国主义的支配;中国人民不得不同时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在这种局面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成了近代中国最根本和最迫切的历史需要。
然而,受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制约,中国社会各阶级既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更不能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完成时代的考卷。反映农民阶级平均主义理想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只是“植根于传统小农社会土壤之上的,具有巨大诱惑力而又永远无法实现的社会乌托邦”。地主阶级的“中体西用”明显就是一个笑话,想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嫁接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无异于马头和牛身的结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更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本是限制皇权的立宪主张却希望光绪帝施行霹雳手段来实现,手段与目的背道而驰;更何况,立宪派根本就不敢与封建主义、与传统进行彻底的决裂,托古改制,借孔子改革的名义实施新政,无异于换汤不换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也有太多的局限性:民族主义缺乏鲜明的反帝内容,民权主义只是一种资产阶级议会式的“精英民主”,民生主义则流于空想。所有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及其指导思想都不为当时社会所接受,最后以历史教训的面貌定格在伟大的民族复兴史之中。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理论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而实践也不能在现实中趋向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缺陷性既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后天的因素,但根源于复杂时代背景下的阶级局限性。
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及其失败说明没有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就不能前进,中国人民就难以解放。“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时代在呼唤和等待满足它需要的新思想横空出世,历史在二十世纪初这个瞬间,好似偶然实则深刻必然地迎来了马克思主义。
(二)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一书认为,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等,都可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些启蒙运动都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传播西方的制度文明。当然这些启蒙运动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逐步深入、逐步提高的一个过程。启蒙的结果就是中国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封建的官僚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再到封建的纲常名教,一步步消解,人们的思想变得开放和宽容,对西方新东西从尝试到逐步接受,到认为理所当然。中国文化盲目的自大心态和专制主义的因袭被打破,这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进行了思想启蒙。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礼乐文化和统治秩序。这种文化和统治方式与中国的小农经济非常匹配,也保持着中国的稳定发展。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是礼仪之邦一直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认识,这种文化心态使中国专制主义的制度基础和纲常名教一直被保留。即使后来帝国主义侵略,也不曾改变中国人的心态。士大夫还在做着外来蛮夷被中国文化同化的美梦,他们没有也不敢正视西方制度和文化,陶醉于所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自我安慰中。
两次鸦片战争完全落败,特别是甲午战争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才真正让中国士大夫感受到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的再也不是历史上的蛮夷之族,而是有着真正先进制度、先进文化的西方列强。“列强”两字就很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人对西方态度的变化。极端自大受到打击后,一些人则滑到了原来的反面,对西方感到恐惧,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得用西方制度和文化来改造中国,崇洋媚外心态开始在一些国人心中潜滋暗长。甲午战争之后,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翻译了西方赫胥黎的《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化理论来分析中国面临的危亡之势,发出了“救亡”的时代强音。梁启超有感于国人思想的颓唐提出了“少年中国说”,呼吁国人振作,以新民说来动员民众挽救时局。但这些思想家的呐喊虽然是天籁之音,奈何整个封建集团颟顸无知,更出于维护自身的特权,拒绝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启蒙也就只是局限于清醒的“先知先觉”,缺乏群众基础。孙中山在长期的中西文化交融中,清醒认识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中国落后的原因,发出了三民主义的时代强音,并发动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辛亥革命后,中国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然而这种在西方管用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形走样。民主成了少数流氓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所谓的议员大都是“猪仔议员”,轻易就能被金钱和强权所收买。原因何在?关键就是中国人的思想没有真正地解放,中国人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识,改造国民性成了“先知先觉”的基本共识。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新文化运动时,历次启蒙运动在思想上的突破终于累积成质的飞跃,它所探讨的问题不再局限于器物或制度层面,而是推进到最深刻的文化和心理层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旧文学、旧道德,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使得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儒家思想受到沉重的打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三)近代中国人“双重超越”的情怀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提供了深沉的思想动力
“双重超越”就是既要超越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也要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在强势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完全破产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也越来越暴露其固有的弊病和矛盾。对中国人民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而言,寻求超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双重超越”情怀从来都不是一种高远的理想,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探索国家出路的自觉实践。或许他们无法清晰地将自己的追求概括为“双重超越”这样高大上的范畴,但他们的实践追求无疑都是趋近、暗合这一理想的。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洋枪洋炮由恐惧而生艳羡,开始模仿,“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使中国开始了对西方器物文明的追求。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写了《盛世危言》,提出了同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主张。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都是学习西方,当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人也产生了很多困惑,很多不解,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也越来越强烈。反思的直接感受,就是中西文化不同,两者有不同的特点,西方文化未必适应中国,中国必须超越西方奠基在资本之上的文化。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独特的“双重超越”情怀到五四前夕更加强烈了,其愿景也更加清晰了。“一战”的爆发以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说明西方文化的本质——充满暴力,充满掠夺。现代科技的发展没有带来人类的和平和发展,反而加剧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这既彻底击碎了启蒙以来“现代性神话”的全部幻象,也极大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合法性。梁启超在1919 年游历欧洲之后,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写下《欧游心影录》一书,其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
中国社会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终于在西方民主人权的虚伪本质彻底暴露后达到了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氛围在全世界盛行。”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公理战胜强权”的“十四点原则”的演说,更是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未来、对新的国际秩序充满了无限的希冀。“但是当列强企图在巴黎和会上重建他们的殖民地政策时,中国人民由空虚的希望坠入深切的失望,于是爱国热情就空前地、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西方民主人权的虚伪、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的漠视不仅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使得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对立面。因此,中国不仅要克服传统中的顽疾,还要超越资本主义,这种“双重超越”的理想就更加炽热而且猛烈。
二、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现实逻辑
(一)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中国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亦步亦趋,虽也有过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因为各种原因都夭折了。这些成果要么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得不到社会精英人物的支持;要么水土不服,不适应中国。太平天国后期曾经出现了一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治国的方案——《资政新篇》,但这是一个早熟的智慧之花,对于农民无异于是一种天书,根本就不是农民所能理解的;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看起来很高大上,但一到中国现实实践中就变形走样,丝毫显示不出一点制度的光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也日益暴露出虚伪的本质,中国这个学生曾经也很虔诚地想移植西方的制度文明和思想,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先生总是打压学生,学生总是感受到一种窝囊和无可奈何。中国人迷惘了,彷徨了,不知路在何方。就在中国思想界歧路彷徨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给中国送来了福音和启示,毛泽东就曾经说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首先,十月革命让一种抽象的理想愿景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天堂,给默默忍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前途。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生活富足、幸福安康,这样的理想社会是古往今来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想竟然在俄国实现了,变成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向往和希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忆中国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心路历程时,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其次,俄国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国情,两者都是具有浓厚封建传统的专制国家,两者都受到了资本主义新型文明的影响,并不同程度地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体系,都是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和打压的对象,资本主义开始有所发展但发展又极不充分。这种相似性,大大地强化了榜样的吸引力,也为中国“第三种文明”的选择提供了强大的事实根据。即便是罗家伦这些后来变成坚定反共分子的人也曾在十月革命爆发后说过“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他认为“在这些革命里民主会战胜君主,平民会战胜军阀,劳动者会战胜资本家”。再次,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发表了两次对华友好宣言,并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愿意把沙俄霸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苏俄这些友好的对华政策,大大提升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和俄国新生政权的好感,进而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道路和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李大钊是中国宣传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从1918年起,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讴歌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革命屡次失败后,也从十月革命中受到了启发,认识到了群众参与的重要性,认为革命必须唤醒民众,必须动员民众。
(二)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新发展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唤醒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动员受苦受难的底层人民造反的科学的理论工具。这种理论工具如果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学理,就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从而也就没有它改造社会的惊天伟力。列宁说得好:“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只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物质力量,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首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这本书的原作是英国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根据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的著作《社会进化》编译了《大同学》,文中提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首推梁启超。他曾著文称“麦喀士”(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泰斗,社会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之一。那个时候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马君武、朱执信等人也在多个场合谈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往往只限于只言片语,甚至是断章取义。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彼时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借来同它的敌人作斗争的一种理论工具,还没有遇到它的物质力量和阶级载体——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未能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刚产生不久,发展有限,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为微弱,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占主要位置。”二是历史还未产生一种社会力量去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牵线搭桥。因此彼时的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学理”和“一种善良的愿望”。
然而,到了五四时期,情况变得大不一样。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出卖了中国,中国人愤怒了,最早是对时局非常敏感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也出现了“火烧赵家楼”的壮举,但北洋政府抓了几个学生,宣布了几个禁令,一切就悄无声息了。即使是大教授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到处呼吁保护学生,爱我国家,保我利权,应和者也是稀少。陈独秀被关进了监狱,北洋政府还是要在卖国的和约上签字。随着全国工人的声援和加入,随着上海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的开始,北洋政府恐惧了,犹豫了,妥协了,学生被释放,卖国贼被免除了职务,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表现出了伟大的力量。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进知识分子,也看到了工人阶级在这次运动中显示出来的力量。他们也明白,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工人运动,只是盲目的运动,工人阶级要么会分化,要么则在自发的经济利益的追逐中模糊斗争的方向,丧失斗争的目标。这些知识分子为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开始积极走近工人,与工人一起劳动,一起谈心,与工人打成一片,利用各种机会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劳动补习学校,创办各种面向工人阶级的宣传册子、刊物,并想方设法成立工人阶级的组织,1920 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受到了启发,新的革命领导力量受到了锻炼,最后催生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三、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成为中国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思想缘由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但马克思主义又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集大成。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没有水土不服,并没有和中国文化发生排斥效应,相反很快与中国文化相融通,并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普适价值,是真正的普适文明,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理想愿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消除了劳动异化、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理想是建立大同社会,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理想不仅是潜藏于所有中国人心中的美好愿景,而且还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为之奋斗的连续不断的社会实践。从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到发动黄巾起义的“天公将军”张角,再到制定《天朝田亩制度》的洪秀全,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都不约而同地选取“大同”理想中的某些内容,作为其政治纲领,以号召群众推翻封建统治者。从康有为《大同书》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到孙中山对“天下为公”“平均地权”的追求和实践,再到中国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可以这样说,“大同”理想是所有中国人在理想追求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最高理想上的契合,无疑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拥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拥有对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为了人的彻底解放。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五四时期,李大钊就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光辉,并能科学地解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阶段性和工具性,指出: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的永恒现象,只适应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的核心也是人,强调的是“仁爱”“仁政”“仁者爱人”。强调博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爱天下苍生,要爱天下万物,体现了一种崇高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强调推己及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马克思主义所饱含的人道主义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善”的追求不谋而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共同的致思倾向。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强调其思想不是学理,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实践,甚至可以说,“实践智慧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和核心”。传统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强调修身为本,但道德修养重在践履,道德也需外化,要“内圣外王”,推崇经世致用,崇尚建功立业。而民间的侠义文化则将中国文化反抗专制、反对暴政的思想推向深入。“路见不平一声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等匡扶正义、伸张正气的侠义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并让统治者恐惧而不敢放肆。可以说中国底层反对暴政的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异曲同工。因此,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很快就能被底层民众所欢呼、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特质。世俗性、凝聚性、包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具有浓厚的世俗性。这里的“世俗性”与“超越性”相对立,指关注现实社会和个人,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其实用追求。“天道远,人道迩”,中国人最关注的是人间生死苦乐悲欢,是现实的生活享受和欲望。“天道”与其说是渺茫难测的神意,不如说是人间社会秩序及伦理规范的折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西方文化,但马克思主义却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肯定世俗生活,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脱离现实的极乐世界和虚幻的乌托邦,不是高远神秘的宗教,而是唯物史观指导下对未来社会的科学畅想,这种社会的实现也不寄托于神秘的上帝、虚幻的良心和绝对观念,而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靠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这些都是根源于世俗基础上的真理性认识。中华文明的另一重要特质就是有着很强的凝聚性。从中华文明的文化内容来看,“中国思想史上的民族精神的五方面特质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主要体现为大一统观”。这种凝聚性使中华文明能够生生不息,始终保持中国社会的团结统一。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在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主张无产阶级不分国家、种族的团结,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神圣的斗争,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和中国文化的凝聚性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庸”,强调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追求“和而不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华文明不论是对内部文明的多样性发展还是对外来文明的传播影响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吐故纳新,中华文化就是在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交流、交融中产生的,也是在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它吸纳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欧洲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形成的。为什么其他的主义在中国喧嚣一阵就烟消云散,而马克思主义却能扎根中国大地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在于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特质。
(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优秀品质和独特魅力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真理性相统一、人民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开放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能扎根中国大地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真理性相统一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不是僵化的抽象的教条,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地观察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规律的工具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强调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物质是处在相互联系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观点为人类从根本上摆脱唯心史观、神学论和神秘主义的束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进而科学地认识自然、人类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的任务就是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思想武器,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质。马克思是天才少年,才华横溢,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来到了《莱茵报》担任编辑工作,本可以过一种上流社会的悠闲生活,但马克思为底层人民的苦难鸣不平,抨击不合理的私有财产制度,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中,马克思对无耻地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而置广大饥寒交迫的底层群众于不顾的腐朽制度进行了辛辣的攻击,得罪了整个统治集团,被驱逐出境。“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成就了伟大人生。”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碑上,镌刻着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伦理社会主义,不是理性的乌托邦,不是一种说教,而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运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封闭的僵化的理论,而是吸取了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站得高,看得远。在自然科学领域,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成为其理论的科学依据和直接来源。在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学说,与时代一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它着力解答当代中国的三大时代课题: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优秀品质和独特魅力,它一来到中国,就引起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并迅速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本来,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时期,旧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其正统地位,西方新的思想不断涌入,当时传入中国的思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改良思想,也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是“隔着纱窗看晓雾”,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有人去宣传、去实践,无怪乎时人慨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的主义。”但这些思想主张往往只能漂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终究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免不了“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喧嚣过后,短短几年就波平浪静、了无痕迹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在风雨之中扎根于中国社会,掀开了新陈代谢的另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