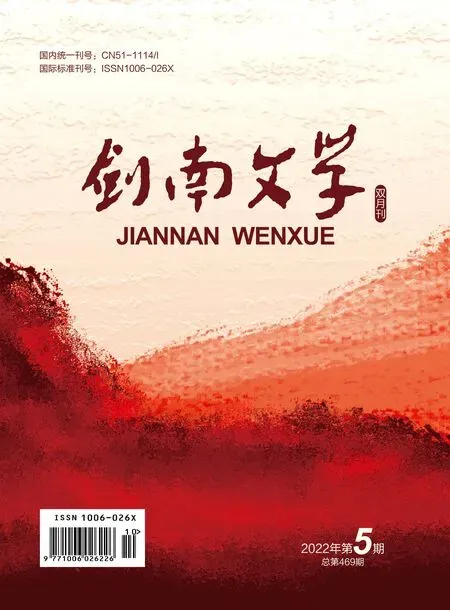远翔的白鸽
□谢松良
十九岁的我跟吴老汉他们是工友,工程烂尾后,我就跟他们一样,以工地为根据地,在小镇周边打打零工,或者在河边码头卖苦力,那装满沙石、煤炭、红砖的木船等着我们一伙人去挑上岸来。
撒完口袋里的玉米粒,吴老汉回头看了看我。
我一惊,赶紧将忍不住拿出来把玩的一柄短刀藏进衣袖里。
吴老汉走近我,严厉地说,快把刀丢了,就算拿不到工钱,我们也不可胡来。
反正吴老汉已知晓我藏在心里的秘密了,我便不再隐瞒,气不打一处来地回道:可我不甘心,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付出血的代价。
小子,也许老板真有难处。我们就在这里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果你走极端,一旦犯事就不划算了。吴老汉开导我。
以100客位的 Arsterwasser号的功率需求为参考进行计算,该船舶1 h的功率需求如图1所示[5]。
我抹了一把眼泪说自己急需钱,回去复读参加高考,不能在这种地方待一辈子。吴老汉摇着头,轻轻地叹了口气,吹出了一声短促的口哨,鸽群听到命令后张开翅膀在草地上跑动几步呼啦啦飞上天空。
望着那群白鸽,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回过神来后慌忙把短刀丢进远处的荒草丛。
这就对了嘛!吴老汉说完,转身提起空鸽笼丢给我,哼着小曲慢悠悠地往家里走。
我和吴老汉,以及原先给工人做饭的肥姨关系较好,我们住在东面一幢烂尾楼的三层。肥姨在靠近码头的大排档做洗碗工,她有时会将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打包回来给我们改善伙食。
肥姨房间没有透出蜡烛的光亮,吴老汉习惯性地喊:四川婆,睡了吗?
无人应声。
这么晚了,四川婆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吴老汉问我。
我没好气地回他,这会儿知道关心人家了,肥姨几次提出搬过来跟你一块儿搭伙过日子,你总拒绝人家,我都看见肥姨为此事伤心地哭过几回了。
早点儿睡吧!吴老汉岔开话题。
望着他的背影,我心想:你吴老汉和肥姨都是苦命的人,俩人一起生活不更好吗?
吴老汉摸进房门,点燃蜡烛,早飞回来的几只鸽子围过来,它们刚才没吃饱,伸直脑袋,拿眼睛盯住吴老汉要吃的。从两个月前开始,吴老汉给鸽子投喂的玉米粒渐渐少了,它们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每到这时候,吴老汉便轻叹一声,打开装玉米粒的木桶,鸽子的目光就转向那只木桶,怕它们失望,他迟迟不敢把手亮出来。
半夜三更的,鸽群在咕咕地叫着,又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我听见隔壁的肥姨和一个陌生男人在说话:这个吴老头,自己都养不活了还养鸽子,让鸽子跟着遭罪,缺不缺德。
肥婆,你跟我走吧,离开这个穷地方。
可我舍不得这儿。
是舍不得吴老头吧?
懒得理你,你带来的玉米粒呢?
接着,传来开门的声音,然后听见了鸽群欢快吃食的声音。夜又恢复了寂静。
第二天,我们在河边的沙船上等吴老汉来装筐,他却在做着另一件事。他把鸽群带到草坪上,和它们说了很多话,语重心长千叮万嘱,劝它们自谋生路。最后,他亲吻了每一只鸽子,吹出一声悲凄悠长的哨声,鸽群应声飞上天空,远去了。
傍晚,我收工吃完饭回来,在空空的鸽房找到了吴老汉,他蹲在地上,对着屋里的鸽笼喃喃自语。我把打包的盒饭丢给他,他全倒地上,说是留给鸽子,可哪还有鸽子的身影儿。
鸽子走了,烂尾楼一下子就显得格外空荡,随那股熟悉的鸽粪和禽鸟身上特有的腥味儿慢慢淡去的还有肥姨,她嫁给了小镇的一名退休医生。
半年后,老板出乎意料地开着大奔回到了工地,他带着歉意给我们补发了拖欠已久的工资,并宣布找到了资金,工程要继续下去。
一群工人在清除工地杂草的时候,发现了一柄锈迹斑斑的短刀,并被当成“宝贝”献给老板。
吴老汉和我相视一笑,我心里暗暗庆幸。
这时,一群鸽子由远及近飞过来,落在我们周围,围住吴老汉咕咕叫着,吴老汉边哭边赶它们……
不久,吴老汉悄悄递给我一张火车票,含着泪说:小子,你也走吧,你还年轻,应该像鸽子一样,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