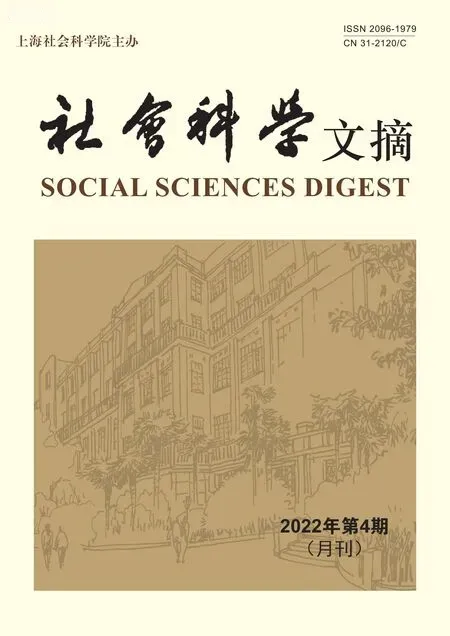“解码”基层群众自治困境:城市社区公共参与的内外分隔逻辑研究
文/樊佩佩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摘自《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住房产权对大城市新市民群体社会融合及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21BSH038)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问题:社区分化与公共性转型的复杂性及新的生长点
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0%,“十四五”期间更高水平的城镇化进程将继续引导人口向城市集聚。根据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现有人户分离人口共49 276万人,流动人口共37 582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了88.52%,流动人口增长了69.73%。这说明近十年来流动人口规模增速迅猛,人户分离程度不断加剧,高流动迁徙态势已然成型。这给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国家引导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另一方面社会的流动性和个体化程度加大了异质性社区的自治难度。那么,社区居民形成一致行动进而实现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社区分化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社区公共性、导致社区疏离和社会关系松散?这些都是开展基层自治所需解答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问题。
为探究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转向之间的复杂机理,不少学者从社会网络、社区信任、社会资本和社区参与等视角来分析社区公共性的演化路径。不过,一方面,部分研究容易陷入循环论证:到底是公共性缺失导致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不足,还是社区参与缺位制约了公共性水平?不同视角研究的解释逻辑指向作为行动主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而主体性缺失的后果,是社区参与动力和参与持续性受到弱化,加剧社区治理的困境。因此,居民的主体性缺失与社区参与缺位就构成一个封闭循环的解释链条,公共性成为串联居民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公共参与形式多元而实质性参与较少,特定群体活跃而整体参与不足几乎是城市社区个体化和异质性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普遍现象。相对于“参与什么”和“如何参与”,学者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寻找“为什么参与”的解释机制上。要么回答“为什么参与”,要么分析“为什么不参与”,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参与,有时候不参与”,以及“为什么对待同样的社区活动或事务,有的居民参与,有的居民不参与”。
结构视角下的社会资源命题聚焦于有差别的结构性位置及其对行为选择的叠加效应,但难以解释有价资源对不同参与层次的影响机制为何呈现出解释维度上向生活领域拓展,价值取向上向政治参与收敛的趋势。能动视角下的理性人行为选择基于不同的激励结构,“搭便车”理论无助于分析松散利益关联的社区中为何不同范畴的参与动机强度不一。可见,到底是“意愿-能力”还是“成本-收益”框架更能解释社区参与逻辑的多样性,需要进一步探讨。贝克提出“个体化进程”和“生存的个体化形式”,意味着过去建立在普遍性的权、责、利共识基础上的社区公共性越来越依赖于个体化的境况和条件。当下个体行动者选择性参与的背后不仅是激励结构的分化,而且还涉及动机、能力和资源的匹配。本文着力揭示不同维度的资源匹配如何制约不同群体的公共参与层次,以及同一群体公共参与的情境选择性为何呈现出社区内外有别的差异,并尝试构建社区内部参与的下沉扩散性以及外部公共事务参与的收敛性与社区公共性关联的分析框架。同时,本文试图拓展复杂多样的社区参与分化的解释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解城市社区的公共性转向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进路。
数据与发现
(一)数据采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9年11月—2020年1月作者主持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南京市20—75岁的城市小区居民。抽样的城市小区类型分为四种,分别为新兴商品房小区、老旧商品房小区、保障性住房小区和拆迁安置小区。通过CAPI(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发放问卷1215份,回收有效问卷1086份,回收率为89.4%。
(二)实证分析
1.对社区内部参与的变量分析
社区内部参与度是测量个体特征和社区特质对内部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的影响。本次调查数据发现,居民年龄、学历以及对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都与社区内部参与的积极性和公共性程度正相关。在社会资本和邻里交往方面,居民在社区内的熟人朋友越多,与社区居民的交往频率越高,就越关注并积极参与社区内部事务。除了个体禀赋和社会基础,小区房价和小区类型对内部参与度也有显著影响。数据表明,小区均价越低,内部公共活动参与度越高。可能的解释是,不同于社会认同主要对社区内部公共性参与发挥正面影响,小区均价可看作是汇聚居民多重经济社会属性的市场结果呈现。房价均价越低,小区居民越依赖低成本、便利性的内部活动参与;小区均价越高,居民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这些都扩展了其小区和社区之外的活动空间,因此降低了内部参与积极性。就小区类型而言,回归模型以拆迁安置小区为参照组,分析发现老旧商品房小区居民的内部参与度明显高于拆迁安置小区居民,是拆迁安置小区的1.345倍。
2.社区内部参与的分类及其差异性分析
性别因素对社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和公共活动参与的影响均有显著差异。男性相对女性参加公共事务的可能性更大,而女性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更高。说明男性对小区内部管理事务这种正式的、制度化参与更有兴趣,公共性卷入程度更高;而女性对参与文体休闲、志愿服务和培训等非正式活动更积极。代际因素在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公共活动参与中均呈现出正相关性,不过代际因素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低于对公共活动参与的影响,说明参与前者的年龄相对年轻。另外,居民学历越高参与公共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而收入越高的居民参与小区内部公共活动的积极性越低。同样,收入越高,越不可能参与社区党支部活动;而宗教活动的参与情况却相反:收入越高的居民,参与社区宗教活动的可能性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地位评价方面,数据显示社会地位与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度显著正相关。可见,经济收入和地位认同对小区内部不同层面参与行为的影响呈现出不同逻辑: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更能提升居民参与内部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而代表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收入指标,呈现出对参与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和党支部活动的排斥性。与此同时,本研究还测量了不同小区房价与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度的关系。与公共活动参与一致,小区均价越高,居民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越低。一般而言,房价越高的小区,居民的社会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网络和交往范畴更加多样,可能相应减弱对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度。
总体而言,小区内部不同维度的公共性参与具有“筛选”门槛:公共事务参与度与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认同以及社会资本变量具有正相关性;而小区内部公共活动的参与度更倚重小区内部社会资本而对收入等经济指标具有“逆向”选择性。这说明公共性卷入程度越高,能力门槛越高的参与行为,对居民超出小区或社区以外的经济社会资源越倚重。因此,从低门槛到高门槛的小区内部公共性参与行为,对小区/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依赖度逐渐降低,而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力逐渐上升。
3.对社区外部参与的变量分析
小区/社区外部公共性参与的测量是以“发现小区或社区存在管理或治理方面的问题或矛盾”为由,询问居民采取何种方式向公共渠道反馈。调查数据表明,当小区出现管理或治理问题时,年龄越大,遭遇问题时向小区外部反馈的可能性越高;而学历越高,对小区内部事务卷入越少,并因小区内部管理事务向外反映的可能性越低;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向小区外部公共渠道反馈的可能性更大。有学者发现,社区自治参与主体主要集中在低保户、党员、楼组长以及社区文艺骨干等。
另外,线上和线下参与,以及社区熟人朋友数量这3项小区或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指标与小区外部参与度的负相关表明,小区或社区内部资源削弱了居民通过小区以外公共渠道解决小区内部问题的可能性,也即社区内部社会资本拥有量相对低的居民更可能求助于外部媒体和公共组织。
4.社区外部参与的分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依照参与程度和难度对“社区外部公共性参与”从高到低分为四个层次。(1)“市域层面参与”是指当具备必要性时,向市域范围的市民热线或新闻媒体投诉,发动组织集体维权或上访活动,可用于测量居民遭遇问题时与参与成本最高的公共渠道互动的可能性。(2)“属地层面参与”指的是在遭遇问题时向属地公共组织,如社区和街道反映问题。(3)“社区层面参与”是指网上反映、就近反映给基层治理人员,便利性高,动用资源有限。(4)“私人渠道参与”是指利用个体社会资本寻求信息或协助以解决小区管理问题。
数据结果表明,当发现小区或社区存在管理或治理方面的问题或矛盾时,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更可能采取最高层面的诉求表达方式;而越年轻的居民,越可能利用公共渠道,采取热线电话、向媒体爆料、发动组织维权上访等方式,也越可能通过私人关系寻求解决。年龄越大的居民,越可能采取规范稳妥的处理方式,如当面到社区或街道反映问题。同时,非党员身份的居民更少顾虑,更可能采取最高层面的诉求表达措施。
除了人口变量,经济变量也对不同层面的问题解决方式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小区房价越高,居民采取市域层面资源表达诉求的可能性越大,同时通过私人关系寻求协助的可能性更高;而小区房价越低,居民越可能在小区内部进行讨论和反映。这意味着,均价越高的小区,居民更能运用最广泛层面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渠道解决问题,因此更可能采取声势浩大、影响力最高的诉求方式。而均价越低的小区,更可能局限于小区内部资源和渠道来反映问题。小区房价反映的是居民在小区以外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以及承担更高表达成本的意愿。
除了经济维度,关系视角下社会资本的占有类型也影响社区外部公共参与的选择。数据发现,市域层面的反馈渠道更多与经济指标相关,并与私人渠道的参与方式有部分一致性;小区和属地层面的反馈方式更多与辖区内社会资本相关。可见,居民倾向于采取什么层面的解决措施,愿意承担什么样的意愿表达成本,除了个体特征之外,更多受制于居民与社区以外公共渠道互动的能力。
结论与讨论:社区参与的分隔、替代和补偿效应
本文分析了主导社区内部参与的社会认同逻辑与主导社区外部参与的资源制约逻辑对社区公共参与分化的影响机制,并从社区内部参与的下沉性和外部参与的收敛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隔如何制约公共参与层次,产生内外有别的参与逻辑。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一是“关键少数命题”——代际和性别因素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参与影响路径不同,社区公共事务卷入的主体更可能是男性和中青年居民。尤其当面临问题或矛盾的情境,有意愿有能力的中青年群体尤其男性更可能充当社区积极分子等“关键少数”。也就是说,具备一定资源和渠道的群体以及学历较高的中青年群体可能具有更好的社区公共性行动基础和潜力发掘空间。二是“经济社会资源命题”——社会地位认同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参与具有积极作用。居民收入对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参与具有抑制性,但会提升外部公共事务参与度;小区房价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具有限制性,但会提高外部诉求层级。小区内外活动和事务性参与受到选择性激励和资源约束的影响,其对应的公共性卷入具有不同指向。社会层面的社区交往和主观社会地位认同能提升小区内部公共性事务参与的积极性;经济维度的收入和房价指标更多是对小区以外的资源渠道发挥正效应,而对小区内部活动参与呈现出排斥性。小区外部参与更多受制于个体经济社会资源和小区阶层结构,可以看作是居民经济社会地位的溢出效应。三是“行动资源命题”——除了经济和社会资源导致内外参与倾向的“分隔”效应之外,小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公共渠道之间存在“替代”和“补偿”效应。
虽然社区参与所依托的资源具有相互转换的可能性,但不同类型的公共性参与意愿却呈现出相互隔离,说明影响参与动机的不光是行动者的结构性位置,还有激励结构在集体利益和非集体利益领域的分化。在个人获益的参与领域,选择性激励发挥主导作用;在涉及群体利益的外部参与领域,越是在资源结构中处于较低位置的个体,越有“搭便车”的可能性,而在资源方面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的占据者,其选择性参与行为倾向于更高诉求层级,即集体性获益程度更高的行动范畴。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等要素作为嵌入社区公共性参与的结构性限定资源,其存量要转化为社区自组织参与行为,还需要匹配相应的资源条件和激励结构。进一步而言,分化的参与逻辑揭示了个体化转型时期公共性的内在矛盾:市场化导向的利益筛选机制与共同体视域下的公共性理念并存却又相互割裂,个体化导向下公共性的边界需要与多维度、利益多元化的生活世界相调适。基层群众自治所面临的这些新的公共性生长点,有助于对不同社群的公共参与倾向进行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