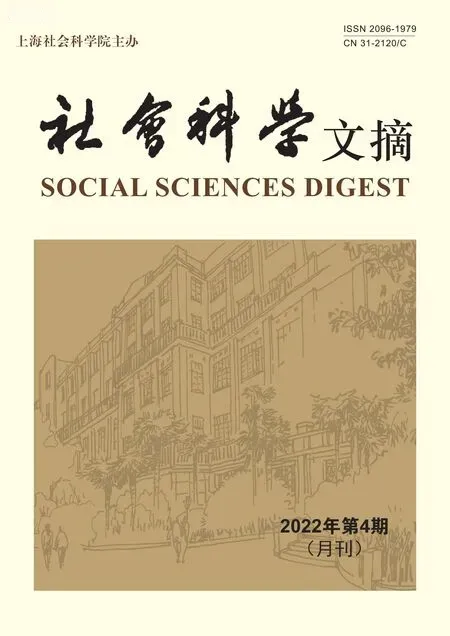“赞天地之化育”与“人是对象性活动”的比较与汇通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的本体论”建构论纲
文/王南湜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摘自《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1期)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哲学层面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而要使这一结合得以深入进行,便须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结合得以可能的契合点。由于本体论在全部哲学之中的基础地位,因此最为重要的便是找到在本体论层面上两种哲学的契合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这种突出人与其周围世界“天地”“赞”“参”互动所构成的“事”的世界视域,可视之为一种“事”的本体论;与之相映照,马克思的“人是对象性活动”之命题,亦将人对自然的生产性之“赞”“参”的关系作为其本体论之第一原理。这两项本体论基本命题在直接语义层面的显著相似,启示着我们思考:这其中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真正深刻的契合点,并由之而探讨是否可通过两种本体论的比较、互释、汇通,进而构造出一种深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的本体论。
“人是对象性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第一原理
与古代及中世纪哲学以超验的终极存在或最高存在为追问对象不同,现代哲学的主导倾向将目光转向了人,以“人是什么”为其总问题。将目光转向人,追问“人是什么”意味着现代哲学不再沉迷于从神或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看世界,而是开始从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及自身。人,在康德这里,相对于绝对的、无限的上帝或自然,其根本特征是具有作为受限的存在的有限性,亦即“有对性”。康德的哲学革命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于主体能动性的弘扬,而必须同时将之理解为对于人的有限性的揭示,因而这种能动性便只能是有限的能动性。但同时,这种有限的能动性指明了人类存在的开放性、未完成性,从而亦表明了人尽管有限却能够自我创造性生成的可能性。
康德哲学所描述的这种有限的能动性虽然是对人类真实处境的真实揭示,但却与西方思想从古代到中世纪关于人在本质上能通过理性或信仰而通达绝对从而在本质上内含无限性的理解,有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在康德之后,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论在其进展中便力图超越康德而消除这种有限性。费尔巴哈的“人是对象性存在”的命题,则是向康德所揭示的人的有限性亦即对象性原则的复归。
马克思接过了费尔巴哈的命题,认为人当然是对象性存在物,但却不是消极地存在于世,而是能动地与对象世界相互作用着。但这种相互作用并不是人作为某种异于自然世界的超验之物而发生的,而是自然世界内部之事。马克思这一“对象性活动”的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其中的关键之处便是,将现实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形态变化发展引入“对象性活动”的内容中。在马克思的世界视域中,我们周围世界被视为纯粹客观的“对象”“物”等,并非如费尔巴哈眼中的那种纯粹的客观之物,而正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之结果,亦即人参与到其中之结果。如果我们把这种由于人的参与才能构成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一种“事”的存在方式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新哲学所体现出来的本体论便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本体论传统的“事”的本体论。
中国哲学“赞天地之化育”的“事”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作为“西学”之一种传入中国,最终能够从众多“西学”中脱颖而出,获得主导性地位,毫无疑问与其能够切中中国社会实际,从而能够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紧密相关。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众多“西学”中为中国思想所选择性地广泛接受,乃由于在深层思想结构的哲学层面,特别是在哲学最基础性的本体论层面有其独特的为中国思想所中意的缘由。这缘由非他,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事”的本体论之间所具有的极为深刻的亲和性。
与西方哲学本体论追问“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则是一种不离现实的人与其世界之关联互动的“事”的世界视域,或“事”的本体论。“事”的本体论意味着中国哲思的世界视域必然是与人及其活动相关的存在,这一视域同西方哲学须是“无人身”的“理性”才能把握的抽象的存在物的世界视域显然是极不相同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事”的本体论思想,初次在《易传》之中得到了明确表达:“《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而《易》之书也被解释为圣者悟道之作:“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一对人在天地之间作用的强调,在《中庸》之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达:“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一以“人道”而“赞”“参”天地之道的“三才之道”,便是周汝昌先生所盛赞不已的“三才主义”:“人是天地的一个精灵的凝结的代表”,“因此,人参天地,共为三才——这是中华文化思想的一大总纲”。
《易传》与《中庸》中的“三才之道”的论述虽然极为简略,但却是一个极富创生性的理论纲领,蕴含着极其广阔的发挥空间。而要将之构成一个本体论体系,尚需创造性的发挥,将其内蕴的至大之“道”充分展现出来。这个“道”的关键之处,乃在于作为天地之生物亦即有限存在物的“人”是如何“赞”“参”于天地之化育的。所谓“赞”“参”者,一方面意味着人虽作为天地之生物但却能够“赞”“参”天地之化育,表明人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通过“赞”而“参”于天地,进而达到人与天地之间的一种新的统一性。如果说人作为天地之生物,乃是被动地从属性地统一于天地,是一种消极的统一性,那么,通过“赞”而“参”于天地,在某种意义上是能动地达致一种积极意义上的统一性。这是说,人与天地之间乃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即从作为原初的天地生物而消极地从属于天地的统一关系,进而通过人对于天地的“赞”“参”之行动,达成一种至少在有限积极意义上的统一关系,并由之而推动了世界变化发展。因此,对这一至大之“道”阐释发挥的关键便在于:如何描绘人与天地之统一性,亦即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以何种方式达成;如何描绘这一“天人相与之际”的关系结构,特别是“天人合一”的实现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之发展变迁,便可看作是对于这一问题描绘或解决的发展变化的历史。
“人是对象性活动”与“赞天地之化育”比较
从上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概要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两者虽然从根本上说同为关于人类世界的本体论,即都持有一种将人对于天地之“赞”“参”或人与其世界的互动视为首要存在的“事”的世界视域,但两者对于“事”的构成的规定却有着重要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涉及中西两种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的传承性影响,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定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匹配的,不同的社会存在方式必然会有与之相应的哲学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从其发生的时的人“赞”“参”天地之化育,到汉代魏晋偏向“天”之宇宙本体论,到隋唐时发展起了心性本体论,再到宋代复又全面回归“三才主义”本体论,这一思想历程何以会发生如此变化呢?缘由恐在于中唐开始的“唐宋变革”,其本质在于门阀世族社会结构的彻底解体,中国社会至宋代成为高度中央集权下的高度平民化的社会,这意味着这一社会结构中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的解放或自主性的增强,从而社会整合以形成社会秩序的方式亦随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个体自主性变化,社会整合需要个体更多的自律或自觉履行。这便是宋明理学回归原始儒家,重新强调人对于天地之“赞”“参”的“三才主义”的社会存在根由。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人是对象性活动”本体论的建立,则处在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存在条件之下,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生产方式并获得大的发展条件下,因而其“事”便必定有着不同的内涵。马克思把握世界的方式,首要的一点便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必须“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而这个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实践”,首先便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活动。
我们看到,两种哲学虽同为关于人类世界的本体论,但在本质性层面存在着差异。
两种本体论的汇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的本体论之建构
前面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事”的本体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概述,已展现出两种本体论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启示我们,应该能够从“事”的本体论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说“人是对象性活动”,即是说人是参与到周围世界之中去的,人的存在方式便是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相互创造,亦即“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对比于前述中国哲学之“三才主义”的“事”的本体论,就如同是说,人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的。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可理解为一种“事”的本体论。反过来说,马克思哲学乃是一种现代的人类学本体论,那么,与之具有亲和性的中国传统哲学亦可以说是一种古代的人类学本体论。这种“同”亦构成了两种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的本体论通过汇通而重建中国哲学“事”的本体论的基本前提。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汇通之目的是重建中国哲学“事”的本体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现代哲学,而两种本体论汇通以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从根本上说就需要“存同纳异”,即保持两种本体论之“同”,并在此基础上吸纳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体现着现代社会之精神的“异”,从而实现中国哲学之现代“生生”。具体说来,就是站在当代中国精神的立场上,回答“人是什么”这一人类学哲学的根本问题。
这一“人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要追问的便是“人能够成为什么”,亦即:“我可以期待什么”。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的回答乃是——“自由王国”中所有人的自由发展;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回答则可以张载的“民胞物与”为代表性答案。“人的自由发展”所针对的乃是以往社会中人的发展受到种种严重限制的“异化”状态,其目标是使人的发展不再受到“异化”了的社会力量的束缚。“民胞物与”所针对的亦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物的间隔状态,这种间隔亦是一种束缚,人处于其中感受到异己力量之压抑,而“民胞物与”之状态则是解除这种束缚、压抑,使人感受到本心自适的状态。就两者都是意指解除异己力量束缚而言,其内涵是类同的。因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便可以“民胞物与”来解读“自由王国”之人的自由发展。
“人的自由发展”与“民胞物与”的理想,都可以作为终极价值准则,进而为回答“我应当做什么”提供前提性奠基。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种价值理想在某种意义上是超时空的,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且一般只限于伦理道德方面;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将“自由王国”之理想放置于为物质生产方式所限定的历史条件下,即“自由王国”作为终极理想若要落实到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中,还须据之而具体化。马克思对于“我应当做什么”的回答中,包含着以物质生产劳动或技术实践改变世界以使之合于价值理想方面的“应当”。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比中国传统哲学的回答更具现实性,因此应该将之吸收进来,也就是将“民胞物与”之价值理想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现实化。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三世”说,可以加以改进,赋予其具体的历史内容,以将终极价值理想具体化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回答“我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原则。
而对于“我能知道什么”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人是对象性活动”的“事”的本体论视域中,则是一个从属于改变世界的技术实践问题。在如何理解现代科学对象的客观性这一问题上,处于前现代科学时代的中国传统哲学自然是欠缺的,因而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吸纳进中国哲学之“事”的本体论中来,使之能够在现代科学条件下合理地回应“我能够认识什么”这一问题。
至此,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是对象性活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赞天地之化育”的“同”与“异”的分析,考查了两者之间汇通与交互吸纳的可能性,提出了一种对于现代哲学之“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式的回答,初步建构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事”的本体论框架。就“事”的本体论存在的可能性空间而言,毫无疑问,这里所揭示出来的还只是一个极为粗糙的轮廓性框架,但也因此而蕴含着能够进一步发展充实自身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生”之德。
——围绕《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若干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