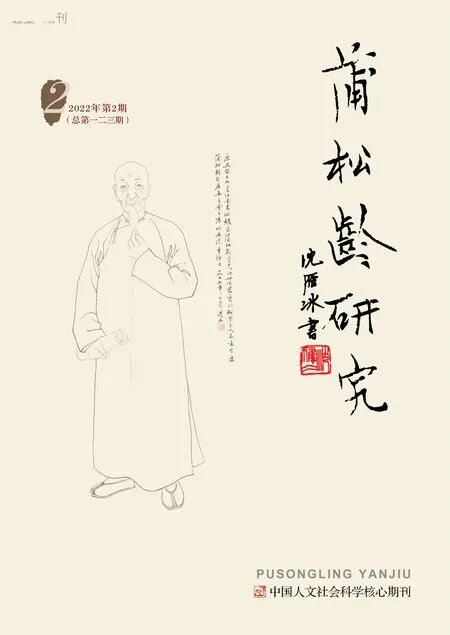当下《聊斋志异》文本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桂奎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主要生活于清代初期的顺治、康熙年间的蒲松龄,虽然长期身居淄川僻壤,身世卑微,饱受落第之痛,却能凭着一腔磊落之才气,引领起传统小说创作的新潮流;凭着天马行空之想象,为清代文学揭开了光辉的新篇章。关于蒲松龄的杰作《聊斋志异》的读法,清代自称“多有会心别解”的评点家冯镇峦曾在《读聊斋杂说》中强调说:“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今天,我们首先仍然要把这部小说当成文章看,既立足于其文本内部,又注意跨越其文本内外,重点看它的美感和深层次意义。为打开研究新局面,原创与互文问题、诗性与史性问题、写梦与写情问题、传奇与传神问题、幻与理问题等几个问题值得特别重视。
一、原创与互文问题
文学创作与阅读,首先要面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原创与互文。所谓“原创”,指的是字字句句皆从肺腑流出,不带模袭痕迹;所谓“互文”,指的是在袭拟前人基础上而赋予文本以新的意蕴。传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文学家常需具备两个条件:“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前者主要助力于“互文”,后者则主要助力于“原创”。以往,我们曾把“行万里路”看成一种身体力行的社会体验,而把“读万卷书”当成是间接的经验。现在看来,无论“读万卷书”也好,“行万里路”也好,对作者来讲,都是一种素养训练,都有助于开阔视野,增强想象力。这两个条件兼具,当然是最好的。但常态是,有的作家偏重“读万卷书”,有的作家偏重“行万里路”。通脱说来,“原创”与“互文”都不是绝对的,具体作家可以作具体分析。
生活的空间、内容可以通过想象来填补。比如,明清时期,很多文人没有出过国,但是却有一些海外想象,《西游记》《镜花缘》等都含有异域想象。就蒲松龄而言,“读万卷书”显然是他的优势,而“行万里路”则是他的不足。蒲松龄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主要靠的是“读万卷书”。说起来,他的生活空间并不广阔,但是他的想象力却非常丰富,可谓海阔天空,这种想象无疑大大丰富了他的小说文本世界。
一个作家的创作意蕴是否丰富,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行万里路”。我们可以做些比较。年龄比蒲松龄稍大一点,跟蒲松龄有密切交往的王士禛,也是山东的大文豪,是当年“神韵派”的领袖。他的人生经历相对较为丰富,曾到过东北和江南,尤其在扬州一待就是五年,按理来说他的诗歌内容应该非常丰富多彩,但由于他在创作中追求以“神韵”为主,诗歌意蕴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丰富。跟蒲松龄同一时代的李渔主要生活在较为广阔的江浙一带,其创作意蕴也并不是那么丰富。蒲松龄的形迹主要是他的家乡淄川,除了因科举考试到过济南十几次,主要的外出活动就是三十岁那年,在好友孙蕙盛情邀请下,一路南行,到江苏宝应县做幕僚。前后不到一年,时间算不上长。此外,他的行迹虽然还到过青岛崂山,但更是短暂的逗留。总体看,蒲松龄的经历并不复杂,没有像苏轼那样“身行万里半天下”,主要凭着读书破万卷、博闻强记、活学活用,创作出内涵丰厚的《聊斋志异》。
身世卑微的蒲松龄是否有“嗜书”情结?答案是肯定的。他喜欢读书,也希望别人像他一样地爱书。这种心迹在小说中有所体现。比如《白秋练》和《刘夫人》两篇作品,分别写商人之子慕蟾宫和廉生,或“聪慧喜读”,或“嗜读”。一面干着生意,一面还不忘读书,即使弃儒为商,还不忘初心,这是蒲松龄别样的人生设想。我们知道,蒲松龄父亲也是一个小商人,他的家庭经历对他的创作是有些影响的,只是他本人没有身体力行。
我们读《聊斋志异》,不时地会从中感到蒲松龄在思考:既然读书清苦,要不要像别人一样弃儒经商,抛弃科举事业,到商场上挣钱养家糊口?他肯定有过这样的思想波动,但最终还是未能像吴敬梓那样弃绝科举。执着而痴迷读书,这是蒲松龄人生中最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他困于场屋、欲罢不能,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但是他坚持屡败屡战。他有诗《寄紫庭》(其一)曰:“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燃。”一次次落榜,一次次死灰复燃,他对功名是那么孜孜以求!有的教科书说他批判科举,根本不符合情理。蒲松龄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不甘心碌碌无为。他善写痴情痴心,也意味着自己就是个痴情人。《阿宝》最后说:“性痴,则其志凝。”有了一片恒心、痴心,才能执着地前行。尽管他是一个科场败者,但其执着精神值得我们敬畏。
蒲松龄爱书如命,我们也可以借他的诗文证明。当年,他设帐教书的主人毕际有刺史去世之后,他曾经写过这样的哀诗:“量可消除天下事,志将读尽世间书。”(《哭毕刺史》)夸说毕刺史气量很大,既能包容别人,又胸怀读遍世间书的志向。当然,这也是蒲松龄自己的夫子自道。他读书的目的除了“雅爱《搜神》”等兴趣爱好,更多是为了功名这一俗务。在小说《小翠》中,他说:“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仙人尽管大多超凡脱俗,但也不免有陷入流俗的一面。另外,他还跟挚友王如水讲自己“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这是借《世说新语》写阮仲容之语传达自己的生存处境。除了《聊斋志异》书名中有个“聊”字,在小说作品之中,我们反复看到作者经常用“聊”字,这个“聊”不是聊天的“聊”,而是一种苟且生存的权宜之计,是“聊慰寂寞”的“聊”。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有一部作品叫《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其实,而今看来,已经消逝的古典灵魂也曾是需要拯救的。在《聊斋志异》中,我们仿佛可以听到蒲松龄发出的阵阵寻求疗救、补救、救助的声音。如此这般,蒲松龄竟然异想天开地把眼前人生的苟且,活脱脱地变成了许多美艳的小说。读《聊斋志异》,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聊”字。当然,除了这个“姑且”“苟且”意义上的“聊”,小说中还不时出现“无聊”这个词。
蒲松龄一生当中,读书非常勤奋,注定跟书结下不解之缘。从一篇名为《书痴》的小说中,我们多多少少地可以嗅到他挥之不去的读书记忆。这篇小说写主人公郎玉柱天天读书,白天晚上都在发愤苦读,无论寒暑都不受影响,可见他读书的努力程度。久而久之,郎玉柱把自己读成了一个书呆子。这里,也许有作者自我反思的意味。天天读书,未免就容易变得呆头呆脑。一旦自己感觉呆了,就幻想着如何救赎。《书痴》中的救赎实施者是一个叫颜如玉的小女子,名字显然来自“书中自有颜如玉”。颜如玉不负期望,通过让郎玉柱参加文艺活动而戒读,最终把他改造成了一个人情练达的社会人。郎玉柱的人生,应该是含有作者自省和反思意味的。
对比《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我们会发现二者的精神境界是不一致的。吴敬梓开始也热衷功名,但经过一番痛苦选择后,决定放弃功名;尽管蒲松龄也曾有过反思,但终于没有放弃功名。他们各自的人生选择并不影响他们各自小说的特色。相对而言,《聊斋志异》比《儒林外史》更接地气,更浪漫,更热烈,与我们的情感、心理距离更近。
为了生存生计,蒲松龄在努力超凡脱俗的同时,又未能免俗。他读得最熟的应该还是应付科举的书。从他创作之中善于将科举应试必备的“四书”“五经”以及时八股文化入到他的作品之中,就可见一斑。本来一些很正经的话语,经他活学活用,便化雅为俗,变得诙谐幽默起来。他的高明在于化用经书而不露痕迹。他也善于将《庄子》《列子》《史记》《李太白集》等“子”“史”“集”方面的典籍化入,这些化入同样非常生动。
当然,蒲松龄最爱的还是那些“旁学杂书”,他善于将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刘义庆的《幽冥录》等散发着秋坟鬼唱气息的小说,以及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等艳情小说顺手拈来,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因而,他的小说大多富有文化底蕴。清代评点家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指出:“故读古书不多,不知《聊斋》之妙。”的确,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很难发掘到《聊斋志异》的深意的,也很难了解其奥妙。反过来讲,要想把握《聊斋志异》的文本之妙,必须要博览群书。
蒲松龄的长处之一,就是注重典故的运用和化用等等。清人舒其锳《聊斋志异跋》有这样一段话:“或又问于余曰:曹雪芹《红楼梦》,此南方人一大手笔,不可与《聊斋》并传?余应之曰:《红楼梦》不过刻画骄奢淫逸,虽无穷生新,然多用北方俗语,非能如《聊斋》之引用经史子集,字字有来历也。”舒氏偏爱《聊斋志异》,认为《聊斋志异》在引用经史方面可能比《红楼梦》做得更多一点。无论如何,读《聊斋志异》,读《红楼梦》,都可增加一些知识,因而在阅读中应该多动动脑子,多想一想,细读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文论中有一种影响深远的“言”“意”之辨,把“言有尽而意无穷”看作为文的最高境界。“意”主要来源于意象,往往具有象征性、双关性、寓意性。基于对传统文献的博约观取,《聊斋志异》得以厚积而薄发,其文本世界富含文化底蕴。我们读每一篇作品,都应注意挖掘它的深意,想象其背后的言外之意、话外之音。如,《莲香》写了一个叫桑生的男性之风流人生。由其“桑”姓,我们可联想到桑梓之地,会联想到一些生动活泼的男女风流故事。由第一女主角“莲香”之“莲”可联想到《西洲曲》“采莲南塘秋”“低头弄莲子”等诗句。再加上第二女主角李氏,合并起来,又自然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连理”意象,有道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李氏跟桑生的交往是通过鞋子传达,鞋子很有灵气。桑生若想见李氏,只要拿着鞋子把玩,李氏就会应约到他面前。从文化上讲,“履”是丝履,“丝”又双关思念。由这些信息,便可见出这场恋情是多么富有文化象征意味。
《聊斋志异》文本的“互文性”创造花样繁多,大多达到了融化而不露痕迹的“化境”高度。后来,又有很多人试图将《聊斋志异》化入到自己文本中,包括《夜谭随录》《夜雨秋灯录》《萤窗异草》等小说,但只能算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往往不到位。这也表明,像《聊斋志异》这样的经典小说已是不可多得,不可超越。
二、诗性与史性问题
《聊斋志异》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其中饱含诗意、诗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蒲松龄自身非但是一个小说家,而且也是个诗人,深得诗道;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善于吸取前辈诗人的诗性精神和诗意精髓。同时,它又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以及其他史书中吸取营养,使得叙事有致,充满史识和才思。
蒲松龄不仅注意脱化屈原、李贺等人的诗,而且还注意借用屈原、李贺天才的想象,并化用他们的诗意创制小说。《聊斋自志》开篇即言:“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所谓“披萝带荔”乃出自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而所谓“牛鬼蛇神”则见于杜牧《李长吉歌诗叙》:“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由此可见,他善于吸取前代那些富有想象力、富有虚荒诞幻感的诗人作品。
除此之外,由于杜甫的儒家风范、婚姻经历都跟蒲松龄有相仿之处,蒲松龄还常引杜甫为隔世知音。杜甫喜欢秋天,有《秋兴八首》等作品;蒲松龄也喜欢秋天,在诗中运用了“秋暮”“秋晚”以及“枫林”等一系列意象。有人曾建言:《聊斋志异》适合秋天读。这是因为《聊斋志异》中的秋气令人感同身受。在婚姻伦理方面,蒲松龄和杜甫都是一夫一妻的模范,杜甫跟杨夫人,蒲松龄跟刘夫人,都是善始善终。与杜甫稍有不同的是,蒲松龄在他想象的天地里,不时会露出一度拥有红颜知己的迹象。也许正是如此,一代多情多才的小说家凭着谋种精神出轨给世人留下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小说兴味。
除了“诗性”十足,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创作中也善于汲取“史性”精神。在《聊斋自志》中,他强调自己的小说“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可见他是在把自己的情感源源不断地寄托在这样一部“孤愤之书”中的。这种创作传统不仅是诗家“发愤以抒情”精神的发扬,而且还是史家“发愤著书”精神的传承。
蒲松龄对史家“发愤著书”的传统始终抱有继承和传承的自觉。在一首题为《十九日得家书感慨,呈孙树百刘孔集》的诗中,他曾经这样表达过:“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垒愁。”这里直称他的《聊斋志异》为“鬼狐史”。虽谓“鬼狐史”,但是故事还是新近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所以他用了“新闻”这个词。他是在用鬼狐故事传达现实人生之感,自然具有史性。
《聊斋志异》创作完成之后,在当时社会上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神韵派”领袖王士禛发现后,非常推崇。还有大才子纪晓岚,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只是他抱有不同看法。根据相关材料,纪晓岚是这样质疑的:“《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这段娓娓道来的言论,被他的弟子盛时彦记录在《阅微草堂笔记跋》中。显然,纪晓岚认为发愤著书,必须讲究严谨,拒绝想象,其立场是“著书者之笔”,故以史家规范刻薄蒲松龄。从我们现在的观念看,《飞燕外传》《会真记》是小说,但纪昀当时把它们看成是一种传记类,而传记类通常是用记史的观念编写的。然而,他又说《太平广记》是“事可类聚,故可并收”,传记类也好,小说类也好,都可以收纳在一起。蒲松龄固然吸取了史家的精神,但毕竟还是懂得小说是“姑妄言之姑听之”的,他把小说、传记混在一起,这是固守史实观念的纪晓岚所无法理解的。
“一书而兼二体”,本是蒲松龄对于小说创作的一大突破和贡献,却不期成为纪晓岚指责的焦点。幸得当时的冯镇峦作了一番辩护:“《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聊斋志异》是传记体叙小说之事,用史传笔法讲小说,虽有弊端,但不这样写,就达不到一种出神入化的高度。这是冯镇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另外,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曾讲,《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是兼具传奇体和志怪体的。其实,无论史稗二体也好,传奇志怪二体也罢,皆可融合的。况且,以叙述婉转、文辞优美的传奇体性笔法写作,比用距离史传笔法更近的志怪,更具优势。为什么人们喜欢读《聊斋志异》甚于喜欢读《阅微草堂笔记》?因为后者太拘谨了,过于拘泥于史的做法。史简约,讲古朴,不讲文采,属于著述者之笔。蒲松龄并没有拘泥于此,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放开想象力,施展才华,因而其《聊斋志异》被称为“才子之笔”,这也是名副其实的。
以往人们谈论文学价值,往往特别看重真实性。而今看来,真情和正理依然很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真”和“实”应该是有所分辨的。文学艺术之“真”应是一个审美术语,并不是史家所追求的信实;而“实”才是史家所谓的“实录”。文的本色以逼真为贵,以仿佛若真为美。尽管蒲松龄惯用写史的形式写小说,但其感人之处主要在于诗家真情与小说传奇因素的注入,而没有落入史家简要的实录。
三、写情与写梦问题
中国文学中漂浮着一场场诡异绮丽的梦,其中的各种美梦令人心驰神往。《红楼梦》以梦为名,大旨谈情,这个“情”当然是广义的,包括各种世态人情,主要是各种人伦常情。其中,梦幻情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戏剧《牡丹亭》之后,小说《红楼梦》之前,文学中写情、写梦的佼佼者当数《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把写梦、写情作为两大重心。
有一种读《聊斋志异》的方法,可以说是史的读法。这种读法就是把小说人物当成真实人物,并希望与他们近距离接触、交流。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作品叫《狐梦》,记录了蒲松龄一个叫毕怡庵朋友,他是把《青凤传》当“史”来读的。这个好朋友,算起来应该和蒲松龄的私塾主人毕际有是叔侄关系。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这个朋友应该是子虚乌有的,且不去管他。且说这个毕怡庵不仅长着大胡子,而且还是大胖子,外表形象很是一般化,但生性多情,爱慕风流,因喜读《青凤》而入迷。读来读去,读成了狐痴,竟信以为真了。朝思暮想,非常渴望能遇到像青凤那样的狐狸精。讲这篇《狐梦》前,需简单地介绍一下《青凤》:故事写狐狸精青凤在叔叔严格管教下,不敢放胆去跟书生耿去病约会,后来还被叔叔强行带走了。次年清明,耿去病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条猎狗追逐两只狐狸,其中一只狐狸就躲到他身下求救。他把它带回家里,这个狐狸就变成了青凤。两人邂逅,喜出望外,便搭伙过日子,享受幸福生活。两年后,青凤的叔叔遭难,托青凤找耿去病救助。耿去病本应怀恨在心,但还是挺身救下叔叔,“由此如家人父子,无复猜忌矣”,实现了两家团圆。在这个故事中,青凤有点淑女气质,并不大胆泼辣,不敢追求爱情,只是机缘之下,才幸运地跟耿去病重新走到一起。按情感基调看,这篇小说应该是蒲松龄较早的作品。《狐梦》写毕怡庵偏偏很向往这个并不野蛮的美女,竟达到“恨不一遇”的地步。估计他喜欢的是青凤的淑女气质。真诚感动下,还真的有狐狸精来了。那是一个暑期的傍晚暮色下,正当他对着门户昏昏然入睡,竟有人将他从梦中晃醒。他一睁眼,发现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风韵犹存,毫不掩饰地自称是狐狸精。见有狐女自己送上门来,毕怡庵免不了要去调戏人家。但这少妇没有应承,而是承诺会带自己刚成年的女儿来。至夜,少妇并没爽约,果然携带女儿来了。少妇简单嘱咐了几句就离开了。女孩子“态度娴婉,旷世无匹”。毕怡庵就与她“握手入帏,款曲备至”,成就了一夜情。小姑娘未等天亮就走了。到了晚上,便熟门熟路自来了,声称大姐要请客,贺新郎。后面就是毕怡庵应邀赴宴,宴会上姐妹们说说笑笑,还搞了一场赌赛喝酒游戏。宴会结束,毕怡庵离席告别,回去以后,猛然醒来,原来是做了一个梦。可“鼻口醺醺,酒气犹浓”。如果是梦,为何口里又酒气熏天呢?这不免令人困惑。还是狐姑娘解释了其中缘故:因为担心毕怡庵,故托此梦,实际上并非梦。故事最后,蒲松龄还不罢休,又交代说“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时间确凿,“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可以看到,作者是在用“史”的笔法来写这场梦的。貌似逼真,其实只是一场梦幻。这就是蒲松龄写情、写梦的游戏笔墨。唐代沈既济《任氏传》篇末曾有这样两句话:“著文章之美,传要眇之情。”强调小说具有以美文传情的功能。戏曲写情、写梦,至《牡丹亭》达到一定高度;小说写情、写梦,至承前启后的《聊斋志异》达到一定高度,再到《红楼梦》方才达到集大成。
《聊斋志异》以写情为本,蒲松龄是基于自身深刻的人生体验而传达人物的深情和真情的。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孤独和寂寞难以排遣,需要疗救。试想,蒲松龄常年在外面做教书先生,夫妻及一家老小难以团聚。夜深人静时分,自然是很孤独的。他创作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聊慰寂寞”。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曾经说过:“知音其难哉!”真正能成为作者的知音是很难的,作者想找到知音也是难的。所以蒲松龄在《聊斋自志》最后不免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是蒲松龄知音难得的一声浩然长叹。
《聊斋志异》世界也写了很多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我们不再细讲,但这样的作品特别有现实意义。为什么蒲松龄一再要争一口气?因为,在现实生活之中,许多人并不是不想超然物外,而是不能超脱;不仅不能超脱,而且还要努力进取争气。《凤仙》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名叫刘赤水的男青年,平日很爱好整洁。后来一次偶然机会,他得到了一个叫凤仙的狐狸精。凤仙姊妹三个,大姐叫八仙,二姐叫水仙。有一次姊妹仨都带着老公给父亲祝寿,但是父亲的表现狠狠刺痛了凤仙。原来,父亲嫌贫爱富,竟当着凤仙的面,拿着真腊国进口的水果给二姐夫丁郎吃,而冷落了她的老公。为的是丁郎有钱有势。凤仙自然很不高兴,就抱怨父亲道:“婿岂以贫富为爱憎耶?”面对女儿的指责,“翁微哂不言”。幸得老大八仙圆场,才避免了一场尴尬。但是凤仙“终不快”,情绪低落地离开了。回来的路上,她就跟老公刘赤水说:“君一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黄金屋自在书中,愿好为之。”告诫他不要天天只是想着臭美,应该以读书为重,书中自有黄金屋,应该为妻子争一口气。凤仙别出心裁,用镜子鼓励丈夫读书。丈夫用功读书,镜子里的凤仙影子就高兴;丈夫一旦读书不用功,镜中凤仙就愁眉苦脸。后来,刘赤水经过励志发奋,终于考中功名,得以扬眉吐气。这个故事也隐约道出了蒲松龄当年为何“未能免俗”的苦衷。
总之,《聊斋志异》写情、写梦,故事多彩,文笔精彩。除了以小说来传情寄梦,蒲松龄也曾在诗词中传情写梦,有一首叫《为友人写梦八十韵》的长诗,写了一场美艳异常、柔情缱绻的男女恋情。赵俪生先生说,这是蒲松龄“先用诗的形式写写试试看,然后再写成小说”,真是不无道理。在《聊斋志异》中,“梦”和“情”常常紧密相连,兼含“情”“梦”之作算来不下百篇,故一时间不胜枚举,只好就此打住。
四、传奇与传神问题
在文学创作种,为了达到某种审美效果,叙事应讲求传奇,写人宜重视传神。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曾有过这样两句断言:“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此可以移之论史书、小说:史书注重“征实”,难于造巧;而小说贵在“传奇”,可通过大胆的想象而引人入胜。在《聊斋志异》这部小说中,蒲松龄凭着奇思妙想、遄飞逸兴、大胆的想象,打破了阴阳两隔,穿越碧落黄泉,冲破了梦里梦外,把各种虚境实象结合在一起。
《聊斋志异》的传奇性,突出表现在时空穿越上。《彭海秋》所叙就是一个关于人物跨越南北的故事,讲述了山东蓬莱书生彭好古和仙家彭海秋之间的情谊。说的是,一年中秋,彭好古孤独过节,他希望能够找一个人陪伴。一时间也没有中意的。这时,碰巧遇到一个姓丘的。尽管这个丘生格调和精神境界不高,经常做一些不上台面的坏事,但眼下彭好古别无选择,只好姑且凑合着与他一起过节。在这种情景下,仙家彭海秋出现了。彭海秋一来,三个人的节日活动就热闹起来。彭海秋先是问莱城有没有名妓。彭好古回答说没有。彭海秋就施展仙术招来了一个,而且声称是从遥远的西湖上找来的。尽管他有能力通过仙术,呼之即来,但毕竟令人好生奇怪。彭好古很惊讶,问他是不是仙人。彭海秋回答说:“仙何敢言,但视万里犹庭户耳。”万里之外不过是比邻相居,真是神乎其神。随后,他们的想法和愿望越来越大胆,竟然想到西湖走一趟。彭海秋便通过仙术,幻化了一条船,载上三人,不一会儿即穿行千里,到了西湖。不用说,西湖上的湖光山色,娇娥佳丽,令三人一饱眼福。当然,我们知道,蒲松龄其实没到过西湖,但是他凭着想象,把西湖的美景写得非常精彩。西湖游玩后,彭海秋又通过仙术搞了一匹马,把彭好古送回了家。彭好古归来,正担心朋友丘生失落,一起去没有一起回,无法对人交代时,竟然发现这匹马就是那个丘生变的。因为丘生人品上有缺陷,仙人就让他变了一回马,算是对他的惩罚。三年后,彭好古来到扬州,又跟中秋那天艳遇的女子娟娘见面了,重续旧缘。这个故事之奇幻,主要表现在时间、空间的穿越上,真令人拍案惊奇。
提起“传奇性”,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明清时期的传奇戏曲,亦即由南戏发展而来的那种戏曲文体。其代表作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这部戏凭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神韵和奇幻,成为一代名剧。《聊斋志异》之传奇,也有不少是属于超越生死恋情方面的。如,《连城》写了乔生与连城之间的生死之恋。对此,王士禛评曰:“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指出它与《牡丹亭》之间的血脉联系。还有些关于幽冥相通的传奇之作,如,《晚霞》这篇作品写的就是一对青年男女是如何在阴曹地府里赢得一场恋情的。
生活本是很琐碎的,并无神奇可言,而蒲松龄善于把庸常的生活传奇化。像《莲香》这样的小说就既富有生活气息,又不乏传奇之感。当然,炫奇谈怪、魔幻荒诞,只不过是小说离奇的表象,并不是传奇的内在规定性。如果小说家一味地奔着故事的怪诞方向去寻求奇幻,那么就会有走向玄幻的风险。传奇一旦走向离奇或玄幻,就会失去艺术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之“传奇”,需要“传神”笔墨来滋补。
我们知道,传神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写人物之笑,写人物之顾盼神飞。这当然是中国的传统写法,比如古老的《诗经》中即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的传神笔墨。《聊斋志异》写人讲究传神性。这种传奇性除了表现在写眼睛方面,还表现在写笑上。这部小说写笑,常借用或化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所谓的“嫣然一笑”一语,真真让人过目不忘。我们知道,《婴宁》是《聊斋志异》中最有名的一篇作品。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善写婴宁各种各样的笑:有“笑容可掬”,有“含笑拈花”,有“嗤嗤笑”,有“笑不可遏”,有“忍笑而立”,还有“大笑”“狂笑欲坠”“微笑而止”“浓笑不顾”“孜孜憨笑”等等。期间,作者还没有忘了点染一笔:“笑处嫣然。”小说的最后,“异史氏曰”赞美道:“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何尝憨耶?”婴宁的笑仿佛无心无肝,天真无邪;而最后却是不再笑了。一方面是社会改变了她,另一方面她又多了几分伦情。作者非常喜欢婴宁这个美女狐狸精,竟然情不自禁地称之为“我婴宁”。
为更好地理解《聊斋志异》世界里的一颦一笑,我们不妨借用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的一个美学观点,即“最富孕育性的那一顷刻”。真正的美往往会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但就是这瞬间一现,却让人刻骨铭心。《聊斋志异》中的一颦一笑常常富有“包孕性”。这种传神之笑,曾出现在《连城》之中。这篇小说写乔生因无法跟自己的红颜知己连城走到一起,便提出了这样一个希望,就是“相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后来,连城做到了,乔生“睨之,女秋波转顾,启齿嫣然”。这个“嫣然一笑”,给故事中的乔生莫大满足,也给故事外的我们以传神之感。这类的传神之笑只可一,不可二,更不可三。如果奢望“三笑”,似乎为的是多多益善,其实反倒是画蛇添足。当然,《聊斋志异》中的这种传神之笑也讲究尺度,这个尺度应该符合《凤仙》等小说所写的“瓠犀微露”那种,牙齿似露非露,否则就沦为其他小说所写的泼妇张口大笑。
《聊斋志异》写人重视传神,服务于一个“美”字。读了这部小说中其他类型的传神情节,我们也会回味无穷。如,《阿绣》写一个小伙子刘子固喜欢杂货铺的美女阿绣,经常借口去买东西,以满足近距离接触的愿望。而且他每次来买东西又从不计较价格。买完东西后,阿绣通常会用纸包装起来,包装后要用唾液粘一下,“刘怀归不敢复动,恐乱其舌痕也”。仅此传神一笔,就让人充分感受到刘子固是多么痴情的。再如,《侠女》写侠女“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有一次一个恶少来调戏她,她很生气,小说写道:“女眉竖颊红,默不一语,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此以“眉竖”二字写侠女气恼,也很传神。由此,我们想到《红楼梦》第十四回写王熙凤生气,也用过“眉立”二字。二者之间有无“互文”关系,可以进一步考察。
《聊斋志异》叙事讲究传奇,写人讲究传神。通过寓传神于传奇,蒲松龄把他的小说写得精彩绝伦。分而言之,传奇性保证的是小说的可读性,传神性则保障了小说的耐读性,二者共同构建起《聊斋志异》小说文本的经典性。
五、幻与理问题
《聊斋志异》叙述了一系列美妙动听的故事,固然带有游戏色彩,但是这不是落脚点。“幻中有理”使得《聊斋志异》艺术生命长青。蒲松龄在《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这首诗中说:“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大意是,我的人生大半是不如意的,讲的这些故事好像是游戏,但其实未必是游戏。游戏背后蕴含着人生道理。这些人生道理用梦的笔法、幻的笔法来表达,属于奇思妙想。虽然属于奇思妙想,但毕竟又有人情、人性、情理支撑。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评曰:“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意愿中。”《聊斋志异》之所以讲鬼怪而让人感觉亲切,主要是因为他笔下人事和百物均符合正常的人情和意愿,讲得在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有这样的赞美:“出于幻域,顿入人间,……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虽然所写花妖狐魅是异物,但均带有人情味。总体说,奇中富于人情,幻中又寓事理,这是《聊斋志异》得以成功的重要秘诀。
明清时期的小说常常存在互相影响的痕迹,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互文性”。有目共睹,《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之间就存在某种程度的“互文性”。如,《西游记》把妖魔当心魔来写,这种观念见于第十三回所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聊斋志异》也说:“幻由人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如果可以将《西游记》中的妖魔解释为心魔的话,那么,也可以视《聊斋志异》世界里的淫心为一种心魔。如,《画壁》写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居京城,偶然进入一间寺庙,看到寺庙里的壁画,“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孝廉注目久视,觉心神恍惚,飘飘如驾云雾,不知不觉就进入画中幻境。蒲松龄对画中幻境的描写是生活化的,很有情趣。后来朱孝廉从幻境中出来,“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作者写入幻出幻,展现了一场场“幻由心生”的故事,这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一种心路历程。这种心路历程重在表达男女之情的乐极生悲,这在《金瓶梅》中也有体现,那里也有《聊斋志异》师法传承的印记。
奇幻的创造是通过跨越和穿越,特别是通过时空的跨越穿越来实现的,再加上幻术、魔术、幻境,《聊斋志异》中的“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梦境就是一种幻境,刚才提到的《狐梦》就写了一种很精彩的梦中幻境。另外《续黄粱》也是写梦幻,旨在写出在幻想的阴曹地府中惩罚贪官,同样写得非常美妙。
幻由心生,意思是“幻”发自人的内心,或叫幻由人生。从《聊斋志异》所写的一些故事,我们可以洞察蒲松龄的心迹。蒲松龄的现实人生是存在不少遗憾或缺憾的,首先是未得金榜题目,早已是他的一块心病。小说《陆判》写助人为乐的陆姓鬼判官与愚笨书生朱尔旦的情谊。有一次,陆判官竟然给朱尔旦换了颗心。换心手术至今看来仍然很难,但陆判官很高明,他安慰朱尔旦说:“勿惧,我为君易慧心耳。”此心一换,朱尔旦第二年果然就考中了。蒲松龄没有考中功名,也许曾认为是因为自己心灵不够灵巧,所以就在这个故事中,传达了一种换心的愿望。小说中的朱尔旦得陇望蜀,竟又提出第二个愿望:“余结发人,下体颇亦不恶,但面目不佳。欲烦君刀斧,何如?”就是说他老婆下半身还可以,上半身不怎么样,麻烦陆判官也做一个手术。陆判官当然有求必应,找个机会就给他老婆换了头。如果从女性主义角度看,这是一场杀戮。但在男权社会里,许多男性只为了妻子的头好看,并不在乎这样的杀戮性的手术。小说最后,蒲松龄现身说法:“陆公者,可谓媸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为岁不远,陵阳陆公犹存乎?尚有灵焉否也?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作者被那位貌相凶恶而心地善良的陆判官的“善举”深深地感动了,并表示愿“为之执鞭”,甘愿效劳。蒲松龄羡慕这些,除了自愧不够聪明,无形之中还道出了自己的另一桩心病:自家夫人固然贤惠,但长相有点对不起观众。
在《聊斋志异》世界里,表象奇幻而内在符合情理的小说还有不少。如,《罗刹海市》,通常认为,这篇小说是在借助叙写主人公马骥航海到如同仙境的罗刹国的奇遇幻境来否定现实。其实不然。我们知道,蒲松龄并没有经商。但他可以设想自己像马骥那样去经商。到另一个国度经商到底是一场怎样的体验?这次经商历险,是蒲松龄的一种心路历程,这种心路历程是很有考验性的,带有挑战性的。这种考验和挑战,是蒲松龄在现实中不可能有的经历。但他可以想象,他可以想象自己长得很漂亮,很有才华,只是在罗刹国那样的地方是阴阳颠倒的,长得漂亮反而被人鄙视,有才华反而被人看不起。后来他到了海市蜃楼,遇到了龙女,与他柔情缱绻,浪漫一场。后来龙女还为他生了孩子。这其实也是一种天真的妄想。马骥与龙女间的恩爱、情意绵绵,不妨视为作者对生活的另一种想象。龙女凭着自己的超凡本领,事先告诉马骥他母亲的寿命,让他做好准备。马骥母亲去世那天,龙女还来吊唁,可见龙女也是人性化了的。最后的“异史氏曰”指出:“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小说与现实人生互相镜照,可以正照,也可以反照。除此之外,小说更重要的意义是,它可以直接映现作者正在走的人生之路,也可以通过想象或梦想,委曲地提供另一种人生选择。现实人生不能假设,小说可以补充这种假设,《罗刹海市》提供了假设蒲松龄经商会遭遇的人生影像,其中也不乏异想天开的梦想。
《聊斋志异》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幻中有理”的小说还有许多,如《画皮》借写幻事蕴含某种美丑之道,《种梨》借写幻术蕴含的惩戒吝啬,等等,皆是理在其中,此竟一度被视为哲理小说,更是不在话下了。关于小说戏曲的“幻境”创造,清代李渔《闲情偶寄·选姿》曾有过这样的探讨:“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毕竟是何情状?岂有踪迹可考,实事可缕陈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传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谱而为法,未有不入闲情三昧者。”在李渔看来,像宋玉《神女赋》、陶渊明《闲情赋》所写的那些美女,皆是出现在幻境中的。惟其以幻写真,才能精彩绝伦。这就是中国文学写人的一种独到境界,也是《聊斋志异》所追去的一种奇妙的审美境界。
在清代文学史上,蒲松龄的贡献是独特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聊斋志异》是原创与互文的结晶,文本之中富有诗情和史性,兼具传奇叙事与传神写人之美,达到了“理”“幻”融会贯通,是一部既善写情又善写梦的杰作。仿佛没有《聊斋志异》的熠熠生辉,便难以有《红楼梦》的精彩辉煌。只有在占有一定的文学积累基础上,才能真正洞晓《聊斋志异》文本之妙。当下,我们应该继续基于已有的文献,以文本发掘为重心,从叙事写人等关键点切入,推动其研究的创新与深化。
(注:本文据2021年12月2日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