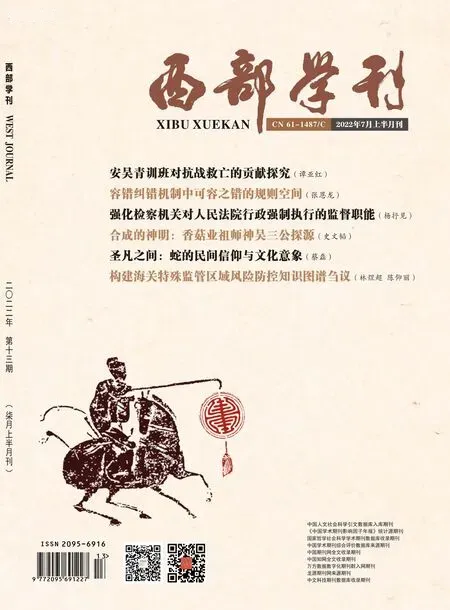南朝家庭伦理思想探颐
陆美贤
伦理是一种品德表现。“文化包括着道德和伦理思想,而伦理思想就是人们的道德生活与道德品质的理论表现。”我国古代的伦理是以品德、德行现象为研究方向的概念,伦理文化是以儒家伦理道德思维为核心的。伦理作为一种文化学说,不仅深刻熏陶着家庭与社会,而且在我国的思想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南朝(公元4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据有江南地区,由汉族建立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统称,上承东晋下启隋朝,共二十四帝,历一百六十九年。南朝社会经历了分裂和朝代更迭、玄学兴起、儒学统治力下降的历程,尽管如此,在以汉人为主体的南朝社会中,儒家伦理依然是社会的主流观念。
一、南朝的伦理观念及风气
家庭伦理是家庭成员相处的道德标准。古代的家族以诸多小家庭构成,家庭主要以父、母、子三种角色构成,因而产生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弟关系等亲属关系,由此而生的家庭伦理思想,即这三种角色的相互关系与道德标准。《孟子·滕文公上》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家庭伦理观念。《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家庭伦理的含义:父慈子孝,兄弟和睦,夫妻和睦,长幼有序。
南朝的儒家道德伦理思想在其混乱、战乱的历史中可见一斑。战争与短暂稳定的反复使得南朝人心浮动,“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社会与政治的变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家庭伦理思想,促使着孝观念的发扬。《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在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孝道作为家庭伦理思想中的首要因素、纲常伦理的基础,因其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功能被统治者赞同认可。
魏晋以来,社会动荡,礼教动摇,上述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开国皇帝无一例外地都是反叛者,可谓不忠,王朝的短暂令人们无处称忠。刘宋末年权臣萧道成辅政,朝野人心浮动。来自琅琊王氏家族的尚书令王僧虔、王延之二人,对此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人们评价他们:“二王持平,不送不迎。”齐明帝废黜皇帝,领着兵马入宫殿,南齐尚书谢瀹却不闻不问,只顾着和客人下棋喝酒。他甚至“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可见这些臣子们对改朝换代态度十分冷静,也全无对王朝或者帝王的忠诚,因此忠这一观念,在南朝时期是相对保守的。
权臣篡位改朝换代之后,难以宣扬忠的观念,为保持政权安稳,又需要属下的忠诚,不忠之人只能以“孝”来装扮自己,因而大肆宣扬孝道、以孝治国,以此强调等级与秩序,根本目的在于以孝求忠。《孝经》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忠与孝,是儒家道德伦理文化的两大内容。《礼记·昏义》:“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孔颖达说:“所以昏礼为礼本者,昏姻得所,则受气纯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则父子亲,忠则朝廷正。”有孝才有忠,有忠才能稳固朝政,而且在儒家的观念中,婚姻是忠孝的一部分,所以历来的统治者都热衷宣扬孝道。
在家庭人伦关系之中,孝顺是极其重要的,婚姻是家庭的前提,两者组成了南朝家庭伦理观念的基础。孝,被认为是维持秩序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孟子说:“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汉朝以来,以孝治天下成了一种重要观念。兵荒马乱的南朝期间,在谋权篡位之后,统治者们亦要开始讲寻孝道,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南齐时代,齐高帝到了华林园,打算去问刘瓛关于为政之道的事情。刘瓛回答:“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可见《孝经》成为治国、为政的重要参考。
《孝经》是古代儒家孝文化的教科书,被各代皇帝、贵族认同推许。南朝时代,讲经在皇室成员与贵族、文人们中很流行。南朝时期,皇帝、储君与贵族亲自讲读《孝经》在史书中并不少见,宣扬《孝经》成了统治阶级发扬、鼓励孝道的重要方法。刘宋时,“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延之同为执经。”“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南齐时,“其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擿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南梁时,“太子性仁孝,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南陈时,“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至德三年,躬出太学讲《孝经》。”皇帝、储君、贵族自发讲读《孝经》,体现了统治阶层对孝道的看重认可,他们利用政治地位加强了孝观念的传播。
因为孝道仁义而免于法律刑罚的例子在南朝时有发生,反映出愚孝、孝大于法的倾向。南齐武帝时期有一太学博士朱异,与朱幼方有世仇,起因是他的祖父朱昭之把已故的妻子尸体埋葬,却被朱幼方放火烧了。朱异的叔父朱谦之为了报仇,长大后谋害朱幼方,然后自首,齐武帝赦免了他。不久之后,朱幼方的儿子朱怿杀了朱谦之报仇。朱异之父、朱谦之的兄弟又因为这件事杀了朱怿。这可谓冤冤相报。“武帝曰:‘此皆是义事,不可问。’悉赦之。吴兴沈顗闻而叹曰:‘弟死于孝,兄殉于义,孝友之节,萃此一门。’”可见朱异一家因孝义得到了称赞与赦免。南梁时期,“李庆绪字孝绪,广汉郪人也。父为人所害,庆绪九岁而孤,为兄所养,日夜号泣,志在复雠。”后来他果真报仇杀了仇人,州府因他的孝顺赦免他,他后来做了太守。
“孝”观念深入人心,不孝之人即便是君主也会被唾弃,甚至被臣子所废。刘宋皇帝刘义符在父亲死后不久便大兴礼乐大肆玩乐,有悖孝道,不堪为人君。“帝梦太后谓曰:‘汝不仁不孝,本无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运祚所及。’”
在统治者推崇“孝”观念的影响下,孝行在普通南朝家庭之中得到推崇,甚至神化。南齐永兴有一王氏孝顺盲女,父亲去世时她在尸体边上哭泣,双目流血,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大家都说是因为她的孝道感动了上天。屠氏女子,父亲是盲人,母亲得了宿疾,她悉心供养。父母去世后,她却听见有人与她说话:“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治病,必得大富。”乡里有人中毒,她前去治病,旁人都说是因为她孝顺得来的能力。南陈时期,陈留尉氏人阮卓的父亲出镇江州时因病去世,阮卓奔赴江州,在彭蠡湖上船舶近乎要被浪打翻。“卓仰天悲号,俄而风息,人皆以为孝感之至焉。”秦郡人吴明彻年幼父母去世,没有钱安葬父母,只能努力耕种田地,但恰逢大旱,禾苗枯竭,他在田地对天哭泣述说自己的苦衷,到了秋天,他的田地就大丰收,得以安葬父母。当时有人预言吴家兄弟安葬父亲时一个乘白马的人会经过坟墓,这是最小的孝子将来大贵的预兆,结果应验。
可见在南朝社会中孝顺成为人性闪光点、良好的社会风气,被人们赞扬乃至神化。
二、南朝的家庭伦理关系
父母、子女两者构成了传统的家庭。《颜氏家训》:“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在传统家庭概念中,一起构成了家庭的主题。《礼记·礼运》:“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中心观念认为,只有父子、兄弟、夫妻三种伦理关系和睦和平,才能成为一个和美的家庭。
(一)父子伦理关系
在家庭关系里,主导因素是父子的伦理关系。“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国有严君。”但是,在南朝的社会与家庭中,女性的社会认可与家庭认可是望尘莫及于男性的:“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与传统观念一样,在家庭中女性是依从于她的丈夫的。《礼记》:“家无二主。”也就是说,在传统观念中,只有父亲、男性大家长才是真正的一家之长,这是家庭伦理关系的首要关系。
《孝经》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可见在古代社会中,父子关系是与君臣之义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政治意义。
父亲作为家长,是家庭权力的掌控者。父亲这一角色,有抚养子女、照顾妻子的义务,而子女则要孝顺父亲。父亲在家庭中对孩子的权力极大,决定儿子、女儿的婚姻,又是他们的教育者。
南朝父亲决定子女婚姻的史载并不少见。经常是某位父亲看中了一位有潜能的青年,就将女儿嫁给他。例如“汝南周弘直重其为人,妻之以女。”“河东裴子野深相赏纳,请以女妻之。”“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谧见而以女妻之。”南刘宋时期人王彧很得宋文帝赏识,宋文帝就做主让儿子娶了他的女儿。“故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也有一对父亲为未出世子女指腹为婚的例子,他们将子女的婚姻看作是一种誓言。“初,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常赡恤之。及为北徐州,时有势族请姻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父母若是去世,则由祖父履行父亲、家长的责任。南梁人何点感念父母之亡故,不愿娶妻,祖父强行为他娶了来自琅琊王氏的妻子。“及长,感家祸,欲绝昏宦,尚之强为娶琅邪王氏。”可见父亲在儿女婚姻的选择上具有决定权,儿女经常不能自主。
父亲是子女的教育者。刘宋时期的文学家张融著有《门律》,告之子弟族人关于成文的写作方法;临死的时候,他曾经告诫自己的儿子。他先是要求儿子通读他的书籍,提出了对儿子的各种要求,有教育的意味。“又戒其子曰:‘手泽存焉,父书不读!况父音情,婉在其韵。吾意不然,别遗尔音。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岂吾天挺,盖不隤家声。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见也。可号哭而看之。’”南梁人周舍幼时聪慧,他的父亲感到奇异,死前告诫儿子应当秉持道德,“汝不患不富贵,但当持之以道德。”周舍长大后博学多通。
南朝的父子关系依然是推崇父慈子孝,迎合统治者对孝、忠的支持,这在史书记载中可见一斑。刘宋时期的孝子潘综与父亲潘骠经历战乱,贼人进入村庄,潘综对贼人下跪叩头求饶过他的父亲,潘骠乞求贼人放过自己的儿子。一贼人于是持刀砍潘父,潘综以身抵挡。另一贼人劝道:“此儿以死救父,云何可杀。杀孝子不祥。”父子才得救了。南朝梁人徐勉的儿子去世,他自言:“宫并降中使,以相慰勖,亲游宾客,毕来吊问,辄恸哭失声,悲不自已,所谓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从来也。”也是慈父之貌。这些记载也反映了南朝人们对父慈子孝、父子和睦情深的向往与认同。
(二)夫妻伦理关系
在家庭伦理文化里,婚姻是非常重要的。《礼记》:“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 “男女有别”“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由此可见,传统观念中妇女的地位是低于男子的,她们出嫁前依从父亲兄长,嫁人后依从丈夫或儿子,这是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阻碍着女子的自由。《礼记·昏义》云:“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代也,故君子重之。”难道婚姻仅仅是男女之爱吗?在古代,婚姻更多的意味着双方家庭的加强联系、结合。对于婚姻,女子也是依从父母的命令、媒妁的意见,难有自己的选择权。《礼记》云:“男女授受不亲。”对男女之间的接触,人们也有礼节上的限制。到了南朝时期,由于多年战乱、社会动荡,儒家伦理的影响渐渐衰落萎靡,对女子的束缚有所减轻,进而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婚姻伦理观念。女子大胆追求爱情,在家庭中,妻子的地位与自由略微上升,而男人我行我素,少有忠贞之行,纳妾蓄养妓女的风气十分流行,有的夫妻之间矛盾重重。
当时有男人好纳姬妾,多则数百人。刘宋人到撝豪富,“宅宇山池,伎妾姿艺,皆穷上品。”他有一爱妾陈玉珠,被宋明帝强行纳去,“爱伎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刘宋南郡王义宣,“义宣多蓄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刘宋人颜师伯,“师伯居权日久,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刘宋人沈庆之,“伎妾十数人,并美容工艺。”南齐人徐君蒨,“颇好声色,侍妾数十。”南齐人张瑰因年纪一大把了还养了许多姬妾被人讥讽,“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者讥其衰暮畜伎。”南梁人曹景宗“好内,伎妾至数百,穷极锦绣。”南梁人鱼弘,“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
与此同时,南朝妇女通过诗文、歌曲与吟唱直白地点明了她们关于爱情的理想与热忱。南梁女诗人沈满愿著《彩毫怨》:“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追求。南梁女子王氏写《连理诗》:“墓前一株柏,连根复并枝。妾心能感木,颓城何足奇。”表达了男女之情的惆怅烦恼,对亡夫的爱恋。南朝民歌《淳于王歌》:“肃肃河中育,育熟须含黄。独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表达女子对爱情的向往。
南齐人徐孝嗣小字遗奴,因为他是遗腹子,父亲被害时,他的母亲已怀孕。他的母亲“欲更行,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无算,又以捣衣杵舂其腰,并服堕胎药,胎更坚。”寡妇不愿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生子,体现了女子自我意识的加强,而不是一味依附男性。
男人如此纵情声色,女人就开始妒忌,于是南朝时期妇女妒悍风气十分盛行。女子的妒悍,表达了妇女在婚姻中自我意识的加强、对女子依从地位的不满、对爱情的独占欲,是这一时期婚姻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常因情以起恨,每传声而妄受。”南梁人张缵如是说。刘宋公主们极其善妒,社会上也有这种嫉妒风气,“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左光禄大夫江湛孙斅当尚世祖女,上乃使人为斅作表让婚。”湖熟令袁慆的妻子因为妒忌惹来了杀身之祸,甚至刘宋皇帝特地以撰写诗文篇章讥讽擅长妒忌的妇人来打击这种风气,也敲打他的公主们。可见女人不再乖顺,她们的妒忌令男人感到烦恼。刘宋的山阴公主告诉她的弟弟宋前废帝,男子可以有数百妻妾,女子却只能守着一个驸马丈夫,认为这并不公平。南齐明帝也厌恶妇人的妒忌,“尚书右丞荣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帝曰:‘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率尔应曰:‘听圣旨。’其夕,遂赐药杀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闻之,赐休妾,敕与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后开小店,使王氏亲卖扫帚皂荚以辱之。”社会风气所致,家庭中的姬妾也有吃醋的情绪。南齐时期,“仲智妾李氏骄妒无礼,珪白太守王敬则杀之。”
可见,虽然这一时期对女子礼教束缚稍有宽松,但南朝依然是男权社会,妒忌之风不能是主流。南梁时期的男人可以肆意蓄妾妓女,女人的妒忌却要遭到反对,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在南朝时期夫妻伦理观念中,夫与妻依然是不平等的,无论是地位还是情感,妻子仍处于弱势。
(三)兄弟伦理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曰:“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兄友弟恭,这是兄弟伦理的基本要求。这意味着哥哥看待弟弟的态度是友爱,弟弟看待哥哥的态度是恭敬。兄长必须做到榜样示范的作用,面对弟弟时友爱仁慈。
南朝期间,兄友弟恭一样被众人推重。南朝历史关于兄弟恭顺的记载,大多是孤儿子弟,兄弟互相帮扶的例子。刘宋时期一位叫谢弘微的官员,他对待兄长就好像对待父亲一样敬爱。“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举世莫及。”江秉之是家中长兄,父母去世后抚育七个弟妹,尽心尽力。“秉之少孤,弟妹七人并幼,抚育姻娶,尽其心力。”檀道济也因侍奉兄姐闻名。“少孤,居丧备礼,奉兄姊以和谨称。”
除了重视父子之孝,南朝时期也十分重视兄弟孝悌,甚至到了为此免惩于律法的地步。蒋恭兄弟被窝藏犯罪亲戚而入狱,哥哥请求赦免弟弟,弟弟请求赦免哥哥。“兄弟二人争求受罪,郡县不能判,依事上详。”州府不仅赦免兄弟二人,还嘉奖了他们的孝悌之行。刘宋时期,孙棘兄弟也是如此,弟弟孙萨没有按期参军应当坐牢,哥哥请求代替弟弟入狱。弟弟不肯:“兄弟少孤,萨三岁失父,一生恃赖,唯在长兄;兄虽可垂愍,有何心处世。”后来这事得到了宋世祖的嘉奖,两兄弟被免于惩罚。
兄弟敦睦成了南朝家庭的一种良性表现,为人父母,也以子弟相亲相爱为善。南梁人徐勉告诫他的长子,做一个兄长不容易,要做到先人后己、内外和谐,“汝既居长,故有此及。凡为人长,殊复不易,当使中外谐缉,人无间言,先物后己,然后可贵。”南朝重视兄弟和睦,兄弟不睦为人不齿,甚至会被惩罚。刘宋人沈演之,“与弟西阳王文学勃忿阋不睦,坐徙始兴郡,勃免官禁锢。”
三、结语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南朝是其中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历经宋、齐、梁、陈四代,短短一百余年,政治混乱,社会不安。这对此时期的家庭伦理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父子天伦、夫妻婚姻伦理、兄弟伦理都在其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发展。父、母、子这三种家庭中的重要角色,在南朝的史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论是男人们丧子的悲恸,子女孝顺父母的传说,或者存在与史书、南北朝诗歌中女人们追求情郎和妒忌丈夫新欢别恋的情感,一直到千年后的现在,也依然为人铭记。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