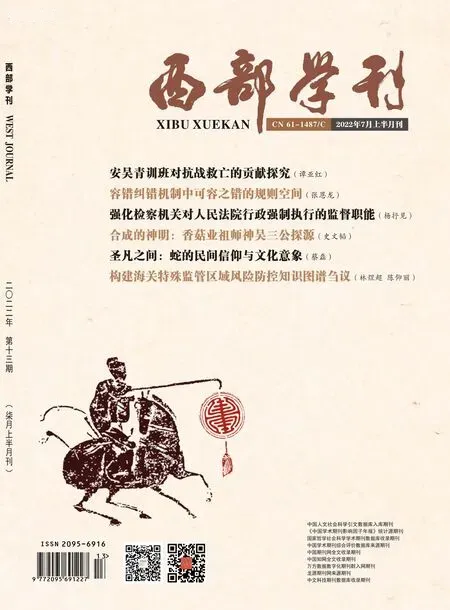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的政治批判探究
——以反牧歌时期的作品为中心
黄 哲
寻求蜕变的反牧歌时期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的文学作品如《我们的时代》《青年的污名》《迟到的青年》《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性的人》中出现了大量露骨的性描写,当时对这一时期大江作品的评价很低,由于滥用过分露骨的“性”用语引起了读者的反感,批评家们批评说很难看出“性”的意图所在。大江是以“性”为手段进行创作尝试的日本第一人,他自创了“政治的人”与“性的人”的对立概念并在小说中进行实践,这一阶段的一系列作品因为手法先行饱受诟病。大江的目标是唤起读者对“性”的“排斥心理”,以排斥为反手,引导读者走向“人类深处的异常”,但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很大。
一、“性”要素是文学创作的手段
从《我们的时代》到《性的人》这一反牧歌时期大江创作最大的特点是大量的性描写,大江说“性”总是伴随悲剧色彩。在《严肃的走钢丝》中的“我们的性世界”一节中,大江列举了有关“性”的具体例子。有一天在神户酒馆里,大江亲眼看到一名从朝鲜战场回来的19岁美国士兵筋疲力尽地靠在木椅背上,凝视着拉开拉链露出的××。这名男子因对战争的恐惧而陷入性障碍,这一场景使大江对“性”这个词产生更深的思考。大江认为战争的恐怖(对被杀的恐怖或对杀戮的恐怖)经常与“性”紧密联系,也就是基于对死亡的恐惧的这种迫切,不仅身体功能紊乱,并且做出丧失人性的行径。
大江说:“从战场回来的有暴露癖的性障碍者,患有性焦躁和战争恐惧症之类的世界性黑暗疾病,让人深切地体会到了人类的悲惨。”受亨利·米勒的影响,大江把“性”作为元素进行创作。“亨利·米勒把他的文学定位于性的快乐、性的阳光的反面,即性的强烈悲剧性,从这一点来看他确实是一位现代作家。对他来说,性行为虽然确实伴随着快乐,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与人类存在背后的深渊相连的苦患。”这是大江在《我们的性世界》中评价亨利·米勒的话。大江将“性”纳入到创作中来,并不是单纯地描写性爱,而是受到亨利·米勒的影响,将“性”与人类社会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此外,在诺曼·梅勒的“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学冒险家留下的未开发之地只有性爱领域”这句话的鼓励下,他对“性与政治(天皇制)”世界的执着,可以说填补了战后的空白区域。黑古一夫指出,在被占领时代和之后的时代除了赞美原子弹和战争之外,一切都可以自由表达,原则上“性”和“天皇(制)”都不是禁忌。然而,关于“性”,日本作家只写了少许具有强烈感官刺激的作品,如田村泰次郎的“肉体之门”为代表的风俗小说,仅仅是风俗小说而已。即使是石原慎太郎描写年轻人淫乱生活的《太阳的季节》和《处刑的房间》,也不能说是以“性”为中心的。在战后相对自由的情况下,大江认识到战后文学最不充分的文学主题是“性”“天皇制”,基于这一认识开始了对“性”和“政治(大江在这阶段文学创作中对政治的考量主要是被美国占领的现实和天皇制)”领域的探索。也就是说,受到战场归来性障碍青年触动,在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的影响下,以及对日本战后文学整体进行考察之后,“性”在大江的创作中成为重要元素出现。
为了体现被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屈辱状态,大江在《人羊》中首次塑造服务外国士兵的妓女形象。在《在看之前便跳》中,他还将外国人、妓女和日本人这三者放在一个构图中,企图从“性”的侧面来把握三者之间的关联。把“性”作为屈辱状况的暗喻,用大江的话来说,在表达中利用想象力活用“性”,也就是“性”是文学创作的手段。
“我想激怒我的读者,唤醒我的读者。然后我想引导生活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进入内心的异常。我采用了‘性’作为方法,我和劳伦斯流派看法不同,劳伦斯认为性本能是人类操纵一切动机和支配潜在意识的动力的唯一源泉。”大江在文库版《我们的时代》的后记中这样说。如上所述,他从《在看之前便跳》到《我们的时代》的过程中确立了“性”作为一种手法的写作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小说中带入了“我们的性世界”,或者可以认为是一部图解的作品——即把已有的理念运用于写作中。以《我们的时代》为展开点,大江利用“性”这一元素展开丰富的想象力。
二、“性的人”和“政治的人”——占领下的抵抗意识
大江大胆地把对个人的认识提高到了对整体日本人的认识。大江创造了“性的人”和“政治的人”的概念,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大江在随笔《我们的性世界》中讲述道:“政治的人与他人进行坚硬、冰冷的对立和抗争,打倒他人或者将他人消解在自己的组织中,让他人主动放弃自己的身份。在与一个他人的战斗中获胜的政治人物在下一个瞬间站在与另一个他人抗争的地方。当一个政治的人逃离与他人对立抗争关系的场合时,他已经不是一个政治的人了。”根据大江的说法,“性的人”不与任何他人对立也不抗争。“性的人”不仅与他人没有强硬冰冷的关系,对“性的人”来说本来就不存在他者。“政治的人”使他人作为对立者存在或作为对立者毁灭,这个围绕着“政治的人”的宇宙充满了他人,到处都是异物。相反,对于“性的人”来说,这个宇宙中既不存在异物,也不存在他人。“性的人”不对立,而是同一的。“政治的人”拒绝“绝对权威者”。当“绝对权威者”开始存在时,“政治的人”的政治功能被压抑,无法发挥其功能。为了与“绝对权威者”一起存在,就要放弃“政治的人”的身份,就必须像雌从属于强大的雄一样作为“性的人”接受“绝对权威者”。也就是说在大江看来,“政治的人”是“雄性”,属于强势的一方,表现为不断抗争;而“性的人”是“雌性,属于弱势一方,表现为不断妥协和依附”。
在国际势力关系中,强大的国家相当于“政治的人”的国家,弱小的国家相当于“性的人”的国家。大江认为现代日本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体制下逐渐成为“性的人”的国家。他认为,现代日本人倾向于认为“政治的人”是极其毫无意义的,满足于天下太平的现状,满足于现代日本社会政治现状享受这种安逸。在这股笼罩现代日本的安逸风潮中,“性的人”的保守满足感给“政治的人”的斗志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大江认为,现代日本是一个强大的雄性美国的从属者,它变成了一个“性的人”的国家,享受现有的和平安逸。大江忧心在日本进步政治运动家面临巨大的障碍。他还指出,日本青年应该注意,在这个“性的人”的国家——现代日本,以“政治的人”为志向的有志青年要防范变成“性的人”。
三、近代天皇制的本质
首先要明确,这里的天皇制指的是从1868年明治维新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这期间的近代天皇制。就在大江的第一次中国之旅(1960年5月)之前,他在《严肃的走钢丝》中的“奉安殿和养雏温室”一章写道:“作为大濑国民学校的学生,我每天早上都被校长用拳头而不是巴掌打。左手支撑在脸颊上,用力打我的另一个脸颊,直到现在我的牙齿还是扭曲的。在奉安殿(供奉着天皇和皇后的照片)礼拜的时候,校长说我不认真就打了我。……日本的农村青年对天皇有特别的敌意吗?当美国二等秘书问我时,我回答说:我最怕校长和天皇……”因为对天皇“御真影”进行礼拜时不认真被校长用拳头殴打,这是大江的真实体验。对着真人就另当别论了,为什么要对照片鞠躬,为什么要因为鞠躬的方式不对而被殴打?从这件事可以窥见大江九至十岁生活的一端,作为孩子的大江本能地发现了天皇作为绝对权威凌驾于人们头上。
在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和1890年帝国教育条例颁布的同时,明治天皇的肖像照片“御真影”被分发到各级教育机构。这一事实说明了“御真影”在强化绝对主义天皇制中所起到的政治作用。大江童年期所在的昭和年代是战争时代,为了培养优秀的“天皇赤子”,“御真影”发挥了巨大威力。那是一个教育领域充满了“征战成为英灵”思想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为什么大江对“御真影”礼拜采取不认真态度?毋庸置疑这意味着大江从小就对天皇制有怀疑。
然而,在大江自传色彩浓厚的作品《迟到的青年》中,描绘了少年时期的“我”在听到战败的广播后仍在想:“天皇陛下,我虽是个孩子,但我可以为你而死的。”这部继《拔牙击仔》《我们的时代》《青年的污名》之后的长篇,是“我”回忆从战败前夕到战后包括初中、高中、大学生活在内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我”的成长史,其中有一段是写少年时期的“我”在国民学校最后一学年战败时的天皇观。来村里做松根油的预科训练人员对“我”说:“战争要结束了,你太小了,赶不上战争了,孩子!”之后,“我”变得有些自暴自弃,用刀刺伤女教师逃跑,“站住,然后回头,如果是天皇的儿子,如果是日本人,就不要逃跑!”“我”听到“来自天际的声音——天皇陛下的声音”回到校舍。然后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不逃跑?因为不再是日本人、不再是天皇的儿子,这比死亡更可怕。我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即使我死了,天皇陛下也会继续活下去。天皇陛下继续活下去,就是我永远不会消失。在老师教我这一点之前我害怕战死,但现在我不再害怕死了。只要是日本人什么都不怕;只要是陛下的孩子什么都不怕。”而且,“我”在听到宣告战败的广播后,也是一个深信“天皇陛下,我虽然是个孩子,但我是为了你而死的”的少年。日本人为什么不怕死而加入战争,这是天皇的恐怖力量,根深蒂固的对天皇的信仰凌驾在个人感情甚至人性之上。
当然,《迟到的青年》中的“我”并不是大江本人。但是,如果追溯《战后世代的印象》《战后一代与宪法》(1964年)等随笔的话,可以认为《迟到的青年》中的“我”是一个有着与少年时期的大江几乎相同经历的人物。只要观照一下战争时期日本对国民的动员情况就会明白,身为皇国少年的大江在战时拥有和《迟到的青年》中的“我”同样的想法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战时教育制度在加强以“现人神”天皇为最高点的国家统合体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教师问道:“喂,怎么样,如果天皇陛下让你去死,你会怎么做?”时,小学生回答说:“我会去死,切腹而死。”
以不认真的态度进行“御真影”礼拜的叛逆少年,还是一个“只要是天皇的孩子,什么都不用害怕”的皇国少年,哪个才是真正的大江?也许可以说这两个故事都讲述了当时大江少年的经历。在没有校长或“御真影”的媒介的情况下,尊皇意识也普遍存在于日本人心中,发动“二·二六”事件的皇道派军官和作为特攻队冲向敌舰的士兵中可以看到尊皇意识,而大江哥哥志愿参加预科训练也体现了尊皇意识。虽然当时大江年幼,但是活在尊皇思想的意识形态之中,然而虽身处其中,但是他对于尊皇思想有着莫名的抵触和清醒。
战后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国占领军带来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就是日本国宪法极大地撼动了大江。例如,读《大江健三郎同时代论文集〈1〉起点》中的文章就知道,从那时起他就把民主思想作为自己生活的基础和创作的根。在采访中他说:“民主是我人生的理想。我反对天皇制,在政治方面我想成为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思想为大江送来了精神食粮,解开了他儿时的困惑,成为创作的根底——批判绝对天皇制。
基于以上创作的根底和原由,从《我们的时代》开始,大江将“性与政治”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来处理,在《性的人》画上了一个句号。在《大江健三郎的世界》中,松原新一这样进行了解析:“《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中的主人公就包含了这种意义上的‘性的人’性格。可以将《我们的时代》中南靖男与赖子的关系与十七岁少年与天皇的关系进行比较,在结构上是类比。在这里,少年是‘雌’,作为‘黄金幻影’的天皇陛下才是强大的雄。少年接受了雄,完美地从属了雄。他与天皇这一绝对者同在,在这一‘绝对者’面前,他的顺从程度终于可以舍弃‘私心’。”确实,在这部《十七岁》中,大江将主人公设定为自渎惯犯,他在实施恐怖行为后被关押的少年鉴别所的单间牢房里自杀时,大江描述了高潮呻吟声:“啊,啊,啊,天皇陛下!啊,啊,啊,天皇啊!啊,啊,啊……”等等,是大江突出对“性与政治”的考虑,使用“性”的元素引起民众或者是读者的广泛关注,根本目的是试图敲醒身处尊皇意识当中而不自知的民众。
大江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各种批评,批评和攻击中也包含着非文学的东西。那时,有批评家把作品中人物和作者思想混为一谈,指责《我们的时代》是一部“新法西斯主义小说”。继《十七岁》之后,大江发表了《政治少年之死》,随之他受到了日本右翼团体的骚扰和威胁。《政治少年之死》是描写右翼少年对“纯粹天皇”的自我认同以及其极致的过激性,并以“性”的寓意提出,因此引起了肤浅的反对。“作为作家,写《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并不是为了直接研究日本的右翼。更本质上,这无非是为了展现在我的印象中,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外部和内部的天皇制具象和抽象的存在。”以上来自大江《作家绝对是反政治的吗?》一文,可以看出,在受到右翼团体的种种骚扰和威胁后,大江决意不惧怕,而是继续通过文学作品暴露和批判普遍深入存在于日本人外部和内部的天皇制。
四、结语
在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的影响下,以及目睹从战场归来的性障碍青年惨状,“性”作为大江先生创作的重要要素登场。同时,大江创造了两个相对的概念,即“政治的人”和“性的人”。“政治的人”与他人僵硬冰冷地对立抗争,相反“性的人”不与任何他人对立抗争。大江认为,现代日本是强大的雄性美国的从属者,它变成了一个“性的人”的国家,安逸享乐。日本被占领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从这里可以看出大江的被占领意识。大江还指出,日本青年应该注意到:在这个“性的人”的国家,“政治的人”要警惕变成“性的人”。大江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不认真对待奉安殿的礼拜被校长用拳头殴打,“御真影”为了培养优秀的“天皇赤子”而存在,可见战时的教育体制中天皇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迟到的青年》中少年认为“只要是天皇的孩子,什么都不用害怕”,这就是战争时代绝对天皇制对日本人思想的毒害,这就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尊皇思想。《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中的少年都是“雌”,作为“黄金幻影”的天皇陛下是“强大的雄”。少年在“绝对者”天皇面前,他的顺从程度终于可以舍弃“私心”。大江通过小说揭露了作为绝对权威凌驾于人们头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