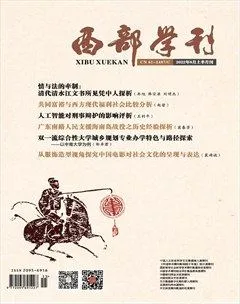破咒:《安提戈涅》的巴特勒式解读
余 薇
《安提戈涅》(Antigone,1956)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KLES)创作的悲剧,讲述了俄狄浦斯的儿子波吕涅克斯为夺皇位攻城,他的兄弟厄忒俄勒克斯为保护城邦与其战斗,兄弟两人双双战死。继位的叔叔克瑞翁下令禁止埋葬反叛者波吕涅克斯,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却违抗禁令掩埋其尸体,最终获死。自此剧诞生以来,理论大师们(如:黑格尔、海德格尔、歌德、德里达、拉康、齐泽克等)对其进行了政治学、心理分析和伦理学、法学等领域的经典阐释。“在‘后学’思潮中”,安提戈涅更是“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典范”。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将安提戈涅当作他者女性的窥镜,试图在性别差异理论框架中构建母系中心系统。西西莉亚·萨让霍姆(CECILIA SJOHOLM)从精神分析视角提出了“安提戈涅情结”。在《安提戈涅》的女性主义批评脉络中,后结构主义大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下简称巴特勒)的解读无疑是令人瞩目的。她对《安提戈涅》的意义重构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根基,却超越了女性主义视域,开启了一场生命政治意义上的追索和叩问。巴特勒的批评主要针对两位男性权威:黑格尔和拉康,她拆解了象征界之法和普遍性原则,质疑了“可活的生命”的规范话语,进而重构了“人”的概念。
一、以法之名
黑格尔认为安提戈涅对抗克瑞翁表征了家族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在《法哲学原理》中,他直接表示:“家礼主要是妇女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同公共的国家法律相对的;这种对立是最高的伦理性的对立,从而也是最高的、悲剧性的对立。”克瑞翁代表建立在普遍法则基础之上新兴的伦理秩序和国家权威,安提戈涅则代表亲缘关系。安提戈涅葬兄表达了亲缘至上的家庭伦理观,黑格尔式解读则认为国家秩序应凌越于亲缘伦理之上。在黑格尔看来,安提戈涅的罪行在于其作为家法的代表杵逆了国法。波吕涅克斯因攻城而成为国家秩序的破坏者,被君王克瑞翁施以曝尸的惩罚。安提戈涅却以亲缘之法为名坚持葬兄。黑格尔和克瑞翁均将国法置于家法之上,而安提戈涅不仅葬兄,还在公共领域公开承认这一行为。依照黑格尔的伦理观,安提戈涅明知故犯地犯下罪行,那么伦理意识就会更加完整,她的过失也会更纯粹。安提戈涅带着清醒的伦理意识犯下罪行,并且不主动承认罪行,其自我意识是反抗律法。
对此,巴特勒以其女性主义者的敏锐性捕捉到安提戈涅在亲缘结构中的模糊位置,并实施反击。首先,安提戈涅并不具备国法认可的家庭身份。作为乱伦行为的后果,安提戈涅的身份不被正常亲缘体系含纳,无法作为家法的代表。讽刺的是,她发表演说借用的是国家政治语汇。也即是说,安提戈涅本身已模糊了家族与国家的界线。其次,克瑞翁以国家之名发号施令,其君王之位却是通过亲缘关系侥幸获取。显然,两个人物的关系无法以简单的家族和国家对立区分。在巴特勒看来,安提戈涅反抗的是规范内的这种二分法。
在国法与家法这组二元对立中,黑格尔认为国法高于家法。这意味着可以牺牲家法,严格地说,是牺牲家庭中的女性利益。当国家宣扬以爱国为荣光,母亲被迫送儿子上战场时,母亲的位置被国家取代,母亲的爱被国家征用。在国家秩序中从未在场的母亲,在家庭结构中又不得不黯然离场。在此,巴特勒批判了黑格尔将女性视为“对共同体永恒的讽刺”。无可否认,安提戈涅彰显了某种男性特质。对于掩埋尸体的行为,安提戈涅的回答是:“我说是我做的,我不否认。”如果以福柯对语言魔性力量的解读作为参照,我说“我说”,意味着我说我在说话,我话中的内容就是我在说话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在“我说”这两个字说完也同时消失。这时,“我说”的客体被悄然悬置甚至抹除,即我说了什么已然不重要,客体是缺席的状态。因此,“我说是我做的”重点不在于是不是“我”做的。安提戈涅巧妙地模糊了掩埋尸体的事实,突显的是正在说话的主体“我”。换言之,不管安提戈涅做了与否,也不管她说了什么,这里被强调的是她在公共领域言说这一行为。巴特勒亦从修辞学含义解析了安提戈涅这一回答。她指出“我不否认”与“我说是我做的”含义不同,“我说是我做的”暗指一个“他者权力赋权于安提戈涅”,表明她并非被迫承认埋尸行为,而是主动认领这一行为。安提戈涅因此被视为拥有某种男子气概。巴特勒得出结论:安提戈涅超越了性别界线。那么,作为“妇女的法律”的家法也已经不适用于安提戈涅,她无法作为家法的代表。此外,巴特勒也认为安提戈涅只是以家兄的名义对抗法律,她的坚持仅指向家兄,而非家族中的每一成员。因此,安提戈涅不具备家神代表的普遍性。
拉康把亲缘关系限定在象征界意义上,使亲缘依循象征界之法。由于象征界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结构,其形式不轻易改变。在象征界中占据某个位置意味着只能产生某种亲缘关系,且这些位置代表正常的关系。由于俄狄浦斯情结被视为由“具有象征意义的乱伦禁忌中派生出来的”,因此,象征界也成为“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用来调整欲望的法则”。换言之,象征界代表着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以此形塑正常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的边界由欲望标注。而安提戈涅对其哥哥的欲望显然触碰了亲缘关系的边界,因而必须被象征界除名,以法之名。安提戈涅因为公开哀悼哥哥而被视为罪犯,亦是以法之名。但是,巴特勒用象征界语言符号的模糊性颠覆了象征界法律的确定性。法令禁止的是对波吕涅克斯的哀悼,而安提戈涅坚持公开哀悼她的哥哥。但事实上,乱伦后代的身份导致她的父亲同时也是她的哥哥。对于安提戈涅而言,“哥哥”这一象征界位置指向不止一个个体,安提戈涅偏离了象征界固化的位置,代表的是血缘的变形和位移。这种含混和偏离消解了象征界之法的确定性。因此,关于哀悼的禁令就变成了抛开公共律法的权威而被独立推行的“非法”。
二、普遍性原则
早在讨论《安提戈涅》之前,黑格尔就认为男性代表基于普遍性原则的国法、人律,可以作为伦理意识的主体,女性则是家法、神律的代名词。由此看来,黑格尔早已预设了安提戈涅无法成为伦理意识的主体,她同时也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以外。对于安提戈涅发表的公共演说,黑格尔这样表述:“女性……竟然以诡计把政府的公共目的改变为一种私人目的”。巴特勒抓住了黑格尔论辩中似乎无处不在的男权主义论调,她指出,在黑格尔鉴定完安提戈涅反抗律法的真实自我之后,他隐去安提戈涅的名字,将其泛化为普遍意义上的女性。不仅如此,黑格尔也无视安提戈涅的特殊性。事实上,作为乱伦行为的后代,安提戈涅的父亲即是兄弟。而由于对流放的父亲俄狄浦斯的忠诚,安提戈涅更是被父亲视为儿子。由此,安提戈涅成了俄狄浦斯的女儿、儿子、妹妹。在象征界中,她实际上占据了不止一个位置,偏离了象征界所定义的正常亲缘关系。然而在黑格尔的表述中,安提戈涅成为了女性特征的代言,仅仅是一个“把国家公共财物变为家庭私有财产”的人。通过以普遍性替换特殊性,黑格尔将安提戈涅所对抗的“女性”概念加诸她身上,从而使安提戈涅发表演说的行为不再具有政治意涵。
拉康的象征界秩序由普遍性表征。象征界的结构,即俄狄浦斯情结,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偶然性。巴特勒认为尽管象征界理论代替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缘关系论,却没有步出普遍性权威的框架。俄狄浦斯情结成为象征界的结构并非因为有大量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相反,往往因为无任何“先验性实例”佐证的普遍性形式的存在,某些现象才具有普遍性。象征界的问题在于一个象征符号并非一定对应一个普遍性。往往正是因为普遍性发挥作用,才出现俄狄浦斯情结。换言之,这种“不依赖于实例”的普遍性原则可以使任何偶然存在成为普遍事实,因为没有一个例外质疑其普遍性。如果普遍性受制于无大量实例的证实,那么偶然性也必然困囿于无大量实例证实其存在是偶然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普遍性原则甚至具有偶然性本质。乱伦禁忌作为偶然性出现后并没有消除,而是获得了一个普遍性形式留存下来,这种普遍性恰好证明了其自身“无根无缘”的偶然性特征。由此看来,任何作为普遍性存在的规范都是“不依赖于实例”的偶然性,因而显得虚无缥缈。
三、“诅咒是一种异常的重复”
在拉康的理论中,象征界结构是一种俄狄浦斯情结,象征界的规则是被父亲的话语所激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父亲的诅咒代表着象征界的秩序。他以安提戈涅为表征,证明了一旦违背象征界之法,将被父亲诅咒,被象征界除名。巴特勒破除对父亲诅咒的拉康式迷信的方法是,她指出了作为一种言语,诅咒是如何转化为行动的。她通过索福克勒斯对两个故事发生顺序的倒置说明诅咒可被理解为一种预言。以安提戈涅为例,巴特勒得出:预言是“一种言语行为”,因为语言会激发行动,并“不断重复,不断激发”。“语词或能指在空白的空间里建构起真实界,使之充满了规范和表演的力量。”主体在传递话语符号的过程中,不仅重复还加强了其效力。这样,前人流传下来的话语被不断推进和强化。到此,巴特勒已十分接近其批判的核心:规范就是以言语行为的方式产生效力。但由于诅咒或预言的历史无法还原,因此在源头对其进行解构的方法并不可取。巴特勒转而提出在以异常形式传递规范的过程中暴露规范的弱点,在重构规则的过程中背离规则。乱伦禁忌正是以此方式在异性恋家庭的基础上将亲缘关系合法化和常态化。这种牢固的亲缘关系准则“支持了我们关于文化认可的持久理念”。正因此,其背后的父亲的法律“限制了社会形式的可变性”。当代亲缘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在将种族、奴隶制历史等因素纳入考量后提出应该以“被承认的家庭关系”取代“以血亲作为亲缘关系的基础”。
四、“人”的概念:关于“可活的生命”的诉求
黑格尔的伦理意识观将安提戈涅标注为有意识的犯罪主体,他认为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注定招致死亡。对于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君王权威和国家秩序的逆鳞,黑格尔不仅接受其死亡收场,甚至“引导她……走向她的墓穴”。换言之,在黑格尔看来,死亡是安提戈涅应受的惩罚。但拉康看到了安提戈涅行动中的死亡欲望,安提戈涅试图求助诸神的行为是在寻求超越象征界的帮助,她求助于死亡并试图“引用死亡的授权”。在死亡欲望的驱动下她“跨越了人类能够跨越的界线”,而这一界线甚至是她自己划定的。因此,在拉康的分析中,安提戈涅的死亡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是向死亡的主动靠近。巴特勒将安提戈涅的位置界定在“生死的摇摆不定的边界上”。安提戈涅所用的语言使她的希望发生褶曲,她的言语偏离了她的意图。再加上从没消散的父亲的诅咒,她的行为带着无意识,也因此她虽活着,却已然死去。安提戈涅的诉求所指向的象征界建构了“可活的生命”概念,正是这一概念将安提戈涅推向生存的边界。可见,在巴特勒这里,将安提戈涅迫出边界的是象征界持久却“无根无缘”的普遍性规范,她的死亡是象征界法律的宰制。当巴特勒指出安提戈涅与城邦首领的矛盾焦点在于该不该公开哀悼波吕涅克斯时,巴特勒实际上也在与黑格尔和拉康据理力争:难道安提戈涅不值得被哀悼?巴特勒甚至在与文化决策者叫板:哪种人类的死是真正值得哀悼的?
乱伦禁忌没能阻止俄狄浦斯与母亲相爱,并预先阻止了安提戈涅生命中一切可能产生的爱。这说明,乱伦禁忌存在与否,人性中最本真的爱都不可磨灭,而乱伦禁忌可能仅仅阻止了并非乱伦的爱。那么它的合法性是否应受质疑?拉康注意到了安提戈涅所依傍的另一种律法——诸神的法,一种“未被写下的法律和无法写下的法律”。如果正如黑格尔所说,安提戈涅代表神律,而神律是“未被写下的法律”,而依照拉康的理论,“未被写下的法律”标注了象征界的边界,那么也就是说,安提戈涅代表的是象征界的边界。她停留在象征界的边界上,被标注为不合法的存在形式,“既没有死去也不算活着……在人性的边缘处于非人的状态。”
一个国家中不被当作合法群体中的生命、不被准许获得人的资格的人越来越多。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模糊领域”也指向这群“由于规则的不成形的界限”“滞留在存在边缘”的人。安提戈涅恰恰是以这样一种“非人”的形象直击法律框架之内的“人”的概念。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在“非人”境况中的言说和行动表达了成为“人”的诉求,其必将使不被文化认可的他异性存在成为“前所未有的未来的社会形式”。
五、结语
巴特勒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父权话语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和拉康,指出安提戈涅从来就不曾在国家认可的亲缘关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从未踏入象征界的秩序中。安提戈涅作为人类最高层级的他者欲望并不具有普遍性,也无法代表国家认可的常态亲缘关系。但与其说安提戈涅是女性主义理论凝视下的悲剧英雄,不如说她是巴特勒后结构主义视域下以“生命多样性”为诉求的战斗者。巴特勒将她对人性的思考嵌入最激烈的女性主义理论平台中。在巴特勒看来,安提戈涅的“致命性超越了她的生命,带着无限的希望进入了诉求承认话语的范围,是变异的和前所未有的未来的社会形式”。安提戈涅的悲剧揭橥了文化承认的局限性,因此巴特勒实际上思考的是如何使其他生命样态也进入“承认话语”的范围以避免悲剧。或许可以说,透过巴特勒的性别讨论,我们得以管窥打破文化承认局限性的生命的多元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