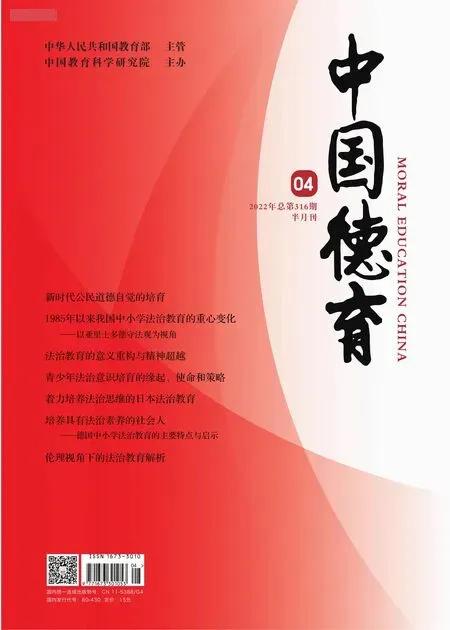法治教育的意义重构与精神超越
■ 翟毅斌
当一个孩子说“这玩具是我的”,这反映了隐含的产权法思想;或是“你答应过我,怎能耍赖”,这反映了隐含的契约法思想;或是“他插队,他是排在我后面的”,这反映了隐含的侵权法思想……既然每个孩子的心智里都潜藏了法治的意识和情感,那么每个孩子对于法治都该有一种必然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是秩序的启蒙,也是正义的探求。
一、公道关系的启蒙
社会成型以前,在自然法的统治下,人们关心的是怎么活着,想着如何续命、寻找食物,在保存自我的同时不去伤害他人。而当社会建立以后,人与人之间原本在自然状态中的平等消失了,人开始有了攻击和自卫的理由,有了个体间的敌对状态。于是出现失范的行为,而每个人又都以自己的偏爱去解决冲突,导致争端四起。为避免这种恶化,就需要基于共同体的善来制定和执行必要的法律,以最大程度上保护人的生命和利益。换句话说,是社会让人失掉了平等,而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恢复。
可见,在人为法律建立公道关系之前,就已经有了公道关系的可能性存在,所以,法治教育实则是一种公道关系的追溯。如果一个孩子被人撞了,那么对他来说,他会在意对方是不是故意的。即使撞得很轻,可若是故意的,那也大大不同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无疑,道德评价会受到这种差别的影响。这种人性内隐了公道关系的争持和法治的情感需求。因此,法治教育旨在将每个学生的行为差别里嵌入平等之思,这不仅构成了道德生活的基础,还充斥着他们的整个社会网络。
二、从一般性规则出发
法治教育并不针对某个特定的具体事实,而是关于一般性的正当行为规则,以应对我们周遭的环境。法治考虑共同体及其抽象的行为,而不考虑个别的人及具体的行为,有些事是以人们不可预见的方式发生变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大社会之整体活动秩序立基于其上的所有的特定事实”。也就是说,人们无力预见某件事的未来,人们只是假定法治能够平等待人。正是这种对未来的无力预见,使得人们愿意将法治作为一种生存手段、一种合作方法、一种普世性的规范科学。例如,在疫情的高峰期,人们永远不可能就谁应当首先得到医治而达成共识;但是人们都觉得,如果医生遵从某种高效率的法治秩序给大家看病,这对大家都有利。当人们明白这个道理后就容易达成共识,所以法治提供的是一种手段,服务于无数大众的不同目的,而不服务于任何特定的单个目的。在服务于多种目的的工具中,法律很可能是继语言之后又一个有助于人类实现多种目的的工具。所以法治教育从一般性规则出发,是一般性知识的引导,而不是对特定的具体事件进行确定。从一般性规则出发,意味着“社会成了仲裁人,用明确不变的法规来公正地和同等地对待一切当事人”。法治教育必然指涉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学生通过学习既定而公开的法律,促进普遍正义的交互性,法律进而成了学生社会性结合的条件。
法治教育能否在学生那里产生权威、使其信服,取决于学生是否将自己视为所要服从的法律的创制者,否则,形式合法性就失去了其正统性。若想通过法治教育引导学生的行为,就必须让学生成为民主的参与者。由此,法治教育的内容可作学情化、日常化处理,比如让学生学习和解读法律,以此为基准,对照着修订出符合自身生活需要的具体规则,即哈耶克所说的一种“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运用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规划他们的行动,从而强化个人自治和尊严。
三、增进预期的确定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稳定的预期,只有在比较稳定的预期下,社会才能正常运作,即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总是建立在我们认为比较靠谱的预期之上的。法治意味着求秩序、求稳定,意味着一种保守的社会力量。法治的这种效用,在许多领域保障着这个社会不会突然地改换模样,以致失去我们赋予的意义。这么看来,法律只不过在保障着、伴随着、矫正着自然关系而已。伴随教育实践的不断创新,不同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学生们已经迫不及待又自然而然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骤变之中。法治教育并不是要培养整齐划一的纪律主义者,更不是把实践智慧视为糟粕,而是要在尊重学生创造力的同时,限制非理性的肆意行为,让学生在价值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建立起稳定的社会预期,以习惯法治社会的生活,发展稳定的社会人格。
在法治教育中,主要的学习内容是对不正当行为的禁令,是一种否定性的规则。因为规则必须适用于未知其数的未来情势,以一种否定性来预防非正义,是对可确定的领域提供保护,进而保护人的合法预期。相反,若用肯定性的一般性规则来规定具体由谁来承担一项义务,比如去扶助摔倒的老人,或去见义勇为,是很困难的。此外,法治教育并不完全根除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只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机遇。从知识、情感、技能上,帮助学生看清事物的真相,有时还得看到事物所呈现的假象,并能以遥远的忧患来制衡当前,帮助学生保持一个较稳定的社会预期,以作好步入社会的思想准备。
四、借助儿童的风俗
在没有法治的日子里,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总会形成一些风俗习惯,有时也起到了法治的作用。在较为简单的社会里,这些风俗习惯甚至比成文的法律更有效。真正的法治社会是用法律去改革法律所建立的东西,用风俗去改变风俗所确定的东西。儿童也有自己的“风俗”,比如不节制、不约束自己,也常常意识不到规范的存在,这些自然原始的激情,形成了非常规的儿童“风俗”。法治教育绝不可用法律去硬改风俗,而要引导人们自己去改变,其实用温和的手段一样能达到目的。风俗随从法律,是因为人们常常缺乏足够的公道心和判断力,所以要让每个人的生活里充溢法治,才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好风俗和好性格的养成。法律随从风俗,则是为了利用风俗促进社会的成熟。风俗就是儿童的生长史,是他们的传统意识,应将此作为现代法治教育的延续性力量,用法治教育串联起儿童的生活。
除了共同的道德准则之外,每个地方都有一些特殊性,使其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有些民族生来就能服从法律,而有些民族等上千年之久也还是做不到,所以柏拉图拒绝为阿加狄亚人和昔兰尼人制定法律,他知道这两个民族习惯了富有,不能够忍受平等。如果法治教育与本土的风俗不协调,就需要更多的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有人不理解法治教育为何可以围绕地方课程来开展,只有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时,我们才恍然,原来法治应便利于人的当下行为,而不是给生活添麻烦。法治不该是纯粹的权力作用,而是应需而生,即适用于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群。法治教育可以从地方性知识入手,密切结合自然与政治环境,如气候、土壤、宗教、政体、人口、生活习性等,以生动平易的方式唤起学生的法治兴趣、道德观念,由此才能打破法治教育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和生硬的教义形象。
五、体验超理性价值
法治的确促进了理性化,为社会提供维持其内部团结所需要的构型,更以其稳定性制约着未来。可人们常常用世俗理性的模式来认识现代法律的特征,把法律视为无情的规则、履职的机器,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人们依法行事,计算行为后果,权衡彼此的利益,而后一味任用理智,压抑爱和信仰,故而轻视了法律被置于其中的语境,更忽略了法律中某些超越了理性的要素。当情感生命力枯竭,法律也将褪色为僵枯的法条。其实,在法律与各种事物的种种关系之中,暗藏着法的精神。例如,古时的中国,妇女生育力强,人口繁衍快,在有限的土地上,无论怎样开垦,都只能勉强维生,以至于人的生计很不稳定,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使老百姓普遍从事农业,以保障各自的温饱。在这种情况下,奢侈是危险且有害的,所以中国历来就有关于节俭的传统法律,鼓励人的勤勉,以预防由奢侈衍生出的更为麻烦的人祸,甚至有的皇帝会出席每年一次的亲耕仪式。可见,勤劳便是中国古代法所必然孕育的风俗。相反,在英国,农作物的供应量绰绰有余,所以会出现一些无关温饱的享乐型工艺,人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宽裕些,故而英国就没有源自法的勤俭精神。又比如,秦法曾明确规定了伐木、采撷、捕猎的具体时间以及行为标准,如不允许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也不允许捕捉幼小的禽兽等,这是敬畏自然的古老生态文明的体现。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内容,更是生活意义的建构,因其象征性的符号语言,它不只是工具理性的厮守,还暗藏着超越理性的价值信仰。法治教育不只是“公意”的传递,还应集合真善美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温情,使学生在法治学习中采撷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美德精神,从而体验法律的超理性精神。
让学生信奉法律,其信念感与归属感等因素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若不能指涉对人的终极关切,难道我们处处都要依仗着警察和监控?即使斯大林曾凭借一些暴力威胁的手段来统治国家,但他仍然把“社会主义合法性”奉为得民心的依据,还试图让人们相信苏维埃法的正义性。所以,法治教育需要建立守法的行为传统,这种传统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赋予法治教育这种超理性的价值,并且由此强化学生的法律情感,还可有以下几种教育方式。一是树立权威感。法律本身所固有的合乎人性和社会秩序的道德要求,是一种“必须服从”的硬气和拘束力,社会是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的。作为一种秩序,法治教育仍要以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学生不会去信仰可随意亵渎的法治。二是法律的仪式感。像宗教一样,让人体验仪节程序的庄严价值,使得法律的正义理念被戏剧化处理,如模拟法庭的严格出场顺序、肃穆的宣誓形式等等,借公开仪式将法治观念和道德义务提升为一种集体信仰,然后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使自己的个性服从于这种“程序形式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构筑逻辑和虔诚,进而营造法律的神圣,唤起学生充满敬畏之情的尊崇。三是礼的吸收。古代圣贤确立了崇高的礼,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约束和管治着人伦秩序,好像一种未成文的法,既保证群体组织的秩序稳定,又为生命增添诗意和审美。相比之下,法虽然功效立见,却被认为是由节制的机械规则组成的,并非根源于人的真性情。于是,“以礼为尊”“礼重于法”是中国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其实,儒家的“礼”正是一种广义的法。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算是道德。这种最广泛的利益的规则,用以维持人民内部的良好秩序,消灭由暴戾性情所产生的邪恶,使人民能够平静而温厚地生活。也就是说,“礼”早已入于法,成为传统法治教育的核心。即便如此,也并没有妨碍中国在近代借鉴法庭、法典等西方模式来发展自身的现代法治。所以,吸收“礼”的特质,必能成为中国特色法治教育的人文跃迁。法治侧重于调整人的行为,只有在行为造成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我们才去考虑其精神层面,而礼法思想要求的是人们由内而外的自律,发扬内在善行,同时也强调外在教化,即在礼的人情关怀之外,辅以法的惩戒作用,可使外在调整与内在调整有机结合。礼法交融为法治教育提供了独具一格的中国方案。
合法或非法,关系道德上的正当和错误,我们诉诸法治教育,为了正义取代本能,为了在听从欲望之前先请教自己的理性,即使被剥落了自然的些许便利,我们也获得了道德的发展、思想的开阔、灵魂的强劲,从而沉淀出秩序良好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