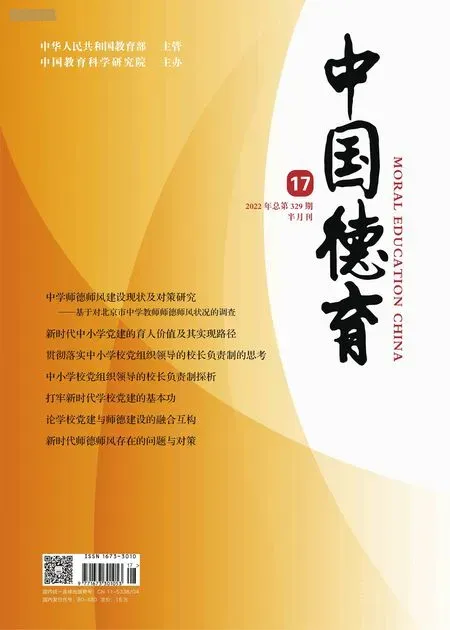论韩愈的“为师之道”及当代启思
■ 戴红宇
韩愈的师道思想对宋代以后儒学教育的发展和我国儒家师道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钱穆就提出:“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师道在广义上包括了为师之道、从师之道、尊师之道,师道尊严的出发点是尊师重师;狭义上则主要指为师之道,师道尊严的出发点是教师的自尊自重。狭义上的师道与师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作为‘师德’价值前提的‘道’,是指同教师履行职能相关的、正当的、不可或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尺度,只有得到舆论与个人良心的支持,才能成为衡量教师职业行为的道德标准”。换言之,师道是师德形成必不可少的价值前提。
在我国教育传统中,师道代表着对教师责任的理想认识,“师道就是人类以社会历史文化成果教育、陶冶、塑造新生一代个体以促进其成长和发展的自我生产、自我化育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绝不仅是知识的传递与再生产过程,也包含着社会道德的传递与生产过程,二者共同构成教育之于学生社会化的作用。如果说现有的高校师德建设更多是借助外部的培训机制和评价机制对教师的师德表现进行引导和约束,那么韩愈提出和坚守的“为师之道”则是在“耻师”的社会风气、缺乏足够的外部引导与约束的条件下的自我道德建设,体现的是教师的文化使命与道德担当。考诸韩愈的师道思想,在强调“以德育德”的当下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韩愈“为师之道”的提出背景
韩愈在“今之世不闻有一师,有则哗笑之,以为狂人”的社会背景下,提出基于儒学的师道思想。柳宗元称赞:“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而抗颜而为师。”韩愈的师道思想阐释了师与道、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而基于这两对关系,亦能进一步明确“耻师”之风的社会背景。
(一)社会变迁的知识适用问题
韩愈提出“师道之不存也久矣”,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和唐代的佛教禅宗事实上就很重视“师承”关系,严肃“师道”以确保教义的正统性和权威性。由此观之,普遍意义上的“师”和“师道”并没有中断。真正陷入困境的毋宁说是儒学由于经义发展的停滞,而无法有效地指导社会生活。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正统性一再受到挑战,儒学的理论威严也随之沉沦。佛道思想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的、最富生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与之相对的则是“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世人借由佛道寻求精神的寄托和生活的继续,而儒学则由于对社会变迁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控制力,产生了知识不适用的问题,失去了教育上的吸引力。
知识往往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传统的文化知识尤为如此。一家之言之所以成为教育的内容,更多是基于人们相信其能够指导具体的社会生活,可以作为社会生活的伦理依据。在相对封闭又变化缓慢的古代社会,传统经验还能够保持内容的适用性,获得人们的教育认同;而一旦社会变化较为剧烈,在带来思想碰撞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先前占据主导位置的教育内容不再具有标准性,东周的“天子失官”、晚清的“中体西用”都是这一情况的体现。汉代形成的家法师守使得儒家教育拘泥于章句,偏重于“回到过去”的解释,而这无疑使儒学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创新力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阐释能力。《学记》基于儒家正统的立场提出“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换而言之,便是道不尊则民不敬学。中唐之际,世道陵迟,不仅是学校教育式微,而且是儒学从广义的教化上对“道”的代表能力的式微,即其所蕴含的教育内容在安顿人心、指导人生上不如佛、道两家的学说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那些对儒家学说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士人以外,也就很难有“求师问道”了。儒家之“道”的现实危机恰恰又进一步导致了“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儒师依附于儒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儒家的师道传统要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同,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需要更新儒家的教育内容、教育学说,对“道”进行更具现实性的解释,从而吸引学生,为“师道”寻求现实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二)官僚体制的教师身份问题
唐代官学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另一面是将官学中的教师身份与行政体系中的官僚身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担任祭酒、司业、博士等学官,往往只是其仕途短暂的一站,甚或只是兼职。教师身份与官员身份高度重合,教育与政治之间缺乏适当的张力。韩愈曾经指出:“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义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资叙,不考艺能。”除了前述儒家对于“道”的解释丧失了神圣性和标准性之外,学官本人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教育能力的不足,亦削弱了“师道”的严肃性。“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虽有而未之知,不智。”但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下,不乏不仁不智之辈充当学官,亦少有人将在官学中从教任职作为长期的事业追求。行政与教育的高度嵌套,不仅使得教育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也进一步弱化了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
此外,与教师的官员身份相反的是,儒家官学的学生却并不主要是通过受教育而获得官职。唐代的官学固然是以培养预备官员为主要任务,但官学教育的学生多为公卿子弟,是其家庭出身决定了仕途的起点,而非接受教育的必然结果。同时,唐朝的科举制亦割裂了儒学教育与进士为官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唐时期“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甚至“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学风之差既体现在不尊重教师上,也体现在不尊重教育上。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主管教育的学官品级不高,至多从三品(国子祭酒),学官难以获得公卿子孙们的尊重”,但事实上在中唐时期从三品仍然是较高的品阶。更直接的原因应当是学生从其功利的求学目的出发,在一定意义上产生了类似“教育无用”的观念。事实上,考诸中国教育史,儒学教育甚或学校教育出现危机之时,往往弥漫着“教育无用论”的气息。教师尊严的获得不能忽视学生的认同,但学生的认同又往往游离于教育之外。在这种交错的“官本位”思想下,教师既难以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亦难以获得学生的认同,所谓“师道”也就无从谈起。
二、韩愈“为师之道”的主要内容
韩愈所谓的“道”是相对于佛老而言的儒家之道,韩愈所谓的“师”则是相对于经师而言的传道之师。由是,“道”与“师”在此形成同构关系:一方面,“道需要通过儒师的论说传述,才能得以绵延不绝”,教师成为道统传承的保证;另一方面,儒师需要维护“道”的神圣性,以保证社会身份的尊崇,儒学成为教师地位的背书。显然,“句读之师”不能承担起这样一种“师”“道”同构的重任,因此韩愈在重塑“师道”传统的过程中,赋予了教师更为深刻的“为师之道”。
(一)师以传道的使命担当
《师说》开篇即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要自觉地把“传道”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和道德责任,将儒家的圣王之道传承下去。魏晋时期儒学衰微,除了有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外,也因儒家学者在“家法师守”的过程中忽视对儒家文化本身的传承与创新。这样的人在韩愈看来,不过是“经师”,远远称不上“人师”。中国教育传统强调的“以文化人”,关键在于化,而不在于文。具体而言,“文”就是“古文,六艺经传”这些承载“道”的“业”,而非“道”本身。换言之,文是教育的载体,而不是教育的全部。作为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授业”,将传授给学生一些实用的文化知识视为教育任务的达成,更重要的是向学生传递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和道德精神。韩愈对“师道”的重塑,乃是树立起教师作为社会道德担纲者和传承者的身份地位,“师道尊严”无疑建立在对教师使命的高度张扬之上。
一方面,韩愈的师道思想为教师树立了道德身份,教师要以道自任。韩愈在儒家哲学上创立了道统说,并将自己纳入传承谱系,接续的“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为教师的道德身份建构了合法性。这一师以载道、师以传道的谱系构建为后世所继承,成为我国师道传统的重要基础。古文、经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学生固然可以通过自学来获得其中的知识成分,但是对“道”的理解和掌握,却必须依靠“闻道在先”的教师的点拨。换而言之,教师并不是简单地进行知识传授,而是“先觉觉后觉”,通过自身对“道”的理解优势,在教育过程中实现人的塑造和“道”的传承。
另一方面,韩愈的师道思想也要求教师要“敢于为师”,使“传道”成为道德自觉和行动自觉。韩愈本人即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敢为人师事实上也意味着教师要做到主动施教,把提高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作为自身的教育动机和教育责任。“要敢于面对种种文化颓废和冲击,抛开个人的利害得失,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继承与发扬儒家学说和伦理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传道’的历史使命。”韩愈的士大夫身份促使他试图去重建儒家的社会伦理体系,以维护岌岌可危的李唐王朝,多次的贬谪并没有动摇他对孔孟之道的坚定信念,而仍然坚持基于教师身份的“舍则传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
(二)文以贯道的探究精神
“道”的神圣性赋予教师群体以道德身份,但教师的道德权威不仅需要“道”的外在支持,亦需要自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探究、阐发,从而证明自己作为“人师”的道德身份,而非传授“记问之学”的“句读之师”。韩愈提出:“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教师可以通过文章中的言与道来判断学生的学识水平,学生亦可以通过对文章的研读来判断教师的学识水平。在“师道”衰微的中唐时期,更需要教师发出“不平则鸣”的道德呼声,为学生树立道德榜样,而这又反过来要求教师更深入地理解儒家经典中的“道”。
首先,为师之人应当探究“道”的精神内涵。韩愈所创的“道统说”打破了师法、家法的儒家教师观,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与原本的教诲合而为一,就可以是一位好老师”。这固然为从事教学的儒家学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但从另一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能够向学生说明经典文本的含义之外,还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向学生阐明经典文本所蕴含的“道”的人生指导意义。历史是流动不居的,教师如果没有能够基于儒家之道,赋予其现实的社会价值,那么教师及其所谓的“道”就可能被学生乃至社会所抛弃。换而言之,教师对于经典必须有所探究,只有对儒家精神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创新,才能使学生信服,才称得上“人师”。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即在于此,探究精神是教师教育活动的学识保障,“凡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人都是值得学习的教师,反之就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教师”。
其次,为师之人应当参与“道”的社会表达。韩愈积极参与道德辩论,以儒家之道抨击佛老之道,认为“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若不胜,则无所为道。”师者之传道,应当有“道”可传,如果只是抱残守缺、自视清高,没有积极表达自己对儒家经典的道德理解、对社会生活的道德理解,那么学生难免会被其他学说的社会表达所吸引,教师就会陷入无道可传、无生可教的困境。文章就是教师特有的道德表达形式,韩愈的“文以贯道”重道而不轻文,既强调通过文章来阐释对社会现状的道德理解,以此吸引学生对教师和儒学的认同,又寄望通过文章来扩大儒家学说的传播范围,突破汉魏家法的神秘性,使更多的人了解儒家的道德主张。无怪乎苏轼盛赞韩愈“道济天下之溺”!然则,朱熹反对“文以贯道”,提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的“文以载道”观。“由于理学家近似宗教的狂热与固执,遂陷入了哲学与文学的迷误。中国正统文学从此屈服于外在的规律而走上异化的道路。”教师失去了“文以明道”的利器,就可能异化为“空谈心性”“悲守穷庐”的腐儒,而腐儒又怎么可能培养出君子呢?
(三)闻道在先的师生关系
教师身份是相对于学生而言的,师道、师德亦是建立在教学关系、师生关系上而提出的不同于一般社会伦理关系的道德要求。学者多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来探讨韩愈的师生观,认为其再次确认了教学相长的师生传统,“师生之间存在着‘道’的双向交流”。这固然为构建相互尊重的、平等的师生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但韩愈的主张更在于破除不良的择师倾向,讽刺“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和“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耻师”风气。即便社会没有形成尊师重教之风,作为教师而言,仍应当从“闻道在先”的立场出发,热爱学生、奖掖后进,坚持自我的道德追求。
其一,教师要热爱学生,帮助学生安心学习。天宝元年设立的崇玄署规定以学生代替斋郎承担日常祠享的任务。韩愈针对这一现象就提出,让太学生兼职斋郎会“隳坏其本业。则是学生之教加少,学生之道益贬”,认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非无所事,“学生之所事者,德与艺也”。换言之,教师应该热爱学生、维护学生,让学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上。而学生只有认真完成学业,实现德与艺的精进,才可能“有以赞于教化”,在更大范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浪费在学校的时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学生把精力集中到学上,教师才有可能把精力集中到教上,反之亦然。其在潮州任上,有感于“里闾后生无所从学”,提出重修州学,并“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充分表现出韩愈对学生的热爱和对学生学习的关心。师生的平等主要指的是人格上的平等,而非社会关系上的完全平等,教师不仅需要从其专业知识和能力角度解答学生的学习困惑,也需要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其他困难给予关照,由此才能将教师的职业性上升为职业道德,凸显“为师之道”。
其二,教师要奖掖后进,发挥主导作用。闻道在先,意味着教师对于“道”的文本意义和社会价值有深刻的理解,以先觉觉后觉,通过引导学生学习来塑造学业志向,避免“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得不到圆满解答”。韩愈出于其教师的本能,告诫张童子:“宜暂息乎其已学者,而勤乎其未学者可也。”面对学生“举明经者累年,不获其选,是弗利于是科也”的学习疑惑,韩愈提出“爵禄之来也,不可辞矣,科宁有利不利耶?”,鼓励其继续学习;又劝勉学生不要因为一时之不顺,而对学业有所动摇,“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当学生有所成就之时,韩愈则希望其能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价值,并以师生之情为出发点,“博士,师属也。于其登第而归,将荣于其乡也,能无说乎!”。可以说,韩愈所构建的师生关系,绝非是知识的传递关系、儒家之道的传承关系,在其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也积极发挥作为教师的主导作用,指导、鼓励学生的学习活动,充满了奖掖后进的深厚情谊。韩愈以“闻道在先”的教师身份,敢于、乐于“成就后进士”,才能在“耻师”的社会风气中形成“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的现象。
三、韩愈“为师之道”的当代启思
韩愈的人格魅力和文化主张通过其坚守师道的教学行为而得到进一步彰显和传承,“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
师德是师道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师地位的重要内在保障之一。不少学者从外部机制建设和内在素养提升两个方面对师德建设提出构想,提出“凝聚信仰,促进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导向化;提升师能,促进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专业化;涵养师爱,促进高校师生关系的健康化;关注社会,促进高校教师社会服务的常态化”。个体道德发展是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教师基于对师德规范认同的自我道德建设,才是确保教师能够坚守“为师之道”的重要因素。
(一)基于师道尊严的教育使命
立德与树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用的人,更在于将学生培养成为合乎道德要求的人,这是教师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使命。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历史传统,“教师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道德传承者的角色”。而之所以要求学生、社会形成广泛的尊师、敬师风气,而不是“耻于言师”,关键在于“道”,教师是作为“道”的具体呈现而获得尊重的。换而言之,教师不仅对学生具有道德责任,对于社会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道德责任。道之不存,师将焉附。教师作为社会的一类特定群体,其身份就具有坚守道德、传承道德的责任与使命,并非某个教师有、某个教师无。教师在道德上的自尊是教师群体的道德感召力和道德影响力的根源。如果教师不能自觉维护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滑坡的社会道德也就不会为其身份与地位提供保障。在此意义上,仅仅不触碰底线显然不够,教师更应当把自己置于社会道德规范建设者和维护者的位置来考量自身的师德建设。而唯有教师认识、认同这一道德责任,才可能把社会的基本规范以及教师身份的更高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素养,将“师道”自我转化为“师德”;亦唯有如此,在外部道德建设机制或道德评价机制弱化之后,或者在纷纷扰扰的社会多元价值之中,教师才能够坚持师德涵养,做到“强立而不反”。
(二)基于教书育人的道德涵养
教师所要传达的道德规范,需要得到学生的认同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传承。现代知识体系下的教师显然拥有更为专业的身份,并成为“专家系统”的一员,这就要求其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化知识和道德知识的简单传递,而是从更为专业的角度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实现“以德育德”。所谓教书育人,上好课、教好书,“在育人实践中锤炼高尚道德情操”,亦是教师进行自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教师要注重提升专业的学科教学能力,以此来强化学生对自己的信任,使学生服膺其教。学生往往会因为教师的专业学识进一步认同教师的人格素养和道德感召,使道德教育不至于沦为被拒斥的道德说教。另一方面,教师也要注重在学科教学过程中实现社会道德的传承,“术业有专攻”赋予不同学科的教师具备从不同角度进行道德教育的可能,而不是将道德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剥离。教师除了教授专业知识外,也应“理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系”,从学科专业的角度丰富学生对于社会道德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实现协同育人。育人之达成,不仅仅是学识传授之达成,才可以视作“为师之道”的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立德树人的过程同时也是师德养成的过程。
(三)基于师生之情的伦理关系
教师身份是相对学生身份而言的,教师道德的主要对象也是学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师的道德失范行为往往也是针对学生而发生的。中华师道中有着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尊重和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而其背后更是蕴含着“爱生如子”和“事师如父”的人伦之情。但受困于当代市场经济“契约式”的人际思维,师生关系异化成了知识的交易关系,教师的教学行为被抽象成了知识的服务过程。师生在课堂上就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和互通,更遑论课堂之外的交往了。应当看到,现代师生关系中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降低自身在师生关系中的道德追求。而构建有道德的师生人伦关系,也不能没有师生之情的存在,需要教师热爱学生、鼓励学生,参与学生的人生成长。“在教师的个人素养中,对师生关系的构建和走向影响最大的当属教师的价值信仰。”教师需要坚定自我的道德理想和道德信念,将培育时代新人作为志业,而不仅是职业;将学生成就作为自身荣誉的来源。良好的师生关系应当是基于师生之情的道德关系,道德意义上的伦理关系要求教师超越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关系,能够对学生有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关爱。事实上,有无良好的师生关系,亦足以作为教师道德建设成果的自我确证。
教师身份自带的道德属性要求教师应当有不同一般的道德追求和道德素养,不能把道德底线作为自己的道德要求。“师道尊严”固然包括了教师层面的为师之道、学生层面的从师之道和社会层面的尊师之道,“在全社会重振师道尊严”固然需要各个层面的参与和各种外部条件的完善,但作为引领时代进步的教师,不能待时而后动,应当以“为师之道”自负,把师德修养作为自觉的行为。韩愈“入迁祭酒”之时,“生徒奔走听闻,皆相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如果教师能够以师道而立、依师道而行,又怎么会没有“师道尊严”呢?